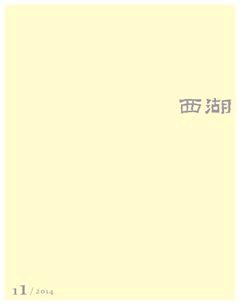南子的诗
南子
何处是故乡
何处是故乡——
当一个人扎下了根
像胡杨树最终弯下干枯的枝条
我的脸浮上了另一棵树的倒影
短或长,都是宿命 都要身临其境
这个身心疲惫的人
忍受着寒风 酷暑 还有越来越多的尘埃
陷入这沙漠与绿洲之中虚掷光阴
体内的血 流向亲人的地平线
祖父的坟地 在等我的歌喉
等着我抓住飘散中的泥土
等着它倒空我 随即又将我填满
等着生命将在删改中延续——
就像锯子将树木剖开
荡漾着木器的倒影:木船、桌子和木桶……
啊 新疆的地理影响了我的一生
不会再有谁 在我身上醒来两次
夜晚多么空旷
夜晚多么空旷
像一封打开很久的信
风收紧了榆树的外衣
也收走了雨水中刚刚绽开的绿意
在这平常的一天这个夜晚
一切都像是刚刚好——
而平常的夜晚往往过于昂贵
使匿身的果实现出原形
但笑声中黯然的悲哀和无用的茫然
不会漏出这个夜晚
不会漏出女主人的叹息,厨房的油烟,邻居们的争吵
废纸上的流水账 以及
受苦人松开的愤怒
不会漏出稿纸静静的水底
那鱼群般推动着的永不止息的波浪
——因为 在所有平常的夜晚
我早已将一座石头山安置在了沉沉笔尖
发育史
我还没有发育
人们就从我的身体里赶出一只猛兽
它没有形状 具有黑夜的属性
靠体内的湖泊止饥渴
但还没长出四蹄
没有人告诉我 它正在,或将要成为什么
总有一天 我会看清它的样子
如认识自己
当它耸着肩 就像一枚被风裹挟的白云的核
有着秘密成熟的危险
在我可能的身体之上
正朝着两个方向流亡
让裸露的石头有了心跳
热血和回音一起成倍增长
孤独影响了大平原
让慢慢醒来的身体恢复着记忆
分解着,敛聚着内在的激情
——让我对这个平乏,残缺的世界
仍有片刻的动容
那被承诺的——
崭新的、尚未动用的辰光
我还没有看见——
当河流的承诺变成了无量的沙粒
鸟儿衔着树枝或石子
要将它填满
当汗血马在骑手的承诺中耸起了脊梁
上了锁的马厩闪亮
它在颤抖中咽下了远处的一声闷雷
当旧时光承诺咬住一些老人
加深了自身的幽黯
却没有线索告诉他们何时做一个被哀悼的人
当天鹅许诺给整个湖水一颗柔软的心
游艇从它们的身旁中驶过
炫耀着暴力
当我见证过的爱情承诺给我多余的胸襟
但最终 我写下的诗歌
不得不再另起一行
当一位儿童的承诺
是成年游方的僧侣最终归入了夕照
——而落日就是镜子 闪电在承诺中劈开了它
明亮的碎渣像整个世界在倾泄
有时落在于刀尖上
有时落在石头上
而我是否要对崭新的、尚未动用的辰光承诺更多?
那些尚未完成的,全部的生活
十四行
晚睡的人
如我 常常对着窗外马路上的行人微笑
为这平安度过的一天
和即将到来的明天
风吹送着每一个路人到睡眠的角落
他们疲倦而困顿的脸
沿着蒙尘的街树缓缓展开
一如展开这弱小的 挣扎的
被无尽命运拍打的细枝
路灯 有一瞬间的闪亮
只有我看见了
他们对着不说话的星空 草丛 沟渠
对着一整个黑夜的踌躇
悄悄伸出呼救的根须
人世间
在人世间
我似乎走得太快——
没来得及成为寂静的一部分
没有来得及成为相爱的布谷鸟
咏唱无尽哀歌的一部分
甚至 也没有让我内心的善
像此刻的雨水一样
顺着人类斜斜撤离的目光
平安 优美地落下
我走得是这样的快
越来越少的话语
比厌世者
更早说出内在的死亡
我与你们
这是又一次
回忆起自己曾有过汁气蓬勃的岁月
没有经常擦拭的时间轻盈
纯洁如一个白昼
独特而与你们相似
如今 渐渐成形的中年的我
爱着生活的困顿
那被情欲、饕餮和无止尽的欲望改变了的内心
独特而与你们相似
如你所见
终于有一天
她的力气在消散
像冬日的炉火聚积着冷
她面容模糊 不爱行走
经常看不见自己的影子 不打听
远处发生的事
全然忘记了自己年轻时
曾参与过多少次自我毁灭的教育
现在 寂寞是她身体上唯一的饰品
冷风吹着的不再是劲草
仿佛命运本身
是的,如你所见——
她终于成为了
一个独自的众人 一个
平凡而无害的人
站在那里 真理一样虚无
现在 她朝向我
像是朝向一个巨大的问号
像是要叫出我的名字
当世界还年轻的时候
当世界还年轻的时候
我爱着和她一样的动荡
爱着她的宿命,偏执和被放逐 也爱着
中了暑的情欲 一些刺痛
一个无关心灵的手艺
以及一个短暂的信仰
它们 一起构成了我的一生
当我迟暮
拧干身体多余的盐分
空留胃里一枚饥饿的针
它曾经尖锐 锋利 对抗过生活的毒
现在 它越来越灰
把被渲染的和夸大的死给了我
一种叫悲伤的力量
在黄昏柳丝间的一丝震颤中
拥有了片刻的动容
像命运的另一面投影
一个无法说出的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