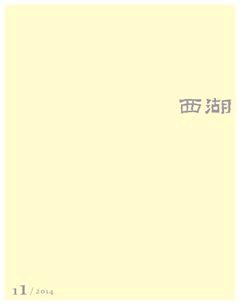接待奈保尔的那两天
麦家

我最早看奈保尔的一本书是《米格尔街》,那时的译本叫《米格尔大街》。好像是浙江文艺社出版的,白底子封面,黑体字书名,没有腰封,没有宣言,简单至极的设计,默默无闻的登场,暗示这不是一本出版社力推的书。我看它是因为有朋友推荐,说这是一部“轻松又聪明”的小说,写贫穷、落后的一条街、一群人,有第三世界的“体温”。吸引我的是“聪明”之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小说写得笨,想变聪明。有一天,我把这本书和几十瓶蓝墨水一起买了回家。
那是2000年初夏,我刚迁新居,是一套当时并不多见的跃层,将近200平方。我从一年前开始装修,亲自设计、招工、买料、监工,装装停停,修修改改,耗时一年多。楼上一层,从楼梯开始,全是我个人的地盘,楼道两边挂着藏式挂毯和挂盆,楼梯口吊着昏暗的马灯,阳台上种着一棵从大凉山移来的三角梅,书房里是我积攒了十多年的书:有些书跟我从福州出发,去了南京、北京、西藏羊卓雍湖,现在终于安耽下来,无需舟车劳顿。我不相信自己还会再迁徙,还会买更宽敞的房子,因此我才会如此不计精力财力,大搞建设,不厌其烦。
其实烦恼每天都缠我,只是想到,既然要一辈子交给它,我理应为它吃苦受累。书房是我的天堂,连地板都是亲自去乡下买老房子拆下来的木料,请木匠现场做的。自己上漆,清漆里加了蓝墨水,一遍一遍刷,刷成钢青蓝。比蔚蓝的大海还要蓝。深蓝。我就是一遍一遍刷着地板,累了,去阳台上抽烟、喝茶、看书。这个时间长达半个多月,我看的书至少有十几本,但现在想得起来的只有这一本:《米格尔大街》。这本书果然是聪明,文笔清丽,幽默轻松,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读,像画册。我头一遍是通读,后来是翻来读,反复读。像刷油漆一样,刷多了,就长牢了,化不掉。记得一天,我就用刷地板剩的蓝墨水写了一则读书笔记,其中有这样一句:他们是如此卑微,却又都如此快乐,像一群蜜蜂。当时我不知道,一年后这位作家将得诺贝尔文学奖,更不知道十四年后我们会在杭州见面。
那时我在成都,现在我居杭州。就是说,当时我也不知道,那套被我以为要厮守一辈子的房子,其实只陪了我七年,离一辈子太远!现在,那一屋子地板依然蓝得发青发亮,我却只能在梦里见到它。我确实时常梦见它,因为那蓝色里漆进了我太多汗水,也漆入了我不少美好记忆,我舍不得。
诺贝尔是地球上少有的几个人造太阳之一,凡是有幸登上这个奖台的人,必将不幸地在灿烂中裸露,每一根汗毛都会被聚光灯丈量,在口水里肥沃。关于奈保尔的口水仗,打得尤为激烈而持久,自私、贪财、刁蛮、嫖妓、对妻子无情、对情妇施虐、对朋友不义、对读者轻蔑,等等,一个在生活中几乎是令人憎恨的恶棍形象,在诺奖光辉照耀下脱颖而出,活灵活现。好在出版商和读者不是道德家,书被一本本翻译出版,一本本在市场上走俏。我就是躺在蓝色的地板上一本本读:《河湾》,《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印度三部曲”等,几年间读了七本书。不能说每一本都喜欢,但毫无疑问,我喜欢这个作家,虽然他和我的写作风格截然不一。
我读书有记笔记的习惯,有些直接记在书上。在他来杭州之前,我又翻看过去读过的一些书,看到不少记录。比如在《河湾》的第187页,页眉记着这样一句话:报上说他有“毒舌”之称,但他不是毒蛇,他“咬人”、放射毒液,是为治人于病,救人于难。在《幽暗的国度》的最后一页,我写道:写这本书时奈保尔31岁,之前已经出版六本书。我马上四十岁了,却一本书都没写出来,愧愧愧!卡夫卡说,人类因为懒惰被逐出天堂,奈保尔不在其列。这本书里还夹着一小纸条,上面有两句没头没脑的话,一句是:虔诚也是一种天赋,他触摸的世界带给我的疼痛,与我脚下的土地是如此之近;另一句是:绝望不是死亡,但比死亡更死亡。我想这肯定是跟这本书有关。我本已忘记了这本书的内容,但这两句话一下让我接近了它,像开了门。阅读的记忆会经常被淹没,又会经常被唤醒。所以,一个饱读诗书的人,正如饱经风霜的人,生活中时有灵性和感悟迸发,其实不过是沉睡的记忆苏醒而已。在《印度:受伤的文明》的第71页,我写道:他没有忘记祖先,但已经被英国宠坏了,躺在一个英国爵士的荣誉里,没有拐杖,起不来。有些记录很长,有些记录又过于琐碎,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总的说,奈保尔是一个生活体验很丰富、视野很广阔、写作很努力的作家。他已经出版二十七本书,至少有一半成为经典,被世界各国的人捧读。读他的作品,你也许不会感到被温暖、激励,很多方面他和库切一样,作品里有一股狠劲,一种深深的冷,让人伤感,甚至绝望。他以恨来传达爱,以绝望来把握希望。世界如斯,他心底如斯,他笔下如斯:种族歧视,文明冲突,爱恨交加,真假难辨;希望和绝望,如影相随,在默默地勾结、斗争。作为一个作家,奈保尔是忠诚的,一直在勤奋地思考、写作,除了诺奖制造的短暂骚动,一切按部就班,波澜不惊,往事和随想,在安静地交配、产卵。他写作的坐标不是情节、故事,而是过去、内心、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对文学虚构,他有独到的理解就是:虚构是文学的常规手段,但目的不是为了制造快乐,而是为了让“真实”从庸碌生活中脱颖而出。他甚至说过:如果活着是为了快乐,对一个男人来说,只需要一个妓女;文学不是妓女,文学是圣人,我活着就是为它服务的。
那一天,当我抬着轮椅,气喘吁吁、一步一停地走在灵隐寺的台阶上时,我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话:现在他已经成圣人了,需要我们为他服务。确实,疾病把他按倒在轮椅上,削掉了他过往的锋芒和乖张,如今他时常举着小鹿和山羊的目光,三缄其口,沉默安详,仿佛一尊佛。
高铁缩短了杭州和上海的距离,但改变不了两个城市的气候,夏天溽湿、燠热,即使立了秋,还有“十八秋老虎”,虎视眈眈蹲着。奈保尔此次来中国,主要是参加上海书展,大部分时间在上海,杭州只待了两天两夜,不到四十八小时。由于临时横事,我未能全程陪他。在相处不多的时间里,我们聊及不少话题:文学、美食、西湖、西溪湿地、气候、媒体等。但记录下来,他说的话记不满一页A4纸。他已经作别了过去的他,不再有宏声高音,不再有如簧巧舌,不再有谈锋,不再有怨毒,甚至不再有表情、手势。毕竟已经八十二岁,加之病魔缠身,更加之长途旅行和频繁出席活动,疲倦像滞热的湿气一样笼罩着他,包抄着他,粘在他身上,让他显得十足像一个高龄老人、虚弱病人,即使思绪万千,也只能长话短说,点到为止。
我相信,思维没有背叛他:自始至终,我没见他说过一句胡话,或乱语。他只是丢失了体力,以致无力谈笑,正如一个人无法在重负下跟人开怀畅叙一样。他的情况就是这样,体力都消耗在支撑沉重的身体上。相对于有限的体力,他的体重显得无限的重了,即便坐在轮椅上,依然累不可支。临别那天晚上,我去宾馆和他道别,当时他已经躺在床上,我第一次看到他把手自如地举起来,向我挥手示意,第一次看到他嘴角浮出粲然笑容,第一次听到他发出常态的声音,连贯地说出一句长长的话,对我致谢,向我母亲问好。我知道,这是因为席梦思卸下了他自身的重负。
老人家确实老了,病了,乃至已经离不开床榻了。
可他显然不服老,不愿向病魔低头、饱受病榻奚落。他要挣脱病榻,走出门,去遥远的地方:中国上海;去更远的地方:杭州。
奈保尔是8月13日下午的晚间时候到杭州的。对生活在皇历时间里的我母亲来说,这一天是农历七月十八。我母亲和奈保尔是同龄人,平时身体很健康,每天早睡早起,洗菜扫地,喂鸡养狗,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天她照例早早起了床,但接迎她的不是雷同的一天,而是和死神交战的一天:一只野猫把她吓死了!
我们家没有养猫,以前也不见有猫来串过门,因为家里有狗,猫怕的。而且,我一直以为,猫也是怕生人的,见了生人会立即蹿走,不可能任人踩踏。但这一天就怪了,猫在我家睡大觉,狗不管不顾;母亲从卧室出来,准备去开客厅灯,一脚踩在这只死猫身上——鬼知道它中了什么邪,这么笨,会躲不掉一个八旬老人的脚板!猫惊叫着,像一道黑色闪电一样夺路而逃,跳窗而去,同时把我母亲的灵魂和心跳也带走了。二姐说,她发现母亲时,母亲像一截木头一样笔直地横在地上,摸不到心跳,任凭捶胸敲背、大呼大叫,都不起用场。好在去医院的路上,母亲心跳又凭空而来。二姐说,是一辆大卡车的喇叭声把母亲叫醒的。谢谢你司机兄弟!二姐说,母亲心跳至少停止跳动了二十分钟。医生说,我母亲的命真大。确实,二十分钟,在阳间,还不够赶到医院,但在阴间,足以踏上不归路。
先送县医院,下午三点转到省医院……这一切,我都不知道。没人告诉我,大家都瞒着我:家人,朋友,包括有关领导,都认为我在接待一位国际贵宾,是件大事情,不应该让我分身担心。
殊不知,我正愁死人呢。这一天,如果我去卜卦,一定是凶象。虽然母亲这边的事被人蛮横地按了下去,但奈保尔这边又生生地翘将起来:原定早上九点从上海出发,赶到杭州吃午饭,却一拖再拖,迟迟不上路。问缘故,说有意外。意外?什么意外?!再三问,终于吐露实情:早晨洗澡,不慎滑倒,左肩膀着地,现在医院拍片检查。事后我算了一下时间,两位同龄老人几乎是在同一时段倒地,被医院召了去,怪不怪你说?
这一天,有点奇。
老年人进医院,似小伙子进妓院,天晓得什么时辰能出来。我傻了,因为第二天下午两点,我同奈保尔有个公开对话活动,在杭州市图书馆500座的报告厅,活动预告已提前两天登报,500张门票在第一时间被抢购一空。现在对话的一方——尊贵的一方——在医院拍片检查,这可怎么办?
没办法,只有烧香。
我们真烧了香:我和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俊兄;他是奈保尔全部著作在中国的唯一出版人,也是我和奈保尔此次见面的牵头人。虽然我没有寻过问,我直觉陈兄心中一定有佛。事实上,奈保尔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也许是烧香灵验了。
当天下午三点半钟,奈保尔一行从上海启程,将近四个小时后,出现在我们面前。尽管我对他身体状况有所预知,但也许是临时伤痛之故,我看到的样子比我料想的要糟得多;他瘫在车里,根本不能行动,下车时动用了宾馆四位保安,他们小心翼翼,左右为难,像在搬弄一件易碎品。我上前跟他握手,手心里全是冷汗,凉飕飕的,且无一丝气力,感觉像握了一块肉。我说:“先生,我十二年前(其实是十四年,因紧张出现口误)就认识你,当然不是真人,是你的书。”他端着一脸憔悴,问我是什么书,声音幽到经不起风碰。我说是《米格尔街》。他似笑非笑,目光迷离,半天张不开口。他夫人见了连忙接过话头,对我说:“那是他早期的一本书,奈保尔很喜欢这本书。”我说:“我也很喜欢,一度把它当作我学习写作的教材,看了很多遍。”他终于说了句什么(翻译没有传译),一边向我伸出手,好像在对我示意,其实是在兀自颤抖:越来越颤抖。我连忙又去握住它,只是为了让它停止颤抖。但我感到自己的心也在颤抖。
是的,接待这样一位病弱交加的高龄贵宾是件冒险的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啊!
相比,六十四岁的奈保尔夫人高大,健硕,健谈,怎么看都不像一个花甲老人。她是印巴人,大眼睛,浓眉毛,长睫毛;高耸的鼻梁、宽厚的鼻翼,像喜马拉雅山一样凸立;鼻翼左侧缀着一粒碎钻,在灯光下晶晶亮。她对人热情,豪放,说话声音高亢,粗犷,像在草原上长大的。另有一位男助理,三十来岁,曾经是银行职员,因为崇敬先生,甘愿全职为他服务。他比我高整整一个头,身板挺拔,身手敏捷,剃个小平头,像个水手。没有他俩,奈保尔也许只能困在病榻上,冲着英国的天花板,对遥远的中国空思妄想。现在可以说,奈保尔的中国行是圆满的,这圆满是靠这两人的四只手合拢、围成的。
好了,不管怎么说,奈保尔终于来了,我们都如释重负。
就在这种情况下,人来了,我吊的心着地了,我妻子终于熬不住(已经熬了一整天),向我道明母亲病重的实情。她心里也担心有意外。不过她是矛盾的,一边是担心,另一边也是担心:对方远道而来,且为国际贵宾,我当主人的岂能临阵逃脱,甩手不管?我走了,整个场面抽了主心骨,万一怠慢了贵宾,发脾气,闹情绪,耍大牌,取消明天活动,我又怎么收场?她尽量安慰我,母亲病情稳定,也有人陪护,我可以陪他们吃完饭再去看她。
开始我也这么思想,我不能走,走是失礼的,可能也是失策的。但在登车去餐馆的一刹那,我改变了主意,直奔医院……已经没人为我服务,我只好亲自开车。天已黑透,且下着雨。雨越下越大。关键是我身负多重压力,心乱如麻,好几次我眼前一片黑暗,车子只好当街停在那,只听到雨刮器刷刷的声音,好像车已抛锚。杭城本是小的,但那天晚上我觉得比非洲撒哈拉沙漠还要大,怎么也穿越不了。当我下车时,内裤都湿透,不是雨水,是汗。什么叫心急如焚,什么叫焦虑万分,什么叫“压力山大”,那天晚上我真正领教了。
母亲的状况还算好,但病因尚未查明,她身体里有地雷,不知埋在哪里。奈保尔那边的情况似乎也好,正常地用了餐,回宾馆睡觉了,没有闹情绪。但谁晓得这是不是真相?我知道,即使奈保尔已拂袖离去,他们也会瞒着我,像瞒着我母亲病情一样。想着奈保尔过往的一些做派,他闹情绪完全有可能的。再说,他也有理由闹情绪,我拖着这么病弱的身体和伤痛从老远来践约,你不领情,不感激,不顾大局,不辞而别,不像话……我就这么想着进入梦幻,看见奈保尔已经连夜返回上海。
这天晚上,我只睡了一个小时。睡不着。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盲目的恐惧和内疚中胡思乱想,浮想联翩。一个念头安慰了我,在母亲生命安危面前,我有权放下任何礼数和利害,我有道德豁免权。另一个念头也安慰了我,母亲是给我生命的人,我有义务、有责任让她的生命活得更健康、长久。这两个念头一起告诉我:即使奈保尔已连夜返回上海也不足惜,什么对话,什么贵宾,不过是名利场上的戏,说到底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既然是虚荣心,丢了也罢,甚至我需要学习把它丢掉。
人在特定的时候总会有些特定的想法,正是这些想法让我痛下决心:明日上午我还要留在医院。母亲病情不明,要做各种检查,然后会诊。家里虽然有几位亲人在,但都生活在乡下,不会说普通话,进了城,像出了国,做什么都缩手缩脚,没有自信,让我也没信心把母亲交给他们。我要留在医院,直到查明母亲病情为止。如果病情严重,我也作好了单方面取消对话的准备。
按计划,第二天上午我要陪奈保尔一行游览西溪,中午在我家吃饭。我黎明前才睡着一会,醒来发现雨止了,天放晴。一夜雨水,尘埃落定,空气清新得想张口喝,我昨日的霉运似乎也被雨水洗涤干净。吃早饭时,妻子发来短信,说奈保尔昨夜休息得很好,现在精神不错,他夫人很关心我母亲病情,祝老人家早日康复。正准备回信,又跳出一句话:奈夫人说今天上午游西溪有我和陈总陪即可,你安心陪母,如病情稳,回来吃午饭。我的心情顿时像天气一样晴朗,几个小时后,更是晴空万里。几项重要检查出来,医生跟我拍了胸脯,母亲并无器质性病原,昨日的惊险是拉警报,挺过来就好了,目前决无生死之虑,让我放心回家接客。
这时已十一点多,奈保尔他们已经游完西溪,准备去我家午餐。我立刻上路,以最快的速度和良好的心情赶回去。他们先我十分钟到家,我进屋时一群人正在客厅里叽叽喳喳,奈保尔背对大门,坐在轮椅上,坐姿端正:不像昨天,四个保安也驾不住,像一潭泥。我走到他面前,果然见他有神气,思路清,不及我开口,领先打问我母亲病情。我说很好,并向他道歉。他说:“这不用道歉,要是我也会这样,人只有一个母亲。”我很感动,上去握他手,手暖暖的,软软的,像我母亲的手。我说:“先生,我母亲与你同龄,但没你身体好,昨天差点去见莎士比亚了。”他摇头说:“我也不好,希望我们都好,我和你母亲。”我说:“这也是我的希望。”他说:“谢谢。”
我想起昨夜梦中怒气冲冲返回上海的奈保尔,心想,这又是虚惊一场,跟母亲对我的惊吓一样。确实,奈保尔一点也没有责怪我失礼,他非常体谅我,真心宽慰我,像个和蔼可亲的慈父。
午宴不丰盛,但颇具特色。奈保尔是美食家,对吃很讲究,不吃肉;坐上轮椅后讲究更多,因为没有运动量,行动不便,有些食物不宜吃。为此,陈明俊专从海南请来一厨师(安妮宝贝的新作《得未曾有》的第一篇《搭花酝春》写的就是他)为他掌勺;做了六道菜,没有一丝肉,却是道道有肉香鱼鲜,不愧为名厨。他还带来自酿的梨花酒,倒在杯中,米酒的色泽,梨花的异香,美酒的口感。听说奈保尔爱喝酒,我倒上一杯请他品尝。他端起酒杯看看又放下,说:“好酒,但我不能喝,因为下午要同你对话。”这么节制,怎么有人说他是酒色之徒?
餐桌上有位苏州客人,一女孩,叫潇潇,是我好友王尧的女儿。她在收集名人手迹,知道奈保尔要来我家,提前一天到我家等着。我们以为的“小事一桩”,却被奈保尔助理明确拒绝,并不婉言。据说在欧洲,奈保尔一本签名书可以卖几千美金,要保这个身价,只有一个策略:尽量少给人签书。我为潇潇白跑一趟遗憾,也为自己不能向老友交差难堪。明俊兄知情后,亲自上阵同奈保尔说;先生听了二话不说,向助理讨来钢笔,爽快地在潇潇的书上签上大名,让我又添惊喜。
接下来的七八个小时里,奈保尔以各种方式不断地给我叠加慈祥、温和、达理、体贴人这种印象,仿佛是有意要揭穿流言蜚语。在下午的对话会上,500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奈保尔有问必答,包括一些刁钻的提问。有读者问:“你曾说过女性作家往往不如男作家,你不怕得罪女性吗?”奈保尔说:“谢谢你给我机会申明,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只是说不喜欢写《傲慢与偏见》的那位女作家。”我想,他需要更正、澄清的谣传一定更多,但他从不理睬。有些名人善于在媒体面前包装自己,他不。“他没有时间做这些事。”他夫人在私下对我说,“他认为一个作家最好的包装是努力写,不停地写,争取不断超越自己。”
我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
可惜,他本人对我说的很少,他太累了。
对话会结束,我们直接去了灵隐寺,这是奈保尔夫妇点名要去的。很遗憾,奈保尔最后未能亲自去大雄宝殿给菩萨烧上一炷香。灵隐寺里四处是门槛、台阶,我们抬着轮椅过了一坎又一坎,前面依然还有一坎又一坎。终于,他摇头了,要放弃。我们问他是不是累了,他说:“我不累,你们累了。我不能为了对菩萨表示虔诚,把你们累垮了。”他请夫人代他去烧香。
我也烧了一炷,祈了一个愿,拜菩萨保佑我母亲和这位英国老人健康长寿。通过短暂的接触和交流,我出乎意料地爱上了这个被众声喧哗、蜚短流长的老头子;我对自己说:不管如何,我看到的是一个慈蔼可敬的老人,一点不像传说的那么怨毒、自私、古怪。也许是岁月改变了他,但终归是他改变了自己,何况他的作品曾经照亮(改变)了无数人的心灵,而且仍将照亮(改变)更多的人。
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我来到他宾馆床前话别,于是看到、听到了如前所述的几个“第一”。其实,他次日还要在杭州待大半天,只是我要走,去上海参加书展,中午有活动,必须起早出门。参加完书展,第二天要北上京城,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汉学家大会,然后又要南下广州,参加南方国际文学周。这些活动早在几个月前安排好,没有不可抗的力量,我没有理由缺席。
不用说,我得还要去跟一个人告别,就是母亲。下午我已跟主治医师电话联系过,道明我将出差一周,行不行?医生让我放心走,便去辞别。到医院已经十点多,母亲本来就睡得早,今天又被一堆仪器轮番折腾,累得不行,睡得酣酣的,呼呼地打着鼾,像个孩子。我先在母亲床前站着,实在太累,站不住,就找来凳子,在床前坐下,双手扒在床上,枕着头,一会就睡过去了。
我也太累了!
我知道,生活不该这样,但生活就是这样。
2014.8.26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