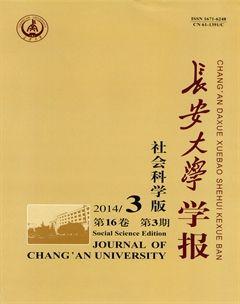象山心学崛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王星 廉永杰
摘要:分析了象山心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自信的性格、严格的家教以及早年的人伦实践构成陆象山为人的主体基础,而孟子思想是其走向社会的精神资源。朱子成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主要取决于《近思录》与《四书集注》的编撰对科举制的适应及其对佛禅之学全面的抗衡与取代上。但朱子突出与强调道问学及其对尊德性传统的疏忽或弱化,则成为以突出德性传统与人伦实践关怀的象山心学的实现条件。
关键词:象山心学;主体基础;思想资源;社会历史条件;科举
中图分类号:B244.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4)03013105
作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象山心学常常被视为程朱理学的对立面。至于这种对立的形成,人们往往求之于象山早年就已经形成的所谓“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之类的高远异见来说明;要么就认为是受了王顺伯、张无垢之类的佞佛之徒的影响。所以,当黄宗羲著《宋元学案》时,就既有所谓“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1]的感慨,同时又不得不以所谓“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2]来漫相牵合。这说明,黄宗羲就已经搞不清朱陆之学的真正关系了,所以不得不以这种两可之说来双向牵合。实际上,象山心学完全是作为程朱理学的继起者与纠偏者出现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程朱理学“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1]的理论规模,也就不会形成陆象山“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式的主体性凝聚;如果没有程朱理学格物致知与读书穷理之类的“道问学”铺陈,也就不会形成陆象山“切己自反,改过迁善”以及“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之道德实践式的指点。而象山心学的这些特点,首先表现在其崛起的社会历史条件中。
一、象山心学的主体基础与
思想资源任何思想的形成都必须具有一定的主体基础,象山心学也不例外。陆象山出生于南宋一个九世同居、阖门百口的大家族,是其父母的第六个儿子。从其祖上来看,其八世祖陆希声在唐代曾官至宰相,五代末其家因避战乱而迁居金溪。但进入宋代后,其祖上似乎并没有出仕的记载,其高祖、曾祖不过是“以学行重于乡里”而已。到了其祖、父两代,就开始“究心典册,见于躬行,酌先儒冠昏丧祭之礼行之家,家道之整,著闻州里”[2]。从这些记载来看,陆象山成长的环境显然属于那种读书明理的乡绅之家,而其特殊性则在于其家族既有很强的乡土根底与较严的家教,又能够以儒家典册见之于躬行,行冠婚丧祭之礼于其家,从而成为州里闻名的大家庭。除此之外,其家族虽然大,且九世同居,但却说不上宽裕,到了象山这一代,还主要是通过药疗与家塾来维持生计的。陆九渊回忆说:“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而食指以千数,仰药疗以生。伯兄總家务,仲兄治药疗,公(三哥九皋)授徒家塾,以束修之馈补其不足。先君晚岁,用是得与族党宾客,优游觞泳,从容琴弈,裕然无穷匮之忧。”[2]可见,象山的家庭虽然说不上宽裕,但却属于乡土根基较重的大家族。不过,从其父亲直到晚年才得以“与族党宾客,优游觞泳,从容琴弈”的情况看,起码说明象山早年的生活还是比较清贫的。
虽然如此,象山祖上以来严整的家教与家风却始终保持着,所以始终维持着一个上百口的大家庭。其长兄陆九思甚至还撰有治家格言一类的《家问》,而其在训诫子弟方面“不以不得科第为病,而深以不识礼仪为忧”[2]。这无疑表现了其家族对礼仪的极度重视,当然,也许是因为其药疗、家塾两种作业本身就足以谋生,所以是否出仕并不影响其一家的生计,而这种“不以不得科第为病”的训条自然会将儒家经典及其礼仪精神推向人伦日用领域,所以又会促成行冠昏丧祭之礼于其家的家风。在早期教育上,象山5岁就开始读书,个性与领悟能力似乎都很强。比如:“丱角时,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亦尝语人曰:‘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初读《论语》,即疑有子之言支离。”[2]这样的记载虽然大多都是出自其弟子的追述,难免存在着文饰与夸大的成分,但也体现了象山弟子对其思想与学术特点的充分自觉。
象山科考出仕较晚,这大概与他的思想常常不合时流有关。他自陈说:“吾自应举,未尝以得失为念。场屋之文,只是直写胸襟。”[2]显然,这是一种极为自信的态度,但这种“直写胸襟”的风格可能也会造成其困于场屋的事实,从而使其能否出仕也就真正成为一个“遇”与“不遇”的问题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当象山24岁以《周礼》中举时,他就在《举送官启》一文的末尾写道:“某少而慕古,长欲穷源,不与世俗背驰而非,必将与圣贤同归而止。忘己意之弗及,引重任以自强,谓先哲同是人,而往训岂欺我?穷则与山林之士,约《六经》之旨,使孔孟之言复闻于学者。达则与庙堂群公,还五服之地,使尧舜之化淳,被于斯民。”[2]这确实是一种远超时俗的高远志向,也洋溢着一种孟子精神。所谓“穷则与山林之士,约《六经》之旨,使孔孟之言复闻于学者”,自然是指对儒家学理的阐发而言;至于所谓“达则与庙堂群公,还五服之地,使尧舜之化淳,被于斯民”,则显然又是指其出仕与为政而言的。而“穷”与“达”的一以贯之,正是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3]精神的活用。而在当时,所谓“穷”与“达”,首先取决于科举考试中的“遇”与“不遇”。但从这一志向可以看出,陆象山已经以孟子的“穷达”之论为自己画出两种不同的人生了。
在当时的社会与文化氛围中,这样一种志向也就决定象山必然会以孟子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资源。所以,当象山多年后开始设帐讲学时,弟子曾问及他的所学授受,他明确地回答说:“因读《孟子》而自得之。”[2]而在《年谱》中,这一说法又被作了这样的表达:“子南尝问:‘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3]从“自得之”到“自得之于心”,也就明确地交待了一个基本事实:象山之学不仅是所谓“自得”之学,而且还是因为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的心学,这显然是将孟子的“自得”精神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与精神传统来运用的。所以,在与友人的论学书札中,《孟子》一书及其思想观点也就成为他的主要援引对象了。比如:“人非木石,安得无心?心于五官最尊大……《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又曰:‘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又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所贵乎学者,为其欲穷此理,尽此心也。”[2]
在一篇书札中能够如数家珍般援引孟子的思想观点,不仅表明象山对《孟子》一书的熟读精思,也是明确地以孟子精神走向宋代理学所面临之社会现实的。而在其讲学中,象山更是明确地以继承孟子精神、阐扬儒家道统意识自居。比如他自我期许说:“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2]很明显,发扬孟子精神、阐扬儒家道统,就已经成为象山进入宋代社会的主体基础及其自我定位了。
二、从佛禅到科举——
理学崛起之双向扬弃宋代之不同于隋唐时代的基本特征,首先就在于它既是一个典型的文治社会,同时又是一个由中小地主所构成的平民社会。作为文治社会,主要是相对于唐末五代以来的武将专政并以重文轻武之基本国策来防范武人专权而言的;而作为平民社会,又主要是因为经过唐末五代农民战争的打击,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代之而起的则是以一家一户、自我耕作为存在方式的中小地主。但唐宋之间的这种重大转向也为儒学的复兴——所谓理学(道学)崛起制造了一种特殊的障碍:在北宋,这种障碍主要表现为佛禅之学的普遍流行;到了南宋,这种障碍又主要表现为由科举制之普及,从而导致士人溺于功利之精神层面的流荡失守。所谓两宋理学,主要在克服、扬弃这双重障碍中艰难前进的。
关于北宋在理学崛起时代所面临的佛禅之学的流行状况,只要看看理学家张载“自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4]的感慨以及其弟子范育在为《正蒙》作序时所提到的“其徒侈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证”的愤恨,再到二程兄弟“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5]之类的回忆,也就完全可以看出当时佛禅之学的流行状况。所以,对于宋代社会的思想状况,余英时先生就在其名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概括说:“皇帝崇信释氏,士大夫好禅,这是宋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6]
但是,由于宋代已经成为一个由中小地主所构成的平民社会,加之赵宋统治者为防范武人专权所采取的“重文轻武”基本国策,因而也就促使宋代的科举制空前普及起来。在当时,科举制的普及既有与赵宋皇室之文治国策相适应且相互促成的因素,同时还有引导士人向儒家人伦纲常回归并向朝廷索要出路的因素。所以对宋代而言,无论科举制的普及与发展在思想上能否真正起到与佛老之学相抗衡的作用,仅从其必须通过科举出仕这种进入社会官场之形式与渠道而言,却无疑起到了与佛老争夺人才的作用。当然这一点也并不那么绝对,因为直到南宋,就是后来成为理学宗主的朱子反而是采用习禅才通过科举考试一关的,比如朱子就曾回忆说:“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7]
作为理学宗主的朱子以禅的意思去“胡说”,居然考中了进士,这对于理学来说无疑是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但又是绝对真实的事实,这一事实起码说明佛禅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还有较为广泛的影响,而习禅也往往被视为自趋高明的表现。在这一背景下,科举制的普及以及其与佛禅对人才的争夺也就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了。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也就完全可以理解朱子何以要花费如此精力来编著综合北宋五子思想的《近思录》一书,又何以要用一生的精力致力于《四书集注》的编撰与诠释。当然,作为理学宗主,朱子的这些努力完全是为了阐扬儒家的道统意识,以弘扬先秦儒学的基本精神,但从《近思录》到《四书集注》的编撰确实为儒家的人伦纲常提供了一种足以与佛老相抗衡的理论依据;而从当时及其以后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则《近思录》与《四书集注》也为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统一士人思想方面提供了法定的教科书。所以,一提到《近思录》与《四书集注》,朱子就有如下感慨:“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7]“《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7]“圣贤说得语言平,如《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皆平易。《近思录》是近来人说话,便较切。”[7]
《近思录》之所以能够获得朱子的如此高评,一方面在于它是北宋五子思想的一种汇编与集成,同时又构成了理解儒家之《四子》、《六经》的阶梯,加之其又具有“近来人说话”的特点,因而也就更加切近当时思想界与士人精神状况的现实。
这样,朱子通过《近思录》的编著,既统一了北宋五子的思想,也为科举考试以及当时的士人提供了一种理想的为人为学之榜样与范本;通过《四书集注》的编撰与诠释,又较为彻底地将士人精神统一到孔孟儒学上来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朱子“《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一说的深意,也才能理解宋元以后朱子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法定教科书、而朱子学则成为两宋理学集大成者这一历史的选择。
但在当时,这一选择只是一个开端却并不是完成;而朱子学的疏漏与薄弱环节,正成为象山心学崛起的历史契机,也是其能够对朱子学发挥救偏补弊作用的重大机缘。
三、“切己自反”——象山心学的
崛起及其特色在说明象山心学对朱子理学的继起关系及其救偏补弊作用之前,让我们先看象山早年的生活经历,并从其早年的生活经历中概括其为学的基本特色。
已如前述,象山出生在一个九世同居、阖家上百口的大家族,而其早年生活是这样度过的:“……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8]而在象山的记忆中,其早年的经历属于一种典型的“事上为学”或实践中为学,而这种“事上为学”也在其以后的为学经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比如他回忆说:“吾家合族而食,每轮差子弟掌库三年。某适当其职,所学大进,这方是‘执事敬。吾家治田,每用长大镢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一尺半许外,方容秧一头。久旱时,田肉深,独得不旱。以他处禾穗数之,每穗谷多不过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以此中禾穗数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每一亩所收,比他处一亩不啻数倍。盖深耕易耨之法如此,凡事独不然乎?时因论及士人专事速化不根之文,故及之。”[2]
从这些早年经历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象山确实是所谓“事上为学”,也可以看出其从生活实践中所激发的深入思考;至于以种田为例来批评当时学界的“速化不根”现象,则可以说是对当时学界风气的一种明确批评。所以,丁为祥曾根据象山借“鬻扇”一讼来指点其弟子杨简当下理解“如何是本心”时概括说:“这种随机指点……也显现了象山为学的一个典型特点,这就是一定要将儒家的学理放到现实生活中来落实、理解;而这一特点又隐含着一条生活实践与道德体验相结合的为学进路。”[9]
那么,象山究竟如何看待当时的学界风气呢?在他看来,由于科举制的普及,当时的风气也就表现为“科举取士人久矣……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向,则有与圣贤背而驰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责哉?”[2]面对这种现实,更值得反思的则是当时的道学领袖们又形成了一种所谓“传注益繁,论说益多,无能发挥,而祗以为蔽”[2]的现象。这样一来,象山也就由对科举制影响下的学界风气之批评进一步指向专门以读书穷理训学者的朱子学了。
在象山看来,要从根本上改变当时学界追名逐利的风气,首先就必须从“义利之辨”入手,從而展开一番“辨志”式的反省。只有在这一语境下,我们才可以理解象山何以对“辨志”,尤其是“义利之辨”如此重视。比如其《语录》载:“傅子渊自此归其家,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教人何先?对曰:‘辨志。正己复问之:‘何辨?对曰:‘义利之辨。”[2]对于傅子渊的这一应对,象山高调表扬说:“若子渊之对,可谓切要。”[2]作为象山的高足弟子,傅子渊自然理解“立志”与“义利之辨”在整个象山心学中的重要地位,所以象山《语录》中也就有这种比喻性的说明:“学者须是打叠田地净洁,然后令他发奋植立。若田地不净洁,则奋发植立不得。古人为学即‘读书然后为学可见。然田地不净洁,亦读书不得。若读书,则是假寇兵,资盗粮。”[2]
在这里,如果“田地不净洁”,即“立志”或“义利之辨”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澄清,亦即所谓为学之发心动念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从而一味地格物致知、读书穷理,那么只能导致“假寇兵,资盗粮”的结果。显然,在为学之入手上,象山的“义利之辨”确实较为准确地把准了当时学界之病的脉搏。
甚至,象山对当时学界尤其是朱子学的这种补充与纠偏作用在他们的初次相逢——朱陆鹅湖之会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比如象山弟子朱亨道记载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7]
在朱子看来,为学自然要格物致知、读书穷理,因为“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7]。但在象山看来,如果作为发心动念之“志”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么一味地格物致知、读书穷理将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只能是所谓“假寇兵,资盗粮”。所以,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虽然朱子已经承认自己“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10],但象山仍然不予认可,并回应说:“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2]这说明,与朱子重视的格物致知、读书穷理之类的道问学相比,象山心学则准确地抓住了具有决定作用的价值观上的“立志”问题。实际上,这也是象山心学对于朱子理学的一个重大纠偏。
但在《宋元学案》中,为了弥合朱陆之间的分歧,黄宗羲在征引了陆象山《祭吕伯恭》一文中的“追惟曩昔,粗心浮气,徒致参辰,岂足酬义”[1]之后,又援引朱子的书札说:“其别与吕子约书云,孟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我事邪?与何叔京书云,但因其良心发见之微,猛醒提撕,使此心不昧,则是做工夫底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见于良心发见处,渺渺茫茫,无下手处也。”[1]
实际上,黄宗羲这种做法与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一样,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只能使两家的分歧成为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虽然朱子也有对自己“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的检讨以及寻找“良心发见处”的反省,但这种检讨与反省毕竟不是朱子学的主调;而其反省也不可能将朱子后学“从册子上”引导到“良心发见处”来。在这种条件下,以“切己自反,改过迁善”[2]为根本指向的象山心学对朱子理学构成了一种重大补充。
四、结语关于朱陆之间的分歧,清代的历史学家章学诚曾有一段著名的评说,他认为:“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11]所谓“千古不可合之同异”,当然是指他们面临着不同的时代任务而言;而所谓“千古不可无之同异”,则是指因为他们之间的先后继起与相互补充,所以能够较为全面地展开了理学的追求与关怀。所以,突出被朱子之重知主义所弱化的尊德性传统及其对人伦生活的实践落实,这就成为象山心学崛起的历史机缘,也是其心学的一种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1]黄宗羲.黄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2]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佚名.十三经[M].吴哲楣,点校.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
[4]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11.
[7]朱熹,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脱脱.宋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9]丁為祥.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的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朱熹.朱熹集[M].成都:巴蜀书社,1992.
[11]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for the rise of
Xiangshans Mind StudiesWANG Xing, LIAN Yongji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48, Shaanxi, China)Abstract: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Xiangshans Mind Studies. LU Xiang-shans confident character, strict family education and early ethical practices constituted the main foundation of his behaviour; Mencius thought was the spiritual resources for him to walk into the society. ZHU Xis compilation of Jin Si Lu and Si Shu Ji Zhu adapted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he competed with zen Buddhism theory comprehensively and tried to replace it, this was the reason why Zhu Xi became the highest achievers in researching neoConfucianism in Song dynasty. ZHU Xi emphasized Dao Wen theory, resulting in negligence or weakening to the tradition of honoring moral nature ,that was an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s to Xiangshans Mind Studies, which was emphasis on tradition of morality and ethical practical care.
Key words: Xiangshans Mind Studies; main foundation; thought resources;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imperial exam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