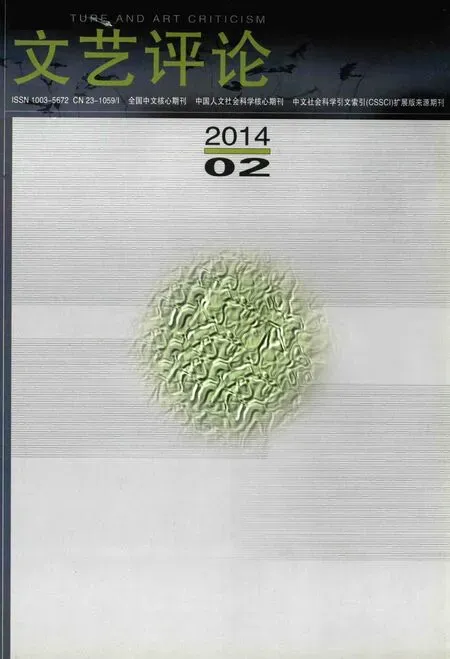“百姓日用即道”与晚明本色论
梁 愿
中国古典美学的本色论发展至晚明,已经由就文体而言本色转向就主体而言本色。这一转向与晚明的哲学思潮紧密相关。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唐顺之本色论所言之主体,指有识主体与纯明主体。它是指向超然无欲境界的,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传统道德的濡染与传统美学的规范。徐渭本色论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但又由于徐渭更多地接受了王畿思想的狂禅倾向,特别是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徐渭本色论最终超越了唐顺之本色论。徐渭本色论所言之主体,即当下的、真实的个体,它并不排斥自然人性。由此徐渭打破了传统美学崇雅抑俗的审美趣味。
本色论并非晚明特有的产物。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一文中就出现了“本色”一词:“夫青生於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古代认为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为本色,刘勰所使用的本色即为这一涵义。北宋诗人陈师道,在评论韩愈与苏东坡时也使用了本色。他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在这里,本色已作为一个专门的文论术语,主要就文体的本质特征这一层面而言。此后南宋诗论家严羽,亦以本色来说明诗歌这一文体的本质特征为妙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沧浪诗话·诗辩》)
一、唐顺之本色论
本色论在晚明时期得到了进一步阐述与拓展。如上所述,本色论在陈师道与严羽那里,都是就文体的本质特征而言的。而发展至唐顺之,则更倾向于创作主体的独特性。《答茅鹿门知县(二)》一文集中体现了唐顺之的本色思想:“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唐顺之的本色论,强调创作主体须直抒胸臆、率性自然。不过,这一创作主体也并非真正的无所约束、绝对自由。如所引段落中的“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已经表明唐顺之所要求的创作主体其实是超然绝欲、纯明虚灵的。除此之外,唐顺之还认为真正的本色是基于有识之见之上的。这一点在唐顺之接下来所提出的本色高与本色卑的见解中,即有明显的体现。他说:“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困缚龌龊,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本色高者,有真知灼见者,完全可以不顾声律与法度而自然成文。而没有真知灼见者,只一味执著于声律与法度,却始终成就不了好诗。同样是在《答茅鹿门知县(二)》中,唐顺之进一步指出,儒家、老庄、纵横家、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而其本色之来源在于各个“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
唐顺之之所以侧重从创作主体的独特性来讲本色,并且将这一创作主体限定于纯明主体与有识主体,与其思想来源有关。关于唐顺之的思想来源,学者们多将其追溯至阳明心学。左东岭先生认为:“(唐顺之)他一生为学有三个阶段,追求八股制艺阶段、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交杂而又以理学为主阶段、悟解阳明心学而形成自我学术思想阶段。其文学主张亦可分为三个阶段,追随前七子复古主张阶段、崇尚唐宋古文阶段、坚持自我见解与自我真精神阶段。”①最集中体现唐顺之本色思想的《答茅鹿门知县(二)》,据推断即写于嘉靖二十四年,也就是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期间。在此之前,廖可斌先生在《唐宋派与阳明心学》一文中也指出了唐顺之对阳明心学有所吸收。的确,唐顺之与众多王门弟子有过交往,其中与王畿、罗洪先的交往尤为密切。嘉靖十一年,王畿赴京应试,唐顺之与之相交,开始接触阳明心学。之后又通过罗洪先进一步接受阳明心学。唐顺之的文学主张本色论,其实是由其哲学思想天机说延伸而来的。而认真分析天机说,则可看到其与阳明心学良知说的种种契合。唐顺之于《与聂双江司马》尝言:“尝验得此心,天机活物,其寂与感,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与之寂,与之感,只自顺此天机而已。……天机即天命也,天命者,天之所使也。故曰天命之谓性,立命在人,人只是立此天之所命者而已。”(《荆川先生文集》卷六)在《与两湖书》中他又论道:“天机尽是圆活,性地尽是洒落。”(《荆川先生文集》卷五)天机说一方面是肯定心的主体性的,另一方面又将心体置于自得自生、寂然洒落境界。这两层意思正是王阳明良知说的核心内容。王阳明晚年以“良知”来指称心体,心体在王阳明“心外无理”的言说中被极力推举,因此良知说当然也是推崇主体性的。同时王阳明又指出:“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人有虚灵,方有良知。”(《传习录》)由此可见,良知是不离虚灵的,虚灵即超然虚明之意。唐顺之是通过王畿等人来接受阳明心学的,但相较于王畿发展阳明心学的一面,他更多是吸收了王畿继承阳明心学的一面。因此唐顺之始终将心体界定在超然无欲之境,如黄宗羲所说,其“以天机为宗,以无欲为工夫”(《明儒学案》卷二十六)。这就不难理解缘何唐顺之本色论将创作主体限定于纯明主体与有识主体了。
阳明心学对主体的肯定,启发了唐顺之从创作主体来阐述本色论。但恰恰又是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唐顺之的本色论依然存在主动叩合传统美学的倾向,尚未真正适合晚明革新思潮的需求。直至徐渭本色论,才真正把晚明革新思潮推向了高潮。
二、徐渭本色论对唐顺之本色论的继承与发展
徐渭本色论与唐顺之本色论并非截然不同,后者是前者的思想来源。不过徐渭本色论在此基础上作了极大发挥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特色。徐渭与唐顺之的学术关系,首先表现在徐渭与唐顺之有直接交往,并且唐顺之还相当赞赏徐渭的诗文。《徐渭集》记曰:“荆公为两师言,自宗师薛公处所见渭文,因招渭,渭过从之始也。”②其中记录的,是徐渭于嘉靖三十一年初始唐顺之时的事情。又据史料载,自嘉靖三十七年冬到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唐顺之在浙江视察军情,期间常出入胡宗宪幕府(此时徐渭已被胡宗宪所招),两人有密切交往。徐渭晚明所作《师类表》中,亦将唐顺之视为其师。其次,徐渭本色论与唐顺之本色论有着共同的思想来源,那就是王畿思想。关于王畿对唐顺之的影响,上一段已叙及,此处略谈王畿之于徐渭的影响。王畿也是徐渭《师类表》中出现的人物。除了师徒关系,王畿与徐渭还是远房表兄弟。两人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决定了王畿思想定将深深影响徐渭思想。不过,徐渭对王畿思想的吸收又与唐顺之有所不同,这一点在具体分析了徐渭本色论之后便十分明晰。
徐渭本色论一开始是针对戏曲而提出的。徐渭认为南戏的高处在于“句句本色语,无今人时文气”(《南词叙录》)。从这句话里面,我们读出了徐渭对今人时文气的不满,这就涉及本色论提出的文化背景。我们看明中后期的文学批评史,即可发现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当时影响很大。他们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诗人情感的抒发必须合乎秦汉文与盛唐诗的格调与法度。这样的话,所抒发的感情其实就与作者的真情实感有了一定距离。徐渭很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复古是一种迂腐气,他认为戏曲语言应该通俗易懂、真实自然。在《西厢序》里面,徐渭把他的本色论更加完整更加深入地表达出来了:“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按一般封建道德的标准,夫人肯定是比婢女高一等的,这让我们联想到唐顺之的有识与无识的区别。但是在徐渭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夫人有夫人的美,婢女有婢女的美,他认为婢女不应该装作夫人,那样不仅终觉羞涩,特不自然,而且反掩其素。徐渭看到了婢女的自身之美,其本色论强调的就是真,就是主体性与个体性。应该说,徐渭继承了唐顺之那种由主体而言本色的做法,但是他又打破了唐顺之本色论那种崇雅抑俗的价值取向,实现了对传统美学的超越。徐渭明确提出:“语入要紧处,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碓,不杂一毫糠衣,真本色。”(《题昆仑奴杂剧后》)好一句“越俗越常越警醒”,徐渭以此高度彰显和肯定了不被传统美学接纳的俗美,即便是笑话,“因为趋向于内心关照,所以即使是因笑话而有所思、有所得,在思想路径上也是由自娱而自悟,由独乐而独善“。③也就是说,徐渭本色论完完全全肯定了自然人性,并且由对自然人性的肯定连带推崇与高雅相对的俗美。这样一种肯定自然人性之美的文论,在晚明商品经济日渐发展,人性与私欲得到某种程度的解放和满足的情形下,无疑十分契合时人的审美需求与审美心态。
三、“百姓日用即道”与徐渭本色论
为何同是吸收了王畿思想,徐渭本色论呈现出与唐顺之本色论如此不同的一面?我们认为,唐顺之所吸收的是王畿继承阳明心学的一面,而徐渭吸收的则是王畿发展阳明心学的一面。王畿曾言:“凡我同盟,既脱世网,下戏台,正好洗去脂粉,觑见本来面目之时。”(《云门乐聚册后语》)同时他又指出:“夫学当以自然为宗。”(《答季彭山龙镜书》)按唐顺之的理解,本来面目是“绝无烟火酸馅习气”的,是超然绝欲、纯明虚灵的,这样的境界才是真正的自然境界。然而,徐渭却是从自然人性上来理解本来面目与自然境界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王畿作为从阳明心学发展至王门狂禅的中间人,其思想本身就存在既高度突出本体又尚未抛弃工夫的逻辑矛盾。唐顺之“以无欲为工夫”,显然是紧紧立足于阳明心学。而徐渭的“越俗越常越警醒”,无疑表现出了狂禅倾向。王畿吸收转型期的禅学思想,以“无”讲良知,否定为善去恶的过程,客观上为自然人性作为合理存在开辟了理论空间。徐渭正是延续了这一哲学思路,才在《论中(一)》中如此道:“中也者,人之情也。”④且在《论中(二)》中重申道:“人有骸,天无骸。”“圣人不能强人以纯天也。”⑤徐渭这种肯定人的自然性情的思想,既是受王畿狂禅倾向的影响,更是受王门狂禅的重要代表人物王艮的影响。尽管找不到徐渭与王艮实际交往的文字材料,但徐渭对王艮的思想是相当崇尚的,有诗为证:“千里神交已十年,况逢安定敞高筵,越国山川寒食到,泰州衣钵夜深传。风云座上双萍合,桃李阴中一榻悬,别去那能随画桨?金山寺下共维船。”⑥诗中的“千里神交”,体现于徐渭肯定自然人性的思想对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叩合。我们知道,王艮借用慧能一系的哲理思路,认为良知是“现现成成,自自在在”的。为进一步说明这种现成性,又以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的思想来言说良知:“良知天性,往古来今,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而措之耳。”(《答朱思斋明府》)王艮之子王襞继续阐述这一思想,将百姓日用与本色联系了起来。他说:“才有纤毫作见于些子力于其间,便非天道,便有窒碍处。故愈平常愈本色,省力处便是得力处也。日用间有多少快活在!”(《寄庐山胡侍御书》)这就是最能代表泰州学派思想特色且引起最多争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暂搁争论不议,我们只看这一思想的理论内涵与理论张力。“百姓日用即道”的重要内涵是,道无所不在,道不离百姓日用。王艮对道不离百姓日用的倡导,意图在于推举天然率性。他认为,良知自有,人人具足,只须顺心任性、自然而然,不必刻意修持、另寻他觅。可是实际上,这句话却蕴含着百姓日用就是道(突出百姓日用,重心落在百姓日用)的理论张力。若按此思路,则人之七情六欲、爱恨嗔痴、雅俗尊卑,都是应该被肯定的。王艮的尊身尊道思想,正是这一张力开始起作用的产物。王艮思想对晚明革新思潮的最大影响所在,应该说也在于这一理论张力。徐渭以“情”论中,以及对“人有骸”的指出,显然与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濡染密不可分。恰恰是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之天然率性的理论内涵及其肯定自然人性的理论张力,赋予了徐渭本色论独特的理论内涵,使之最终超越了唐顺之本色论,并真正适应了晚明革新思潮的发展需求。
王畿的狂禅倾向,与王艮吸收狂禅思想而形成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使得徐渭本色论在唐顺之侧重主体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人的自然情性。徐渭本色论的这一思想特点,不仅表现在戏曲理论中,从其诗文书画理论亦可看出。诗文方面,徐渭强调“古之诗本乎情”。此情为未经道德熏陶浸染、未经法度剪裁规范的自然之情。诗歌就是这样的自然情感的自然生成。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肖甫诗序》中:“古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是以有诗而无诗人。迨于后世,则有诗人矣,乞诗之目多至不可胜应,而诗之格亦多至不可胜品,然其于诗,类皆本无是情,而设情以为之。夫设情以为之者,其趋在于干诗之名,干诗之名,其势必至于袭诗之格而剿其华词,审如是,则诗之实亡矣,是之谓有诗人而无诗。”此外,于《叶子肃诗序》一文,徐渭再次强调了真实本性、自然真我的重要性:“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盖所谓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窃于人所尝言者也。”书画方面,对自然人性的肯定,主要以有别于古典美学尚雅趣味的,崇尚粗服乱头的审美形态表现出来。徐渭的书法颇有个性,如《墨葡萄图》的题画诗,字形偏斜摇晃,笔墨浓淡错落,以此表达十足的风中飘零、落拓不羁之味。徐渭认为,书法的最好形态,是随自然情感的真实流露而来的,而不是按照某些技巧某些格调所构建出来的。因此天成之作,即为基于真实个体之作。他是这样说的:“夫不学而天成者尚矣……天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乎己而不由人也。”(《跋张东海草书千文卷后》)徐渭在书法上这种随性挥洒的作风,也体现在其绘画中。徐渭常以狂草入画,但求神韵,不求形似。其大写意画展现给人的,就是一种随意涂抹、气势逼人、淋漓尽致之感。在这里,画面经营、笔法技巧似乎全不复存在,唯有创作主体的凛然之气、率然之性!
必须指明,在晚明文人那里,对私心情欲的肯定,是始终被置于肯定个体价值、自然人性这一大前提之下的,并非目的仅仅在于张扬、放纵私心情欲。由此我们说,与徐渭书画的粗服乱头互为表里的,是对个体价值的关注与深思。换言之,徐渭一方面以粗服乱头的审美形式来尽宣泄之能事,另一方面又将深深的个体之思寄寓其中。徐渭曾提出“画为戏影”的创作思想,即画中之象并不是本来面目,因此我们须透过画中之象去领悟本来面目。从徐渭如下这一对联可知,本来面目又是不离个体真我的。“世上假形骸,恁人捏塑。本来真面目,由我主张。”(《子母祠》)总之,徐渭本色论是以个体价值为核心与旨归的。
徐渭本色论吸收了王门狂禅“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把唐顺之本色论的高高在上的有识主体与纯明主体,降落为日常生活与俗世生活当中的现成主体、当下主体。这一转变影响及具体创作,使得晚明艺术更加注重个体真我,其情感意蕴也更加浓烈而明晰。明末清初,徐渭的本色思想被傅山与八大山人作了进一步阐释,分别发展为“四宁四毋”说与“画者东西影”的创作思想。可见,徐渭对晚明本色论的发展契合了晚明革新思潮的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