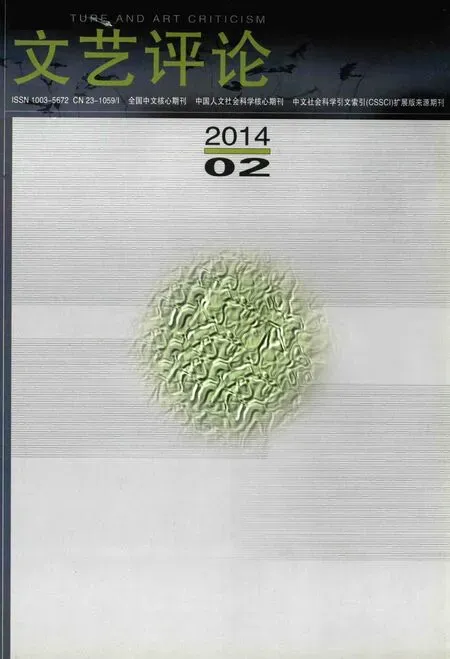从脱离到返本:新诗与古典诗歌格律
李 丹
对新诗格律问题的探讨是一个老话题,研究成果也相对丰富。多数研究从新诗自身的角度进行,有探讨其发展演变历程的①,有专门研究某一时期格律理论的②,有针对某一派别的格律理论进行梳理的③,也有研究某位诗论家的格律理论的④,还有对格律和自由两种诗体进行比较的⑤,此外,也有谈及传统文化与新诗格律问题⑥以及继承传统诗律以建构新诗格律的⑦,但未见研究古典诗词格律与新诗格律之间继承与演变关系的;针对这一状况,本文尝试进行探讨。
一
永明声律论的出现,标志着古代汉语艺术运用规则的成立,它既有总原则,力求文字声音富于变化,以构成音调的错综和谐;在具体运用中,又有四声八病的规定。永明声律论对发掘汉语诗歌的音韵美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到唐代已演变为一套完备的格律规则。近体诗可以作为中国古典诗词格律的典型,这里将其分为声音与体式两个方面来说明,其中声音方面的规则有:一是叶韵。要求一韵到底,除首句外,偶句末字须押同一韵部的韵。押韵是构成诗歌音乐性的关键环节,在诗行固定位置出现相同的韵脚,可以加强节奏,使诗歌在声音层面形成一个整体。二是平仄。这是诗句词语声调安排的规则,将四声二元化,把平上去入四声分为平声和仄声;诗中多以两字为一组,其平仄或交错或相对或相粘,一句之内平仄相间,两句之间平仄相对,两联之间平仄相粘,末字除外。律诗的平仄及其变化的规则还有避免孤平、三平调或三仄脚,首句末字可平可仄可入韵可不入韵即“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等。“在格律诗中,重要的是二、四、六等偶字亦即音组的落点上必须相同,只要这些字的声调一致,便是粘合了。所谓粘,其功用在于使全诗联与联之间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联之间紧相啮合,整体感得到强化。”“这样一种规则,表面上看是相对立的,但实际上却是利用平仄二元对立的性质,既使上下两句间因差异各具不同的音调特性,又通过二者的中和与更高层次上的类似获得一种整体感。可见,充分利用平仄二元之间既相异又互补的特点是格律诗音乐性的奥妙所在。”⑧正由于其排列的精妙,故自唐代定型后,持续了千年之久。
体式方面的要求表现在,一是对仗。以律诗为例,全诗由八句组成,每两句为一联,共四联,依次称为首联、颔联、颈联、尾联,每一联中,上句为出句,下句为对句,一般要求中间二联对仗:出句与对句同一位置所用字词,其词性、色彩、方位等要同类相应,而意义则要相反相成。“就唐诗中的对仗来说,它大致有几个规则:一是词性要相同或相近,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二是上下两句的句法结构要相同或相近;三是偶对字词的平仄要相对——平仄的对立不仅不会造成偶对的不和谐,反而突出了各自或高或低或长或短的声音特性,由此获得一种超越对立的统一。”⑨较常见的对仗有流水对、借对、交错对、当句对等,从分类的精细程度就可看出近体诗的对仗要求极为工巧。作为一种并置的方式,对仗在诗句语言线性进展的流程中设置出一块或并列、或对反的停留空间,以强化时间流动中的空间排列,达到拓展内容的目的。在杜甫、李商隐等大家的笔下,对仗不仅仅是体式方面的外在要求,而是为貌似简短的律诗辟出一方容纳开阔境界的领域。“进一步来看,诗中的对仗还有一种特殊的功用,那就是扩展、改变作者的思维方向,增加诗歌的意义内涵。……表面看只是一种技巧,实际上却是由于对仗的原因,而使得诗人在写作时不由自主地、必然地向与之相反的一个方向和物体靠拢,由此改变了人的思维习惯或思维方向。……由于整个思维方向的改变,就大大扩展了空间场景,增加了诗句的情感张力,并在未写的中间地带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余地。”⑩二是篇制。这是关于诗篇字数的规定,分为绝句、律诗、排律,绝句为四句二十字或二十八字,律诗为八句四十字或五十六字,排律可更长。将绝句、律诗的体量限制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有利于激发诗人选用最恰切的字词和饱含情思的语句,以集中地传情达意。近体诗的五、七言,是依音节而定的,一个字构成一个音节;诗句停顿点也是固定的。以此构成诗篇体式层面的节奏。
概括地说,近体诗的格律规则对于发挥古代汉语的声音与意义功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有学者认为,“从整体来看,格律诗的最大特点在于对立统一。对立,指声调之平仄、诗句之对偶,在两句之间都是两两相反相对的;统一,既指由这种对立形成的一种互补结构,也指联与联之间的紧相粘合与全诗的整体和谐。这是由对立形成的统一,也是整体统一中的对立,对立与统一,便是格律诗形成的基本法则。”⑪近体诗格律规则有利于促成诗歌这一文体自身特性的突出,并造就了汉语诗歌的巅峰,鲁迅就曾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⑫,这当然是就近体诗范围而言的。
二
直到20世纪初,中国诗歌仍在沿用近体诗规则,实际上,这种古典用语系统与日常口语之间已出现颇大的距离,难以准确地表达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新感受,可以说,谨严的古典格律束缚了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的创造力,使诗歌创作成为刻板的古典形式应用。此时,赴域外的学习经历使得中国留学生接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尤其欧洲国别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规律,促使先行者思考相应的问题;新诗的诞生便是这一影响的产物。1916年,胡适在美国首先提倡摆脱古典诗词格律的束缚,旨在打破古人设定的形式规则对今人诗作的制约。与此相并列的另一条线索是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于五四运动前后创作的新诗,以情感内容决定诗歌的形式。它们都力图以自由的体式取代传统的格律。
1.“自然的音节”说。于认识到传统诗词格律强大的规范力量,胡适革新主张的第一步是摒除古典格律的影响,他倡导的“不更做文言诗词”,而作“长短不一的白话诗”⑬,就是针对传统格律而言的。他认为,“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⑭所谓“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⑮在此意义上,胡适倡导的是自由诗。
在“诗体的大解放”倡导之下,古典诗词格律中的平仄、对仗、篇制等规矩都被抛却,只剩下用韵这一项要素。除韵脚问题外,胡适还注重新诗“音节上的试验”,他曾专门讨论“双声”、“叠韵”、“齐齿”对“增加音节上的美感”的认识,认为“凡能充分表现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的,便是诗的最好音节。”⑯“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⑰。在实践的基础上,胡适将“自然的音节”⑱理论总结为
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用韵,即他所谓的“音”,主要表现为韵脚,新诗押韵比较自由,可以一韵到底,也可以一节一转韵,还可以采用交韵、抱韵、随韵等;另一个是音节,即他所谓的“节”,是新诗格律理论探讨的关键所在,涉及诗行词语停顿的问题。胡适将传统诗句以“言”为计量单位转化成现代汉语诗歌以“节”为计量单位。尽管提出了“节”的概念,也就是关系到新诗节奏的问题,但由于胡适顺从口语的习惯,重视白话而不重视诗歌艺术,导致初期新诗呈现散文化倾向。不过“音节”概念的提出,对新诗格律理论建设具有奠基的作用,后来闻一多的“音尺”,叶公超、孙大雨的“音组”,朱光潜的“顿”,林庚的“节奏音组”,郑敏的“字群的组合”⑲等概念,都是在胡适“节”的概念基础上的探讨。
五四时期还有一些讨论传统格律问题的意见,如刘半农提出废除律诗、排律,“更造他种诗体”⑳的观点,皆是对古典诗词格律的摆脱。
2.“自然流露”说。自由诗这一源自西方的概念,是相对于古典格律诗而言的;自由,指其形式的不受囿限,并不是不要形式,而是不要传统的格律形式。自由体的形式由内容决定,即由内容形成韵律,或曰“思想韵律”㉑。思想韵律依循情感的起伏,可以采用重复、排比等方式。诗人兼诗论家艾略特说:“好的自由诗基本上是一种对比较为人熟知的英语诗节奏形式的逃避”㉒。可见,不论中西,现代诗的成立都需要经过脱离古典诗歌格律的过程。
郭沫若接受西方自由体式的影响,大胆跳出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套路,提倡依据内容跌宕起伏的自由诗。他说:“我也是最厌恶形式的人”,“总觉得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㉓,这种自然流露观的准则是要体现内在的节奏或内在的韵律。“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㉔并进而认为,“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诗不是‘做’出来的,是‘写’出来的。”㉕这种自然流露说还包含直接“摹拟我们底心情”的意味,由情感控制诗的进程。在此理论导引下,崇奉形式绝端自由的郭沫若任情绪像脱缰之马尽情驰骋,而不注重打磨,以致造成某些诗作艺术粗糙的弊端。
陆志韦在1923年出版的《渡河·自序》中指出,“破四声”、“舍平仄而采抑扬”,抑制新诗的“放荡”,创造有节奏的“自由诗”㉖,一定程度是针对郭沫若自由体观点而言的。抗战期间出版的《诗论》代表艾青对自由诗理论的推进,他注重节奏与旋律,而不注重格律,更不迷信形式,“节奏与旋律是情感与理性之间的调节,是一种奔放与约束之间的调协。”㉗艾青将胡适的白话入诗观念提升为散文入诗的观念,将郭沫若对情绪的宣泄引向对情感内在节奏的把握,从而将初期新诗的散文化擢升至自由诗的散文美,并将自由诗的形式艺术定位在制造韵律上。
三
尽管新诗脱离古典诗词格律的束缚而得以成立,但自由诗随之产生了散文化和艺术粗糙的弊病㉘,也就是说,新诗对传统诗词格律的规定抛弃得太多了。对此,闻一多强调新诗的节奏理论。这是对诗歌格律的重新认识,实际上构成对汉语诗词格律传统的归返。在新诗格律建构中,闻一多、叶公超、孙大雨等人主要围绕诗行的顿数问题展开,这就与传统格律里的篇制问题相关联。
1.“音尺”说。作为新格律派的纲领性文件,《诗的格律》一文提出“音尺”的概念,这是英语诗格律术语foot的中文翻译,闻一多借来用以称谓新诗的节奏单位。他认为新诗的音尺主要分为“二字尺”或“三字尺”,以《死水》为例,每一诗行为四个音尺,或由两个二字尺和两个三字尺组成,或由三个二字尺和一个三字尺组成,音尺在诗行里等时地流动,整首诗的节奏就得以突显。这里,闻一多将传统诗歌的等音计量转化为现代汉语诗歌的等顿计量,由传统的“几言”转化为“几个音尺”(几顿),奠定了新诗格律中通过控制节奏来控制诗行长度的基础。
基于“音尺”计量单位的确定,闻一多还提出“句的均齐”的观点,这是依据音尺数相等而形成的诗行之整齐。如果说古典格律的五、七言是在文言的基础上对诗歌句式、字数要求的话,那么闻一多对新诗行的要求与前者的思路是一致的,却更适合新诗的组句特点。进一步地,他提出“节的匀称”的观点,这是在句式均齐的基础上形成的诗节之整齐。
整齐的字句是调和的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绝对的调和音节,字句必定整齐。
这样讲来,字数整齐的关系可大了,因为从这一点表面上的形式,可以证明诗的内在的精神——节奏的存在与否。㉙
由于对格律规则的循环应用,一边说“没有音尺,也就没有句的均齐;没有格式,也就没有节的匀称”,一边说“字数整齐的关系可大了”,这样就忽视了诗行音尺数相等与字数相等的差别,因此他提出的“字数整齐”产生了绝对划一的诗句长度问题,违背了新诗行按音尺数(顿数)计量的法则。
尽管如此,闻一多格律理论的进步性在于,解决了新诗行停顿次数整齐所产生的节奏问题,比胡适“自然的音节”观点更突出了新诗的格律。
2.“音组”说。在闻一多之后,叶公超也发表了关于新诗格律的观点,他认为,“格律是任何诗的必需条件,惟有在合适的格律里我们的情绪才能得到一种最有力量的传达形式;没有格律,我们的情绪只是散漫的、单调的、无组织的,所以格律根本不是束缚情绪的东西,而是根据诗人内在的要求而形成的。假使诗人有自由的话,那必然就是探索适应于内在的要求的格律的自由,恰如歌德所说的,只有格律能给我们自由。”㉚他提出新诗是“说话的节奏”和“音组”的概念,“在文言里,尤其在文言诗里,单个字的势力比较大,但在说话的时候,词语的势力比较大,故新诗的节奏单位多半是由二个乃至四个或五个字的词语组织成功的,而不复是单音的了,虽然复音的语词中还夹着少数的单音。……中国语言的音组(即语词的字音)是很短的,大概五个字的音组已是不多听见的。在每个音组里,至少有一个略微长而重,或重而高,或长而重而高的音。……我们只有大致相等的音组和音组上下的停逗做我们新诗的节奏基础。”㉛这里的“音组”概念的提出,原则上与闻一多的“音尺”概念是一致的,但叶公超强调新诗行音组数相等而诗句长度可能不等的自由,这是对闻一多格律理论的推进。
孙大雨对新诗格律的贡献在于界定了音组的概念,他认为诗的节奏总是相当整齐有度的,因而总可以分析成为规律化的音组,音组是由久暂显得相同或相似的一个个单位组成的:
这些相似但又不尽相同的单位川流不息而来,接连几个单位(通常以二至六为度)以成行,积聚几行以成节段,在时间里秩序井然而又变化不绝地进行着,使作者听者都感觉到内容和意义风格之间有一脉活力推动着,活跃着:这就是韵文所有而散文所没有的“音组”。㉜
至此,在新诗格律建构里,由音组的流动形成的节奏,其性质、功用被清晰地揭示出来。由于古典格律要求每句字数相等,故整首诗的停顿点是一致的,而新诗则因现代汉语组词字数不一的缘故,诗行并不一定整齐;如果能在整首诗内形成音组(顿)有节奏的流动,则诗歌的音乐性就得以产生。
对新诗格律的探讨既是对诗歌格律本源的回归,也是在忠实于新诗节奏特点的情况下对传统格律的发展,等顿计量与等音计量的区别,构成新诗格律与古典诗词格律在篇制问题上的差异。
四
从上文分析可知,不论是要破除旧格律套路的自由体,还是要建立新形式的格律体,实际上都围绕着这样两个共同的问题:一个是用韵;一个是节奏,即音节、音尺、音组、顿等。对于前者,理论与创作都不存在歧义;对于后者,关于诗歌节奏的原则问题也没有争议,凡是诗歌就应该有节奏,而在是否应像近体诗一样,其节奏应有形式上的定型要求这一点存在分歧,格律派一直在寻找新诗行的节奏规则,即固定的诗行模式,只是至今仍未确定下来;而自由派则反对规定一种形式作为新诗的主要形式,他们将诗句节奏样式的决定权留给诗人自己。这样,问题的焦点就在于,不论古今,也不论自由体还是格律体,都遵循着诗歌语言的运作规律,也就是发挥汉语言的音乐性,只是由于现代汉语不同于古代汉语,新诗人应该像音乐家那样创造读者喜爱的节奏,以口语的节奏代替传统格律,把诗歌从机械呆板的节奏中解放出来,将凝固的古典格律转变为自然灵活、富于弹性的现代节奏。就是说,新诗行的停顿样式是不定的,每首诗的诗行顿数也是不定的,尽管四顿可能是最常用的,但其他顿数的出现也是有可能的。这样新格律的多样化并存状态,一方面成为新诗的一种现代性表现;另一方面又与自由体的节奏论相靠拢,即使两者仍存在严格与宽松的区别。一言以蔽之,尽管自由体、格律体的名称不同,而实质上两者探索的是同一个问题。
关于新诗格律与自由的问题,曾在1950年代出现集中的讨论,如何其芳界定的现代格律诗,“每行的顿数有规律,每顿所占时间大致相等,而且有规律地押韵”㉝;卞之琳也认可以顿作为新诗格律的计量单位,并认为“诗经、楚辞、古诗、近体诗等都可以用顿来分析它们的格律基础”㉞,这是用新诗格律计量单位衡量古典诗歌,这一反观说明新诗格律衡量尺度是有效的;此前用古典格律衡量新诗往往遇到阻碍,那么这种反证法的运用,也是一种对新诗格律可行性的论证。当代自由诗创作的流行,一定程度说明其符合现代汉语诗歌节奏多元化的要求,正如徐訏所说,“诗词的节奏和韵律,应该是语言的节奏与韵律,所谓语言的节奏与韵律实是生命生活节奏与韵律,一个人的走路有节奏韵律,呼吸有节奏韵律,血液循环有节奏韵律,消化工程有节奏韵律,这是生命的节奏韵律。生命的节奏韵律,一方面可说人人相同,另一方面也可说人人不同,……在诗歌方面,五言也好,七言也好,一方面,它们的节奏与韵律相同,另一方面讲,每个诗人都有个别的节奏与韵律。”㉟将诗行节奏韵律的顿挫起伏交由创作处理,就是令每首诗都能获得适合自己节奏韵律的表达方式。还有一种调和格律与自由两派的观点出现,即“精炼,大体整齐,押韵”㊱的提法,这貌似一种折中,实际上希望对两派理论优长进行调谐,既要克服格律派的刻板,也要克服自由派的放荡。总之,不论两派调和与否,它们都将节奏韵律视为新诗的必要条件。
新诗格律问题仍处在探索过程之中,如果说新诗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格律,也许意味着新诗格律并不像古典格律那样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即基本格律原则是应该有的,而在具体创作中则可以变通处理。就新诗格律与古典格律的关系而言,所谓脱离古典诗词格律,是由古今汉语的差异造成的;所谓归返格律精神,是由诗歌的文体性质决定的。一方面,古典诗词的格律精神与节奏规律可以作为建构新诗格律规则的参照基础,另一方面,新诗格律的建构可以也应该超越古典模式。在新诗格律建构中,古典诗词格律规则发生不同的变化:用韵仍是一项重要的因素,且现代汉语诗句的押韵较古典诗词宽泛,故应用较广。由于多音节词的出现,难于按近体诗的要求进行平仄搭配,但可以将其转化为声调上的差异排列,抑扬起伏而非单调划一就能展示声音上的错落协调之美。因为构词方式与古代汉语的差异,尽管不排除有对仗的诗句,但难于绝对地要求形式上的对仗,而对偶思维的功能往往应用于新诗内容之中,转化为一种诗意表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