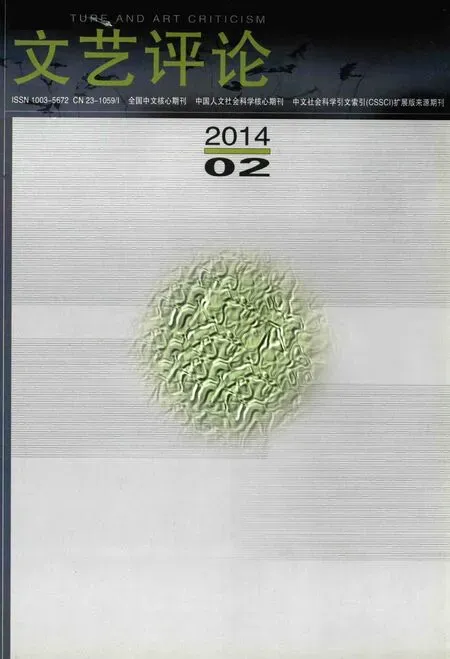明清乐论的客观化趋向探析
韩 伟
明清乐论尤其是明代乐论与宋代乐论有相似之处,但又存在自身特点。就相似处言之,在理学的大背景下都表现出一定的维护儒家乐统的倾向,这一点在以王守仁、王夫之为代表的理学家乐论中表现明显,他们仍然十分推崇儒家中和之德对音乐的指导意义,仍然推崇雅乐而否定新声,对儒家的“中和”、“雅正”、“德行”等理想推崇备至,从而形成了理学家乐论与具有进步色彩的民间乐论分庭抗礼之势。可以说,王守仁、王夫之等人的乐论也体现了正统文人及道学家乐论内在的自足性,同时这种自足性也带有天然的封闭性,从而与音乐实践的距离越来越远。就明清乐论的自身特点而言,由于世俗化的逐步扩展加之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便使宋代就已经十分繁荣的通俗文化进一步深化,相形之下,传统儒家艺术观念中的政治性、伦理性和神秘性倾向开始受到挑战,此种背景下明清乐论亦表现出鲜明的客观化倾向。我们认为,这一点是明清乐论区别于前代乐论的重要特质。
一、明清乐论的“主情”色彩
就主情而言,首先应提及者是李贽。李贽对“情”的重视事实上是其“童心说”的副产品,并将其与“性”放在一起,他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想,主张在创作中要遵循“最初一念之本心”,表达自己的真实性情,崇尚自然真情。在《焚书·读律肤说》中他指出:“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乐论从先秦时期开始就对与“情”相关的“性”十分关注,这一点在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乐论中表现十分明显,《乐记》尝言“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推崇人之本性,但这种“性”则是具备儒家之“德”的内涵的,与今天意义上的“性情”概念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乐记》所言之“性”、“情”不同于李贽所言之“性”、“情”,虽然在宋代理学家乐论中也提到了“情”,但其与“性”相似仍是在“天理”的框架下言说的。而李贽所言之“性情”则是自然之情,甚至也不排除“欲”的成分。对真实情性的重视,在李贽琴论中也表现明显:“《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余谓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②此处李贽对传统琴论观提出挑战,《白虎通》中的琴论思想代表了汉代以来对琴乐的普遍认识,赋予琴鲜明的政治色彩和道德内涵,认为其是禁止淫邪思想产生的重要工具。对此,李贽的观点十分鲜明,他更多的是将其看成表达人内在情感的工具。
可以说,李贽的这种认识在明中叶以后是具有非常强大的号召力的。比如汤显祖便从戏曲创作角度谈到了情的重要性,“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③。而公安三袁则从歌诗角度表达他们对“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解,袁宏道尝言:“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④明清时期,对“情”的重视,除了上述诸人的乐论之外,还有张琦、李开先、冯梦龙等人,他们的基本立场与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人较为相似,限于篇幅不赘述。
二、明清乐论的“尚俗”取向
明清乐论的客观化潮流的第二个表现是尚俗。所谓尚俗,是说明清乐论表现出鲜明的雅俗通变立场,甚至认为俗乐是雅乐的基础。事实上,这种现象在宋代朱熹、郑樵等人的乐论中就曾有所表现⑤,但直到明清两代,俗乐的地位才被正式确立下来。俗乐由于能够自由地表达真情实感,加之形式上很少受到束缚,所以在明清时期获得了蓬勃发展。在乐论中,与上述“主情”倾向一致,这一时期的乐论对俗乐多持肯定赞赏的态度,本书认为对俗乐的重视李贽、冯梦龙、李渔代表了逐渐深化的三个阶段。李贽乐论亦如前述,对自然情性的重视使得其对民间音乐更为推崇。下面重点谈一下冯梦龙和李渔。明代中期以后的很多文人普遍持“真诗只在民间”(李开先语)的看法,此种背景下冯梦龙对民歌十分推崇,并辑有《山歌》、《挂枝儿》等民歌集,其对俗乐的看法在《山歌》一书的序言中有明确的展现:
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真情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与?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⑥
由此可见,冯梦龙认为山歌与诗文同等重要,而且与李贽、汤显祖等人相似,其推崇山歌的深层原因仍是源于真情,并希望能够“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在冯梦龙眼中郑卫之音、桑间濮上之曲与山歌相似,在各自的时代都起到同样的作用。无疑,这种看法是具有进步性的。
冯梦龙之后,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对俗乐的认识又有所深入,这也是明清俗乐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李渔在《答同席诸子》一文中谈到欣赏歌舞的感受时他说“然胸中所见,自谓帘内之丝,胜于堂上之竹;堂上之竹,又胜于阶下之肉”⑦,表明他肯定“丝胜于竹,竹胜于肉”。可以说,李渔的这一认识是对传统乐论中“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观念的反叛,承认了世俗乐器的重要性,其中原因一方面在于,丝竹的乐声虽属于人为,与天然的肉声不同,但丝竹之声却带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含混性,因此会带给欣赏者更大的想象空间,这一点是肉声稍显逊色的地方,而这种想象空间恰是艺术的生命,正因如此李渔主张“即不如离,近不如远;和盘托出,不若使人想象于无穷耳”⑧。另一方面的原因则与李渔的鲜明民间立场密不可分,自明代李贽开始,经过冯梦龙,到李渔这里,文人对民间文艺越发推崇,而丝竹等乐器恰是演奏民间音乐的主要工具,所以李渔对丝竹的肯定恰可反映出其对通俗音乐的基本态度。与其对民间艺术的态度一致,他对具有鲜明民间特点的戏曲和填词都较为肯定:“文字之最豪宕,最风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过填词一种。……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⑨
除此之外,在对待古乐与新声这对一直以来的矛盾艺术方面,李渔的观点也较为透脱,在他看来,古乐与新声并无明确界限,大可不必机械地拘于固有成见,“听古乐而思卧,听新乐而忘倦。古乐不必《箫韶》,《琵琶》、《幽闺》等曲,即今之古乐也”⑩。即是说,只要能表现人的真实情感无论是古乐还是新声都是值得肯定的音乐。
李渔对待古乐与新声的这一态度,在清代音乐研究者中较为普遍。这一点在毛奇龄、李塨、江永等人的乐论中有较为集中的表现。毛奇龄认为雅乐、俗乐并无价值论层面的区别,他对历来备受推崇的雅乐有自己的看法:“古乐有贞淫而无雅俗。自唐分雅乐、俗乐、番乐三等,而近世论乐者动辄以俗乐为讥。殊不知唐时分部之意原非贵雅而贱俗也,以番乐难习,俗乐稍易,最下不足学则雅乐耳。故考伎分等反重番乐,其能习番乐者,即赐之坐,名坐部伎。其不能番乐则降习俗乐,不坐而立,名立部伎。若俗乐不能则于是斥习雅乐,不齿于众,雅乐之贱如此。”⑪在他看来,雅乐的价值和难度绝不比俗乐和番乐大,前世帝王往往也用俗乐和番乐祭祀郊庙、侍奉祖先,俗乐只要内容上真纯自然,雅俗的界限是不存在的。对此,清代的另一名学者李塨便一阵见血地指出:“天地元音今古中外只此一辙,辞有淫正,腔分雅靡,而音调必无二致。”⑫由此可见随着通俗文艺在明清两代的盛行,理论层面的雅与俗、古与今、中与外之间的巨大鸿沟被最大限度地填平了。
与毛奇龄、李塨的立场相似,江永在《律吕新论》中也以通变的态度看待古乐与新声,且其观点更为辩证,在《俗乐可求雅乐》中他说:
俗乐以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十字为谱,十二律与四清声皆在其中,随其调之高下而进退焉。所谓雅乐亦当不出乎此,为雅乐者必深明乎俗乐之理,而后可求雅乐。即不能肄习于此者亦必于俗乐,工之稍知义理者,参合而图之,未有徒考器数、虚谈声律而能成乐者也。宋世制乐诸贤,唯刘几知俗乐,常与伶人善笛者游,其余诸君子既未尝肄其事,又鄙伶工为贱伎不足与谋,则亦安能深知乐中之曲折哉?判雅俗为二途,学士大夫不与伶工相习,此亦从来作乐者之通患也。⑬
由此可见,在江永眼中欲求雅乐,则必须先明俗乐之理,甚至要向士大夫所不齿的伶工贱隶学习,实际上江永已经将雅俗的界限取消掉,大俗即为大雅。而这一简单的道理则一直被正统文人所摒弃,自宋代以后仅有刘几等有限的几位音乐理论家能明白这一点。江永除了在雅乐与俗乐方面的观点较为灵活之外,对乐器、律准的看法也是如此,在《乐器不必泥古》篇中他说:“声寓于器,器不古雅则声亦随之。然天下事,今不如古者固多,古不如今者亦不少。古之笙用匏,今之笙用木,匏音劣于木,则亦何必拘于用匏而谓八音不可缺一乎?……后世诸部乐器中,择其善者用之可也。”⑭在《度量权衡不必泥古》中他亦认为古代律准以黄钟为根据,较为固定,因为度量的标准是统一的。而后世度量衡则很难统一,相应黄钟管的长度便很难确定,此种背景下各音的高度自然出入较大。鉴于此,他认为律准与乐器相似,都不必泥古不化。可以说,江永的上述思想是十分辩证的,这也是其乐论的基本指导思想,其在《声音自有流变》中便明确指出:“若不察乎流变之理,而欲高言复古,是犹以人心不安之礼强人以必行也,岂所谓知时识势者哉!”由此,其“通变”思想可见一斑。
三、明清乐论的“去神秘性”
明清乐论客观化潮流的第三个表现是去神秘性。中国古代乐论的去神秘化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虽然魏晋时期出现了嵇康《声无哀乐论》这样的乐论名篇,但从总体而言先秦的天道观、汉代的五行思想乃至宋明的天理观,都使得古代乐论带有天然的神秘性色彩。明代总体而言虽然在心学的影响之下更加强调主体真实性情的作用,但乐论中的神秘性因素仍时有表现,即便是在阳明心学中较为自由的泰州学派的代表李贽处,也有这种影子。其在《焚书·征途与共后语》⑮中明确提到了“声音之道可与禅通”的观点,认为音乐创作和欣赏都与禅悟有相通之处,“所谓音在于是,偶触而即得者,不可以学人为也”。很显然,虽然如上文所述李贽乐论中有若干进步之处,但仍有神秘化的影子,所不同的是其更多的是从禅宗的角度来看待音乐的。
而明清乐论在整体上毕竟是以去神秘化为主的,李贽作为开端性的人物虽不彻底,但毕竟对后来者有“导夫先路”之功。在清代的毛奇龄和李塨的乐论中,可以更鲜明地看到对神秘化乐论的摒弃。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有如下言论:
故凡为乐书者多画一元两仪、三才五行、十二辰、六十四卦、三百六十五度之图,斐然成文而又畅为之说,以引证诸黄钟、太簇、阴阳、生死、上下、顺逆、增减,以及时气、卦位、历数之学,凿凿配合者,则其书必可废。何者?使观其书而乐由以明,五声由以着,六律、十二律皆由之而晓然以晰,则传之可也;乃毕力求之,穷竟篇帙,而按之声而声茫然,按之律而律茫然,则虽欲不废而何待已?故未求声而求器,未求器而求数,未求数而先求之度量衡之铢、两、丝、黍、百、千、万、亿之璅璅,是皆亡乐之具。……然后知迁、固以后京房、郑玄、张华、荀勖、范镇、房庶、王朴、李照、陈旸,以及近代之韩尚书、郑恭王、杨主事辈,凡言铸钟均弦、造器算数,皆欺人之学,不足道也。⑯
在毛奇龄的这段话中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他承认“人声”的重要性,并将其看做音乐之根本,即“乐以声为主,乐之声以人声为主”是也。其次,对汉以后中国乐论中的神秘化和伦理化色彩提出质疑,认为从圣王、天地、五行等角度讨论音乐是古代乐论的最大弊端,这种做法往往会使音乐沦为某种伦理思想或哲学思想的附属品,而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所以毛奇龄称这种做法“与声律之事绝不相关”。再次,他也对历来的“以尺定律”的机械做法提出质疑,所谓“以尺定律”是与“以律定尺”截然相反的定准方式,前者重视古制,往往以史料中的记载为准,而后者则以实际音声和谐为准,所以“以尺定律”便是以先入为主的方式确定固定的标准,这一标准多出于前代乐书或本朝的音乐制度,然后确定律准,进而确定各音的高低。对于“以尺定律”还是“以律定尺”的问题,汉代以后一直争论不休,尤以宋代最为激烈,李照、胡瑗、陈旸、房庶、范镇等人都曾参与其中。今天看来,“以律定尺”当更为科学,更为符合音乐的自身规律。毛奇龄所批判的“未求声而求器,未求器而求数,未求数而先求之度量衡”便属于这一范围。可以说,毛奇龄的观点代表了明清以来乐论渐趋客观化、科学化的潮流,这已是明清乐论尤其是清代乐论较之前代神秘化乐论的重要进步,为近代乐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受毛奇龄影响,他的学生李塨在《学乐录》中也持类似观点:“今中华实学陵替,西洋人入呈其历法算法,与先王度数大端皆同,所谓天地一本,人性同然,不知足而为屦必不为蒉者也,乃于乐独谓今古参商,而传习利用之音为夷乐俗乐,亦大误矣。”⑰在他看来,包括西洋乐在内的一切音乐并无本质区别,甚至中华音乐与西洋音乐其“度数大端皆同”,这一方面表明西洋音乐此时已经进入国人视野,并对本土音乐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表明随着西洋乐的普及,中国传统文人表现出相对接受的态度,可以说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也是本土乐论逐渐客观化的鲜明标志。另外,李塨在《学乐录》中也记载了毛奇龄否定神秘化乐论的言论:“塨问曰:‘五声配五行、十二律配十二月皆秦汉以后牵掣之论,圣经未有也。今扭合之终不确,且滋纷无益也,不如一概巳之。’河右答曰:‘是’。”⑱这段话中的“河右”便是毛奇龄的号,李塨曾从学于毛奇龄,并对其思想较为认同,其《学乐录》自序云:“塨学乐河右先生一年余矣,虽窥涯岸,未尽精微也。”⑲由此不难看出,李塨是深受毛奇龄影响的,而上述对西洋乐的态度、对神秘化乐论的否定恰可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当然,明清乐论中仍无法决然摒弃掉传统乐论伦理化、政治化甚至是神秘化的色彩,在很多人尤其是明代道学家的乐论中这种情况仍十分明显,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明清尊奉传统乐论一系虽然仍对《乐记》等乐论经典十分推崇,但其直接承续的对象则是以周敦颐为代表的宋代新儒家乐论,较突出的例子便是往往以周敦颐的“淡和”思想为指导讨论音乐问题,如明末琴家徐上瀛在《溪山琴况》中曾提出古琴美学的二十四况,其中前九况为: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便蕴含着宋代理学之“淡和”的因素,蔡仲德先生说:“前九况的精神……归纳为‘清和’、‘和静’、‘清淡’,不如归纳为‘淡和’之为宜。”⑳清人汪烜在《乐经律吕通解》卷一《乐记或问》中也有如下文字:“曰:‘五声皆乱,便不成声矣。然则郑卫之音不和律乎?’曰:‘不如此说。乐贵淡和,八风从律,其律便自淡和。不和固不是正乐,不淡亦不是正乐。’”㉑甚至上文提到的较具通变意识的江永也有类似观点:“故古乐难复,亦无容强复,但当于今乐中去其粗厉高急、繁促淫荡诸声,节奏纡徐,曲调和雅,稍近乎周子之所谓淡者焉,则所以欢畅神人、移风易俗者在此矣。”㉒事实上,对周敦颐“淡和”乐论思想的接受仅是明清乐论接受宋代乐论的一个缩影,经宋代新儒家改造过的传统儒家乐论由于其更贴近现实社会、更符合新的审美倾向,被明清两代乐论广泛接受。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认为,虽然明清两代乐论已经表现出鲜明的主情、尚俗、去神秘性的客观化色彩,但仍然无法决然抛开固有的文化“模子”,仍带有一定的不彻底性,但不管怎样,明清时期较之前代乐论毕竟在客观化层面有所突破,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评苏夏先生乐论文章 蒲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