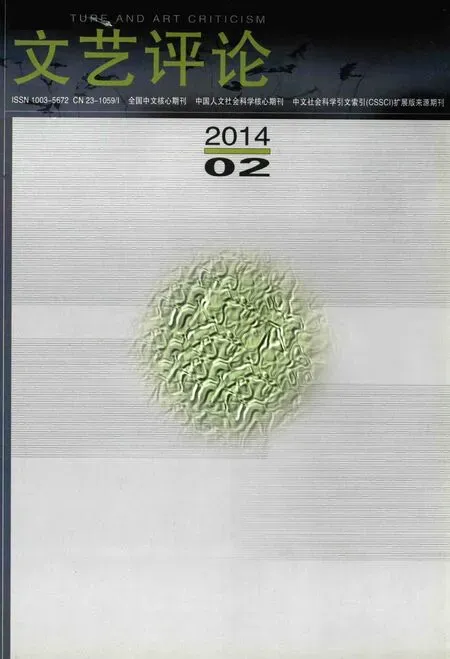苏轼以“余技”为词与词体之变
于东新 刘少坤
《四库全书总目》称:“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①四库馆臣看到词至苏轼为“两变”中的“一变”,而且直开辛弃疾一派,值得肯定。惜其只是从词风变化而言,故未能揭示“苏轼之变”的内涵、原因,小看了苏轼对词体革新的意义。其实,苏轼对词体的革新在于他把词当做文人的一种“余技”、一种“翰墨游戏”。这种“余技”治词的理念使“词”一变而成为了士大夫工作之余的娱乐品与消遣品。这种创作观念的变化促成了词的风格日趋多样化,促成了词体体制的日渐繁复与完备。
一、以“余技”为词的内涵
苏轼是第一个把词作为“文人余技”的,他在《题张子野诗集后》谈道:
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耳。《湖州西溪》云:“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与余和诗云:“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胡碟为春忙。”若此之类,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称其词。昔周昉画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欤!②
苏轼又在《书文与可画竹屏风赞》中谈到:
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③
苏辙《墨竹赋》谈到文与可创作的心态:“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崇竹矣。始予隐乎崇山之阳,庐乎修竹之林,视听漠然,无概乎予心,朝与竹乎为游,莫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④文与可与竹倾心而谈,心灵洞彻了竹之“神”,人与竹交融到一起,以至合二为一,就达到了庄子所说的“人蝶不分,梦觉难辨”的境界,故竹之神情即人之神情,人之神情亦为竹之神情,这就完全超出了社会功利之心。苏辙体悟到:“盖予闻之,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万物一理也,其所从为之者异尔,况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非耶?”⑤苏辙在这里正是从“万物一理”的角度解析了当时儒释道的融合,这种融合使当时的作家们深透物理,使作家们达到了物我两忘的超功利的精神境界。后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⑥苏轼肯定了文与可与苏辙二人的认识,赞美了文与可“墨戏”创作超功利的审美的态度。苏轼云:“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草木鱼虫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⑦苏轼关于词为“余技”的具体内涵并没有直接解释,而通过其对文与可墨竹的观念,我们能发现“余技”创作的内涵。苏轼的这种文人余事的态度是把词、书、画完全作为了文人的消遣品,是文人修养德行之余品味人性的深层次的体验,恰恰说明了苏轼超越了功利境界。
自魏晋以来,士大夫为文的观念虽已开始自觉,但总体没有超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⑧的汉儒强化的儒家说教,文学的地位没有摆脱统治阶级的附庸。这种附庸的地位一直持续到唐代。连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也不能超越,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更是一生事功心切。到了中唐时期,啖助、赵匡、韩愈等人怀疑汉儒所建立的经学体系,并率先重建“新春秋学”。这虽未从根本上动摇汉学的地位,但士大夫们开始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并重新审视先前的诗、文创作。到了宋代,日益繁荣的商品文化终于打破了诗、文作为教化工具的观念,打破了诗、文神圣的地位,遂引起了整个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⑨
莫砺锋等先生认为自宋代后,士大夫迥异于前代士大夫:
士大夫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斥的两极。前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大致可分为仕、隐二途,仕是为了兼济天下,隐是为了独善其身。这两者是不可兼容的。宋人则不然。宋代士人都有参政的热情,经科举考试而入仕是多数人的人生道路。入仕之后也大多能勤于政务,勇于言事。然而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比较宁静的心态,即使功业彪炳者也不例外。因为宋人已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一切事功仅是人格修养的外部表现而已。⑩
这种独立的文人身份,标志着文学、文化自觉的时代的到来。这种心态下使词的创作完全不同于唐五代以来一直到大小晏的创作观念,而有了质的变化、质的飞跃。可以说,苏轼更多的思考并实践了文人之所以为文人的最本质、最内在的东西。刘崇德先生则把士大夫变化的开始提前到韩愈,他认为,韩愈在《和席八十二韵》提出“多情怀酒伴,余事做诗人”的诗歌理论,有力地冲击了诗言志的观念。诗歌首先成了士大夫的余事,即士大夫闲暇之余舞文弄墨,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性。欧阳修承继韩愈对诗的态度,他在《六一诗话》中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做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⑪刘崇德先生又指出:
诗,历来被视为文章之首,故杜甫所谓‘名岂文章著’、‘文章千古事’、‘文章憎命达’,皆指其诗。而韩愈评李杜诗亦有‘李杜文章在’之语。而这里欧阳修却引韩愈‘余事做诗人’一语,揭出‘以诗为文章末事’,此可谓古来诗歌观念上的一大转变。诗既已为‘文章末事’、‘文人余事’,那么‘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沉重政治功利负担自然也就可以解脱了。不仅如此,欧阳修这里又将诗本身‘兴观群怨’的严肃诗旨转到了‘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的轻松的娱乐功能上。‘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这几乎如同谈梨园杂剧。此便是苏轼所谓的‘诗格之变自韩愈始’。‘诗格之变’首先在于诗歌观念的转变,当苏轼接替欧阳修文坛盟主地位时,更以‘文章如精金美玉’之说,淡化了文章的政治功能。……当苏黄这些文人去写那些‘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的作品时,诗也就由文学教化的‘千古事’沦为文人案头的翰墨游戏了。⑫
诗成了翰墨游戏,而“词”又为“诗人之余技”,“词”就更成了文人“翰墨游戏”中的“游戏”,那么词体所承载的政治功能更是微乎其微,完全成为文人的“消遣品”、“娱乐品”了。叶嘉莹先生也谈到:“当时的士大夫们,在为诗为文方面,既曾长久的受到了‘言志’与‘载道’之说的压抑,而今竟有一种歌辞之文体,使其写作时可以完全脱除‘言志’与‘载道’之压抑与束缚,而纯以游戏笔墨做任性的写作,遂使其久蕴于内心的某种幽微的浪漫的感情,得到了宣泄的机会。”⑬
这种游戏笔墨的态度促成了“文人好变”的一种思维习惯,而“好变”的思维习惯本质上是一种全面革新的理念,它本身不在乎能改变多少、能革新多少,而是把改变、把革新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思想贯穿于人的头脑中、贯穿于整个文学艺术的创作。这样的思维习惯,使创作者摆脱了文人集团或流派创作的脸谱化、程式化的弊端,自此以后,文人画(士夫画)、题画诗、词为文学艺术发展的创造一股清新的空气。这种勇气首先使我们折服,而开天下之先的尝试带来整个词学史的重大变化。
二、以“余技”为词的表现
从现存的唐代词来看,唐词尤其是敦煌词的内容、风格非常多样。而词发展到了五代,词体却形成了绮艳的单一风格,内容更是不出花间绮艳。这种单一的内容与风格发展到宋代,得到晏殊等人的承继,但很快就不再适应宋代日益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柳永、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则开始打破这种单一的风格。如果说柳永还是偶尔作一些出格的词、范仲淹只是偶尔为词,欧阳修开始从创作与理论上尝试打破单一绮艳的风格的话,苏轼就完全发展到了“翰墨游戏”的创作心态。他不仅从创作角度创作了许多风格多样的词,更是从词体批评的角度来改变词体单一的情况。
第一,打破了五代形成的绮艳的词乐体系。词体到了五代,词风趋于单一,王兆鹏认为温庭筠词对词体有定型之功⑭,单一化反而标志着词体趋于成熟。欧阳炯《花间集序》云:“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⑮孙光宪云:“(温)词有《金荃集》,盖取其香而软也。”⑯词体传统的形成,直接影响着后人创作以及对词体的认识与批评。由于唐五代词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是用来歌唱的,其音乐的风格与歌词应该是一致的,绮艳的歌词的程式化肯定也促成了词乐的程式化。这种程式化了的词乐也就是一套以歌者身份、表演乐器、旋律、观众身份为一体的音乐体系。从欧阳炯《花间集序》来看,“香径春风,红楼夜月”,可见当时的歌者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宁寻越艳,自锁嫦娥”,可见当时的观众多为富家子弟。这样的歌者与观众,也就决定了歌者需要与轻艳、香软的旋律来伴奏。
由于苏轼性情洒脱,任性自然,很快不满足于这种绮艳的单一色调,于是努力创新。他不仅借鉴诗歌、乐府的写法入词,借鉴当时的琴曲、民歌题材而创制诸多词牌,而且更在理论上为词体改革开路。
许多人说苏轼虽然学际天人,但不甚懂音乐,甚至给后人留下“三不如人”之说,其中之一就是音乐不如人,于是落下口实,很多人说苏词不可歌。史料上留下的几条“反证”是很难说服众人的。下面,不妨先列举一下这几条反证:
苏东坡词,人谓多不协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⑰
至晏元献、欧阳文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谐音律者。⑱
子瞻常自言“平生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于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⑲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⑳
其实,这个问题需要辩证的看待,由于词乐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柔婉的旋律、适合的乐器、与“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檀板”㉑的音乐体系。苏轼打破了这个音乐体系所能表演的范围,故十七八女郎用既有的音乐体系歌唱时感觉不协音律,甚至是很难听。苏轼自己也在致书鲜于子骏谈到:“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㉒他认为自己的词需要“东州壮士”“吹笛击鼓”“顿足”而歌,效果是“颇壮观”。俞文豹《吹剑续录》也载“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㉓而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长久形成的习惯力更是成了传统词家的嗤笑苏词的原因。故晁补之为之辩驳为“曲子中缚不住者”;胡寅为之辩驳:“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㉔;王灼为之辩驳:“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㉕《切韵序》(载在《广韵》卷首)谈到:“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相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㉖词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不可能要求作者达到像伯牙、子期那样神通的境地。而且音律精通者与可歌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故“人谓多不协律”,“世言东坡不能歌”,更或者是保守的词人与唱者不能接受苏轼对词体的革新。现在很多人认为苏轼对词体的贡献是“以诗为词”,其实,从根本上讲,苏轼的对词体的贡献是打破了“绮艳”词乐的的限制,使词乐可以歌唱各种风格、各种内容的词,让人感觉苏轼有“以诗为词”的主观动机。故所谓几条“反证”根本不能说明苏词不可歌,而是说苏词打破了长久以来绮艳香软的词乐体系,使人听之而“不谐音律”。
第二,强化了词的表现力。在唐、五代时期,词是当时的流行音乐,所以歌词只是音乐的附庸。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写作词时自觉或不自觉已经开始重视起歌词的审美性,甚至把自己的创作自诩为“诗客曲子词”㉗,但基于音乐需要的客观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
如果说欧阳修、范仲淹只是偶尔尝试新题材的话,那么,苏轼不仅超越了单纯创作上的尝试,而是大量的进行了创作,他隐括陶渊明《归去来辞》为〔哨遍〕,隐括周穆王与西王母之事为〔戚氏〕,集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诗句而为〔南乡子〕三首,更是首次把农村题材引入到词体中而为〔浣溪沙〕联章词五首。苏轼甚至直接提出了改变词体现状的理论:苏轼在《与蔡竟繁》书中谈到“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也。”㉘又在《答陈季常》书中谈到“又惠新词,句句警拔,此诗人之雄,非小词也。”㉙苏轼的这两句话强调的是自己所作词与当时其他人所作词不同,即苏词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题材范围由原来的专一艳情变为多种多样。故黄庭坚《跋东坡醉翁操》认为:“人谓东坡作此文,困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㉚胡寅评价之:“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㉛
值得说明的是,苏轼这里的“古人长短句”、“诗人之雄”与汉唐“诗言志”已是不同,前面已经讲到,自韩愈以来,更多的文人对诗的态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诗歌已成为文人之“余事”。苏轼的作法其实是降低了诗歌的教化地位而提高了词的文体地位,二者的鸿沟不再像五代时那么明显。
第三,在词调史上贡献莫大。苏轼的创作与贵族词很大不同在于创作态度。首先,贵族词限于词体传统功能,其词传统保守。贵族词认为词乃宴享时之俗乐,是宴享的工具,又因为他们生活在上层,基本难以接触到民间词,故不创作词语尘下的俚词,其所用词牌少的可怜,如晏殊只用了四十来个,而且其所用词牌有偏雅倾向,基本承袭晚唐五代以来宫廷所采用的比较雅驯的词牌。由于苏轼才分颇高、文化素养颇深,其写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出入经、史、子、集,徜徉琴、棋、书、画,俗典、俚语信手拈来,因此,苏轼打破了词的单一风格,一方面他大量使用俗词牌,如〔婆罗门〕、〔苏幕遮〕、〔定风波〕、〔念奴娇〕等,另一方面,他完全打破了词牌对内容的限制,词牌不再承担对内容的规范作用。这就跟“新乐府”一样,题名不与内容相同,甚至是相反,对词内容的介绍就变的越来越重要,词题、小序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苏轼第一个开始大量使用词题、小序的人,而其小序往往用散文化的笔法写创作时的环境、心态,本身就是一篇美文。这样,词题、小序成为了词体的构成部分,而且,有限的词牌可以抒写无限的内容题材,词的题材扩到了诗、文的范围,词体的抒情功能与表现领域无边界的扩大了。
苏轼还创制了很多新词牌,如他改编〔醉翁操〕、〔瑶池燕〕、〔昭君怨〕等琴曲为词,从大曲中摘取〔哨遍〕,还采用民歌体创制〔皂罗特髻〕,另外创制了〔贺新凉〕、〔翻香令〕、〔荷花媚〕、〔占春去〕、〔华清引〕、〔桃源忆故人〕等词牌。这种创新也影响到其弟子,如黄庭坚创制〔步蟾宫〕、〔逍遥乐〕、〔归田乐令〕、〔望江东〕、〔品令〕、〔鼓笛令〕、〔瑞鹤仙〕等;晁端礼创制〔金盏倒垂莲〕、〔庆寿光〕、〔黄鹂绕碧树〕等。
三、以“余技”为词的影响
由于苏轼的人格魅力与丰厚学养,他在整个宋代文化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宋代更多的人认可了这种创作态度,词论界多人承“余技”说,以词为诗人余事的观念开始泛滥,这种“余事”、“游戏”的创作理念流露出了士大夫的真性情、真人生。士大夫的思维开放了,眼界开阔了,他们积极地在日常生活、自然世界中寻找着创作的源泉,其创作理念得到了后来者的响应,深刻影响了后人的创作观念,更促成了词学理论的成熟。
第一,加快了词体向文学体裁的转变。词究竟是一种音乐体裁还是文学体裁,历来争论不休,后来学者采取一种折中的观点,把词归为“音乐的文学”㉜。事实上而从词体的演进历程来看,我们会发现词体是由一种通俗音乐渐变到一种与词乐脱离后的文学体裁。这种对词的统一定性的判断无疑是一种僵化的、有失客观的认识,因此是不准确的。其实,若考虑到词体的发展变化的轨迹,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分阶段定性的办法。而词体由音乐体裁过渡到文学体裁,苏轼正是变化的关键所在。
苏轼学究天人,以学养为词,他厉行改革,其词雅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最终形成了一种清旷的词风,苏轼及其弟子拓展歌词的内容,用多样化的风格作词,并以藉此来以词抒发个人性情,这种做法客观上促成了词与音乐的分离,使词开始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而被关注。靖康之变后,宫廷的乐师、乐器以及音乐文献被金朝兵将大量掠走,更是加速了词与乐的分离。虽然这种演变脱离了市井娱乐市场,但作为文人案头读物的趋势却越来越明显,这种剥离促成了词体发展的新阶段。苏轼拓展歌词的内容,并以藉此来以词抒发个人性情,这种做法客观上促成了词与音乐的分离,使词开始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而被关注。苏轼之后,词的风格日渐多样,姜张之清空、吴文英之密丽浓挚、辛弃疾之刚柔并济、奇思壮采无不使词体的文学表现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正是苏轼对词体的改革,才使词有了新的活力,词开始由一种音乐体裁向文学体裁转变,苏轼为后来词的创作者开启了无数法门,后起作者,沿着苏轼开拓的某一途径,继续深入下去,就足以“自成一家”,最终铸就了词亦为“一代之文学”的格局。
第二,促成了词体的“众体皆备”。苏轼的最大贡献不仅仅是他的创作丰厚而被后人景仰、学习,更在于他把文艺创新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理念、一种思想、一种行动指南加以贯穿,苏轼《超然台记》云“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㉝以致达到了“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㉞的境地,他鼓励弟子们要善于发现,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文学艺术不竭的源泉。所以苏门弟子学习苏轼而不为苏轼所拘泥,每个人秉承自己的性格、学养、经历而各自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文人余事”的观念没有丝毫规定词体内容、风格、语言等写作的具体要求,而只是强调用一种超功利的心态去创作。苏轼的门生弟子们通过这种超功利的心态,创作出不同的词风。他们学苏而不似苏,根本原因就是“文人余技”的创作思想,这种创作思想避免了词体走向脸谱化、程式化。如秦观词“妍丽丰逸”㉟,张炎评之曰:“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㊱。黄庭坚词风格多样,有雅有俗,雅者似诗,俗者近曲,亦庄亦谐,且颇喜艳词。
词体发展到南宋,更是日渐繁复,词之各体兼备:咏物词、咏史词、爱国词等都大张旗鼓,得到更多的人极力的推崇,以诗为词、以学问为词、以议论为词,词到文人手里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境地。词的内容含量的变化也促使词的体式变化。如长调慢词开始兴盛。小令在五代时已达到顶峰,晏殊沿袭,只能是在一些微小之处再下功夫。长调慢词善于铺叙的特点使词的内容含量扩大。长调慢词含量的扩大,又促使词体摆脱了单纯的宴席间的谐谑。柳永第一个开始大量创作长调慢词,继柳永之后,苏轼第二个开始大量写长调慢词,继苏轼者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张炎等,更是发挥了长调慢词的善于铺叙、长于言情的特点。
总之,苏轼虽自谦词为小道,但是,这种观念适应了日渐丰富发达的市民文化发展,更适应了宋代民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含蕴丰富的风格与特点似乎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这种“新词体”的创作,词体开始了全新的变化,一步步走向高峰。
第三,词学理论的日渐成熟。由于苏轼极力打破词体单一的风格,从多方面对词体进行改革,词学理论开始极大丰富,并逐步完善。首先,词学观念的争锋促成了对词体认识的深入。苏轼有意的提升词体地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领域与抒情范围的做法,很快引来许多人支持,如黄庭坚《小山词序》:“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㊲罗泌《欧阳文公近体乐府跋》谓欧阳修“吟咏之余,溢为歌词”㊳;孙兢《竹坡长短句序》认为:“竹坡先生少慕张右史而师之。稍长,从李姑溪游。与之上下其议论,由是尽得前辈作文关纽,其大者固已掀揭汉唐,凌历骚雅,烨然名一世矣。至其嬉笑之余,溢为乐章,则清丽婉曲,是岂苦心刻意而为之者哉?”㊴关注《题石林词》谓叶梦得“翰墨之余,作为歌词。”㊵陆游《后山居上长短句跋》亦认为:“唐宋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凡汉魏。陈无已诗妙天下,以其余作词,宜其工矣,顾乃不然,殆未易晓也。”㊶赵与訔《白石道人歌曲跋》谈到:“歌曲,特文人余事耳,或者少谐音律。白石留心学古,有志雅乐,如《会要》所载,奉常所录,未能尽见也,声文之美,概具此编。”㊷连元代钟嗣成在其元曲著作《录鬼簿》中亦云戏曲:“乐府歌曲,特余事耳。”㊸可见这种“余事”、“余技”创作观念影响之深远。
苏轼力行改革的做法也遭到了一些比较守旧的词人的批评,如陈师道批评曰:“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㊹李清照批评:“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㊺沈义父《乐府指迷》标举写词圣手周邦彦,张炎《词源》则标举新词人姜夔,都是从词体内部特点而归结的。正是在对苏轼对词体进行革新的批评与赞扬的交锋中,词学家们对词的风格、样式、题材进入更加深入的辨析与认识,客观上更加快了词学理论日渐丰富。到了清代还形成了一场范围颇广、历时颇久的诗词之辨。
其次,促进了词学理论专著的出现。词体若停滞于五代形成的绮艳风格而不变,充其量也就是一种流行音乐,不可能形成系统而深入的词学理论专。蔡嵩云谈到:“两宋词学,盛极一时,其间作者如林,而论词之书,实不多观。可目为词学专著者,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陆辅之《词旨》。”㊻其中,王灼《碧鸡漫志》完全是用诗歌的理论解释词的发生、发展,尤其指出了苏轼在词体中的贡献,一定程度上说,王灼就是在为苏轼的创作观树立理论。而张炎的《词源》,虽没有直接谈他词学渊源,但从其所评论的词人来看,张炎《词源》下卷以“清空骚雅”为标准准共评论作家24位,作品45首(重复者不计),评论频率较高的词人姜夔8次10首,苏轼5次8首,史达祖3次5首,秦观3次2首,周邦彦3次2首,吴文英3次4首(其中一首被张炎否定);评论频率较高的词作姜夔〔疏影〕5次,〔暗香〕4次,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3次,〔洞仙歌〕2次,姜夔〔扬州慢〕2次,史达祖〔东风第一枝〕《咏春雪》2次,〔绮罗香〕《咏春雨》2次。苏轼排在了第二位。张炎又曰:“东坡词如〔水龙吟〕《咏杨花》、《咏闻笛》,又如〔过秦楼〕、〔洞仙歌〕、〔卜算子〕等作,皆清丽舒徐,高出人表。〔哨遍〕一曲,隐括《归去来辞》,更是精妙,周、秦诸人所不能到。”㊼可见张炎虽没有直接谈其词学渊源是苏轼,但这并不能否定他对苏轼的承继。因为清空需要学识涵养,并通过超功利的创作观念来实现却是不二法门。
再次,促成了词派出现。由于欧苏文人集团大开词体发展之门,后人多沿其一路发展,形成了不同的词派。辛弃疾等人学苏之淸雄,形成了南宋中后期著名的“辛派”。姜夔、张炎等人学苏之清丽,并受当时的诗学思想影响,创制了“清空”、“骚雅”等独立的词学范畴,到了清代,朱彝尊等人更是依“清空”词学范畴而形成影响深远的“浙西词派”。正是因为苏轼从多方面对词体进行革新,才使更多的词人关注词体的发展与变化。词学理论日渐繁复与系统,最后形成宋代的词学大观。
综上,在词学发展史上,苏轼有着特殊而重大的贡献,“文人余技”的创作观念打破了词体单纯作为流行音乐的传统观念,他极力拓展歌词的内容,并以藉此来以词抒发个人性情,增强了词体的表现力,他还完全打破了词牌对词内容的限制。他影响了后人的创作观念,并促进了词学理论的成熟,给整个词坛带了质的变化。苏轼在词体演进过程中的功劳莫大,自此以后,词体开始了多样化发展,走上了康庄大道,最终形成了“一代之文学”的壮观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