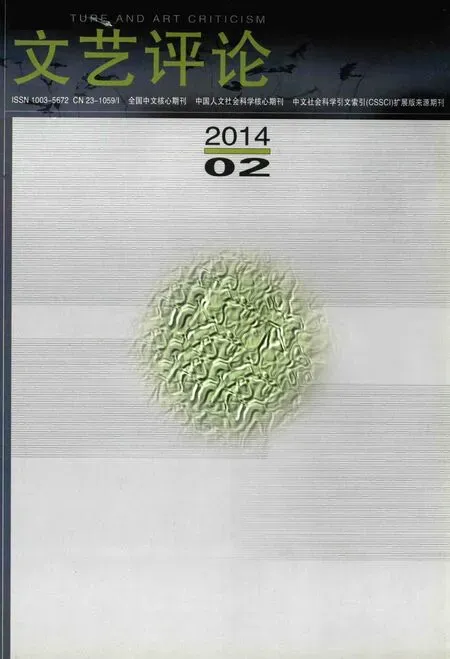儒家“天命有德”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
王以兴
中国儒家天命观中有一个非常积极进步的思想,即认为上天是公正无私的,只有那些有德的君主才能得到天命的辅佐,用《尚书·皋陶谟》中的话就是“天命有德”①。然而今天学术界对《三国志通俗演义》②中天命观的研究,均停留在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上,如刘孝严《〈三国演义〉的天命观》总结小说中的天命观有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宿命夭定等③;李培建、曾良《论〈三国演义〉中的天命观》一文从命由天定、天命可知不可违、天人合一和天命转移等方面探讨《三国演义》中的天命观,其实与刘文总结基本一致,只是更为细致和有条理性④。而魏孔玉《〈三国演义〉中的天命观探析》则讨论天命观对文本叙事所起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悲剧气氛的渲染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⑤由于作者将天命观仅仅看作是一种宿命论,因此在解释天命观对《演义》叙事影响时显得单薄不够全面。李培建、曾良在对《三国演义》中天命观总结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讨了天命观覆盖下的《三国演义》的叙事机制,试图构建起一个系统完整的天命叙事机制”。⑥该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阐述:第一、天命观对《三国演义》叙事情节发生、发展和结局的统摄引领作用;第二、天命与人事的照应方面,包括人物命运和军事战争的描写。然而文章作者对天命观的界定仍不出“天人感应”、命由天定和梦兆休徵等范围。
其实,“天命有德”思想才是《三国演义》天命观中最重要、也是对小说叙述影响最为直接的理论支柱。因为,作为一部具有宏大历史题材和严肃主题表达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对历史兴衰和朝代更替表现出来极大的关注和热情。而“天命有德”作为一种政治伦理观,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精髓所在,同时也是儒家对朝代兴衰演变的理论说明,从这个角度看,“天命有德”作为《三国演义》历史叙述的理论支撑是非常合宜的。在下文的论述中,我们会发现诸如天人合一、谶纬神学及梦兆符瑞等天命观均是以“天命有德“为中心并服务于后者的,而且在“天命有德”视角下也会对“拥刘反曹”和曹魏建国等问题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一、“天命有德”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和影响
“天命有德”最早产生于周初统治者借上天的权威来论证自己政权合法性的功利性需要。周朝本是殷商诸侯国,那么武王的伐纣兴周实际就是以下犯上、逆反叛乱。因此,周朝建国之初统治者需要为这种造反行为寻找一个理论依据,而在当时只有把原来专属于殷商的一家之神改造成为公正无私的共有之神,然后向臣民宣告自己的统治是因德行承天神之命而来,才能稳固新生政权。先秦时期“天命有德”思想十分普遍,有各种不同的表述。比如《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⑦《左传·僖公五年》引有此句云:“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紧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⑧《左传·宣公三年》则云:“天祚明德。”⑨屈原《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朱熹对此解释说:“犹言惟德是辅也。言皇天神明,无所私阿,观民之德,有圣贤者,则置其辅助之力,而立以为君也。”⑩王逸和洪兴祖的解释与朱熹意义全同,兹不赘述。⑪《尚书·康诰》则直接点明文王德行“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⑫这些说法都可以用“天命有德”来简单概括。西汉董仲舒正是在先秦“天命有德”思想基础上结合五行学说等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由于西汉以降儒家成为封建社会之正统思想,“天命有德”也随之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唐颜师古注《汉书》就提到“天命无常,归于有德”⑬和“天命无常,唯善是佑”⑭。《南齐书·高祖本纪》亦云:“朕闻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无常,惟德是与。”⑮由此可见,“天命有德”在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天命有德”并非纯粹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其本质是一种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儒家政治伦理观。虽然周朝统治者宣扬自己的政权受命于天,但这只是借助上天的无尚权威性和神秘性来维护政权的稳定,而“天命有德”最终的落脚点却是在“德”上。《尚书》中多次明确讲到为君者要敬德为民,比如《大禹谟》记大禹之言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⑯《盘庚上》则云:“施实德于民。”⑰因此,“天命有德”之“德”实为养民、惠民的民本政策,而“有德”即指那些能够做到实施德政、仁政的人间君主。如此一来,天意即是民意,天命即是民命了。正如《尚书·泰誓中》记武王在誓师大会上宣言伐纣是上天旨意,而上天旨意又以民意为转移,他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⑱《皋陶谟》亦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⑲这两句话意思是说上天对人间君王的判断以人民百姓的判断为标准。在《尚书》中这种得民心得天下、失民心而失天下的论调可以说弥漫全书。故而可知,“天命”只是幌子,而民心民意才是根本,也即是说“天命有德”可以换作“民命有德”。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左传·桓公六年》云:“上思利民,忠也……夫民,神之主也。”⑳而孟子的“仁政”思想更与“天命有德”本质内涵相一致,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和“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等。范晔《后汉书》分别记有“天命无常,百姓与能”(《公孙述传》)和“天道无亲,百姓与能”(《皇甫嵩传》)之语。《贞观治要》记贞观六年(632)魏征用舟与水的关系比喻君与民的关系,他引古语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㉑此言来自《荀子》中《王制篇》和《哀公篇》。明太祖朱元璋在攻取处州后,征聘了刘基、叶琛、宋濂和章溢,曾向章溢请教如何统一天下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是:“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㉒诸如此类实际都是对“天命有德”中“德”的积极阐发和把握。
总之,“天命有德”表面上看是一种唯心主义天命观,这是由于周朝统治者在借助上天的权威为自己因爱民而夺取殷商天下这样的事实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实质上它包含着十分进步的意义,对“德”即民本思想的强调,说明上天与君王的关系本质上是人民与君王的关系,这就使得君王能够充分认识到努力施德于民才是在天人关系中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另外,由于中国古代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皇权至上是其突出特点,因此君主是否“有德”即能否施行德政、仁政,关键在于君主个人的品行和意愿如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君主的个人道德品行直接就等同于其政治作为。这一点不可不察。
二、“天命有德”在《三国演义》中的表述
由上可知,“天命有德”对中国古代政治生活起码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和价值。一是借天命的幌子来稳定新生政权或者作为造反夺权行动的宣传口号;二是使得后来君王懂得民心民意对于国家政权的重要性。《三国演义》对此有着具体而丰富的表述,可以看出罗贯中对“天命有德”的情有独钟。
自始至终,“天命有德”都被《三国演义》中各路英雄抬出来作为自己争夺刘汉天下的理论依据。《司徒王允说貂蝉》一则中王允在家宴上假意奉承董卓说:“太师功德振于天下,若舜之受尧,禹之继舜,正合天心人意。”王允正是借“天命有德”来恭维董卓,获得了后者的极大欢心。董卓也默认了自己的野心,但仍需要借天命来做挡箭牌:“果然天命归吾,司徒当为元勋。”可见,“天命有德”观念在二人心目中的地位!而“袁术在淮南,地广粮多,克取于民,仓库盈满;又有孙策所当玉玺,遂议称帝”,他在大会群臣时打出的招牌也是“天命有德”:“吾家四世公卿,百姓所归,吾欲应天顺明,位登九五。”主薄阎象反对的理由也是从“天命有德”的角度立论的。(《袁术七路下徐州》)这是两个明明无德却要逆天而为的例子,自然以失败结局。
后来曹丕篡汉受禅时禅册中的“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废献帝曹丕篡汉》)和王朗口中的“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于有德之人,此定然之理也”(《孔明祁山破曹真》)则是“天命有德”的同义句。王朗在上面一句话后接着对诸葛亮说:“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里倾心,四方仰德,非权势而取之,实乃天命所归也。”可见,曹魏集团也是借“天命有德”作为行动的理论依据。
贾充逼魏主曹奂退位时同样以“天命有德”为据:“今天禄永终,天命在晋。司马氏功德弥隆,极天际地,可即皇帝位,以绍魏统。”(《司马复夺受禅台》)而“古者以天下为公,惟贤是与”的作者评语就是“天命有德”的同义转述。《汉中王成都称帝》一则更是“天命有德”思想的形象演绎,渔翁张嘉捕鱼得一玉玺,“上篆八字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嘉大喜,素知汉中王仁德布于天下,遂密入成都,到孔明府献之。”谯周也将祥云庆云盘旋而下、黄气冲霄而起、帝星出现作为“天命有德”的祥瑞征兆看待。而孙权称帝时向天告祝,其中“休徵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诸葛亮三出祁山》)等表达的也是“天命有德”意思。
“天命有德”在《三国演义》中频繁出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同时也说明罗贯中已经充分认识到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除以上对“天命有德”的直接表述外,作者还用“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来表达对“天命有德”之积极意义即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认识和把握。这句话源自《吕氏春秋》和相传姜尚所作的《六韬》。《吕氏春秋·贵公篇》:“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㉓《六韬》中《文韬·文师》和《武韬·发启》亦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之语。但该句话更完整的表达应该是《武韬·顺启》所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㉔“有道者”即“有德者”,意思即是说天下是天下人所共有的,只有那些品行高尚得民心者人才有资格治理天下。与“天命有德”相比,这句话强调的是“有道者”坐拥天下的主动性。因此,这句话正是对“天命有德”积极意义的准确把握。该句话在《三国演义》中以相似的面貌出现达七次之多,意义非凡。它们分别是: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司徒王允说貂蝉》中王允对董卓之言)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诸葛亮舌战群儒》中吴国谋士薛综对诸葛亮之言)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周瑜南郡战曹仁》中诸葛亮对周瑜之言)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周瑜定计取荆州》中诸葛亮对鲁肃之言)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废献帝曹丕篡汉》中华歆对汉献帝之言)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张永年反难杨修》中张松对诸葛亮、刘备之言:)
“天上地下,为有德者居之。”(《关云长单刀赴会》中周仓对鲁肃之言)
这七次分别出自于魏蜀吴三家之口,说明对“天命有德”中“德”的重视是当时政治人物的共识。另外,邓芝出使吴国时对孙权曾说:“大王未识天命所归何人。但为君者,各修其德;为臣者,各尽其忠。”(《难张温秦宓论天》)张纮哀书中劝诫孙权要任用贤臣以修“德政”(《曹操兴兵下江南》)还有刘备那段著名的与曹操相对的行政宣言及被习凿齿评为刘备“第一件好处”(《诸葛亮火烧新野》)的不弃十万百姓之事等,这些也都是说明了他们已经认识到只有修德为民才是一统天下的正道。
总之,“天命有德”在《三国演义》中分布广泛,贯穿始终,反映了罗贯中对这种观念的尊重和认可。“天命有德”不仅是各个政治军事集团借以为自己争霸行为做掩护的合法外衣和神秘招牌,也是有识之士、开明之君所信奉和秉持的一种进步政治伦理观。作者不仅在小说中对“天命有德”进行了反复的凸显,更重要的是,他还将“天命有德”作为《三国演义》整个历史叙述的内在依据,目的则在于通过对三国归晋这段历史的主观化叙述来论证“天命有德”实际具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性质和意义。
三、“天命有德”对《三国演义》历史叙述的统摄作用
罗贯中对“天命有德”的信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将其作为小说的内在行文依据,即《三国演义》整个历史叙述都是在“天命有德”的统摄下进行和完成的。这是因为罗贯中对这段纷繁复杂、波诡云谲的风云历史并非只是简单地做通俗讲述,其目的不是普及历史知识,而是利用通俗化的小说形式对“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进行主观化叙述,以论证“天命有德”实际具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性质和意义。笔者所谓的对历史的主观化叙述,是指作者按照自己的旨趣、认识和目的等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新选择、整合甚至虚构、夸张,强调作者对素材处理的主动性,用清人觚庵的话说就是“虽无一事不本史乘,实无一语未经陶冶”㉕。虽然自明朝至今,学者对“演义”之“义”为何众说纷纭均莫衷一是,但这充分说明了《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丰富性,而笔者所云的罗贯中将“天命有德”作为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理解和把握实际也是所演之“义”中的一种。
“天命有德”对《三国演义》历史叙述的统摄表现,简单来说就是汉末皇帝因败德而天命不振,导致天下大乱各路英雄逐鹿中原,魏蜀吴三国的建立是因为曹丕(准确地说是曹操)、刘备和孙权每个人根据各自的德行只堪承受汉家天命的三分之一,而最后三国归晋天下一统则是晋主之仁德足以完全承天命。
《三国演义》开篇就写到桓帝去世,年仅十二岁的灵帝即位,朝政大权被宦官所包揽。所以上天震怒,不断地通过灾异向汉家天子警示:朝廷惊现大蛇、雷雨冰雹、洛阳地震、海水泛滥、雌鸡化雄,“种种不祥,非止一端”。虽然蔡邕上疏讲明了此“乃妇寺干政之所致”,但是灵帝仍然重用张让等“十常侍”:“朝廷侍十人如师父,由是出入宫闱,稍无忌惮,府第依宫院盖造不题。”显然,罗贯中将这些不祥之兆出现的原因归结到最高统治者灵帝身上,用《尚书》中的话说就是“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汤誓》)㉖、“商罪贯盈,天命诛之”(《泰誓上》)㉗,正是“天命有德”的反面。书中这种灾兆描写则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具体表现。董仲舒认为“天道”与人事是相呼应的,他在《贤良对策》中说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本质上与“天命有德”仍是一致的,不过浸染了更多的神学色彩。罗贯中多次用“天数”“气数”“天意”等申明了刘汉因君王德行不修而导致天命不永难以挽回。比如在《何进谋杀十常侍》一则中引史官叹何进无谋:“汉室倾危天数尽,无谋何进作三公。”在《虎牢关三战吕布》一则中引古风云:“汉朝天数当恒、灵,炎炎红日将西倾。”《曹孟德刺杀董卓》中曹操自叹刺杀董卓不成“乃天意也!”《迁銮舆曹操秉政》中侍中太史令王立曾观天象,发现“大汉气数终矣”,并密奏献帝说:“天命又去就,五行不常盛。”而在《耿纪韦晃讨曹操》中耿纪和韦晃密谋杀曹扶汉,可惜不能成功,作者引诗曰:“耿纪精忠韦晃贤,各持空手欲扶天。谁知汉祚相将尽,恨满心胸丧九泉。”。总之,所谓“天意”、“天命”如此等等,最根本原因在于汉家天子的败德无行。
而后,各路诸侯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逐渐被吞并消灭,剩下的刘备、曹操和孙权三家“各据汉地为三国”(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他们的不同结局取决于各自的德行厚薄。其中失败者如董卓、袁术,他们残忍暴虐、倒行逆施却想称帝为王,最终落得个惨死的下场。在罗贯中看来,魏蜀吴三家称帝其实是汉家天命继续衰落不振的表现。汉家天命的中大部分已经转移到曹魏和孙吴一边,而剩下的一部分则继续留在刘备身上,也就是说君王德行有厚薄、天命随之有大小。这样一来,罗贯中就把魏蜀吴三国的建立也拉拢在“天命有德”统罩之下了。蜀汉政权自不用多说,刘备“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诸葛亮语),是维系汉家天命的仁德之君。《刘玄德遇司马徽》中司马徽向刘备解释诸郡小儿谣言:“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到头天命有所归,泥中蟠龙向天飞。”其中,“天命有所归”就应在刘备身上,所以后来刘备成都称帝就是“天命不可不答”(《汉中王成都称帝》)。但刘备德行尚不足以恢复刘汉大一统的局面,司马徽得知刘备要请诸葛亮的出山时,仰天大笑:“虽卧龙得其主,不得其时。”“不得其时”是指汉家天下因德行亏损太多而无法挽回了。孙吴一方较其他两家处于次要地位,因此描述得也相对简单。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割据江东,他招贤纳士、任人唯贤,在孙策死后很快就稳定了局面,“自孙权威震江东,乃深得民心。”(《孙权领众据江东》)他听从周瑜劝告没有入朝为官,而是“韬略扛威,以待天命”(《孙权跨江破黄祖》),最后终于得到了天命的眷顾,在“武昌东山,凤凰来仪;大江之中,黄龙累现”(《诸葛亮三出祁山》)的祥瑞中祭天称帝。
事实上,罗贯中对曹操的形象塑造更能体现出他以“天命有德”作为《三国演义》历史叙述之内在根据的用心。作为一名传统的儒家读书人,罗贯中固有的正统思想及“拥刘反曹”的政治情感必然使得他最不愿意看到曹丕继承曹操之功业而篡汉称帝。作者对曹操的狡诈、不择手段和心胸狭窄等人品方面的缺陷,尤其是政治上的欺君罔上进行了极力批判和指斥。《曹操勒死董贵妃》和《曹操杖杀伏皇后》二则记叙曹操以下犯上大逆不道之事。对于后者,书中有小字注云:“此是曹操平生最不是处。”而作者则直接引诗评曰:“献帝当时何太懦,曹瞒得志弄威权。……华歆、郗虑儿曹辈,同恶相滋逆上天。”㉘由此可见作者对曹操的不满和痛恨。但历史作为既定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曹操也毕竟是魏国的实际奠基人,无奈之下作者也只能以“天命有德”为标准对曹魏建国一事进行衡量。曹操自称:“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此语源自《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朱熹也曾说过:“其(周朝)受天命而有天下,则自文王始也”(《孟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上》),所以尽管罗贯中对此感到愤慨:“操欲篡位久矣,犹畏其名而不敢行,故言愿为周文王也。”(引司马光语)但他仍不得不对其“有德”一面进行违心的刻画、评说以证明魏国受天命而有天下,则自曹操始。比如罗贯中引裴松之注对曹操放关羽归刘备一事进行评说:“曹公知公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氏之休美!”而宋贤诗后亦有小字注曰:“此言曹公平生好处,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的曹公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关云长千里独行》)尤其是《曹操乌巢烧粮草》一则中写曹操大败袁绍后将自己部下之前与袁绍私通的信件通通烧毁,此事出自《三国志·魏太祖本纪》,罗贯中引诗对此表示了赞赏:“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此句下有小字注云:“此言曹公能牢笼天下之人,因而的天下也。”章培恒、马美信两位先生曾说过:“凡是史料上所有的、能够显示出曹操‘好处’的事迹,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基本上都加以描写,有些并作了艺术夸张;同时,他还以一些虚构的情节来赞扬曹操。”㉙并举曹操破下邳、杀陈宫为例进行说明,在罗贯中笔下,当曹兵攻入下邳时,曹操就“差人入城,不许劫掠良民”,而这个命令在史料上没有根据,是作者的虚构自造;而曹操也不想杀陈宫,然陈宫却甘愿以死殉义,这时,“操与从者曰:‘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吾府中恩养,怠慢者斩。’后曹公养其母,嫁其女,待之深厚,此乃曹公之德也。”(《白门曹操斩吕布》)总之,即使罗贯中再痛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欺君罔上和曹丕的篡汉自立,仍要尽量渲染甚至虚构曹操仁德的一面。如此一来,曹魏的建国也是“天命有德”的合法事实了。
三国鼎立局面虽已形成,但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兼并其他两国以统一天下。而在蜀汉的刘备和诸葛亮,吴国的孙权、孙亮和孙休,魏国的曹丕、曹睿和曹芳相继辞世后,谁能最终将三家各自的天命合而为一从而一统天下就关键看蜀汉后主刘禅、吴国孙皓和魏国曹奂三人中谁的仁心最宅厚、德政施行最彻底。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任意胡为,宠信宦官黄皓,朝政日非,以致天命不再汉室彻底败亡,正如作者引诗所云:“后主昏迷汉祚颠,天差邓艾取西川。”(《诸葛瞻大战邓艾》)孙皓即位为吴主后,“凶暴日盛,酷溺酒色,大小失望”(《羊祜病中荐杜预》),以至“凡饮宴,必令群臣大醉;却立黄门郎十人纠弹,若有过失者,或剥其面皮,或凿其眼睛”(同上)。而“此时魏主曹奂,名为天子,实不能主张,皆由司马氏为之。”(《司马复夺受禅台》)比较之下司马炎则“恢弘大度,容纳直言;明达善谋,能断大事”(同上)。所以司马氏代魏兴晋在作者看来正是史官所评的“古者以天下为公,惟贤是与”(《司马复夺受禅台》),而晋朝吞并吴国统一全国则实乃“有道代无道,无德让有德”(《司徒王允说貂蝉》中王允对董卓语)罢了。在上面笔者提到君主的“有德”与否关键看其个性品行和意愿如何,所以此处罗贯中对刘禅、孙皓和司马炎不同品行修养的对比描写,可以看出作者是在刻意说明天命予夺的合理性,也即是借“天命有德”来解释晋朝的一统天下。
由上所述,《三国演义》的整个历史叙述是在“天命有德”的统摄之下完成的。一言以蔽之,作者罗贯中描述的就是刘汉一统之天命向司马晋朝一统之天命转移的历史过程,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即三国鼎立时期,而天命的这一转移变化则直接取决于人间君主的德行如何。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书中随处可见的“天数”、“天意”、“气数”等表达以及休徵祥瑞等描写其实是服务和附庸于“天命有德”思想和情景叙述的。这样,我们也就不会随意地认定“小说中‘天命’、‘天数’、‘天运’、‘定数’等描写,是对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解释”㉚了。因此,如果对《三国演义》做整体观照的话,从天命观角度看就是天命的“一”——“多”——“一”的转化;从国家政权的角度看就是天下的合——分——合的趋向。二者若和符契如影随形,而以人间君主的德行盈亏厚薄为粘合剂。至此,“天命有德”在《三国演义》中的叙事意义即对整个历史叙述的统摄作用就表现得十分清楚了。
三、结语
“天命有德”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史上,不仅是简单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天命观,还是一种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政治伦理观。它在我国古带政治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清晰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强调了统治者德行及德政在国家政权中的积极作用。对此,作为被正统士大夫视为“小道”的小说,《三国演义》却成了“天命有德”思想集中展示的舞台,书中人物动辄以“天命有德”作为行动口号,也表达了对该思想的本质认识。更重要的是,作者还借“天命有德”来观照这段令人惊心动魄的风云历史,这也就赋予了它统摄整个历史叙述的叙事意义。或者说,罗贯中实际也是在借“天命”之权威来说明和论证“有德”者据天下实乃一种正常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因为“天命有德”本身就是统治者从天命观角度对历史兴亡、朝代更替所作的唯心解释,当然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罗贯中则特地用小说形式对这种合理性进行绝对化。从上面第三部分中作者所引史评、后人诗歌和对兴国之君、亡国之君德行厚薄的对比刻画及对曹操仁德方面的赞扬等主观化叙述上,我们对此可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结合“有志图王者”的作者身份和当时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我们也能深刻体会到罗贯中略带理想化的儒家道德情怀和用世之心是多么得强烈!另外,如上所述罗贯中对这段历史的主观化叙述,目的是将“天命有德”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待,这无疑极大提升了《三国演义》的文化品格,使之具有了司马迁创作《史记》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的伟大气魄。这也许就是自《三国演义》之后历史小说的创作虽然蔚然成风,却没有一部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的一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