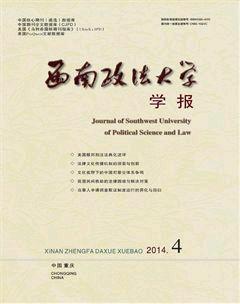美国联邦刑法法典化述评
摘要:美国联邦尚无刑法典,然自建国后,联邦一直致力于刑法法典化,从1790年《治罪法》至1948年《联邦法典》第18主题,到1982年《联邦刑法典草案》,长达200多年的刑法法典化事业至今未竟。联邦刑法法典化呈现独有品性,即启于内外因素双重驱动、历经形式编纂到实质编纂、本体即权力扩张与限制、价值思维系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统合。联邦刑法法典化目的理性,其搁浅缘于工具不善。基于现有刑法不力、刑法治危机以及刑法典的天然优势之事实,结合刑法有效、公正、人道之目的,得以推导出刑法法典化仍需继续之应然结论。未来,联邦刑法法典化之路仍旧遍地荆棘,而联邦刑法典能否问世,取决于美国所动用的实践理性。
关键词:美国;联邦刑法;法典化;刑法渊源
中图分类号:DF0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4.04.01
美国系普通法系的核心成员,法官造法、遵循先例是美国法之精髓及身份标识。常人可能理所当然地以为判例法在美国法中独照鳌头,而事实并非如此,制定法是美国法中能够与判例法并驾齐驱的法律渊源,特别是在联邦刑法领域,制定法几乎构成了刑法渊源的全部。为了刑法治理想、践行合法制原则,联邦几乎用了与美国历史同样长的时间践行刑法法典化法典编纂分为实质性及形式性两种,前者以构建或修正某一法律秩序为目的,塑造由规则组成的完整的法律体系,后者即将既有的、分散的规则汇集,而不改变规则的内容。一般认为,真正的法典是实质性法典编纂的成果,形式性法典编纂实为法律汇编。本文的法典化包括实质性及形式性的法典编纂活动。,但至今仍未颁布刑法典,且刑法法典化遭遇瓶颈、难为再续,联邦刑法典命运未卜。了解联邦刑法法典化历史、阐析联邦刑法法典化搁浅之事实、判断联邦刑法法典化之于刑法治之价值,是推导联邦刑法法典化应该与否、何以可能之必要步骤。
一、联邦刑法法典化之缘起作为殖民的附属,北美殖民地自然继受英国法。“唯有英国能够为北美殖民地提供无需转换的法律。”[1]美国成为普通法系的核心成员,法官造法、遵循先例是其精髓及身份标识。英国普通法在美国法律成型实践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但自美国改造英国普通法始,制定法地位日愈凸显,成就了美国法特色以及其对宗主国法的超越。“美国法律史是一部法典化的奋斗史。”[2]在刑事法领域,制定法地位尤为显赫,美国独立后,联邦迅速地否弃了普通法罪,确立了合法制原则。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其宪政理念根深蒂固,任何法律的正当性须溯源于宪法,刑法亦是如此。
(一)联邦刑法的宪法基础
美国共有包括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及联邦在内的52个司法辖区,它们相对独立,均有各自的法律系统、刑事司法制度。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分配来源于《联邦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宪法》修正案第10条规定,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分别由各州或由人民保留。据此,联邦政府为被授权机构,其权力仅限于宪法明文列举之列,而州政府拥有未让渡给联邦及未被宪法禁止一切权力。
《宪法》授予国会立法权,并基本框定其范围。《宪法》第1条第1款规定:本宪法所授予的全部立法权均属于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在刑事立法方面,国会享有宪法明文列举的立法权包括制定关于伪造合众国证券和流通货币的惩罚规则、规定和惩罚在公海中所犯的海盗罪与重罪以及违犯国际公法之罪、宣告和惩罚叛国罪。
但《宪法》授予国会的立法权并非足够明确,因为,《宪法》第1条第8款规定,国会拥有的权力包括制定为执行以上各项权力和依据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政府中任何机关或官员的其他一切权力所必要的和恰当的法律。此规定被视为国会立法权的“默示条款”,实际为国会原本狭窄的立法空间打开了一扇后门。不过,《宪法》对于国会刑事立法又作出一些特别限制。 《宪法》第1条第9款规定,不得通过公民权利剥夺法案或追溯既往的法律。《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
《宪法》明确规定了极少数的犯罪,包括弹劾罪(第1条第3款)、公海上所犯的海盗罪与重罪以及违反国际法的犯罪(第1条第8款)、叛国罪(第3条第3款规定)。
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州际流动性的扩大,国会利用立法默示权制定了大量关于商务、征税、战争、公民权利及管理邮政的“必要及适当”联邦刑法,联邦刑事管辖权亦不断扩大。
(二)普通法罪之否弃及“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原则的确立
联邦宪法规定的犯罪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传统犯罪未被纳及,在联邦管辖范围内发生的、未被宪法规定且无国会制定刑法的危害行为可否依据普通法罪审理,引发长期激烈的争论。
普通法罪(common law crime),亦称法官创立的罪,由于早期的英国国会很少制定法律,法官遇到无法律规定的危害行为,可根据习惯及法理认定犯罪并科以刑罚。法官所认定的犯罪的定义于司法实践中逐渐精确并固定,形成了普通法罪。北美殖民地继受英国普通法时,大量吸收了普通法罪,但美国独立后,普通法罪在联邦司法中的正当性就成为了问题。宏观而言,美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适用其他国家的法律必为不当。就美国的宪政框架下,由于宪法规定之罪甚少,其授予国会的刑事立法有限,且国会当时制定的刑法及规定的犯罪极少,很多传统犯罪未被纳入联邦管辖范围,面对侵害联邦利益的危害行为,联邦司法无力应对,颇为棘手。关于危害行为可否依据普通法罪审理及国会是否有必要明确规定所有侵害联邦权威的犯罪,人们各持己见。不少联邦法官认为国会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如司法部长埃尔斯沃思(Ellsworth)就告诉陪审团基于普通法作出判断,而相反的立场亦很明确。
1812年的United States v. Hudson & Goodwin案决定了普通法罪在联邦的命运。在该案中,Hudson及Goodwin被指控诽谤总统及国会,被告指称总统和国会私下给拿破仑·波拿巴200万美元以使其与西班牙签约。巡回法庭在该案能否行使普通法审判权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联邦最高院认定,联邦政府是一个授权政府,宪法未授权联邦机构行使普通法管辖权,各级联邦法院在刑事案件中不能行使该权力,只能行使国会授予的权力,一个行为在作为侵犯联邦利益的犯罪而受到刑罚之前,国会必须事先确定犯罪及刑罚,并宣告法院有这种司法管辖权。该案判决终结了美国联邦法院依据普通法定罪的历史,真正确立了国会须通过立法确定犯罪及刑罚的制度,“结束了美国20多年的关于联邦普通法罪的论争”[3]。这也意味着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null poena sine lege)原则被引入联邦司法。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李仲民:美国联邦刑法法典化述评二、联邦刑法法典化巡历美国虽大规模地继受了英国法,但亦对之进行了深入改造,19世纪70年代成型的美国法极富特色,其中制定法与判例法并重便是例证。特别是在联邦刑法领域,制定法日渐占据鳌头。1790年,国会颁布了《治罪法》。此后,大量单行刑法及附属刑法冒涌。在排斥英国法、亲睐法国法的历史氛围中,利文斯通及菲德尔不失时机地贡献了刑法典智慧,但也留下遗憾。面对日益繁多、错综复杂的刑法规范,联邦对之进行了整理。1877年、1909年、1948年,联邦整体性整理、汇编了刑法,成果最终呈现于美国《联邦法典》第18主题——“刑法与刑事诉讼”,而普遍认为,《联邦法典》第18主题系名不副实的“刑法典”,其并无刑法典的品性。1962年,美国法学会制定出《模范刑法典》,该法典非官方文本、无强制力,但掀起了刑法典修订风潮,大部分州采取了行动,联邦机构亦被震动。1966年,联邦成立了刑法改革委员会,1971年《联邦刑法典草案》完成,1972年至1982年,政府及国会联袂数度修改草案,但草案未获通过。至此,宏观刑法法典化被搁浅,联邦进入了一个碎片化刑法改革的时代。
(一)1790年《治罪法》及1825年《治罪法》
可以说,联邦刑法史始于1790年《治罪法》(The Crime Act of 1790)。“在此法之前,国会仅通过了很少的联邦犯罪。”[4]该法由埃尔斯沃思起草,于1790年4月30日在第一届国会通过,它往往被视为一个准宪法文本。1790《治罪法》是处罚侵犯联邦利益罪行的正式的综合性法案,定义了一些侵犯联邦的罪行,并补充了1789司法法的刑事诉讼规定。
1790年《治罪法》规定了叛国罪、叛国渎职罪、海盗罪、公海上的谋杀及抢劫等重罪,以及伪造罪、违反国家法律的犯罪、谋杀罪、过失杀人罪、暴乱罪、盗窃罪、重罪渎职罪、破坏司法程序完整罪等。所规定的普通法罪甚少,而联邦法院没有普通法罪管辖权,导致联邦法院无法处罚严重侵犯联邦的行为。刑罚方面,1790年《治罪法》对于叛国罪、伪造罪、蓄意谋杀罪、帮助死刑犯逃逸罪以及公海上的海盗罪、谋杀罪、抢劫罪规定了死刑,对于伪证罪规定了耻辱柱刑,对于谋杀者规定了解剖刑。刑事诉讼程序方面,1790年《治罪法》第32部分规定诉讼时效,对于蓄意谋杀、伪造、逃避司法追究的罪犯,无时效限制,死刑犯罪的追诉时效为3年,非死刑犯罪追诉时效为2年;第8部分规定司法管辖范围,对于公海犯罪或州际犯罪的审判,以被告被逮捕地或被先带到的区域为准。该法还确立了关于联邦罪行的限制性条款,保障叛国罪及被判处死刑被告的程序权利,简化了伪证罪的上诉请求,并扩大保障宪法的反腐力度。
1825年《治罪法》可视为1790年《治罪法》的延续、扩展。1816年,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及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开始起草刑法典,《治罪法》于1825年3月3日通过。该法取消了先前不一致的法律,“取代”1790年《治罪法》的第12节、1819年《盗版法》的一部分、1820年《盗版法》及1816年《银行法》的全部。1825年《治罪法》增加了联邦专属管辖的犯罪,扩大了公海的范围,使之包括海湾、河流、溪、沼泽、港口,规定联邦法院对于在国外的美国船只上的犯罪有管辖权。在刑罚方面,增加了苦役。
(二)利文斯通及菲尔德法典
自16世纪始,英国便发展了法典编纂理论并付诸实践,直至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系统的法典编纂理论之前,普通法已经积累了不少法典编纂的经验。“在美国,最早的刑法法典化者应是1776年以托马斯·杰弗逊为首的委员会,它编纂了弗吉尼亚州的刑罚典草案。”[5]1802年,边沁的《立法原理》(Theory of Legislation)实际上,边沁未出版过名为《立法理论》之著作,此书名是在边沁去世多年之后流行起来的原由迪蒙以法语形式编撰,于1802年在巴黎以三卷本形式出版,Theory of Legislation系法译英之书名。出版,该书系统地阐述了法典编纂理论,功利主义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边沁立法理论的起点,法律成为实现功利原则的手段,而唯有法典能够给予法律理性形式,应排除法官法及习惯法。“法典应满足四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完整的,以至无需用注释或判例的形式加以补充。第二,叙述法则,必须使每一句话都达到最大可能的普遍性。第三,法则以严格的逻辑顺序叙述。第四,叙述法则,必须用严格一致的术语。”[6]
边沁不仅向祖国进贡其法典编纂理论,而且还热情地向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推销其成果。1811年, 边沁给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总统写信,表示志愿效劳美国法典编纂,但次年的美英战争,导致麦迪逊总统没能及时回信。随后,边沁给各州州长写信,仅有新罕布什尔州的州长威廉·普纳姆(William Plumer)对边沁的建议感兴趣,但该州的议会则无动于衷。尽管一无所获, 但边沁却为法典化运动贡献了智识及内容,“其思想成为19世纪英语世界法典化运动的滥觞”[7]。在美国,爱德华·利文斯通(Edward Livingston)即是边沁的追随者。“戴维·达德利·菲尔德(David Dudley Field)在对纽约州进行法典化论证时,即引用了边沁在印度法典中的话语。”[8]
美国独立后,其对英国敌对的民族情绪衍生了排斥英国判例法的风潮,制定成文法典的气候逐渐形成。1820年,路易斯安那州通过了一个法令,呼吁起草一部基于预防原则的综合性刑法典,清晰、详细地定义各种犯罪,并配置适当刑罚,利文斯通被任命组织起草路易斯安那州刑法典。利文斯通熟悉罗马法,在比较普通法的基础上,起草刑法典。但突如其来的大火使利文斯通的刑法典第一稿付诸东流,利文斯通再次启动工作。1824年,路易斯安那州刑法典草案问世,却没能在州议会以足够的票数通过。路易斯安那州刑法典草案也构成利文斯通向国会呈递刑法典的基础,但联邦亦未通过刑法典。利文斯通于1826年完成的联邦刑法典体现了边沁功利主义思想,刑法典分为单独的四个法典,即《犯罪与刑罚法典》、《程序法典》、《证据法典》、《改造和监狱纪律法典》,囊括了刑法所有领域。利文斯通雄心勃勃却战绩不佳,但他赢得巨大赞誉,被称为“美国法典化运动之父”[9]。
菲尔德并无利文斯通的雄心壮志,却获得得更大成就。菲尔德在1846年纽约州宪法会议上提出成立改革及法典化委员会。1947年,纽约州成立了菲尔德为首的法律修订委员会,至1865年,该委员会制定了《民事诉讼法典》、《刑法典》、《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政治法典》,即“菲尔德法典”。遗憾的是,菲尔德委员会起草的诸法典只有刑法典被采用,而且是在其起草完成17 年之后。但“菲尔德法典”影响广泛,加利福利亚等4各州全部采用了“菲尔德法典”,17个州部分采用了某些法典。“菲尔德法典的理念及前提假设与其同时代的大为不同。”[10]这些超前的理论持续影响了整个美国及很多国家的法典编纂。“法律史会公正地对待菲尔德强大的、有用的、高尚的职业生涯。”[11]
然而,19世纪美国的法典化运动未获成功,“其处处暗藏失败的因子”[12]。
(三)1877年《联邦修正法律》
刑法典编纂未果,但单行及附属刑法迭出不穷。1873年,国会尝试将持续增长的、有效的刑法整合、修订,1877年,分散的刑法条款被汇编成册,册子依据题、章、节等分类,分为超过227个犯罪主题及5600部分。该法使用类罪方式将联邦刑法划分侵害政府存在罪、侵害政府运行罪、海陆司法域内的犯罪、妨害司法罪、官员不当行为罪、破坏选举权及侵犯公民权利罪等,增加了妨害选举和公权罪,首次对谋杀及过失杀人罪定义,删除了一些过时及相互矛盾的条款,同时还规定了关于共犯的处罚、监禁者及其待遇,并区分了重罪和轻罪的刑罚。1878年,国会于颁布了《联邦修正法律》(The Revised Statutes of 1877)。
(四)1909年《编纂、修正、改订联邦刑事法规的法律》
时逾30年,修订刑法再成必要。1909年,国会通过了《编纂、修正、改订联邦刑事法规的法律》(The Criminal Code of 1909)。该法修缮历经数年,刑法典报告于1901完成并被送至各行业审议;1906年,又完成进一步修正,该版本包括74个新部分,21款明细,10个新罪名;1908年7月7日,特别组成委员会就修正刑法草案做了报告;刑法于1910年1月1日生效。《编纂、修正、改订联邦刑事法规的法律》搜索、汇集了颁布的法律、临时法案及未通过的法律,形成了34卷,它被预设为本土最权威的法律。该法撤销了许多犯罪,同时增加了不少犯罪,其中很多为制定法罪,包括破坏邮政业务的犯罪、侵害国际及州际贸易的犯罪,且其形式颇受重视,宛若依据清晰、系统的编译形式编排。
(五)1948年《联邦法典》
1926年,美国正式制定《联邦法典》(United States Code),该法系法美国全部联邦法律的官方汇编,根据法律规范所涉及的领域及调整对象划分为50个主题,主题之下依次为卷、章、部分、节、条等。国会法律修订委员将国会颁布的法律分解为若干部分,编排到50个相应主题当中。《联邦法典》每隔六年重新编纂颁布一次,在此期间,国会每年颁布的法律会按照法典编排的序号编辑成一个补充卷。普遍认为,《联邦法典》并非名副其实的法典,亦非单纯法律汇编,其所汇编的系经修订的制定法,实则简明的法律重述。
1948年,国会通过“修正、法典化及实施有效法律”的法令,创制《联邦法典》第18主题——犯罪及刑事程序,收纳了联邦几乎所有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实际上,刑法修订工作于1943年启动,为了完善刑法典,国会发送了1500封邮件至法官、检察官、学者、协会征集意见,并收到很多附带具体意见的回复,所提交给第79届国会的草案的副本送达至每一位国会议员、个人及组织审议。
《联邦法典》第18主题分为5部分,即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监狱及监禁者、青少年罪犯矫正、证人豁免,犯罪部分共分为123节。除法条外,该法还包括判例注解、编者注解、作者评论、交互索引、研究索引、判决意见等。《联邦法典》第18主题特点明显:其一,刑法的内部结构方面,依据字母顺序排列取代了旧的分类制度,且编排方式灵活,章节先依奇数排列,将偶数章节以及章节末尾空间留给未来增加的犯罪。其二,于初始章节中规定一般性条款。其三,删除条款重复部分。其四,剔除模棱两可、修辞的语言,并对很多部分做了统一定义。其五,对处罚条款中的不一致进行补正。至此,联邦刑事法律体系初步成型,后来的《联邦法典》虽历经上百次修改,但其基本方面并无大变化。
(六)1962年《模范刑法典》
20世纪,美国立法及判例数量惊人,且该数量持续膨胀,数量庞大、杂乱无章的法律已令适用者茫然无措。美国法学会担当起编纂法典式的法律体系化工作。1923年成立的美国法学会,是最有开创性的独立组织,旨在学术性地澄清、现代化及完善法律,其主要工作是编写法律重述及编撰统一法典。法律重述往往成为立法机关及法官信服的权威及法律解释、适用的凭仗。在着手刑法重述时,学会发现现有刑法过于混乱、极不合理,不值得重述,最后,学会决定起草一部可供各州参照的《模范刑法典》。
1931年,学会启动了刑法典起草工作,得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的支持。“但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它的经费过于昂贵,不得不中断。”[13]1951年,刑法典起草因洛克菲勒基金赞助得以恢复。赫伯特·威克斯勒(Herbert Wechsler)召集了由法学教授、法官、监狱官员及精神病学、犯罪学、语言学家组成了咨询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数度修改,1962年,学会通过一部完整的《正式建议草案》。之前多个版本的《暂行草案》经整理及修正于1985年连同1962年《正式建议草案》以七卷本的方式出版。
《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实际为《刑法和矫正法典》(Penal and Correctional Code),共分为四编,即总则、具体犯罪的界定、处遇和矫正及矫正组织。它不仅包括刑法,还涵括了有关刑罚执行的法律及部分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程序性规定散见于整部法典。《模范刑法典》完成了很多创举性工作,如创制了综合性一般规定、评价刑事责任的分析框架、犯罪构成,完整界定犯罪,使用规范术语,等等。
1962年《模范刑法典》颁布之后,掀起各州法典改革的浪潮,美国2/3的州1962年伊利诺伊州,1963年明尼苏达州及新墨西哥州,1967年纽约州,1969年佐治亚州,1970年堪萨斯州,1971年康涅狄格州,1972年科罗拉多州及俄勒冈州,1973年特拉华州、夏威夷州、新罕布什尔州、宾夕法尼亚州及犹他州,1974年蒙大拿州、俄亥俄州及德克萨斯州,1975年佛罗里达州、肯塔基州、北达科他州及弗吉尼亚州,1976年阿肯色州、缅因州及华盛顿州,1977年南达科他州及印第安纳州,1978年亚利桑那州及爱荷华州,1979年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及新泽西州,1980年阿拉巴马州及阿拉斯加州, 1983年怀俄明州。其他州, 如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俄克拉荷马州、罗得岛州、田纳西州、佛蒙特州及西弗吉尼亚洲, 起草的刑法典未获通过, 但日后仍可能被重新审议。重新编纂了刑法典,均以《模范刑法典》为蓝本。实践中,《模范刑法典》常被法庭作为权威资料引用以论证判决。另外,《模范刑法典》的《正式释义》(Official Commentaries)亦影响深远,在对以《模范刑法典》为蓝本的州刑法典进行解释时,溯源至《正式释义》通常是探究规定背后法理的理想途径;而且,《正式释义》亦是刑法学者一项重要的研究资源。《模范刑法典》一问世,便满载盛誉,被称为“无以伦比、最美国化的刑法典”[14],“是过去半个世纪最大的成就,突出贡献于刑法典编纂、学术成就成熟化、犯罪心理理论进步”[15],“承载了刑法的精华”[16]。
当然,《模范刑法典》亦有瑕疵,为人诟病。如《模范刑法典》时常考虑便宜而牺牲理论连贯性,以未遂犯为例,《模范刑法典》对严重犯罪未一以贯之未遂与既遂同等刑罚原则;另外,《模范刑法典》保留死刑,而死刑与其“处遇及矫正”的原则冲突。《模范刑法典》关于刑罚的规定被视为重大败笔之一,量刑及处遇理论前提——康复矫治(rehabilitative )已被否弃,其规定的犯罪等级不够细化,犯罪等级刑罚裁量空间极大,这被后来的确定刑改革彻底否定。
《模范刑法典》并非官方刑法典,无强制力,但它影响广泛而深远,它给予联邦编纂刑法典的启示及热情,其部分内容亦被后来《联邦刑法典草案》采用。
(七)1971年-1982年《联邦刑法典草案》
20世纪60年代,种种迹象表明,联邦确实需要一部刑法典,且编纂刑法典的良机已降临。最直接、最有力的因素莫过于联邦政府及国会空前重视犯罪及刑事司法,多重原因造就了该局面。首先,严重的犯罪形势已触及民众底线。其次,电脑数量化分析、经济分析及管理技术等研究方法被引入犯罪学研究,应对犯罪理论大有进步。再次,《模范刑法典》的成功启示了联邦机构。执法及司法复查委员会强烈建议审视及修改刑法,不过不乏反对修法者。
当然,反对修法者的看法并不削减编纂联邦刑法典的热情。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总统表示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为公民提供安全及保障,并呼吁制定应对犯罪的国家战略,修订联邦刑法被列为战略的一部分。国会立即给予回应,众议院提出成立刑法改革委员会的议案,且其工作不局限于审视、修订或编纂现有法律,它有权决定整个刑法框架。联邦刑法改革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Reform of Federal Criminal law)于1966年成立,由参议员、众议院及联邦法官各三名组成,致力于制定一部综合、完整、协调、公正的刑法。委员会征求并采纳了公众意见,经数度修改,1971年1月,联邦刑法改革委员会的最终报告提交至总统及国会,并附上每部分的评论、1700页的法律状态分析及修订版的影响。
联邦刑法典草案对于《联邦法典》第18主题的改革被视为“近200年以来整合联邦刑法的最重要的尝试”[17]。草案考量了联邦所有的刑事法律,并将法官造法纳入,设计超前、综合、有序、简洁。草案主体分为A、B、C三部分,A部分分为7章,即基本规定、联邦刑法管辖权、刑事责任基础、共谋、缺乏责任能力的辩护事由、关于正当事由及免责的辩护、起诉的限制。B部分包括第10至第18章,规定具体犯罪。C部分为量刑体系,包括第30至第36章,即量刑一般规定、缓刑及无条件释放、监禁、罚金、假释、剥夺资格刑及终生监禁。草案另附三个表格及附件A。
草案大大推进犯罪联邦化、扩大联邦刑事管辖权。联邦刑法的适用范围扩大,犯罪类别包括关于国家安全、国际秩序、侵犯人身及财产犯罪等;规定针对国家高级领导人或美国驻外使节的犯罪、侵害美国政府的犯罪,各州在管辖权上存在争议的犯罪,也适用联邦刑法,且当联邦与州发生管辖冲突时,联邦管辖优先。《联邦刑法典草案》最显著的理念及结构性变化即是联邦管辖权的扩大。
从1972年至1982年,刑法典草案审议长达10之久,国会每年均召开听证会,且公布了24000页的听证词及相关成果。1978年,参议院通过了刑法典草案,1980年,众议院未通过刑法典草案,1982年,因审议程序问题,参议院决定撤除草案,将摘出部分并入小案法。
(八)1984年《综合犯罪控制法》
1982年之后,刑法法典化搁浅,但美国依然面临日益紧迫、严重的犯罪及量刑公正问题。国会及政府不得不将精力转移至能够取得够立竿见影成效的部分刑法改革,宏观的、根本的刑法法典化让位于微观的、紧迫的问题,1984年《综合犯罪控制法》(Comprehensive Crime Control Act of 1984)应运而生。《量刑改革法》(Sentencing Reform Act)是《综合犯罪控制法》组成部分,其从参议院S.1630版本刑法典草案中摘出。之于刑法法典化,这是一个转折点,意味着刑法典根本改革的碎片化。自此,大量条款从刑法典草案流出,并被签署成法律。
对联邦刑法法典化影响更为戏剧的是联邦量刑委员会,该委员会依《量刑改革法》成立,其有权制定法律,1987年《联邦量刑指南》(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便是其作品。《量刑改革法》及《联邦量刑指南》对联邦刑罚领域进行了根本性改革——从不确定刑转为确定刑,而刑罚恰恰是联邦刑法典草案最核心、最富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倘若《联邦量刑指南》功成,也就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联邦刑法典草案的成功以及1982年之后的搁浅尚不耽误。遗憾的是,在2005年的Booker v. United States案中,联邦最高院宣布《联邦量刑指南》违宪,其效力从强制性转为转为建议性。而且,实践证明,《联邦量刑指南》未达至减少量刑差异及犯罪之目的,而美国深陷犯罪问题严峻、“大规模监禁”、司法财政过度膨胀的沼泽。事实证明,确定刑改革失利了,联邦须对刑法典改革从长计议。
三、联邦刑法法典化之品性刑法法典化是文明社会对法治的基本信仰承诺及兑现,是世界范围紧迫、寻常、持久的事业。不同地区共享刑法法典化诸多习性,但个体差异性亦非常明显。美国特有文化造就了其联邦刑法法典化的独有品性,联邦刑法法典化启于内外因素双重驱动、历经形式编纂到实质编纂、本体上即权力扩张与抑制、价值思维系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统合。
(一)起点:内外驱动
美国联邦的刑法法典化是内、外因素双重驱动的结果。英属殖民地的北美秉承了英国判例法传统,遵循先例是其司法主轴。后来,美国并重制定法与判例法,且刑法制定法最终独占鳌头,缘于其内、外因素的综合驱动,从而完成对历史习性的挣脱。
就建国之后的法典化运动而言,于内,“美国人对法制定法具有天生的信任感”[18],且“美国对英国的敌对情绪延续至其法律制度”[19],普通法在北美陷入信任危机,美国禁用英国判例法俨然成风。于外,美法因独立战争中的联盟亲近不少,而此时的法国成文法成果丰硕、显赫,自然吸引美国的目光。另外,边沁的法典化理论催化了美国的法典化运动。《联邦宪法》、利文斯通及菲尔德的刑法典均是美国特定历史时期内、外因素的结合体。就1966年后的《联邦刑法典草案》而言,于内,美国犯罪率骤增、量刑差异严重,而庞杂、错乱的《联邦法典》第18主题无力回应,另外,获得无数美誉的《模范刑法典》来带珍贵的启示及热情。于外,英美法系的许多国家刑法法典化成果颇丰,而大陆法系刑法典愈加成熟、精湛,且法律全球化、一体化日渐成风。联邦政府、国会不得不紧锣密鼓地将制定刑法典提上议程,以应内忧外患。
总之,联邦刑法法典化是内、外因素双重驱动的结果,倘若仅有美国内部因素,这些运动很难突破判例法的传统桎梏而开花结果;假设无外部因素的强烈撞击,美国联邦亦不太可能里应外合地实施“同质”的造法活动。刑法汇编或刑法法典化实际上是对刑法渊源的理想化、一体化整合,它改变了刑法渊源多元状态,使国内刑法渊源形式上统一为一体,也是法律全球化预演或部分正演。实际上,区域或全球刑法的一体化是任何社会规范有效性的前提——可普遍化的基本诉求及具体表现,亦即,刑法规范唯有可普遍化,才是真正有效,而有效的刑法规范,必然具有普遍性、能够一体化。
(二)路径:从形式编纂到实质编纂
在联邦刑法改革委员会起草刑法典之前,联邦关于刑法典的改革实际都是对刑法渊源的形式上整合,即刑法汇编,其价值在于使法律更为简明、易于查找、便于反复更新。
20世纪60年代,刑事法治的糟糕局面及《模范刑法典》带来的曙光促使联邦作出起草刑法典的决定,这项法典编纂事业与以往的法律汇编存在根本性区别。实质法典编纂,以构建或修正某一法律秩序为目的,塑造由规则组成的完整的法律体系,其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面,其一,理念,任何真正法典编纂均将一定理念注入法律,且该理念及目的持久性指引法典编纂的展开及法典的运行。其二,体系性,即法典由不同要素依据一定的规则组成有机整体,该整体结构反映出其条文的独立性、协调性及整体性。其三,特定表达,条文借助特定术语和措辞确定、简明、清晰及精确地表达。实质性法典编纂与法律汇编在理念、内容、体系、表达方式、稳定性存在巨大区别,正是这些区别,构成了1971年《联邦刑法典草案》与《联邦法典》第18主题的本质差异。
联邦刑法法典化历经形式编纂到实质编纂,系刑事立法之重大进步。因为,法典是制度文明的精髓,是法形式中的最高级,其覆盖面广,能够浓缩及统一大量、复杂的法律信息,最具明确性、准确性、普遍性、稳定性及沟通性,更便于人们获取、了解、理解及适用。联邦刑法典编纂,是整肃刑法立法、维护法制统一及实现刑事法治的有效手段,是彰显美国法律理念及制度的重要方法,亦是美国输出刑法文明的前提步骤。
当然,刑法汇编及刑法典编纂都是立法的重要方法,在历史上及世界范围内均具有重大价值,都深刻影响着法律体系的合理性。美国联邦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变换这两种立法方法,展示了其刑法立法的丰富性及进步性。
(三)本体:权力之扩张与限制
作为一项立法活动,联邦法典化实质涉及权力配置,犯罪联邦化意味着联邦刑事管辖权的扩大,联邦政府与国会共同组织联邦刑法典草案工作蕴意着行政权的扩张以及司法权的式微,同时,联邦刑法法典化是权力之隐形自制,此遂美国宪政框架调整的重要表现。
联邦与州权力分配方面,呈现犯罪联邦化、联邦刑事管辖权扩大趋势。宪法直接规定的犯罪较少,且所赋予的国会刑事立法权有限,刑法修正案第十条规定,将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保留给由各州或由人民。然而,《宪法》第1条第8款授予国会制定“必要及恰当”法律的兜底条款。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州际流动性的扩大,国会利用《宪法》第1条第8款制定了大量关于商务条款、征税权、战争权、公民权利及管理邮政的权力等联邦刑事法律,犯罪联邦化越来越普遍。犯罪联邦化意味着联邦刑事权的扩大,它改变了联邦与州分权的框架,是美国联邦主义巩固及加强的表现形式之一。“犯罪联邦化是社会结构及政治风向转变的结果。”[20]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关系方面,联邦刑法法典化体现了三者之间的动态调适。《联邦宪法》规定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权而治、制约平衡,但自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违宪审查制度后,联邦最高院一路高歌猛进,司法成为美国法律发展的中心。刑法解释及量刑方面,法院拥有极大自由裁量权,这当然很大归因于立法不善。刑法汇编或刑法典编纂实际上是国会对司法权的规范及限制,但国会对司法的这种制约远远不达三权平衡的水准。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为行政权的崛起提供了契机,联邦政府全面接管社会,出现行政主导立法局势,而且罗斯福政府改组联邦最高院的计划改变了司法权的高昂姿态,联邦最高院自此保守、低调。在刑法典改革问题上,总统提议成立联邦刑法改革委员会,白宫与国会联合起草、审议及修改议案,且在没有联邦政府的倡导之下,1982年的联邦刑法法典化至今再无任何建树。“无论是联邦刑事管辖权的扩大,还是行政权的扩张,其背后的历史、政治原因是美国当时社会动乱及乱世用重典的观念。”[21]
“法,本质上是权力及其管理之规范。”[22]法之优良是政治优良最基本、最核心的条件。作为一种形式上刑法渊源的理想化,刑法汇编或刑法典编纂是促成法优良的重要方法,在此意义上,联邦刑法法典化是规范权力、政治的有效手段,故此,无论是联邦政府,亦或国会组织编纂联邦刑法典,实际上是权力及其运行的一种自制。
(四)价值思维: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统合
联邦刑法法典化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美国核心价值思维——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这一对价值思维自始至终贯穿并指引联邦刑法法典化,并造就了刑法法典化的最后局面。
美国法虽传承了英国判例法之精髓,由于政治体制等差异,美国未如同英国严格恪守遵循先例制度,其制定法日愈重要,并占据半壁江山,而且美国发展出许多价值厚重、别致一格的法律制度,完成了对英国法的超越,并在英美法系、世界法律体系上产生重大、深远、持久的影响。美国法律所取得的成就,终极原因在于美国的拓殖精神及理想主义。“理想是价值意识的最高范畴,是指导和推动人的实践活动的精神力量源泉。”[23]它们使美国法律不甘恪守历史、墨守成规,而勇于冒险、敢于尝试地追求理想法治国及幸福的生活。联邦刑法法典化即充分体现了美国对判例制度的反思、批判、及革新。对于刑法法典化,联邦给予高规格的重视,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起草5年、审议10年,即使最终未能通过亦能说明美国对刑法典的完美化追求。从普通法罪否弃,至大量单行刑法及附属刑法制定,再到对刑法规范汇编,最终抵达刑法典编纂,无一不透露着美国对刑法治锲而不舍、不断提升的理想追求,也是表达了其对社会公正、人类幸福图景的憧憬及努力。
然而,在追求刑法治的道路上,美国的实用主义处世哲学亦随处显露,刑法典工作或漫不经心,或走走停停、至今未竟。“实用主义被认为是美国民族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理论象征,甚至具有美国准国家哲学的意义。”[24]实用主义强调,对现实的解释完全取决于利益效果的考量,行动及经验优于教条,纵观联邦刑法法典化,实用主义理念无时不在。美国建国后的法典化风潮实际未能催生联邦编纂刑法典的决心,随即而来的是不完整的、不连贯的、无规划性的大量单行刑法及附属刑法,从1877年至1966年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联邦最常态、最主要的相关工作即是将刑法集合于一体,而这个被批得体无完肤的集合体至今仍旧是联邦官方唯一运行的“刑法典”。1982年,联邦刑法法典化搁浅之后,为了减少犯罪、量刑差异及回应民众对安全与秩序的强烈诉求,联邦果断、迅速地从联邦刑法典草案摘出部分并入了1984年《犯罪控制法》,该法中的《量刑改革法》催生了联邦量刑委员会及《联邦量刑指南》。这些适用范围较窄的法律解决了美国紧迫的问题,虽然后来的实践证明其并未成功,但它们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联邦刑法法典化的步伐,时至今日,联邦刑法法典化未被正式载上议程。
联邦刑法法典化仅是美国价值思维的一隅缩影,美国对于理想未来雄心壮志,面对现实利益暂可妥协,此辩证价值思维或许是美国能够保持生机勃勃但又能乐享安逸的秘诀。
四、联邦刑法法典化之应然现今,我们似乎可以更客观、更合理地认知与评价美国联邦刑法法典化。联邦刑法法典化的搁浅缘由复杂,可谓有天时,但尚缺地利及人和。20世纪60年代,促成联邦刑法典编纂的原因基本尚存,而今又添加了联邦刑法典编化耽搁造成的诸多负面后果,联邦刑法法典化的必要不言而喻。 美国需要更多的实践理性妥适、及时地完成这项事业。
(一)刑法法典化缘何搁浅
刑法典是刑法文明的显赫篇章。美国联邦刑法典编纂是刑法渊源理想化的重要途径,是整肃刑法立法、维护法制统一及实现刑事法治的有效手段,是彰显美国刑法文明的前提。联邦编纂刑法典无疑具有重大价值,旨在刑法有效、公正、人道,维护秩序、保障自由,就此而言,联邦编纂刑法典目的理性。
即使目的理性,事实是耗费了15年之久的联邦刑法典草案未通过。联邦刑法典草案未通过的缘由复杂,其一,1972年至1982年的联邦刑法典草案每一版本都很厚实,均超过500页,内容冗长、复杂,而一届国会的周期为2年,在任何情形下,分委会或全体委员会都难以完成草案审议工作,另外,行政机构、立法机构难以保证充分的时间及资源予修订、审议,且行政机构、立法机构的协调并不充分。其二,很多情况下,参议院与众议院审议的草案版本并不一样,第93届国会,参议院的版本是S.1和S.1400,而众议院没有该版本;第94届国会,参议院有S.1版本,但众议院没有;第95届国会,参议院的版本是S.1437和S.1722,众议院的版本是HR2311和HR6869;第96届国会,参议院的版本是S.1722和S.1723,众议院的版本是HR6915;第97届国会,参议院及众议院的版本分别是有S.1630和HR4711.39,参众议院审议版本不一,很大程度上抹杀了草案在国会通过的机会。其三,联邦立法程序规则繁琐,草案在任何一个环节都面临着夭折的风险,草案成为联邦法律必须经至少9个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力中心通过:众议院分委员,参议院分委会,参众两院各自全体委员会,众议院法律委员会,全体众议院,全体参议院,参众会议委员会,如果有必要,还有白宫。草案反对者在任何一个阶段可轻而易举地否决草案。其四,不同版本的草案包含着很多争议性问题,对于争议性问题,国会一般会举行为时很长的听证会,但结果往往是争议双方僵持不下,问题解决毫无进展。《联邦刑法典草案》未通过,很大原因在于其包含了很多有争议的关于政策改变的建议。其五,人们对于草案褒贬不一,有人冠之以“自由”之名,而有人将S.1和S.1400年版本喻以“法西斯”,尚无共识,草案通过尚漫漫修远兮。
另外,联邦刑法典编纂本身并没有获得必要支持,虽然,致力于公平、效率最大化的刑法法典化无疑价值重大,但这本身不会引起民众的热情。人们不会关注及细究刑法法典化的特殊原因及意义,故在认定刑法典是否需要重大改革的问题上,很多市民立场不明确。同时,不少律师及法官容忍的现行刑法的缺陷,他们倾向于在熟悉环境下寻找答案,且他们一直以美国法为豪,大陆法系的刑法典尚未能激发其兴趣。“美国律师对于德国的哲学家会冷眼相看,在其眼中,美国法律完完全全是自家事。”[25]
实际上,1984年《犯罪控制法》的实施构成联邦刑法法典化继续的障碍。因为,刑罚是《联邦刑法典草案》最核心、最富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犯罪控制法》、《量刑改革法》及《联邦量刑指南》对联邦刑罚领域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美国刑事司法当时最紧迫的需要,缓解了刑法法典化继续的压力。
(二)刑法法典化必要之推导
时过30多年,联邦刑法法典化仍无建设性进展,联邦刑法法典化有无继续的必要?其结论的推导须基于相应的事实及目的。
事实1:《联邦法典》第18主题弊病重重,难以获取、了解、理解、适用。
事实2:犯罪、矫正、监禁问题严峻,司法财政膨胀,刑法不力与前述问题存在关联。
事实3:刑法典具有天然优势,是刑法渊源最高形式,是刑法优良的关键因子。
目的:刑法的机能为行为规制、法益保护及自由保障,其前提是刑法优良。
价值判断:刑法典能够满足美国的现实需求。
结论:联邦刑法法典化之必要,应继续前行。
该推导过程分解如下:
《联邦法典》第18主题弊病重重,“所谓的联邦刑法典是国家的一种耻辱”[26]。《联邦法典》第18主题,形式杂乱无章。其一,刑法第18主题按照字母而非依据犯罪类型或一定理念排序,“是200多年来法条的怪异集合体”[27],刑法最为诟病的莫过于其“无组织、无结构、流水型排序”[28]。且其卷头太大,内容繁杂,难以查询、适用。其二,“无数的犯罪规定不协调或多余”[29],至1998年,“大约有215处涉及对政府官员的虚假陈述罪,有232处涉及盗窃及欺诈罪,有99处涉及伪造罪,有96处涉及破坏财产罪”[30]。其三,很多重要的犯罪并未出现于第18主题,而是分布于另外的49个主题,第18主题约有600多条款附带刑罚,约有3000个附带刑罚的条款分布于其他主题。如劫持飞机罪出现于处理州际运输的规定中,大多数间谍罪出现于有关原子能监管规定中,毒品犯罪出现于涉及食品和药品管理规定中。其四,条文不简明,很多规定超过200字,如第793部分的主句就用了约700多字。
《联邦法典》第18主题的内容极不合理。其一,未使用规范术语,也未使用统一的格式,法条难以理解。多个法条规定同一犯罪行为,但所做的定义大不一样,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在改革联邦刑法的两个世纪里,每平均2.5年,国会便创造出新名称意指犯罪心理,1970年至2000年,国会使用过的表述犯罪心理的名称约有80个。其二,很多法律应激,并无规划,20世纪30年代,翰·迪林格银行劫案催生了联邦银行抢劫法,林白绑架婴儿案催生了联邦绑架法,60年代,肯尼迪总统遭暗杀催生了有关暗杀总统的法令,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遭受杀害催生了杀害国会成员罪。其三,存在诸多立法空白。如抢劫联邦银行资金构成犯罪,但1986年之前,勒索联邦银行资金却不构成犯罪,直到1988年,贿赂国家政府官员的大多严重行为不构成犯罪。其四,有些犯罪规定过时,如禁止船员隐瞒船长而引诱女乘客乘美国船只、禁止美国政府截回未完成任务信鸽的规定。而有些犯罪已被后来立法替代,但仍占据原有位置,未被清除出法典。如第81章“海盗和私掠”,这一章已经更新为对付恐怖主义新法,但第81节仍未被废除。其五,纳入非真正意义及不重要的犯罪,第18主题包含许多仅为违反监管及商业制度的而被处以较轻刑罚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这些行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犯罪,还囊括了其他形式的“罪行”,如跨州运送空心莲子草、伪装4-H俱乐部成员意图诈骗等行为。其六,制定法罪严重扩张,且规定的不要求证明存在犯罪心理的严格责任犯罪越来越普遍,已经有1700多种与传统犯罪无关的行为被犯罪化。人们以为,刑法忽视了罪与非罪区分原则,当然,制定法罪与普通法罪的危害可能无二致,但1700种制定法罪中的某些犯罪还是值得审视,诸如对在政府大楼前遛狗、出售2种以上的松节油等行为。
《联邦法典》第18主题形式及内容的缺陷并非局部修正可应付,它需要根本的、全面的改革。“这些缺陷不能修复或通过增加新法规补救,因为它们是根本性的”[31]。
联邦刑法难获取、难了解、难理解、难适用,折损刑法的行为规制、法益保护及自由保障机能,刑罚的惩罚及预防效果必然不佳。美国历来重视犯罪问题,从不间断研习新理论、创制新制度予以应对犯罪,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的犯罪率骤增,70年代起,出现“大规模监禁”现象,随之,司法财政急剧攀升。当然,这些现象由综合原因引发,但倘若刑法不力减损刑法机能,进而影响刑罚的惩罚及预防效果的推导成立或是既定事实,那么,当前刑法必然要为上述刑事司法恶果买单。下表将简要列举美国犯罪、监禁、司法财政数据。年份数值
作为刑法有效的基本条件,刑法必须易于获取、理解、适用,合法制原则也要求法律主义、明确性,虽然刑法典并非刑法渊源的唯一形式,但是其最理想的形式,刑法典最能体现刑法规范的明确性、普遍性等特点。毫无疑问,完备、统一、协调、明确的刑法典能够最高效、最大化的实现刑法的机能。
基于现有刑法不力、刑法治危机以及刑法典的天然优势之事实,结合刑法有效、公正、人道之目的,得以推导出刑法法典化仍需继续之应然结论。而且,在联邦量刑改革遭受重大失利之后,这项事业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三)可能的实践
法作为实践理性之体现,是近代以来一个严格的命题。实践理性,即在认知与把握事实的基础上选择及从事正当行为的机能及能力,其有效性并非单纯源于思维与实在的同一,根源于善之最大化。形式理性仅是法律的基本、外在的要求,而法规范的有效性深层蕴含于实质理性,亦即,一个真正有效的法规范须根基于相应地价值、道德、伦理基础。如同其他社会规范,法规范推导于价值判断,而价值或善的最大化是规范如何的依据。
刑法法典化是刑法理性化的过程,是一个事实与规范、客观与主观、逻辑与价值、认知与评价缠绕的过程,在事实、客观、认知及逻辑的基础上进行涉及主观、评价、价值及规范的选择,最终决定了刑法典的合理性。
美国联邦刑法法典化失利归根结底可简单表述为,既过分苛求刑法典的形式理性,又过度纠结于刑法实质理性,标准的过度沉重是刑法典不能承受之重。形式方面,草案内容磅礴、详尽,审议程序严格、细致,期待为期2年的一届国会完成审议,实无可能性。1978年S.1437版本在参议院以72:15通过,但众议院未及时审议草案,最后,国会期满,有史以来最有希望的草案夭折。1980年参议院S.1722版本可谓万事俱备,无奈被总统竞选、国会的政党易权耽搁。可以说,草案的失利最直接的原因系程序、形式问题。实质方面,草案涉及太多争议问题,而争议问题解决标准不明确、解决方式不明智,结果论争循环、耗时过长、共识鲜少。联邦刑法典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并非纯粹的法律问题,还涉及政治、历史、宗教、种族、经济、伦理等问题,其中遍布雷区、禁区,如堕胎、淫秽、毒品、枪支管制、窃听及死刑等话题。“在任何一个情感纠缠的问题上协调2.2亿美国人的思想,便是钻山填海。”[32]
任何法律均是矛盾的结合体,任何正当的法律同时也是价值最大化选择的成果。联邦刑法典无法避免事实矛盾,但其优良与否还在于刑法法典化的价值择定、价值判断机制、规范推导系统,实则在于人所动用的实践理性。当然,美国人也意识到这些,亦已提出不少的具体建议,如强化联邦机构的责任感、获取法律人与公众的支持、加强国会两院及联邦政府的沟通及合作、审议高效化、以国会时间及工作量为参考妥适简化草案、尽量绕开争议性问题以及在争议问题的终结上设定标准、程序,等等。如此,未来的行动便是启动联邦刑法法典化,并在其中实践理性。JS
参考文献:
[1]Lawrence Meir Friedman.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M]. 3th ed.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2005:34.
[2]Gunther A. Weisst. The Enchantment of Codification in the CommonLaw World[J].The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0,(25):515.
[3]Gary D. Rowe. The Sound of Silence: United States v. Hudson & Goodwin, the Jeffersonian Ascendancy, and the Abolition of Federal Common Law Crimes[J].Yale Law Journal,1992,(101):919.
[4] Paul Taylor. Congresss Power to Regulate the Federal Judiciary: What the First Congress and the First Federal Courts Can Teach Todays Congress and Courts[J]. Pepperdine Law Review,2010,(37):847.
[5] Kathryn Preyer. Crime, the Criminal Law and Reform in Postrevolutionary Virginia[J].Law and History Review,1983,(1):53.
[6]边沁.政府片论[M].沈叔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51.
[7]Andrew P. Morriss, Scott J. Burnham and Hon. James C. Nelson. Montana Field Code Debate: Debating the Field Civil Code 105 Years Later[J].Montana Law Review,2000,(61):132.
[8]Charles Noble Gregory. Bentham and the Codifiers[J].Harvard Law Review,1900,(13):334.
[9]John L. McClellan. Law Codification, Reform, and Revision:The Challenge of a Modern Federal Criminal Code[J].Duke Law Journal,1971,(4):663.
[10] Stephen N. Subrin. David Dudley Field and the Field Code: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an Earlier Procedural Vision[J].Law and History Review,1988,(6):311.
[11]Irving Browne. David Dudley Field[J].Boston,1891,(III):49.
[12]Wienczyslaw J. Wagner. Codification of Law in Europe and the Codification Movemen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United States[J].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1952,(2):826.
[13] Herbert Wechsler. Codification of Criminal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del Penal Code[J].Columbia Law Review,1968,(68):1425.
[14] Paul H. Robinson. The America Model Penal Code:A Brief Overview[J].New Criminal Law Review,2007,(10):319.
[15]Robert H. Joost. Simplifying Federal Criminal Laws[J].Pepperdine Law Review,1986,(14):1.
[16]Herbert L. Packer. The Model Penal Code and Beyond[J].Columbia Law Review, 1963,(63):594.
[17]Richard H. Brody.The Proposed Federal Criminal Code:An Unwarranted Expansion in Federal Criminal Jurisdiction[J].Criminal Code,1978,(39):133.
[18]Albert J. Harno. Som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in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in the Last Century[J].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1951,(42):427.
[19]Roscoe Pound.The Formative Ear of America Law [M]. 2th ed.New York :Little Brown,1938:12.
[20]Kathleen F. Brickey.Criminal Mischief: The Federalization of American Criminal Law[J].Hastings Law Journal,1995,(46):1135.
[21] John Quigley. The Federal Criminal Code Revision plan:An Epitaph for the Wellburied Dead[J].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1979,(47):459.
[22]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4.
[23]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10.
[24]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76.
[25]Shael Herman. The Fate and the Future of Codification in America[J].The Amei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1996,(XL):407.
[26]Julie R. OSullivan. The Federal Criminal Code Is a Disgrace:Obstruction Statutes as Case Study[J].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2006,(96):643.
[27]Paul H. Robinson. Reforming the Federal Criminal Code: A Top Ten List[Q].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1997(1):225.
[28]John F. Dobbyn. A Proposal for Changing the Jurisdictional Provisions of the New Federal Criminal Code[J].Cornell Law Review,1972,(57):1.
[29]Edward M. Kennedy. Federal Criminal Code: An Overview[J].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1979,(47):451.
[30]Ronald L. Gainer. Federal Criminal Code Reform: Past and Future[J].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1998,(2):45.
[31]Robert H. Joost. Federal Criminal Code Reform:Is It Possible?[J].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1997,(1):195.
[32]Louis B. Schwartz. Law Reform of the Federal Criminal Laws: Issues, Tactics, and Prospects[J].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77,(41):2.
[14] Paul H. Robinson. The America Model Penal Code:A Brief Overview[J].New Criminal Law Review,2007,(10):319.
[15]Robert H. Joost. Simplifying Federal Criminal Laws[J].Pepperdine Law Review,1986,(14):1.
[16]Herbert L. Packer. The Model Penal Code and Beyond[J].Columbia Law Review, 1963,(63):594.
[17]Richard H. Brody.The Proposed Federal Criminal Code:An Unwarranted Expansion in Federal Criminal Jurisdiction[J].Criminal Code,1978,(39):133.
[18]Albert J. Harno. Som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in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in the Last Century[J].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1951,(42):427.
[19]Roscoe Pound.The Formative Ear of America Law [M]. 2th ed.New York :Little Brown,1938:12.
[20]Kathleen F. Brickey.Criminal Mischief: The Federalization of American Criminal Law[J].Hastings Law Journal,1995,(46):1135.
[21] John Quigley. The Federal Criminal Code Revision plan:An Epitaph for the Wellburied Dead[J].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1979,(47):459.
[22]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4.
[23]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10.
[24]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76.
[25]Shael Herman. The Fate and the Future of Codification in America[J].The Amei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1996,(XL):407.
[26]Julie R. OSullivan. The Federal Criminal Code Is a Disgrace:Obstruction Statutes as Case Study[J].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2006,(96):643.
[27]Paul H. Robinson. Reforming the Federal Criminal Code: A Top Ten List[Q].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1997(1):225.
[28]John F. Dobbyn. A Proposal for Changing the Jurisdictional Provisions of the New Federal Criminal Code[J].Cornell Law Review,1972,(57):1.
[29]Edward M. Kennedy. Federal Criminal Code: An Overview[J].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1979,(47):451.
[30]Ronald L. Gainer. Federal Criminal Code Reform: Past and Future[J].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1998,(2):45.
[31]Robert H. Joost. Federal Criminal Code Reform:Is It Possible?[J].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1997,(1):195.
[32]Louis B. Schwartz. Law Reform of the Federal Criminal Laws: Issues, Tactics, and Prospects[J].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77,(41):2.
[14] Paul H. Robinson. The America Model Penal Code:A Brief Overview[J].New Criminal Law Review,2007,(10):319.
[15]Robert H. Joost. Simplifying Federal Criminal Laws[J].Pepperdine Law Review,1986,(14):1.
[16]Herbert L. Packer. The Model Penal Code and Beyond[J].Columbia Law Review, 1963,(63):594.
[17]Richard H. Brody.The Proposed Federal Criminal Code:An Unwarranted Expansion in Federal Criminal Jurisdiction[J].Criminal Code,1978,(39):133.
[18]Albert J. Harno. Som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in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in the Last Century[J].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1951,(42):427.
[19]Roscoe Pound.The Formative Ear of America Law [M]. 2th ed.New York :Little Brown,1938:12.
[20]Kathleen F. Brickey.Criminal Mischief: The Federalization of American Criminal Law[J].Hastings Law Journal,1995,(46):1135.
[21] John Quigley. The Federal Criminal Code Revision plan:An Epitaph for the Wellburied Dead[J].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1979,(47):459.
[22]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4.
[23]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10.
[24]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76.
[25]Shael Herman. The Fate and the Future of Codification in America[J].The Amei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1996,(XL):407.
[26]Julie R. OSullivan. The Federal Criminal Code Is a Disgrace:Obstruction Statutes as Case Study[J].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2006,(96):643.
[27]Paul H. Robinson. Reforming the Federal Criminal Code: A Top Ten List[Q].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1997(1):225.
[28]John F. Dobbyn. A Proposal for Changing the Jurisdictional Provisions of the New Federal Criminal Code[J].Cornell Law Review,1972,(57):1.
[29]Edward M. Kennedy. Federal Criminal Code: An Overview[J].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1979,(47):451.
[30]Ronald L. Gainer. Federal Criminal Code Reform: Past and Future[J].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1998,(2):45.
[31]Robert H. Joost. Federal Criminal Code Reform:Is It Possible?[J].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1997,(1):195.
[32]Louis B. Schwartz. Law Reform of the Federal Criminal Laws: Issues, Tactics, and Prospects[J].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77,(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