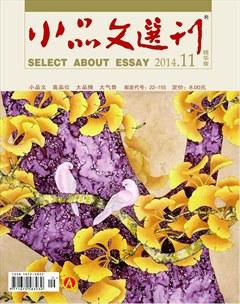舌尖上的无知与偏见
佚名
一
作为一个正宗的南方人、湘西的土家女,小时候我对面这种东西几乎是到了厌恶的地步。当然,一个人厌恶一个地方的食物,莫名其妙地也会厌恶那个地方的人。
读大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一个北方女生,每天早上去食堂买五个馒头,一粒米饭都不吃,中午晚上都打菜,然后就着两个冷馒头啃得津津有味,还要感叹“一点儿没我姥姥蒸的好吃”。惹得我们三个地地道道的湖南人背后总要嘀咕,说那样的一个面疙瘩,干巴巴,无滋无味,有什么好吃不好吃的。后来居然还排斥到觉得吃面的人又粗又莽又蠢,可北方美女也丝毫不跟我们一般见识,照样啃着她的馒头,腰圆体壮,就像那个馒头一样。当然,这个干粮渐渐成为我们半夜饿肚子时的佳肴,谁饿了,一定能在她的饭盒里找到个冷馒头,来点儿湖南风味的老干妈辣椒酱,津津有味地啃一顿。到了毕业的时候,我们三个湖南妹抱着这个“馒头女”哭得一塌糊涂,还相约以后一定要到她家里去吃她姥姥蒸的馒头。
十二姐写了一篇文章,里面说肉汤可融化一颗心。说吵架后男人莫名其妙回了家,看见肉汤里还放着一个黄澄澄的荷包蛋,立刻心下柔软。有人回复说:“真有人往肉汤里放荷包蛋?×,还不如给狗吃。”然后借此抨击整篇文章,说是傻女人做的事情。一向淡定的十二姐暴跳如雷,骂道:“真是连狗的情趣都不如。”其实嘛,那篇文章讲的就是我,我就是那个往肉湯里放荷包蛋的傻女人。
二
当我们因为不理解然后不尊重北方人的一个馒头的时候,一个异乡人也会认为湖南人的肉汤窝蛋是狗吃的东西。一个地域的食物总会与那个地方的人紧密地联系起来,嗜辣如命的湖南人搞不懂上海人又放盐又放糖是个什么滋味;上海人同样不明白湖南与四川的这些乡巴佬把自己麻辣到眼泪鼻涕乱成一糟还喊爽是个什么心态。
我们不知道是厌恶一个地方的食物才厌恶那里的人,还是因为厌恶别家的人而连人家吃的东西也要一并厌弃。我在广州漂泊的时候,恨死了那种细不溜秋像方便面的“细蓉”,觉得是放了塑料,不然怎么会咬起来那么脆响,死活也不肯吃。后来才知道那是南国有名的竹升面,那样的爽脆来源于用人力对面的不断碾压,才有那样的好劲道。一碗云吞面的背后,是劳动者的汗水。而我,因为讨厌那个快节奏与工业化的城市,才会偏见到觉得人家的面里头都放了塑料。
这个国家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到无法形容,也养育了个性截然不同的子孙。
当漂泊过后,尘埃落定,才懂得一块儿面皮里包一坨肉那种叫饺子的东西为什么让北方人魂牵梦萦。南方人不太吃这个东西,当然也少有七大姑八大姨围坐在家里包饺子的情景。对于北方人而言,一个素饺子也是一个家,正如于湘西人而言,一块黑不溜秋的烟熏肉才是家。我们开始品尝另一个地方的食物,才开始懂得另外一个地方的情分。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幸运,曾经在漂泊的时候,尝到过本地房东送给你的一碗面或是一碗饭或是一个馒头,才让你这个从来不爱吃面或者不吃米饭或者不吃馒头的人第一次懂得了那个地方的味道。你的胃、舌尖,开始接受这个地方,你的心,才慢慢开始变大,接纳这个地方的人。正因为有一日,阿婆给饥肠辘辘的我煮了一碗竹升面,我才知道什么是无与伦比的竹升面。如今回想起广州,那位阿婆,不知道是否还在。
三
看《舌尖上的中国》看到肉夹馍那一段儿,我几乎要跳起来跟老公说,我吃过这个,可好吃了。他很疑惑,说你没去过西安,怎么会吃过这个。我回他:当年大学的楼下有个摊儿,我们都称老板为肉夹馍王子。那个陕西男子长得浓眉大眼,他的媳妇儿也有着红扑扑的脸蛋。一个肉夹馍代替了我在大学里所有的消夜记忆,也赐予了我圆润到如今的身材。如今再和大学舍友聊起那个肉夹馍王子,那种味道,已经再也找不回来了。那不是湖南的味道,那却是青春的味道。那种味道让你的舌尖上也长出一颗心,凭着这样的味道,你笑,你也哭,你爱,你也痛。
所以,当长沙的无名粉店,爆出用下粉的锅子洗拖把的巨大丑闻时,整个星城都愤怒了。我们管早上吃饭,叫嗦粉,嗦这个字,形容着吃粉时那个吸溜和爽利的场面。一碗米粉一个清晨,一个清晨一个好天,这是长沙人对于生活的最初记忆。当谁毁了这一碗粉,也是给那份记忆上浇了一瓢脏水。
当我们知道超市里那个肉粽可能是隔年芯,一条假冒的金华火腿可能是病猪肉时,我们从来不会怨恨这些食物,我们只憎恨人,是那样的无知,毁了对食物本该有的尊重。
舌尖上的中国绝对不是一颗烟幕弹,相反,我觉得它是一颗照明弹,让我们清清楚楚看到食物,原本纯粹而珍贵。不纯粹不珍贵的,是那些被钱迷了心智的人而已。我们会更加热爱食物,更加痛恨这些人。
所以,我能想象每个异乡的湖北人看到挖藕人的那集会不会泪流满面,进而想到家里的熬锅里那块儿淡粉色的湖藕,配着母亲的手不断搅动。每个漂泊的湖南人看到烟熏肉的时候会不会喉头哽咽,想起那样炭黑的一块儿,被父亲的手提着烧洗刷熬过后,会变成你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肥白瘦红的浓郁香味。每个上海人心里都有糖醋的味道,每个草原人心头都深藏着一抹奶香。当我们懂得了那些食物,才会懂得那些人,才会懂得乡愁。
四
正如古时作为富庶的鱼米之乡出来的子孙,一开始我们当然会鄙薄面。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新鲜蔬菜,哪里会喜欢那样平淡无奇的面,哪里懂得窑洞里的阿妈、草原的阿婆在缺乏维生素和蛋白质的环境里,拿着一种叫面或者叫鲜奶的东西可以玩出百般花样的智慧。我们惦记那些吃着不同食物的挚友,我们的心头,终于有了最真诚的尊重。从此,我们听到觉得不可思议的食物,都不会忙着鄙薄,而是惊叹过后说:“教我!怎么做!”我一个南方人可以对兰州拉面情有独钟,开着车到星城去寻最好吃的拉面。东北菜馆里曾经被我说成是猪食的一锅乱炖,那点儿底汤泡饭已经成为我的最爱。
其实食物没有高低贵贱,有爱的人更没有高低贵贱。
那是食物,那是家,那是我们的朋友,那是我们的爱人,是我们头顶的天,是我们热爱的这片土地。
《大河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