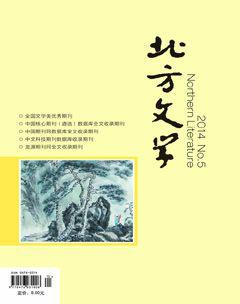论文学作品翻译之“变通”
摘 要: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离不开翻译。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艺术,译者不应该拘泥于原作品一词一句的得失。恰当的“变通”可以再现原作品的情感和美感,从而使文学作品在另一种文化里重新获得生命力。
关键词:文学翻译;再创造;变通
一、为什么要变通
当今时代,外国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了解中国,更想深入了解中国。中国的文学作品不断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然而,相对于外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的数量和质量,中国的文学作品被译介成外文的量还是很少,被外国读者所阅读,接受并喜欢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笔者认为,为了争取国外的读者阅读了解并接受中国的文学作品,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必须做适当的变通。
变通并不是对原作品随意的修改变动。文学作品翻译的变通即不拘泥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在不改变原作品意思的前提下,对原作内容或舍弃,或增加,或加以改变,以达到让译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原作品的目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西方读者有很大的不同,翻译时要充分考虑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迎合”他们的阅读需求。我们一贯主张的“归化”翻译原则其实就是一种变通,因为“化”即“变”, “变”则“通”。变通的道理很简单,作者进行创作时,他心目中的读者不可能包含译语读者,作者的审美观、价值观,所处时代和文化的语境特征也与译文读者的知识结构相差甚远,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文化鸿沟。诚如E. Sapir 所言,分属于两种不同文化的语言“在表述同一社会现实时是不可能完满一致的。”[1]所以,文学作品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变通。尤金•奈达说过,“优秀的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它既是再现,又是转变,因为它的目的是要在本义和联想义两个方面达到表象上与结构上的真实”[2]在我国,文学大师郭沫若先生很早就提出了“翻译即创作”的观点,他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法国文学家埃斯卡皮更是提出了“创造性叛逆”这一文学术语,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谢天振在《译介学》中对创造性叛逆也作了论述:文学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和叛逆性是根本无法分开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3]
“信、达、雅”是世界各国从事翻译工作人员的一个准绳,也是一个较切合实际的标准。 从文学翻译的实践来看,在翻译中要做到绝对的“信”是比较困难的。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尽量使译文符合原作者当时所要表达的内容和主题思想,其根据还是作者的作品本身。那种逐字逐句直译的做法通常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译法往往是从“信”开始,但以“费解”而告终,原作的内容完全未能表达出来。所以片面强调“信”的结果反而是“失信”。而恰当的“变通”译法可以让译者走出“死胡同”,让译文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理想境界。
二、什么时候需要变通
既然“变”是为了“通”,那么在读者读不通的情况下,译文就要做适当变通。例如文学作品常常用到双关语,因为双关语机智幽默又意义深刻。但双关语的翻译永远都让译者倍感头疼,甚至完全放弃努力,因为很多情况下,按照原文字意翻译,译文读者是读不通的。其实翻译时做适当变通,双关语同样可以在译文里绽放光彩。请看下面一则英语双关语:
Marriage is an institution where a man loses his bachelors degree and a woman gets her mastersstatus,
直译:“婚姻是一所学院,在里面男人失去学士学位而女人得到硕士学位”。
可是这样片面追求“信”的翻译,有哪位汉语读者能够读懂,读通呢? 把一则妙趣横生的双关语译得不着边际,“信”又何来呢? 翻译是将一种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言语的意义与内涵移植于另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中。比照这则双关语的汉译,其所蕴含的“意义与内涵”到底在“另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中”得到了体现没有?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要真实再现这个句子的意义与内涵,就需要译者做适当的变通。可以试作如下翻译:
“婚姻是一所医学院———男生入学主修“气管炎(妻管严) ”,女生入学主攻“肤必治( 夫必治) ”。
这种大刀阔斧的变动在有些译者看来是对译文的大不尊重,是冒翻译界之大不韪。 殊不知,这就是变通。诚如奥泽洛夫所说,“翻译艺术中存在着一个奇妙的辩证法,并为无数实践所证实,接近原著有时反脱离原著,脱离原著有时却是接近原著。” [4] 如果从传递语义信息的角度讲,这种改译的确离谱; 但从传递原文诙谐幽默的效果讲,已经达到了目的。
再看下面一例翻译:
原文:“这么着吧,伙计,我给三十五块钱吧;我要说这不是个便宜,我是小狗子;我要是能再多拿一块,也是个小狗子!” ---- 《骆驼祥子》
译文:“How about this, young man—Ill give you thirty five yuan. Id be a liar if I said I wasnt getting them cheap, but Id also be a liar if I said I could give you even one yuan more.”---- 葛浩文译
这段话描写的是一位养骆驼的老者与祥子就三匹骆驼讨价还价的一幕。老者为表示他的坦诚与直率,两次使用“小狗子”一词,这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狗”一词卑劣性的一面。在汉语中,很多词都被用来形容对狗的贬低,如“狗腿子”、“偷鸡摸狗”、“狗急跳墙”、“人模狗样”等。然而,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对“狗”的态度恰恰相反,认为狗人类忠诚的朋友,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有很多谚语都是褒扬狗的,如“love me, love my dog”、“a lucky dog”等。正是考虑到“狗”在中西方文化中内涵的差异,翻译时做了变通,将“小狗子”译为“liar”,以避免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试比较穆木天先生和傅雷先生翻译的《欧也妮 葛朗台》
英文:The hand of this woman stanches the secret wounds in many families.She goes on her way to heaven attended by a train of benefactions.The grandeur of her soul redeems the narrowness of her education and the petty habits of her early life.
穆木天译:这位女儿的手,给所有的家族的隐秘的创伤绑了绷带。欧贞尼,被那些善行的一个行列伴随着,走向天国。她的灵魂的伟大,减轻了她的教育的狭隘和幼年生活的诸习惯。
傅雷译:这女子的手抚慰了多少家庭的隐痛。她挟着一连串的善行义举向天国前进。心灵的伟大,抵消了她教育的鄙陋和早年的习惯。[5]
比较这两个译本,可以看出穆译基本顺着原文译,字真句确,非常忠实于原文,认真但显得迂腐。而傅译本则比较灵活变通,没有拘泥于文字的限制,重在传意,读起来比较顺畅。时至今日,穆的译本已鲜见,而傅的译本则流传甚广。
傅东华先生翻译的《飘》在第一代中国读者中影响十分深远。在今天看来,他的译本用语灵活多变,行文自然,清楚明了。为了让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他有意将男、女主人公Red Butler 和Scarlet 译成了颇具中国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译入语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不同,尤其是译文读者对原文化的接受。因为不同文化的读者,其审美意象、伦理道德观等是不同的,而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让读者阅读。因此,译者必然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从他们的接受能力出发,对原作进行恰当的“变通”,否则,翻译的目的便无法实现。
三、“变通”翻译之意义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学界对于其作品与翻译的关系予以了关注。不少学者认为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在世界文学殿堂获得最高荣誉,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翻译葛浩文先生。莫言本人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翻译对于文学创造的重要性,他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了对译者的尊敬与感激,并邀请英语、法语、瑞典语和日语的译者共同出席诺贝尔奖颁奖礼。他在诺贝尔晚宴中致辞说:“没有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为世界的文学。”莫言站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对译者对于原作所作的具有创造意义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葛浩文无疑是现代文学翻译界一个多产高效的翻译家。他翻译了莫言,老舍,巴金、萧红、李敖、贾平凹、王朔等中国近现代作家五十多部长篇小说,经他翻译的短篇小说更是不计其数。我们研究一下他的翻译可以发现,他的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翻译,甚至不是逐段翻译,有人说葛氏的翻译其实更可以说是整体的 “编译”,如果单从忠实的角度看,并不能算好的翻译。 但经他翻译得文学作品却在西方英语读者中广为流传。在西方英语世界,“如果你曾读过一本在过去二十年里任何时间出版的中文小说的英译本,那么它有可能就是由葛浩文翻译的”[6]
葛浩文先生的译作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能够从西方英语读者的接受角度审视问题,翻译时做到融会贯通。他的变通理据非常明确: 以读者为重。他认为翻译的责任很大,“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文本,对得起读者”,“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读者,而不是作者”,“因为翻译不是给作者看,也不是给译者看,而是给读者看,即读者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他反对僵硬呆板的死译、直译。宣称,真正摧毁翻译的是硬译(literalism)。大凡有翻译经验者都会认同葛的做法。“忠实”过度的译文不可能再现原文的深刻内涵和语言的精妙。[7]这种以读者为中心的变通译法尽管有悖于传统的译论,但实践证明却是成功的翻译。正如林纾的翻译,林纾不懂外文,在合作翻译出的译作中有意或无意删节、增补或改译原文的现象非常普遍,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的译作受到读者的喜爱。
意大利著名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安伯托•艾柯认为,在创作中,作家并没有给作品一个确定的、一成不变的顺序,相反,他提供给公众的是一个可以重组的、有多种选择的作品。这也是文学的魅力之处。国内读者的阅读是根据自身的经验对作品加以阐释,而译者首先是个阅读者,那么翻译就是跨语言、跨文化意义上的译者对于作品的另一种阐释的尝试,这也是文学作品开放性的一种体现。文学作品的价值也就在不断地被理解、被接受的阅读过程中得到拓展。通过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中国众多作家及其作品走向了世界文学殿堂并获得认可。贾平凹的《浮躁》于1991 年荣获美国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姜戎的《狼图腾》2007 年荣获第一届曼氏亚洲文学奖,2012年莫言更是凭借其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中国文学界取得的这些成就,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功不可没。
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译者的劳动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变通”是文学翻译的基本属性。中国文学翻译要帮助中国文学“走出去”,译者首先得有开放的心态,敢于舍弃和变通。中国文化的特色更多是通过精神和思想来体现的,一字一词的得失或改变不会影响中国文化的精髓。译者只有“变通”意识指引下才能最大程度的摆脱原文形式的束缚,进入“再创造”的心态,从而再现原作的情感和美感,让西方读者也能欣赏到中国文学作品的无尽之美。
参考文献:
[1]Sapir. E. Culture,Language and Personality[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168。
[2]安新奎. 翻译教学与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 2) : 43
[3]谢天振.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137
[4]张传彪. 变通乃翻译基本属性. 中国科技翻译,2012,(5):41
[5]罗新璋. 释“译作”[M ]// 金圣华,黄国彬.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138-140
[6]Berry, Michael. The Translators Studio: A Dialogue with Howard Goldblatt [J]. Persimmon: Asian Literature, Arts,and Culture, 2002 (2): 18-25.
[7]侯羽,朱虹. 葛浩文为读者负责的翻译思想探究[J],燕山大学学报,2013,(6):94
作者简介:王卫红(1976-),女,河南省滑县人,硕士,讲师,现就职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翻译和跨文化研究,英语语言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