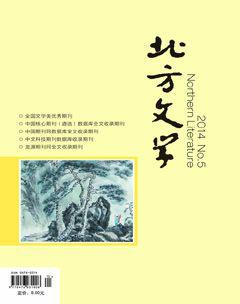浅谈翻译研究中的话语政治
摘 要:以福柯权力话语理论作为理论来源,后殖民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翻译已不在是单纯语言转换的过程,而是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要求把政治、权力和意识等外部因素纳入翻译研究领域,拓宽起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揭示了翻译的社会性,为翻译研究更深远更广泛的探究提供了坚固深厚的理论根源,而话语分析通过文本语言的批判审查,使得深深隐藏在文本中的预设逐渐地显现出来。
关键词:后殖民理论;知识与权力;话语分析;话语政治
引言:20世纪初, 以索绪尔结构主义为基础的翻译科学派的研究范式把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言学模式中解脱出来,使翻译研究走上了系统化的道路。后殖民文化研究对翻译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使翻译面临了一次巨大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学者多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将翻译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考察,这就使翻译研究有了新的理论视角。在福柯看来,知识本身就是权力,话语本身就是权力的体现,一种话语的出现以压抑和剥夺其他声音出现为手段。当然,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权力并不等同于政治意味上的权力含义,虽然它并不完全排斥后者。本文讨论的是在一种特殊化的话语分析路径下,来探视话语是如何在某些特殊的社会状况下生产出一种新的,复杂的话语。通过这样的文本分析,语言不再被理解为透明的工具,它同政治和制度有复杂的建构性关系。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揭示了翻译的社会性,为翻译研究更深远更广泛的探究提供了坚固深厚的理论根源。
一.关于后殖民理论
罗宾逊(D.Robinson)对后殖民主义的定义::“后殖民主义 ( postcolonialism) 是起源于殖民主义经历及殖民主义终结之后的一种文化状况和文化研究状况。 关注反映在语言,文化,法律,教育,政治等等与群体身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1997;121)”。[1] 虽对其涵盖的研究领域颇有争议,但根本的一点是它主要研究殖民终结后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文化话语权力斗争。或者说, 后殖民除了关心不同文化差异还关注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权力之争,反映在学科领域, 提供可借鉴的方法论。 受福柯理论的影响,“后殖民理论”或“后殖民研究”呈现为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因此,后殖民翻译研究观察的是在历史语境下进行的翻译活动背后存在的隐形的文化或话语权力之争。历史性的翻译行为均受一定的文化政治制约和操控,影响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翻译功用。这个视角把翻译回归到他所承载的正式的历史文化背景下, 为本土翻译提供了问题意识。
二. 福柯的 “知识”与 “权力”关系
法国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对思想体系史进行的所谓 “考古学”的研究实际上是探索知识与权力之间不可跨越的内在联系。 福柯确定话语的特殊性, 对话语方式做出差异分析,他认为知识是从话语与科学之间的特殊关系中得到自身定义, 其知识考古学所观察的就是在话语实践上产生的知识。他将所有层面上的话语实践从历史的角度去描述话语间的相互关系, 认为 “权力”在话语实践中起决定作用, “人类知识的积累都在权力对话语的影响下构建下形成的。 而翻译作为知识的主要传播媒介, 其话语实践应放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考察。”[2] 在福柯看来,翻译的透明性只是乌托邦似的意象。更重要的是,“话语是一种具有本身的连贯和连续形式的思想实践,它深深的扎根于其他书籍,其他文本,其他句子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络中。此外,它还要受到话语之外一系列非话语因素诸如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的影响。” [3](p1)“福柯认为知识考古学对话语形成的描述分析不同于一般理论和思想史的写作方法,因为一般思想史的写作都把‘时间衔接和连贯的现象作为基本主题,按照发展的模式分析这些现象,进而描述话语的历史脉络,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与之相反,‘考古学在描述话语形成的同时,忽略可能出现在其中的时间体系;它寻求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各个时代皆有效的普遍规律( 米歇尔 福柯:知识考古学,北京: 三联书店,1998年6月,第213页)可借助知识考古学即局部话语分析的方法学的方式…”[4](p11)
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研究语料。而要理解严复对几个关键词的翻译,首先了解其当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至关重要。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国家这一“他者”的强行闯入,“自我”即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而固有的文化不足以应对外来危机。 因此,“西方这一异质的‘他者文化的理解和应对,遂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重建民族‘自我所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课题,其他种种学术问题,都与此密切相关。中华民族立国的问题,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成为各派政治思想家所力求解决的重大问题。严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系统翻译引进了近代西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名学(逻辑学),法学,政治学等学说,并发表了大量系统阐发中西文化关系及中国里国道路的文章和论著,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5] (p4) 促使严复翻译此书有一定的社会,政治与制度动因,严复的翻译体现了本土文化与原本所代表的近代西方文化是如何通过翻译实践与译者的母体文化融为一体, “社会”“国家”“民族”“小己”等一些最为重要的观念是如何实现交融互释,而这些观念的解释对未来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安排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透过这些关键词,可看出严复是如何融会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文化, 这不仅涉及到中文与英文两种不同语言文字所代表的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之间的转换。因此,研究近代国家的历史,似乎不可避免的会提及到“国家”、“民族”、“国民”(“个人”“小己”)等基本概念。这也是严复《社会通诠》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 此处只讨论严复笔下“国家 ” “民族 ”的含义。根据王宪明先生对于严复《社会通诠》的研究,西文中表示国家的“ state”一词出现较晚,英语中“state ”一词最早出现于13世纪。这类团体集力量(might)权力(power)与权威(authority)于一体。古罗马人用“共和国”(res publica)来描述类似于国家的组织。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第一次使用国家(state),法国思想家鲍丹提出国家“主权 ”说。至19世纪,国家“三要素”说(领土,主权,人民)基本定型。西方民族国家的思想发展因起特定的历史环境,国家更多的带有强力,强权和暴力色彩。中国古代无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国家”观念,中文中的 “天下”大致与“state”相当。秦统一全国后, “天下”与“国家”从形式上构成“天下国家”。在甄克思的观念中,国家并非是为某个团体而言,而是为全体而言,国家是自然形成,无好坏之分,每个国家都拥有主权。严复观念中的国家已不是西方那种充满暴力的国家观念,而是中国传统的“天下”国家的概念,即多“人道”的意味。西文中的“ nation”一词来自古拉丁语的“ natio”,古罗马人用此词指外人。17世纪,“ 民族”一词含有“领土的”(整个国家的人口)“文化的”(祖先观念)意义,可与country互相替换,而nation被视作主权国家并有不同的文化和风俗。 “race” 指同一系统的部落,民族。“Tribe”一词属中古英语指罗马人的一个分支,与race 强调的血缘和nation强调的领土文化不同,带有宗教色彩。中文中的“民族”一词通常被研究者认为等同于“族类”等。“民族”一词出现于中国是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部分留日学生开始介绍政治学说,将日文词“民族主义”介绍到中国开始。因文化因素,这一时期的译者,一方面用“民族”一词来翻译不同的外文词或等同于不同的西文词,主要有nation, race, people, tribe等。而另一方面,这些西文词又有不同的译法,如nation有“人民”“民”“国”“邦”“族”。这就决定了这些词在不同语言环境的转换中注定会发生相互纠缠的情况。[6] (p 100) “甄克思所指的tribe,是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政治组织,也是建立现代社会之前必须首先破坏的社会组织。甄克思所指的nation是指在消灭了前述tribe 这一政治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近代的或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政治组织。”[7] (P 110) 在他看来,race是“人类学或人种学意义上的人种,种族…”。中文中原无“民族”概念,从严复译文内容来看,“种族”与“种人”主要是以血缘为纽带结合在一起的群体。严复将tribe译作“种人”“种族”对应于“blood or race”,严复将 “clan”译作“族”,表达的都只是相当于中国社会中由四世同堂所组成的团体。可以看出,“严复所说的‘民族不是对应于甄克思原文中的nation,而是对应于原文中的‘tribe、 ‘clan 、‘patriarch 、‘communities等数个不同的词,基本意思主要指处宗法社会阶段的 ‘宗族‘家族等社会组织,是建立近现代国家过程中所必须扫除的过时之物”。 [8] (p 121) 可见,严复笔下的“民族“与今天理解的 “民族”有很大差异。这种文本间的分析使得话语分析同时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分析。重释了两种语言的接触和碰撞和跨语际翻译的历史过程。翻译活动从来都受到政治、制度、文化等外部因素制约,而知识作为权力的一种表征,以话语得以体现。
三.“语际书写”命题下的话语政治
刘禾的“语际书写”以“语言的互译性”的基点为思想史写作寻找新的理论框架,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义和新话语被接受在译语中的原因是否与这一语言与另语言的最初接触和碰撞有难以纠葛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个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里得到了(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 翻译已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9] (P 7) 刘禾探讨了“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在中国的话语实践是如何在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下进行运作。鲁迅又是如何面对“国民性”的两难处境。“self”有何以等于“己”?其意义是如何给定的,“self 与 individual间意义的滑动,反映了跨语际书写及其政治运作在中国环境里的复杂情景”(刘禾 p38)。如此文化政治制约在译入外来词语的过程中有哪些可寻求的话语痕迹呢?
例如,“private”这个词在英语和汉语中是如何取得对应的呢?在英语中,“private”指 “个人的”,与‘public/公共的相对应。从这里派生出一系列的概念:“private property/私有财产” “the rights to privacy/隐私”; “private law/私法”,在英文中 “private”引起的主要是褒义的联想,是由强调个人的独立性。相反,在汉语中最接近“private”的对词“私”的内涵却与之甚远。当然,它也与“公”相对应,现代汉语中,也有 “私事”、“私有财产”等表达方式。但是,语义上的对等全然不同。汉语中的“私”让人联想到的是“自私”“自私自利”“私心(自私自利的动机)”“隐私(不体面的秘密)之类的表达。 “私”常常和耻辱联系在一起,与意味着无私、公平和正义的“公”相比,它是不可取的。再如,“freedom/自由”一词首先表达出来的观念是免受或者脱离专断权力的支配。其先决条件是承认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对立。而在在现代汉语中(经由日语转译过来)并没有传达脱离于专断权力的含义。相比之下,更多的是这两个字的字面意义——按某人自己的意愿行事。诸如“革命”“民主”“经济”等词在译语中的游离又何曾不是对翻译对政治的隐语?[10]
结语:可见,历史话语分析作为一种阐释行动,研究一种语言在进入另一种语言时,其意义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本文将跨语际下翻译活动所涉及的话语分析,话语政治并在后殖民语境下通过福柯知识考古学,刘禾对语言痕迹的搜寻来透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中语言时,在翻译这一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话语的有译语意义是如何被历史地给定以及翻译的外在因素如何制约翻译这一历史活动。翻译已不在是单纯语言转换的过程,而是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语言也不再被理解为透明的工具,它同政治和制度有复杂的建构性关系。另外,历史的,后殖民语境下的话语实践--翻译行为,在跨文化转换中也无法摆脱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对话和权力话语的支配。那么,翻译就不仅仅是语言与语言之间单纯的意义对等,它是语言的交际行为,更是两种语言在权力话语之下进行的交流与对话。话语分析并不对各类社会问题,各类思想(如现代性)提供出一个切实的答案,但它为在翻译研究的微观层面上所涉及的问题提供了批判性的主张和研究路径,从而使隐藏在话语背后各种预设通过话语分析得以显现。
参考文献:
[1]Robinson,Douglas. Translation and Empire[M].Manchester,UK: St Jerome,1997.(转引自王东风) 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 中国翻译(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2003,(4):3-8
[2]朱安博.翻译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话语[J] 中国翻译,2005 , (2): 10-13.
[3][4]张清民. 话语与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6][7][8]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刘禾. 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10]黄宗智.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文章来源:法律思想网 (中文版原载《开放时代》,2005,(4)
作者简介:都庭芳,就读于青海师范大学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