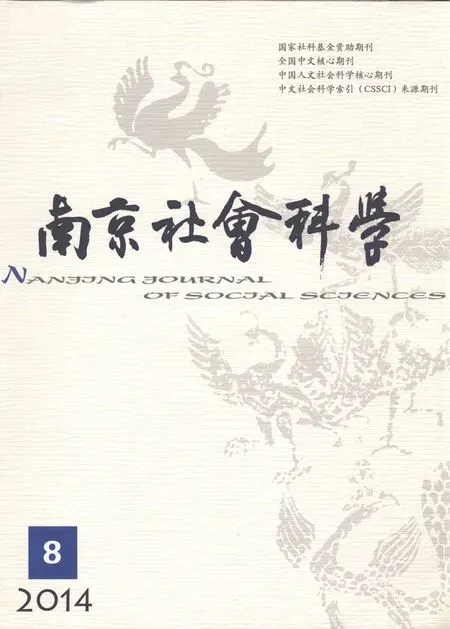中国城乡居民政府信任及其影响因素
王毅杰 乔文俊
中国城乡居民政府信任及其影响因素
王毅杰 乔文俊
基于2010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比较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类社会群体对中央和地方两层级政府的信任差异,并从利己主义、文化主义、户籍制度、世代四方面探讨了影响因素。分析发现:总体上,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依然“央强地弱”,但不同户籍下的居民政府信任则呈现不同特点。利己维度的阶层地位、文化维度的权威主义价值观和人际信任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均显著影响。而教育年限和政府责任认知仅对中央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世代因素则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显著。
政府信任;城乡比较;利己主义;文化主义;世代
一、问题提出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呈现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政治格局总体稳定、社会问题多发凸显”的特点(李培林,2011)。同时,伴随着社会成员流动空间与交往范围的扩大,传统熟人社会正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这一过程中,很多由人际信任承载的功能正逐渐被系统信任承担(郑也夫,2001),系统信任尤其是政府信任的作用和地位变得日益突出和重要。
政府信任是民众在与政府长期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政府的一种信赖与期待,是衡量民众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指标。政府信任水平过低,会阻碍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增加社会成本(马得勇,2007),而高水平的政府信任,则能增强执政者的合法性,实现社会有机整合,有效提升民众对国家和个人未来前景的信心,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保障(李砚忠,2007)。
那么,当前我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状况如何,又受哪些因素影响呢?本文将以2010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资料为基础,比较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类社会群体对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的政府信任差异,并从利己主义、文化主义两个维度来探讨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0世纪60、70年代,政府信任研究在西方政治学界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而学者们对政府信任的产生机制主要有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利己主义、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主义两种解释路径。
(一)利己主义
利己主义从个体角度出发,指出民众会对政府提供的各种物品和服务进行计算,从而做出对政府信任与否的理性判断。具体而言,人们会将对社会经济环境的感知与自身的期望进行比较,如有落差,就容易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换言之,较差的政府绩效和办事能力会导致不信任(Nye,1997)。民众在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中,不但会权衡潜在收益与潜在损失,还会对失信造成损失时自身的承受能力,即相对易损性进行分析(王绍光、刘欣,2002)。一般来说,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的人,其所拥有的资源越多,相对易损性越低,就越可能倾向于信任政府。因此,本文将阶层地位作为利己主义的体现,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阶层地位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民众的阶层地位越高,对政府越信任。
(二)文化主义
虽然利益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行动,但“由‘观念’创造的‘世界的意象’像扳道工一样”(Weber,1978),常常决定着受利益动力驱使的行动驶向何方。在文化主义者看来,道德标准、价值观和人际信任等文化观念都影响着民众政府信任水平的高低。
在对“文化”的解读中,有研究者指出,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则形成于个体早期社会化阶段,是对政府信任具有更为持久影响的文化因素(王正绪等,2011)。其中,权威主义价值观作为传统文化的典范,表征着个体对于中国特殊政治文化的认可程度,因而是中国政府信任的一项重要解释变量(Shi,2001;后梦婷、翟学伟,2014)。马得勇在政府信任的国际比较中也明确指出,权威主义价值观是影响中国政府信任的重要文化因素(马得勇,2007)。
与此同时,受到传统文化和集体化时期的影响,中国人对政府的责权认知较为模糊,往往将各类社会事务都视为政府责任范围。而这种观念则深刻塑造了他们的政府信任。因此,对政府责任的认知是文化主义的重要体现。
当然,文化对个体的塑造不能脱离其社会化过程,而教育作为社会化,尤其是政治社会化的最重要机制,对政府信任意义非凡。官方意识形态正是通过正式的教育渠道向民众传授各种政治信息和文化观念,从而使政治社会化成为可能(孟天广,2014)。不过,教育还具有启蒙作用,它会唤起民众的批判意识,也会向人们传递同情社会弱者的价值观等(李骏、吴晓刚,2012),这些都可能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此外,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溢出”效应(Mishler & Rose,2001),也是文化主义的重要体现。人际信任来源于政治体制之外,但却有助于政治制度的运转。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际信任水平普遍较高,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集体合作,包括民众的社会参与、政治参与,进而对该地区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产生提升作用(福山,2001;帕特南,2001)。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文化主义维度因素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
假设2a:受权威主义价值观影响程度越深的民众,对政府越信任。
假设2b:政府责任认可度越高的民众,对政府越信任。
假设2c:不同受教育年限的民众对政府信任是有差异的。
假设2d:人际信任水平越高的民众,对政府越信任。
(三)户籍制度
作为一项特殊的制度安排,户籍制度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农业与非农业户籍居民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进而表现出不同的政府信任态度。有研究指出,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的评价略高于城市居民,但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却低于城市居民(胡荣,2011)。但也有研究认为,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普遍要低,且表现出对基层政府更不信任的趋势(高学德、翟学伟,2013)。所以,本文将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户籍制度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影响,因政府层级不同而有所差异,其影响机制也会有明显差异。
(四)世代影响
最后,我们还需要分析不同年龄人群对政府信任影响的差异,以检视世代效应。有研究认为,政府信任是终身学习的过程,个体的政府信任水平是其终生政治经历的加权总和,因此政府信任会因年龄因素而产生个体差异(Mishler & Rose,2001)。史天健(Shi,1999)就在其研究中发现,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更加积极、开放,乐于接受变革,他们更可能通过参与政府抗议等活动来表达政治诉求。有研究进一步指出,这种年龄差异即为政治代际。在中国,不同政治代际的政府信任差异显著,年龄越小,越会表现出对政府的不信任(孟天广,2014)。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不同世代的人对政府信任是有差异的。年龄越大的民众,则越信任政府,反之则越不信任政府。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测量
我们使用的数据资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联合部分高校进行的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调查范围覆盖了港澳台以外的所有省份,最后获得样本11785个。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分析样本限于18-70岁的受访者,其中非农户口样本有5178人,占48.1%;农业户口样本有5578人,占51.8%。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政府信任。以“您对于下面这些机构的信任程度怎么样?”,包括“中央政府”和“本地政府(农村指乡政府)”加以测量。并将选项“完全不可信”、“比较不可信”和“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合并为“不信任”,将“比较可信”和“完全可信”合并为“信任”。
利己维度的阶层地位,以“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群体居于顶层,有些群体则处于底层。‘10’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加以测量。
文化维度中,人际信任通过“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来测量,选项“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和“无所谓同意不同意”合并为“不信任”,“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合并为“信任”。
权威主义价值观,以“您是否同意老百姓应该服从政府”测量,将“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和“无所谓同意不同意”合并为“不服从”,将“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合并为“服从”。
政府责任认知,则通过“政府能通过收税与支出来减少贫富悬殊”和“政府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减少或缓和社会不平等”两道得分加总测量。分值越大,表明对政府责任认可度越高。
教育年限,以“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包括目前在读的)”测量。我们对教育程度进行了赋值,“文盲”=0,“私塾、小学”=6,“初中”=9,“中专、技校”=11,“职高、高中”=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
户籍制度则根据受访者目前的户口登记状况,分为非农户口与农业户口两类。
世代则以年龄反映。本研究中,年龄为18岁以上70岁以下的连续变量。
各变量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分析结果
(一)政府信任现状
通过表2可以看到,在全样本中,有88.7%的被访者认为中央政府“完全可信”或“比较可信”,仅3.5%的表示“不可信”。可见,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非常高。但相较而言,中国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明显偏低,只有63.9%的被访者表示地方政府“比较可信”或“完全可信”,而且多达16.7%的明确指出地方政府“不可信”。这表明,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存在层级差异的,呈现“央强地弱”,与以往研究一致(Li,2004;胡荣,2007;高学德、翟学伟,2013)。

表2 不同层级的政府信任状况
另外,不同户口类别的民众对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信任也有着明显差异。在非农业户口群体,有85.1%的民众认为中央政府“完全可信”或“比较可信”,而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比例只有62.9%;对地方政府“完全不可信”或“比较不可信”的有15.3%,而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比例低至4.7%。与此同时,拥有农业户口的民众呈现出更高水平的政府信任,表示“完全可信”或“比较可信”中央政府的民众占92.2%,比非农户口多出7.1%,“完全可信”或“比较可信”地方政府的民众占65%,比非农户口多出2.1%。
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央政府相比,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表现出“更加模糊、更加矛盾”的特点,例如在全样本中,对中央政府“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的只有7.8%,而对地方政府却高达19.4%。在农业户口样本、非农户口样本中也具有类似发现。
那么,中国民众的政府信任为何呈现上述特征?接下来,通过农业与非农业两类居民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比较,来分析其中原因。
(二)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因变量是二项变量,因此笔者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来统计估计。在模型中,除了纳入前述变量外,为考察阶层地位和年龄是否与政府信任存在非线性关系,笔者还纳入了阶层地位平方和年龄平方。统计结果见表3。

表3 中国居民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注:(1)政府信任的参照类别为“不信任”。a的参照类别为“不服从”;b的参照类别为“不信任”;c的参照类别为“农业户口”;d的参照类别为“女”。(2)***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利己主义维度中,除模型5外,阶层地位对政府信任均有显著影响,即民众的阶层地位越高,政府信任程度也越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2和模型4中,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阶层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说明随着阶层地位的提高,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几率(odds)增加,但是达到一定阶层地位后,这种信任的几率开始下滑。这说明民众在对地方政府信任进行主观判定时,并非完全符合利己主义假设。
就文化主义而言,权威主义价值观、人际信任这两个变量在所有各个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检验。这表明,在中国,以权威主义价值观和人际信任为代表的文化因素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对政府信任有很强的预测力。如在全样本中,权威主义价值观每增加一个单位,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几率就提高约173%(e1.004-1=1.73,p<0.001),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几率提高约123%(e.800-1=1.23,p<0.001)。
相较前两个变量所发挥的稳定正向影响而言,文化主义中的政府责任认知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影响有差别。我们发现,与权威主义价值观和人际信任不同,政府责任认知在所有中央政府信任模型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地方政府信任模型中则不然,仅在非农业户口群体中且是0.05显著水平上获得通过。这意味着,政府责任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不像其在中央政府信任模型中的那样显著和稳定。
同样地,教育也在所有中央政府信任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值,具体而言,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非农业户口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几率就下降约4.4%(1-e-.045=0.440,p<0.01),农业户口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几率也下降约4.2%(1-e-.043=0.420,p<0.05)。可以看出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不管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人群,对中央政府呈现出更不信任的趋势。其可能原因是,现代教育发挥了启蒙作用,使得民众将当下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增多等现象归咎于中央政府。而对于地方政府信任而言,教育却并未显现出此种影响。教育努力给公民塑造的较高层次的社会理想及道德要求并未与日常生活紧密对接、呼应,而且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区域性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更多的民众对地方政府态度模糊而复杂。
就户籍制度而言,可以看出在全样本模型中,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群体对于中央政府信任有显著差异,但对于地方政府信任却无差别。具体而言,控制其他因素之后,非农业户口居民比农业户口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几率低了将近37%(1-e-.467=0.371,p<0.001),呈现出更加不信任中央政府态势。
进而对不同户口样本所构建的模型进行比较,发现对两类户口样本而言,各种因素对于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具体而言,第一,权威主义、政府责任、教育年限和人际信任都是影响两类户口人群对中央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而阶层地位只对非农户口居民的中央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第二,阶层地位、权威主义、人际信任和性别都是影响两类户口人群地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而政府责任认知仅在非农户口居民、年龄仅在农业户口居民的地方政府信任模型中影响显著。
此外,年龄也是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变量。具体来说,年龄在模型2和模型6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效果相同。这说明年龄是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但与孟天广(2014)的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年龄并非与政府信任呈线性关系。年龄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几率减小,而到了一定年纪后,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几率则增加。
需要指出的是,年龄仅对地方政府信任尤其是农业户口的样本有显著作用,而对非农户口的则没有;年龄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尽管都为正向,但都没有通过检验。已有研究证实,重大的历史变动和政治事件会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达米科等,2012),进而在不同政治代际间呈现出显著差异(孟天广,2014)。而对于政治代际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它在不同群体对各级政府信任的机理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其历史脉络。
五、结论
本文利用CGSS2010的数据资料,探讨了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状况,比较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类社会群体对中央和地方两层级政府的信任差异,并从利己主义、文化主义、户籍制度、世代四方面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政府信任现状呈现出“央强地弱”的总体性格局,不同维度因素对中国政府信任的影响在城乡两个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显现出不同效果,且对不同层级的政府信任影响机制也不尽相同。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深层的文化因素和户籍制度因素是影响政府信任的关键。文化因素方面,在所有中央政府信任模型中,人际信任、权威主义价值观、政府责任、教育年限均通过了显著检验,均对民众的中央政府信任水平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对提高中央政府信任而言,不仅仅需要发挥中央政府自身功能,而且需要中央政府之外的一些措施给予保障。中央政府出于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中最高也是最核心位置,代表全体民众实施对经济社会管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其职能的发挥和定位以及对民众利益的考虑将直接影响到民众对其的信任。同时,在社会中也需要积极建立人际间普遍信任的良好氛围,加强国家政治宣传教育,为提升政府信任奠定良好的基础。
而在户籍制度层面,呈现城市居民比农民对中央政府更不信任的现象。近年来,随着政策的放宽,社会流动不断加强,与农业户籍捆绑的资源配置正向效果正在不断加强,负面效果正在减弱,而对于城市居民则没有明显改变。2004年至今,中共中央已连续十一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使农民切实感受到,中国政府为促进农业生产、改善农村建设及提高农民福利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而长久以来,在中国,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多倚靠单位而行,因此多会将公共物品的提供归咎于政府,有事找政府的观念根植于心;但对于终生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们而言,靠天吃饭,靠自己能力讨生活的观念,促使他们对于公共物品的分配和获得更多是靠协商、自治来加以解决,而非动辄就去找政府。对此,各级政府需要坚持、切实地履行好政府职责,同时在资源分配中、在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需要关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群体在面对与制度相伴而生的机会和境遇时,所产生不同的生活态度与心理预期。
相较中央政府而言,民众对于地方政府信任的因素更趋个体化。除了权威主义价值观、人际信任这些文化因素,个体层面的阶层地位等因素均在所有地方政府信任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检验,同时,年龄、性别也是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因此,针对影响因素的个体化倾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要妥善处理好社会资源再分配的问题,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缩小社会成员间的差距,在努力提高居民社会生活水平的同时,还应重点加大对社会中层的保障力度,扩大社会中层群体的数量,进而有效保证和提升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1〕Li,L. J.,2004,“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ModernChina,30(2):228-258.
〔2〕Mishler,W. & Rose,R.,2001,“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ComparativePoliticalStudies,34(1):30-62.
〔3〕Nye,J. S. Jr.,Zelikow,P. D. & King,D. C. Eds.,1997,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M 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4〕Newton,K.,2001,“Trust,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and Democracy”,InternationalPoliticalScienceReview,22(2):201-214.
〔5〕Shi,T. J.,2001,“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ComparativePolitics,33(4):401-419.
〔6〕Shi,T. J.,1999,“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in China”,World Scientific.
〔7〕Weber,Max.,1978,Economy and Societ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8〕A.J.达米科等:《政治信任与不信任的模式:民主政治中的公民生活》,张巍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0期。
〔9〕福朗西斯·福山:《信任:杜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
〔10〕后梦婷、翟学伟:《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基于五城市的抽样调查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1期。
〔11〕高学德、翟学伟:《政府信任的城乡比较》,《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2期。
〔12〕胡荣:《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13〕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李骏、吴晓刚:《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15〕李培林:《我国发展新阶段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16〕李砚忠:《政府信任: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学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第4期。
〔17〕马得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5期。
〔18〕孟天广:《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信任:实证测量与全貌概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19〕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20〕王正绪、德拉干·帕夫利切维奇、郭承斌:《公民与民主:史天健对中国研究及政治学方面的贡献》,《开放时代》2011年第9期。
〔21〕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责任编辑:宁岩〕
GovernmentTrustandItsInfluencingFactorsofUrbanandRuralResidentsinChina
WangYijie&QiaoWenju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0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this paper compares differences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trust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four aspects of egoism, culturalism,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generation. The findings are: Overall, there is still the trust structure of weak local and strong central government in China, howev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rust in government under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Class status of egoism dimension, authoritarian values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of culturalism dimensio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trust. The years of education and the cognition on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rust, and generation factor affects the local government trust significantly.
government trust;comparis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egoism;culturalism; generation
王毅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南京 210098;乔文俊,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南京 210098
C913
A
1001-8263(2014)08-007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