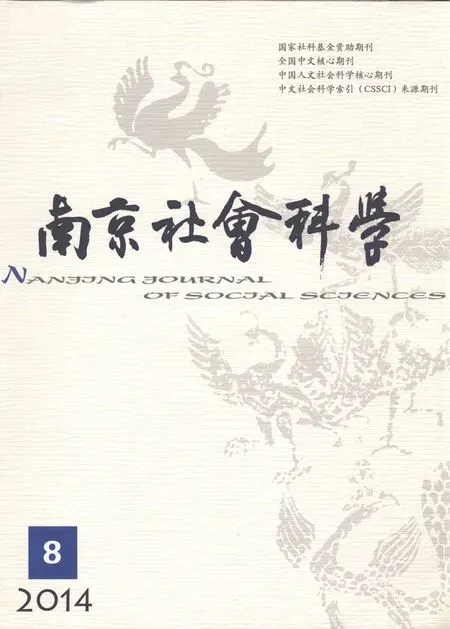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语境与当代使命*
王占魁
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语境与当代使命*
王占魁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公”字具有指称“尊长”、“诸侯”、“国君”等社会伦理和政治多方面的主体性内涵。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公”字的主体性内涵,又相继经历了从指称国家(政府)的“公家”,到面向全体国民开放的“公域”(公共领域),再到可以直接面对国家的个体“公民”的演变。这一平民化的历史演变路线,昭示着当代中国公民教育在确认全体国民作为“合法公民”政治身份的同时,还必须改造传统儒家“家国一体”、“公私不分”的血缘、亲缘和家族伦理模式,从而使当代中国公民在当前的流动社会中承担起对“陌生人”的道德责任。与此同时,为有效抑制作为公权力执行者的官员之私,应当使“公家”成为中国“法治公民”的质询对象。它意味着,“公域”,不仅应当成为“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交往平台,而且应当同时成为“公民与公家”之间的交往平台。惟其如此,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我们才能形成一种个体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可以普遍通过自主选择成为“法治公民”、“道德公民”和“荣誉公民”的教育生态。
公家;公域;公民;公民教育;中国语境
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变革,我们会发现:自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民主”观念的引入,在“天子皇权”去神圣化的同时,传统中国儒家人本主义也受到了西方原子式个体主义的极大挑战,一时间人们竟不知该借助何种文化去解读这个舶来的“公民”身份。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短短十余年时间中,随着“解放”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中国民众一面表现出对“公域”和“公家”的热烈欢迎,另一面也暴露出“臣民旧习”对“公民新政”的适应不良。从“多党轮替的议会民主制”到“总统独裁的行政威权制”,再到“党国体制”的政治转型,诠释着中国现代政治以“私意”、“国家”和“人民”代表“公意”的不懈尝试。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在日常话语里,还是在理论表述中,中国民众对“公民教育”的理解时常在东方与西方文化的摇摆中纠缠不清。为此,要想明确当下中国“公民教育”的时代使命,我们有必要首先厘清“公民”在中国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具体涵义。
一、中国古代“家国一体”、“公私不分”的家族政治传统
自20世纪初,一直有人批评国人缺乏“公共意识”:做事只顾个人利益与方便,不懂经营公共生活,不擅处理公共事务。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一涉公字,其事立败”(《国民浅训》,1916)。此后,国人开始大举检讨自己的文化。对此,黄浚认为,清末中西方相反的文化情态凸显了近代国人“公共意识匮乏”的问题:“予意以为东西俗尚所判,即在于国人最重男女礼节之防,而于公私之分,反熟视若无睹。西人则反之。其实公私之分,即是义字,古圣贤所教导甚明,后人渐泯忘其界。唐有不书官纸者,史已称其美德,则公物私用之恶习,相承已久。海通以来,外交久视为专科,而献媚教谄之逸闻,指不胜屈。滥用官物,犹其余事。”①简言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最看重的是“男女之别”和“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信条,而非“公私之分”的法理观念;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人们首先看重的则是“公私严谨”的法理精神,而非“男女之别”的道德规范。
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一差别的关键所在,20世纪初,梁启超曾参照日本学者福泽渝吉在《文明论概略》中对私德与公德的区分方式,向国人引介关乎“群”的“公德”和关乎“己”的“私德”概念:“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而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梁启超认为,传统儒家所授国人之德性皆为私德:“如《皋陶谟》之九德,《洪范》之三德,《论语》所谓温良恭俭让,所谓克己复礼,所谓忠信笃敬,所谓寡尤寡悔,所谓刚毅木讷,所谓知命知言,《大学》所谓知止慎独,戒欺求慊,《中庸》所谓好学力行知耻,所谓戒慎恐惧,所谓致曲,《孟子》所谓存心养性,所谓反身强恕,凡此之类,关于私德者发挥几无余蕴,于养成私人之资格,庶乎备矣。”②不过,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儒家这种“庶乎备矣”的私德教育,对于“完全人格”之养成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在《论公德》中曾极力呼吁中国加强“利群”、“利国”的公德教育。然而,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早已形成了一种要么(对统治者而言)“公私不分”、要么(对平民百姓而言)“公私对立”的思维习惯,换言之,国人一度是在“以公灭私”的意识形态下理解“公德教育”的,致使当时中国的“公德教育”成效甚微。故此,时隔不到两年,梁启超又在《论私德》中为“私德”正名:“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③在梁启超看来,虽然传统儒家所教私德“庶乎备矣”,但是,现实中的中国国民,不仅缺乏利群利国的公德,同时也缺乏独立自主和修身养性的私德,而且,归根结底,公德缺乏的最终原因乃在于私德的缺乏。在笔者看来,国人在对“公德”与“私德”观念认同上的双双失败,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公私不分”之专制政治弊病的一种生动表征。
另据台湾学者周法高的研究,在甲骨文、金文当中,“公”主要是指“祖先”、“尊长”或“国君”④。后来,作为“国君”的“公”字,又被人们引申为“朝廷”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或“政府”。所以,笔者这里所说的“公私不分”并非笼统意义上的,而是以“家国一体”为前提的“公私不分”——即说,按照“朕即国家”的理念,皇帝本人就是国家的象征,从而“国家”也就是“皇家”(皇帝的家),由此所产生的政治组织形式(政府),也往往具有鲜明的家族特征,比如:唐朝的李家、汉朝的刘家、宋朝的赵家,等等。与此相应,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开始或结束,似乎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家族统治的结束或开始。所以,古代中国的公私不分,首先指向了国家“皇帝的公私不分”,之后才在“垂直权力”运行机制下衍生出民间“庶民的公私不分”。进一步而言,按照国人所习惯的那种“概念对生”的价值原则:如果“国君”代表了“公”,那么“臣民”就代表着“私”;如果“国家”代表了“公”,那么“个人”就代表着“私”。在这种“公私对立”的认知传统中,“私”只有“消极”(不论是从权力象征的意义上来讲,还是从生活实际的意义上来讲都是如此)的意义,因而,代表“私”的“臣民”和“个体”几乎难以逃脱“不被肯定”、“饱受压抑”和“终被灭亡”的命运。究其根本原因,正如郑观应(1841-1923)在19世纪末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传贤”的禅让制变为“世袭”的君主制之后,“以举国为私产,兆庶为奴隶”,结果君臣相与追求私利,“熙熙攘攘之民遂交受其害而不得复沾其利”⑤。其中原委,亦如黄宗羲(1610-1695)所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厉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⑥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政体分类中,这也正是“为了公众利益的君主制”与“为了私人利益的僭主制”的根本区别。然而,在金戈铁马的暴力政治和强权统治面前,人们终究是“不敢过问”统治君主究竟是如何在“为了公众利益”的庄严承诺下践行“为了私人利益”的事实的。与此同时,在政治启蒙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公”概念在“国君”和“国家”两种主体内涵之间的自由转换,也造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民众对有关“公家”、“公域”和“公民”命题的认同障碍。
二、中国近代“聚私为公”、“君民共治”的宪政法治探索
或许是出于化解“君民矛盾”和“公私对立”的考虑,或许是出于重新厘清“公”概念价值内涵的需要,早在明清之际,顾炎武(1613-1682)就曾提出以“国君之公”成就“国人之私”的主张:“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已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亭林文集?郡县论五》)“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为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日知录·卷三·言私其豵》)很显然,顾炎武所反对的“私”乃是公权力的行使者(如统治者或士人)有悖儒家“仁义”与“爱民”原则的“徇私”行为,而他们所肯定的“私”则是每一个个体的“合理之私”(如个人的“隐私”与“亲亲之私”等)。在笔者看来,顾炎武所提出的这种“合私以为公”的主张,与前面梁启超所谓“将私德作为公德养成前提”的观点,全都服膺从“自爱之美”(私德)到“爱人之善”(公德)递推的美善法则⑦。它意味着,不肯定“个体之私”,就无法达成“集体之公”。更为明确地讲,肯定每个人的“合理之私”,乃是人们构建“公”的出发点;讲求“公”的最终目的,也在于捍卫每个人的“合理之私”。
至20世纪末,即1899年,在“君主立宪”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在《自助论》一文中介绍了日本学者中村正直(1832-1891)翻译的英国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所著的《西国立志篇》(Self-Help,1859)。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借助“驾车”与“乘车”的比喻,阐发了一种来自西方世界的“积私为公”、“公私无别”的思想:“盖西国之君,譬则御者也,民人,譬则乘车者也,其当向何方而发,当由何路而进,固乘车者之意也,御者不过从其意,施控御之术耳。故君主之权者,非其私有也,阖国民人之权,萃于其身者是已。唯然,故君主之所令者,国人之所欲行也;君主之所禁者,国人之所不欲行也。君民一体,上下同情,朝野共好,公私无别,国之所以昌盛者,其不由此欤!”⑧不难看出,梁启超在这里所讲的“公私无别”亦即“君民无别”的意思,具体是指,统治者依照被统治者的愿望执政,就能达到“天下为公”或“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当然,这种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还意味着公民的“政权”与政府的“治权”相平,亦即“民权力”与“公权力”相互制衡。换言之,“国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其有自主之志行。……盖总称曰国,分言曰民,殆无二致也。”⑨具体而言,这种“君民无别”的实际内涵,诚如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宋教仁所言,“宪政”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立宪国民,其义务必平等,其最普通者,则纳国税是也。……一立宪国民,其权利必平等,其最普通者,则人人有被选举之权利是也。……一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⑩此外,“立宪国有行政裁判之制度,所以正行政官署违背法规损害人民权利之失者。人民对于违背法规损害权利之行政处分,得提出诉讼于特别机关,求其取消变更,特别机关乃裁判其处分与诉讼之孰为当否,而决定之,是之谓行政裁判,其特别机关,即为行政裁判所。……其裁判之结果,足使该行政处分受其羁束,监督官署,保护人民权利,固莫尚于此矣。惟其效力,乃在监督行政,只能使国家负其责任,与中国自古设立都察院之精意不合。”由此可见,“宪政”事实上包含着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平民政治”,即一切国民(包括君主或最高统治者)所享有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且受宪法保护;其二是所谓“君民共治”,亦即政府代理人民行使公权力,而人民享有监督公权力的代理者(亦即政府官员)的权利,同样受宪法保护。通俗地讲,亦即我们通常所谓“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对于政府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所承担的这种“为全体公民负责”的代理责任,诚如英国政治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所说:“只有在政治社会里,每个成员才都放弃了这种惩罚罪犯的自然权力,把他可以请求社会制定的法律给予保护的一切事情,都交给社会来处理。这样,每一个特定社会成员的一切私人判断都被排除了,社会成了仲裁人,用固定不变的法律来公正平等地对待所有当事人。社会授权给一些人,由他们来执行这些法律,裁决社会成员之间可能发生的关于任何权利问题的一切争执,并根据法律规定的惩罚措施来处罚任何成员对社会所犯的罪行。根据这条规则,就很容易区别哪些人是共处于一个政治社会中,哪些人不是共处于一个政治社会中。只要人们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拥有共同制定的法律,拥有人们可以向其申诉、有权仲裁他们之间的纠纷并能惩罚罪犯的司法机关,这些人就同处于公民社会之中。”问题是,随着“国君专制国”被转换为一种“君民共治国”,之前用以指称国君的“公”,也就被转换为一种所有国民共有的“公”。正因为如此,在这种宪政体制中,不但人民要“合私以为公”且以“公德”自律,立宪之君也应“为公而忘私”且以“公仆”自居。诚如严复所说:“立宪之君者,知其身为天下之公仆,眼光心计,动及千年,而不计一姓一人之私利。”换言之,“无论是谁掌握了国家的立法权或最高权力,他都应该根据既定的、当众公布而且众所周知的、长期有效的法律,而不能以临时的命令进行统治;应该由公正无私的法官根据这些法律来裁决纠纷。而且只有在对内执行这些法律,对外制止侵略或索取赔偿以及保障社会免受外来袭击和入侵时,才能动用社会的力量。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为了其他目的,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人曾一度习惯把“政府”和“国家”称作“公家”。进而,官府就是“公家”、“公门”,官服又叫“公服”,政府签发的文件又叫“公文”,打官司则叫“对簿公堂”——即使到现在,政府工作人员也仍然叫作“公务员”。
三、中国现代“克己奉公”、“大公无私”的党国体制
自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经历接连不断的政治大变动,建立新政治秩序的诸多尝试——君主立宪、士绅政治、民族革命、共和政体、地方自治、政党政治、军阀统治——都因接连失败而归于无效,国家的整体力量始终无法凝聚。到1920年代初期以后,许多政治精英决心以列宁式的革命政党为手段,进行组织、动员,并成立军队,夺取全国的政治控制权,借此建立他们心目中的国家秩序。这个新方向的出现,最终决定了以后很长时期中国的走势。其间,“个人利益”为“全体福祉”献身的观念,成为建设革命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其内在所包含的价值逻辑,恰如刘师培在《伦理教科书》结论中所说:“故欲人民有公德,仍自成立完全社会始。欲成立完全社会,贵于有党,党也者,万物之公性情也……盖各国均以党而兴,则欲兴中国亦不得讳言朋党……必先自民各有党始,然民各有党,又必自事各有会始,事各有会,庶对于社会之伦理可以实行矣。”简言之,就是要以“党”来建立“完全社会”。这种思想,首先要求党员为党的“集体领导制”效忠,再而要求国民遵从党所设定的目标。毫无疑问,国民党和共产党是这场革命运动中的主角。
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1866-1925)在总结既往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曾郑重指出:“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这是因为,“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非有很正确共同的目标,不能够改造得好的。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具体而言,“此次本党改组,想以后用党义战胜,用党员奋斗。……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今由俄国观之,则党人奋斗始能为最后之成功。今日有民国之名,而仍然失败者,何以故?则由于党人不为主义而奋斗之故。”“本党的三民主义,便是无形中改造人民思想的。何谓三民主义呢?简单的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的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项主义的意思,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我们将来的国家,做到了民有、民治、民享,便是世界上最安乐的国家;在此国家之内的人民,便是世界上最安乐的人民。”此外,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1879-1936)在1929年3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场演讲中就曾明确指出:“训政时期本来是培养一切,训练一切的时期,这件事如果及今不图,更待何日!所以赶紧把全体国民的行动统一起来去为公,去对外,正是我们同志应该立刻负起责任去做的工作。至于同志们在本党以内,在自己的一切行动上,如何还能有一丝一毫的不统一不为公与不对外呢!”
其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现代中国的“政治集体主义”开始与宪制政府的“公仆”观念发生关联。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次年7月,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必备的一个主要价值观就是“奉公”,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根据这个原则,在每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中,都要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这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总而言之……党员个人应该完全服从党的利益,克己奉公。”这是因为,“共产主义事业中一项极大的艰苦的工作,是要把人类改造成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民。”换言之,“公而忘私”不仅是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最终还是人类整体改造的目的。直到建国以后,面对一些人所谓“取缔政府”、“消灭国家权力”的诘难,毛泽东又说:“‘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值得肯定的是,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社会革命取得重大成果:“公天下”的“共和制”取代了“家天下”的“专制制”,天子的“特权”也被“公之天下”,转变为人民的“平权”。概而言之,无论是对国民党而言,还是对共产党而言,“立党为公”都是进行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价值基础。正是建立在这一个价值基础之上,党国体制才拥有了坚实可靠的道德依据。同理,当这种作为党国代表的“公仆”或“政府官员”出现言(说得好)行(做得差)上的不一致时,党国体制也将随之丧失其可靠的道德依据,并因而失去国民的信赖和拥戴。在20世纪中叶,国民党政府的溃败和共产党政府的崛起,便是最清楚不过的一例明证。不过,总体来看,近代国人所谓的“公德”观念,多半还是一个更具“政治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或许是迫于近代中国所面临危亡局势,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诸多近代学者才共同强调,“公德”应以“爱国心”为重,其主要目的也在于呼唤“能够为国献身的人民”,否则当时“一盘散沙”的中国就无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国家;相比之下,那种旨在培养“社会伦理”的公德问题在当时则处于次要地位。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一般也还是将“公德”概念的社会性内涵简单地“化约”为“爱国心”,而没能迅速将其转换为指向“公共心”或“公益心”的社会伦理建设。直到现在,中国人一般也不容易把“公”与事关人民大众的“社会伦理”和“公共领域”联系在一起,而更多是把“社会”或“公域”当作个人可以“任意活动”、“自由出入”的天地。这种情况诚如黄克武所言:在实然方面,作为社会范畴的区分,“公”一般指称“国家部门”(state sector),有时也包括地方公共事务;而“私”则指“非国家部门”(non-state sector),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个人与社会群体,如家族、党社等。在应然方面,作为道德价值的判断,“公”指称“利他主义”(altruism),“私”指追求自我利益,亦即强调一己的独占性,也包含“自私自利”(selfishness)。
四、“公域”成为现代政府和现代公民的养成平台
回顾20世纪前十年中国有关“国族主义”(又称“国家主义”)的讨论,我们大致可以将之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严复、梁启超所主张的建立在“新国民”和“新国家认同”基础之上的“政治性的国族主义”(political nationalism),它倾向于以“国民”的概念为中心,建立一个不分族群的、由“具有自由、权利之国民”组成国家;后者则是“种族性的国族主义”(racial nationalism),主张将这种国族认同转化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而成的民族国家,例如当时国内的“反满”情绪和孙中山早期所提的民族主义即是这一主张的生动体现。不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将“公民的国族认同”与“种族的国族认同”结合成为一种“革命的主张”,即首先推翻清廷的专制政体,建立一个属于整个国族(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最终成为国共两党的政治共识,并成为两党在各自执政过程中赢得民众公信的价值支撑。尽管市场经济的洪潮一度给中国(包括台湾)政界有关“克己奉公”的道德理想造成不小的冲击,但是,不管怎样,在主流媒体的舆论宣传中,“大公无私”仍旧是支配两党政府工作人员处理群己关系的重要价值导向。
据此,笔者认为,中国语境下的“公民”概念具有广泛的“能指性”:它不仅可以指称古代的国家主人(统治者)、享有公权力者(官员、士绅),也可以指称近代的全天下人(世界公民)、全体国民(合法公民),还可以指称现代中国的荣誉公民(烈士、英雄、模范)、道德公民(民间绅士、公共知识分子、志愿者、好心人)和法治公民(依法履行义务并享有权利的人)。其整体图景,如下表所示:

政体类型常用词例价值内涵主体内涵公民类型古代君主制周公、恩公、国公尊长/国君国王或皇帝最高统帅贵族制公堂、公帑、公署、公函政府/国家享有公权力者政府官员近代民主制(聚私利为公利)公约、公告、公理、公有全体/共同的全天下人、全人类世界公民公园、公厕、公交、公海公开/开放的每一个国民合法公民现代共和制立宪制(平等法治)公平、公正、公允、公道契约/协商伦理一切依法履行义务并享有相应政治权利的人法治公民社会伦理(君子美德)公德、公益、公害、公心、公共秩序、公共卫生为公众利益着想/利他的民间绅士、公共知识分子、志愿者、好心人道德公民党国体制(政党政治)克己奉公、大公无私、公仆为党国而献身烈士、英雄、模范荣誉公民
问题是,在城镇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征程中,“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原则和家族等级原则,它在当代的陌生人社会中已经暴露出了极端的不适应,成为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毒食品泛滥、以邻为壑等丑恶现象的文化根源和心理上的护身符,也导致了中国人在面对国际社会不能通过能效谈判达成共赢。这种不适应,主要在于中国传统“三纲五常”、“五伦六纪”的族群狭隘性和自然情感的非理性、无反思的本性,它妨碍我们接受国际通行并在正常的公民社会中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普世价值原则,总觉得那种原则是某些敌对族群的阴谋诡计。”与此同时,在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洪潮中,随着“官员腐败”问题在中国政坛日渐显现,从中我们也发现民众在公共领域不自为、官员在公共领域不自律的问题。由此可见,中国当前的“公民文化”与哈贝马斯所强调的那种以“公共政治文化”取代“国族公民”的公民政治理念还相去甚远。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公民教育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公共领域的活动中,诸如“不为私事使用工作单位的物品”、“在公事关系中不掺入私情”等这样一些常识性的公德观念尚且不能被国人所普遍认同和接受,人们依然习惯于按照传统“血缘”和“家族”圈层进行有关“社会性”的群落分割;另一方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官方的政治组织在尊重“庶民的合理之私”的同时,还缺乏有效抑制“官员的不法之私”的政治机制。与此相应,改造儒家的“亲缘伦理”和加强对“官员之私”的监督力度,已然成为现时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两项重要使命。
具体而言,这种“现代政府”和“现代公民”的形成,最终有赖以下两个方面的教育实践:其一是,遵照近代宪政讨论中有关国家(政府)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公共性内涵,赋予国家(政府)以“人格”的意义,即从“公家”的意义上来理解“国家”(政府)——进而,作为“合法公民”参与政治实践的基本形式,使得中国普通民众在其疑惑或者质疑“公家”行为正当性的时候,能够向“公家”(相关部门)依法提出质询,从而养成“公民(集体)”参与“公事”、有效监督“公权力”的社会伦理互动机制;其二是,以普遍的“社会伦理”(比如契约精神和商讨伦理)改造传统儒家的“亲缘政治”模式,使公民在当前流动社会中承担起对“陌生人”的道德责任,进而转变当前那种通过“市场化”的分解手段将“公域”(公共领域)私有化的做法,在实行“法治”(依法共治)的同时,实现中国民众对“公域”的理解从“纯政治性”向“偏社会性”的价值转向——进而,在切实保障一切普通民众成为能够依法履行义务和享有权利的“法治公民”的基础上,鼓励“公民(个体)”通过自主选择成为不妨害他人及造福社会公众的“道德公民”和能够为党国利益而英勇献身的“荣誉公民”,从而普遍提升整个社会对“国际通行并在正常的公民社会中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普世价值原则”的认同水平。重要的是,这一“政治问题”的解决,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提升官员的“道德意识”或者“服务意识”就能够得到根本解决。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手段还是要让民众切实地从政治实践中逐渐改变传统私德惯习,进而养成一种自觉履行义务和依法行使权力的法治精神。与此同时,它也意味着,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要让那些曾经得到政府嘉奖的“荣誉公民”们,首先恪守“法治公民”和“道德公民”的底线伦理,而不应使之成为进而在社会中“尊享特权”乃至“违法乱纪”的政治资本,抑或是他们借以享有不受人民监督之特权和摆脱法律约束的护身符。由此,我们就能在“公家”(政权)与“公民”(治权)之间形成一种通过平等对话依法解决双方权益纠纷问题的政治实践机制。它意味着,要让“公域”(公共领域)不仅成为“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交往平台,也要成为“公民与公家”之间的交往平台,进而使之成为中国培养“荣誉公民”、“道德公民”和“法治公民”的主要途径。
注:
①黄浚:《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页。
②③梁启超:《论公德》,《新民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7、163页。
④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7年版,第90页。
⑤【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⑥【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8页。
⑦王占魁:《“公平”抑或“美善”——道德教育哲学基础的再思考》,《教育研究》2011年第3期。
⑧⑨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自助论》,《清议报》第28册(1899),第5、6页。
⑩宋教仁:《清太后之宪政谈》,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页。
〔责任编辑:于是〕
TheState,PublicSphereandCitizenship:TheHistoricalContextandContemporaryTasksofChineseCivicEducation
WangZhankui
The term “public” in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has multiple aspects meanings which including social, political and ethical values. While the concept of “public” in Chinese context has transformed its subjectivities from “the king” to “the state” and then to “public sphere”, such a popularizing route has also indicated that China’s citizenship education not only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western concept of “legislating citizenship” which based on democratic politics but also should shoulder the mission of reconstruct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to undertake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others” in contemporary mobile society. To form a mechanism to restrict the private tendency of the government, which should not be put back on the old way of improving “moral education”, but to make sure “the state” become the object to which inquiries are addressed and by which found a political practical mechanism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tizens” to balance the rights disputes through consultation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That is to say, the “public sphere” should not only become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between the citizens but also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tizens”, and then the “public sphere” may become the main approach to form China’s “honorary citizenship”, “moral citizenship” and “legislating citizenship”.
the state; public sphere; citizenship; civic education; Chinese context.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转型期我国公民教育的哲学基础研究”(12YJC880112)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路径、方法创新研究”(12JZD001)的阶段性成果。
王占魁,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讲师、博士 上海 200062
G40
A
1001-8263(2014)08-01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