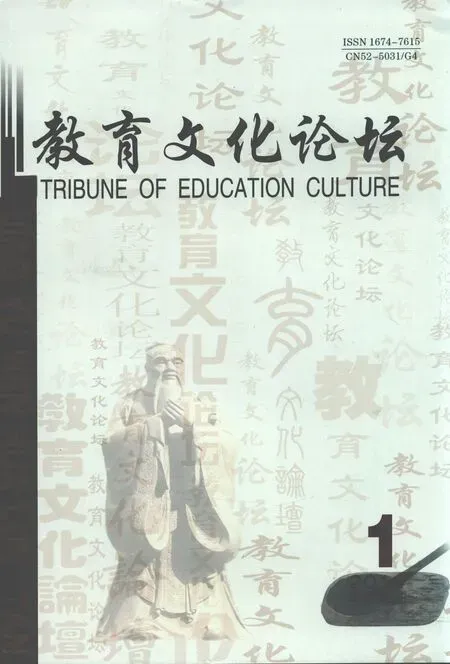刁培萼教授的遗产是什么
——用思维完成一个人
毕世响
刁培萼教授的遗产是什么
——用思维完成一个人
毕世响
编者按: 我刊顾问刁培萼教授于2014年1月8日去世,这位勤于治学可敬的老先生,在新年伊始,终于永远停下了他写不完的书稿,放下了他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牵挂和思考,远行天国。刁先生从我刊创办担任顾问至今,从未懈怠过对我们的关注和指导,尤其是刁先生严谨治学,甘于奉献、淡泊名利的精神,以及多年来给予我们的无私关怀和帮助,令我们感动和难忘!我们为失去一位好师长而痛心;我们为失去一位好朋友而哀泣。对刁先生的离去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在此特请我刊另外一位顾问,刁培萼教授的学生毕世响教授,撰文纪念。
教育可归结为思维教育
刁培萼老师“大行”了!
我觉得对刁培萼老师最大的纪念,是考虑一个根本问题:刁培萼老师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什么。我这样届知天命之年的老师,忝列教育学教授之门,说起自己老师辈的人,甚为复杂,因为,我似乎是说我的父母的一生。更微妙的是,似乎是我的学生在我像刁培萼老师“大行”以后,说着老师的什么。我在思考,若干年以后,我也会像刁培萼老师一样大行,我又会给后人留下什么遗产。
刁培萼老师于1950年上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我是1982年上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论学缘,他是我的老前辈,是我的老师,论年甲,他比我父亲还大11岁呢。二年级的时候他给我们当班主任一直到我1986毕业。期间,他给我们上《教育哲学》和《马列论教育》两门课程。他的夫人吴也显老师(1930年出生),和令狐昌毅老师一起给我们上《教育学》,令狐昌毅老师是1928年出生的,前几年已驾赴瑶池。所以,刁老师夫妻两人都是我的授业老师。自从我1999年又回南师上博士,我与两位师尊来往就多起来了,我毕业离开南京以后,刁老师吴老师已经不仅仅把我当作他们的学生,还是他们的朋友了,我们之间学术交流和问候很稠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三个学者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三个思维者之间的关系,师生关系只是思维的一个借口。
刁培萼老师是南京师范大学,特别是教育科学学院,一个叫人想忘都不能不能忘记的人,也是中国教育理论界一个叫人不能忘记的人。因为,他的思维已经触摸到思想的境界,我并不是说刁培萼老师已经是思想家了,我敢说刁培萼老师能够站在思想的立场上说话。我不知道这样说合适不合适:在中国教育理论界,能够达到思维的人,不多,能够达到思想的人,极少。2005年我来到福建师范大学以后,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老前辈李明德教授,也是刁老师的学术朋友(少刁老师一岁),还在我面前说起刁老师二十多年前提出的“自然·社会·思维”的教育哲学观念。他在80岁的时候,又在“自然·社会·思维”发展链与教育实践辩证法之后,提出第二个发展链与教育实践辩证法:“自然·社会·人”,把时代的“人”或者“人学”架构在教育实践上。我觉得这两个观念,应该是哲学上“思维与存在同一性”,“思维必然有一个思维者在思维”的教育思维,所以,我一直试图把教育学理解成思维,刁老师也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可归结为思维教育。”[1]
刁老师那个年代的学者,青年的时候以政府编译的马克思主义为学习,既下过功夫,又带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同时,他们经历了建国以后的每次政治运动,他们的知识与精神,都不再是纯粹的士,却是政治化的知识分子,我在他们那一辈学者身上甚有体验。我这个年龄的学者,也不是纯粹的士,也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我们的知识与精神有点不僧不道。我们对中国和外国的哲学与文化,东学一句,西学两行,“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地嘴上笔上翻飞,怪唬人的,却像孩子吃泡泡糖。所以,我和刁老师是两代知识分子,可能是两种文明形态的人。
刁老师的思维,并不容易被学生或者同行弄清楚,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没有哲学训练,大学老师和大学生根本就不会思维。在真思维真知识面前,我们往往并不表现谦虚,而是狂妄和愚昧,这很容易使我想起苏格拉底的话: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思想者的落寞是人类的常态,刁老师却不是一个落寞的人,他有自己思维的气场。刁老师的思维本身就是思想,就是思想者,就是人的观念,是我多少年以后才能够摸到的感悟。
我觉得,很长时间,刁老师是一个既能够叫所有人记住,又叫人不怎么懂得的人。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既寂寞又热闹的人。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三年际遇的热闹的学术场合,比我2002年博士毕业到现在际遇的学术场合还要多。刁老师的寂寞在于,他退休在家,他和吴老师的身体,不能出没于各种各样热闹的学术场合。那么,刁老师的思维,就不容易在没有受过他的教诲的老师和学生中传播,他们可能会听人说过刁老师的某些说法,却无缘当面领教;他的热闹在于,教育理论惯常的说法在我们唇齿间吞吐的时候,他的说法总会使我们的口舌搅得不实在,或者说,我们总会想起刁老师的说法,我们的内心有些虚。即使不同意他的说法的人,也往往会记住刁培萼其人其说,并且不能轻易地把刁培萼其人其说挥之而去,而刁培萼并没有缠住我们不放,是我们的思维缠住他不能放手。所以,我们这些聆听过刁老师教诲的人,无论操何业,总会在某个时候想起刁老师,如果几个人在一起,总会说到他。正是他的思维,使我们知道思想是怎么生成的。
完成一个人
一所大学,应该有不同年龄与阅历的几代老师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聒噪,把各种各样的人话、鬼话和神话像刮旋风那样祭起来,学生才能分辨出人、鬼、神,大学本来就应该是一个魔鬼和天使打架的地方。柏拉图说人性由人性、兽性和神性构成,知识就是基于人性的真实存在。而当下的大学老师,大都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上大学的人,实际上是单一文化群体的人,嘴里喷的是“政治正确”的标准答案,没有分辨人、鬼、神的知识,虽然名义上是老师,弄不好倒像乌合之众,更多的只是“教师”的名号罢了。所以,当下的大学什么都像,就是不像大学,大学老师什么都像,就是不像大学老师。
刁培萼老师出生于1927年,那是民国,大学给我上过课的老师,相当大一部分人是横跨了民国和新中国两个天地的人。系里的老师和学校的老师,是公孙的辈分,如教育系的教育学名教授罗炳之先生,是刁老师吴老师的老师。不过,我们当学生的时候,老教授们早已不出来上课,文化大革命把他们的知识和性命都革得差不多了,只给他们剩下了一点喘息的夕阳。老院长陈鹤琴先生,从50年代初起,他的活教育思想就受到当局的批判,他的教育思想被全盘否定,甚至1959年离开幼儿教育工作。刁老师和他的许多同学,当年考南师教育系,往往就是冲着陈鹤琴先生去的。在我上大学的1982年,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一代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辞世了,我等后生小辈无缘拜见教育家,却沐浴在教育家的学园里,也算浸染得几缕余辉。那么,给恢复招生以后的大学生上课,成就了刁老师那一辈人,也是他们的历史使命。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思想,刁老师等学生辈薪火相传。我想,正是这个机缘,刁老师才能成为新中国第一本教育哲学教材《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丁沅教授也是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前几年也驾鹤赴瑶池。丁老师出生于1929年。刁老师82岁的时候,又独立修订了这本书,以《追寻发展链:教育的辩证拷问》出版,也是他一生唯一的专著。《追寻发展链:教育的辩证拷问》的出版和我有些许关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老师的水平是教育理论界公认的,缺憾在于那些师尊们都不爱写专著。我把这个意思在电话里说给刁老师,希望他能够写一本专著,给他的身后留下东西。他很认真地考虑了我的说法,说:“我已经80岁了,不容易完成这个任务,我会努力。”当书出版以后,他给我说:“我完成了你的任务。我再给你一个任务:给我的书写一个书评。”我后来写成了10000字的文章:《跟着吾师去思——教育可归结为思维教育》(《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6期)。
刁老师另外一个开创是《教育文化学》。在他完成《追寻发展链:教育的辩证拷问》以后,也和几位老师一起修订。去年11月份我去他们家,他和吴老师还和我说了一些他们对这本书下的几年的心思,有些他本人以外的原因,使这本书没有顺畅地修订下去。刁老师患眼疾,几近失明,幸运的是,南京鼓楼医院高明的医生,刚刚使刁老师的单眼视力恢复到0.1,他可以重新拿笔撰写了。刁老师还拿出我的一篇文章讨论了一些文化问题。我希望南师的师友,能够把刁老师未竟的事业完成,这既是南师师友的责任,更是南师师友接续老师的使命。因为,这是刁老师为南师给中国教育理论界挣得的一份光荣。
刁老师为南师给中国教育理论界挣得的另外一份光荣是《农村教育学》,也是刁老师的一个开创。也希望南师师友不辱师命,拿出一个新的《农村教育学》。中国多少农村,在几十年以后就消失了。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进而太空文明转型的初期过渡,而中国人仍然是几千年前的农民!农民就是上了月亮,也只不过替嫦娥养兔子,替吴刚酿伐桂花树而已。教育要使中国人脱胎换骨,彻底改变气质,现在的教育是就业,以就业为目的教育不是教育,是职业养成所。其实,不接受教育,也能职业养成。对农民的关怀,是中国近代教育家和思想家的共同情怀,刁老师不是思想家,他却摸到了中国社会的根,也摸到了教育家的根,他的教育思维,站在了教育家和思想家的立场上。我们现在的教育学,农村与农民仍然阙如。
一家大学,一个专业,几十年上百年下来,最终必须积淀出几个人,几个学说。南师教育学,从三江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高师)、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无疑积淀了中国的教育学精魂;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南师教育学的师尊们,为中国教育理论积淀出了南山。南师教育学代表性的著作就是198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学》,俗称“绿皮《教育学》”,它应该是新中国《教育学》的代表作,标志着一个时代,到现在还没有哪本《教育学》能够达到它的意境。《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德育》、《教学论》、《教育文化学》、《农村教育学》等都是新时代开创性的,在这个积淀中,刁老师在几个方向,都有开创之功,刁培萼完成了一个人。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到现在的教育学,就是刁老师那一代人在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之间建立起来的一套体系,带有意识形态味道,我们仍然吃着他们那一代老师的饭,我们没有逃出他们的“魔爪”。刁老师那一代人在政治极权下为教育学挣得了尊严,我们才有当硕士、博士、教授的福分,刁老师一个人就在三个方向上有建树。所以,我们这一代学者有愧于我们的老师辈,我们没有为教育学挣得多少荣耀,我们想扔掉学术的意识形态,却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文化或者文明形态的学术体系,仍然溺陷于意识形态。尽管我们活得异常沉重,我的学生辈比我这一代人活得更不堪。实际上,正是人类的苦难成就了人类的光荣。所以,刁老师身后事,不是刁老师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南师一个学校的事情,应该是整个学术界的事情。
凌厉的南师教育学,最近十几年,竟然养成“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境界,哀哉!南师教育学后学,下面怎么完成一个人?绿皮《教育学》以后,会是什么皮的《教育学》呢?

2012年《教育文化论坛》副主编周感芬(左一)、李琼英(右一)到南京看望刁先生夫妇时的合影
注 释:
[1] 刁培萼.追寻发展链:教育的辩证拷问[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211.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李琼英)

刁培萼先生
——《教育学原理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