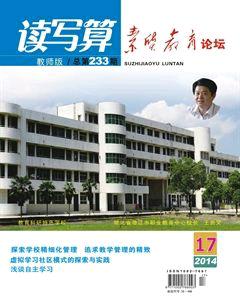论文学作品艺术阐释的未定性
原晓芸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7-0002-02
文学艺术世界是一个恢弘博大的世界,它包含了作者的人生体验和审美追求,成为读者作无限品味的自由广阔的天地。古人云:“声无听一,物无文一,味无果一”(《国语?郑语》)今人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精确地阐释之于文学艺术何其难矣!对文学作品作艺术的把握,是一个复杂的审美过程,文学作品的典型形象的复杂性、主题意蕴的模糊性、审美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艺术阐释的未定性。传统阐释中的那种章句训诂式的抱残守缺,狭隘单一的明白无误,只能肢解、扭曲作品的审美价值,误导读者,销蚀掉文学作品无限的丰富性、生动性及深刻性。研究文学作品的艺术阐释的未定性,正是为了使读者从评论家的视野中跳出来,在由读者积极参与的阅读过程中进入作品无限丰富的自由天地。从而深刻地把握美感效应的多样性,更好地发挥欣赏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作品的美感因素。
形成文学作品阐释的未定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典型形象、主题意蕴、审美个体几个方面予以论述。
1.典型形象的复杂性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是作家对现实生活艺术发现的结晶,是作品处于最高审美层次的艺术形象,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它除了一般艺术形象的特点外,还具有高度的审美独创性和丰富多彩的个别性。关于艺术典型复杂性,歌德精粹地概括为“单一的杂多”。在中国古典典型理论中,脂砚斋最是反对“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单薄浅显。成功的典型形象,总是呈现出多侧面的立体结构,表现出“单一杂多”,人物的性格以复杂性、流动性、以至于矛盾的对立性而存在。普希金曾将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创造的人物形象作比较道:“莫里哀的悭吝人只是悭吝而已;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是悭吝、机灵、复仇心理重,热爱子女而锐敏多智。”
《阿Q正传》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高高矗立的丰碑”。但对阿Q这一文学典型的争议,也是文学史上最为罕见的。解放后,数十位文学家为此撰写了二百多篇分析评论,不少高等院校曾举行过阿Q典型性问题的讨论,众说纷纭。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有的,似乎是人类普遍的弱点的一种,至少,在“色厉内荏”这一点上,写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茅盾《读〈呐喊〉》)阿Q性格的特殊并不在于他所代表的农民以外的人群而言,而是就在于他所代表的农民中,他也是一人特殊的存在。(周扬《现实主义试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奴隶的失败主义精华,奴隶的被压迫史,才正是阿Q主义的产生史。(冯雪峰《过来的时代》)对阿Q的“大团圆”的结局,至少在人格上不统一,似乎是两个(郑振铎《呐喊》)当前,文艺研究者认为阿Q是一个呈对立统一的圆形结构系统。他在性格上是一个具有两重人格的复合体:既朴质愚昧而又圆滑无赖,既率直任性而又正统卫道,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既争强好胜而又忍辱服从,既狭隘保守而又盲目趋时,既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不安于现状又安于现状,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胆小怯懦,敏捷而又健忘等等。对这样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典型人物,阐释为“尚未觉悟的贫苦农民”,“破产农民”⑤是“一个物质上受到残酷剥削,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的农民典型”⑥,远远不能准确地阐释出鲁迅创作这一形象的目的和态度(“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⑦)也不能帮助读者认识作家塑造艺术典型具有的高度的审美的独创性,丰富多彩的个别性以及人物的复杂性。
2.主题意蕴的模糊性
艺术的本质,是人对世界掌握的一种方式和对自身的肯定。文学艺术的活动,一方面要获得对于客观世界真理性的人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智慧和理想,以至于实现自己的品格和个性,满足于审美的需要。文学家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表现出与哲学家的不同,“一个是证明,一个是显示。”这种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特征的图情再现,必然表现出不确定性、多义性、甚至模糊性。优秀的文学作品,决不会“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总是把“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恩格斯甚至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文学作品不等于宣传品,不是那种朝生暮死的东西。经典作品的主题意蕴有着超越时代的永恒与随世推移的变更出新,在巨大的历史内容中隐藏着较大的思想深度。不同时代、不同的欣赏主体对作品的理解就会发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 。作为对作品阐释的评论家,不能是仅仅帮助读者去寻找概念、抽取意义,而是要引导读者在欣赏艺术形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多维多向地理解作家的美学情趣,理解作家对客观世界的理解评价,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作家在作品中所散发的思想感情。
李商隐的《锦瑟》一诗,辞彩华诞,形象鲜明。但主旨为何,一千多年来众说纷纭,见解各异。有爱情说的:锦瑟是令孤楚家中的一个女子的名字,李商隐爱慕过她,写此诗以寄情(刘攽《中山诗话》);有悼哀说的:是悼亡妻王氏(冯浩《玉溪生诗笺注》);有咏物说的:是写锦瑟这种乐器的,中国四句写适、怨、请、和中种声调(《彦周诗话》);有“自伤”说的,抒写自己落拓失意,“美人迟暮”之感(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还有人说是伤唐室残破的,真是“一篇《锦瑟》解人难”,其实我们只要透过那华丽的词藻,富于暗示的形象,抓住“思华年”这条追忆的线索,去咀嚼诗中间四个典型情境,就可通过字面而进入诗的意境。“庄生晓梦迷蝴蝶”,是夏夜,是喜;“望帝春心托杜鹃”,是春夜,是怨;“沧海月明珠有泪”,是月夜,是悲;“蓝田日暖玉生烟”,是秋日,是欢乐,它们交织出当年一年四时的朝、暮、日、夜的喜、悲、怨、欢,表出对逝去的美好年华的回忆,一种缠绵缱绻的情思。我们大可不必解得太实,说得太破。从而增强诗作的暗示性,给读者更大的想空间。
3.审美个体的差异性
在艺术阐释过程中,由于个体感受的差异性,形成了所谓“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的现象。差异的存在一方面给艺术探索提供了多侧面多层次的可能,给欣赏者的自由活动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艺术阐释的见仁见智或偏执一端,使艺术阐释显现不确定性。生活经验、学识修养、人生态度及审美情趣的不同,表现在艺术阐释中就形成欣赏的侧重点不同与欣赏效果的差异。
(1)生活经验的影响。王安石读到李贺的诗:“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认为不可思议:方黑云压城之时,焉有向日之甲光耶?杨慎却认为这是状物的佳句,讥笑“宋老头巾不知诗”,因为他曾在云南目睹过这种奇异的景象。
(2)文学功底修养不同。《祝福》,“我”与“四叔”见面后,“谈话总是不投机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对这个“剩”字,汪曾祺解释道:假如要编一本鲁迅字典,这个“剩”字将怎么注释呢?除了注明出处,标出绍兴话的读音之外,大概只有这样写:“剩是余下的意思,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孤寂之感,仿佛被世界遗弃,孑然地存在着了。而且,连四叔何时离去的,也都未感觉,可见四叔既是不以鲁迅(原文如此)为意,鲁迅也对四叔并不挽留,确实是不投机了。四叔似乎已经走了一会了,鲁迅才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剩在那里。这不是鲁迅的世界,鲁迅只有走。”
(3)审美层次的高下。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吴功正从社会历史意识层面予以审美阐释:表面看来,这是诗人写他晚年和著名歌手李龟年的会见。但在深层结构里,“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岐五宅里,崔九堂前,频频相遇,李龟年已是名重歌坛,诗人也已崭露头角在文坛。美妙动听的歌喉和诗人少年浪漫意气,都是跟烈火烹油的开元盛世相联结的。往事如烟,过眼即逝,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盛况只能留嵌在记忆中了。而时过了几十年,他们偶然邂逅,不是在岐王宅里、崔九堂,却是在“江南”、“落花时节”。好景不再,透露出伤感。其间的几十年,杜甫如转蓬也似的离蜀、入鄂,辗转漂到潭州。而李龟年也流落江南。其间的飘零各地,有几多家国兴亡,身世沦落;于晚年穷途相见,又有几多感伤,诗人却不正面置一词,全部凝聚在今昔相逢如此不同空间地点、“落花”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时节之中。在诗的深层次中是安史之乱的国破愁、家世悲,如黄生《杜诗说》所言:“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操笔,亦无以过。”
由上可见,文学作品的艺术阐释呈现出开放性、多义性和未定性,任何评论分析都有其相对的局限性。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审美价值永远不可能被什么人一次完整地感知。只有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积极地参与作品所叙述的事件,作品的审美效果才得以形成,艺术阐释者不应以全知全能的身份去教导读者,积极引导读者去挖掘,发现文学作品的丰富宝藏。总之,更好地发掘文学作品的美感因素的无限丰富性。使读者不必凝滞于评论家的既定模型,去独立地发现文学作品的新的审美价值。这就是探究艺术阐释的未定性的意义。
(责任编辑 全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