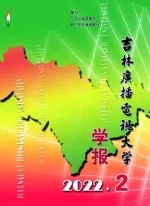论现代性语境下道德话语与伦理话语的错位
李依贝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 100875)
一、“善”与“正当”:两种话语体系的分离
在传统社会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德性伦理学话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和中国孔子的儒家伦理思想是典型的代表。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伦理学话语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等学说兴起,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规范伦理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这种转变从理论上主要表现为由“善”的优先性转向“正当”的优先性,从对象上则表现为以“行动者”为中心转向以“行为”为中心。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一个人拥有好的德性,也就同时意味着他是一个好人并且能够发出正当的行为,“对每个人来说,适合他的品质的那种实现活动最值得欲求。”由于行动者蕴含着行为,一个正当的行为就是他自身美好德性的实践过程。然而,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则更加重视对一个独立的行为正当性的考察,行为本身以及行为之效用成为了最重要的评价标准。这一转变在伦理理论的建构方法上体现得更为明显,无论中外,越是年代久远的哲学家似乎就越是喜欢探讨人性自身的善恶问题,理论构建也多从最根本的人性假设出发,重视人的德性特质,而越是近现代的哲学家,则越倾向于简化人性和德性的多样性,从而将个体抽象为一种可以普遍化规范化的无差别原子,以便寻求理论的普适性和有效性。如罗尔斯正义理论中对原初状态的设计——“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和“正义的环境”(circumstance of justice)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特征。他首先设定人们之间是互相冷淡的,即不愿为了他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简化起见,我常常强调客观环境中的中等匮乏条件,强调主观环境中的相互冷淡或对别人利益的不感兴趣的条件,这样,一个人可以扼要地说,只要互相冷淡的人们对中等匮乏条件下社会利益的划分提出了互相冲突的要求,正义的环境就算达到了。”
从“善”到“正当”的话语转变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更替是一个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在传统的熟人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具有常规性和反复性,交往空间范围较小并且比较稳定。这就决定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贯通具有较大的可能性,在以亲情、友情、宗教情感和传统习俗所联结起来的关系网络中,一种公共价值或公共精神相对比较容易形成。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逐渐消解,在陌生人社会的交往关系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分离。吉登斯将现代性的社会关系结构称为“被脱域的抽象体系中的信任关系”,传统的亲情、友情、习俗、宗教等因素远远不足以维系复杂而庞大的社会秩序,人们由此开始转向一种对外在规范化、制度化社会整合方式的诉求。由此逐渐形成的规范伦理话语致力于寻求一种社会公共认可的、尽可能广泛有效实行的普遍伦理规范,从传统的“交往型道德”转变为“制度型道德”,可以说这种转变是现代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二、“现代性道德危机”的根源
由现代性所引发的伦理主题的转变导致了两种伦理学话语体系的分离,即以“善”为主题的传统伦理学话语和以“正当”为主题的现代伦理学话语的分离。二者本质的区别,并不简单在于“善”与“正当”何者具有优先性的问题,而是在于:传统伦理学话语中的“善”与“正当”由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具有可以贯通统一起来的较大的可能性,但在现代伦理学话语中却由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而导致了二者之间明显的断裂,“善恶与对错分家”成为了现代伦理学话语的一大特征。由此随之而来的便是广泛的现代性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包括两个方面——现代道德生活世界的价值危机和现代伦理知识的合法性危机。
现代性道德危机的真正根源来自于现代性自身的矛盾,是现代社会固有的内在结构所致,是两种话语体系分离的必然后果。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德性之美与城邦之善是具有一致性的,德性之美可以推出城邦之善。中国儒家亦有“修齐治平”的家国同构理想,个体内在的德性和其外在的行为规范乃至社会的制度是可以贯通起来的。如前文所述,这种“一致”和“贯通”的可能性有赖于传统社会特有的社会结构和条件。在孔子的时代,即便那时的社会并没有一套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和一系列完善的规范化制度,但却可以通过道德教化将人的内在德性“外化”为社会的伦理规范,从而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例如传统意义上的“孝”这一伦理规范并非一种工具性的理论制定,而是源自于“亲亲之爱”的道德情感基础。于是人们在履行一个规范时,并不会认为是出于一种外在的制约和强迫,而是在实现他们自身的生命情感和德性价值。这样,“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可以说在传统社会,“道德的”和“伦理的”①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同步性和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传统社会的社会整合正是通过“内在道德价值”和“外在伦理规范”的统一而实现的。
现代性背景下伦理学话语的转变所带来的正是“内在道德价值”和“外在伦理规范”的分离,也就是德性话语与规范话语的分离。这种分离恰好印证了现代性道德危机的两个表现:(1)现代道德生活世界的价值危机。现代社会中,权威性和永恒性的道德价值之所以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判,其根本原因是德性的价值不能够再以一种规范化的方式得以呈现,即道德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可以通过“外化”为伦理规范的方式而被社会群体接受,从而失去了一种外在的执行力和控制力,德性的光辉似乎早已退隐成为一种个人的内在修养和气质,而不再具有强大的社会管理和操控功能。(2)现代伦理知识的合法性危机。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和理性启蒙,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等都对伦理知识的合法性进行了拷问,20世纪兴起的元伦理学更是对伦理学自身合法性的挑战。伦理学知识是否具有观念的普遍性和实践的合理性这一问题之所以陷入了巨大困境,正是由于这种伦理知识框架的背后缺少了传统道德或宗教价值内涵的有力支撑。现代社会的伦理规范不再由某种内在的德性价值或宗教情感“外化”而来,而是被迫要去独立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根基,即当“德性”不足以构成“规范”的理由时,“规范”必须自己为自己寻找理由。
三、道德话语与伦理话语的错位
如上文所述,由传统与现代两种伦理学话语体系的分离所导致的现代性道德危机,在理论上表现为“德性”与“规范”的分离。当内在的德性价值与外在的伦理规范逐渐失去了贯通的可能性时,“道德的”与“伦理的”也逐渐开始分离并各自划分出独立的领域和空间。现代性道德危机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理论上的语境转变并没有在话语的实践运用上真正带来“道德的”和“伦理的”的区分,作为阐释内在德性价值的“道德话语”和作为制定外在行为规范的“伦理话语”出现了混淆和相互僭越:
(一)道德教育的“伦理化”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演变中道德教育的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性道德危机实际上并不意味着道德教育的弱化,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意味着应该提高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德性在现代社会并不是真的被边缘化从而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德性从未离开,只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明确它在现代社会环境之下应有的范围和界限,没有为它找到合适的位置来发挥作用。例如现代道德教育的一个普遍误区就是倾向于将道德教育“伦理化”,即试图将多种内在德性价值以固化、僵硬的外在伦理规范形式加以呈现,将人人都能够遵守社会规范和秩序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其中,以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言说方式去表达某种道德精神价值,从而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让人厌恶的“道德说教”。
这种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是对道德教育理解的一种偏差,是伦理话语对道德话语的侵入。外在的伦理规范本质上只是一种社会整合的“技术”,而内在的心灵德性却是超越于这一层面之上的价值诉求。无论一种德性价值有多么美好和高尚,一旦被抽象化、理论化为某种制度规范,那么必然会失去自身的感染力从而僵化为理论教条。以《论语》中所讲的“君子”为例,在传统社会中,成为君子是内在修身养性功夫与外在合乎礼仪行为的完美结合,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却总是会觉得,君子的内在修为方式与实际的社会操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似乎道德精神层面的内在修养是一回事,而外在的行为规范以及行为效率则成为另外一回事。如果成为君子不是出于个人内在精神上的自愿选择,而只是为了符合某种外在的评价标准和规范,那么这时的君子就很可能是虚伪的。传统的道德教育总是表现为一种“吸引式”的教育方式,即将一种道德价值以“做某事是好的”这样的话语方式来呈现,并最后将这种道德价值的实践过程完全交给个人。一个人发出一个好的行为是出于这种好的道德价值本身,也就是出于内心对这一道德价值的信念,而并非出于某种外在强迫性的规范和要求。然而,现代社会普遍的道德教育却常常表现为“命令式”,即“应该做某事”。这是传统道德话语受到现代性“规范主义”思路影响的表现。这种言说方式导致了道德教育的“伦理化”,其结果是:不但没有提高道德教育自身的效率和力度,反而导致了整个道德话语的空洞化和虚假化,使得现代社会普遍产生了一种对传统道德教育的厌倦情绪。究其根本原因,这并不是德性自身的隐退,而是伦理话语相对于道德话语的一种越界。
(二)伦理教育的“道德泛化”及伦理教育的缺失
内在的德性要求与外在的规范要求之根本区别在于,外在规范所要求的是一种“底线伦理”(theminimalistethics),其所关注的是社会最基本层面的伦理规范和公共秩序。这种底线伦理最终的目标指向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行,为个体提供一个良好的公共环境,也就是“好的社会”,而道德教育终极的目标指向则是要培养和提升个体的内在品性与人格境界,它所描绘的是“好人”、“好生活”这样更大的图景。与传统的道德教育不同,对于一种纯粹的社会伦理规范来说,是应该有着明确指向和明确界限的,因为它本身就具有规范性和制度性的特质,规定了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有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只要是社会成员中的一员在特定的场合下就必须按照这种规范执行,唯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一种最基本的公共生活并维护社会大环境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它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种“公共理性”,而不是个人的“内在德性”。本文所说的“伦理教育”指的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公共教育或者说是公共理性和公共意识的培养,即一种对社会成员共同维护社会基本规范制度和树立底线伦理责任意识的教育。
社会伦理规范所做的实际上是要在义务与超义务之间划清界限——一个社会没有必要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圣人君子,但却非常有必要要求每人都恪守他作为一个社会公民的最基本职责,使其行为符合最基本的规范以保证社会的稳定,这是一种伦理要求而不是道德要求。鲍曼说:“‘现代运动’将任何道德律令能够令人信服地建立于其上的根基彻底击碎——它同样破坏了道德:超出签约义务之外的责任。”[7]当一个人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其行为符合了社会最基本的规范时,我们可以说他达到了社会“伦理”的要求,而只有当一个人超出自身的义务去做了更多义务之外的好的行为时,我们才说他的行为涉及到了“道德”。例如在公共场合当多人需求同一有限资源时需要“排队”,这时我们所遵循的“先到先得”原则就是一个典型的伦理要求,“排队”属于典型的“伦理行为”,但假设这时我发现自己身后有一位身体虚弱的年迈老者,出于体谅和关怀牺牲自己的时间让他排在我的前面,那么此时这一行为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行为”。以此类推,如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明显是一个“道德行为”,因为这一行为是超出于“伦理行为”(先到先得原则)的一个举动,只有“超乎”而不是“合乎”的行为才是值得称赞的,它才真正从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
然而,原本应该清晰的伦理行为和道德行为之界定却经常被混为一谈。例如人们经常把在公共场合排队、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等一系列行为笼统地称之为“道德素质”或“文明素养”等,这种模糊的概念以及以这种概念实行的教育模式最终导致了一种“道德的泛化”,具体来说也就是“伦理要求的道德泛化”,即将一个具有明确规范性制度性的伦理要求以一种道德美化的方式加以叙述。由于伦理要求自身的命令式特征(合乎)本质上不同于道德要求的可选择性特征(超乎),导致这种貌似被美化了的伦理规范不但没有加强自身的管理力度,反而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可做可不做的心态,弱化了其执行力。实则大多数所谓“道德素质”或“文明素养”问题的背后,并未涉及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德性”,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公共理性”的极大缺失。其根本原因依旧在于,现代性语境下所带来的内在德性价值与外在伦理规范的话语分离,要求二者各自明确自身的表达方式(伦理话语的“命令式”和道德话语的“吸引式”),无论是伦理话语还是道德话语的僭越都会引起二者界限上的错位,从而导致某种程度上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的失效。
在中国当代社会中,传统的儒家学说及其思维方式受到了现代西方理性主义、规范主义、契约精神等现代思潮的冲击,根深蒂固的德性教育传统更是受到了现代规范伦理的挑战,在“道德教育”思路依然占据主流地位的今天也更加突显出当代中国社会“伦理教育”的缺失。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下,保证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和社会环境的稳定性成为了首要目标,社会的道德建设同样需要在这种“稳定”之上得以立足——这也就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伦理教育”有必要成为“道德教育”的基础。如果缺乏一种最基本的公共意识培养和公共理性构建,不仅难以维持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也会使得位于其上的“道德教育”失去根基,难以实行,从而变得虚假和空洞无味。“伦理教育”的道德泛化和缺失是导致社会诸多问题的内在原因,因此,公共理性的建设与公民意识的启蒙在当代中国社会应该被给予高度的重视。我们当下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与传统社会大有不同,在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和话语体系之下,成为“好人”需要同时建立在成为“好公民”的基础上才得以可能。
四、结语
现代性伦理主题的转变带来了“德性”与“规范”两种话语的分离,同时也意味着“道德教育”与“伦理教育”不再能够互相替代。面对现代性的道德危机,无论是伦理话语的僭越还是道德话语的僭越都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确道德要求和伦理要求各自的范围和领域,即二者的“划界”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种界限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完全孤立,道德教育和伦理教育只有各司其职、各行其是、在各自的领域范围内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发展为一个完善的共同体——既有制度规范上的完备和稳定,又有精神价值上的开放空间。由此,伦理话语作为一种“向下”的底线制约,其教育方法和实践方式有必要遵循规范性、制度化的原则,而道德话语作为一种“向上”的价值倡导,则应该以一种吸引式、激发式的实践形式来给个体德性的培养与人格境界的提升提供无限可能的发展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适应现代性的话语坏境,为社会新的伦理道德建设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的思路。
注释:
①需要说明,关于“道德”(moral)和“伦理”(ethic)这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关系,从语源学方面已经有过许多研究。本文在这里使用这两个概念仅用于表示两种不同的维度,取其狭义的概念,即“道德的”指向人的内在德性价值维度,“伦理的”指向人的外在行为规范维度。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04.
[2][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27.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李泽厚.伦理学纲要[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5]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J].社会科学战线,2002,1.
[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3.
[7][英]奇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