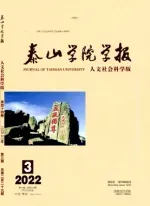近10年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新进展
唐芷馨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6021)
语法学一直是语言学中最活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马氏文通》问世以后的百余年中,汉语语法研究经历了草创、革新、蓬勃发展和繁荣昌盛的发展时期,涌现出一批批老、中、青致力于语法研究的学者,成果丰硕,并将语法研究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峰。近10年,随着人们的视野、认识的不断深入及一些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及应用,语法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方面出现了新的趋势和更大的进展。
我们对近10年语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理论方法及取得的成绩加以总结归纳,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简单的参考与借鉴。
一、词类问题研究
词类问题是语法研究的首要问题之一,前人在词类划分的标准、词类的本质以及分类结果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果显著。近10年的词类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可从下面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实词研究新动向
近10年,实词仍然是语法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研究数量来看,有关实词研究的著作出版了50余本;相关论文,仅以中国知网为例,共检索到现代汉语实词研究论文269篇。从研究对象看,多数研究定位于某一实词内部的某一小类,如“路径动词”、“人体名词”等。从研究内容看,加大了对实词的重叠和功能的研究。
较以往相比,近10年的重叠研究扩大了广度和深度,增加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主要是计算机语言学和汉语史角度,语料丰富,例证充分。例如,尚英[1](2004)从计算机语言方面进行切入,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素材(包括表格、举例等)详细分析了动词vv式与V-V式的语法特征及其形式特征。张晓涛(2005)、刘毅(2006)、王大成(2009)、许函(2012)等也通过动词的语用规则解答动词重叠的语法特征,解决了许多动词重叠的界定、功能等有争议的问题。形容词重叠方面:石锓[2](2007)从现代汉语与汉语史两个角度,以单音节和双音节为划分标准,将形容词重叠研究分为重叠(双音节)和叠加(单音节)两种方式进行讨论,也是运用大量的例子深入分析和解答了形容词重叠的内部机制及其形式、语法特征。类似的研究还有李劲荣(2004)、石湘玉(2009)、徐秋月(2010),探讨了形容词重叠的内部机制及其语法功能。
学界一般认为汉语的名词不能重叠,随着研究深入,也有一些学者对名词重叠展开了研究,认为名词的重叠也具有一定的形式、语法特征及语法意义。蔡朝辉[3](2007)针对名词重叠的现象作了详尽的讨论,从其构成形式、语义特征、语法功能三个方面,提出名词重叠也具有形容词的功能,具有全民性的特点。再如岳中奇(2006)论述了单音节名词AA重叠式同量词AA重叠式的比较分析;尤婵(2011)提出了名词重叠具有动词的句法功能;李娇(2013)主要将名词重叠的形式、表义功能、诱因、基式与重叠式的语法功能比较等。
在词类功能方面:近10年,学者关注了词类的动态功能,更关注具体的句子对词类功能的影响。有以某一类词为切入点,分析该类词在不同句式中功能差异的研究,如张黎[4](2003)以动词位置不同为例,引出汉语的“镜像”规律,探讨了动词在不同的位置表现出不同的句法功能。任鹰[5](2007)通过对动词的词义在句子中的不断变化,指出其句法能力和组合能力发生了变化,深入探讨了词义与功能的密切联系。也有以某类句式为着眼点,分析可以用于此类句式关键位置的全部词语的功能特点。如刘承峰[6]在《能进入“被/把”字句的光杆动词》(2003)中指出进入此句式的动词都不是“光杆动词”,并分析此类动词的句法功能。
(二)虚词研究新动向
虚词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虚词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也不断推进和完善。近10年,从类型学和语法化视角展开研究是虚词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趋势。比如王继红和陈前瑞[7]《副词“方”多种时体用法的关系》主要以副词“方”为例,从类型学角度解释了它的时体用法。同类研究还有徐以中(2003)、单韵鸣(2004)、温锁林(2009)、雷东平(2011)等,他们分别研究了副词“只”“真、很”“并”“暴、超”的语用功能和语法功能。吴福祥[8](2003)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了“与、及、将”等“和”类虚词,提出介词大于连词的类型学蕴含及其句法因素。曹炜[9]《近代汉语并列连词“并”的产生、发展及其消亡》(2003)则认为:作为“和”类虚词之一的“并”的语法化轨迹并没有经历这么一个语法化链,它是由伴随动词直接语法化为并列连词的,中间并没有经历一个“伴随介词”的阶段。邵敬敏[10](2006)以介词“对”三个义项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指出介词“对”的语用形式及对象;还考察了介词“对于”和“对……来说”的比较。林华东[11](2005)指出受介词语法化的影响,与介词的组合式“V+介+Np”形成了述宾结构的特征,并针对这一情况做出了细致的探讨。
总之,国内对汉语的词类划分从一开始的多标准逐渐向单一的标准靠拢,对于词类的功能解释也是日趋精细。但是,对于划分词类的理论问题仍有很大争议,对词类的本质或性质都有不同的看法。较之前相比,词类的研究比较注重词在语言中的表现,而现在更加重视词在语言使用中的规律问题,注重词的多功能解释。
二、话语标记研究
话语标记是指一些词在句中无法用句法解释的语言成分,多用于口语,且无实在意义却又不可缺少。西方学者们从认知语言学、语义学、类型学、语法化、历时发展和语言习得等角度对话语标记语进行了研究。20世纪80年代,受国外话语标记语法的影响,汉语话语标记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近期成绩更是显著。首先专著类,刘丽艳2011年著有《汉语话语标记研究》,对话语标记语法做出了新的界定;刘秀明《汉语元话语标记语研究》对元话语标记的构成及功能做了系统的分析;殷树林2012年著《现代汉语话语标记研究》,从宏观到微观,系统地描绘了话语标记语的全貌等等。还有论文类,我们在中国知网共检索914篇,其中汉语语法标记语法相关理论研究105篇,汉语话语标记语个例研究152篇。近10年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代词话语标记研究和疑问小句的话语标记研究。
王海峰[12](2003)对新形成的口语“那个什么”进行了研究,指出自然口语“什么”的虚化与指示代词“那个”结合形成合体的虚化,成为一种话语标记的形成过程、原因,并指出其语义功能和篇章功能的联系。同样的研究还有王志恺[13](2007),研究了新兴口语“那是”的原因分析,他指出“那是”既不是词,也不是短语,而成了一种标记性答语。这类词的研究还有像“那么”、“不是”、“完了”、“我看”、“你看”、“我说”、“你说”等。
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汉语小句演化成话语标记的现象。张聪燕[14](2008)认为话语标记语作为口语大量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分析了小句“你知道吗”作为一种口语表达,表现了它又引起注意,解释强调的语用功能。李宗江[15](2013)针对是不是、是不、是吧;对不对、对不、对吧;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吧等疑问小句不同的形式特征,系统地分析了他们作为话语标记语语法功能弱化和语用功能的增强。以上的研究都注重话语标记语的语法功能弱化以及语用、语义功能的强化问题。
三、情态研究
一般来说,情态是说话人对句子所表达的命题或命题所描写的情境的观点或态度。但对于情态的分析,主要要素有:可能性与必然性概念;说话人的观点与态度;命题的限制成分。近10年来,关于情态的语法研究主要关注于动词、副词以及形容词方面。
许和平曾指出,情态动词主要包括“会、应该、容、许、能够、要、愿意”等,这样的名称比起“助动词”、“能愿动词”来,能较好地反映汉语情态的语义和用法特点。[16]李明[17]《从“容”、“许”、“保”等动词看一类情态词的形成》、彭利贞《论应该的两种情态语体的同现限制》等的论述都是通过举例及对比的方式,深入解说了汉语动词在各种范畴中、组合形式等对情态的影响。情态副词指表示情态的副词,如“特地、百般、互相、擅自、亲自、逐步、仍然、依然、当然、毅然……”。情态副词不能单说,只能作状语,放于动词前。钱如玉曾指出,这类词虽然数量多,但是内部性质大致一致,故用法比较单一。董正存[18](2008)提出了情态副词“反正”的使用、成为情态副词的原因以及它语法化过程。肖应平[19](2012)从情态意义的角度对情态副词进行分类,总结出一个现代汉语情态副词的分类系统。
四、语法化问题
语法化是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20](沈家煊1994)。近10 年来,“语法化”是文章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语,是近几年的一个热点研究,并且不断有新的文章出现。汉语语法化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句法化、形态化。近10年关于语法化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专著类30余本,如2005年吴福祥编著《汉语语法化研究》,还有2003年到2013年出版的《语法化与语法研究》(1-6);2009年王兴才编著的《汉语词汇语法化和语法词汇研究》等。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下面两个方面:
(一)词汇语法化
词汇语法化,简称“语法化”,在中国传统的语言学中又称为“实词虚化”。由于汉语的词汇缺少形态变化,所以实词虚化就成了现代汉语语法化研究的中心内容。[21](王兴才,2009)。现代汉语中出现的许多不可缺少的虚词,像较为、马上、得(děi)、难道、关于等,都是人类在交流的过程中出现的非常普遍的词汇语法化现象。
关于实词虚化这类研究,早在1995年吴福祥[22]等就发表了《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论述近代汉语动态助词“将、着、取、得”语法化过程和机制。词汇语法化的研究对象包括实词完全虚化为虚词的词语。例如:徐时仪[23]《“一味”的词汇化与语法化考探》(2006),首先介绍了“一味”在唐朝时期以前至唐朝,意义为“滋味、味道”,直至宋代,逐渐虚化为了副词,表示“一直”的意思。“一味”由一个偏正短语虚化为副词,这个词汇语法化的过程实质就是一个词组特性不断弱化以致最终消失的过程。罗耀华等[24]《何必/何苦词汇化与语法化》(2010),提出“何必/何苦”在原来的用法,都是以短语的形式出现“何+必/苦”,本义为“为什么 一定/必须”,后来由于它的高频使用和语境的问题,它的用法发生了变化,逐渐变成了反问的语气词,在反问中表否定判断,表示“不必”,具有一定的主观化。与之相同的还有像蒋协众(2010)、张顺(2010)、管志斌(2012)等分别论述了“到家”、“算了”、“得了”的语法化过程。还有的学者注意到单音节词的用法。刘永耕[25]《动词“给”语法化过程的义素传承及相关问题》(2005),主要阐述了“给”的动词义位、虚词义位及其演化关系,先说“给”的本来用法,然后分别论述了动词“给”语法化为介词和助词的过程。还有像张定(2009)就论述了“助动词‘好’”的虚化过程。
这部分研究还包括仍保留实词用法的同形词,这部分侧重核心义的转移及保留。这类语法化主要是指“词在虚义水平上的意义演变活动,是语法意义的再生现象”,也包括意义具体的词变成意义抽象的词。[26](宋艳欣,2008)比如姚小鹏[27]《副词“可是”的语法化及相关问题》,主要讲解了“可是”作为副词而不是连词时,经历了由疑问标记到强调标记的演化过程。王志恺[28]《“那是”的对话衔接功能及其固化过程——兼论“是”的进一步语法化》,文章指出“那是”的最常见用法是“那”是指示代词,“是”是判断词。还有“那是”也可以是主谓短语,而新出现的用法是“那是”出现在口语对话里,单独成句。“那是”是“是”的进一步语法化,从判断词变为固化形式的不可分析的成分。
这部分研究还包括与语法化词语相关的结构研究。雷冬平[29](2007)《语气助词“便是”的语法化及相关结构研究》从另一种研究角度,针对“NP+是”、“NP+便是”和“VP+便是”的句式及其演变关系进行了研究,还对争议较多的“NP+的+便是”与“N1+(便)是+N2P+的+便是”结构进行了探讨,认为其中的“便是”不是语气助词,而是判断动词,并对两种结构的来源进行了探索。汪如东[30](2010)《助词“就是了(就是)”的语法化及相关结构研究》从共时角度分析了“就是了”的结构问题以及它语法化形成的动因和机制,并且探讨了“就是了”的相关结构“便是了”。同类研究还有刘芳(2009)在《“到”的语法化及相关问题》研究了“到”+O+V、“到”+了等形式的语法化问题;曹秀玲(2010)在《从主谓结构到话语标记——“我/你V”的语法化及相关问题》中也是从结构角度入手,对它的语法化进行分析。
综合各家所言,对于词汇语法化的研究,总体上都是先从词汇本义或者词汇的本来的语法意义进行切入,然后分析动因,总结规律。他们主要研究词汇成分到语法成分的演变,涉及词义的虚化和语法作用的增强两个方面。
(二)构式语法化
江蓝生指出“语法化也指短语或词组逐渐凝结为一个单词的过程,可分别简称为词汇的虚化和短语的词汇化。”[31]关于语法化的研究,大多数学者以词汇为主,但2007年左右,随着国内语法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外构式语法的兴起,国内也越来越多地关注构式语法研究。汉语因有着丰富发达的句式系统,自先秦以来产生过大量的句法结构,如连动式、双宾语句、粘合式和组合式述补结构、被字句、把字句、比字句、使役句等,为汉语构式语法化研究提供丰富的考查空间,也使句法构式研究成为语法化研究重要内容。[32](宋艳欣,2008)
此类研究都是先解释所研究的构式形式中各个词的语义功能、语法功能,进而研究其组成结构及语法化的路径和机制。构式语法化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固定句式,而且还包括很多特殊结构的语法化研究。例如,罗耀华[33]等《“X+多/少”的语法化及相关问题》(2012)考察三组词:至多/至少;最多/最少;顶多/顶少。首先就探讨了他们的词性性质,是语气副词还是范围副词,进而研究了他的语法化路径和机制,指出相同的词不同的词性或语法意义所表现的内容也不相同。类似的研究还有鹿钦佞(2008)董淑慧(2012)韩玉强(2011)龙国富(2013)分别论述了“搞不好”、“弄不好”、“闹不好”三个述补结构的功能及语法化、“V+上+数量”构式的语义功能及其语法化、“在+L+VP”结构中处所介词的形成的语法化历程和机制、“越来越…”构式的语法化——从语法化的视角看语法构式的显现等等。还有少量短语语法化研究,于康(2004),江蓝生(2005)鹿钦佞(2008)分别论述了构词短语“V不得”、“VP的好”、“V+不好”的语法化过程。
五、方言语法研究
中国最早的方言研究要追溯到西汉时期,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此书对后世的方言研究提供语料资源及研究方法。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学术界再次注意到方言的重要性,尤其是90年代后期,方言研究进入兴盛时期。主要成就有朱德熙《上海市区方言志》、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等。还有专著类,像方惠英的《汉语方言代词研究》、钱曾怡《汉语官话方言研究》等215部。这些文献收录大量的词条,展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方言研究论文13607篇,其中关于方言语法研讨会论文1606篇,方言语法研究4110篇等。近10年,方言语法研究受到学者重视,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研究侧重点包括方言词重叠研究、方言特殊句式研究、方言中特殊词研究等。
(一)重叠研究
重叠是一种语法形式,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方言词重叠后的语义特征和句法功能。重叠主要包括形容词、动词和名词的重叠,其中以形容词的研究最多。
形容词重叠研究的主要内容多以构词为主。田艳[34]在《东北方言中形容词重叠类型及功能分析》(2009)中描写了AA式(慢慢(地))、ABB式(紧绷绷)、A儿A儿式(悠儿悠儿)、BBA式(梆梆硬)、BABA式(梆硬梆硬)和 AABB式(干干净净)等六种形容词重叠形式,主要研究它语义和功能两个方面。还有刘晓微(2008)、朱笑莹(2009)、曹中军(2013)分别从形容词AABB式、ABB式等方面,论证东北方言形容词不同的构词形式决定它不同的句法功能。动词重叠基本从重叠的形式角度进行研究:朱蕾[35](2005)主要研究了安徽泾县方言“VV的”的重叠式,其语义相当于普通话中的“V过的”(我吃吃的=我吃过的)。同类研究还有姜文振(2006),研究东北方言AA式结构的语义和句法功能;石毓智(2007)通过方言动词重叠与普通话的比较研究,深入探讨其语法意义和功能的差别;陈燕玲(2009)从单音节动词重叠AA式和双音节动词AABB式两个方面分析了它们的句法、语用、语义等功能。对于名词重叠的研究也多数从重叠形式的角度入手。例如,辛菊[36](2009)研究稷山方言合成的一种名词,是方言研究的一个新视点,她将这种合成名词重叠形式分成AA式、ABB式、AAB式以及AABB式、ABCC式、ABBC式进行分析,指出稷山方言重叠式合成名词与普通话相比,不仅有复杂多样的构成类型,而且有很丰富的语法意义。还有杨月蓉[37](2003)也是从词语重叠后呈名词性的角度进行研究,她以四川方言为例,将其名词重叠形式分为XYY(“手爪爪儿”—手的贱称)和XXY(顶顶上—顶上)两类。也有些研究的角度多在词性本身就是名词的词,例如张辉(2004)、刘凤丽(2009)分别研究了南阳方言名词的重叠、广西桂北平话及相关土话名词重叠的独特类型,表意特征和语法功能的研究。
(二)词缀研究
词缀研究以单音节词为主,主要着眼于方言中的特有词缀及其构词功能和特殊用法。吴继章[38](2005)主要通过“圪、子、忽、达、日、头、老”等词缀进行描写分析,指出其语义功能在词缀发展过程中的的作用。王红梅[39](2003)主要通过吉林洮南方言后缀“的”形式:A的B的(扁的哈的)、AB的(干吧的)、AABB的(冷冷清清的)等形式,指出它可做名词、状态形容词、动词三种词类的后级,并且受到语义以及形式的制约。同类研究还包括张爽(2009)研究了东北方言词缀“儿”;侯海霞(2010)研究了东北方言中极具特色的词缀“挺”;刘珊珊、刘莹(2013)二人分别研究北方方言词缀“吧”和“子”。
(三)句法研究
方言所涉及的句法研究包括方言小句或习语结构的研究,还有一些方言中固定的特殊句式研究。学者大多从类型学的角度,利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介绍了各地方言中一些特殊句式以及它们的语用功能等。吴长安[40](2007)指出方言中某些形式以及词语的使用,不能用一般规则来解释。文章主要分析方言小句“爱咋咋地”的结构,通过为了表达求简以及形式的自由化等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解释了东北方言中AVV结构的特点。祖迪(2012)研究东北方言的常用表达方式“老……了”,通过对其语法组合能力的分析(包括形容词、名词、短语等进入结构),突显了其语用功能。还有李文浩(2008)研究了动(叠)+补的结构;方清明(2011)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带宾语分别;张明辉(2012)东北方言反问句结构类型。
(四)其他研究
对于方言语法方面还有许多研究,像方言中的话语标记(郭风岚(2009)北京话话语标记“这个/那个”)、方言词的语法化及语义与分析(王晶(2007)“疙瘩”的词义和用法表达)、个别词的研究(对东北方言“整”的语义、语法、语用分析)等等。
除上述研究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新兴的语法现象,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主要包括对新兴语素的研究,比如“零”、“负”、“哥”、“妹”、“货”“霸”等;新词语功能的多角度研究,比如“非常”、“给力”、“女汉子”等;旧有词语的新用法研究,比如不及物动词扩大使用范围、普通名词做状语等;新兴结构的多角度研究,如“很 +N”、“~style”等。
总体来说,近10年汉语语法研究在词类、情态研究和语法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很可观,为我们学习和研究提供了素材和借鉴。只是研究的理论方法容易扎堆,本土的理论较少,近5年来也稍有改善。今后,我们应该更注重深入汉语实际,发现问题并做出更多的研究。
[1]尚英.vv与v-v式动词重叠的特征调查研究[A].2004年辞书与数字化研讨会论文集[C].2004.6
[2]石锓.从叠加到重叠:汉语形容词AABB重叠形式[J].语言研究,2007,(02).
[3]蔡朝辉.探析汉语中名词的重叠[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3).
[4]张黎.“有意”和“无意”——汉语“镜像”表达中的意合范畴[J].世界汉语教学,2003,(01).
[5]任鹰.动词词义在结构中的游移与实现——兼议动宾结构的寓意关系问题[J].中国语文,2007,(05).
[6]刘承峰.能进入“被/把”字句的光杆动词[J].中国语文,2003,(05).
[7]王继红,陈前瑞.副词方多种时体用法的关系[J].中国语文,2012,(06).
[8]吴福祥.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兼论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J].中国语文,2003,(01).
[9]曹炜.近代汉语并列连词“并”的产生、发展及其消亡[J].语文研究,2003,(04).
[10]邵敬敏.试探介词“对”的语法化过程[J].语文研究,2006,(01).
[11]林华东.介词虚化与“V+介+Np”的述宾化趋势[J].语文研究,2005,(01).
[12]王海峰.自然口语中“什么”的话语分析[J].汉语学习,2003,(02).
[13]王志恺.“那是”的对话衔接功能及其固化过程——兼论“是”的进一步语法化[J].汉语学习,2007,(03).
[14]张聪燕.话语标记语“你知道吗”[J].哈尔滨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1).
[15]李宗江.几个疑问小句的话语标记功能——兼及对话语标记功能描写的一点看法[J].当代修辞,2013,(02).
[16]彭利贞.现代汉语情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7]李明.从“容”、“许”、“保”等动词看一类情态词的形成[J].中国语文,2008,(03).
[18]董正存.情态副词“反正”的用法及相关问题研究[J].语文研究,2008,(02).
[19]肖应平.现代汉语情态副词与形容词类型的选择性分析[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2).
[20]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纵观[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04).
[21]王兴才.汉语词汇语法化和语法词汇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2]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J].中国语文,1995,(03).
[23]徐时仪.“一味”的词汇化与语法化考探[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6,(06).
[24]罗耀华.何必/何苦词汇化与语法化[J].汉语学习,2010,(02).
[25]刘永耕.动词“给”语法化过程的义素传承及相关问题[J].中国语文,2005,(02).
[26]宋艳欣.汉语语法化研究综述[J].语文学刊,2008,(14).
[27]姚小鹏.副词“可是”的语法化及相关问题[J].汉语学习,2003,(03).
[28]王志恺.“那是”的对话衔接功能及其固化过程——兼论“是”的进一步语法化[J].汉语学习,2007,(03).
[29]雷冬平.语气助词“便是”的语法化及相关结构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02).
[30]汪如东.助词“就是了(就是)”的语法化及相关结构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2).
[31]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2]宋艳欣.汉语语法化研究综述[J].语文学刊,2008,(14).
[33]罗耀华.何必/何苦词汇化与语法化[J].汉语学习,2010,(02).
[34]田艳.东北方言中形容词重叠类型及功能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4).
[35]朱蕾.安徽泾县方言的“VV的”重叠式[J].中国语文,2005,(03).
[36]辛菊.稷山方言重叠式合成名词的构成及意义[J].语文研究,2009,(02).
[37]杨月蓉.四川方言的三字格重叠式名词[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12).
[38]吴继章.河北方言词缀发展演变的趋势及语义在其中的作用[J].语言研究,2005,(01).
[39]王红梅.吉林洮南方言中的后缀“的”[J].北方论丛,2003,(06).
[40]吴长安.“爱咋咋地”的构式特点[J].汉语学习,2007,(06).
(责任编辑 闵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