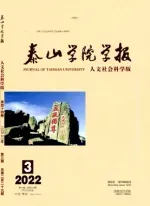早年主题的回旋与变奏:试论穆旦诗作的晚期风格
陈齐乐,陈 彦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穆旦晚期诗作在诗情表达上发生很大转变,正如穆旦昔日校友、同为“联大”诗人的郑敏所察觉的,“一个能爱,能恨,能诅咒而又常自责的敏感的心灵在晚期的作品里显得凄凉而驯顺了”。对此,有论者表达“赞美之后的失望”;亦有研究者认为,正是通过对自我感性体验的真实表达,诗人才能够摆脱意识形态话语对彼时绝大部分汉语诗歌写作的箝制,所谓在晚年变得“凄凉而驯顺”的地方,“正是穆旦的现代性所在——只依据个我的内向性原则行事:生活‘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不以廉价的关于未来的许诺抚慰受伤的生命。”
然而,问题尚有值得探讨之处:穆旦晚期写作确实发生很大变化,这不仅表现在诗情上,一位以写“自我分裂”与“自我驳难”而见长的现代主义诗人似乎回归了浪漫诗风的抒情性表达;而且,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些抒情性表达指向的是早年写作不断复现的主题,虽然此时已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早年主题的回旋与变奏,确实构成穆旦晚期诗作特别突出、却为研究者忽略不察的现象。“回旋”与“变奏”原本都是音乐术语。回旋曲,是指由相同的主部和几个不同的插部交替出现而构成的乐曲;变奏曲,则是由主题及其一系列变化反复、并按照统一的艺术构思而组成的乐曲。
穆旦晚期诗作萦绕于一些相对固定的情绪体验,虽然这些诗作很大可能并非写于一时、一地,亦非出于有意识的构思、布局,但是文本间确实形成一种交互指涉的关系;而且,在晚期存留的不多诗作中,诗人似乎并非不经心地回旋于早年写作的题材或经验,但是这些晚期诗作已经对早期题材进行了特定而丰富的变奏。本文将借用“回旋”与“变奏”概念,尝试对穆旦晚期诗作一些新的探讨与检视,以期能够对穆旦晚期诗作获得更具总体性的理解与认识。
一、回旋:作为主部的“智慧之歌”
穆旦晚期存留的诗作一共有二十九首。进入晚年,诗人确实成为那一类擅于在相同主部与不同插部之间交替往复的作曲家。《智慧之歌》的抒情主体表明自己“已走到幻想底的尽头”,在这片“落叶飘零的树林”里枯黄地堆积着三种“欢喜”:青春的爱情,喧腾的友谊,迷人的理想;现在,只有日常生活的痛苦还在,并且以它的苦汁浇灌了“一棵智慧之树不凋”。可以看到,“智慧之歌”关于幻想失落的主部萦绕着穆旦的晚期诗作,在《妖女的歌》、《爱情》、《友谊》、《理想》、《沉没》、《好梦》等不同插部之间形成一种交替往复的关系,以强化苦涩的“智慧之歌”。
插部1、梦/幻想:我们已无法推测晚年穆旦到底写过多少诗,而他的诗的复苏又具体出现于何时。假设我们可以将《妖女的歌》看作其诗歌写作复苏的讯号,那么它确实是最有意义的一个表征。穆旦深刻意识到自己是属于那一类受到招引而迷失的“失踪者”行列,然而对已知未知的崇山峻岭的翻越并没有开启广阔的时间与空间,相反是“丧失”成为了幸福、是脚步留下了一片野火,而这一切都源于“爱情和梦想”的招引、对“泥土仍将归于泥土”的深切领悟,正如“所有伟大的写作都源于‘最后的欲望’,源于精神对抗死亡的刺眼光芒,源于利用创造力战胜时间的希冀”。于是,“她醒来看见明朗的世界,/但那荒诞的梦钉住了我”。(《“我”形成》)梦/幻想、理想成为穆旦晚期诗作反复出现的主题,并形象化为“一片落叶凋零的树林”——“我已走到了幻想的尽头”——这里,“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智慧之歌》)
插部2、爱情:在《智慧之歌》中,抒情主体对凋零的“爱情”、“友谊”与“理想”的感知还是一种比较抽象的认识,到了《爱情》、《友谊》、《理想》中则分别扩展对此三者的认识。在老年诗人的体验中,爱情已经失去其热情、诗意的特质,早年在《诗八首》中所呈现的对爱情本质的形而上凝思被冷峭的怀疑与批判所取代。曾经是渴望,“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让我在你底怀抱里得到安憩——”(《诗八首》)如今是冷峻,“爱情是个快破产的企业,/假如为了维护自己的信誉;/它雇佣的是些美丽的谎,/向头脑去推销它的威力。”(《爱情》)曾经是谅解,“再没有更近的接近,/所有的偶然在我们间定型”(《诗八首》,如今是披露,“别看忠诚包围着笑容,/行动的手却悄悄地提取存款。”
插部3、友谊:青年时代,穆旦在诗作中几乎没有触及过“友谊”的主题,诗人几乎完全置身于一个公共世界中,承受历史的全部压力,而抒写“自我的分裂”与“自我的驳难”,至于作为其心灵宿地的内部空间则是由“爱情”这一亲密关系所构建的。但是,在其晚期诗作中,“友谊”成为苦涩的“智慧之歌”中反复交替的插部。值得注意的是,“爱情”带给抒情主体的只是茫然的消逝感与冷峻的幻灭感,“友谊”带给诗人的则要温和、并且重要得多,甚至取代最具私密性的“爱情”关系,成为抒情主体构建其内部空间的重要维度。诗人写到,死亡已经从我的生活中带走了许多心爱的人,以致“我的小屋被撤去了藩篱,/越来越卷入怒号的风中”,“但它依旧微笑地存在,虽然残破了,接近于塌毁,/朋友,趁这里还烧着一点火,且让我们暖暖地聚会。”(《老年的梦呓》)
可以看到,“友谊”对于抒情主体来说是庇护的“藩篱”,虽然死亡击打它、狂风摇晃它,但是只要面向友谊敞开,有友谊的信物存在,那逝去的就依然与“我”同在。青年时代,通过“爱情”主体的书写,诗人审视主体间不可跨越的距离;晚期诗作中,在历史压力下极度蜷缩的抒情主体反而在最为内在的层面敞开了,“受到书信和共感的细致的雕塑,/摆在老年底窗口,不仅点缀寂寞,/而且像明镜般反映窗外的世界,/使那粗糙的世界显得如此柔和。”(《友谊》)“友谊”构建了一处隐秘而内在的心灵宿地;但是,也正是在此内在而亲切的私人关系,“死亡”化身为人形,直接进入与诗人的紧密联系中,“你永远关闭了,不管多珍贵的记忆;……永远关闭了,我再也无法跨进一步/到这冰冷的石门后漫步和休憩”。(《友谊》)
插部4、理想:在《理想》中,诗人对《智慧之歌》中的主题进行反向的强化,之前诗人写到,“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为笑谈”。到了《理想》中,诗人几乎是以一种奋起的反抗,去抵挡理想有可能变为笑谈的虚无感。诗人反复抒发“理想”之于存在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理想”背后现实的反讽,但是抒情主体却自有他的确信:“别管的多少人为她献身,/我们的智慧终于来自于疑问。”(《理想》)青年时代,诗人坦言“我曾经迷误在自然底梦中”(《自然底梦》),并且认为自己是“从幻想底航线卸下的乘客,/永远走上了错误的一站”(《幻想底乘客》)。在此后的幻灭、希望、再幻灭的自我寻索中,诗人把肉身性的个体自我确立为存在的基石,大声宣告“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岩石/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我歌颂肉体》)。但是,在晚期诗作中,已经被“死亡”萦绕围困的诗人重新登上幻想的航程,“‘但我常常和大雁在碧空翱翔,/或者和蛟龙在海里翻腾,/凝神的山峦也时常邀请我/到它那辽阔的静穆里做梦。’”(《听说我老了》)——这首深心旷野中的真正的自我之歌已经具有与青年时代完全不同的情调。曾经“我底的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我是吹过林木的叹息,早晨底颜色,/当太阳染给我刹那的年轻”(《自然底梦》),现在诗人则在自然之梦中呈现出庄严、高迈与严峻,正如一位真正的老年的勇者。
插部5、现实:于是,一位真正的老年的勇者也必然遭遇更大的困苦。在《沉没》与《好梦》中,“智慧之歌”的幻灭的痛苦以更为沉痛而激越的笔调被抒发,并且在“死亡”主题的迫近下被强化,“爱憎、情谊、职位、蛛网的劳作,/都曾使我坚强地生活于其中,/而这一切之搭造了死亡之宫”(《沉没》)。诗人大声呼救,“我能抛出什么信息到它的窗外?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现在’?”(《沉没》)诗人不再能够像青年时代那样,宣称“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我们消失,乃由一片‘无人地带’”(《被围者》);相反,因为“死亡”终结了所有的可能性,老年诗人不得不带着激奋抗辩现实,并且大声宣告“让我们哭泣好梦不长”。(《好梦》)这种强烈的亲密情感具有一种修辞上的震撼力,诗人不仅没有变得“凄凉而驯顺”,反而显得“强大并且严峻”。
二、变奏:“原野的道路还一望无际”
在穆旦晚期写作中还有一种富有意味的现象,即诗人不断复写早年写作的题材,甚至有前后期同题诗作的现象。经历过漫长的生命历程,同样的题材在诗歌表达中形成既有对应性、又有对立性的变奏。
变奏1、春:穆旦有过三首以春天为题或者以春天为题材的诗作,分别是作于1942年1月的《春底降临》、1942年2月的《春》、1976年5月的《春》。前两首诗的时间相近,但是趣旨却大相径庭,这和诗人的心境有很大的关系。作于当年1月的《春底降临》表现的是一种从严酷的冬天中解放出来的欣喜之情。春天在这首诗中象征着不可阻挡的希望和未来——“坟墓里再不是牢固的梦乡,因为沉默和恐惧底季节已经过去……因为我们是在新的星象下行走,那些死难者,要在我们底身上复生……”。而在作于2月的《春》中,诗人在春天的包围中所感受到的则是“欲望”、“迷惑”、“渴求”和“火焰”此类完全属于春天的情感了,春天在这首诗中指涉着诗人自身的年轻生命。
一般来说,我们对于春天的联想,或者说,春天在文本中和其他季节显出区别的地方,在于那些春天特有的意象——绿色、小鸟、花朵、春风。在《春底降临》中,“一个绿色的秩序,我们底母亲”,绿色就是春天本身;在1942年的《春》中,绿色是一种可以用火焰来比喻的感情;在《春底降临》中,花朵是从心的荒原中生长出来的,在1942年的《春》中,花朵则是反抗着土壤挣扎出来的;在《春底降临》中,燕子的呢喃取代了过去悲哀的回忆,在1942年的《春》中,用土做成的鸟则变成了诗人自己;在《春底降临》和1942年的《春》中,都提到了春风可以作为一种情感的载体传播个人的感情。在这两首诗中,春天带给诗人的感情完全是正面和舒缓的,春天甚至可以作为诗人本体的象征。
但是这些意象在1976年的《春》中却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作为感情载体的春风不见了;这成为穆旦晚年寂苦心态的一个信号。其次,在1976年的这首作品中,花朵和新绿试图推翻穆旦的“小王国”,为什么要使用“王国”这样带有边界和主权意识的词来表征自己的精神世界呢?“春天的花和鸟”都对诗人暗含着敌意。光是由这两句,我们就可以看到诗人和所有可以象征着春天的事物都保持着一种紧张的关系。诗人对他们怀有戒心和敌意,而这种心态借由他的观察又反射到了诗人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在这首诗中,诗人多次提到“寒冷的智慧”、“寒冷的城”,可以视作对前文中的“王国”的一种补充——诗人“弱小的王国”是一座寂静、寒冷的小城,这座小城里没有早年的活力和温暖。穆旦晚年的诗作虽然以春天为题,但是与以春天指涉生命本体不同,诗人洞悉了人这一主体性存在的有死性,“春天/生命”反而成为存在的悖论。
变奏2、城:穆旦在1948年和1976年分别有两首诗作处置人与城的主题。1948年《城市的舞》,诗中充满了拟人化的建筑物、同一的、毫无特征和区别的个体、以及充满毁灭的生存方式。《城市的舞》是穆旦在还没有高度城市化的时代下敏锐的探查,这种对于社会的观察方式充满了现代性和先锋意识。而在1976年《城市的街心》,抒情主体的视角从自己脚下发散出去,在他眼中,城市的街道是一条五线谱,而在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行人乃至不会移动的建筑物都是这五线谱上的符号,穆旦几乎是用两句话就把《城市的舞》中对于城市景观的叙述即写出来了;然后从第三句开始,穆旦迅速转向了对自己命运的思考,而这种流动的生命意识又处处出现在了穆旦晚年的诗歌中。1976年的《城市的街心》和《春》在精神层面上有着共通性,城市景观的“超时间性”依然揭示的是一种“时间性”主题——抒情主体对“年老/衰朽/死亡”的体认,一种对作为时间性存在的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与洞察。纵观穆旦晚期诗作,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诗人依然回旋于早年写作的题材或主题,但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写作已经演变为一门关于死亡的艺术。
变奏3、“我”:穆旦写过三首以“我”为主题的诗,《我》写于1940年11月,《自己》与《“我”的形成》写于1976年。从这三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死亡变奏对于穆旦晚期诗作呈现方式的影响。
1940年代的《我》明显涉及现代个体的孤独感与疏离感,1976年的《自己》则将自我对象化,以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在自我内部形成一种对话关系,以此呈现主体自我裂变的流动经验,在经历各种理想幻灭以及现实变形之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在《“我”的形成》中,抒情主体则将“自我”放进与外部力量的冲突当中,不仅呈现巨大的外部压力对“自我”的箝制与约束,呈现生命形式的固定、以及意义的虚无,同时亦呈现“自我”某种难以挣脱的梦境,“仿佛在疯女的睡眠中,/一个怪梦闪一闪就沉没;/她醒来看见明朗的世界,/但那荒诞的梦钉住了我。”——一抒情主体仿佛“中魔者”,一个明朗的世界,一种合理性的生存秩序也不能把它抹除。三首诗中都提及梦境,一种诗意的、幻想性的、甚或是非理性的可能性。但是,与早年关于“我”的抒写相比,虽然青年时代诗人即有强烈的时间意识,“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我》1940年),但是在晚期写作中,死亡直接进入了诗歌。穆旦对“意义”的固执,使他从青年时代一直到晚年都在不断抒写同样的主题,但是由于生命境遇的变化,对生命有死性的深刻体验,使青年时代就生成的“意义”寻求发生一种“悲观”的回旋与变奏——所谓在深心狂野中高唱的自我之歌——在一个主体被践踏、被摧毁的年代,什么样的歌声能比这苦涩的智慧之歌更动人、更真诚呢?
变奏4、冬:穆旦在1934年写过一首《冬夜》,抒写少年诗人所感受到模糊难言的冷寂体验。四十二年之后,从少年时代走到老年,诗人终于可以对冬季/冷寂/死亡表达丰富的观感。写于1976年的《冬》从文本形式上来看是非常特别的一组诗作,诗作第一节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视点,第二节则以隐含的复数性的“我们”作为叙述视点,第三节叙述视点则分化在了不同的“你”身上,第四节则突然脱离开抒情主体的经验世界,一变而为叙事化的“雪夜夜行”场面。这种同一题材的变奏既给《冬》增添了丰富的魅力,同时也给读者带来疑惑,诗人为何在文本中推进一种突然的叙事转化?如果我们已经洞悉了穆旦晚期诗作的对意义主题的回旋以及所遭遇的死亡变奏,那么就不难看到,《冬》的第四节的叙事化场面对于诗歌前三节构成一种指涉关系。《冬》的前三节分别从“我”、“我们”、不同的“你”的角度反复抒写主体所承受的“冬天体验”,第四节的“雪夜夜行”场面则是对人的基本存在境况的总体隐喻。虽然冬夜大雪有着强烈的凛冽之气,但是诗人并未表现出死亡的哀感,相反面对“枯燥的原野上枯燥的事物”,雪夜夜行的人们反而散发着暖意,在短暂的歇息与闲谈之后,“几条暖和的身子走出屋,/又迎面扑进寒冷的空气。”(《冬》)
关于诗歌阅读:读一首诗,与读一位诗人所存留的全部诗,我们所面对的经验与所获得的感受完全不同。小说家帕慕克在谈论小说阅读时说到,“面对一幅大型绘画,我们因所有事物同时尽收眼底而感到激动并渴望进入绘画之中。在一部长篇小说之中,我们会因为置身于一个无法一览无余的世界而感到眩晕的快乐。为了看到所有事物,我们必须不断将离散的小说时刻转化为意识中的图画。”对小说的总体理解有赖于对无数细节、及其绵密呼应的交互关系的把握。诗歌当然并不像小说一样具有某种可供我们确定其细节、及其所构成的总体景观的绘画性,但是在诗人的全部创作中确实存在由“离散的抒情时刻”(每一首诗)所形成的总体性的关系。因为诗学表达更为切近音乐的抽象性,为了对诗人创作的总体理解,我们或许应该学习小说家的阅读方法,“我们必须不断将离散的抒情时刻转化为意识中的音乐。”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老年穆旦不断回旋其早年主题,并在特别的压力中经历变化,“让死亡直接进入写作”。
[注 释]
①目前,在《穆旦诗全集》与《穆旦诗文集》中对《妖女的歌》的写作时间存在分歧,前者将之归为1956年作品,后者将之归为1975年作品,编者没有任何说明,此从《穆旦诗文集》。李方编:《穆旦诗全集》,“目录”,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穆旦:《穆旦诗文集》,“目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亦见易彬:《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6页。
[1]郑敏.诗人与矛盾[A].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8.
[2]黄灿然.穆旦:赞美之后的失望[A].孙文波,张曙光,肖开愚.语言:形式的命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陈彦.穆旦在新中国的诗歌创作及意义[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4).
[4](美)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M].李小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9.
[5](土)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与感伤的小说家[M].彭发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92.
[6](美)爱德华·萨义德.论晚期风格[M].阎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