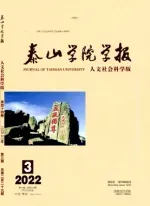南朝宋伍缉之《从征记》考论
鲍远航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浙江湖州 313000)
魏晋南北朝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各地的山川地理,涌现出一大批地记作品。这些地记作品种类繁多,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足堪瞩目,在我国古代地志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名类杂芜的地记中有一类作品,如《北征记》、《西征记》、《述征记》、《从征记》等,较为独特,它不同于《湘中记》、《宜都记》、《荆州记》、《齐记》、《吴记》等专记一方的作品,而是记述征途见闻而兼及地方山川地理、史迹人物、资源物产、人文风俗等方面的内容,为后世留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刘宋时代的伍缉之的《从征记》,就是这类作品中最早、也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伍缉之《从征记》,隋唐诸志不著录,今已亡佚,其内容只散见于类书、杂史、前人注释等文献著作中。零圭断璧,弥足珍贵。但是,尽管《从征记》对文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学界目前却还没有文章对它作出深入细致的探究。本文拟对《从征记》作出较为详细的考察,庶几有助于学者们的相关研究。
一、《从征记》作者考辨
《从征记》一书,史志没有著录,而《水经注》引《从征记》,也不署撰人姓名。陈桥驿先生《水经注研究》以《水经注》卷十五洛水“又东过偃师县南”,引戴延之《从刘武王西征记》,认为《从征记》当是戴书略称[1](P451),恐非是。详下考辨。
《水经注》卷二十四汶水:
《从征记》曰:泰山有下中上三庙,墙阙严整,庙中柏树夹两阶,大二十余围,盖汉武所植也。赤眉尝斫一树,见血而止,今斧创犹存。门阁三重,楼榭四所,三层坛一所,高丈余,广八尺。树前有大井,极香冷,异于凡水,不知何代所掘?不常浚渫,而水旱不减。库中有汉时故乐器及神车木偶,皆靡密巧丽。[2](P2063)
按,此节,《北堂书钞》卷一百六十地理部三庙、《艺文类聚》卷八十八木部上柏、《初学记》卷五地理上、《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四木部三柏,并皆引之,互有详略,合之可为此《注》之证。有的直接注明是“伍缉之《从征记》”,如《初学记》卷五地理上:伍缉之《从征记》曰:泰山有上中下三庙,庙前有大井,水极香冷,异于凡水,不知何日代所掘。
《初学记》明确该文引自“伍缉之《从征记》”,可作为《水经注》所引《从征记》文段,作者为伍缉之而非戴延之的证据之一。
又,《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
《从征记》曰:洙、泗二水,交于鲁城东北十七里。阙里背洙面泗,南北一百二十步,东西六十步,四门各有石阃。北门去洙百步余。[2](P2099)
按,此条,唐张守节《史记·孔子世家》正义、《太平御览》卷六十三洙水并尝引之。《史记正义》明确引自“伍缉之《从征记》”,又可作为《水经注》所引《从征记》作者为伍缉之而非戴延之的证据之一。
根据《水经注》文字与《初学记》、《史记正义》所引伍缉之《从征记》文字对照,可知《水经注》所引《从征记》作者为伍缉之而非戴延之。戴延之的书,《水经注》亦多引,但都引作《西征记》。
另外,《艺文类聚》卷四十冢与《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礼仪部三十九冢墓四,都是既有征引伍缉之《从征记》的条目,又有征引戴延之《西征记》的条目。唐宋类书征引两书时,又时常略去撰者姓名,仅称《从征记》或《西征记》。《从征记》内容大多是今山东域内事,《西征记》多言关中之事。这些,都证明:《从征记》与《西征记》是两书,《从征记》为伍缉之作,《西征记》为戴延之作。
二、《从征记》作者生平考
诸书征引《从征记》,作者一般都题“伍缉之”,但《北堂书钞》卷八十七、《艺文类聚》卷三十九及卷四十、《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及卷五百六十等,又作“伍辑之”。但《艺文类聚》与《太平御览》有时,也作“伍缉之”。按:应从正史著录,作“伍缉之”,“辑”字乃形近之讹。
伍缉之,刘宋时官奉朝请。《隋书·经籍志》著录:宋奉朝请《伍缉之集》十二卷。两《唐志》作:《伍缉之集》十一卷。郑樵《通志》卷六十九艺文略也著录:奉朝请《伍缉之集》十二卷。
伍缉之有文集传世,说明他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或许其所作《从征记》,亦在集中。两宋之交的郑樵,在《通志》中著录此文集,说明文集在南宋初还存世。现在,其文集也早就亡佚了。
伍缉之文集不存,但其人诗文,还是在后世的类书或总集中,有一些留存。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六新歌谣辞中,有伍缉之《劳歌二首》[3](P1206):
幼童轻岁月,谓言可久长,一朝见零悴,叹息向秋霜。迍邅已穷极,疢疴复不康,每恐先朝露,不见白日光。庶及盛年时,暂遂情所望。吉辰既乖越,来期眇未央。促促岁月尽,穷年空怨伤。
女萝依附松,终已冠高枝;浮萍生托水,至死不枯萎。伤哉抱关士,独无松与期。月色似冬草,居身苦且危。幽生重泉下,穷年冰与澌。多谢负郭生,无所事六奇。劳为社下宰,时无魏无知。
这是伍缉之仅留存的两首完整的诗歌。而且,这两首诗歌还给我们提供了作者身世经历方面的一些信息。通过诗歌来看,作者应该是具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一位文士。他迫切想望有所成就,惟恐时不我待。但从“女萝依附松,终已冠高枝;浮萍生托水,至死不枯萎”数句看,其人或许生于庶族之家,在南北朝门阀制度的压抑之下,志不得伸,才不得展,故有“迍邅已穷极”的感慨。求仙之事本来渺茫,希求宦达又苦于无人荐举,只好沉沦下僚,“居身苦且危”。
第二首末句“劳为社下宰,时无魏无知”,用汉朝事典,说明自身境遇之困窘。魏无知,秦末人,楚汉战争时跟随汉王刘邦。陈平背楚降汉,正是通过魏无知求见刘邦,方才得到重用。后来周勃、灌婴等说陈平盗嫂受金,刘邦即责魏无知荐人不当。魏无知回答:“今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盗嫂受金又安足疑乎?”刘邦于是拜陈平为护军中尉,诸将不敢复言。《资治通鉴》卷十一高祖六年:
乃封陈平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4](P402)
伍缉之用魏无知举荐陈平事,感慨自己身世,可见其人必怀才不遇而又不自甘颓废,是一位积极用世的文人。郭茂倩为此诗作注曰:
《庄子》曰:“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韩诗》曰:“饥者歌食,劳者歌事。”若伍缉之云“迍邅已穷极”,又云“居身苦且危”,则劳生可知矣。[3](P1206)
可见郭茂倩对于伍缉之的不遇之悲,也非常同情。伍缉之精通乐府。《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注仪饰部一:“伍缉之曰:古铙歌有《巫山高》、《有所思》、《将进酒》及《芳树》,皆鼔吹词也。”[5](P649)
根据《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等书的零星记载,伍缉之作有《春芳诗》、《苦雨赋》、《柳花赋》、《园桃赋》等。有的文句也颇精彩。其《苦雨赋》,今已不传,或以苦雨愁霖写劳生之悲。但他写春天的诗文,则满蕴生机与活力。如:
步江皋兮骋望,感春柳之依依。垂绿叶而云布,飚零花而雪飞。[6](P691)
(《初学记》卷二十八果木部引伍缉之《柳花赋》)
桃柳发葇荣,丹绿粲郊邑。[6](P45)
(《初学记》卷三岁时部引伍缉之《春芳诗》)
伍缉之是写桃花的高手,不仅在《春芳诗》中写桃叶,更有一篇《园桃赋》,曲尽园桃情致:
嗟王母之奇果,特华实兮兼副。既陶照之夏成,又凌寒而冬就。嗟异殖兮难拔,亦晚枯兮先葳。农黄品其味,汉帝惊其珍。林休反耕之牛,宅树同恶之神。景毙勇于不足,弥增罪于甘分。虽无言兮成蹊,叵充肴于魏君。时令载始,周南申章。瞻择有制,药齐惟良。鲁拂柩以悔荆,楚供弧以事王。[7](P1470)
(《艺文类聚》卷八十六·果部上引伍缉之《园桃赋》)
作者连用事典,极力铺写园桃的色味香形,以及其避暑镇宅之用,一句一典,尽铺排之能事。即由此一文,也足见作者的博学与才思。而在他的《从征记》中,展示给我们的,则是另一种谨慎而自如的文笔。
东晋义熙五年(409年),东晋中军将军刘裕率军北伐,进攻南燕。伍缉之跟随刘裕北征,后来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从征记》。
三、《从征记》亡佚时代考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最早征引《从征记》,卷二十四到卷二十六,三卷中共引八节,说明此书是郦氏撰写山东地理时的重要参考书籍。
唐代,虞世南《北堂书钞》征引《从征记》四节,欧阳询《艺文类聚》征引五节,徐坚《初学记》引四节。《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章怀太子注,引一节。此外,司马贞《史记索隐》卷九、张守节《史记正义》卷四,各征引一节,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十三海州临沂县引一节。唐代诸书皆征引伍缉之《从征记》,表明其书在唐存世。
北宋,《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著录:伍辑之《从征记》(按,“辑”乃“缉”之误)。李昉等《太平御览》征引《从征记》最多,达九节。乐史《太平寰宇记》引三节。《册府元龟卷》三十九帝王部引一节。由著录和征引情况看,北宋时,其书应该还在。
但南宋征引《从征记》者骤减。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九引一节,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九十五引一节,朱长文《墨池编》卷六引一节,罗泌《路史》引一节。宋末王应麟《玉海》引二节,《困学纪闻》卷十六引一节。查考诸书所引内容,大抵不出前人征引内容之外,仅罗泌《路史》卷二十六《国名纪三·闾丘》引《从征记》:“高平东、阳东北,有漆县,漆乡东北十里有闾丛乡。”不知此节文字是罗泌从何书转引而来。[8](P291)罗泌(1131—1189)是南宋初人,但与其同时的吕祖谦(1137—1181),在其《大事记解题》卷九引《从征记》,已经明确说明其是自《水经注》转引而来的,即“洙泗二水交于鲁城”一节[9](P329),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六所引之一节,也是该节,也明确说明转引自《水经注》。王应麟《玉海》卷九十八封禅所引一节,也标明其转引自《史记·汉武封禅》正义。[10](P599)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似可推测:伍缉之《从征记》原本在南宋已经亡佚,甚至可能在南宋初即已亡佚。《从征记》今尚无辑本。
四、《从征记》的史料价值
伍缉之《从征记》,具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从《水经注》大量征引已经能够略见一斑。首先,《从征记》尤其详细地记述了汶水和淄水流域的情况及其相关的历史遗迹,是郦道元撰写《水经注》今山东地区水域地理时的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从征记》的相关记载,为更好地研究汶水、淄水流域的文化状况提供了便利。
《从征记》中还有一些记述,受到了后世学者的普遍关注。如《水经注》二十五泗水:
庙屋三间,夫子在西间,东向;颜母在中间,南向;夫人隔东一间,东向。夫子床前有石砚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时物也。鲁人藏孔子所乘车于庙中,是颜路所请者也。献帝时遇火烧之。[2](P2108)
按,《水经注》此条,郦氏并未说明其是引自他人之书。但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四艺文部砚引《从征记》云:
夫子床前有石砚一枚,作甚古朴,盖孔子生平时物也。[5](P510)
可见,《水经注》所述,即是从《从征记》而来,所以郦道元用“云平生时物也”这样的语气叙述,这个“云”,即伍缉之所云。而且,《艺文类聚》卷五十八杂文部四砚、《初学记》卷二十一文部、《太平御览》卷六百五文部二十一砚、朱长文《墨池编》卷六、陶宗仪《说郛》卷九十六等,都征引《从征记》此条。但也有学者对《从征记》的这个记述提出过怀疑,如宋孙奕《示儿编》卷二十三就说:“然伍缉之《从征记》:孔子庙中有石砚一枚,乃夫子平生物。非经史不足信。”[11](P580)但从以上征引情况来看,还是相信者居多。儒者慎终追远,传留祖宗遗物,也很正常。又《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唐章怀太子贤注:
伍缉之《从西征记》曰:
鲁人藏孔子所乘车于庙中,是颜路所请者也。献帝时庙遇火,烧之。[12](P1440)
按,《从征记》所说孔子所乘车是“颜路所请者”,可见《论语·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13](P124)《从征记》中的这些内容,也同样被很多学者征引。如《册府元龟卷》三十九帝王部,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九,王应麟《玉海》卷七十八,元陶宗仪《说郛》卷九十六等,均引之。
综合以上两条《从征记》内容,知《水经注》所叙,正是出自《从征记》,郦氏乃暗引或抄变《从征记》内容,而未明确指出所引之书。同时,后世有这么多学者转引《从征记》关于孔子的这些记述,《从征记》的史料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从征记》中关于孔子的遗闻,还有一些。如:
伍缉之《从征记》曰:
洙、泗二水,交于鲁城东北十七里。阙里背洙面泗,南北一百二十步,东西六十步,四门各有石阃。北门去洙百步余。[2](P2099)
(《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
伍缉之《从征记》曰:
孔丛云,夫子墓方二里,诸弟子各以四方木来植之,今盘根犹存。[7](P732)
(《艺文类聚》卷四十冢墓)
伍缉之《从征记》曰:
谯周云,孔子后,鲁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余家,曰孔里。[14](P766)
(《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七州郡部三里)
这些关于孔子逸闻遗事的记述,为后世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从征记》最早指出孔子的故乡阙里所在位置是“背洙面泗”,此说也一直被《水经注》、《括地志》、《史记正义》等沿说。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在辨析阙里地名渊源时说:
“孔子时无阙里之名。阙里首仅见《汉书·梅福传》,东汉后方盛称之。盖缘鲁恭王徙鲁,于孔子所居之里造宫室,有双阙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阙里。《北史》宋版引王肃注本《七十二弟子》,解阙里作闾里,《家语》乃是闾字,非阙字,犹能知孔子时断无阙里之名。陬城之阙里,以曲阜之阙里名,其地非真阙里也。真阙里则伍缉之所云‘背洙面泗’。按:陬,今山东曲阜县东南陬城。”[15](P4)
除了孔子墓外,《从征记》还介绍了今山东地区的一些其他古代名人冢墓的情况。如:伍缉之《从征记》曰:
齐襄王墓在汝水西。墓西有僖公墓,东有四田墓,传云,倨、荣、广、布也。墓皆方墓圆坟。[14](P2530)
(《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冢墓)
尤其是刘表冢的记述,很有研究价值:
刘表冢在高平郡,表之子琮,捣四方珍香数十斛,著棺中,苏合消疾之香,莫不毕备,永嘉中,郡人发其墓,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7](P732)
(《艺文类聚》卷四十冢墓引)
按,此条,《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三关西道庆州、《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二香部亦引。《太平寰宇记》所引,还有盗墓者的名字,叫卫熙,当看到“表貌如生”时,“熙惧不敢犯”。[16](P285)这条记述,对于现在研究汉代墓葬及尸体处理技术,都有参考价值。《从征记》记述说刘表被随葬珍香数十斛,其墓被发时,“表白如生,香闻数十里”。这似乎在暗示刘表的“白如生”乃得益于珍香。珍香大概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尸体的腐烂进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伍缉之《从征记》还记述了古代临沂一带的人祭风俗:
临沂厚邱间,有次睢里社,常以人祭。襄公使邾子用鄫子其俗,相承雇贫人,命齐洁祭时缚着社前,如见牲牺,魏初乃止。[5](P409)
(《北堂书钞》卷八十七礼仪部社稷引)
此条,《艺文类聚》卷三十九社稷也有征引,略同。从这条记述看到春秋时期人祭仪式被逐渐废除的历史过程,反映了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人的价值和尊严逐渐受到重视的转变。
《从征记》还有关于泰山的一些记述。如:
泰山于所经诸山为最高。见岑崿轩举,凌跨众阜,云霞草木,霭然灵异,苑囿神奇,故无螫虫猛兽。[14](P188)
(《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地部四泰山引)
自天岘至太山,皆有紫石英,太山所出,特复瑰殊。[14](P4367)
(《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七药部四紫石英引)
汉武封坛,广丈三尺,高丈尺,下有玉箓书,以金银为镂,封以玺。[10](P599)
(《史记·汉武封禅》正义引)
关于泰山的高峻、神奇,泰山的物产,以及汉武封禅泰山的情况,都见诸记载,而前文《水经注》所引《从征记》关于“泰山有下中上三庙”的记述更为详尽。这些,也都是我国地理书籍中关于泰山的较早的记录,具有很大的资料价值。其实,不仅是泰山,齐鲁之地的其他一些山水,《从征记》也有记述:
青岘,一名小岘,木多栌杏。[14](P272)
(《太平御览》卷五十六岘引)
峄山,北岩有秦始皇所勒之铭。[17](P1367)
(《史记·封禅书》张守节正义引)
这些,也都成为后世研究齐鲁历史文化和资源矿产等的重要资料。
五、《从征记》的文学价值
由于伍缉之是刘宋时期的文学家,故其《从征记》也表现出了相当浓烈的文采。
首先,是山水描写的精彩生动。如:
大岘去半城八十里,直度山十五里,崖坎稍曲,石径幽危,四岳三涂不是过也。山高三里,周回四十二里。[16](P202)
(《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沂州引)
前写大岘山“石径幽危”,以“四岳三涂”为比衬,加深读者印象;后节写泰山,以“岑崿轩举,凌跨众阜”状其高,以“云霞草木”写其美,以“无螫虫猛兽”道其奇。不但写山如此,写谷写水写泉亦复如此。如:
汶水出(莱芜)县西南流……自入莱芜谷,夹路连山百数里。水隍多行石涧中,出药草,饶松柏,林藿绵濛,崖壁相望,或倾岑阻径,或回严绝谷。清风鸣条,山壑俱响,凌高降深,兼惴慓之惧,危蹊绝径,过悬度之艰。未出谷十余里,有别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数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余,高九尺许,广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处,薪爨烟墨犹存。谷中林木致密,行人鲜有能至矣。又有少许山田,引灌之踪尚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种麦,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麦,齐人相承以殖之,意谓麦丘所栖愚公谷也,何其深沉幽翳,可以托业怡生如此也!余时迳此,为之踟蹰,为之屡眷矣。[2]2057
(《水经注》卷二十四汶水引)
这段关于莱芜谷的描写,实在精彩,是一篇优美的山水文。先写山谷,再写山谷中的清泉,再写因为水的滋润而可以“托业怡生”的山田,由水之所出写到水之所利,叙述描写,逻辑严密,次序井然。写谷之美,以药草、松柏为点缀,写“林藿绵濛”之景,又以“崖壁相望,或倾岑阻径,或回严绝谷”写其幽邃,又以“凌高降深”、“危蹊绝径”写其过往之艰,作者还特意描写“清风鸣条,山壑俱响”,以增加画面的动感,愈显真实。写清泉石穴,插入一句“言是昔人居山之处,薪爨烟墨犹存”,显现幽秘色彩。最后写水利怡生,作者更是情不自禁地直接抒情:“余时迳此,为之踟蹰,为之屡眷矣。”凡此描写,引人入胜。
此外,《从征记》关于古迹的记述,也同样文笔精彩。如:
泰山有下中上三庙,墙阙严整,庙中柏树夹两阶,大二十余围,盖汉武所植也。赤眉尝斫一树,见血而止,今斧创犹存。门阁三重,楼榭四所,三层坛一所,高丈余,广八尺。树前有大井,极香冷,异于凡水,不知何代所掘?不常浚渫,而水旱不减。库中有汉时故乐器及神车木偶,皆靡密巧丽。[2](P2063)
(《水经注》卷二十四汶水引)
广固城北三里有尧山祠,尧因巡狩登此山,后人遂以名山。庙在山之左麓,庙像东面,华宇修整,帝图严饰,轩冕之容穆然,山之上顶,旧有上祠,今也毁废,无复遗式。盘石上尚有人马之迹,徒黄石而已,惟刀剑之踪逼真矣。至于燕锋代锷,魏铗齐铭,与今剑莫殊,以密模写,知人功所制矣。[2](P2235)
(《水经注》卷二十六淄水引)
前节写泰山三庙,作者主要写两处遗迹,一是庙中柏树,二是树前大井。写柏树,加入“汉武所植”、“赤眉尝斫”以显现其历史感;写大井,则写其“香冷”和“水旱不减”的神异,再加上作者“不知何代所掘?”的一问,立刻把读者引入了关于古庙历史的深沉思索中去。后节写尧山祠,作者主要写两处遗迹,一是庙像,二是盘石刀剑之迹。写刀剑之迹时,作者说其无异于今剑,是“人功所制”,看来古人也会造假。其实,这两节所写的遗迹,都很平常,不过是普通的树,普通的井,普通的庙像,普通的石头,但一经作者道出,便尽显其历史的沧桑。
《从征记》也给后世的文学创作留下了一些创作素材。如前文所引刘表墓事,庾信就曾多次在文中化用。庾信《周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同州刺史尔绵永神道碑》:“刘荆州之墓,合葬于襄水之阳;卫将军之陵,同穴于庐山之下。”又庾信《周太傅郑国公夫人郑氏墓志铭》:“家亡淑女,国丧贤姬。香坟永送,舞鹤长辞。”其中“刘荆州之墓”、“香坟”的说法,即出自伍缉之《从征记》。再如《从征记》中所记“阙里,背洙面泗”一节,徐陵《皇太子临辟雍颂》有云“洙泗兴业,阙里增荣”,李商隐《为安平公兖州谢上表》说“本孔里周封,有尧祠舜泽”,也都是其《从征记》中的相关记载。
总之,伍缉之以文学家的手笔而撰著历史地理作品《从征记》,使其表现出浓烈的文学意味。尤其是其山水描写,为此后包括《水经注》在内的地理文学著作树立了很好的创作榜样,对中国山水散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1]陈桥驿.水经注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2](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注疏[M].(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3](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四库全书本第88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唐)徐坚撰.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唐)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8](宋)罗泌.路史(四库全书第38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四库全书第32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宋)王应麟.玉海(四库全书第94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宋)孙奕.示儿编(四库全书第86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唐)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1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宋)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5](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16](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四库全书第46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7](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