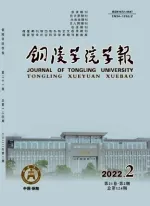新诗教学在文学史教材中的渐变研究——以唐弢、黄修己及钱理群编著教材为中心
黄晓东
(铜陵学院, 安徽 铜陵 244000)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教育与此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点在教材中也反映得很明显。而新诗由于其文体本身所具有的“短平快”等特征,更能让我们清晰地看出“新时期”以来文学史教材对诗人、新诗流派、新诗文本的叙述与评价所呈现出的缓慢但却又持续的变化。所以本文就拟通过对唐弢、黄修已及钱理群编著的新文学史教材中“诗歌章节”的细读,分析教材对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李金发等人及其所代表的诗歌流派的评价如何呈现出一种渐变,并最终重估非左翼诗人的新诗史价值,使新诗史的叙述由政治回归审美,从而恢复新诗史本来面目的。
一、对胡适新诗史地位的逐步重估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对“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清理,以及思想的逐步解放,新诗史的本来面目逐渐得以恢复。而这种变化最早是从新文学史教材对新诗史上的一些由于政治等原因而长期被遮蔽的诗人的叙述、评价进行逐步的调整、改变开始的。例如,唐弢主编的共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1979年至1980年短短两年内编写完成并出版,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新形势下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需要。1984年3月为了对外交流的需要,唐弢主编的这三卷本的文学史被压缩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但是,就在1979年至1984年这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压缩本的文学史“简编”中对新诗史的叙述却与此前的“三卷本”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黄修己所言,“与三卷本对比,《简编》提高了非左翼的,甚至曾经反共的,却在新文学发展中有过贡献的作家的地位。所谓‘提高’,是与以前对比而言,准确地说,是‘恢复’,也就是说这样评价才更接近历史的实际”[1]。当然,这也说明“从‘三卷本’到《简编》,反映了从1979年到1984年五年间作者思想的变化和学术研究的进展”[1]138。唐弢的“简编本”现代文学史中对新诗史叙述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充分肯定了胡适对新诗尝试的功绩,明确指出胡适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然后,花了较大的篇幅来介绍胡适的《尝试集》及其中的代表性诗作。例如胡适在“民国”期间曾经多次入选小学国文课本的《上山》,教材认为它“摆脱了旧诗的窠臼,运用近似口语的白话,把日常生活中的爬山一事写得诗意盎然,富有节奏,表达了积极进取,努力向上的主题,在文学革命初期产生过积极影响。后来这首诗曾谱成歌曲传唱”[2],这样就还原了单篇作品在历史上的面目及其文学史意义。另外,教材也开始摒弃以阶级观点来评价和分析诗人及诗作,同时还原新诗创作的背景,从而力图客观平正地评价诗作。例如,教材指出胡适的《周岁》是为《晨报》出版周年纪念而写;《乐观》是为《每周评论》被查禁时所写;而《一颗遭劫的星》则为《国民公报》被封而作,“表达了对封建黑暗的诅咒和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向往”[2]。而对胡适参加的新文化运动与《尝试集》的关系也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认为胡适“那时参加了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思想上具有要求冲破封建束缚、争取自由民主的积极因素,《尝试集》里的有些诗篇表达了这种思想情绪”[2]。对于胡适《尝试集》的文学史意义的评价则是“思想内容并不引人注目,语言形式的革新在文学革命初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2]。教材也开始承认郭沫若的《女神》是《尝试集》之后出现的,指出继《尝试集》之后“郭沫若《女神》的出版,更为诗歌创作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局面”[2]。当然,这种“局面”也是在“继胡适发表白话诗之后,《新青年》等不少报刊陆续发表不少白话诗作”的情况下出现的[2]。这样,教材就对胡适及其新诗创作基本上给予了客观公允的叙述与评价,纠正了“十七年”及“文革”期间从政治及阶级立场出发,以及在大陆对“反共”作家胡适进行大批判的背景之下,出现的对于胡适无限上纲上线的非客观的“评价”。从而,对于新诗史的肇始,在大陆1949年之后的新文学史中,开始出现了与历史实际相符合或接近的叙述与评价。
二、对徐志摩新诗史地位的逐步重估
唐弢的“简编本”教材中的第二个重要调整,是对胡适之后的另外一个非左翼作家,甚至是“反共”作家徐志摩的新诗创作及其文学史地位,作出了与此前大相径庭同时也是较为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叙述。在“简编本”中,徐志摩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教材章节的目录中,并且排在闻一多的前面,被称之为新月派的“盟主”。教材从《晨报副刊》开始谈论徐志摩以及胡适等人的文学活动及文学主张,指出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同他们‘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相反,实际上政治意识极为强烈”[2]。对于徐志摩对资产阶级民主社会的向往,教材也给出了历史的分析,指出“这种空泛的向往,曾经是‘五四’时代许多青年共同的心声。因此,《志摩的诗》里虽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但主调还是同‘五四’的时代声音协和的,可以说是‘五四’时代思潮的一个产物”[2]。而对于徐志摩反对暴力革命和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诗作《西窗》等,教材也只是引用了茅盾当年的评价,即徐志摩希望的那个“洁白肥胖的婴儿并没有在中国出世”。同时,教材淡淡地说“徐志摩同时代和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是,徐志摩转而“却以全部精力去追求诗的格律的改革与创造,诗的音调的和谐与匀称。由于诗人感情的真挚,对西洋诗歌的深厚的造诣和不懈的探索,也终于写出了一些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好诗”[2]。教材中对“五四”时期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人道主义也作出了肯定,认为在“诗集《翡冷翠的一夜》里,诗人还没有完全忘却人间的疾苦,《大帅》描述军阀混战带来的灾难,《庐山石工之歌》对劳动者仍寄以同情……”[2]。而在之前的“三卷本”文学史中却并非如此,编者曾经认为徐志摩用其浙江故乡的方言“硖石土白”写的一首诗表现人道主义的诗作《一条金色的光痕》中“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消极性也有所暴露:《一条金色的光痕》借被施舍者之口,对一个‘体恤穷人’的阔太太作了肉麻的歌颂”[3]。另外,“简编本”对徐氏诗歌艺术的一些分析,在当时看来亦是颇有见地的。例如,认为“代表徐志摩艺术成就的,是那些并无明显社会内容的抒情诗。如诗人自己说,它们是‘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2]。同时对徐志摩的新诗史地位亦作出了较高的评价,认为“这些诗音节和谐,想象丰富,比喻贴切(如《沙扬娜拉》),能构成优美的意境,具有圆熟的技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我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2]。
唐弢的“简编”本现代文学史中也开始提及到周作人的新诗创作。确实,周作人在新诗肇始期为新诗的发展曾经做出了自己了努力和贡献,其诗作《小河》及《乐观》在民国时期的国文教材中入选的频率很高。但是在“十七年”的新文学史中,对周作人的评价还是在“汉奸文人”这一框架之内,即使在唐弢的三卷本新文学史中对周作人的叙述也是相当谨慎的,因为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曾经明确指出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的,是汉奸文艺。但是简编本新文学史尽可能摒弃了从作家的政治立场和个人的历史评价来对文学史进行叙述的弊病,客观、历史而且较高地评价了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新诗写作:
一九一九年初,周作人的白话新诗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如《小河》、《两个扫雪的人》、《路上所见》、《北风》、《画家》等篇,以清新的语言表达了作者的情思。尽管“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但以接近口语的白话作诗,而且完全摆脱某些旧诗无病呻吟的情调和束缚思想的格律,在新诗开创时期产生过积极影响。这些诗后来选入文学研究会编的诗集《雪朝》(第二卷)和作者自编的诗集《过去的生命》。其中《小河》、《画家》、《歧路》等篇意境新颖,以轻盈的笔调写出了作者对人生问题的沉思默想。[2]
而唐弢主编的前后两版教材对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的评价也是前后差别极大。“三卷本”认为李金发的诗歌“实际上大多是一组组词和字的杂乱堆砌,连句法都不象中文。这种畸形怪异的形式,除了掩饰其内容浅陋之外,正便于发泄他们世纪末的追求梦幻、逃避现实的颓废没落的感情”[3]。甚至认为,在“我国新诗发展过程中,象征派所起的作用是反动的”[3]。而之所以这样评价象征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诗的内容让人读不懂,因为“稍后的‘现代派’诗人,虽然创作倾向跟法国象征派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诗的内容已较明白好懂,而且也确实有几首好诗了”[3]。而“简编版”教材只是客观地指出象征派诗歌的比喻让人无法捉摸,而不再认为其是“反动”的,只是认为“在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同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相比,象征派的影响比较微弱”[2]。
三、对周作人等新诗史地位的逐步重估
在1980年代前期的新文学史教材中,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以下简称为《简史》)也是当时在高校内使用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一部。如黄修己本人所言,《简史》是“间断了近三十年后最早出现的个人编著的新文学史著”,“出版后,反响比较热烈,见诸报刊的评论多给与好评”[1]。“当时引起反响的原因主要在于教材有一些新鲜独特之处,它较多地吸收了1980年代这个领域的新成果,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1]。而这些特点具体到教材的内容上,就是黄修己当时认为对于1949年之后在大陆的文学史中被划入“反动”作家行列的胡适、周作人等非左翼作家,“应该历史地评价他们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1]。1988年,为了更加适应于教学的需要,作者也将这部教材修订后再版,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发展史》)。修订后的《发展史》篇幅有所扩大,作者自称只是为了便于学生自学,对教材《简史》中的一些重点内容分析得更为详细。其实,比较而言,《发展史》对有些作家包括诗人的论述在观点上前后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尤其是对胡适、徐志摩等一些在中国大陆评价不断发生变化的作家。可见当时对新诗及诗人的评价一直在调整和变动之中,而这在1980年代也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简史》中对胡适新诗创作的评价,“胡适的诗大多思想内容空虚,未能充分表达‘五四’时代的精神,……艺术上较之俞平伯的《冬夜》(1921)、康白情的《草儿》(1922)也相形见绌”[4]。在《发展史》中,上述这些评价被删除了,相应的叙述则被调整得更为平和:
“在诗的艺术创造上,它的确不如晚一年出版的郭沫若的 《女神》,而且也赶不上俞平伯的 《冬夜》(1921)、康白情的《草儿》(1922)等初期的诗集。 它毕竟是最早出版的个人的诗集(别集)。如果说《女神》在新诗发展中起了奠基作用,那么《尝试集》就是以它的开辟作用而取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4]
《简史》与之后的《发展史》在对胡适的叙述上前后一致的观点是认为,“《尝试集》在短期内能多次再版,销售量超过万册,这在当时已很不容易,说明他的尝试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尽管后来有人认为《尝试集》只不过给后人做了垫脚石,但起到垫脚石的作用,就是一种肯定性的评价”[5]。同时,两版教材都通过对胡适与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写作及其总体的文学史意义作出比较后,得出了当时看来较为个性化、学理性的结论,即胡适对新诗之功主要在于“开辟”与“尝试”。
对于周作人早期的新诗创作,作者在《简史》中也未从“阶级论”或者“历史身份论”出发去叙述和评价。对于周氏在“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给予了不低的评价。例如,教材指出“周作人的《小河》曾发生较大的影响。……《小河》一诗不但用了相当平白自然的口语,而且虽系说理却用了象征的手法,使人耳目一新”[5]。而到了《发展史》中对周作人新诗的阐释则更进了一步,认为《小河》不仅是用新诗象征手法来说理“启蒙”,反对束缚人性应该使人的个性自由的发展。同时,还从文艺思潮的角度指出周作人《小河》的象征手法来自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的影响。
下面仍然来考察黄氏的文学史对新月派及徐志摩的评价及在教材前后版本中的变化。在《简史》中,“新月派”及闻一多、徐志摩是放在第七章“探索中的新诗”这一大标题下,和各派诗人放在一起叙述和评价的。在《发展史》中,则是放在第五章第二节“闻一多、徐志摩和格律派诗”中,专节来叙述的。在《简史》中编者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从“历史身份”的角度对徐志摩进行评价,将徐氏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称为“幼稚”的“幻想”。同时,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天生的具有软骨病,所以面对社会黑暗的现实只能陷入颓废与幻灭。这种观点其实还是来自于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阐述。在《发展史》中编者对徐氏政治思想的评述则改为引用茅盾对徐志摩的评价。另外《简史》中对徐志摩《残诗》的分析还是沿用了“十七年”以来的错误的分析,认为“《残诗》对皇族的没落表示哀伤是不足取的”[4]。其实,徐志摩在《残诗》中表达的是对封建专制政权覆亡的一种嘲讽和快意。因此,在《发展史》中这个观点得到了纠正。不仅如此,《简史》对于徐志摩诗中表达出的对下层民众的同情的人道主义,黄氏也和之前的一些文学史一样,认为徐志摩也能勉强的“对贫苦的人民表示一些同情心”[4],这一点在修订版中也有改变。最后,《发展史》中对徐氏的诗歌叙述的篇幅大为增加,而且更注重从“三美”理论展开阐释。在《简史》中对李金发的象征派诗歌更多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因为社会黑暗,一些知识分子感到生活不安、前程渺茫,产生悲观、颓唐的情绪,接受了西方世纪末情绪和现代派文学的感染,便在诗的创作中加以表现”[4]。在《发展史》中对象征派的社会学分析大致没变,但是改成了引用“马拉美”的观点。当然,修订版开始大篇幅地从艺术的角度分析象征派的诗作。最后黄氏的《简史》开始将“九叶诗派”纳入自己的叙述视野。黄氏自己也认为对现代主义文学作出了较为完整的描述。编者想说明的是,自己对新文学史上长期以来因为政治等原因被遮蔽或有意无意忽略,以及重视不够的诗人、诗派,力图进行重新发掘或对其进行合乎史实的还原及评价:
“从李金发的象征派诗,到1930年代戴望舒的诗,还分析了卞之琳、何其芳等的诗与现代派艺术的关系。对于1940年代,给穆旦等九位诗人以一定地位,并冠以‘九叶诗人’之名。此后也有人称之为《中国新诗》派,但似乎‘九叶诗人’的名称被用得更普遍些”。[1]
四、新文学教材中新诗史面目的逐步恢复
对新诗史的叙述经过上述逐步的调整后在教材中逐渐稳定下来。1987年钱理群等人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三十年》)出版,并逐渐在高校内大范围使用。教材对新诗的叙述进一步摒弃政治定性、阶级分析等思路,更多地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着眼,对新诗的阐释也更加富有学理性及学术个性。黄修己认为《三十年》的文学史观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奋斗的文学,……这个观点没有脱离强调文学社会作用的大框架,思路偏向于与文学关系更近的文化,……较之只强调新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有其优越性”[1]。与之前的众多新文学史教材相比较,黄修己指出,“人们不满过去新文学史著作千人一面的状况,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指导编书的文学史观大致相同相近。《三十年》在这方面有所突破”[1]。《三十年》在 1998年修订出版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较之前的版本对新诗的叙述再次作出不小的调整,吸收了近些年的新成果和新观点。因此,其中对新诗史的叙述和阐释更趋于稳定,并且其中的一些论点在近年似乎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学术观点。而《三十年》修订前后的一些主要观点表现在:修订本在强调胡适新诗创作“尝试”之功的同时,进一步从共时的角度出发指出胡适的诗歌风格和当时的另外一路“晦涩难懂”的诗歌形成了一种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而对于“新月派”和徐志摩等人的文学史意义教材指出,“新月派”所作的对于格律诗的艺术实验是严肃的,因为其力图将新诗重新纳入一种“规范”。同时,格律诗和自由体新诗互相竞争和渗透,共同推动了新诗的发展。对于徐志摩的评价在教材中则是确定的并且前后一致的,“徐志摩总是在不拘一格的不断实验、创造中追求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的统一,以其美的艺术珍品提高着读者的审美力:徐志摩在新诗史上的独特贡献正在于此”[6]。总的来说,教材在进一步提升象征诗派、“九叶诗派”以及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等人为主的现代诗派地位的同时,也没有遮蔽中国诗歌会等左翼诗歌流派及其创作或早期以蒋光慈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诗歌创作”。这样,教材中新诗史的叙述在内容上更加趋于丰富和多元,这也与新诗发展的历史更为接近。这一切也为此后的新诗教学转向更为注重艺术阐释和审美分析奠定了基础。
总之,从唐弢的“三卷本”到“简编本”,黄修己的“简史”到“发展史”,钱理群等人的《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初版”到“修订版”,随着政治文化的变化,教材对新诗史的叙述也出现了逐步的调整,对诗人诗派也开始逐步重估,从而某种程度上最终还原了新诗史的原貌。
[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
[5]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6]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