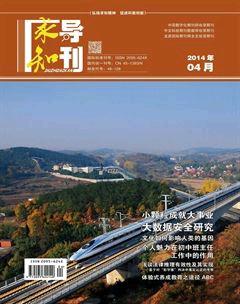论读书
凌宗伟
时下教师很少读书,甚至有不读书的情况,貌似早已成为社会的诟病,于是有人认为要是哪一天我们这些教师真的成为名副其实的“读书人”的话,我们教师都能守住应有的专业操守也许会成为一种可能,教师的专业成长也许有希望成为现实。于是有不少有识之士将自己身边志同道合的同仁组织起来读书,思考,实践,更有人到处呼吁教师要沉下来读几本书,用自己的阅读来改变自己的教育人生。
一时间教师读书貌似正变得越来越时髦,不管是民间的学习组织,还是官方的考核评定,都将之纳入其中,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同时,出书更似乎成了推动“名师成长”的必由之路,甚至成了某些人将自己推上某把交椅,成为某个群体的“老大”甚至“开山之祖”的捷径了,当然也并不排除极个别高人瞅准了势道,利用现有的身份既谋名又牟利的。
呵呵,似乎扯远了。且不论是否人人动机纯正,意坚志满,勤勉笃厚,扒皮在这里只想从读书本身来扯一扯,在我看来,时下的书其实不是遍地黄金,我们一不小心,搞不好,也许读成了纸上谈兵的赵括,或做了东施效颦的蠢事,非但无益,还贻害无穷,即扒皮所谓的“人身读书糊涂死”。尤其是在当下有人动辄炫耀一年读了“好几十本书”,似乎读书多少,已成高低贵贱的评判。却忘了老祖宗训诫:“刘项原来不读书”,又说“信尽书不如无书”,从某种意义上看,极具反讽之意。
刘邦、项羽从不读书,缘何成王成霸?六祖慧能,根本就不识字,遑论读书,如何留下震古烁今的《坛经》?如此看来,读书还是有讲究和说道的,否则,不读也罢。在图书市场日渐丰富的今天,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海量选择下,如何确定自己的可读和必读的书呢?
我以为读什么书,成就什么思想。书,有可读与不可读之分,有些书根本就不能读;有些书读一两句足矣;有一些则是要读一辈子的。书,非选不能读!具体来说,我有“五不读”原则,也可以说就是“一不读”:
东拼西凑者,不读。虽说“天下文章一大抄”,但“抄”的前提是有方法,有智慧,有创新,有精进,而不是东拼西凑,抓到碗里就是菜。现今做教育读物也简单,拿几个所谓的“名校”“名师”,乃至于某些“成功”了“模式”“经验”反复炒作,加上三五案例,人物成长“故事”,就是一本书。过两年,再凑几个故事,变个名头,换个出版社,再来一个“新书发布”的什么的。这类的精神鸦片,就如同前几年泛滥的“成功学”“励志学”一样,同质化、空心化、虚假化最甚,书商卖的根本不是书,而是“虚名”和“妄念”,明着教你“跟某某学做学问”,实际上去操作,没人能变现,最好只好安慰自己一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以为,此类书最不能读。
胡编乱造者,不读。有些“名家”出一本书早已经不过瘾了,总想着“重磅推出”,尽快使自己成为中国教育的“大家”,乃至影响全球的“大家”,动辄一出几卷,甚至全集。或者“曲线救国”,将书出到国外,然后再翻译进来。而我们这些“好读书”的教师呢,又往往忘了历史的经验,所谓大家名著,对一个作者而言,值得自豪的,万古流传的,不就那么一本,甚至一句,几句的东西哦。
自以为是者,不读。这种书的作者多善自说自话和自我表彰,常以所谓的中国“第一本”“第一部”或者“独创”“唯一”之类的词语自诩。许许多多文字原本就是他今天飞这,明天飞那,吐沫横飞,今天说这个“课堂”,明天谈那个“模式”满世界忽悠的言辞,听起来都是“课改”理念,“自主”“探究”“合作”什么的,实则也不外乎为树大旗,立山头,玩弄名词,左右世人;又或者,以煽情矫饰为能事,以博取同情为卖点,如此钻营,看似金玉其外,实则败絮其中。读来读去,最后发现,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除了自以为是的闭门造车和拍胸脯式的夸夸其谈外,还有什么?
脱离实践者,不读。教师所读的书,一要“真实”,二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因为他们每天面对的都是活生生的孩子,所处理的也是繁复多变的工作,因此他们读的书,必须要能“接地气”,这与学院派的研究是完全不同的。从这点上看,有些理论书本身是有益的,但对绝大多数教师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现场感”和“在地性”,也即实践指导,此其一。其二,有些书存在“伪实践”的状况,看似在谈实践举措或教学实验,实际上还是东抄西挪,胡乱编造。稍加分析,就能看出一个个“造神运动”“奇迹工厂”“大师制造”中的有悖情理之处,这又如何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我一直以为,教育要回到人之常情上来,不要迷信和盲从,于是,就谈到下一个原则。
一言以蔽之,无独立思考者,不读。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在装点门面,攫取荣誉,附庸风雅,还是在迎合检查,还是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显然,都不是。它的功能,在使人思路开阔、目光深邃、思维理性、行动有力,是人的精神支柱。这其中,人的独立性是根本前提,所以,一本好书,就应该有说自己的话,想自己的问题,践行自己的理想——甚至可以说,有时候,仅仅一句话,就足够支撑一本书的生命。所以扒皮特别认同刘良华老师的那句:“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只要你读到‘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败,就够了,这句话,就抵一本书。”是的,有些道理本就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得很清楚,很明白的,愣是那些“说书艺人”出于生计的缘故,将武松打虎之类的故事给演绎成了几天几夜说不完的故事了。
心理学上有个“手表定律”,即戴一只手表尚可以知道时间,而戴两只读数不同的表反而就错乱了。这种书做的,就是这类“贡献”:你不读还懂一点教育,读了,却反而糊涂了。因为它们根本就是从“拍脑袋主义”里走下生产线的,内容粗浅,情节杜撰,道理泛泛,语言浮夸,实在是尽“山寨”之能事。虽然满纸的调查数据、课堂教学、道德文章、名人名典,但多不过是“障眼法”——前后逻辑、内核精神、价值体系都无从谈起,倘若今天花一分气力去读书,明日必得用十分精神去“排毒”,孰得孰失?
如果一部书句句如此,那就成了“经”,成了“典”,成了永恒。
实际上,我们在书市翻到的书中,能教人独立思考者,能成就独立人格者,少之又少。一般都是上述四种情况,读了之后,才知道“刘项原来不读书”的宝贵,所以近年来很多有识之士提出“阅读经典”“回归传统”,可能正是在这种痛苦之下的无奈之举吧。
今天,读到一本书,若能理性的解构文本,若能间有闪光之处,若能妙手偶得一二句,就已经万幸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在茫茫书海中做出选择的重要性,可能远远大于阅读本身的重要性。只有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在乏善可陈、滥竽充数的时下环境中找到一处心灵栖息之地。
所以,扒皮认为,有些书是不能读的。或者说,书,非选不能读!否则,读之愈深,害之愈甚。(来源:《湖南工人报》,2013-11-22,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