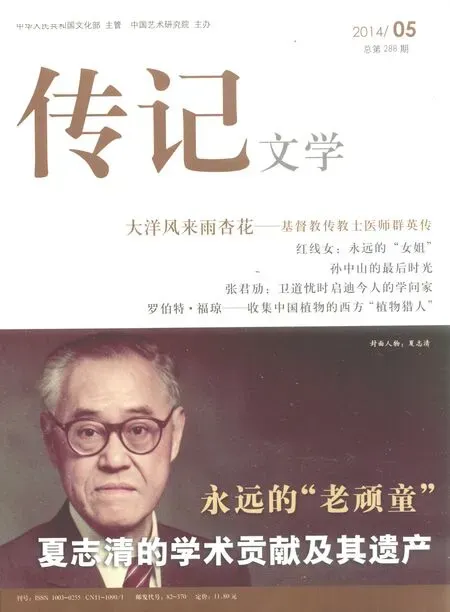在普世与入世间
——70年代后 夏志清的现代 文学批评
黄文倩
在普世与入世间——70年代后 夏志清的现代 文学批评
黄文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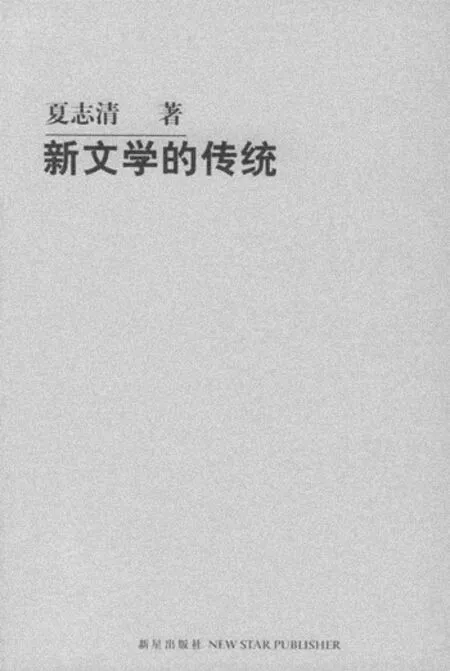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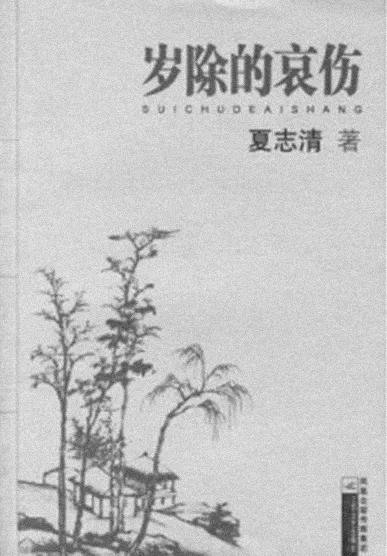
一
2013年12月29日,一
代文学批评家夏志清(1921-2013)病逝于美国纽约。众所周知,冷战初期,夏志清曾接受美国政府的资助,和饶大卫(David N.Rowe)等人编写过一
部《中国手册》(China: An Area Manual),并以196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奠定他在美国汉学圈的学术地位。这部专书的中译本,由刘绍铭、李欧梵等编译,于1979年台北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及香港的友联出版社出版。夏志清后来的著作中译本,也多先在台湾出版,主要包括:《爱情·社会·小说》(1970年)、《文学的前途》(1974年)、《人的文学》(1977年)、《新文学的传统》(1979年)、《夏志清文学评论集》(1987年)、《鸡窗集》(1984年),《谈文艺、忆师友——夏志清自选集》(2007年),及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2013年)等。其中一
部分,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亦陆续引进。在20世纪下半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夏志清和他的著作,在两岸甚至美国、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圈,都有相当的影响,具有一
定的地位和代表性。夏志清对中共的批判立场清楚明确,在著作里也并不遮掩。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他抑鲁迅扬张爱玲的批评,以处处类比西方经典的比较,反衬与相对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色,自然引发不同学术或实践立场者的响应与争议,除了20世纪60年代与普实克基于不同的治学立场、方法和意识型态,针对《中国现代小说史》展开的论战外,90年代亦有刘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转型》,间接地批评夏志清的文学史对中国左翼文学理解的限制。近年来,孙郁、陈思和、陈子善、王德威等,也曾对夏志清的文学批评,提出过一
些研究与看法。孙郁、陈子善和陈思和的主要观点的交集,是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批评方法和视野,作为改革开放后大陆文学批评的一种补充——毕竟,新中国建国以降的文学批评,尤其在十七年和“文革”阶段,确实有极左与教条化的部分历史事实,80年代后,需要引入另一种西化参照和不同方法的视角,从辨证的角度上,不完全没有健康与过渡的功能。而王德威与夏志清一样出身外文系统,同站在西方自由菁英和普世价值的立场,以世故精致、文学大同来理解夏志清,也不乏没有为某种文学场域的话语权的护卫意义。
而在两岸一片去中心与后现代的新历史条件下,重读夏志清和他的文学批评,吕正惠曾对争议中的细节,开展了伦理关注。他曾在《战后台湾小说批评的起点——夏氏兄弟与颜元叔》(收录于吕正惠《台湾文学研究自省录,2014》)一文中说:“跟夏济安相比,夏志清比较没有强烈的‘历史感性’,比较没有身处于‘社会变迁’中的那种‘切肤之感’。他在论中国现代小说家时,虽然‘理性’上知道他们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但夏志清却以‘客观’的立场去看他们小说中的文化与道德问题。”吕正惠想强调的是,不能过多地以西方的经典作品和价值取向,来参照与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及其优劣,各个国家、民族文学都有其自身的本土特性,和他们企图要响应与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批评家跟研究对象的关系,或许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客观”,或者说,排除自身主观/主体性上的紧张。
斯人已逝,更丰富化地清理与反思夏志清,和他的现代文学批评的时机已经来到。当我较完整地搜集与阅读夏志清一生的文学批评著作后,我注意到前述各大家对夏志清和他的文学批评的理解,仍多集中在他1961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但更有意思的是,夏志清在70年代以降,开始在许多的批评中,反省了他早年诸多批评观与实践,有些部分,扩充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表达了对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感时忧国”的同情,同时,对台湾文学一些代表作家,如余光中、琦君、白先勇等,也有一些虽然不无保守,但仍然可谓之细腻敏感的见识(甚至有些言外之音,在今天看来可能更具价值)。在具有总论性质的批评文章中,亦曾对包括黄春明、宋泽莱等台湾乡土文学的作品给予应有的肯定,甚至可以说,相当程度地修正与节制了他早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西化菁英为上、过于去社会与历史化的参照方法与史观。因此,本文主要想重新疏理与脉络化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后的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重构70年代以来,夏志清逐步调整与展开的批评环节与视野,以让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夏志清,和他为中国现代文学所作出的历史“基础”工作。

1953年摄于耶鲁大学魯魯
二
《中国现代小说史》阶段的夏志清,曾受F.R.李维斯《伟大的传统》与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等批评观的影响,在李维斯的信念里:“所谓小说大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但要如何生产出这种艺术与生活的“潜能”?李维斯在上书中,谈到简·奥斯汀,除了作家个人的才能,他更为看重的是作家跟传统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关系,李维斯说:“奥斯汀本是博览群书之人,举凡有益,便吸纳不拒……她本身就是‘个人才能’与传统关系的绝佳典范。假使她所师承的影响没有包含某种可以担当传统之名的东西,她便不可能发现自己,找到真正的方向;但她与传统的关系却是创造性的。”这种接近中国古代的“正变”史观,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夏志清的关键起点。

夏济安(左)夏志清兄弟
在现代文学诠释与分析作品的方法上,夏志清非常重视作品在传统同类型主题及文学史间的排比,但早期的夏文背后的文学传统与典律,确实主要常以西方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经典为参照和标准,因此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他自然会省略作家作品的在地历史与社会,更快地上升到普世性并加以批判。所以,夏文特别看重有深刻性、人间永恒的矛盾和冲突的细节,主张好的作品应该超越作者个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传达出具有道德意味的内涵等。类似的批评信念和实践,运用在比较好的总论或作品的分析时,别有一种视野宽广的智慧风貌。其优点处,我们日后挪用作参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例如,在《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收录于《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一文中,夏志清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作家的展望,从不逾越中国的范畴……以为西方国家或苏联的思想、制度,也许能挽救日渐式微的中国。假使他们能独具慧眼,以无比的勇气,把中国的困蹇,喻为现代人的病态,则他们的作品,或许能在现代文学的主流中占一席位。但他们不敢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把他们改善中国民生、重建人的尊严的希望完全打破了,这种‘姑息’的心理,慢慢变质,流为一种嫌狭窄的爱国主义。”此个说法,虽然欠缺对晚清以降的乡土中国和历史,之所以会日渐走向革命的理解,对现代作家和历史的阶段性成就和发展,也期望的过于急切,但既然是普世性话语,如果放在今天世俗化、民族主义式的中国热之下,作为一种对两岸目前及未来的作家眼界和实践的反省,仍然不失为一种带有责任感的呼吁。
所以,夏志清在早年批评上比较明显的限制,恐怕不能完全从他去历史与社会化、重视普世性的角度来批评,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批评他也是一种外于夏志清的抽象立场,更何况文学确实该有一定的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式的通感与理解,也不可能不应该完全排除普世性。问题在于夏志清文学批评观中的普世价值究竟是什么?我以为,夏早年比较少思考到文学和文学批评工作中真善美的层次和综合的考虑。夏志清早年文学批评的后设标准,极看重真和美,他对鲁迅的许多批评、对张爱玲的过多赞扬、对共产党的不以为然、对左翼作家欠缺同情的理解,在本质上,都跟这些理想的原型设想有关。他对“真”的追求,带有明显的个人性,因为要求作家“个人”的真诚,他对左翼作家和相关作品,包括鲁迅晚期的作品和杂文,便以为过于教条和简化,例如在《中国现代小说史》谈晚期鲁迅时,夏说:“一九二九年他皈依共产主义以后,变成文坛领袖,得到广大读者群的拥戴。他很难再保持他写最佳小说所必须的那种诚实态度而不暴露自己新政治立场的浅薄。为了政治意识的一贯,鲁迅只好让自己的感情枯竭。”在这里,夏志清关键重视“真”、他所谓的“诚实”——在他的文学思维逻辑中,这些概念的内涵,应该跟深刻与复杂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如果有了一定的政治立场,文学在“真”的意义上就浅薄了、情感就枯竭了,从他自身的逻辑上来推演并没有错,但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如此成熟且敏感的作家,会宁愿暂时选择让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简化(逻辑的意义上)?这样的“个人”和“真”的内涵,夏志清并没有进一步以他长于深入的才能来加以再辩护。当夏高举“真”为标准时,并没有综合思考到其“善”的作用问题,用孟子的说法,“善”乃是“有不忍人之心”,有时候运用在文学上,是不惜简单化自我的文艺世界,也要将可能影响他人/读者的综合作用考虑进去,如此,我们才能理解,鲁迅晚期选择杂文书写而非小说的意义,选择时而面向普罗而非绝对菁英化的立场,也才能更贴切地解释,即使在20年代的《药》中,鲁迅最终要给死去的孩子的坟上多加一个花圈的秘密情感,这种情感并非从逻辑意义上的浅薄与枯竭。
类似的限制也发生在夏志清对丁玲作品的评价上,夏志清批评丁玲时说:“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过于简化的公式信仰,使他们的头脑陷于抽象的概念,而对人类生存的具体存在现象,不能发生很大的兴趣。”夏所批评的这样的现象,确实不能说没有,但与其说丁玲的写作失误也是在于抽象或简单化,不如说,延安时期的丁玲,所面对与书写的某些人物,就是单纯且善良的,她们的转折因此也不若知识分子那么自苦,甚至产生了自苦下的无力与软弱,例如《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慰安妇贞贞,就是简单无惧,某种意义上更令人怜惜——已经失去到一无所有,也没有什么不能从头开始了,因此,知识分子和乡土社会中的保守和道德都无法再摧残或干扰她,她有生命力再往前走,并且能在革命工作的学习里,争取更大的成长。这样的书写本身,就是作者抑制了知识分子“个人”的偏好,而将真善美的内涵扩大化理解与实践下的综合产物。所以,问题还不在于夏志清没有阶级与左翼视野(他本来就不是这种立场),而是即使是从普世的理想,夏的一些论述恐怕仍然需要再周延一些。
三
然而,70年代的夏志清,也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反省。这个阶段他在台湾出了四本评论集:《爱情·社会·小说》(1970年)、《文学的前途》(1974年)、《人的文学》(1977年)和《新文学的传统》(1979年),80年代以后的选集也多以70年代为基础,1978年,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正式出了中译本,可以说,70年代才是他文学评论的高峰与成熟期。
就批评观来说,首先,夏志清开始检讨过去唯西方是尚的评论标准,对中国现代文学跟旧社会的关系,也比较有同情的理解。在台湾版的传记文学出版社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的《原作者序》(1978年)中,夏志清不无感慨地作了这样的反省与表述:
本书撰写期间,我总觉得“同情”“讽刺”兼重的中国现代小说不够伟大;它处理人世道德问题比较粗鲁,也状不出多少人的精神面貌来。但现在想想,拿富有宗教意义的西方名著尺度来衡量现代中国文学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必要的。到今天西方文明也已变了质,今日的西方文艺也说不上有什么“伟大”。但在深受西方影响的全世界自由地区内,人民生活的确已改善不少,社会制度也比较合理;假如大多数人生活幸福,而大艺术家因之难产,我觉得这并没有多少遗憾。
在这里,夏志清明白地指出,以西方菁英的尺度为批评标准的不公平,甚至上升到对西方文明质疑的见识。同时,过去的夏志清,在引述西方文学为标准看待中国现代文学时,目的多在突显中国现代文学的缺点或限制,但在70年代后的诸多批评里,夏志清更加自觉地意识到,在这样的方法参照下,中国现代文学跟中国传统联系下所能产生的相对特质,恰恰是有了中国传统(无论是古典传统或其衍生出来的封建传统),中国现代文学才真正得以有不同于外国文学的特殊性,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下,中国现代文学的优点与缺点,能够提供给世界文学以滋养。在《爱情.社会.小说》中的同名论文《爱情·社会·小说》(1970年)中,夏志清曾这样说:“不久以后,我们生活方式受美国影响太深,可能会全盘美化,那时候的现实可能同样有趣,但是我们的小说家不能再观察到礼教社会的特性,和在礼教社会下培养的处世方式和待人接物的种种特点,他们在世界文学上对人性观察这方面也少有独特的贡献了。”夏此言似乎也成为一种预言了。

1963年,夏志清(前排)与后排左起:白先勇、鲍凤志、陈若曦、欧阳子合影
另一方面,夏志清对于“文学”、艺术,跟思想、内容的关系,也有进一步的反省。过去,本文前面已述,夏志清非常看重作家作品“个人”式的“真”和“美”,过高抬举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念,罪恶、自私,黑暗如恶之华般的细节,甚至人世间一切负面的情感与状态,都在美学的对象化中,视它们为只能继续如此的悲观和虚无,仿佛创作的目的,最终只在成就艺术和人性上的终极自由,但“善”的向度始终未能充分被同等地理解与展开。但显然70年代的夏志清也慢慢认清,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限制,尤有甚者,质疑起“五四”以降“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二元对立的简单化,他似乎有意在7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把“文学”再重新扩大化,其方法之一,是要再一次跟中国古典传统勾连,在《人的文学》(1976年)中,夏志清曾这样说:“汉代以来,真有好多部具有思想性、学术性的精心巨著,研究文学的人因为它们不是‘文学’,而不加理会,真是作茧自缚,剥夺了自己对中国文化有更精深了解的机会。”在这里,“文学”跟传统、思想与文化,再度被联系在一起考虑。同时,作为“文学”材料的现实,夏志清也开始能接受,书写他们的史料价值和社会责任。也是在这个认识的前提下,即使是“五四”左翼作家初阶段难免较为粗糙的写作技术,对中国旧思想、旧道德、旧社会的抨击和揭露,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内容价值。是以我们才能历史化地理解,他在《人的文学》中对艾略特这段话的引用意义:“一部作品是否为文学诚然全靠文学标准来决定,一部作品的‘伟大’与否则不能单靠文学标准来决定的”,在“文学”标准之外,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及善的作用),已成为夏志清70年代以降,品评作品时综合判断的方法与环节。
当然,作品的思想水平,乃是一部作品能否“伟大”的重要标准,“文学”绝对不只是艺术与技术的手法,但70年代后,夏志清理解中的思想内容又是什么?虽然他对“感时忧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已能更多同情,但窄化下的普世价值,仍是支配着夏志清思维模式中的关键信念。我认为,就整体上来说,即使是70年代后的夏志清,还是比较强调作家应该从忠于自己的感性出发,表达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他仍然对中国作家、作品以及具体的社会和历史的关系,没有更深的知性上的兴趣,但比起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阶段,他已经对社会和历史多了从感情上的认同,落实在他谈论思想的内容问题时,夏志清在《文学·思想·智能》(收录于《爱情·社会·小说》)中,联系上的是普世价值中的“人类文明的传统和习性”的说法:
创作所运用的思想,虽和纯理智的思想不是一回事,但决定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优劣,纯理智的思想仍是一个基本考虑。这种考虑不是以哲学的眼光去鉴别其思想的真伪,而是以人类文明的传统和习性去鉴别其思想的成熟或幼稚。
夏志清这样的理解,是站在人文主义者的立场,这时候批评家本身的文史哲的会通能力和格局,将是决定他能否作出相对准确评价的关键,这其实相当不容易,因为参照的标准或说范畴太大,很容易在品评过程中失之粗糙,甚至易流于抽象。但他在这方面的实际批评实践,仍有许多值得清理的地方,尤其,整合他70年代以来的相关批评观的扩充,有一些很少被前人学者充分领悟其细腻的部分,值得我们再看重。
首先,70年以降,夏志清选择品评的对象、材料大致分两类:一类是跟他一样有留美读书、治学或有一定往来、了解的外省籍知识分子或作家,除了已经广被人所熟知的张爱玲、钱钟书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吴鲁芹、林以亮、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琦君、陈世骧、卢飞白、何怀硕等。另一类则是台湾70年代的本土与乡土代表作家的总论和印象点评,如陈映真、黄春明、宋泽莱等。
就前者而言,夏志清因为比较欣赏文人型的作家(夏在谈到吴鲁芹和他欣赏的作家英美作家的类型时,曾说他喜欢的其实都是读书多,有批评头脑的文人型作家,这也可以从他特别欣赏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来理解。可参见夏志清《鸡窗集》),他所选择评点的对象,多为才学突出,同时因缘际会有一些往来的人士,因而旁采故实,体兼说部时也亲切,这是夏志清的文评能写的流畅自然的原因之一。举例来说,他谈余光中的核心观点,主要落实在余光中作品的中国乡愁,有点为“文化中国”的意识辩护,至今已广为学术界熟悉。60年代中到70年代中,中国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国民党在台湾亦积极继续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因此余光中和许多同世代或更年轻的外省作家,以“文化中国”式的伤感书写,在怀国与乡愁间,将典律上溯中国古典传统,也不能说没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也是冷战结构下的文化生产的必然结果。但更有意味的是,夏志清也看出了这种书写之于外省作家的整体艺术特质,在《余光中:怀国与乡愁的延续》(1976年)一文(收录于《人的文学》)中,他点评说:“这些散文词藻华美,韵律动人,把回忆、描述、冥想,巧妙地编织成章。”怀国与乡愁等主题,本来就极为切身,但却需要多以回忆、冥想、巧妙编织等技术来成章,处处联系上古诗来自我安慰与安顿,夏反而间接地不小心看出此类作品的限制。
因此,在夏志清70年代评论的台湾外省作家中,他敏锐地看出他们最好的特质,我以为并不是过去广被众学人所熟知的“文化中国”式的视野或感性,尽管他在70年代以降的批评观,开始意识到中国古典传统与视野的重要,但就整合他的批评实践来说,他对琦君的评论可能更为到位且有长远价值。夏志清为她提出了一个“传统型感性”的概念,并将谱系上溯到萧红的《呼兰河传》,同时,他虽然也将琦君跟李后主、李清照的传统联系在一起,但重点并不在于突出“文化中国”,而在于突出真情实感,有“文化中国”不一定有真情实感,但从真情实感出发,最终若能导向“文化中国”,那样的中国的内涵才可能具体且厚实,并有传统下的创造性推进。琦君何以能如此,夏志清以她的散文作品《髻》为例,认为如果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可以传世,《髻》更应该传世,相比许多外省籍小说家、作家幻想中的“文化中国”,或怀念昔日在大陆的光辉岁月(如白先勇的一些作品),琦君的作品,从生活出发,不但事实与形象细节饱满,以《髻》写女人与女人间从怨恨、冷淡到包容,自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善意,这种写法尤其适合散文这种文类。夏志清说:“假如我们觉得‘亲情、友情、爱情’以及对于祖国、故乡思念之情是值得珍贵的,直抒真情的散文永远会有人写,也永远延续了我国‘传统型感性’的活力”(可参见《琦君的散文》,收录于《人的文学》),此言并不过时。
另一方面,70年代的夏志清也仍然没有改变批判中共的立场,所以在评陈若曦的“文革”小说时,他不免处处流露对中共建国及其历史存在合理性的怀疑。陈若曦和她当年的先生段世尧,在1966年选择“回归”祖国时,确实是对社会主义抱持着真诚的理想,而她的“文革”小说,虽然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下的一些人物的残酷生活与命运,但也保留且反省了一些大陆在社会主义实践下,海归派学人在大陆受到特殊待遇的旁观限制,并非全然外在于中国社会说风凉。而在新中国建国的历史上,也确实仍有部分如茹志鹃、周立波、柳青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式的优秀作品,以夏志清一向能进入具体文学作品的感性能力,如果不是这样的立场,和当年的冷战氛围与条件,如果能参照更多的材料,或许对中共治理下的中国的想法和文学批评,会有更具层次与通达的见识。远比一面以负面批判,来论述新中国建国以降到70年代的各阶段历史状态,当中的概括性仍有牵强。

80年代沈从文(中)访美,与夏志清(右)等合影

1979年,钱钟书(右)访问哥伦比亚大学与夏志清合影
因此,如果暂不考虑意识形态,夏志清在评陈若曦时,以传记文学的方法评点仍是可观的。陈是地道的台湾本省女性,出身基层,吃苦耐劳,长于朴实地观察人事物,夏志清事实上非常能欣赏这些现实性的书写,这种能力也展现在他70年代对台湾乡土小说家的品评上。
《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1976年),是夏志清综合阅读齐邦缓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1949-1974》(英文版)、刘绍铭编《台湾短篇小说选:1960-1970》(英文版),以及他在1971年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英文版)的论文,该文印象点评了包括陈映真、于梨华、杨青矗、陈若曦、张系国、七等生、黄春明、白先勇等作品的作品,以及战后台湾小说家的相关特质。非常有意思的是,即使不从左翼的角度,夏志清在这批作家中,特别肯定乡土小说家黄春明,也将他的作品《看海的日子》,跟中国传统《诗经》以降的平民文学的典律联系起来,甚至,大为欣赏主人公妓女白梅的崇高的品格,和作品的那种乡土与光明的现实主义倾向。他曾在《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收录于《新文学的传统》)中这样说:
在堕胎已在世界各地成为合法的今天,能够读到一个以如此庄严穆肃的笔触,去描写为了生孩子而性交、为了自我救赎而分娩的故事,实在是一种——容我再用一次成语——感人肺腑的经验。……黄春明的信念与福克纳相同,福氏相信作家的职责是教人想起人类昔日的光荣——勇气、荣誉、希望、自信心、骄傲、同情心、慈悲心、牺牲精神——藉以鼓励人心,使人增加忍受苦难的能力。
在这里,夏志清虽然仍援引西方文学大家福克纳作为参照,但他似乎更多地靠近了台湾实际乡土经验与感性——一种中国传统里为母则强的力量。其实,如果就文学求“真”的目的来说,《看海的日子》里,长期身为妓女仍能保持高尚品性与希望的白梅,现实度令人怀疑,但似乎此阶段的夏志清,不但愿意相信这样的“现实”,还可以认同黄春明创造的“善”的信念。如果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终极理想之一,是指出光明、给出希望、承担个人之外更大的责任,夏志清似乎在不自觉间,发挥他具体出入文学的敏感度,靠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尽管他必然不会使用这个概念)。所以他才能进一步在《正经危坐读小说》(收录于《新文学的传统》)中说:“乡土文学假如专写贫苦社会的丑恶面,就一无足观了。只有在看似绝望的生活里,找到了希望,找到了相濡以沫的爱,这才是真正‘人的文学’。”
是以,夏志清最终不见得不能更靠近他的祖国,在60年代末,他曾在《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收入《文学的前途》)评述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时,肯定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的成熟乃是在于:“他忘不了祖国,他的命运已和中国的命运戚戚有关。”而80年代初,夏在《时代与真实——杂谈台湾小说》(收入《夏志清文学评论集》)谈台湾作家张系国与乡土文学时,也明确地说过:“我不愿放弃中国是一个整体的理想。对我来说,‘乡土’应包括中国所有的区域。……中国现代的文学既然一直都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我们如果满足于仅仅改善台湾穷人的生活,而忘了大陆上的亿万同胞更加的穷苦,丝毫享受不到台湾人民大致都享有的尊严和自由,那我们就背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这话当然仍是从自由主义菁英立场出发,但是,当中也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职责。只要能具体地响应与贴近文学作品,有可能节制先验的意识型态并且接近更复杂的历史现实。

夏志清在书房
四
夏志清一生致力于现代文学批评,他的博雅和才能,许多部分至今仍值得肯定,是我们继续发展现当代文学、小说批评的一种重要“基础”(吕正惠语)。他对“文学”、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与理解,事实上早已远远超过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他的中国历史感性,也并非未曾发挥。在最好的状况下,他对其他非文学的媒介,也能有宽广的类推与理解能力——1977年,在评述山水画家何怀硕的散文《域外邮稿》时,他就深切地认同何怀硕对社会和政治的关心,肯定他不愿再仿拟古画里的山水、花卉、仕女化的新实践路线,认同何怀硕企图作为一种现代中国人的努力。
尤有甚者,夏志清藉评述何怀硕(《何怀硕的襟怀》——《域外邮稿》序,收入《谈文艺·忆师友——夏志清自选集》),想起了T.S.艾略特的一段话,或许,这可以作为一种综合知识、情感与意志的总括——夏志清作为一代批评家所曾到达的自省与自觉的高度:
艾略特虽然有意写达到音乐境况的“纯诗”,可喜的是他的诗并不纯,其中包涵了潜藏内心深处的欲望和回忆。一开头,他也想写“纯”诗评,写到后来也愈来愈不纯,实在发现诗的了解和评判同诗人的时代和社会关系太大了。他创办criterion季刊后,更是每期都写有关当时西方政治、社会变动的社会。……他也写过几本讨论宗教、社会、文化的小册子。这些书想来读者也愈来愈少,艾略特传世的作品无疑是他的诗、诗剧和诗评。但艾略特这样一开头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而抱着诗人写诗以外不问世事的态度,后来变得这样入世,极端关心英国和欧洲文化的前途,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清醒而克己时的夏志清和他的文学批评,难道不也是留给中国人的一份遗产吗?
责任编辑/胡仰曦
- 传记文学的其它文章
- 伯驾
- 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与勤工俭学蔡元培的留欧故事之留法篇(七)
- 嘉约翰
- 大洋风来雨杏花
——基督教传教士医师群英传 - 卫道忧时启迪今人的学问家
- ——缅怀恩师 夏志清先生">永远天真的"老顽童"
——缅怀恩师 夏志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