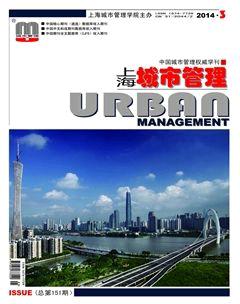时光的赠礼:跟随城市一同典藏的人文记忆
张炜等
导读:从城市文明进程的角度去审视,城市人文记忆是一种资源,而且是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当今社会有一种共识,即城市人文精神作为软实力,业已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并发挥着越来越强大的作用,而城市人文精神范畴内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城市的人文记忆。
一
叶:今天对话的内容,在我的文档里已存放多日了,此时钩沉面世,源自我见到多家媒体报道的一则新闻:上海市民邓平安数年间奔走于申城的老弄堂,收集了5000多块形状各异的老砖头。他这么做的缘由是因为心存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把这些旧砖砌成一面特别的墙,让后人能从某个侧面了解上海城市的发展。
有人认为邓平安的这种个人行为,是一种升华了的公民责任,还有人说邓平安是在以一己之力,顽强地坚守着城市人文记忆的堡垒。你对此有何见解?
张:虽然不是普世共鸣,但我个人很同意上述的说法。从城市文明进程的角度去审视,城市人文记忆是一种资源,而且是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当今社会有一种共识,即城市人文精神作为软实力,业已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并发挥着越来越强大的作用,而城市人文精神范畴内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城市的人文记忆。
再者,常言道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成就一项公益事业或实现一个公益愿望,光有政府的行政作为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公众觉悟的基础上,即有千万个邓平安、张平安、李平安的积极参与,方能事半功倍。说到这儿,有一点我想更正,上海坚守城市人文记忆堡垒的人不在少数,社会各界都有不少人默默无闻、但却是任劳任怨地从事着城市人文记忆的薪火传承工作。比如,上海青浦有个福寿园人文纪念馆,是全国第一家由企业申办成功的人文纪念馆,迄今已历十载春秋,它的主题就是“珍藏城市记忆”。纪念馆展示了百位名人的近千件实物史料,包括历史相册、回忆文章、著述手迹、视频资料及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学习、工作用品等。
叶:十年前,人民日报的记者李舫写了一篇《不要让城市失去记忆》的文章,其中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城市不仅仅是单体建筑的简单集合,不仅仅意味着高楼大厦、立交桥、高架路,更是一股从远古吹向未来的心灵之风,是一个民族赓续绵延的记忆载体,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生态环境、深厚的文化内涵、优秀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人文景观,都是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保存城市的记忆,保护历史的延续性,保留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
我个人认为这段话应该编入教科书,特别是要编入各级干部培训班的教材读物中,因为中国大陆在城市化进程中,毁弃城市人文记忆载体的案例不胜枚举,而这种毁弃行为,很多是在城市决策者的行政命令下进行的。如果把“市民拾砖”和“毁掉文物”两种行为同时在城市文化的平台上去晒一晒,世人对此将作何理解?!后人又将作何历史评说?!
张:现在业内有专家把发掘和传承城市人文记忆的重要性概括为三点,即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历史具有资源性的文脉意义、对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具有认同性的独特意义、对于提升城市人文精神定位具有点睛性的形象意义。这是很值得我们在当今蓬勃发展的时代好好地加以慎思和推究的。
近些年来,城市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怪象,并在媒介的暗示或操纵下形成若干有违生存环境与诗意想象的文化事件,如早些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等恶搞、一夜成名的超女现象、关于“文坛子”的斯文扫尽之争等。这些事件在今天看来,其伴随的种种负面效应,就像灰屑飘落的城市雾霾一样,恋心剪影的性灵生活转化为对城市生活的苦闷拒绝与试图逃离。有人因此将关于城市的种种文化记忆的颠覆,喻之为“造成了城市文化意识形态的精神缺钙现象”。关于城市的记忆在这样的念头下,真的可以说是一种对人们向往的自由生活的痛苦纠缠了。
叶:把发掘和传承城市记忆提到这么一个理论高度,我倒是还没意识到,我只是觉得城市人文记忆是城市历史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高等级、高品味城市资源,而城市人文记忆又具有非具象性、稀缺性、脆弱性等特点,所以唤起人们的城市人文记忆,有助于增加市民对本源文化的自豪感,也有助于提升广大市民的向心力。
城市人文记忆在城市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性是举世公认的。当年梁思成先生保护日本京都和奈良两大古城的建言曾传为佳话——二战后期,美军将对中国境内的敌占区和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但在行动之前,美军先向梁思成先生咨询:哪些城市的古建筑应受到保护?梁递交了一张有明确保护标记的图纸,随后又说:还有两个城市也希望能得到保护,但这两个城市不在中国。美国人问:是哪两个城市?梁答曰:是日本的京都和奈良。梁思成这种不计民族恩怨的高风亮节,让在场的盟军将士甚为钦佩。因为有了梁思成的建议和嘱托,京都和奈良长达千年的城市记忆得以幸存。所以,直到今日,日本人都奉梁思成为两大古都的恩人。
张:人类文明的成果,需要人类的共同守望。梁思成先生的高风亮节诚然可嘉,但盟军体现人类良知大义的行为也感人至深,因为即便是在战争中,他们也不忘保护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成果,哪怕是敌对国的。我记得你以前在与邓伟志先生的对话中,也谈到一个类似的案例(叶:二战时美军不轰炸德国的科隆大教堂。),所以,这就再次验证了人类的文明成果和文化成就属于全人类。以此类推,城市人文记忆也属于整座城市乃至整个民族,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随意处置和毁弃城市的人文记忆,即便是藉开发或发展之名。
当年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的行为之所以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就是因为巴米扬佛像是人类的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你不能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或是意识形态的相异而人为地毁坏它。
叶:有一句流行词很精辟:当人类砍倒第一棵树的时候,文明开始了;而当人类砍倒最后一棵树的时候,文明结束了。因无知和愚昧导致的破环性开发,不是中国大陆独有,在别的国家也曾发生过。韩国首尔为了加速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曾填平了古城内的清溪川建高速公路,但后来人们觉得城市现代化建设固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可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却遭式微。两者相权取其重,2003年,首尔市政府毅然决定炸掉高速公路,重现清溪川古河道。这是恢复城市历史记忆的典型实例。endprint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每年有数以亿计平方米面积的钢筋水泥丛林矗立起来,但很多极富人文价值的历史遗迹却因此而消失了,这现象常使我想起了李煜的词: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张:不只是“朱颜改”,而是连“雕栏玉砌”也荡然无存了。半个世纪前,决策者不顾梁思成先生劝阻而拆毁北京古城墙,今天还有不少有识之士指责此种缺乏历史观的行为。但我不太理解,五十多年过去了,社会已大大地进步了,可同样的行为,在同样的口号下,为什么仍在频发,比如襄樊古城的千年城墙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定海古城被夷为平地,等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所以,人文精神即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文明的核心,而城市的人文记忆,恰是城市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叶:把城市记忆这一无形资产转换为经营城市的宝贵财富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发展文化旅游业。我认为这一点上,意大利中部城市维罗纳堪称典范。实际上,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资源、抑或是知名度上,维罗纳都难以与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市比肩,但就因为莎士比亚的一出《罗密欧和朱丽叶》,使这座小城每年接待上百万的观光客,甚至还有不少情侣从世界各地专程赶到那儿去结婚。其实,游客在维罗纳驻足的景点,也就是27号小院里的朱丽叶铜像和朱丽叶阳台,别的一些如古代圆形剧场遗迹什么的,游客鲜有兴致。我去维罗纳的那一天,通往27号小院的街道上人流如涌,小院门口更是挤得水泄不通。当地人告诉我,即便是旅游淡季,来这儿的游客也是摩肩接踵。窃以为维罗纳把城市人文记忆这一无形资产,最大限度地转换成了经营城市的宝贵财富。
张:我记得你曾多次、多角度地举过“维罗纳”这个例子,反正不管你是刻意还是无意,我都觉得是一种吻合,因为只要冠以“人文”一词,就不能绕开意大利这个人文主义的发祥地。
不过,城市人文记忆是经营城市的宝贵财富,这可是个众所周知的道理。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被莎士比亚定格在了维罗纳,当地充分利用这一文化资源实属必然,因为莎翁这样世界级大文豪留下的财富,当然不可能任其失之交臂。即便是比沙翁低一档次、低二档次,甚至是低三、四档次的,也为世人争得不可开交。我曾在网上看到一张中国大陆各地争夺名人或历史人物故里的图表,不但曹雪芹故里有三个省参与竞争,就是貂蝉、花木兰也有三个省在争夺。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像西门庆、孙悟空这样的小说人物,亦有几个地区试图“占为己有”……
叶:这岂非几近浅薄无知了嘛?但名人或历史人物的故里之争并非中国独有,国外也屡见不鲜,比如现在世界上有9个城市在争夺荷马故里。我在雅典旅行时,就有人对我说荷马是雅典人。但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所知,荷马出生在小亚细亚是定论,而他生前也是居无定所。我臆测雅典人如是说,概因荷马被冠以“古希腊盲诗人”之缘故。
中国的名人和历史人物故里之争虽坠入无聊和荒唐,但有几点还是可以肯定的:首先是人们懂得了人文记忆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其次是可提升一方土地的名声和影响力;再次是注重潜在的经济效益和软实力;最后是故里之争还可以在争创历史文化名城上增加砝码,一旦成功,即可享受一些财政扶持或政策优惠之类的利益。这最后一点对部分城市管理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争到这么一个名份,可纳入到自己的政绩账册上。
张:所以,这就是一个悖论,争名人故里要死要活,对历史古迹却弃如敝屣。他们知道名人或历史人物对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性,因为这关乎GDP,但就是不明历史古迹对一座城市人文记忆的可贵性,就是不懂城市人文记忆对弘扬城市人文精神的不可或缺性。城市文化建设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所作所为却是南辕北辙,这是否属于口是心非,或是言行不一?!以文化论输赢,以文明比高低,以精神定成败,已是现代城市竞争的最终选择。
三
叶:我也姓叶,所以叫叶老师有些拗口,还是叫您本家大哥比较顺。您对保存和发掘城市人文记忆有何看法?
叶辛:你们今天这个对话的内容不但很有现实意义,也是我本人所感兴趣的,而且还与我目前从事的一些社会活动有关联。鉴于此,我先把话题扯开一点。
我许多年前写《蹉跎岁月》、《孽债》等作品时,是将自己的整个知青岁月融入到小说的写作中了,而且在写作中一直在思考关于人的担当、责任,以及正义感等人性的永恒意义。描绘上山下乡的生活苦痛、凄美爱情、未来憧憬,似乎都在回答这样一个事实:关于人的记忆就是应该突破芜杂与井然、困乱与念往的精神对峙,应该留住所有关于仁慈、智慧与希望的时光缪斯。
龙年的时候,我曾应媒体之邀,特意推荐了5本值得阅读的好书,分别是《路西法效应》、《复仇女神》、《裂舌》、《东山魁夷散文选》和《大自然的日历》。也许我是写小说的,我深深觉得,知识演进循从人的思想,所以阅读的某种意义,就是对人类珍贵记忆的一种酸甜苦辣的梳理,为的是让人们感受到,人类所感受到的不仅是视觉的、肉眼所看到的,还是心眼所看到的,而这当中最根本的、最沉得住气的就是人文记忆——患得患失的心路历程、超脱世俗的襟怀世界。
叶:您在保护和发掘城市人文记忆的社会活动中身体力行,是否源自您这些对城市人文精神和城市人文记忆的高度认识?
叶辛:我知道你这提问的所指,因为我也是创办上海知青博物馆的拥趸者,知青博物馆属于我们上海,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城市人文记忆。
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即意味着背叛。就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而言,我非常认同这句话。40多年前,上海有一百多万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奔赴祖国各地上山下乡,当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孩子卷入这一洪流中,这是全社会性质的一项大活动。今天,尽管对这段历史有见仁见智的说法,但一代城市青年人难以忘怀的青葱记忆,则是被镌刻于我们的城市历史中了。(叶:所以你小说大都取材于此,概因是知青岁月刻骨铭心的缘故吧?)是的,岁月虽然远去,记忆实难忘却。知青博物馆收藏的脱粒机、手扶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犁、镐、镰刀、坎土镘、割胶杯等各式农具,上山下乡通知书和数以万计的老照片,亲历者见了谁不感慨万千?!谁不浮想联翩?!endprint
这些藏品都是老知青们无偿捐赠的,很多都是他们珍藏了40年的心爱之物,而且每一件藏品的背后都有着一段感人的故事。这样的行为说明了什么?一言以蔽之,为了守护城市人文记忆!为了弘扬城市人文精神!
张:您刚才说到保存和发掘身处城市人文记忆还与您目前从事的一些社会活动有关联,这是否有具体指代?
叶辛:既然说到这个话题,我就赘言几句。
我说的这事,与你刚才提到的福寿园人文纪念馆有关。今年清明节期间,《百姓家史》系列丛书第一套6本书出版了。丛书的始作俑者,就是青浦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他们在两年前的清明前夕发起的“替亲人出书,为百姓立传”的文稿征集活动。毋庸置疑,他们这是做了一件发掘城市人文记忆的好事,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首发仪式上我曾说过,《百姓家史》把原先以上海名人和社会精英为主体的人文纪念延伸、扩展为面向普通人的、全民性的人文纪念。它让每个生命都能像书一样流传千古,让民间的上海故事、海派文化能通过书本继续传承。
我有幸为此书的出版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与沈颙、叶永烈、赵长天等参与了编审工作,可惜赵长天去世了,没能看到此书的出版。(叶:我记得您还有过一场专题讲座,为《百姓家史》的作者传授写作回忆文章的技艺。)那是去年在上海徐汇区图书馆,来的人不少,我也没料到人们对此是如此踊跃。我想,用文字留下对亲人的记忆,或许是大多数人的心意所在。
叶:我有个同学是美籍华人,她是原上海工部局掌门人潘宗周的后裔,也是原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潘世兹的侄孙女,她写了一篇纪念她祖父潘世琪的文章(附于文后),就内容而言,既是城市人文记忆,亦属典型的百姓家史。我替她向你投稿,争取上第二套《百姓家史》。
叶辛:欢迎欢迎。
[附录]
祖父与故宅往事点滴
潘耀华
我祖父潘世琪是是潘宗周的长子,年轻时留学美国,毕业于纽约大学。回国后,娶梁秀萱(我祖母)为妻。梁家比我们潘家富有,梁大小姐又是唯一的女儿,在娘家受万般宠爱,所以陪嫁财物足以让新婚夫妇一世享用不尽。据老一辈的人说,祖母有4个陪嫁丫环,印度巡捕站岗并一路护送嫁妆,其盛况曾是十里洋场的茶余饭后的话题。婚后,他们仍与我曾祖父同住于蒲石路666号(现为长乐路680号,已为中日厚诚口腔医院)的“宝礼堂”旧宅内。我父亲与他的兄弟姐妹们也相继出生和成长于那里。我曾祖父退休时,英国人念旧,所以就推荐我祖父潘世琪为工部局的副总办。1949年后,我祖父母寓居淮海中路2038号,是栋西班牙式的洋房,我出生在该所房子里,一直住到1966年。我对宝礼堂的认知,来自我家的3个仆人(都是从宝礼堂中带来的),因为闲来无事时,她们会嗑着瓜子,喝着茶,聊蒲石路旧宅中许多过去的人与事。对于她们来说,宝礼堂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她们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大部分岁月。
我祖母51岁就去世了(那时我只有10个月大),我祖父哀痛万分,因对亡妻情深意重,所以从没有过一丝续弦的念头。在以后的岁月里,祖父把关爱大都倾注于我的身上——关心我的饮食起居,给我吃好好穿好用,即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祖父仍想方设法搞到牛奶和鸡蛋等给我吃。我身体有恙时,祖父从不带我去普通医院排队候诊,他宁可出高价带我去一个姓祝的医生那儿就诊。祝医生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私人诊所就位于淮海路上。祝医生诊所不远处就是老大昌西餐馆,每次看完病,征得医生的同意后,我祖父就会带我去老大昌买冰琪淋圣代给我吃,随后我们祖孙俩就在那里消磨半天,以致后来那里的营业员都认识我们了。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我祖父就会去淮海路上的襄阳公园,与一批和他有着相同背景的先生太太们闲聊,然后一起去饮茶吃午饭。他也常带我一起去,我是那群人中唯一的孩子。
1965年,我10岁。有天早上我的肠胃有些不适,祖父就带我去看病,完事后他要我自己回家,他说是要去淮海路买些点心。我下午放学回家后,家中人告诉我,祖父因心肌梗塞已被送去医院急救了。临走前,他或许有预感,叮嘱老仆人要照顾好我们姐弟3人,还特别叮咛说是要把我照顾好。下午5点多,我父亲从医院打来电话说我祖父因抢救无效而去世了。噩耗传来,我当时真有天塌的感觉。从我出生以来,我从未如此地伤心过,整晚睡不着觉,总希望这一切只是个恶梦,梦醒之后,祖父又会笑咪咪地坐在他的沙发上给我念《新民晚报》上的故事连载,又会高兴地笑着看我品学兼优的奖状……古语云:人七十,古来稀。我祖父离世时正好70岁,但以今日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很年轻。可后来家人还是为他去世得及时而庆幸,因为一年以后发生的那场浩劫,以他的经历和心气,能顶住降临到他身上的屈辱和苦难吗?
1966年,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搬到兴国路的一幢房里,一家六口人(我们一家5口,加上1位宝礼堂硕果仅存的老仆人)挤在33平方米的两间屋里,虽说和以前不能同日而语,但父母自我安慰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984年,我和祖父当年一样赴美留学,完成学业后在美结婚,随后相夫教女,转眼30年过去了。现在每次回乡省亲,我都会去淮海中路走走,去看一下2038号——那幢留给我美好童年记忆的故居,并幻想着祖父从里面出来,牵着我的手,一块去西餐馆吃午饭。但今日现于我眼前的那幢曾经典雅的洋房已不复当年的面貌,而且外面还加了一道围墙。而长乐路680号的宝礼堂,尽管耳熟能详,但我只能在计程车经过时朝它惊鸿一瞥……
说明:
1.宝礼堂位于旧上海法租界蒲石路中段,今长乐路680号,主人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工部局总办、广东人潘宗周(字明训)。这幢豪宅名“宝礼堂”,一度曾是中国藏书界的“重镇”——拥有100多部宋元古版藏书。
“宝礼堂”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建筑风格属于新古典主义建筑,外形庄重气派。1949年,潘家主人把“宝礼堂”捐献给了国家,此后一直是上海邮电职工医院一部分,现改为中日合资上海厚诚口腔医院。
2.潘世兹(1906~1992)潘宗周之子,广东南海人,现代藏书家、学者。193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学位。曾任圣约翰大学历史政治系主任、教导长、代理校长。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图书馆馆长。
1939年潘宗周去世后,潘世兹继承了全部藏书,其中有宋元本110余部,1088册。经张元济、徐森玉等版本目录学家鉴定,均为精品。其中宋刊孤本《礼记正义》,原为袁克文藏品,潘以10万两银子购得,遂将其藏书处命名为“宝礼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世兹唯恐藏书落入日寇之手,故联系英国驻华机构的朋友,用一艘军舰将藏书运抵香港,存入汇丰银行。1951年,美国、日本等外国收藏家曾开价50万美元购买藏书,潘不为所动。随后亲自致书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将“宝礼堂”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郑振铎着手安排在香港银行任职的徐伯郊先生多方奔走,将这批藏书安然运回上海,再由政务院特批火车专列运至北京,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
责任编辑:施 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