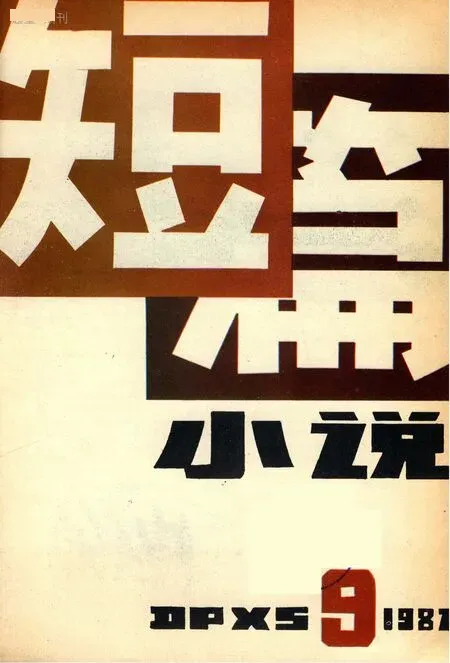福克纳小说中的神话原型探析
张 颖
福克纳小说中的神话原型探析
张 颖
一、引 言
威廉·卡斯伯特·福克纳出生于1897年,卒于1962年,是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在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福克纳公开出版了19部长篇小说和百余部短篇小说,在这些长短篇小说中,作者大都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在了约克纳帕塔法县,讲述其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几代人的家庭生活,被称为 “约克纳帕塔法世系”[1],在 “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有600余位有姓名的人物贯穿其中。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福克纳曾说:“我发现我那邮票大小的故土很值得书写,而且无论我能活多久,我也讲述不完她的故事,对我而言故乡就是支撑创作的基石,虽然很小,但一旦抽离,创作的世界便会崩塌。”[2]
1925年,福克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士兵的报酬》出版,正式拉开了福克纳的文学创作之幕,两年后,福克纳创作了又一部长篇小说 《蚁群》并大获成功。在两部康普生家族小说的初探后,福克纳很快创作出版了小说 《黄昏》,即后来鼎鼎大名的 《喧哗与骚动》。在此之后,福克纳还创作了 《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八月之光》《野棕榈》 《去吧,摩西》 《寓言》 《掠夺者》等著名文学作品。[3]1949年,福克纳在与海明威、加缪、斯坦贝克等著名作家的角逐中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用奖金设立了 “福克纳小说奖”以鼓励、资助年轻作家。此外,福克纳还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法国荣誉团勋章、普利策小说奖等至高荣誉。作为美国文学史上最为著名的小说家之一,福克纳不仅拥有广泛的读者,而且在文艺评论界也饱受关注与赞誉,有评论者曾言,对于福克纳的研究堪称近20年间英美文学研究中之显学。在国内,对于福克纳的研究主要从现代主义、宗教神学、美国南方历史文化、种族问题、女性主义等方面切入,同时福克纳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及对比研究也日渐兴盛。可以说,福克纳其人其作在国内的译介逐渐全面、深入,对于其人的研究视野也更加开阔,对于其作的研究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读包括 《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在内的福克纳代表作品,结合西方宗教文化背景,探析福克纳小说中的 “基督”“夏娃”“漂泊”等神话原型。
二、福克纳小说中的神话原型
“原型”作为文学研究术语最早出自荣格的理论,即为原始的模型,指文艺创作中塑造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的依据,是在神话、宗教、梦境、文学中不断重复出现的意象,这一意象是广义而言的,既可以是一个人物、一个物件,也可以是一个细节描述或一个剧情模式等。荣格认为这种意象源自人类的集体潜意识,能够引发读者或观众潜意识中的种族记忆和原始经验,使之产生强烈的非理性情感。[4]在文学作品中,“原型”可依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为多种类别,就福克纳的长篇小说创作而言,其中神话原型尤为突出,这些神话原型主要出现在 “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之中,以 《沙多里斯》为开端,“斯诺普斯三部曲”为句点,集中体现于 《喧哗与骚动》中的 “基督”原型和 “夏娃”原型及 《我弥留之际》中的 “漂泊”原型。
(一)福克纳小说中的神话原型之 “基督”
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基督”这一原型大都指代沉重的责任、巨大的痛苦和沉默的承受,在福克纳笔下也不例外,但不同于 《圣经》中的是基督受难后的结局。在 《圣经》中,基督受难后复活,带来了无尽的感召与希望;而在福克纳笔下的 “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受难的基督代表着整个家族的不幸,这种不幸是不可逆转的,“约克纳帕塔法”中的基督没有复活。
在福克纳的 《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寓言》等小说中,“基督”原型均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存在,其中 《喧哗与骚动》无疑是其中的代表。通观 《喧哗与骚动》的文本框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玄妙,福克纳以倒叙的方式展现了 “基督”受难的过程。此中的 “基督”是指以 《圣经》基督为原型的人物形象,即为小说中的班吉,班吉的超能力与年龄较为直白地指出这一形象对基督的隐喻。小说中的故事也是以班吉受难开始的,在第三章标题中的 “4月6日”即为基督受难日的隐喻。在这一部分中,卑鄙的杰生将整个家族逼上绝境,阉割白痴弟弟班吉、阻止凯蒂与家人的往来、处处刁难小昆丁等,杰生的作为使象征着基督的班吉受难,使整个家族面临灾难。按故事发展顺序来看,基督受难后的故事发生在小说第一章中,其中 “4月7日”和 “4月8日”分别隐喻复活节前夜和复活节,在这个守斋和哀伤的日子中,小说通过班吉的眼睛展现了家族受难后的悲剧,其中凯蒂失去贞洁为其中之核心。在复活节之后,《圣经》中的基督复活了,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喧哗与骚动》中的家族并没有迎来复活,获得重生。在第二章中,“6月2日”是圣体节,即再次庆祝基督复活的隐喻,在这一天,象征着康普生家族之希望的昆丁自杀了,打破了整个家族复活的希望,“有复活的人,也不是在康普生家族的人身上”[5]。
(二)福克纳小说中的神话原型之 “夏娃”
众所周知,伊甸园中的夏娃是人类之祖先,在《圣经》中是重要的人物形象,夏娃因受到了蛇的诱惑而偷食了智慧果,与亚当一同被逐出伊甸园,来到人间。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夏娃指代着失去天真、触动神怒的失落者。福克纳在小说 《喧哗与骚动》中便塑造了两位 “夏娃”形象,即康普生家族中的凯蒂及其女儿小昆丁,凯蒂的天真、善良、可爱一直是康普生家族的荣耀,家族成员将凯蒂的贞洁视为至高荣誉加以保护,事实上这种保护使凯蒂的人格发展受到了长期的压抑,“真空”下生活的她在少女时代遭遇了引诱其偷食 “智慧果”的 “蛇”——凯蒂爱上了一个名为查利的男孩并与之初尝禁果。怀孕的凯蒂被家人视为耻辱,她被迫离开了康普生家族,随后又遭遇了查利的抛弃。凯蒂与查利的孩子小昆丁与母亲的遭遇如出一辙,康普生家族将对于凯蒂的希望全部转嫁到小昆丁身上,对小昆丁的管教十分严厉,然而小昆丁在强压之下反而越发桀骜不驯,在未成年时便与人私奔,使康普生家族重拾贞洁之荣耀的梦想彻底破灭。对比 《喧哗与骚动》中的两个 “夏娃”形象,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之异同,凯蒂与小昆丁的 “夏娃”成长之路具有相同的过程:严厉的管教、家族的荣誉、在少女时代偷尝禁果;而二人的不同则在于凯蒂是被逐出“伊甸园”,小昆丁是主动逃离 “伊甸园”,在两代人之间的主动与被动的区别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于康普生家族悲剧的独特理解。虽然福克纳感叹于康普生家族的严厉家教,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男权思想的统摄下,作者依然把凯蒂和小昆丁这两个人物形象定义为失落的 “夏娃”,有评论者曾言:“成长于美国南方的福克纳无疑是男性话语的代表,失落的女性是福克纳将支撑这种话语权的内心范式转化为象征性范式的结果。”[6]
(三)福克纳小说中的神话原型之 “漂泊”
在福克纳的另一部著名长篇小说 《我弥留之际》中,作者叙述的整个故事情节的原型鲜明地指向了 “漂泊”,美国研究者俄康纳曾这样评论:“小说中的葬礼行列让我联想到了摩西的 《出埃及记》,那些跨越约旦河、涉渡史梯河的艰难跋涉本身就是一个祭典……”[7]在《圣经》中摩西带领人类在漂泊中实现了皈依,但在《我弥留之际》中,本德伦家族的 “漂泊”并没有实现皈依,而是与 《喧哗与骚动》中的康普生家族一样走向了毁灭。《我弥留之际》的故事开始于本德伦家族的女主人的逝世,家族中的男主人在妻子弥留之际曾允诺妻子将其尸体送回到四十英里之外的娘家进行安葬,于是整个家族为了践行诺言开始了 “漂泊”。在护送遗体的路上,家族成员没有悲伤,没有怅惘,而是各怀鬼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漠,可以说这次家族的 “漂泊”没有达到净化的作用,更不可能实现皈依的结果。在灵柩达到目的地时,本德伦家族的女主人的尸体已经散发着浓重的腐臭气味,男主人则急切地为自己寻找到了下一任妻子,家族的女儿无奈地生下了私生子,儿子们也都或残疾,或疯癫。可以说,这次 “漂泊”是对本德伦家族的一次考验,然而各怀鬼胎、亲情淡漠的家族显然没有安然度过这次考验,整个家族走向没落。
三、结 语
在福克纳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 “基督”的受难、“夏娃”的失落和 “漂泊”的艰难,没有看到的是“基督”的复活、 “夏娃”的悔过和 “漂泊”后的皈依,这与作者福克纳的生活状态有着很大关系。福克纳的一生均奔波在对于创作和爱情的追寻中,然而接踵而至的失意使他长期抑郁,曾几度酗酒被送至医院抢救。在福克纳的心中,人生或许就是一场经历艰难的 “漂泊”,在 “漂泊”的过程中面临着 “基督”受难的洗礼,经历着偷食禁果的诱惑,期间人性的罪恶与脆弱将逐渐被放大,倘若无法克服这种罪与弱,则会如康普生家族与本德伦家族一样走向没落。
[1]李文俊,编.福克纳评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潘小松.福克纳——美国南方文学巨匠[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5.
[3][美]詹姆士·O·罗伯逊.美国神话 美国现实[M].贾秀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5]肖明翰.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家庭小说比较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俄]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M].魏庆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7][美]威廉·范·俄康纳,编.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M].张爱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张颖(1981— ),女,吉林公主岭人,吉林医药学院外语教研室讲师,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