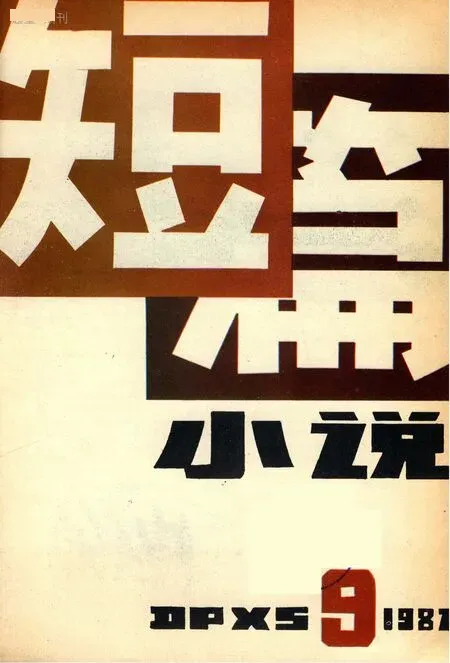一夜情
◎刘向阳
一夜情
◎刘向阳
夜幕早已降临。山子无精打采、低头耷脑、漫无目的地走着,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街头非但一点没提起他的情绪,反倒令他更加沮丧。
那位大哥,过来尝尝正宗的东北大拉皮吧!唉唉唉!咋不搭理人呢?哟哟哟,还破大盆端上了,不怕端散喽!山子的耳畔传来高门大嗓的女人吆喝声。
干哈干哈?大老娘们儿家家的,随便拉拉扯扯大老爷们儿,也不寒碜?山子身子不回,头都懒得抬。
呀!你是东北哪疙瘩的?尽管遭遇冷落,女人的热情丝毫没减。
嗯呐,咋地?山子终于停住了脚步,回转过头。
嘿!老乡呀,俺也是东北那疙瘩的!女人热情更加高涨。
真的呀?没成想呀!老乡?老家哪疙瘩?山子对眼前半老徐娘,风韵犹存的老乡顿时产生了莫名的好感。
前郭旗,稀拉套海乡,木喇嘎村,东岔古脑屯。女人毫无戒备地道出了老家的详细地址。
哎呀我的妈呀!我是西岔古脑屯的,才隔一条霍林河,咋这些年没碰过面呢?山子惊讶天下竟然真有这么巧遇的事。
缘分没到呗,今儿不就碰上了吗!女人的眉眼儿漾溢着灿烂,夜色让女人看起来很妩媚。
也是,也是,俺说大妹子,别的摊儿都俩人忙活,你咋耍单儿呢?直爽的山子说话连弯都不会拐。
咳!别提了,俺那挨千刀的回家快半年了,还在老家磨叽,我不挑单儿咋整!女人那一边一个小酒窝的嘴角挂着无奈。
横是有事,要不哪能把你晾到这儿!山子为自己的冒失打着圆场。
真让你估摸着了,俺孩儿他奶得了大肚子病,肚子胀得像鼓,他能撒手不管吗!女人用两手在自己的腹前比划着,流露出一脸的心疼。
就是嘛,搁谁身上,谁不得上心关照!人心都是肉长的,那可是自个儿的亲娘!说到这儿,山子心里咯噔一下,想到了孩儿他妈。带着孩子回去少说也有五个月了,也是去照顾肝癌晚期的娘了。咳!理解是理解,可,可这没媳妇的滋味也真难熬哇!
还傻愣着干哈!快坐下,大晚上的,喝杯生啤凉快凉快!手脚麻利的女人,嘴上说着,手已经把一大扎冒着沫的啤酒放到了山子身旁的桌子上。
望着那该凸的凸,该凹的凹的腰身,山子本就挪不动脚步了。再闻到麦香扑鼻的啤酒香,山子不由自主地坐下了。
女人又一转身,一大盘子东北人爱吃的大拉皮,像变戏法般地出现在山子面前。那颤微微的绿豆拉皮,水灵灵的细黄瓜丝儿,掺合到一块,本就馋人了,再加上鲜亮亮的辣油、肥瘦均匀的肉冒,早把山子的哈喇子勾引出来了。山子从桌子上的筷笼子抄过一双筷子,夹了一大箸,填进嘴里,只嚼几下,久违的家乡滋味便溢满了喉咙。
好吃!好吃!真是咱老家那疙瘩的味,纯正得没掺乎!山子边夸着,边端起啤酒杯,一仰脖,半杯酒下肚了。再一箸菜,再一仰脖,杯里的酒没了。
眼尖手快的女人又麻利地端过来一杯。山子接过杯,都没让杯底碰到桌上,咕咚咚,一口气全进了肚。抬眼望向天空,繁星点点,圆月高挂。嘴里喃喃着,今儿几儿了?
傻大哥,今儿是八月十五,中秋节!过节了都不知道,啧啧啧!女人仍然高门大嗓地说笑着,在给山子倒酒时,顺手拍了山子一下肩膀头。
是老糊涂了,连节都不知道过了!山子自嘲地端起杯又倒肚里大半杯啤酒。
看你也就四十出头,咋就报老了?女人微皱秀眉。
让你估摸着了,属牛的,四十一了。山子嘿嘿地笑了几声。
哟哟哟,还叫我大妹子呢,俺长你两岁,属猪的,你该叫姐!说着用手指头点了一下山子的脑门儿。
那就叫嫂子吧。山子嘿嘿着说。
嫂子!你认识大哥吗?女人嘟起了肉乎乎的小嘴。
你我才认识一个钟头,哪认识大哥去!厚道的山子答。
那你凭啥叫俺嫂子?女人说着揪住山子的耳朵,不依不饶。
唉哟哟!叫姐还不中吗?山子求饶着试图将女人的手从耳朵拉开,可那细皮嫩肉一抓到手里,好像一股电流电得胳膊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心也跟着颤了一下。在急忙抽手时,又碰到了女人那颤颤的胸脯。弄得山子顿时脸像火烧火燎似的,汗都淌了下来。
哟哟哟!看这光景该十点多了吧,咋还这么热?女人说着拿来一个大蒲扇,一边给山子扇着一边说,也难怪,这关里就是比咱关外热,在咱老家那,就这时候,睡觉还得盖被子。在这儿,盖被子还不得起一身痱子呀!别人俺不知道,还没入伏,俺就一丝不挂,四仰八叉地睡了。哈哈哈!
女人的笑让山子发现街上已经人车稀少了。想到明天还要上工,便欠起身子,同时将手伸进裤兜,大妹子,不,姐,算账吧。
干哈?要走?女人一惊一乍地说。
嗯哪。山子说着已经站起了身子。
别介!不成!今儿过节。人人都在家过节,俺这摊子也点儿背了,今儿就你一个客,还陪俺唠这长工夫的嗑,让俺没觉得一人孤单,账就免了。女人说着伸出双手放到山子肩膀上,使劲儿一按,山子就又坐下了。
咱不认不识的,哪好白吃!山子还想掏钱。
干哈干哈?俺这个姐敢情你不认了?就算姐你不认,咱还是老乡啊!就不能陪姐再呆会儿吗?女人说着眼里起了雾。
中中中!姐,俺陪你!山子的屁股刚坐实成,女人又将山子拉了起来,走,咱进屋唠嗑。外头苍蝇、蚊子哄哄的,不得呆。山子跟着女人进屋时,心咚咚地跳了起来。
山子离家七八年了,一直干的是家装的活计。凭经验,一看这屋山子就知道,满打满算不到二十平米。中间有个隔扇。估计里间是厨房,这外间就是招待客人的堂屋了。中间是个四人桌,两边靠墙还放四个二人桌。再里面可能就是卧室了。就那个四面不透风的卧室,不闷死人才怪呢!今晚莫非?山子不敢往下想了。
女人真是个麻利人,在山子胡思乱想的工夫,女人已经将门外的摊床收拾到屋里头。又在靠墙的桌面上摆了一盘大拉皮,两扎生啤。
还傻愣着干哈!过来陪姐喝酒。没等山子过来,女人已经坐稳了。女人自顾自地抄起筷子,喝了一大口啤酒,又夹了一箸拉皮,边嚼边说,这半年,忙里忙外都是我自个儿,累是小事,到了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五月端午,就我自个儿过的,跟着酒杯唠嗑,眼泪掺和到拉皮上,吃着别提多心酸了!
女人的话也勾起了山子的心事,虽说与孩儿他妈也算老夫老妻了,在一块时觉不出啥,可一分开,就不是个滋味了。跟孩儿他妈一起出来快十年了,都是白天一块干活,晚上一块在装修的房子打地铺。虽然油漆味大,虽然地铺凉,可只要身边有孩儿他妈在,就踏实,累也不觉着累,苦也不觉着苦了。可这五个月就难过了,原因是孩儿他妈不在身边了。毕竟是男人,没有女人的日子哪成呢!
山子闷闷地坐到女人的对过,连菜都没夹,就将一杯酒倒肚子里了。
今儿好了,俺白天正犯愁这个节咋过呢,天擦黑儿你就来了。哈哈!今儿有伴儿了,咱凑一块儿,也算过个团圆节!女人开心地让大半杯啤酒见了底。
山子也跟着开心起来。姐,咱有缘能在一块儿过十五,是老天的照应,感谢天老爷,再给俺倒一杯,俺全闷喽!已经喝了五六大扎生啤的山子,头有点晕了,身子感觉燥热难耐,不自觉地将T恤衫撩了起来,露出了古铜色的肚皮。女人见了索性隔着桌子伸过手,只往上一提,就将山子的体恤衫脱了下来,在姐跟前还害臊,假假咕咕的,像个老娘们!
姐,你说这话俺可不愿意了!山子将一只攥着拳头的胳膊伸到了女人面前,你看看俺这胳膊,敢和铁杠子比!
女人没有摸山子的胳膊,而是将手伸到了山子的胸脯上,反复地摸着捏着揉着,啧啧!这肌肉疙瘩,杠杠的,姐喜欢!俺那挨千刀的,哈,就是你姐夫,也有跟你一样的肌肉疙瘩。晚上,俺就愿意拿他的胳膊当枕头,贴着他那胸脯的肉疙瘩睡。女人眯缝着毛嘟嘟的双眼皮,陷入了幸福的回忆。
女人的话也让山子想起了老婆。怪不得她老愿枕着俺的胳膊,搂着俺的胸脯睡,闹了归其,这女人都得意男人的肌肉疙瘩。
不说你是不知道,你姐夫起根是在铁工厂轮大锤的。俺两手铆足了劲儿才能拿起的大锤,他抡起来带着风,一口气儿抡百八十下,气儿都不长喘一下。后来,厂子转制了,他也下岗了。俺就跟着他来到这儿,开了这间铺子。
女人的话勾起了山子的回忆。当年,自个儿在建筑公司当泥瓦工时,孩儿他妈在被服厂上班。一次全县大比武,孩儿他妈夺了红旗,自个儿也当了标兵。两口子不也是因转制下岗来到这儿的吗?
咱个泥腿子,从乡下熬到县城,当上工人就是个奇迹了!如今,又来到了这样大的城市,还能落下脚,容易吗?啊!你说容易吗?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女人无比感慨,想当初,俺一下了火车,就傻眼了,到处是人,到处是车,上哪去找活呀!俺后悔了,俺拽着你姐夫就往车站里钻,俺想回去,县城呆不下,就回东岔古脑屯,大不了,叶落归根,重操旧业,种地呗,俺就不信天老爷能饿死瞎家雀!可俺孩儿他爸不干,他说,大城市咋地,倒退几百年,也是庄稼地。大城市人咋地,倒退几辈儿,也是庄稼人。来了就不走了,不但要落脚,还要扎根!还真应了他的验,这不也有了自个儿的买卖!
女人的一席话,也让山子唏嘘不已。可不呗!刚来到这儿时,两眼一摸黑,想尿尿都找不着地方。自个儿不也是想打退堂鼓吗!还不是孩儿他妈有主意,东打听西打听,最后谋到了家装的活计。活虽说是累了些,算算存的钱,可比在县城工厂的收入强多了,翻个三倍五倍也不止!按孩儿他妈的计划,不出五年,也能在这买楼了,孩子还能来这儿读书了。就这点,打心眼儿佩服孩儿他妈,就是有远见!就是能耐!
咳!身边没个男人就是不中。俺和孩儿他爸有个明确分工,他主外,俺主内。搁细了说,采购他管,招待客人俺管。要说俺们这个小门面,能够在这条街上立得住,吃得开,有一定的名气,那可是俺爷们儿的功劳。你知道这色如翡翠的大拉皮是啥料抡出来的?是俺爷们儿从咱老家背来的绿豆!你知道绿豆是咋背来的?是经开拉油罐和煤炭的火车司机老乡帮忙,坐货龙背回来的。一看他那灰头土脸的样,俺能不心疼吗?可叫他托运,就是不干,说小家小铺的,处处都得省,要不能赚着钱吗!要说咱老家的绿豆就是好,俺用粉旋子抡出的拉皮就比别人家的薄拉、实成、筋道,放到太阳下晒,四十多度的高温,绝对不会化!俺绝对不干坑人的事,什么明胶啊,什么防腐剂,咱一概不用。咱也不短斤少两,不看人下菜碟,你说,咱的店开得能不红火吗?女人说着说着眼光暗淡了。自从这个挨千刀的走后,里里外外都得俺一个人打点,哪顾过来呀!累了一大天,晚上连个揉揉膀子、捶捶腰的人都没有,寻思寻思就有点儿散心了!
看着流了泪的女人,山子的心里也不是个滋味。隔着桌子,伸过来满是老茧的大手,笨手笨脚地给女人抹泪。可是,女人的泪越抹越多。山子索性将闲着的那只手也伸了过来。女人跟着伸出了双手将山子的手腕抓住,站起来,只一扭身,就来到了山子的身边,将半个身子委到了山子的怀里了。山子有些不知所措了。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别,别这样,你家大哥看见多不好!
女人将身子又往山子身上贴了贴,傻弟弟,那个挨千刀的在千里之外,他能看到个屁!女人将两只白嫩如鲜藕的胳膊搂住了山子的脖子,撒娇般地问,俺长得咋样?山子如实地答,俊。哪儿俊?女人又问。眉眼都俊。山子答。哪最俊?女人追问。嘴,姐姐的嘴最俊。山子答。想尝尝吗?女人用勾魂的眼睛审视着山子。山子浑身颤栗,再也顾不得什么。一低头,便将女人那带着俩酒窝的肉嘟嘟的两片唇含到了嘴里。
足有一支烟的工夫,女人挣脱了山子的怀抱。边整理有些散乱的头发,边对山子说,有胆量,还算个男人。
这算哈!我还敢睡了你!山子喘着粗气说。
还是去睡你的老婆吧!女人又恢复了高门大嗓的笑声。女人将两个酒杯倒满了酒,坐到了山子的对面。说说吧,你老婆好不好?
一提起孩儿他妈,山子就兴奋,就满足,就幸福得快找不到北了。十五岁那年,同屯女子,双双考上了县城的职业学校。毕业后,两人又当上了国营工人,有了同县城人一样的户口和粮本。同屯女子长得好看,追她的人多得数不过来。可是,女子就是心不动,头不抬。22岁那年,两人办了证,结了婚。新婚之夜,山子搂着怀里的妻子问,恁多有钱有势的你为啥不嫁,非嫁给俺这穷小子?媳妇说,穷怕啥?咱有一身子力气,早晚咱也能挣到花不完的钱。俺图你是个诚实厚道、知疼知热的人,跟你过日子,俺舒心、踏实。
女人听着听着,竟也跟着山子的情绪掉起泪来。抹着泪说,多好的老婆,你该珍惜这份老天给的真情。
女人的话,让山子不由回想起刚才的情形。山子有些不好意思了。伸手抄起酒杯,一仰脖将酒喝个底朝天。姐,俺知道孩儿他妈在老家伺候老人实属不易,可分开的时间太长了!这人想人的滋味多难受呀!山子开始流泪了,稀里哗啦地像决堤的水。
这回该女人安慰山子了。男人离不开女人,女人也离不开男人!可是没法子呀!老人把儿女拉扯大了,现如今老人病了,儿女就应该在身旁尽孝。想女人的滋味俺没尝过,可想男人的滋味俺正品着呢,实在是不好受。你媳妇啊选了你,算她没有瞎了眼,你会一辈子对她好!
女人拿来一条湿毛巾,像搂着孩子般地搂着山子,柔柔地给山子擦着。倒在女人的怀里,山子感到很温暖。困意和醉意一齐朝山子袭来。山子安静地合上了双眼。
责任编辑/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