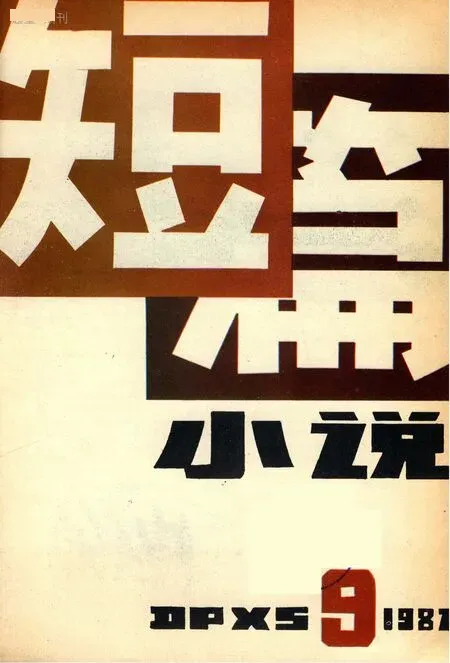王安忆都市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张智明
王安忆都市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张智明
王安忆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获得多项奖项以及提名。生长于上海的王安忆以其独有的女性视角、人生阅历和对现实生活的敏锐体察,为读者塑造了一个个丰满、个性鲜明、充满时代气息的女性形象。作家对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女性有着强烈的情感,这些上海都市女性形象在她的笔下迸发出迷人的光彩和活力。她用细腻的文字描绘出上海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写着她们在时代变迁中跟随上海一起经历的人生起伏和岁月轮转。相比于张爱玲,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女性更多了一些烟火气,多了些生活的影子,这使得这些上海女性与我们更贴近,也更真实一些。本文从作家笔下独有的都市女性气质、在时代变迁和个人阅历中流变的都市女性形象以及作为上海城市代言人的女性三方面探讨王安忆都市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一、王安忆笔下的都市女性气质
王安忆笔下的都市女性们,从雯雯系列到 《流逝》中的欧阳端丽,再到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生活态度与人生经历,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是千千万万个大上海女性汇集到一点的传奇,这点传奇是她们活得精彩的骄傲,带着她们心底的贵气。但是同时也汇集了她们在里弄里生活的烟火气,世俗却又是近人感动的。就是这些传奇和世俗的交点创造出了欧阳端丽,走来了王琦瑶。王安忆笔下的都市女性正是在这种平凡与不平凡之间,既具有真实感,又充满艺术张力。
首先,王安忆都市小说中的女性无疑都是聪慧的。《流逝》中的端丽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奶奶蜕变为承担起全家担子的 “一家之主”,《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甚至在年纪轻轻之时便懂得审时度势、进退从容。这些上海都市女性都是受过教育的,但在王安忆的笔下,她们的聪慧却仿佛与教育无关,更确切地说,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使然。与教育对立的是,她们的聪慧是带着小家子气的。那些智慧不是心胸深处偶尔露一点端倪的大志向,而是从眉眼中闪烁的小聪明。她们的聪慧体现在生活的边边角角:对自己境遇的清楚,选择的果敢勇毅;穿衣吃饭的精明打算;处理女性之间关系的微妙体贴,相依对峙;对待男人,处理感情上勇于争取,同时又留三分退路。就像 《长恨歌》中王琦瑶说的那样:“做什么都要留三分余地,供自己回心转意。而那要做的七分,且是悉心悉意,毫不马虎的。”这句话清醒而自知地概括了这些上海女性的聪慧。
其次,固守是王安忆笔下都市女性的又一典型特征。在她的许多作品中,女主人公都有自己内心的固守。这种固守在现实生活中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中产阶级生活模式的认同与向往。这种追求与其建立自我认同感的要求有着必然的联系。[1]对认同的渴望又使得她们的生活里有抵制不住的舞会,丢不掉的小资。她们融入到大上海的摩登里,是城市生活方式最忠实的拥护者。她们的内心是固守着一分俗贵的梦不肯放弃,她们对浮华是留着底线的向往,可攻可守的一种姿态。恰恰是这一点固守才有了传奇,有了十里洋场,有了夜上海,有了上海小姐。
最后,精致也是王安忆作品中女性气质的标签。没有人能否认上海女性的精致,她们是住在淮海路的精灵,她们的精致是全面的精致,就像那悉心悉意的七分,精致到极端。爱丽丝公寓摆设有致的家具,装饰的大朵大朵的花纹;严伯母家里金丝边的细瓷碗,精挑细选通透又有韵味的窗帘。吃也是精致的。上海女人离不开下午茶。哪怕外面世界惊天动地的变迁,王琦瑶家里冬日下午的茶点也是令人眼花缭乱:烤朝鲜鱼干、烤年糕片、开水锅涮羊肉、蛋饺、烤面包……再匮乏的年代也不妨碍她们的精致,因为那精致是从心底来的,是上海女人代代相传的灵魂所在,是无法磨灭的。从穿衣吃饭到言行举止,到室内装饰,到一步步人生路,上海女人是带着风情的精致。
二、在时代变迁和个人阅历中流变的都市女性形象
这里说的个人阅历指的是王安忆的人生经历,创作雯雯系列、《流逝》时的王安忆犹是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女性,而写出 《长恨歌》的王安忆已经是47岁,间隔20年的时间里,王安忆在成长变化,她小说中的女性也和她一起成长变化。这些上海女性身上有王安忆的影子,有王安忆的寄托,在不同的时代反映了她关注重心的不同。这些女性形象的建构也越来越细腻化,越来越形象化,从简单怀揣着梦想的少女到家长里短集于一身的女人。
王安忆的笔端从来也无法避开时代给上海女性身上打上的烙印,无论是轻描淡写,还是浓墨重彩,这些时代就像是脸上、衣服上的褶皱,细心观察总会在每个细微处体现。《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是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从三四十年代贯穿到八九十年代的一个传奇,30年代上海走过来的她感慨着80年代女人们的粗糙,怀念着自己年轻时代的美好。欧阳端丽则是特定时代里的一笔,“文革”中她可以放下身段去做工养家,“文革”后也渐渐端起少奶奶的态度继续享受生活,似乎和从前一样,但是迟迟不肯辞去的工厂职位代表着她在那个时代的伤痛,是她害怕那个时代继续来临而为自己保留的退路。
这些上海女性形象的流变还体现在与新一代的对立妥协中,即她们的女儿们的时代和她们的时代的对立。王安忆在写这些上海女性的成长时不惜笔墨地描绘了她们女儿一代的形象,薇薇、多多、咪咪、张永红等无疑是上海女性的延伸,带着一些继承性,但是开放的时代使得她们更多地表现的是个性。她们也摩登,也精致,但是都是打了折扣的。王琦瑶、欧阳端丽身上是包容着众多的性格的,她们聪慧、坚韧,性格平素是一团,但是在遇到外界变化时是带着伸展性的。而新时代的女孩儿们不同,她们的性格是个性化的,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点,仿佛是把她们母亲性格中的特色各分一点放大成长。哪怕最敏感最像王琦瑶的张永红,她的聪慧也是比不上的。这些新生的力量将上海女性的传奇和世俗打破重组,用个性书写传奇。但是无法否认,她们也是上海的都市女性。新秀锐利的成长,老去的上海女性的感慨,成为一种冲突的张力美,是对旧去的怀念,也是对新时的感慨。凭这一点说,王安忆展开的世界是远广阔于张爱玲的,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女性是别人的女儿,王安忆写着上海女性从别人的女儿变成女儿的母亲。她们用女儿的角度敏感过她们的时代,也用母亲的目光审视批判着这个新的时代。
三、作为上海城市代言人的女性
隔着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有两个女作家在文字里编织着上海和上海女性的故事。她们都用繁复精致的文字勾勒出上海的光与影以及散落在这座城市从繁华的淮海路到安静的平安里的女人。半个世纪前的张爱玲已经带着她的 《半生缘》 《倾城之恋》离场,半个世纪后的王安忆带着她的 《长恨歌》与 《流逝》登台,在流转的光年里继续那些上海女人和上海的故事。她们聪慧坚韧,她们带着摇曳的风情缓缓地走出大上海的光影,又隐去在岁月的痕迹里。她们和上海这座城市一起,用自己的传奇或平凡、喜乐和悲欢,构成这座城市一个又一个时代。
王安忆笔下的每一位上海女性都是上海的代言人。她将日常生活、女性与城市文明融为一体,诠释了一种在审美形态上极具女性魅力、在文化心理上旨在复归的城市女性文化。作为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一方面加速了城市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城市文明中从未停歇过的女性话语的努力。[2]因此,这些女性的生命经历和生命态度都是文明过去与现在的体现者。她们和上海这座城市一起在时代的变迁中浮沉,她们演绎的精致是上海的精致,她们固守的姿态是上海的姿态,她们内心的聪慧是上海的聪慧。她们从头到脚都打上了上海的烙印,她们就是上海的化身。这些都市女性的故事也是上海的故事。倘若上海也能化身成一个人,必定是个女子,穿着纹路繁复的旗袍,摇曳地走在淮海路。
上海也正如这些女人一样,从容不迫地走过一个又一个时代,随遇而安,稍有机会便紧紧抓住,在任何年代都带着小资的风情。淮海路两边的法国梧桐是上海;里弄交错的花枝翠影是上海;摩登的女郎是上海;固守着姿态融入大时代的是上海。渐渐地,在王安忆的都市小说中,我们分不清哪些是女性形象,哪些是上海形象,它们本来就是无法分割的整体。上海是那些都市女性,那些都市女性也是上海,她们本就是浑然天成的一个体系。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王安忆在20多年的小说创作历程中,长期自觉地关注着女性当下生存状况,探索女性的前途和命运问题。[3]王安忆的大量作品为读者描绘了诸多的都市女性,展现了她们生活中的磨难与喜乐、生命的脆弱与坚韧以及心灵深处的执著与渴望,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李海燕.王安忆女性人物形象论[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5).
[2]刘敏慧.城市和女人 海上繁华的梦——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探微[J].小说评论,2000(05).
[3]杨吉翠.新世纪以来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张智明(1970— ),男,四川广元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