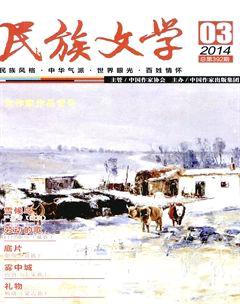人间路远
我有脚臭。
诸位看官,且慢嫌弃。因为这大概是她来世间一趟给我留下的唯一赖以怀念的气息了。
我不愿意说出她的真姓名——无论现在的她以何种方式存在于这个空间。
这里就姑且称她为苇苇好了。
我是个有轻度洁癖的人,不愿意穿别人的衣物,也不愿意让别人碰我的衣物。
当然,苇苇除外。
她是“别人”以外的人。她母亲是景颇族,父亲是布依族;而我父亲是汉族,母亲是傣族,由此可见我和她并无半丝半缕的血缘关系。但在这个奇怪的世界上,她就成了我至亲的人,之一。
而在我14岁到20岁这个阶段,她是我唯一的至亲,是唯一,不是之一。
我认识苇苇的时候,她尚是一个愤怒女青年。
甫相识,并不互相喜欢,她在的地方,我退避三舍。浓眉大眼的她太暴烈,我恐灼伤。
再往后相处,原本就是同班,或多或少有一些场合、时问是避不开的,就多了一些了解。原来苇苇的父亲同她母亲已经是再婚,生了两个女儿,可惜父亲生性暴躁,苇苇的姐姐早早在中专时候便嫁作他人妇,不论怎么说,总是脱离了充满阴霾的娘家。父母离婚后,父亲和前妻所生的大儿子过,每个月给苇苇九十元生活费。她用这九十元钱买米、买油、买菜、买衣服、交学费,交所有的一切开支。
除此之外,她有若孤儿。
而我这边的情况则是:继父总是趁母亲不在时撵我离家,我每次背了书包就投奔苇苇家——反正她一个人,去了也妨碍不了谁。所幸父亲在物质上对我很是慷慨,所以我和苇苇两人在一起的日子还算不错,至少互补——我有钱而苇苇有地方容身。
苇苇做得一手好菜,最好吃的是黄焖鸡,我追问她缘由何在。她搔搔头说,大概是放了酒的缘故吧?自己都不确定。
每次我们都会吃掉整整一只炒黄焖鸡,吃完还要咂咂手指头,真真的意犹未尽。
不知道苇苇什么时候认识了他,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富家公子。
是年,她15岁,站起来已经是亭亭玉立顾盼生辉的美少女了。
可怜苇苇自小失去太多,对于“爱”有一种迫切的心理,想抓住,留住,温暖自己太寒冷太孤寂的心灵。
也就是因为这样,男孩儿对她稍稍施予关注,便轻易攫住了苇苇的寂寞芳心。
苇苇如同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般的死死抓住了他,她用15岁的身躯取悦他,天真地以为这样便可以拴住这个浪子。
一日,我一个人呆在苇苇家里,坐在沙发上看书。沙发已经很旧了,有褐色的茶斑污渍,我刚找了一块干净的格子布盖住,看起来还算洁净。门那边有轻微的动静,是苇苇回来了。
我闲闲地问了句,回来了?她不语。我抬头看,不禁吓一大跳:苇苇目光涣散,面色青白,看上去甚至能感觉到冰冷的质感,还有几丝长发凌乱地贴在脸颊边。
一向视容貌为生命的她,如今状若女鬼。
我被吓着了,赶紧站起来扶她坐下,只觉她瘦瘦的手僵硬寒冷。就在我已经出现错觉,以为身边坐的这个人化成传说中石像的时候,她开口了。
他说孩子不是他的。
苇苇的八个字好像八颗钉子一样硬生生地凿进我心里,涔涔的冷汗湿了衣裳——无论我经历过多少不堪的精神折磨,但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黑洞,超越了我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范围。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旁边,握着苇苇冰冷的手掌,不能言语。
我给他跪下磕头了,我跟他发誓孩子是他的,他还是不信。
15岁的苇苇,向孩子的父亲下跪磕头。
我哭了起来,心要命地疼。
苇苇呆呆地转过来看我,勉强地笑,竟然还劝我:你别哭。
她脸上那笑,比哭还凄凉。
我抹了抹眼泪,站起身来拉苇苇:走,我跟你找他去!
她抽出手,呆滞地看着我:不用,他已经将我赶回家了,他死活都不信孩子是他的。他说我可以跟他睡,也可以跟别的男人睡。
我要生下来证明给他看,孩子到底是谁的。
我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眼前发黑,这世界上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吗?脑海里不停回旋的只有三个字: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苇苇浑身都烈烈地散发出寒气,双手抱肩,开始发抖。我回过神来,立刻用毯子将她裹住,接了盆热水过来,解开她的鞋子——将她和手一样僵硬而冰冷的双脚放到热水里。此刻的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头人,一个牵线木偶。
这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陪着一样未成年的好朋友,战战兢兢到医院妇产科堕胎。
第一次帮人洗脚,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事情,都是为了她,苇苇。
后来,她的身体痊愈了。但我要在多年以后才知道,她心灵上巨大的创伤从未停止过化脓、发炎。
从小被父母形同遗弃,及笄之年遭遇登徒子始乱终弃。
从未拥有过安全感。
高二还是高三的时候,我被物理老师骂,绣花枕头一包草。我愤愤地逃课,她跑出来陪我。我们在学校背后的荒野里走,一只小老鼠蹿出来,我惊叫一声,她火速将我拨到身后,随手捡起一根木棒追赶老鼠。我骇笑:你居然还敢打老鼠!她呵呵笑,你是不怕人,我是不怕动物。所以和人相处的时候是你保护我,在其他事情面前,就是我保护你了。
我笑到泪出。真是精辟。
我们继续这样的同居生活很多年,一直到我们都高中毕业。
这期间,我无数次警告苇苇:不准穿我的鞋子,小心你的脚气过给我。
我们不说传染,是说“过”。
她永远充耳不闻,总是脚一伸,就穿上我的鞋子。
高中毕业那一天,我被继父驱赶,连夜离家出走,第一次丢下苇苇——我们都是弃儿,还没有力量照顾彼此。
中间的曲折一言难尽,我被父亲找回来,又通过考试以后到昆明读书。她在瑞丽过得很不好,我劝她来昆明——我觉得我可以照顾她。
当时她帮一家街头售卖鲜榨柠檬汁的小摊主打零工。一杯柠檬汁3元钱,摊主十分信任苇苇,从不到摊子上去监视,苇苇则每晚按时收摊,将一兜兜零钱碎币交予摊主。
到现在为止,我从未见过在金钱方面比她更坦荡、更没有邪念的人。我和她相交十数年,哪怕经济再拮据,再捉襟见肘,也从未见她有过一丝欲将他人财物占为己有的贪念。
可是等她来了以后,我才发现我的力量是那么的微弱。首当其冲的就是父母震怒,将我每月的生活费停掉。没有钱才发现生活有多么凄惶无助。她中间去找工作,总是不成功——我依然没有发现,她和常人的思维有多不一样。
第一次工作是她自己看着报纸去应聘的——我想让她学着自立。
我再怎么愿意陪伴她,也不能搀扶着她走一辈子。总得让她学会自己走路才是。
苇苇去了两天就带回了辞职的消息。
为什么?我看着她,这两天的时间,苇苇很明显被晒黑了,大概因为昆明气候干燥的缘故,她看上去嘴唇干涩,皮肤粗糙,一双大眼睛神采全无。
上班的路那么远,还叫我整天在外面拉业务,我做不来。
她说完若无其事地倒头睡觉了。
你就不能坚持坚持吗?我咽下了这句话。
眼看包里的钱一张一张地少下去,我也开始着急了。
睡醒吃,吃饱睡。苇苇就这么在我的宿舍里没心没肺地过着日子,完全不知人间忧愁。
无奈之下,我利用课余时间带她去找工作。
那个时候,我每天晚上要从小菜园的校区穿越云南大学,然后到翠湖边上的讲武堂,参加跆拳道训练。我记得每天经过的路段上,有一个看上去还算雅致的酒吧招服务生。原本我是不打算让她做这个行业的一观念里总觉得“酒吧”这个行业不是善男信女聚集的场所,又怕她不懂得保护自己,有什么闪失。但经过几次不是苇苇炒人就是被人炒的工作经历,我开始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至少地理位置上挨近我,好照顾。
有点忐忑地推开酒吧洁净的玻璃门,一位小姑娘接待了我们,听说是应聘,转身叫了打扮入时的老板娘出来。
老板娘长得珠圆玉润,她上下打量一下苇苇。随便问了几句就要她即刻留下来上班。
看来苇苇这大眼浓眉、身形娇小的外形很得老板娘的喜欢。
于是苇苇就留下来,我看老板娘还算端庄善良,才放心地去讲武堂了。
晚上10点左右,我的训练结束了,到酒吧去看苇苇是否下班。苇苇跑过来跟我说:我还不能下班呢,估计要晚上一两点钟。
那怎么办?
没关系,老板娘说这里包住的,我今天晚上可以睡这里。
我探头看看酒吧里面,人不是很多,但看上去都衣着整洁,并无不妥。于是叮嘱了几句,便自己回宿舍了。
好梦正酣,被隐约的开门声惊醒了。这一下,可吓得不轻。
我浑身僵硬,心脏狂跳,竖起耳朵听动静。只听得不速之客进门之后,轻轻将门关上,然后蹑手蹑脚朝我的方向走过来。这黑影走到我床铺面前,悄悄地叫一声“乔丽!”
我的心脏刚复位,还没来得及责怪她,心又提起来了:
“现在几点钟?怎么回来了?不是说那边可以住的吗?”
苇苇苦笑一声,在我床边坐下。“他们不要我了。说我近视眼,服务不好。”
他妈的!这么晚让你一个人回来?现在几点?我忍不住骂粗话。
四点半。
次日,我带着苇苇去找那家酒吧。苇苇一路上怯怯地劝我:我们不要去了吧?他们是当地人,我们是外地人,而且我们还只是学生……
我没好气地叫她闭嘴。
进到酒吧,昨天吧台的那小姑娘看到我们,知道来者不善,先声夺人地问:你们来干什么?
叫你们老板娘出来。
有事跟我说就行了,不用叫我们老板娘。小姑娘很神气。
我上下打量她,“跟你说?你来负责?你昨天的这位同事半夜被赶回去,如果路上遇到什么乱七八糟的事,你来承担一切后果吗?如果你承担不了,麻烦你闭嘴,请你们老板娘出来说话。”小姑娘一听,果然闭嘴了。老板娘也从里间出来。
老板娘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身后的衣角被扯了扯,是苇苇。
老板娘还笑嘻嘻地跟我们打了个招呼。关心地问:怎么了?
我单刀直入:老板娘,麻烦你告诉我,不用苇苇的理由是什么?
“她近视眼啊,我怎么用她呢?”
“我想请问的是,您近视吗?”
“我?我当然没有近视眼。”老板娘仍然端庄地笑着回答我。
“既然您没有近视,那我奇怪的是,她从一开始进来应聘的时候就是戴着眼镜的,莫非您到打烊时才突然发现吗?”
“我……”老板娘有点不镇定了。站在她旁边的小姑娘准备帮她解围,我指着她说:“这没你的事,你闭嘴。”小姑娘果然又把嘴巴闭上了。
“你们都是本地人,你们也看得出来我们两个女孩子都是外地的,而且年纪都还不大。可是你在把我们当成免费雇工来用一个晚上的时候,想过一个问题吗?让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女孩子凌晨两点多从店里离开,会有多危险?我想告诉你的是,她晚上两点多被迫离店,没钱坐车,硬是走回来的,又不熟悉路,在偌大一个昆明城里兜兜转转两个小时,才走回我们学校!”我越说越愤怒,越说越心寒。
我将苇苇带到昆明来,就是为了好好照顾她。如果出了事,有任何不堪,我怎样面对她,面对以后的人生?
老板娘听到这里有点心虚了,瞥了一眼躲在我背后的苇苇。
苇苇又小声地说:算了,我们走吧。
我拂开她的手,继续愤慨声讨。
老板娘先是吓了一跳,然后镇静下来想了想,说:“那你现在想怎么办?”
“她没出事,我不打算怎么办。今天来找你,一是讨个公道,二是拿她该得的报酬。”
珠圆玉润的老板娘一听我这话,明显松了一口气,笑出声来:“哎呀,拿钱啊?好好好,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旁边的小姑娘也故意笑出声来。
拿到薄薄几张小额纸币,我看看苇苇,她畏缩的样子让我心里难受得不行。在衣着鲜亮的老板娘和吧台小姑娘的冷笑中,我将这些钱撕成两半,慢慢地扔到地上,转身走了。
做人,留点良心吧。
我留下这句话。
苇苇静悄悄地跟在我背后,像个孩子。
届时,我18,她20。
回去后,我用剩下的一点钱全部买了方便面,袋装的,整整两箱。苇苇人很瘦,但很能吃,一次两袋,而我一天一袋。她奇怪地问我,你怎么吃那么少?
我说我减肥。
后来,当两箱方便面也告罄的时候,她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仍然没心没肺地过着日子。我不知道怎样告诉她,我没有钱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义务献血,没有电脑存档。于是我到昆明中心血站,一个月的时间,卖了两次血,每次140元,给一个白水煮蛋和一盒牛奶。我给她买了回程的票,剩下的钱也一并交给她。送走她,打电话给母亲,平静地说,我已经送走苇苇了。
于是,我又得以生存。
时光跳到1994年。我回到瑞丽时,苇苇已经有了男友,也有了一份薪酬不低的工作。环顾四周,我只觉满目疮痍,无比彷徨,我只有找她。家,是回不去的。
她又收留了我。并且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月薪四百元,酒店服务员。
我并不满意,甚至还有些嗔怪:原本我是想要和她一样的工作啊。心中恨她藏了私心。早晨给客人打扫房间;拿着马桶刷子刷马桶,泪便唰唰地流下来。
虽然心中嗔怪她,但交情依然如故。听她絮絮叨叨地说:我所有的工资都给了他,想吃点东西他都不给我钱。连十块钱都拿不到。看她一副祥林嫂的模样,‘觉得不可思议;你为何不在手里留点钱?
给他管钱的呀!
她又开始帮他说话了。
后来我发现自己简直是枉做坏人。两人相处无非就是一个闹,一个笑而已。
他们结婚了。没有太多的人祝福,他们也并不在乎,依旧笑得见牙不见眼。
多好,多好一如果,这个好能永远,多好。
我离开酒店,通过信用社的同学贷到了一万块钱,开了一间小小的书屋。生意不错,每日里看苇苇和她的男人出双入对。后来有一日,她拎着一袋苹果来到书店,我简直是受宠若惊,这么多年来,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啊!谁料她一句话就叫我倒足了胃口:我花了那么多钱买给某人的苹果,她说不爱吃!我还不如拿来给你算了。
我一听,立马沉下脸来。
苇苇!这么多年来,我为你做了多少事,花了多少钱,从未想过要你回报。可是人家不要的东西,是不是别拿来恶心我?
苇苇被吓到了,我从未这样粗声大气跟她说过话。她嗫嚅地离开了。
我余怒未消,决定不再搭理她。
一日,母亲买了鸭子回来,说要做啤酒鸭。我想起当年苇苇做的“酒”鸡,就自告奋勇要下厨。母亲怀疑地看着我:你?
嗯,我做啤酒鸭给大家吃。
啤酒鸭,顾名思义应该是需要啤酒的。我买来一瓶啤酒,叫工人帮忙,把鸭子的扁嘴掰开,喂它喝啤酒……一瓶啤酒一会儿就灌完了,鸭子的翅膀还扑棱扑棱的,活力四射的样子。母亲在旁边看得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皱眉。
看来这只鸭子的酒量太好了。我自言自语。
又嘱工人去买了一斤白酒回来。白酒下去三分之一,鸭子就倒在地上了。母亲诧异地问:它死了?
没死,它醉了。
其实我心里在想:为什么苇苇的“酒鸡”没喝醉呢?
日子就在这些不咸不淡的小插曲中翻来覆去地重复……我的书店日渐喧闹,每天来往的人一波一波,却再也不见她的身影。一直按捺了半年,后来听说她离婚了,终于忍不住拉住她的前夫问个究竟。
男的是四川人,当初为了不离婚,被执意要分开的苇苇歇斯底里地打过骂过,几乎要闹出人命了,他才不得不放手——我们都不知道,当时的苇苇其实已经无药可救了。偏执、紧张、敏感、易怒。
男人说:她得精神病了撒。
我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说正经的。
男人还说:她是真的得了精神病了撒!现在关在芒市的精神病院里了。
我觉得我头脑发昏,辨不出这些话的虚实了。
男人将地址给了我,说我过几天就要去看她了,你一起去不?
我点头。
直到站在医院精神病科的铁门外,我仍然难以相信这个事实:苇苇疯了。
打开铁门大锁的声音很大,人一进去,就遍体生寒。特别阴冷的一个地方。
医生护士静悄悄地坐在办公室里,一个个精神病人幽灵一般穿梭于各个场地。有的脸上带着呆滞的笑,有的麻木着一张脸,走路都双手下垂,静悄悄的。
我寒毛直竖,如同置身幻境。
苇苇的前夫熟稔地将我带到一个办公室,跟医生登记了一下。过了大概五分钟,一个瘦削得不可思议的女人走了进来,我喉头发哽,鼻子好像被人打了一拳。她穿着一套白底蓝条纹的病号服,黝黑的长发不见了,剪得短短的而且参差不齐。肤色变得很黑,还长满了大颗的痘痘。
这还是苇苇吗?
她见到我,迟缓地笑了起来:你来了呀?
好像我和她中间发生过的一切不开心,都不曾存在过。
我抱住她,那身子,薄得像纸。
许久,她轻轻推开痛哭的我,微微地笑着,说不要这样子,我已经好很多了。
多少年,我没有这样痛哭过,没有这样锥心地火辣辣地疼痛过。
一直到离开,我都没法开口说一句话。我是多么悔恨,悔恨我曾经骂她的那句话。
或许是因为我的离开和放弃,她才最终崩溃的。
男人劝慰我:医生说苇苇的病根子早就有了,至少十年以上,和你没有半点关系。苇苇的情况要是发现得早,及时做心理疏导,可能还有救。现在已经从重度抑郁症转为精神分裂症了,只能终生吃药治疗,好的话不会复发,坏的话就可能永远这样了。
十年。
十年。医生的这番话让我在以后的岁月里时常想,如果当时有多一点的人关注到我们这些特殊家庭的孩子,多一些关爱和心理疏导,可能苇苇这样的悲剧人物会少一些。
恍惚间忆起当年,她每次发怒生气,我都嗔怪她脾气不好,吹毛求疵。却从不知那已经是一种前兆。
后来,情况时好时坏。苇苇发病过无数次,甚至还在我屋子里自杀过两次——这些都是重度抑郁症的典型特征。
所幸的是,苇苇的前夫待她不薄,甚至可以说恩重如山。离婚的时候,苇苇还好好的,从法律和道义的角度上来说,那男人都不必对她施以援手。但他一直陪在她身边,发病了送她入院,病情稳定了,又殷殷地接她回家。辛苦挣来的钱亦一把一把地撒进医院里,从未见得他们有何储蓄。男人也从不开口要帮助,甚至我要帮忙,他亦不容许。
苇苇得病后,经常疑心脚痒,从脚板一直痒到小腿,不能睡觉,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只有两个方法可以缓解:一是不停地走;二是不停地按摩。于是男人就一夜一夜地陪着苇苇,不停地走,从天黑走到天亮。要不就一夜一夜地给苇苇按摩。白天得空就睡一会,令人鼻酸。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开始骂苇苇:你这就是典型的心理毛病!你不能自己控制控制呐?这么下去,你男人迟早断送在你手里!骂了以后,苇苇还真的见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后来,苇苇和身边的人都劝男人,再找一个吧。苇苇终生服药,是不能生育了,你不能没有个孩子啊。
劝了好几年,男人终于松了口,但每谈一个女朋友,总要加一个条件:你要跟我相处可以,但是要和我一起养着苇苇。好心的男人居然还找到一个肯答应他的女孩子,也真的将苇苇接到一起照顾着。时间不久,女孩子受不了了,走了。
苇苇清醒的时候,还会跟我抱怨男人。抱怨得多了,我又忍不住:苇苇,你知足吧你。我们这些好手好脚的人,都遇不到好男人,即使遇到了还有可能会遭到抛弃和嫌弃。喏,你照照镜子去,160斤的体重,身材在哪里?脸肿得像什么一样,谈何姿色?没有美色也罢了,你连钱都没有。人家在你这能图什么呀?你还不知足。
苇苇经一顿好骂,又对男人好些。
见男人对苇苇如此关爱,我心中放下大半负担。
但有时候见旧时照片,看照片中有着一双顾盼生辉大眼睛的苇苇,身材轻盈,长发及腰,难免又是一番唏嘘。
再往后,苇苇发病时不单是自杀了,还跑,越跑越远。
男人又要生活下去,又要给苇苇筹备住院的钱。实在没办法了,男人带着苇苇投奔河南一个远房亲戚,他一人打工养活她。
这一去,竟成了诀别。
跑过两次。
一次是发病时候,跑到街上捡垃圾为生,找不到回家的路。后来男人带了照片四处找,有好心人看见苇苇,便带了给他。男人千恩万谢,将苇苇带回家,褪去了脏衣服给她洗澡,结团的头发也一一剪掉。
再一次跑,就找不到了。
男人在河南找不到,疑心苇苇会记得回家的路,于是打电话问苇苇的父母。苇苇母亲哀哀地劝男人,你死心了吧,好好地过你的日子,我女儿回不来了。
男人不甘心,迄今单身。
而我,因为当年被苇苇过了脚病的缘故,两只脚多汗易臭。所以每次洗脚上肥皂,我都会想起苇苇。
想着想着,就觉得脚上那点微微散发出来的味道,无比珍贵。
她怎样了?她还在世间吗?她轮回了吗?
人间路远,我和你曾经同行了那么久,如今既已失散,请一定好好地活着——若不能好好地活着,我宁愿你已长眠。
人间路远,要坚持内心的清白谈何容易,要保持内心的追求已经让我付出良多,如今我还在继续艰难前行,请佑护我,苇苇。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