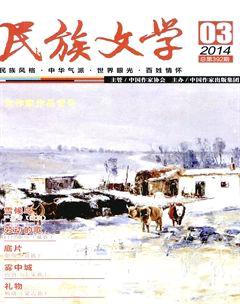底片
朝颜
1
当我回望青春的时候,我的青春早已同歌手朴树的歌声一样,烙上了深深的怀旧色彩。那些往事是一帧帧业已发黄的底片,再也还原不出当初的明艳。但我又无时无刻不想念它,就像想念从窗台上飞走一去不返的鸟儿。它有着青涩的,柔软的,鼓胀的质地,和现在干瘦单薄的我,形成鲜明的反叛。
就在不久前,一个朋友在看完我发表文章的网络日志后,突然问我:“你的青春呢?”我翻遍了整个电脑的全部文档,包括所有的电子邮箱备份,仍是一无所获。这才醒悟,许多年的写作岁月里,我竟然没有为青春时光留下只言片语。那些成长的秘密,那些难以言说的隐痛,我究竟是在刻意地回避,还是担心太过庞杂而无法驾驭?
一定是这样的!比如今天,我突然下定决心要将青春深深划过的痕迹从记忆的档案里翻找出来,它们势必滂沱而下,琐碎、杂乱无章,我唯一能够保证的,是它的真实。
2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为自己的单纯无知而感到羞耻?我只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嫩草的气息从窗外的原野涌进教室,我有一种要勃发的腾跃感。我重新购买了一本日记本,并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了其时流行的激励语:“日记日记,一天不记,不如不记。”刚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美丽的张老师告诉我们,写日记是通往作家的必由之路。那个年代,文学是多么激荡人心的东西啊。
但是在那本崭新的日记本上写下第一篇日记的却不是我。虹,我一向敬佩的好学生,她居然偷偷地翻开我的日记本的第一页,写下了一句让我倍感羞耻的话:“今天,我来月经了。”至今,我不知道她是出于恶作剧,还是出于某种无法表达和交流的困惑。她想要寻找一个出口,显然,她比我早熟。我撕碎了那张纸,爬到学校的后山顶上,看着它们在风里飞远。我保持了足够宽容的沉默,但是一种直击内心的颓败感却许久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是的,我不懂,我不懂,她们懂的我都不懂。我只是一个羞涩的还没有开放的女孩。
我注意到我的好朋友娟,她天真的眼睛里开始蒙上了一层忧愁的雾一般的东西。她开始像懒懒的猫儿那样发胖,明媚活泼的身形逐渐变得拙笨,她不再蹦蹦跳跳,不再快言快语。她那些曾经让我羡慕的漂亮衣服已经无法包裹住她的身体,她只好换上她妈妈那肥大的外套。有一次,我们一起上厕所,我看到有血从她的身体里落下来。那么殷红,惨艳,而她的脸色那么苍白。我难过地看着她一天换几次裤子仍难掩秘密,我想问的问题有很多很多,但我无法启口。我隐隐知道,她从此进入了女人的苦难。这种苦难,是疼痛与幸福相伴的夹着甜蜜的苦难。
在一次劳作之后,浑身汗津津的哥哥将手伸向腋下,似乎要捻住什么东西。然后,他迅速地抽出手来,伸到我眼前。我满腹狐疑,他的手掌上空空如也。他鼓励我凑近,我忽然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味道,灌入肺腑,我被呛得直往后退。“是狐臭!”哥哥狠狠地甩了一下手,仿佛要抛弃什么,又仿佛要打捞起什么。我第一次震惊,哥哥的身体里有了大人的味道。他每天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步,练习俯卧撑、引体向上,肌肉一日一日地凸显于手臂。他为一个女孩子写日记,我偷偷地看过,那些语言让我眼热心跳。而我的日记,仍旧鸡零狗碎,挤满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愤愤不平。其实稍加留意,就能发现校园里狐臭者、爆肥者和鸭公嗓男孩充斥其问。他们大多沉默自卑,勾着头走路,企图隐去他人的关注。在成长的道路上,男生和女生一样经历蝉蜕的苦难,囿于无法伸展青春的孤独。
那个喜欢把“踝关节”念成“果关节”的生理老师又搬着讲义走上了讲台。他刻板,面无表情,让我们翻到某一个关于青春期的章节,然后宣布自习。教室后面响起了一簇“吃吃”的笑声,一定是那几个脸上长满了青春痘的男生,他们叛逆,却又一无所知。大多数人都在装模作样地回避这一个章节,以示自己的满不在乎,或者干脆说不敢坦然面对。我也一样,若无其事地合上了书做几何题。但是趁着午休的时间,我一个人,一口气地读完了它,然后一字一句地推敲了许久,对照自己,对照长期以来默默观察到的东西。我迫切地想要探究成长,探究一直以来隐忍于胸的疑问。然而相比于我的懵懂,那些文字太过浮光掠影,我感到不够,太不够了。
那些年留下的饥渴的感觉,像嵌进水泥的石子一样,时常硌痛着我的心。后来,我有了孩子,我买下了相当数量的科普光碟,给予她足够的滋养。我不要她再重复着好奇而无法得到满足的痛苦,我要她如同四季更替般自然地生长。
3
虹在我的日记本上留下的那行字,仿佛是一句披上了巫术的盅语,指引着我朝那条未知的路一步一步地进发。虽然我毫无知觉,但那一天还是在一点一点地逼近。我发现自己的胸部长了一个胞块,硬硬的,一按便是生疼。而另一个,却依然扁平而毫无动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父亲的面前清洗身体,从未回避。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父亲,父亲又喊来了母亲。我的母亲是个粗心大意的母亲,她忘了自己是怎么长大的,也忘了她的女儿正在蓄势着抽出芽苞。
父亲把我带到诊所里,那个总是浑身泛着药味儿的老医生看了,似笑非笑,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什么也不说,却仍淡定地坐下来给我开了一大堆消炎祛肿的口服外用药。直到我胸部的另一侧也鼓胀起来,母亲才慌乱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她在屋侧砌起了一个简易的浴室,挂上了一块布帘,给予我一个隐私的空间。我似懂非懂,莫名地从此与父亲生分起来。
那年夏天,我在睡梦中感到了一股暗流在涌动,温热的,湿漉漉的,像要冲破某种束缚一般奔涌而出。醒来,我惶惑,恐惧,不知所措,我仅有的从生理卫生书上获取的知识没有告诉我如何处置。我胡乱地换了衣服,赶去学校,却再也无心上课。我时刻担心着血再次奔涌。可想而知,我有多么狼狈。
母亲闻讯,给我送来了一件我至今不知道如何使用的物件。我羞于启齿,羞于说出不懂,我只能把内衣束得紧紧的,整天静坐,不敢走动。幸亏我足够机敏,很快从商店里发现了更先进更简单易行的东西,足以代替母亲几十年来习惯的落后用具。那个从未启用的物件,被塞在某个蒙尘的角落,最后不知所终,仿若时间的隐喻,在我的生命里结了一个迅速脱落的痂。
黄昏的时候,我时常坐在校园外面的驼背树上,做种种不着边际的白日梦。从学校的广播里传来郭富城赤裸裸热辣辣的歌声:“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什么是爱,我担心自己永远不懂。我摘下池塘边的青草卷在手指上,忽然想起在琼瑶的言情小说里有一个情节,男主角用草编成戒指送给他心爱的女孩。我知道村里的新媳妇嫁进来的时候,手上戴的都是明晃晃的金戒指。那么,真正的爱情,是不是戴着草戒指也会感到幸福呢?
许多年以后,我打开一个男孩的来信,信封里夹着他剪下的如何预防感冒的文章。我们隔着千山万水,我们无法相见,他什么也给不了我,甚至于给不了一个草戒指。但我知道,那是真正的爱情。
4
我嗅到了果实成熟的气息。那个星期六的上午,一场突如其来的起哄声打破了我孤单的冥想。几个痞子一样的男生站在路旁,阴阳怪气地叫“漂亮!”和着我的脚步,他们喊起了“一二一”。
回过头来,我看到十四岁的我,穿着粉红的衬衣,绷得紧紧的健美裤,阳光正好,我走在路上,披在脑后的长头发一甩一甩,清爽的发丝一根一根地闪着油亮的光泽。我能感觉到自己正在渐渐饱满,脚步有着乒乓球一样按压不住的弹性。我感到了害怕,害怕的背面是一丝丝翘着尾巴的得意。
我还隐约地感觉到,我的背后长着一双眼睛。它善于窥视,又善于躲闪,当我想要捕捉的时候,它又沉入不可知的深渊。我捉住它,是在一个傍晚,他害羞地走过来,问我借一把梳子,好像一个犯错的孩子,犹疑地扫了我一眼,又迅速地垂下眼帘,飞也似地逃跑。我愣愣地望着那个男孩,夕阳正从窗外斜射进来,截断他已经有点高大的背影。此后,每当我走进教室,旁边的那个男生就会捅捅他:“嗨,抬头。”据说,我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他会在台下紧张得发抖。他的秘密在男生寝室早已无处遁形,借梳子只是许多人和一个人的一次“赌博,'而已。我无法付诸相同的情愫,但一种朦朦胧胧的忧伤却莫名地击中了我。
早熟的虹在教室里织一件纯白的毛衣。她面容端庄,谙熟女红,眼神里荡漾着母性的柔波。我们曾一起参加过英语比赛,但此时的她早已无心上学。而我,只会织那种千疮百孔的手套。对她,我有着既崇拜又不以为然的矛盾情感。
我的害怕终于在一个晚上成为现实,一群来路不明的男孩子在下晚自习后尾随着我,他们用石子、泥块攻击我,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我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仓惶逃跑,心惊肉跳。我求助于虹,虹的母性之光绽放得如此灿烂。每天晚上铃声一响,她就拉着我的手,飞速奔跑,将暗处的偷窥攻击者甩得远远的。
夜晚总是闪着鬼魅的眼睛,夜晚藏污纳垢,隐匿了太多的人性之恶。虹拉着我的手奔跑过一条窄巷,后面忽然传来雷点般的脚步,我在惊慌中丢失了手电筒,也丢失了虹温暖的手。我像兔子一样地奔跑,奔跑,一直跑到数里之外,才敢停下来喘气。可是虹,她竟没有跟来。她仿佛被黑夜吞噬,消失在冰冷的幕后。
从那以后,她再没有坐在教室里安祥地打毛衣。她的书包,是她的姐姐来收拾的。关于虹,没有人对我询问过半句。我知道,虹保持了绝对的缄默,这和当初我对她偷偷写下的日记只字不提如出一辙。
再后来,听说虹嫁了,而我却哭了。
5
就在我沉浸于哀伤中难以自拔的时候,霹雳舞开始在校园里大行其道。
那台晚会的音响是蹩脚的,音乐震耳欲聋,音色混沌不清,低音炮嗡嗡作响。但这些似乎都不足以妨碍一群蠢蠢欲动的孩子的狂欢。一群女孩穿梭来回,不停更换衣服表演着时装秀。穿上高跟鞋的她们,脸上便有了凛然的味道。引爆全场的是在台上翻滚的副校长的儿子,那个痞子一样的男孩。他头上扎着一块辨不清颜色的花布条,穿的是花哨的灯笼衫和灯笼裤。随着“太空步”、“木偶人”、“风车转”的舞步……一些女孩子开始尖叫。
她们围着他,宛如一群扑扇着翅膀咯咯叫的躁动的小母鸡。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喜欢他,在我无数次回想起的影像中,摧毁虹的男生,似乎头上也扎着一块彩色的布条。我痛恨一切像痞子的男生,那些动不动就为了炫耀自己,来一段“擦玻璃”动作的男生。
我的目光停留在球场上,那是我每天傍晚的必修课。他总是抱着一个篮球准时出现,腾挪闪跃的样子帅得像一头麋鹿。他转过头来,脸上带着健康明净的笑容。我安静地站在树阴下,掩饰着自己内心的激越,装作漠然地看,目光随着他板得笔直的背,从球场的这头追到那头。我不敢鼓掌,不能喊叫,所有的萌动都被硬生生地拽落到肚子里。
他是我的老师。他会把位置最好的电影票拉出来,暗示我抽到它。当然,我明白他的偏宠仅仅是因为我的成绩。当他请假由其他老师代课的时候,我的心便开始落雨,有紊乱的思绪迅疾蠕动。我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他是去约会了。我惊慌、忐忑,直到他回归校园,看到他的目光依旧平静,一块石头才落下地来。
有一个晚上,我和几个女生去找他要试卷看,打打闹闹的当儿,他突然开玩笑一般拉住了我的手,说我带你去看电影吧。电流于瞬间击中我的每一个细胞,我脑子里懵懂地冒出了从小说中习得的“非礼”这样的词汇。他说出了我的渴望,而我却本能地甩开了他的手,说:“我才不去呢,我爸在电影院上班,我什么电影没看过?”语气中带着和年龄不相称的骄傲与不屑。我的抗拒,究竟是因为胆怯,还是因为我担心得到或失去些什么?事后,我曾无数次地想象过,当我和他并排坐在电影院里,幸福之光将怎样倾泄而下,在我萌动的青春里写下诗行。
事情的结局,带着某种不可预知的偶然,或者说也是一种必然。作为学习委员,我可以随时出入他的办公室兼卧室。我轻手轻脚地拨开门闩,甫一抬头,却看见他正背对着门,一个人悄悄地温习着霹雳舞。他回过头来,动作僵在“太空步”上。我突然尖叫一声,作业本散落一地。
我逃离了那个房间,也掐灭了一段燃烧过的火焰。
6
1990年代,充斥于各种杂志的交友信息铺天盖地。文学书籍里的作者都附上了通信地址,很多人因此鸿雁传书,用虚幻的慰藉来逃避现实的溃败。
班里最先收到信件的人是娇。没有人知道她的秘密从何时因何事开始,只是慢慢发现她的手心里,常常捧着一封来自南方某个师范学校的来信。她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那个秘密,但又矛盾地渴望那个秘密能给她带来无上的荣耀。那大概是她现实里唯一的骄傲了。因为鼻炎,因为终日擤鼻涕的声音,还有身体里散发出的难闻的气味,她成为被众男生厌弃的对象,并被强行摊上了一个难听的外号。化学老师发到她的试卷时,常常不无讥诮地大声说:“恭喜你,又考了倒数。”她常常像一只受伤的羔羊形单影只地穿行在从教室通往寝室的路上,耳朵里塞着耳机,磁带里放的歌总是和爱情有关。与其说她令人同情,毋宁说她在享受孤独,活在有她和那个写信者存在的世界里。
她的隐私被一点一点地剥开来,支离破碎的,我知道那个师范的男孩名叫春,写得一手俊朗的好字,他还亲昵地称她娇妹。娇在收到信的时候,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得意。我们扮演着一面鄙夷一面窥探的丑陋角色,内心里却羡慕得发狂。和她相比,我们的世界薄如蝉翼。
那些来自于遥远的迷梦,祛除了现世的种种粗鄙,外壳由一种叫做美好的东西包裹,既能够满足虚荣,又适合诞生幻想。我和同桌媛谋划着也要交一个这样的笔友,目的是为了打败娇的傲然独立。当然,也许还有蠢蠢欲动的不安分在内。经过反复筛选,我们从众多交友信息里选择了内蒙古和云南的两个高中生作为写信对象。他们天遥地远,有着无比神秘的吸引力。在我们心里,他们披着一层圣灵般的光辉。
一切都在密不告人中悄悄地进行,我们炮制的第一封信载着希望被偷偷地放进绿色的邮筒。等待的日子如此漫长,如此煎熬。我们互相鼓励,并互相严守内心的隐秘。我们想象它是一只洁白的鸽子,飞过千山万水,落到一双宽大的手掌里。几个月后,我收到了回信。而媛的信,始终如石沉大海。我在狂喜中摊开属于我的私人的第一封信,并请来媛一同分享。但我最终仅收获了失落与郁闷。他的书写幼稚到令我不耻,语言颠三倒四,不知所云,与我的梦幻隔着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我放弃了那个与娇抗衡的念头,羞臊得将信,将那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压在箱子的最底端,再也无意翻起。
等到我读师范的时候,一个安徽的初中女孩子辗转与我成为笔友。我们在信中膜拜文学,畅谈理想……正在友情渐入佳境之时,我收到另一个女孩的来信,那是她的同学,对她的攻击和鄙夷之词再小心翼翼也昭然若揭。故事如此熟悉,又如此老套,美丽的花瓣被生生碾碎,和几年前的我们如出一辙。她是一面镜子,用窥探和觊觎映照着我隐隐作痛的耻辱。我心痛地发现,一枚叫做青春的玉永远做不到白璧无瑕。
7
我开始迷恋诗歌。舒婷、顾城,还有席慕容、汪国真……无论良莠,全盘吸收。我有一个由十本练习本装订而成的诗抄,上面抄满了我所能找到的所有诗歌,点缀诗歌的,是时下流行的明星贴纸。他们搭配得格格不入,却将我的喜好暴露无遗。一打开来,郑智化颓废地撑着双拐的模样打湿了我的眼眶。我喜欢他的才气,他歌声里的沧桑,他的无可奈何,像一个迷途的孩子那样的呐喊。在他的头像旁边,我抄下了《会唱歌的鸢尾花》。我常常在无人的时候,一个人朗诵着:“在你的胸前/我已变成会唱歌的鸢尾花/你呼吸的轻风吹动我,在一片叮当响的月光下……”那时候我的心中总是弥漫着素淡的,无以言说的忧伤,我常常幻想着用自己的温柔去抚慰一个远方的浪子,诗歌是我唯一能够抵达的途径。
就在我把一本朦胧诗选翻到每一个汉字都沾满了我的体味,仍舍不得还掉的时候,我诞生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一首诗——《曾经》。那一天,在哗哗流淌的河流中,我坐在一块条石上濯洗衣物,周围的人和事物全都往虚无处退去,只剩下我一个人,一个人深陷进对于时光、对于未来最初的愁绪和恐慌中。“我坐在时间的河流里/我今天所吟唱过的歌儿/在明天就要烙上曾经的印……”美丽的张老师如获至宝,抄在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上,并在课堂上大声宣读。我埋下头去,不敢接受那么多问询的目光,但是一份自我的肯定从心底逐渐漫漶而出。
学校里成立了以全乡最高的山命名的铜钵文学社,还定期油印一份文学刊物《铜钵风》。那仿佛是一种无言的具备着某种魔力的召唤,我像飞蛾扑火一般投奔进去,追逐着那些写诗的师兄师姐的脚步,将自己弄得神经兮兮。我膜拜着一个高三的师姐,她叫岚。岚长得并不漂亮,但她的脸上时常飘拂着火烧云一样的红晕,这使她显得格外动人。她担任着文学社的副主编,还刻得一手漂亮的钢板字,她是我心中的女神。
但是这尊神像却迅速地凋零和幻灭了,撕裂她蓬勃向上的青春之男主角,是那个长着一头卷毛的男老师。故事很恶俗,在那个年代的许多中学校园里反复地上演。他假恋爱之名,强行占有了饱满欲滴的她。而她却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处理方式,她没有隐忍,毅然决然地告发了他。她的勇敢掀起了一股轩然大波,但从此,她的诗歌被世俗之手狠狠地揉碎。不愿意怜惜自己的岚最终令我大跌眼镜,她屈从于命运,嫁给了卷毛。没过多久,传来了离婚的消息。我听到了心痛的声音,像玻璃一样碎裂,清脆,不带任何弹性。
那段时间,阴霾之花笼罩校园,创办文学社的宋老师常常拧着眉头,表情沉痛。他失去了志同道合的左膀右臂,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刻着钢板。在最新_期的《铜钵风》封面上,他刻下了一句至今还能搅动我胸膛的诗行;“哪怕天空中只剩下最后一颗星,我也要伴他唱出黎明!”那么锋利,那么决绝。
在时光的暗流里,我敬畏着潜藏于隐秘之中的宿命。许多年以后,我和宋老师在博客上偶遇。他凭着一腔对诗歌的热忱,早已冲出铜钵山下那方狭窄的天空。在南方的某座城市里,他打拼出了一份不错的事业,拥有了一个安稳的家庭。唯一不变的,是他从未停止过写诗。
去年国庆,他短信告知了他归来的消息。在饭桌上,他捧出了最新出版的散文诗集。而我,仍保留着18年前文学社的合影。漫漫文学路上,我紧紧地守护着那张照片,担心我就是天空中最后的那一颗星。虽然没有他的陪伴,我却一直没有停下攀向黎明的步伐。那一刹那,我的灵魂和肉体的眼睛一起睁开,望见诗歌像一柄银光闪闪的利剑,刺穿了漫延18年的哀伤。
席慕容的诗歌《青春》哗然而至,那是一帧复活的青春底片,一字一句,带着祭奠的疼痛,还有泪水,重新打开我那匆忙逝去的青春——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
所有的泪水都已启程。
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
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
命运将它装扮的极为拙劣,
含着泪,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本太仓促的书。”
责任编辑 陈集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