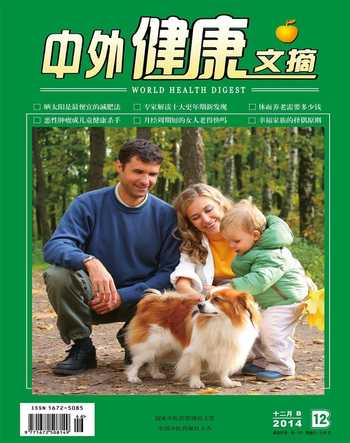那些暖,无声流淌
王举芳
1
小时候,父亲在贵州工作,母亲每天要下地,我便成了外婆家的常客。
记忆中,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天黑了,母亲还没有来接我。外婆点起煤油灯,我缠着外婆讲故事。外婆拿来针线簸箕,一边纳鞋底,一边用细柔的声音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还有一个小和尚……”
微风拂过,煤油灯的火苗左右摇曳,我的眼睛一闪一闪,看看外婆,外婆的眼睛里也有两汪光泽在闪烁。
灯芯短了,光显得黯淡了。我拿起外婆手边的针,学着外婆的样子想把灯芯挑长拨亮一点,火苗子一下子跳起来,吓得我一头钻进外婆的怀里。
外婆搂着我,轻轻拍着我:“不怕不怕,那是灯在感谢你呢,你看它现在多亮,它感谢妞妞帮它亮起来呢,你看,它好像在跳舞给你看呢。”我望着灯火,果然,那灯火摇摇摆摆的,像是在跳“迪斯科”。我笑了。
橘黄色的灯光把外婆的身影映在墙上,好大好大,覆盖了整面墙。灯火微光,映照着外婆脸上那些深深浅浅的皱纹。白色的麻线在外婆瘦削的手中来回穿梭,鞋底上早已布满了一行行、一列列整齐而斑驳的印迹。我又缠着外婆讲故事,外婆笑着,轻轻讲起:“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不幸的孩子叫牛郎,父母双亡,他和哥哥分家只得了一头老牛……”
“那后来呢?”我总是担心七仙女丢下自己的孩子。“后来鸟儿搭桥,让牛郎一家团圆。”外婆笑着摸摸我的头。“那个天上的王母也是外婆,咋那么坏呢?我的外婆最好。”我又投进外婆的怀里。
“不是王母坏,是人和神仙不是一路人。等你长大了就懂了。”外婆放下针线,把我揽起来。
外婆的怀抱真暖和,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2
上中学的时候需要住校,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
星期天早上还没起床,就听见母亲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忙活,饭菜的香夹着疼爱的味道,勾引着我的味蕾,睡意全无,穿衣起床,顾不得洗漱,直奔厨房,饭桌上的咸肉粥升腾着暖洋洋的热气,我舀一勺吸溜着喝入嘴里,顿时,满嘴萦绕熟悉的香。
那些咸肉,是父亲用在单位省下来的伙食费买来的,母亲用最少的食材,做出尽可能多的食物,她自己却很少吃,只笑着看我们吃。仿佛我们吃得开心,便是她最大的欢愉。
她用那些在田地里长出的普普通通的时令蔬菜或者野菜,炒制成独到的特色小菜,让我们的清苦岁月,增色生香,吃得贴心暖胃。
那个早春,我生了病,对任何食物都没有食欲。看我日渐消瘦的脸,父母很着急。那一天,我随便说:“不知道苦菜长出来了没有。”
母亲让父亲照顾我,自己走出了家门。直到天擦黑,母亲才回来,头发凌乱,满身尘土,原来她去挖苦菜了。她与父亲轻声说:“今春冷,苦菜还没长出来,真难找,我几乎是趴在地上才能看到它们的一点点痕迹……”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那一盘清炒的苦菜,我吃得津津有味,胜过那些绝顶的珍馐。
父母的爱,如桌上饭菜的热气一般,蒸腾弥漫,温暖着所有凄苦的日子。
3
结婚时,他说:“我也许给不了你优越的生活,但我会永远做守候你的那盏灯。”
那时,我们租住在一个农户家里,房子很小,只有小小的一间房。
下班归来,常常是暮色深浓时。拐过街口,我就开始张望,看看那间小屋有没有亮起灯盏。只要那盏灯亮着,心里便有温暖流淌,驱散夜色的寒冷。
有一段时间常常加班到深夜,他嗔怪道:“能不能不那么拼命工作啊?”一双手伸过来,将我的手安放进手心,我的手如鸟儿那样栖息在他掌心筑成的巢,顿觉温暖踏实,岁月安稳。
生活的艰辛难免疲累脆弱,但一回到家,心就变得饱满充盈,因为身边有一个那么在意我的人,给我微笑,给我鼓励,给我一个坚实的臂膀让我依靠。
小屋没有暖气,寒夜里,我们只能和衣而眠,他用体温的热量,传递着爱,给我营造一个温暖的港湾,一个饱满的爱的空间。我们依偎着相互取暖,在陌生的城市里相依为命。
他是我迷路时亮在不远处的那盏灯,是我记忆中永远不变的温存。记得有人说,每一盏灯亮的地方,都是一个家,一个温暖的家。
家,一个多么暖和的字,散发着热力,照亮着我,温暖着我。我感激着,却不用说出口。
(摘自《快乐阅读·语丝》)
——家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