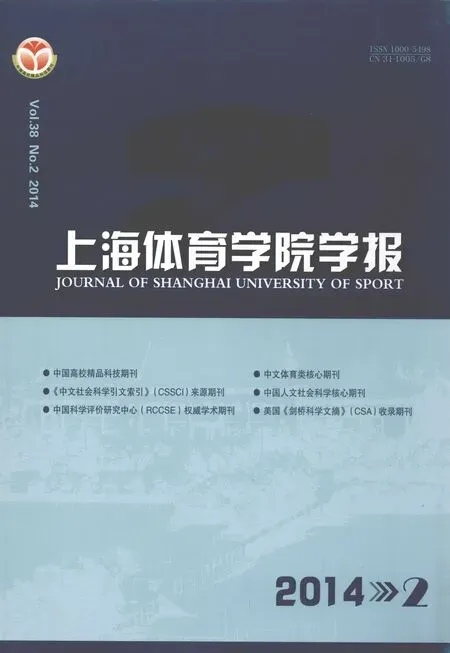想象的共同体:跨境族群仪式性民俗体育的人类学阐释
---基于傣族村寨“马鹿舞”的田野调查
杨海晨, 王 斌, 胡小明, 沈柳红, 赵 芳
(1.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9;2.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31;3.玉林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广西玉林537000;4.广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想象的共同体:跨境族群仪式性民俗体育的人类学阐释
---基于傣族村寨“马鹿舞”的田野调查
杨海晨1, 王 斌1, 胡小明2, 沈柳红3, 赵 芳4
(1.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9;2.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31;3.玉林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广西玉林537000;4.广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采用田野调查法,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出发,对云南省孟连县傣族村寨的仪式性民俗体育活动“马鹿舞”进行研究。通过对马鹿舞的仪式过程及其文化生态的参与感知、深度访谈后认为:关于马鹿舞起源的民间传说,“原型”或“母题”应来自傣族社会的生活环境和宗教信仰;马鹿舞的跨境传承、传播与傣族社会历史变迁中重大事件相对应;拥有想象的共同体是仪式性民俗体育活动得以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原因。
想象的共同体;跨境族群;仪式性民俗体育;马鹿舞;傣族村寨
Author's address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2.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Guangdong,China;3.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Yulin Normal University,Yulin 537000,Guangxi,China;4.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Guangxi,China
在中国漫长的边境沿线及其毗邻的周边国家之间,世代居住着众多跨境族群,其中仅云南就有傣、哈尼、壮、拉祜等16个民族跨境而居。尽管这些族群生活于不同的政治语境中,但他们在亲缘、地缘、业缘、物缘、神缘、语缘[1]影响下,激发了多边文化交流和互动的内在动力。因其凭借这诸多的文化纽带进行的跨国流动和信息交换较为便利,由此在族群文化演进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世居族群的特有文化模式。鉴于跨境族群文化的特殊性,在着力构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国际环境中,人类学者有必要深入研究这些跨境族群的文化生态所蕴含的丰富意义,这对促进东南亚不同地域间族群理解同源及异源文化,促成和谐共生的周边文化生态,在现实与学术层面均具有积极意义。
前人对跨境族群的研究或侧重于对某一族群历史渊源和迁徙等方面的考证,或在宏观视野下关注跨境族群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等。在体育领域,基于人类学的宏观视野,从某一具体的跨境族群所参与的身体运动入手,探讨身体运动文化在传承与传播上的共时状态、历时过程等,并且以此提升对东南亚文化圈相互理解的微观个案研究鲜见。为此,笔者借助参加“2012年云南大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生暑期研修与田野调查学校”学习的机会,与学习班的部分人员一起,对云南省孟连县勐梭寨的傣族社会文化及傣族特有的跨境族群仪式性民俗体育活动---马鹿舞(图1)进行专项性田野调查,期望借助对“马鹿舞”这一“地方性知识”的阐释,推论出关于跨境族群体育在传播与传承等问题上的一般性观点。

图1 马鹿舞表演Figure 1. Performance of Malu Dance
1 中缅边境的勐梭寨
“田野”是“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2],也是人类学研究任何人类问题的基础,优秀的田野工作者应力争做到“成为当地人生活的共同分担者和分享者”[3]42。由于运用人类学理论对身体运动的专项性研究与对传统的初民社会(primitive society)的全景式研究在选取对象、关注内容上等均不相同,因此当前体育人类学较为流行的是采用“多次、短期、深度访谈式”的田野调查。其中,笔者及参加学习的人员于2012年7月18-26日主要就马鹿舞的仪式展演过程、起源、传承与传播等进行田野调查。随后,笔者自2012年9月28日-10月7日对勐梭寨再次进行田野调查,此次主要是在人类学整体观理论下,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从勐梭寨及傣族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生活方式、宗教民俗等方面进行考察,并对上一次调查中存在的疑问进行重复求证。在2次田野调查中,主要探访了孟连县文化馆相关负责人、民间文学传承人、多位勐梭寨马鹿舞传承人以及普通寨民,共计访谈50余人次,拍摄访谈及参与式观察视频约600 min。此外,为了弥补参与观察不够深入的缺陷,笔者还采用了文献资料调研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勐梭寨地处横断山脉南麓的澜沧江流域,位于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是该县娜允镇芒弄村下属的一个傣族村寨。孟连县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缅甸第二特区掸邦接壤。勐梭寨位于孟连县城郊东南,距县城约2.5 km,距昆明市约660 km,距中缅边界约40 km(图2)。据该村已故老会计岩(音ái)依罕们(亦被称为波叶嫩)用傣艮文撰写的村史大事文本可知,现今的勐梭寨人是因害怕佤人猎头,而在1938年从当时西盟的“大勐梭”搬迁过来的。

图2 孟连县勐梭寨区位图Figure 2. Map of Mengsuo Village of Menglian County
云南大部分傣族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笔者调查的孟连县及勐梭寨傣族亦如此。为了日常佛事需要,当地各种佛寺随处可见,几乎每个下属乡镇、村寨等均有小型佛寺,傣族社会称之为“缅寺”。寨子里年龄较大的傣族人大都使用傣语,并能听懂缅语及泰语,而对于汉语较为陌生。年龄较小者由于接受了汉语教育,大都能同时熟练运用傣语和汉语进行交流,并能听懂部分缅语及泰语。勐梭寨傣族尽管与缅甸的掸族、泰国的泰族分别属于不同的国家,族称不同,但他们的居住地相连,有共同的民族特征,在语言使用、宗教信仰、族群认同等方面与缅甸、泰国的相同族群能够产生较强的共鸣。他们经常活跃于国境两侧,有史以来,探亲、访友、通婚、互市、过耕放牧、朝庙拜佛、节日聚会等传统交往从未间断。本次调查的马鹿舞正是在这样的跨境族群所在村落中进行的。
2 跨越边境的马鹿舞
马鹿舞是傣族民间在赕佛仪式时进行展演的一种拟态道具舞。据经常往来于中缅、中泰的勐梭寨村民介绍,在缅甸的掸族、泰国的泰族赕佛仪式中,也经常会跳马鹿舞。马鹿道具现在大都用竹及藤条编制骨架,彩布缝制外壳,再配上精雕细刻的木制鹿头。表演的马鹿一般为双数,且为一公配一母,但公母在动作及颜色上没有严格的区分。表演时,在傣族传统的象脚鼓、排铓、镲等乐器伴奏下,每具道具由2名男性钻进鹿身,一人为头,一人为尾,鹿头由前面一人用一只手紧贴耳部高举过头进行控制,鹿尾则俯身在后予以配合(类似舞狮)表演。
2.1 马鹿舞仪式过程的人类学解读 胡小明等[4]认为,参与性感知能够对一些处在偏远地区的、缺少记载的历史文化内容中具有个性化特征的关键信息进行较好的解答。笔者在勐梭寨的2次田野调查期间,傣族村寨正处在关门节期间;但在跟他们慢慢熟悉之后,寨民们了解到笔者一行的调研对勐梭寨的宣传及马鹿舞的传承与发展颇有益处,便在村长及佛爷的准许之下,待晚上收工后,多次在缅寺前为笔者一行表演马鹿舞。尽管此时所表演的马鹿舞缺少了赕佛仪式的象征意义,但在整个展演过程中,马鹿舞表演者及寨民们的沉浸状态仍然一览无余。通过对多次马鹿舞表演的参与式观察发现,整个展演过程基本上由热身锣鼓,孔雀舞、白象舞垫场,马鹿舞表演,嘎光舞收尾等几个部分组成。
2.1.1 开场---热身锣鼓 锣鼓队成员构成并不固定,只要掌握了击打技巧的男性均可参与。一般为3人以上,其中击铓者1人,击镲者1人,击象脚鼓者1至多人。锣鼓在整个仪式活动中主要起到活跃现场气氛、调控舞者节奏的作用。由于正值关门节期间,在传统傣族人群里,此时是不宜进行娱乐活动的,否则佛祖会怪罪寨民;但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盛行于东南亚的南传佛教逐渐世俗化、生活化,寨子里每遇特殊情况,在关门节期间进行娱乐活动也被予以默许。此外,热身锣鼓还能起到召集寨民们到缅寺汇集参与和观看表演的作用。
2.1.2 垫场---孔雀舞、白象舞 随着锣鼓声而来的寨民,有些会主动地带上跳孔雀舞和白象舞的道具。在主角马鹿舞尚未登场之前,勐梭寨会跳孔雀舞的女孩便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孔雀舞为单人表演,舞步比较简单,主要是模仿孔雀的碎步急跑、跳、起伏步,再加上一些手部控制孔雀尾羽的动作等。白象舞道具为竹篾做架、外糊白纸的大白象,由2名男性一前一后进入白象体内驾驭,动作多为起伏步,缓慢而笨重。访谈得知,无论是在缅甸、泰国还是孟连地区,由于受“男尊女卑、女人不应在大众面前过分抛头露面”的影响,1980年以前,民间的孔雀舞、白象舞等大都由男人进行表演,这与中原地区所了解的傣族孔雀舞多由曼妙多姿的女子表演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在文化全球化扩展之际,特别是在以白族人杨丽萍为代表所表演的孔雀舞的影响之下,傣族社会中原本由男性所表演的孔雀舞也开始被女性所替代,传统在解构中实现了重构,并开始形成了新的传统。现在所看到的傣族社会中,已少有男性跳孔雀舞了。
2.1.3 主角---马鹿舞 在孔雀舞、白象舞的垫场之下,马鹿舞表演者开始入场表演。马鹿舞表演主要由鹿头、鹿身及脚步动作组合而成,动作以拟态为主。鹿头是通过运用手腕关节灵活地上下左右划“∞”字体现鹿的左顾右盼、机灵敏捷;鹿身则主要表现抖水、蹭痒等生活状态;脚步动作比较丰富,基本动作为走步、点步、跳步、碎步跑、起伏步等。表演者通过模仿马鹿的跑、跳、抖身、翻滚、嬉戏及争斗等动作,体现自然生态的和谐情景,同时也向佛祖祈求傣族社会的幸福安康、多金多福。
笔者通过适时地与多位传承人、寨民等交流后得知,勐梭寨的马鹿舞表演风格与其他地方略有不同,且勐梭寨不同的师父所表演的风格也各有差异。同属孟连的勐阿,也盛行马鹿舞,但与勐梭寨的马鹿舞相比,他们的“马鹿”颈更短,脚上的动作富于跳跃,更具武术表演性。勐梭寨马鹿舞第1代传承人波帅帮表演的马鹿舞主要体现马鹿柔美的一面,而波五相表现的是马鹿机灵、活泼的一面。第3代传承人岩三嫩综合了2位老艺人跳马鹿舞的特点,集中体现了马鹿的活泼“灵”性和宁静“柔”性的特点,艺术表演力更为丰富。普洱市每年都在神鱼节、泼水节上从各地抽调马鹿舞表演队到各市县进行巡演,寨民们会依据马鹿舞的风格特征判断各马鹿的地域归属,并通过对马鹿舞表演水平的“优劣”评价,提升族群认同与族群归宿感。
勐梭寨第1、2代传承人的马鹿舞表演通常为40~60 min,由20几个动作组成。1988年前后,为了适应外出舞台表演的需要,在孟连县文化馆职员陈志明的组织下,在保留勐梭寨马鹿舞原有风格的基础上,适当加快了动作节奏,并对动作进行了简化,增加了一些诸如跳跃、打斗等更具观赏性的动作。最后整套马鹿舞共约七八个动作,4~5 min。可见,如今在勐梭寨所看到的马鹿舞其实当属近30年来才“被发明的传统”。
胡小明等[4]认为,对体育的一切研究,其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的依托主干都离不开对人类身体的影响,这也是体育学存在的依据……对于体育人类学而言,研究人类的身体形态和机能,是为促进人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怎样研究身体状况,都是文化的需要。为此,就马鹿舞对于舞者的身体质量的影响及动作删减原因等问题,笔者还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简单探究。
笔者及学习班成员对共计12人次的马鹿舞表演者的心率进行了测量,他们在表演前平均心率为66次/m in,在表演后即刻再次进行测量,饰马鹿头者平均心率为177次/min,饰马鹿尾者平均心率为153次/ min。此外,笔者还对马鹿舞表演者的力量、速度、柔韧性及协调性进行估测,认为这些指标均比勐梭寨其他村民要好。通过对马鹿舞表演者各项身体素质的评估,笔者认为其作为“被发明的传统”的生物学依据较为明显:在现有马鹿舞表演风格下,很少有未经过专业体育训练的人员能在150次/min以上的心率下进行长达40~60 min的表演。为此,生物载体的极限性决定了对动作进行删减成为必要。对于马鹿舞表演者为何在力量、速度、柔韧性及协调性上好于其他村民,是否因为练习马鹿舞而引起的身体适应性发展,或因为表演者的身体天赋优势而使得在马鹿舞传习过程中自然选择了他们,有待进一步研究。
2.1.4 收尾---嘎光舞 如果说孔雀舞、白象舞及马鹿舞等是部分傣族人参与的向佛祖敬献的仪式性牺牲,那么嘎光舞则是现场所有人向佛祖的祈福与献礼。除了击打锣鼓者,几乎所有现场者都会参与其中,经常是几十人、上百人围着篝火,女性在里圈,男性在外圈,逆时针方向,在象脚鼓、排铓、镲的伴奏下起舞。通常以4小节、8小节或平16小节为一个舞节,且每一舞节可循环往复地进行,也可把几个舞节串联成一组。整个舞蹈由丁字点步、搓踢步、扣腿旁点步及“之”字点步等脚步动作,侧平展翅、甩手高合抱翅等手上动作,配以傣族特有的三道弯身体造型构成,并不时呼喊“水-水水水(谐岁岁平安)……”“哟-哟哟哟……”以烘托热闹气氛。表现出佛教洗礼之下傣家人的轻盈、含蓄、柔和、感恩及祈求来世的文化特性。
2.2 马鹿舞源起传说的人类学解读 田野调查中经常会发现,对于民间传说的探讨往往符合民俗文化的不可重复性逻辑,即每个人对同一民间活动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如笔者在对马鹿舞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在调查对象所陈述的与马鹿舞有关的每个民间故事中,都会有不同版本的神话传说。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认为,把不可重复性的传说置于傣族社会中进行理解时,仍然是有其特定逻辑可循的。结合访谈和观察,经逻辑分析,归纳整理出马鹿舞的民间起源传说主要有以下4种版本。
岩三嫩(马鹿舞第三代传承人):马鹿舞傣语称为“戛朵”“烦朵”。“戛与烦”都为“跳”的意思,“朵”即为“马鹿”。佛祖做摆,来朝贺的有人、有鬼、有动物,“朵”也来了。“朵”是从幸福的地方---“来少勐”来的,它带来了发达与兴旺,很受群众的欢迎,之后,民众便扮成马鹿来跳舞。
昆弄(孟连县民间艺术家,孔雀舞传承人):马鹿是佛祖升天时的吉祥物,因为它很吉祥,人们认为模仿它的跳能带来好运,就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做马鹿的头,并跳“朵恩、朵喊、朵豪”(“恩、喊、豪”为傣语,即“银子、金子、粮食”,“豪”同时还有“进来”的意思),意思是跳马鹿舞就会把金银财宝拱进自己家里。
波相三(孟连县民间文学传承人):佛祖降世后,世界上所有信奉佛教的人和动物都想来拜佛。马鹿和孔雀说没有别的心意来赕给佛,就只是会跳舞,佛祖于是让它们跳舞。后来傣族赕佛中,不管赕多赕少,都要有马鹿和孔雀参加,这就形成了傣族佛事活动中的马鹿舞和孔雀舞。
勐梭寨村民:佛祖曾到孟连傣族寨子传经,傣族在寨子里跳舞欢迎,马鹿听到了铓、鼓的声音,被吸引过来,并到寨门口与人们一起听经。马鹿本来是没有灵性的动物,受佛祖传经之后,通了灵性,人们便把它迎进寨中挨家挨户照顾它。自从马鹿进寨之后,寨子里的人们安居乐业,幸福安康,因此大家便以跳马鹿舞的形式祈求寨子风调雨顺,多金多福。
斯特劳斯认为,对民族的文化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不是神话与传说的真伪,而是在神话和传说(符号、信码)背后所蕴含的普遍具有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结构)[5]。我们所能够做的是将一个神话的所有已知变体归入一个系列,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一组置换……这样一来,我们就在原本是一片混沌当中引进了一点点秩序。另一个附带的好处是可以提取出若干逻辑运作,它们本是神话思维的基础[6]。民族学家还认为,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及其神话之间存在着常规性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有一种一致性是必然存在的,而且确实存在于一个神话的无意识的寓意,即它试图解决的问题和它的有意识的内容之间,后者就是这个社会为了期待这个结果而营造起来的情节;然而,这种一致性不一定是一种准确无误的复制,它同样可能以一种符合逻辑的转换面目出现[6]。对于马鹿舞源起的阐释,实质上应要求人类学者考察不同文化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领域通过它们互补的功能而连接在一起[7]。此外,还应对他们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描述,这种描述与其所处的文化圈有关,是一定文化圈内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8]。
一个流传下来的民俗仪式,通常都会伴随一些相关的故事,这些故事无外乎就是关于这个仪式的起源、演变以及各种禁忌,这也构成了仪式背后故事的叙事结构;因此,很多仪式传说的叙事结构都有“原型”或者“母题”,而叙事或者仪式中大量的符号隐喻往往需要从基本的叙事结构中来寻找[9]。以上对马鹿舞的民间传说的陈述,同样证明了隐喻作为象征文化体系的一种表述,在仪式性民俗体育活动中也普遍使用。在傣族的文化体系中,人们选择什么样的东西进行表述,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东西,所表达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意义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这些象征符号是否具有“工具”的作用等[10],都可以放到他们的生活环境、宗教信仰中进行阐释。一是佛。尽管在不同的陈述人口中,佛出现的场合、时机各不一样(有些是“做摆、朝佛”,有些是佛祖“降临、西去”,还有些是佛祖“传道”),但都与他们所信奉的南传佛教有关。二是吉祥的动物。傣族经常跟各种动物打交道,他们会根据本民族传统的观念来想象各种动物的喻意。他们认为,马鹿、孔雀等均象征了吉祥,能给人带来好运或富足。三是美好的愿望。因为他们信奉南传佛教,讲究来世,因此日常生活中都会向佛祖诉说心愿,祈求得到保佑。
2.3 马鹿舞跨境传播与传承的人类学解读 在进行部落文化研究时,必须同样对待那些普遍、乏味的事物与俗人感到震惊、不同寻常的事物。与此同时,整个地区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在各个方面之间通行的连续性、规则性和秩序把他们连接成为系统的整体[11]。在对民族、民俗、民间体育进行个案研究时,要想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所产生的体育文化内涵,真实地还原研究对象的缘起动力、传承脉络及变迁原因,把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2种方法结合起来,将能起到互补有无的作用[12]。为此,笔者将依据这些指导思想,对勐梭寨历史场景中的马鹿舞跨境传承与传播等问题进行探讨。
勐梭寨的建寨时间较短,就历史不足80年的小寨子里发生的事情进行调查,部分村民(特别是部分长者)会有一定的记忆。对于勐梭寨马鹿舞这样缺少文献记载的民俗体育活动在寨子内代际间的变迁与传承的调查,口述史及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尤为重要。由于访谈样本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内容与事实接近与否,取决于样本的选取情况。为了尽量避免主观干扰,笔者及同行人员对与马鹿舞相关的各阶层人物进行了访谈,且每天都坚持撰写详细的田野调查日记。在随后进行的成员之间讨论中,大家把多种户访材料统筹综合起来进行分析与整理,最终形成了勐梭寨近80年内的6代马鹿舞传承谱系(表1)。

表1 云南省孟连县勐梭寨马鹿舞传承谱系Table 1 Heritage Pedigree of M alu Dance in Mengsuo Village of M englian County,Yunan Province
人类学整体观认为,构成人类整体的各种要素是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只要其中一种要素发生变化,其他要素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13]。为此,理解和认识跨境族群中的仪式性民俗体育活动传承谱系的变迁与传承问题,不仅需要关注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还需要重视历史进程中各类社会事件对该仪式性民俗体育活动变迁与传承所产生的影响作用。笔者认为,要想对传承谱系的代际特点进行合理的阐释,如要探讨“第1代是基于什么原因学习马鹿舞,接下来的各代又是在什么社会环境下进行传承的”等问题,就需要采用文化整体观的视角,把傣族马鹿舞置于整个社会历史变迁事件中进行分析。
从傣文文献的记载来看,马鹿舞传入孟连的时间应该是在第3代孟连土司“刀派送”(1349-1406年)执政时期,并在随后的历代土司赕佛活动中成为重要的活动内容之一。同时,当地每有盛大的节庆活动,如泼水节、开门节,各寨子都要派出马鹿舞的演出队伍到孟连宣抚司为土司们进行表演祈福。笔者通过与多位报告人的访谈了解到,在1939年前的西盟大勐梭时期,人们并不跳马鹿舞,只是在赕佛时,用纸扎了“白马鹿、白象、白马、白水牛”等动物赕给佛祖。由此推测,此前西盟县与孟连县对于赕佛活动中的“马鹿”表现形式或许存在一定的差异:孟连县在刀派送之后的历代土司主导下的赕佛活动中,有可能存在以马鹿舞、白象舞、鱼舞等为主要拟态舞蹈的动态供奉品;而西盟县是以马鹿、白象、白马、白水牛等纸扎的静态供奉品。访谈发现,在勐梭寨建寨初期,在各种赕佛活动中,马鹿舞还没有出现,而是采用西盟时期赕纸扎马鹿的形式。随着勐梭寨与相邻各寨之间的文化交流增多,赕佛活动产生了“涵化”,使得各家赕佛活动中,那些纸扎的马鹿逐渐开始改为由人操纵进行表演---勐梭寨马鹿舞开始形成,而在表演结束之后,这些纸扎的已进行过表演的纸马鹿,又成为静态供奉品,被摆放在缅寺之内用来继续供奉。
1950年云南解放之后,国家权力系统深入村落,无产阶级无神论思想开始实现对村落的全面控制,并明令取缔各种宗法制度,傣族社会的赕佛活动被视为封建糟粕予以禁止。随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对孟连县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如在“土地改革”“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部分解放前拥有一定财富和地位的傣族士绅、对人民犯下罪行的傣族权贵以及听信各种流言的傣族平民们,借助便利的地理条件及相似的族源文化等,避难到缅甸、越南及泰国等国家,其中,逃往缅甸的当时就逾万人[14],波喃短、波五相及波帅帮等人就多次加入了这些避难队伍。他们在国外期间,见到缅甸掸族、泰国泰族等在赕佛活动中与孟连县不同风格的马鹿舞表演后,基于族群认同及宗教信仰的需要,产生了要把这些国外的马鹿舞传播到国内的愿望。在国内局势趋于平稳之后,出于故土难离的乡土情怀,他们带着从缅甸、泰国等学习到的被认为属于本族群的最原生态的文化回到了孟连。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几年是国人信仰极为匮乏的时期,这样的时代为民俗提供了回归的契机,傣族人们希望借助马鹿这一通灵的神兽,实现自己对西方极乐世界的终极皈依,于是波喃短、波帅帮等人把从缅甸、泰国学到的马鹿舞技艺,再融汇之前的孟连马鹿舞特点,传授给了第2代和第3代。
1990年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民族地区文化形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和影响力逐渐从民族村寨中退出,民族地区自在的民俗文化逐步回归。在经历了30余年无产阶级无神论思想洗礼后,此时重现复兴之势的民间信仰,开始抛弃原来单纯意义上“封建祭祀”的娱神功能。傣族社会的赕佛及其他佛事活动出现了世俗化趋势,表现在由传统自在时期的严格师徒传承转向较为随意的师徒与集体传承相结合。此时,年轻一代大都是节庆时观看长辈的马鹿舞表演时,跟着鼓点自己学会的,基本上没有举行专门的拜师学习程序。当人手不够时,便会有所谓的第4代人进行临时兼职。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及文化全球化向边远民族地区的扩张加剧,中国、缅甸、泰国等与佛教有关的民俗、宗教及祭祀等活动基本上被世俗化,傣族社会的赕佛活动逐渐成为只是一种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仪式活动,而非之前傣族人们实现来世极乐的绝对的精神寄托。作为沟通人与佛祖之间桥梁的马鹿舞,也只是在一些集体活动中实现传承,代际之间的关系开始模糊化。
3 在想象共同体下实现传承与传播的仪式性民俗体育活动
人类学界一般对个案比较关注,但个案研究并不只是因为需要深入细致地分析某一单一事项并对其进行文化阐释,而是为了通过单一事项的阐释,归纳出普遍的意义,从而实现理论的借鉴、证伪或是对相似事象的理论推演。借助马鹿舞这一跨境族群的仪式性民俗体育活动,笔者得出“拥有想象的共同体是仪式性民俗体育活动得以实现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原因”的理论观点。
安德森[15]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对“民族主义”进行探讨时,参考了沃森(Hugh Watson)在《民族与国家》中的观点,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探讨“族群”这一文化概念:它是通过具体象征物(如旗帜、民族服装、仪式)想象出来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笔者认为,这种相互联结的意象主要是基于原生的共同文化信仰及其具体象征物,联结的结果是行动者为了“祈福”这一“工具性”目的,使用族群认同将“我族”和“他族”区分开来,从而形成族群边界。在族群边界之内,作为共同文化的信仰或仪式便因族群认同而由某一中心向周围产生传播,而传播的结果是强化了“我族”与“他族”区别以及对“我族”认同的加强。
从傣族马鹿舞这一个案来看,它起源于缅甸的勐娃地区,尽管缅甸与中国、泰国、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傣人之间存在有形的国界,但是在共同的南传佛教信仰和傣人族群认同之下,马鹿舞的传播使有形国界臣服于文化认同。傣人通过在赕佛仪式中的马鹿舞、白象舞、鱼舞等的展演,不仅实现神人共娱,而且也促进了本族群文化的传承及传播。同时,“在他族观点与本族观点推动下,使族群内部认同具有更为持久能动作用”[16],这也使得族群认同比其他认同有着更为持久的聚合力,其强大的聚合力使族群认同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3]367。笔者在勐梭寨田野调查期间,听人们提及马鹿舞道具、技术动作、风格以及伴奏锣鼓等都是从“我们那边(缅甸)的家人传过来的”“我们的马鹿舞与其他寨子的不一样”等表达。从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观念中,“国界”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而“傣人”在“族群文化”这一特定情境之下是超越国界的,族群边界才是他们所关注的。
同样,不仅是跨境族群的民俗性体育活动传承与传播是如此情况,乡土中国下的大多数仪式性民俗体育活动都是在“想象的共同体”下得以在族群中传播。它们都会有一个共同信仰的神灵作为支撑,然后借助一定程序的身体运动在同一或相似族群中实现共同的历史记忆。如:李志清[3]369认为广西三江侗族通过抢花炮这一仪式性活动,实现了侗族集体性记忆及结构性健忘,并凝聚及调整了侗族及周边族群的人际关系,以此适应现实资源竞争的人类社会结群现象;陈奇等[17]在对广西南丹拉者村“演武节”中的“斗牛斗”仪式性民俗体育活动的研究中也认为,斗牛斗运动起到了承载壮族族群文化的功能,延续了包括民俗信仰与生活习惯在内的传统文化生命。
4 结束语
就勐梭寨的“马鹿舞”这一个案而言,它只是为笔者提供了在某一特定场景中对跨境族群文化的较为细致、特定角度的观察,然后试图将这一特定田野点置于宏观社会背景中解释,并期望在一定层面上将抽象和概化的理论与现实中的族群文化现象结合起来,得以理论印证。笔者同时也意识到,本文中所提及的跨境族群仪式性民俗体育活动在“跨境传播”问题上的探讨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跨越中缅边境进行田野作业,只能囿于中国地理区域内,把马鹿舞定位于从缅甸传往中国进行的单向度研究。笔者认为,要想促进族际的相互理解,加强东盟各国的文化包容,应从跨文化的视角并跨越边境对其他诸如瑶、苗、壮等跨境民族的身体运动文化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1] 黄光成.跨界民族的文化异同与互动:以中国和缅甸的德昂族为例[J].世界民族,1999(1):25-30
[2] George Stoking.The Ethnographer's Magic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M].Madison:University of W isconsin Press,1992:28
[3] 李志清.乡土中国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 胡小明,杨世如,夏五四,等.黔东南独木龙舟的田野调查[J].体育学刊,2009,16(12):1-8
[5] 胡小明,杨世如.独木龙舟的文化解析[J].体育学刊,2010,17(1):1-9
[6] 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06
[7] 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M].欧阳敏,邹乔,王晶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58
[8] 李延超,饶远.傣族体育与“水文化”缘由探析[J].体育科学,2006.26(4):76-79
[9] 熊迅.仪式结构与国家认同:跨越中缅边境的傈僳族刀杆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2):45-50
[10]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07
[11] Malinowski B K.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M]. London:George Routledge&Sons,1922:11
[12] 杨海晨,王斌,胡小明,等.论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中的跨文化比较[J].体育科学,2012,32(8):3-15
[13] 胡小明.体育人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4
[14] 万丽.云南万人1958年逃亡缅甸 86年后回国至今无户口[EB/OL].[2013-07-06].http:∥news.qq.com/a/ 20121029/001037.htm
[15]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
[16]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96
[17] 陈奇,杨海晨,沈柳红.一项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J].体育科学,2013,33(2):30-37
Imagined Community: An Anthro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Ritualized Folk Sport of the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Field W ork on“M aluDance”in Dai Village
∥YANG Haichen1,WANG Bin1,HU Xiaoming2,SHEN Liuhong3,ZHAO Fang4
imagined community;cross-border ethnic group;ritualized folk sport;Malu Dance;Dai village
G80-05
A
1000 -5498(2014)02 -0052 -07Abstract The study adopted field work to investigate the ritualized fork sport-Malu Dance,which exists in the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 of a Dai village of Menglian County,Yunan Province.It finds that the prototype of Malu Dance originates from the living environmentand religious beliefsof the Daisociety.The cross-border inheritance and communication correspond to the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Dai society.The study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an imagined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makes the inheritance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ritualized folk sport come true.
2013 -09 -10;
2013 -11 -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10ATY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11CTY0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西部项目(12XTY005);“广西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计划资助项目;玉林师范学院青年科研项目(2011YJQN15)
杨海晨(1977-),男,回族,湖南武冈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体育部副教授;Tel:18064007139,E-mail:yhaichen2011@126.com
胡小明(1952-),男,土家族,四川涪陵人,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Tel:(020)39310230,E-mail:hxmzw@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