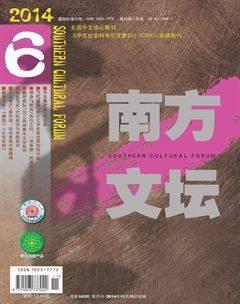鲁迅之后:“战争期”(1937—1945)的满系文坛与文艺
主持人王尧:日本学者李文卿的《鲁迅之后:“战争期”(1937-1945)的满系文坛与文艺》,是她研究“伪满洲国”文学的系列成果之一。论文仔细爬梳“伪满洲国”的满系文艺发展脉络,深入讨论了左翼作家出走关内之后,鲁迅对满系文艺的影响极其复杂的背景。作者认为:“伪满洲国”内虽无法直接阅读鲁迅的中文作品,然而在满洲“建国”前引进的鲁迅文本,却有可能透过地下文学社团在文学创作者之间加以流传,虽然在当局严厉的监控下,文本流动的范围可能仅限于左翼知识分子间的传阅。然而,即使是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以鲁迅作为批判文艺典范的论述仍可见于满系的报纸刊物,由此可知,鲁迅的中文文本虽不能见于“伪满洲国”,但鲁迅确实影响了满洲文坛。而欲探究鲁迅之所以能出现在满系文艺论述之中的原因,不能忽视鲁迅文本的日译传播脉络。鲁迅被视为抗争符码在满系文艺被传承与摹写的过程中抗衡了泛滥的国策文学,以及通俗文学的传播,并给了满系文化人理想的文学想象,提供了精神的寄托。——作者的这些见地对我们认识“伪满洲国”文学的复杂性颇有启示。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载体。当代文学如何走出去,面临哪些挑战与困境,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应对的策略,这些问题也因此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访谈录《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的受访者白睿文是北美学界年轻一代学者中的佼佼者,既勤于学术研究,也致力于当代文学的英译,成果斐然,影响颇大。他作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亲历者,现身说法,就当代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提出了自己的观察,特别是他翻译实践中的切身体验,大到翻译文本的选择,语言风格的处理,小到具体语句的转译等等,都为我们思考相关问题提供了生动可感的第一手材料。
一、前言:左翼系谱与东北文坛
五四新文学运动不仅刺激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文坛,也启动了东北的新文学脉动(1)。在此新文学风潮的带动之下,作为新文学运动舵手的鲁迅,也为中国的新文学树立了一个标杆,其风格成为后人仿效的书写典范,是揭发现实与抗争的模型,奠立了东北左翼文学系谱的概貌。此左翼系谱之继承到了1932年因溥仪在新京(长春)创立“满洲国”,而有了不同的方向,对于左派文人而言,“改朝换代”之后的东北文坛,除了旧式封建的残余之外,更大的议题是殖民与国族。
1934年对于东北的左翼系谱而言,可说是一个转折的年代。萧军、萧红、舒群等人的离开造成满系文坛的重编,以山丁、古丁、疑迟、小松、爵青、秋萤等人为主的满系文学系谱正式开启。本文将讨论战争期间乃至于大东亚时期,作为新文学启蒙者之一的鲁迅,如何成为满系文艺的典范符码,亦即探究满洲文坛的满系文学如何师法鲁迅文风,以及战争期的鲁迅叙事传播的可能及其效应。
二、变动中的文坛:鲁迅文本于
满洲国(伪满)传播的可能
为了宣传伪满洲国“民族协和”的政治口号,并形塑“王道乐土”之意象,在日本的支撑下,伪满洲国初期欲透过舆论快速地合理化其“建国”的正当性,因此使得报纸的出刊量大增,而这种现代的宣传媒介也带给满洲文艺一个崭新的发展空间。除了中文报纸的刊行之外,日文报刊也迅速地扩增,自伪满洲国成立至1936年左右,由官方弘报协会直接经营或握有主要股份的日文报社有满洲日日新闻社、大新京日报社、哈尔滨日日新闻社;中文报社有大同报社、盛京时报社;朝鲜语的报社有满蒙日报社,此外还有英文报刊《满洲日日新闻》,可说是同时掌控多种语系的发言权,也因此形成了伪满洲国特有的多语社会形态。
满洲的文艺的最大特点便是此多语系统的创作背景,除了满系的中文系谱外,日系文学以大连、旅顺为起点,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而逐渐将中心扩充转移至新京(长春),同时期还有白系(俄罗斯)文学、鲜系(朝鲜)文学的作品。满洲文坛的复线式发展样态,使得满系文学在各种文艺理论的刺激下也展现了多元性之样貌,在新文学作家的努力之下,各式的新文学作品拜当时报纸盛行之赐,使得文艺创作也能依附报纸副刊得以传播,此种文艺风潮又被称为“报端文艺”,俗称“报屁股”(2)。然而,随着日益严苛的言论管制以及对左派文人的监控、打压,使得左翼文学色彩最为鲜明的北满哈尔滨作家群流亡关内,伪满洲国的文艺重心也转移至新京。流亡作家群中,以在上海直接受到鲁迅帮助的萧军、萧红,在文学创作、出版上表现得最为活跃,其与鲁迅之间的往来以及由鲁迅作序,编入《奴隶丛书》的《八月的乡村》〔田军(萧军)〕、《生死场》(萧红),这两部作品中所暴露的东北现实,使得“东北流亡作家群”在上海文坛受到了注目(3)。
藉由鲁迅的背书,萧军与萧红进入了上海文坛,同时也提升了“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名声,他们透过书写东北持续抗争之路,并卷入了中日战争以及国共争斗的洪流中,与其他的左翼文人开始了行动救国,在动乱的时代中辗转武汉、临汾、西安、延安、香港等地。相较于萧军、萧红等亡命关内作家的积极态度,满洲文坛的左翼作家们在严密的政治控管之下一度沉寂,1936年6月發生了“黑龙江民报事件”,此事件中,担任《黑龙江民报》副刊“芜田”编辑的金剑啸及相关的左翼人士遭到逮捕后被处决,对于整个北满的左翼文学之发展影响甚巨。除了持续地对左派文人活动的打压之外,当局也彻底清查各地的报纸文艺副刊,凡有涉及抗日、反满思想以及“左”倾色彩的刊物全都遭到查禁,强迫停刊。此时期值得注目的文学研究社团是田贲于1936年(4)所组织的“L.S(鲁迅)文学研究社”,这个社团无疑是左翼文艺由明转暗后鲁迅精神的直接承续,对外的名称是“灵莎文学研究社”,对内则称为“鲁迅文学研究社”,以抗日为主要宗旨。1940年田贲更通过《营口新报》主编《星火》,并于发刊词中声明:“‘星火是为人们开花的,不是为何人插花的。期望其读者不止于知识层,且应有农夫、樵夫、老父和壮汉。”田贲想透过文艺动员满洲大众的用心由此可见,其对于文艺大众化的努力以及企图透过文艺进行的抗争形态,虽然在满洲严密的援日战争态势中并未引起反抗的波澜,但却也在左翼式微的战争期间接续了左翼思潮的系谱,后因日益鲜明的抗日色彩,终于在1941年被迫停刊。进入战争期后,为了因应更为严厉的查禁手段,满洲文坛的左翼文艺可以说是在查禁、转移、再生这种循环中进行着,作家们的写作形式与发表样态也随着社会氛围的改变而持续变动。
除了上述的“L.S(鲁迅)文学研究社”以秘密结社的形式传承鲁迅精神外,公开的鲁迅传播路径究竟通过何种形式进行开展?1932年满洲国(伪满)政府颁布《出版法》,第四条法规中规定禁止刊登、出版的八项内容,包括:(1)危及国家基础的内容。(2)有关外交、军事的机密。(3)对外交有重大影响的内容。(4)煽动犯罪的内容。(5)不能公开的法庭诉讼的辩论内容。(6)蛊惑民心、搅乱财政的内容。(7)检察官、警察禁止的内容。(8)有害秩序稳定和风俗的内容;同时要求从满洲国(伪满)外输入之出版物,也必须遵循国内出版物的法律准则,举凡有违满洲国体之出版物一律禁止(5)。从这些规范中可以窥见伪满洲国欲通过国家机器掌控发言的企图,出版法的颁布不仅是加强对内部出版的管理,更是要严格控管关内(中国)引进的中文出版刊物的传播,彻底区分“满洲国”与“中国”,为了更有效地加强国家论述,只要是内容牵涉到反满、反日之思想的出版物一律禁止输入,在这种氛围下,鲁迅的中文作品当然也在禁止名单中。
伪满洲国内虽无法直接阅读鲁迅的中文作品,然而在满洲建国前引进的鲁迅文本,却有可能通过地下文学社团在文学创作者之间加以流传,虽然在当局严厉的监控下,文本流动的范围可能仅限于左翼知识分子间的传阅。然而,即使是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以“鲁迅”作为批判文艺典范的论述仍可见于满系的报纸刊物,由此可知,鲁迅的中文文本虽不能见于伪满洲国,但鲁迅确实影响了满洲文坛。欲探究鲁迅之所以能出现在满系文艺论述之中的原因,不能忽视鲁迅文本的日译传播脉络。早在1920年,日本的汉学家青木正儿(1887—1964)撰写的《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中便提及:“就小说而言,鲁迅是大有可为的作家。如他在《狂人日记》中对于患有可怕迫害妄想症的人之描写,已经跨足到现今中国小说家所未曾到达的境界了。”(6)这是鲁迅第一次以其笔名被介绍入日本。而鲁迅作品的最初日译是于1922年,由周作人翻译《孔乙己》,刊载在北京的日文周刊志《北京周报》第19号,此周刊志也刊载过鲁迅翻译的童话《兔与猫》以及鲁迅的访谈录,后通过清水安三(1891—1988)(7)于《读卖新闻》上以散文《周三人》连载介绍,鲁迅也一举被引介入日本文坛。1920年的前半,鲁迅的作品也被编入中国语的中级教科书中,一举使得鲁迅成为中国五四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也有助于鲁迅作品在日本的流传。到了1927年,武者小路实笃主导的月刊志《大调和》10月号上刊出鲁迅的《故乡》日译版,这是鲁迅在日本被翻译的第一篇作品。1928年以后鲁迅的日译作品逐渐增多,其中以1935年佐藤春夫、增田涉编译的岩波书店文库版之《鲁迅选集》影响较广,除了在日本国内流傳之外,同时还传介至殖民地的台湾与朝鲜,其中增田涉于1934年刊载在《改造》4月号上的《鲁迅传》也被译为中文,连载于《台湾文艺》第2卷1号、2号、3号之上,给了台湾文坛理解鲁迅的契机,并点燃了“文艺大众化”之议题。
除了上述文坛的中国研究者们开始译介鲁迅、研究鲁迅外,鲁迅去世之后,1937年改造社便整理出版七卷的《大鲁迅全集》,此举也可得知鲁迅受到日本知识人重视的程度,并且在增田涉之后,1941年3月由小田岳夫执笔的《鲁迅传》(筑摩书房)出版,这也是日本最初完整统合鲁迅一生的传记。另外,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核心成员的竹内好也于1944年12月出版《鲁迅》,对于增田涉与小田岳夫的鲁迅理解多有批判与修正,并且也树立他自我的鲁迅观(8)。从上述的鲁迅作品的日本译介概况可以得知,鲁迅的作品自1920年代之后便开始在日本流传,及至战争期间也仍是以中国新文学的启蒙者被传译,可以说,在战争氛围下,“鲁迅”在这些文学者的笔下已经脱离了时代,被上纲成为近代中国文人的理想形象,是中国的民族魂也是精神与文学的启蒙者。通过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对鲁迅的符码化与译介,使得鲁迅成为中日间共同的文化符码,在战争期乃至于大东亚战争时期“日满一体”“民族协和”的国策下,被神话化以及理想化的“鲁迅”身影,俨然成为日中友好的桥梁,这可从1937年古丁发表的《鲁迅著书解题》译介以及1944年外文翻译出版小田岳夫《鲁迅传》得到印证,而在此共识下,鲁迅的传播也成为可能。
三、一场论争:倘若伪满洲国会
产生鲁迅似的大作家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中国各地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纷纷推出鲁迅追悼纪念专号,透过各纪念专刊的出版也迅速将鲁迅予以典范化,鲁迅俨然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灯塔,是民族灵魂的象征。满洲文坛自1936年6月开始直至11月止,《盛京时报》《大同报》以及《泰东日报》上也先后报道关于鲁迅病重、逝世的消息,并刊载了纪念鲁迅的相关文章。中日战争爆发之后,1937年3月创刊的纯文学志《明明》于11月也推出鲁迅纪念特辑号,其中古丁特别将日本出版的《大鲁迅全集》中置于各卷卷末的“解题”统整翻译,题名为《鲁迅著书解题》发表在此纪念专号上,共收录了增田涉、鹿地亘、胡风、松枝茂夫、小田岳夫等人的作品,最后由古丁附上《译后赘记》。
在《译后赘记》当中,古丁直接提出除了鲁迅之外,“东洋还有几个作家值得刊印全集的呢?”(9)将鲁迅置于东洋最伟大的作家之列。
古丁特别强调鲁迅能谈今溯古,又论古及今,并认为其反复论说的目的就在于“在绝望中觅希望”。对于满系作家而言,古丁所提出的鲁迅精神恰巧扣合了其自身境遇,在战争期间言论备受压抑、限制的空间中,期待通过鲁迅精神的传承,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古丁在文中也表明自己翻译的目的,是要让无缘阅读鲁迅著作的满洲读者们,通过这些解说、介绍一窥鲁迅之梗概,如此一来,也加速了鲁迅的符码化过程,他提到,“然而,鲁迅怕终究是‘鲁迅罢,我们甚至于不能以‘周树人来代替‘鲁迅。”他想以“鲁迅”为镜,借以照看满洲的文学。从古丁对鲁迅精神的提出与摹写,可以看出这位周旋于日满之间的文化人,意识到的日满共同符码:“鲁迅”之效用,并欲以此推动、刺激战争氛围下的满洲文坛之用意,古丁透过高举鲁迅精神,一方面激励满系文学的创作,给予文学者们一盏指导明灯;另一方面也以此制衡文坛泛滥的通俗文学。对于古丁而言,“鲁迅”不再只是文学革命中的一员,他成为抗争、不屈与奋发的象征,也在满洲的多语境书写场域中,成为其创作的保护盾(10)。
综观满系的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战争初期支撑满系文学活动的文学杂志主要有《明明》(1937)、《艺文志》(1939)、《文选》(1939)、《作风》(1939)等刊物。其中受到月刊满洲社创办人城岛舟礼的资金支持,于1937年3月1日创刊的《明明》,可说是战争期间最具启发性的满系文艺刊物(11)。《明明》从发刊到停刊虽仅一年多,然而《明明》的发刊对于满系文学的发展实有具体的作用与意义,首先,《明明》的创刊将满系文学者们以报纸副刊文艺栏为主的“报屁股”文学提升为纯文学志的层面。其次,提供满系文学者们因“弘报协会”整顿报纸之故而萎缩的发表空间。
此外,《明明》的发刊也意外引发了山丁、古丁等人的“乡土文学”论争,这场论争揭示了满系文学者们对于政治议题的不同对应,以及创作方向的分歧。《明明》于第3期(1937.5)中登载了疑迟的《山丁花》,而主张乡土文学的山丁便于第5期(1937.7)中发表了《乡土文学与〈山丁花〉》一文,将《山丁花》视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主张这是一篇写实主义的乡土文学之创作。对此,古丁以及《明明》的成员不表赞同,因而引发了双方对于乡土文学的论战。
对于山丁而言,乡土文学中所揭露的阶级对立、殖民主的剥削最能切中当时伪满洲国的现状,相对于政府主张的“王道乐土”之假象,唯有以写实的才能彻底对抗官方文艺;加上满洲国(伪满)“建国”初期,山丁在北满与前述的东北左翼作家群有过密切的来往,更强化了其欲以乡土文学进行文艺抗争之路。而古丁则不同,古丁曾就读于日本人开办的长春公学堂以及沈阳的南满中学堂,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3年返回长春之后曾任职于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统计处的事务官,1940年以后专心从文,经营艺文书房,并担任过满洲文艺家协会大东亚联络部部长,可以说,由于古丁处在日、满间的位置,使其对于文艺的看法可说更形复杂,然而,从他以笔名史之子发表于《明明》第5期的《大作家随话》可以窥见其对满洲文艺的看法。
首先他呼应了石敢当发表于《月刊满洲》上“倘若满洲国会产生鲁迅似的大作家”的提问,并认为这是满洲文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大课题。鲁迅似的大作家,该是怎样的呢?古丁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他先界定鲁迅似的大作家应有的态度,他认为鲁迅的杂文“全是肉搏社会的匕首,因此知道他非特是大作家而且是大战士”(12),文中再三肯定鲁迅的战士精神。第二点他讨论了满洲文坛应该如何产生鲁迅似的大作家的方法,首要条件是针对文坛的出版统治,他认为文化统治者(当局)在文艺上应该放松钳制,给予读书人读书与思索的自由(此处意指当时颁布的出版法而言),由于中文書籍遭禁,古丁调侃当局:“我们连买《辞源》都犯罪的,我们的案头只剩下了“四书”、“五经”,“五经”里即便蕴藏着几多珍宝,似乎并不能产生‘鲁迅似的大作家。”接着古丁也提出满洲文坛当前的歌颂“王道乐土”的王道文艺的弊端,他指出:我们的文坛,自从大主笔(指穆儒丐)创作了《感谢情调》之后,是只许堆笑言不准做哭脸,只许发赞声不准泄叹息的了。我始终相信:唯有大声疾呼才能震撼萎靡的灵魂,佯笑假赞却只会压缩欲裂的血管。最后古丁讨论了“鲁迅似的大作家产生后将如何呢?”可能也因为找不到出版社以及使用白话文而遭查禁,这样一来,鲁迅似的大作家也将会被斩首消失了。古丁最后以“大寂寞。大荒原。不可救治的哑巴和聋子”来总结满洲文坛,而期许文学者们“不妨朝着不知道方向的方向奔突”。相对于执着乡土文学之路的山丁,古丁在文艺主张上可说顾及了满洲文坛之现状,也预见乡土之路将会在政治压迫下走上末途,因此着眼于出版与发表。他之所以提出鲁迅作为文艺典范,首先是意识到鲁迅作为伪满洲国的满系与日系文人间所共通的符码的功效,透过这个共通的符码,古丁不仅能得到日本方面的助力,并且在鲁迅的名义之下也得以发展满系的文艺,另外,鲁迅弃官从文,以文针砭时局的创作历程与古丁自身也有相似之处,因而古丁摹写大量的杂文,并以此推动其无方向的方向之文学主张(13)。
古丁强调自己的文学路线,亦即“没有方向的方向”,反对一切主义的标签,这个文艺思路是承袭他发表的《大作家随话》而来,其主张的“写与印”以及“无方向的方向”与山丁主张的“乡土文学”所引发的满系文学路线之争,使得战争期的满系文学呈现了两大流派,以古丁、小松、辛嘉、疑迟为主的“写印派”与以山丁、秋萤、季疯、吴郎为主的“乡土派”,强调建设“热与力”“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东北新文学路线呈现对立的状态。在刊物的发行上也呈现两大路线,《明明》与《城岛文库》的发行支撑了古丁诉求的“写与印”文学路线,另一方面1938年7月2日以山丁为首的乡土派文学者则透过《大同报》发刊的文艺专页上与《明明》成为战争初期两大满系文学路线。此次论争中也揭露出满系文人对于当局的态度,一方面古丁等人的写印主义可以视为对政治议题的消极回避,以文学为主轴的文学路线刻意模糊了政治的焦点,另一方面山丁等人的写实主义之“乡土文学”,其意在暴露满洲现况的书写模式则具有明确的抗拒色彩,特别是呈现出与当局之间的微妙不妥协感与古丁等人的暧昧思维有所不同。
对古丁等艺文志派同人而言,推动满洲文学的途径唯有通过创作以及出版,他们认为满系文学尚在发展,未达到可以提倡主义的境界,并且单靠满人作家的单独力量达到的成果相当有限,此也为古丁与日系文化人的密切互动提出了解释。意即,在出版的前提下,为了推动文学与日本之间的提携互动成为无可避免的策略,然而却也埋下了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之文化策略协力的契机(14)。
有别于“艺文志派”的日满合作,在《艺文志》盛大的出刊之际,秋萤、袁犀、孟素、李乔、李妹、陈因等人在奉天成立文选刊行会,同年12月创刊《文选》,由秋萤、佟子松任编辑。在《刊行缘起》中明言,现阶段的文学已经不是超时代的为艺术而艺术或个人主义的牢骚泄愤了,现在的文艺是教养的利器,认识现实的工具,因此作家不能逃避客观的现实,遮蔽了客观的真实,要在真正的实践中创造有生命的作品。此言论承续了山丁所言的“暴露真实”之路线,可以说在1941年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前,满系的文艺工作便是以此两大路线为发展的主轴。
四、小结
仔细爬梳伪满洲国的满系文艺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战争期间被视为文艺符码的“鲁迅”,在满系文学中的指导位置,通过满洲文坛的“鲁迅”译介传递,也提供一个观看满系文艺发展的视阈,由此也可窥出在五四思潮刺激下萌芽的东北新文学,虽历经满洲“建国”、打压左翼以及种种的出版发表之钳制,但仍保留了其批判与揭露现实的文艺本质。特别是在左翼作家出走关内之际,‘鲁迅被视为抗争符码在满系文艺被传承与摹写的过程中抗衡了泛滥的国策文学,以及通俗文学的传播,并给了满系文化人理想的文学形象,提供了精神的寄托。并且,如古丁的《鲁迅著书解题》以及外文的《鲁迅传》都是鉴于满洲文坛对于日本读本监控的相对和缓而得以出版发表,由此也可看出战争期间满系文人们在译介路径下所持续的鲁迅传播之成效。战争时期,在“民族协和”以及“日满一体”的国策下,辞世后的鲁迅吊诡地成为日中、日满的共通符码,而在符码化的过程中,满系文人也通过鲁迅的提倡传递其文学理念,可以说为战争期间众声纷纭的满洲文坛之满系书写保留了一条反映现实的书写之路。
【注释】
(1)此时期著名的文学活动与刊物如:1925年由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所组成的文学研究会与启明学会,前者多以学生为主;后者则由学校教员、新闻记者以及各机关的职员所组成。文学研究会发行《奉天学生》;启明学会则出刊《启明学报》,活跃的作家有:金小天、郭心秋、李笛晨、赵虽语、赵鲜文、郝心易、赵石溪、周筠溪、周东郊、屈以诚、苏子元、杨予秀、孙百急、王莲友、吳以伯、罗慕华、张崇羽等人。另外,1926年由周筠溪、周謇鄂等人于沈阳成立春潮社,发行《漫声》。此外,1926年至1928年间,《盛京时报》的“紫陌”、《民报》《晨光报》以及《新亚日报》等副刊上也刊载了相当数量的新文学作品,1927年《新亚日报》与《奉天商工日报》也各自推出“绿痕”、“文学副刊”等新文学发表园地,此时期著名的作家有:王一叶、孙孚生、杨一、张弓、张笑潜、王语绿、新痴女士等人。1928年王一叶等人更组成了东北文学研究会,另外,东北大学的学生也发行了定期刊物《夜航》。个人推出的文学志有张士丐的《长虹》;此外,《国际协报》《泰东日报》的副刊也都重新改版,延吉的《民声报》更推出批判性十足的《荒原》。到了1929年,赵鲜文的《昭陵红叶》、林霁融的《鲜血》以及张露薇的《情歌》等单行本的发行受到注目,同时期活跃的作家群尚有:白晓光、李别天、秋嵩、朗烟、茄啸、黃旭等人。参见大內隆雄:《满人の作家たちに就いて》(关于满人作家们),收于《满洲文艺年鉴》(第一辑),1937年10月。
(2)当时的中文创作,由于为了凸显“满州国”的独立色彩,因从地方色彩浓厚的东北文学一律被改称为满洲文学以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而生活于满洲国的汉人也一律被归为“满人”,便于当时民族协和论的推动,本文中对于此时期的汉族与中文创作皆采用当时之称谓。参见大內隆雄:《满人の作家たちに就いて》(关于满人作家们),收于《满洲文艺年鉴(第一辑),1937年10月。
(3)《八月的乡村》于1935年8月由奴隶社出版,假托上海容光书局发行;《生死场》于同年12月出版,同样由奴隶社出版,假托上海容光书局发行。许广平对于这两部作品回忆道:“作为东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议的里程碑作品,是如众所知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无疑地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参见许广平:《追忆萧红》,收于《文艺复兴》1卷6期,1946年7月。
(4)关于田贲组织“鲁迅文学研究社”的组织时间,也有说是1935年。参见刘慧娟编著:《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料》,84-8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参见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日本殖民地文化研究会编:《伪满洲国的真相:中日学者共同研究》,181-18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6)参见《支那学》1卷1号—1卷3号,1920年9月—11月。
(7)清水安三(1891—1988),为《北京周报》的投稿人,通过投稿与鲁迅有所交流。1924年将其撰写之散文整理出版《支那当代新人物》及《支那新人与黎明运动》两本著作,是大正時期鲁迅作品在日本的传介的先道者之一。参见藤井省三:《鲁迅:东????を生きる文学》,156页,东京岩波书店2011年版。
(8)参见铃木将久:《竹內好与〈鲁迅〉》,收入徐秀慧、吴彩娥主编《从近代到后冷战亚洲的政治记忆与历史叙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73-90页,台北里仁书局2011年10月初版。
(9)古丁:《鲁迅著书解题》,后收入李春燕编《古丁作品选》,529-563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0)对此,黄万华也在《古丁文学创作论》中有过相同的主张,他提到:“古丁编译的《鲁迅著书解题》,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如此全面地向无缘读鲁迅著作的东北读者介绍了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诗乃至日记,还在于它向‘在无声里偏要私语的东北作家们提供了一种精神支柱、民族力量。”收入李春燕编:《古丁作品选》,643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1)《明明》停刊之后,原《明明》社的同人:古丁、辛嘉、疑迟、外文、百灵于1939年8月组成诗歌刊行会,文学主张上承继古丁一贯的写印主义,共出版了古丁的《浮沉》(散文诗集)、小松的《木筏》(诗集)、百灵的《未明集》(诗集)、成弦的《青色诗抄》(诗集),此诗歌刊行会的同人们更在同年10月组成了艺文志事务会,出版艺文季刊《艺文志》。
(12)参见史之子(古丁):《大作家随话》,收于《明明》第1卷5期,1937年7月。
(13)黄玄在《古丁论——文学“乌托邦”梦者的悲剧》一文中,便指出:(古丁)“这种‘不可为而为之的拗劲,就近于鲁迅那种‘明知前面是坟,而偏要走的烈性。他主张凡是有志于文学的人,便应有‘私淑的毅力。从他出奇的杂文看,在那暗云低迷的文艺界能闪出若干亮点,便看出他多年来曾私淑过鲁迅文风。”见李春燕编《古丁作品选》,56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从他提倡的“无方向的方向”“写与印”等文艺理念,也可看出其对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的继承。
(14)《艺文志》除了有来自城岛舟礼的民间文化人的资金外,此外从1940年5月、1941年1月的《满日文化协会纪要》,以及满日文化协会理事长荣厚给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三谷隆幸部长的文书中可以知道,《艺文志》也接受了官方性质的满日文化协会的补助,1941年《满日文化协会纪要》中关于文艺的部分指出:为了振兴满系文学,必须对《艺文志》等的满系青年文学团体给予后援(从1939年以来)。参见石田卓生:《〈艺文志〉と满日文化协会》,见《中国东北文化研究の広场——《满洲国》文学研究会论集》第1号,2007年9月,15-19页。作为满洲文坛代表的古丁企图通过日本的补助达到文学推动的目的,一方面官方也想利用古丁在满洲文坛的号召力,进行对满洲文坛的收编工作,在此双向的思考下,《艺文志》也在这种双方立场下创刊。
(李文卿,日本名古屋外国语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