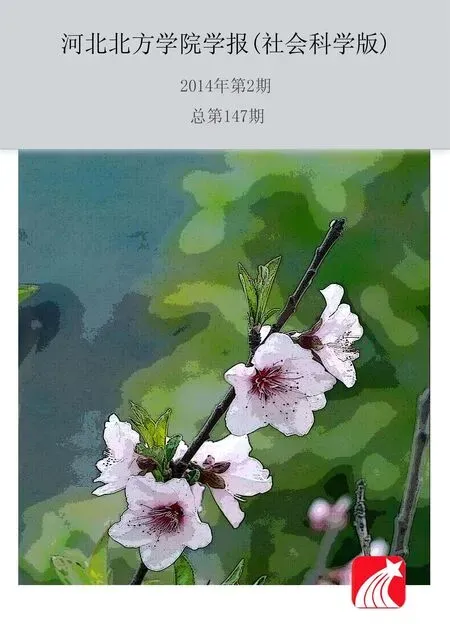罪犯危险性评估研究综述
何 川,马 皑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100088)
罪犯危险性评估研究综述
何 川,马 皑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100088)
如何预防犯罪,是人们始终关注的问题。而罪犯危险性评估,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手段。在回顾、比较中西方危险性评估的理论发展与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尝试总结一些影响评估准确性的可能因素,分析指出中国应当建立“分类矫治为主、统计分析为辅”的评估模式,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西方差距,提高评估准确性,降低再犯率,以保护社会利益、实现社会安定。
罪犯危险性;评估工具;分类矫治;暴力预测
网络出版时间:2014-03-28 17:40
罪犯的人身危险性概念最初源于犯罪学和刑法学领域。刑事古典学派基于理性假设,强调个体的主观决策过程,认为犯罪源于个体独特的认知加工方式,是否实行犯罪行为是可以通过主体的“自由意志”来控制的。反之,如果个体的行为对社会造成了实害结果,也就可以说明其具有主观上的“实害”。因此,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只需要考量行为的社会实害结果即可,犯罪主体的主客观因素是统一并相互应证的。而刑事实证学派的代表龙勃罗梭认为,人们犯罪是由于生物学因素的异常,从基因、遗传的角度出发,发现犯罪人在颧骨、脑型等生理构造方面和正常人存在很多差异,据此提出了“天生犯罪人”思想;加罗法洛则将犯罪原因归为行为人心理因素的异常,如缺乏道德感、仁慈感和正义感。“无道德异常,就无自然犯罪”(no moral anomaly,no natural crime)。犯罪的本能(crime instinct)或是道德异常不是疾病,而是一种心理偏离(psychic variation)。对精神病人而言,对外部的知觉引起了扩大的印象,这种印象又导致了与外部原因不相符的心理过程,精神病人的犯罪便产生了。缺乏道德的人则是由于扩大的自尊、过分的虚荣和极端的敏感性。与古典学派相比,实证学派认为“该处罚的不是犯罪行为,而是犯罪行为人”,人们开始关注行为人自身的特质同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人身危险性研究最初的起源。
中国刑法学界现行通说观点认为,人身危险性的基本含义是犯罪行为人再次实施犯罪的危险,即再犯可能[1]205。故而人身危险性又被成为“再犯可能性”。而社会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重点关注的个体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对他们进行干预矫正以减小这种可能性(Monahan,1995;Monahan &Steadman,1994)。研究表明,现在国外对于罪犯危险性的研究,开始越来越关注对于犯罪人的矫治过程、矫治效果的评估。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具有国家强制力性质的刑罚在本能的、冲动的报应中难以完整表达它的目的性,刑事立法与司法都有必要体现一般和特殊预防的需要”[2]359。刑罚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对犯罪人实施惩罚,“消除犯罪所引起的罪恶”,更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阻止有罪的人再使社会遭受到危害,并制止其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3],并通过帮教、感化等手段,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Beck &Bemand(1989)通过档案分析发现,5%的犯罪人要对45%案件的发生负责;同样,Farrington(1996)的研究也显示,在所有案件中,有将近一半是由6%的犯罪人完成的。这一现象表明,通过对高危险性犯罪人的有效识别和管理,是可以显著减少社会的犯罪率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各国学者开始了相关问题的探讨,研究个体特别是特定服刑人员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危险性程度如何等问题,并且形成了一系列评估手段、方法。从心理学角度而言,Paul Meehl(1954)将危险性的评估方法归纳为两种:一是临床判断法,即通过生活常识以及心理学家、假释官的经验,来对罪犯的危险性进行评估。但这种方法的主观性过强,没有一个标准化的鉴定标准,评分者一致性信度较低,在实际司法活动中预测力也不理想(Stephen,1998)。二是精算法:评分者根据固定的标准,利用已有信息,采取统计学手段,通过访谈和调查,提取出影响再犯的因子,并对这些因子进行加权处理,建立一个系统的评估体系。这种方式又被称为“机械式”或者“算数式”方法(Grove &Meehl,1996)。除了常见的通过相关求得预测效度之外,Harris等人借鉴了信号检测论的方法,利用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ROC)来进行评估,在找出高危险性罪犯的同时,尽量避免冤枉无辜者。总体而言,在假释决策及风险评估方面,精算法要优于非结构化方法(Monahan,1981/1995)。
不论是临床法还是精算法,危险性评估都需要分为如下4个过程:一是识别实证性风险影响因素;二是确定这些因素的测量/计分方法;三是建立一个将分数与风险因素相结合的程序;四是对犯罪人的危险性水平作出预测判断。
一、西方危险性评估理论及发展
虽然危险性评估进入司法心理学的视野较晚,但是自史德曼和科库扎(Steadman &Cocozza)的《精神病人犯罪人的生涯》(1974)一书出版以来,西方心理学界对于暴力行为倾向预测的热情空前高涨。阿根廷的拉普拉特在2011年实施了“风险评估试点项目”,在当地法院的申请下,通过HCR-20、PCL-R和VARG,对65名有假释资格的罪犯进行了评估;日本成立了“专门监督官特别队”,对缓刑、驾驶者进行再犯风险评估;英国研发出了“犯罪人需要评价量表”,根据量表得分划分风险程度并将不同风险的犯罪人划分为高、中、低3种监管等级。
短短的几十年间,危险性评估就已经有了4代成型的评估工具,并且以David Nussbaum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正在开展第5代评估工具的研发工作。通过荟萃分析发现,大部分评估工具的预测效度在r=0.2~0.4之间(Gendreau,Little,&Goggin,1996)。

表1 各代评估工具的评价预测效度
通过表1不难发现,虽然评估工具的预测效度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从最初的0.1提高到了0.4左右,但是整体而言效果仍然不够理想。危险性评估的预测效果如何不仅涉及社会安定,还关乎到犯罪人是否受到了公正对待,将其视为危险性评估的核心问题并不为过。
(一)第一代评估工具
第一代评估工具基于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的观察和临床经验,通过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访谈,来收集再犯原因的相关信息,将罪犯评定为“有危险”和“无危险”两种情况(Holsinger et al.,2006)。虽然,危险性评估有一段较为漫长的历史,但是人们似乎并不太关注临床学家们的评估效果如何。直到史德曼和科库扎(Stadman &Cocozza,1974)对强尼·博克斯东(Johnny Baxstrom)的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之前被关押的1 000名精神病人中有966人的暴力倾向被错误高估,人们才意识到之前临床学家对于暴力行为的预测结果并不可靠。但由于评估缺乏系统性和客观指标,通常预测信效度结果都很低。
针对上述问题,Webster、Eaves和Wintrup(1995)基于实证研究,选取了10个关于过去评价的影响因子(暴力行为史、就业困难、精神病态、人格障碍等)、5个目前的表现因子(负性态度、冲动、对矫治的不配合等),以及5个未来导向的预测因子(缺乏计划性、缺乏社会支持、压力等),共同组成了今天应用甚广的“HCR-20”。每个项目都以0、1、2计分,最后统计总分来判断危险性的高低,Dahle(2006)发现,得分超过20分的犯罪人的再犯率达到了68%。总体而言,HCR-20的预测效度在0.1~0.2之间,信度在0.8以上[4]。
(二)第二代评估工具
针对HCR-20在预测效度上存在的严重问题,研究者们开始采取统计学的方法,基于实证研究,选取已经被证明的会影响再犯的因素作为评估指标。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精算式评定”。根据个体过去的劣迹史,如酗酒、物质滥用等因素,来判断一个罪犯的危险性。它的基本假设同保险制度很类似:如果一个人过去有过越多的危险行为,那他在未来做出相似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危险性也就越高。Menzies和Sepejak(1985)基于上述假设,遴选出12个主要考察因素,建立起“危险行为评估方案”(dangerous behaviour rating scheme,DBRS)。在这一时期,最常用的工具是“病态人格检索表(PCL-R)”和“暴力危险性评估指南(VRAG)”。
Hare教授基于Cleckley研究的基础,制定出了PCL-R及其操作手册,被认为是“评估精神病态的黄金法则”[5]429-431。虽然PCL-R的设计初衷是考察反社会人格,但是实践表明,反社会人格同暴力预测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Douglas(1999)的研究就发现,PCL-R得分超过8分的个体,更有可能产生暴力行为。因此PCL能够作为罪犯危险性评估的可靠标准。PCL-R量表包含了“巧言令色”、“病态性说谎”、“无责任感”、“自我控制能力差”、“情感冷漠”、“易于冲动”等20个项目,每个项目以0、1、2计分,最后对总分进行评定,分数越高表明其危险性越大。它对2年、5年、10年后罪犯再次入狱的预测力分别为0.31、0.32和0.34,并且得分超过16分的个体的再犯率达到了74%(K.P.Dhale,2006)。总体而言,PCL-R的预测效度为0.27;VRAG则是由研究人员通过统计分析,总结出了酗酒、以前假释失败、非暴力犯罪史等12个预测项目。对罪犯进行了15个月(Quinsey,2002)到10年(Rice &Harris,1995)的追踪后发现,VRAG对于再犯预测的准确率在0.22~0.57之间(Rice &Harris,1995)。
但是第二代评估工具仅仅考虑静态因素,而忽视了动态情境的作用以及在押人员的改造需求。静态因素是指那些历史性的、不易改变的、干预治疗无效的因素,包括之前的暴力史、罪前的物质滥用情况、初犯年龄等。举例而言,一个强奸犯过去有过多次犯罪,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生理机能等指标逐渐下降,其危险性应当是有所降低的,但第二代工具却基于其过去行为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因而其预测力是有待验证的。
(三)第三代评估工具
第三代评估工具同样基于实证,但同第二代不同的是,它同时将静态因素和动态因素作为评估指标。经过大量相关文献的整理,Douglas &Skeem(2005)总结出了7个稳定的动态因素:冲动性、他人负面影响、精神病态、反社会态度、当前物质滥用情况、人际关系障碍以及对治疗的不配合。通过反复、多次评估,反映出在押人员危险性的变化情况。
第三代评估工具基于RNR(risk-need-responsivity)理论模型,根据在押人员再犯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犯罪原因和改造需求,培养他们的人际交往、挫折应对等技能。Andrews &Bonta(2003)根据RNR模型提出了他的“大八理论”(the Big Eight),认为反社会态度、犯罪同伙、反社会行为史、反社会人格、家庭问题、工作及学校问题、休闲方式异常、物质滥用,是暴力犯罪的有效预测因子,并且针对每个风险因素提出了矫治目标和手段。

表2 再犯主要影响因素及犯罪人需求
注:除上述因素外,还包括:人格障碍和情绪障碍、精神疾病、机体健康水平、害怕刑罚、智商、社会阶层、罪行严重性等。
第三代评估工具中,最常用的是“水平评估量表”(LSI-R)和“威斯康星危险性评估工具(WRNAI)”。LSI-R共有54个问题,分为犯罪史、教育/就业、经济状况、家庭/婚姻、物质滥用、情绪/人格、态度取向等10个分量表,根据总得分将罪犯分为低度危险、中度危险和高度危险3个等级,实证研究发现,总体而言,LSI-R的总体预测效度为0.36,对于暴力犯罪的预测效度为0.25(James Bonta,2006)。
WRNAI由Baird和Heinz(1979)编制,包括酗酒、初犯年龄、一年内就业时间百分数等11个问题,每个问题有3个选项,每个选项依据其权重计分,最后根据总分判断其危险性。Andrews(2006)在对信效度资料进行总结后发现,LSI-R对于再犯预测的准确度达到了0.36,略高于前两代工具。
风险—需求评估工具,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Andrews &Bonta,2003)。但是,动态因素也存在着缺陷和风险。计划和现实关系的不稳定、狱中成瘾物质的缺乏、缺少人格支持、对治疗的不配合以及应激等因素,都可能造成风险评估的偏差。
(四)第四代评估工具
第四代工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犯罪人给予更有效的改造和治疗,以保护社会免遭再犯危害(Andrews,2006)。Harris(1999)通过调查发现,经过治疗的犯罪人比未经治疗的犯罪人风险性更低,这说明第四代评估—矫治工具是有效的。
COMPAS(Brennan &Oliver,2000)是第四代工具中最常用的一个,它被用来评估罪犯的风险及需求,进而为社区矫治的罪犯安置提供决策依据。同其他工具仅仅提供一个总体的风险分数不同,COMPAS对暴力、再犯、拒绝出庭和社区矫治失败都分别进行评估,其中犯罪史、罪犯需求、态度、社会环境、社会化、犯罪机会、犯罪人格及社会支持都是需要评估的重要内容。Brennan &Oliver(2000)通过对241名纽约缓刑犯的追踪研究发现,COMPAS对于再犯预测有着很好的预测力(r=0.79)
LS/CMI(Andrews,Bonta &Wormith,2004)是另一常用工具,它在设计时考虑了诸多尚未被测量的风险因素以及影响矫治的人格因素,并与干预和监控措施系统的结合起来。经检验,LS/CMI对于整体犯罪的预测效度为0.41,对于暴力犯罪的预测效度为0.29。
(五)第五代评估工具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同样是暴力犯罪,但它也可能表现为不同的形式。David Nussbaum &Bell(1997)将攻击分为了掠夺型攻击(predatory aggression)、激惹型攻击(irritable aggression)和防御型攻击(defensive aggression)3种类型,不同的攻击类型具有各自的神经递质特点(Nussbaum,1997)。而现有评估方法多采取问卷形式,并且几乎没有考查神经因素,这就需要通过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针对这一问题,David Nussbaum教授主张,通过脑电等生理仪器来探求犯罪人神经递质、人格等个体差异,从而对症下药、实现分类矫治。已有研究表明,神经和人格变量能够有效区分暴力犯、非暴力犯各自的特点(Levi,2004;Nussbaum,Watson,Levi&Ax,2005)。脑电等设备虽然精确度高,但价格过于昂贵,并不适于大范围推广。
除去脑电,另一常用评估手段就是爱荷华赌博实验(IGT)。研究表明,个体在实验不同阶段受到不同神经递质的影响,例如获得阶段(acquisition phase)个体受到多巴胺影响,而在保持阶段(maintenance phase)则受到血清素影响。Van Honk(2004)也发现,即时奖励聚焦(immediate reward focus)同睾酮水平直接相关,而同皮质醇则是负相关关系。这些发现表明,心理学家是可以通过IGT来对个体信息加工进行评估的。这一结果可以通过EEG检测,并且是药理特异性(多巴胺—血清素平衡)、内分泌功能(睾酮和皮质醇)的反映。这些发现的重要性在于,上述神经递质,包括5-羟色胺在内,对于冲动型暴力犯影响巨大,而通过爱荷华赌博实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的激素水平,因此也就具备了再犯预测、控制,以及分类矫治的可能性。人的行为具有一致性,如果他在IGT中更多地表现出冲动行为和不理智行为,那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冲动犯罪的可能性自然也就较大。
二、国内危险性评估研究进展
在理论层面,中国对于再犯可能性最全面、最系统的研究,是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于1992年出版的《中国重新犯罪研究》,通过专家的经验性总结,提出了影响刑释人员再犯的可能性因素及其动机。但由于缺少实证数据和科学手段的支持,也没有提出如何对再犯可能性进行评估,对于中国的司法实践的意义并不是很大。由此可以看出,国外研究大多采取定量分析,而中国则更多的选择定性分析。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将“态度评价”(如是否认罪伏法)代替人身危险性评估的错误做法。态度作为内隐变量,是可以通过伪装来造成司法工作人员判断失误的,具有很高的主观性,可信度较差。
在司法实践中,中国监狱系统通常会在犯罪人入监的时候,建立罪犯入监登记表,内容除了姓名、性别、籍贯、罪名、刑期等基本信息外,还包括犯罪人的简历、主要犯罪活动、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以及同案犯资料,希望可以借此对犯罪人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改造和社会帮教。然而事实证明,入监登记表并没发挥出预期的作用。北京市顺义区法院(2010)对1-10月的被告人调查后发现,犯罪人的再犯率达到了10%,这是因为在现有制度下,以在押犯的劳动量、卫生等积分指标作为减刑依据,证明其主观恶性逐步减少、“确有悔改不致危害社会”,显然是不科学的。出于伪装、被迫遵守规则等原因,很多犯罪人都能做到表现良好。但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脱离了监所环境,表现良好才能获得的积分已然失去了强化物的效用,同时由于刑期压力和狱警监管的丧失,犯罪人此时不再需要做出遵守规则的行为。此外,中国的矫正采取的是“劳动改造”模式,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希望通过生活技能、劳动技能的培养,来建立犯罪人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这种改造模式,对因缺乏技能而谋生困难的犯罪人较为有用,而对精神病态、反社会人格、冲动型犯罪人却可能并不适合。也就是说,国内的分类矫治工作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刑法学视角下,通过传统的积分制度来判断在押犯是否悔改,进而确定其危险性的方法缺乏科学性,一场新的方法变革势在必行。心理学除了能描述和解释现象,更注重如何对其进行预测和控制,这同刑罚的目的殊途同归。无论是古典学派的客观归罪、惩罚犯罪行为,还是实证学派的主观归罪、惩罚犯罪人,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行为人这个中心,行为是由特定人所实施的。人的心理是一个“黑箱”,无法直接观察到,这也是入监登记表、积分制度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所在。而心理学可以通过内省、实验、心理测验、心理调查、心理统计、口语报告等多种方法,打开这个“心理黑箱”,了解犯罪人内心深处的需要、动机、人格特征,进而确定其危险性。
许多学者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章恩友教授认为,再犯预测评估体系的建立,应包括在押人员自评量表、他评量表和实验模拟3个主要手段,主要考察在押人员的掩饰倾向、个性特质的变化、社会适应水平、改造质量等方面,通过评定计算出罪前和最后这些因素的一致性或者差异,来确定在犯罪概率[6]218。
邬庆祥在对1.5万名刑释人员调查后,筛选提取出了14个同再犯显著相关的因素,编著出了《刑释人员个体人身危险性量表》,并用多元回归法进行再犯预测,“刑释人员人身危险性标志值P=性别× 0.081+文化程度×0.034+捕前职业×0.012+婚否×0.01+罪名×0.077-刑期×0.007+剥政× 0.033+前科次数×0.11063+离监类型×0.065+改造×0.074+就业×0.155+帮教情况×0.2042-逮捕年龄×0.032-释放年龄×0.024-7.379。(P值介于0~1,表示犯罪人再犯可能性大小)。经检验,其准确率为92%[7]。
上海监狱局也制定了《违法犯罪可能性量表(修订版)》,来对假释、减刑、监外执行的犯罪人实施危险性预测,有效率达到了85%以上[8];此外,黄兴瑞(2004)也对700余名犯罪人进行了调查,通过统计学手段,总结出了婚姻状况、有无稳定工作等12个与再犯显著相关的因素。陈伟(2011)将评估分为罪前、罪中、罪后3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因子,对这些因子进行权重处理后按照1~5分进行打分,参考总分来判断其人身危险性。曾赟(2011)根据对浙江省不同类型监狱的1 238在押犯的调查统计结果,提取了11项再犯预测因子,创建了罪犯出监前重新犯罪风险预测量表(RRPI),量表总体正确判断比率达86.3%,数据拟合度较好[9]。
然而即使有了如此多的成果,中国的罪犯危险性研究现状,仍然大致停留在西方第一代、第二代工具水平上,差距十分明显。如何探索出适合中国的一条道路,是需要思考的重点。量表测试本身就有其局限性。虽然可以通过多次施测,来考查动态因素的变化,但是一个量表一旦被制定出来,其项目内容在一段时间内就是相对固定的了,考查的风险因素也就成为了一个固定的机械程式,缺乏灵活性、变通性,容易忽略其他风险因素的影响。学界如此重视罪犯危险性评估,归根到底就是为了预测、防止犯罪人进行再犯。因此,与其痛苦地寻求再犯影响因子,还不如直接从目标出发,通过David Nussbaum教授提到的IGT、脑电等工具,对罪犯进行分类管理、分类矫治,“分类矫治为主,统计分析为辅”。以此来实现跳跃式发展,缩小与西方差距,找出适合中国本土的危险性评估方法。
三、影响评估准确性的因素
(一)工具项目本身
首先,现有工具过多地关注于一小部分已被普遍证明的预测力极强的因子,而忽视了个体差异。精算式评估可能包括一些法律领域之外的因素(性别),而将某些预测效度不明但是却很符合逻辑的因素(杀人意图)排除在外(Hart,1996)。其次,一些评估工具只在特定时期、特定人群才有最佳的预测力(Gottfredson,1986),将其生硬地应用到其他环境中去,可能会造成不合适甚至可笑的结果(Hart,1996;Lyon,1997)。文化差异、社会发展、社会经济水平、地理环境等因素,都是学者需要考虑到的问题。
此外,暴力行为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及目的动机,但是现有的评估工具并不能够将其区分开来。正如前文所以,攻击行为有3种表现形式,它们各自的产生机制和需求不一样,预测指标自然也就不同,而这正是现有工具所忽视的重要问题。Patrick和Zempolich(1998)发现,PCL-R各因素得分都很高的个体,他们的犯罪动机并不唯一,可能是由于一种习惯倾向,也可能源于攻击他人的欲望,还可以是出于自卫的目的。现有量表工具并不能将不同类型的罪犯区分开来,分类矫治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二)犯罪人的掩饰
目前的评估方法主要有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和行为观察法。这些方法都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缺陷,就是犯罪人此时已经被收押,为了避免惩罚和获得减刑机会,他们通常会通过伪装和虚假作答,来证明自己已不再具有危险性,即使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这种情况在精神病态犯罪人身上尤为明显,Skeem(2003)发现,精神病态犯罪人通常欺骗性很强,甚至有些人在同他们接触后会认为他们极其具有魅力,而对其言听计从。
针对这种情况,既可以通过使用迫选问题,也可以学习《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藏入测谎问题,还可以通过Nussbaum使用的眼动、脉搏、唾液等测谎技术来检验在押犯是否说谎。
即使犯罪人并未有意去掩饰欺骗司法工作人员,也仍然存在着其影响工作人员判断的因素。在监狱中,毒品等成瘾物质并不容易得到,在对犯罪人进行评估时这些成瘾物质也并不会呈现在他们面前。而当他们出狱后,这些成瘾物质确是可以通过很多途径获得的,这时候犯罪人的危险性显然有了较大的提高。因此,评估环境和现实环境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影响评估准确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性别差异
虽然为了更好地预测罪犯的再犯可能性很多评估工具都得到了改进和修订(例如HCR-20,Webster,Douglas,1997;VRAG,Quinsey,Harris,1998),但是大多数工具在制定的时候,通常都是以男性为样本来采集信息,取样偏差造成了预测结果的局限性。Harris等人(2002)的研究就发现,VRAG对于女性的暴力犯罪并不能够有效预测。此外,男性和女性在很多层面也存在着差异。
首先,在犯罪类型上,女性罪名多为挪用公款等(FBI,2006),即使是暴力犯罪,侵犯对象也多为家庭成员,而不是陌生人,在实施暴力行为时也不存在醉酒情形(Greenfeld &Snell,1999;Robbins,Monahan,&Silver,2003)。其次,女性的风险因素可能同男性不同。同样一个事件,对于男性而言不能称之为再犯影响因子,而女性一旦经历,其犯罪的可能性将会显著提升。例如,童年被虐待经历,在女性罪犯中更为常见,女性遭受性虐待的概率是男性的5倍(26% vs 5%)(McClellan,Farabee,&Crouch,1997;James&Glaze,2006)。在精神疾病方面,女性的患病概率是男性的两倍(Hodgins,Lapalme,&Toupin,1999),而一旦患病,女性出现暴力犯罪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Robbins,2003)。
四、启示与展望
经过4代工具的发展,罪犯危险性评估的信效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即使评估工具再精确,其预测力也不可能达到100%。现代科学强调事物的复杂性,任何一个环节细微的变化,都可能造成结果的不同,“混沌理论”、“蝴蝶效应”表明的就是这一道理,罪犯人身危险性评估也不例外。它能够总体上判断罪犯危险性,但是由于监内环境和生活环境的不一致、社会发展、文化差异、监内负性家庭事件、出监后个人发展前途等诸多环境因素的不确定性,以及犯罪人个体之间在认知、态度、信念、动机需求等心理特征存在差异、并非同质,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都有着不可控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每个人的思想也都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这在客观上造成了预测结果存在着偏差的可能。这给学界带来重要启示:对犯罪人的评估绝不是一劳永逸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借鉴加拿大相关机构的经验,定期、多次对犯罪人重新进行评估。
其次,在现有工具的修订和发展上,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期。研究者可以通过引入一些新的评估方法来提高预测力,比如内隐态度的测量(Nock,2010)和启发式方法(Goldstein &Gigerenzer,2009)。并且随着犯罪防控需求的逐渐增大,日后研究重点应当从再犯可能性大小的预测,逐步转向对于个体犯罪原因的探索,以及如何对罪犯进行有效矫治,使其回归社会、防止再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正如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所言,“受奴役的人比自由的人更加纵欲、放荡和残忍”,因此犯罪预防的价值取向是保护公民自由,而不是以刑罚或形势政策来限制和剥夺公民的自由[10]。
[1] 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立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 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3] 耿丹樱.人身危险性的评判和量刑研究[J].宿州学院学报,2008,(5):25.
[4] 王成奎.暴力风险评估的研究[M].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6,(10):1186.
[5] Acheson.Review of the Hare psychopathy Checklist revised[J].The sixteenth mental measurements yearbook,2005,(2):429-431.
[6] 章恩友.罪犯心理矫治[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
[7] 邬庆祥.刑释人员人身危险性的测评研究[J].心理科学,2005,(28):222-224.
[8] 胡庆生.行刑方式的文明进步——上海市积极拓展社区矫治新空间[N].法制日报,2003-08-04(8).
[9] 曾赟.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前重新犯罪风险预测研究[J].法学评论,2001,(32):131.
[10] 周胜蛟,曾赟.论犯罪预防的价值范畴——关于个人自由之保护的一种解读[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5(2):4.
Research Overview on Criminal Risk Assessment
HE Chuan,MA Ai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How to prevent crimes is an issue that people are always concerned about,and criminal risk assessment is a most important means to solve this problem.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and comparing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juridical practi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the paper makes an attempt to summarize some of the affecting factors on the veracity of assessment,and points out that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n assessment model which is“based on classified correction and supplemented by statistical analysis"to achieve leapfrogging development,narrow the gap with the West,improve the accuracy of evaluation,reduce the recidivism rate,and realize the goals of protecting the socil interests and achieve social stability.
criminal risk;assessment tool;classified correction;violence prediction
D 90
A
2095-462X(2014)02-0067-07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40328.1740.039.html
(责任编辑 薛志清)
2013-12-2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2YJAZH088)
何川(1989-),河北石家庄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犯罪与司法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