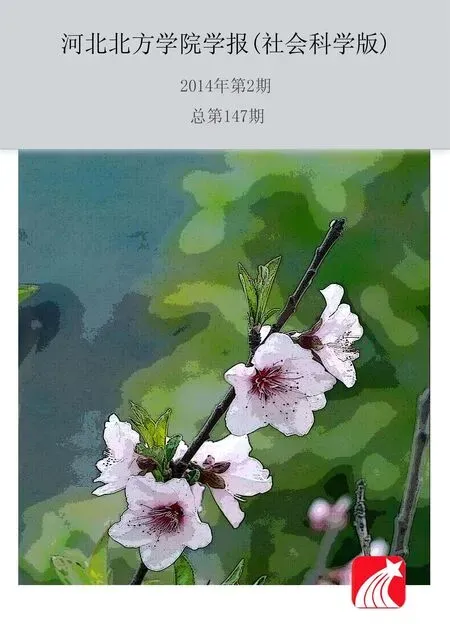清顺治年间“泛滥投充”现象探析
李立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清顺治年间“泛滥投充”现象探析
李立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清初多尔衮擅权,欲借“泛滥投充”之乱局,实现削弱皇权、稳固统治的目的,成为清初“威逼投充”与“带地投充”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顺治帝亲政后,在投充问题上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使这一现象得到初步遏制,但顺治帝本人也是投充政策的受益者,其所出台的制约措施,不过是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的一种权宜之计。故而“泛滥投充”之风平息一时后,于康熙中期又逐渐在社会上蔓延。清初皇权与八旗诸王间围绕投充问题所产生的权益冲突,本质上反映的则是八旗领主制与封建专制主义君主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投充;皇权;王权
网络出版时间:2014-03-28 17:39
一、多尔衮擅权与投充之泛滥
清初制定了一项准许汉人投充于满洲旗下为奴的政策。据刘余祐《请革投充疏》中称,清初投充“起于墨勒根王许各旗收投贫民,为役使之用”[1]卷92。墨勒根王即清太祖第十四子多尔衮,以其从征蒙古而赐封“墨勒根戴清”(意为聪明主)。然考《满文老档》“天命六年十一月”条曰:“有不愿在汉官辖下而愿依赖诸申过活者,无论何人均可前来。”[2]255这里的“诸申”即主要指满洲贵族。据此,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即有汉人投充满洲者,其时投充人数寥寥,尚未形成定例。
自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廷开始了3次较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致使劳动力严重不足。为此,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摄政王多尔衮谕户部曰:“又闻贫民无衣食,饥寒切身者甚众。如因不能资生,欲投入满洲家为奴者,本主禀明该部,果系不能资生,即准投充。”[3]133解决贫民衣食问题,不过是清廷的冠冕之词,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为了解决满洲贵族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由此,投充政策在清廷内外得以大规模推行。
然而这一政策甫行即弊端丛生。一些满洲权贵为争抢劳动力,有威逼汉人投充者。据史载:“距京三百里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庄村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逼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以致民心不靖,讹言繁兴。”[3]140一些平民也因土地被圈占而被迫投充,孙家淦便道:顺治初年“民人投充旗下,原非得已,或地已被圈,无处栖身,乃投充以种地。或地尚未圈,恐被霸占,因投充以保家”[4]卷6。
对于那些既有土地,又有劳动力的汉族地主,满洲贵族则以免除他们所承担的国家赋役为诱饵,凡投充满洲旗下者,均可“既免完粮,又得种地”,故一些汉族地主也借机“带地投充”。如怀柔县有“将民地投入旗下,名曰带地投充,其始不过借旗名色,希免征徭,其地仍系本人为业”[5]92。甚至“将他姓地土,认为己业,带投旗下者;一人投充而一家皆冒为旗下,府县无册可查,真假莫辨”[3]508。“带地投充”后的地主又可凭借带地数量之多少,充当满洲旗主庄园内的大小庄头,自身又可借“旗主”之权势,横行乡里,以致“有司畏威而不敢问,大吏徇隐而不能纠”[6]卷1,可见其势力甚大。一些“无赖游手之人”也巧借投充,“夺人之田,攘人之稼,其被攘夺者,愤不甘心,亦投旗下,争讼无已,刁风滋甚”[3]216。由此,形成了“汉人不论贫富,相率投充”[3]257之乱局。
一方面是“威逼投充”与“带地投充”之乱象,另一方面清廷却对当时投充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多尔衮谕诸王曰:“其新附军民,力能自赡者,宜各安本业,不许投充势要,甘为奴仆。如有奸棍土豪,自知积恶,畏惧有司,因而委曲钻营,结交权贵,希图掩饰前非,仍欲肆志害民者,定行加等重治。”[3]69同年,又规定:“凡旗下汉人,有父母、兄弟、妻子情愿入旗同居者,地方官给文,赴部入册,不许带田地投充。”[7]卷156明确禁止带地投充。顺治二年(1645年),又称:“凡包衣大等新收投充汉人,于本分产业外妄行搜取,又较原给园地册内所载人丁有浮冒者,包衣大处死不赦。”[3]122三月,又下谕曰:“此后有实不聊生,愿投者听,不愿投者,毋得逼勒。”[3]135顺治四年(1647年)又曰:“自今以后,投充一事,著永行停止。”[3]257然而,投充不但没有废止,反而愈演愈烈,这几道谕旨最终不过是一纸空文。那么,清初投充为何如此泛滥,以致渐成尾大不掉之势?笔者认为,这是与顺治初年的政治形势紧密相关的。
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崇号,顺治帝在晋封册文中称,多尔衮“靖乱定策,辅翊幼躬,推诚尽忠,克全慈孝;中原赖以扩清,万方从而底定,有此殊勋,尤宜褒显”[3]98。在这溢美之词的背后,隐讳的是皇权之衰微。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后,不仅掌控了批票本章之权,而且诸朝政“刑政除拜,大小国事,九王专掌之”[8]282,足见其权势煊赫一时。但多尔衮对权势的掌控,也不过是逞一时之威,因为他要待福临成年后,当即归政。这便使其对自己的专权要“从长计议”。为此,拉拢诸王大臣,削弱皇权是多尔衮的首要之务。而清初满洲王公大臣在经济上的重大利益需求,就是如何解决圈地后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多尔衮欲以“投充”为筹码,来赢得诸王大臣对其专权的持久支持,时云南道监察御史杨世学便云:清初之投充“皆系睿亲王(即多尔衮)独占皇上之农民,以投充为名,投各大臣之所好,使有田舍者,亦尽行投充,因此争端不止”[9]73。一语道破了多尔衮借助投充,以迎合满洲权贵的企图。
在多尔衮看来,“泛滥投充”还是削弱和制约皇权的一种手段。据学者统计,清初八旗王公大臣在畿辅地区共占有280余万亩投充地,无地投充为奴的人数近5万人。这些投充田地、人丁,均不在国家纳税范围,“一人离去,君寡一丁之税。一地投充,君减一地之赋”[9]73。当时的一些投充者“将他人之地,无论同姓异姓,其地尽附于己以献主,多多益善,于是以旗移部,令其于本地方除丁粮之籍,赋税不归于公家矣”[10]卷3。一些王公大臣甚至将投充地亩隐匿。“国家纳税之疆土,匿为一己之私壤,租课不归公家,有司莫敢谁何。如此欺罔,尚知有朝廷乎?”[9]69可见这种“泛滥投充”的弊端之一,便是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福临作为此时的皇帝,在名义上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其对国家收入的掌控减少,就意味着行使权力的减弱。而满洲权贵大肆接受“带地投充”者,造成国家收入的减少,这势必又会在皇帝与满洲贵族之间产生权益冲突。这又为多尔衮所利用,在两者之间坐收渔利,从而形成对皇权的约制,为其进一步实现专权统治奠定基础和保证。而如何有效地治理“泛滥投充”之乱局,也就成为顺治帝亲政以后不得不面对的当务之急。
二、顺治亲政后对泛滥投充的约制措施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摄政王多尔衮暴病身亡。次年正月,福临在太和殿宣布亲政。顺治帝亲政伊始,就对“泛滥投充”的乱象进行了整顿。他首先将矛头指向了多尔衮家族,彻底清查其违规投充地亩、人丁。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十六日,谕户部曰:
汉人投充旗下,原令穷民借以养生,又恐多投,以致冒滥,是以定有额数。乃睿王所收人数已足,又指称伊子多尔博名下,亦应投充,遂滥收至八百之多。且有借势投充,遂占人田地者,甚属不合。尔部即查多尔博投充人役册,逐名开写,发回该州县,与平民一体当差。其投充人本身田地,仍著留给,如有带投他人田地者,俱著查明,归还各原主为业。[3]467
这道谕旨严查了多尔衮父子所接收的违规投充者,令其“与平民一体当差”,恢复了其“民人”身份;将带投他人之田“归还各原主为业”,使原“旗田”转而成为“民田”,意味着这些人丁、田地又重新恢复了向国家纳税的义务。继此之后,又再次纠察出多尔衮父子所领庄内的假冒投充者。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二十八日又谕户部曰:
今又闻其指称庄内人数不足,滥令投充至六百八十余名。夫庄内人数不足,亦止可收贫乏无业者,用以力农,乃所收尽皆带有房地富厚之家,殊属不合。尔部查照投充原册,逐名开写,发还各州县,照例纳粮应差。其中或有带投他人房地者,俱严责各地方官,确查明白,归还各原主为业。[3]472
这680多人的富户之所以投充多尔衮父子,主要还是为逃避赋税,而多尔衮父子亦可借富户投充所带来之人丁、田地,满足其日益膨胀之经济需求。顺治帝清查后,将其“发还各州县,照例纳粮应差”,既有效地打击了多尔衮家族的经济实力,同时又使国家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从中亦折射出皇权的与日俱增。
这种清查和收缴违规投充地亩之风还蔓延至京畿各州县。据乌廷玉先生的统计,清初仅在顺天、永平、河间3府收缴多尔衮的投充地亩有150余万亩。同样是以上3府,收缴的其他满洲诸王的投充地亩却仅有30余万亩[11]93-95。可见顺治帝已将“投充”作为打击多尔衮家族的手段之一。通过彻底清查、收缴其违规投充地亩,最终实现削弱王权,加强皇权的目的。但另一方面,收缴多尔衮家族与诸王投充地亩在数量上相差如此悬殊,顺治帝又为何“薄此厚彼”?笔者认为,这体现了顺治帝在治理“泛滥投充”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即对多尔衮及其势力以清查、收缴为主,而对其他诸王则多倾向于在制度层面上的制约。
多尔衮专权时期,对诸王的违规投充现象,也曾在制度层面予以制约,但当时出于拉拢诸王的需要,那些制约措施也不过是对民怨的一种敷衍。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谕户部曰:
京城内外满洲人等,凡恐吓民人,逼胁投充为奴者,许令本人赴部告理。或赴五城御史及顺天府衙门控诉,转送尔部,治以迫胁之罪。距京城三百里外庄头人等,有逼勒投充为奴,及将工匠逼胁为奴者,道府州县官审明,即将受逼之人释放;如有庄头及奴仆人等,恃强不从者,该道即行拏,解尔部,审明定罪。[3]140
虽然多尔衮规定准许被逼胁的投充者“赴部告理”,但是当时许多满洲庄头凭借旗主身份武断乡曲,抗拒官府,“地方有司虽谙民冤,亦惧而不行国法,以致一经投充旗下,即为法外之人”[9]73。官吏尚惧其三分,一介平民就更无处申冤了。
顺治帝亲政后,重点在制度层面加大了惩罚力度。顺治八年(1651年)七月初一日,颁谕旨曰:
数年以来,投充汉人生事害民,民不能堪。甚至有为盗窝盗者,朕闻之不胜痛恨。帝王以天下为家,岂有厚视投充,薄待编氓之理?况供我赋役者民也,国家元气赖之。投充者,奴隶也。今反借主为护身之符,藐视有司,颠倒是非,弁髦国法,欺压小民。若不大加惩治,成何法纪!自今以后,上自朕之包衣、牛录,下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侯、伯、诸臣等,若有投充之人,仍前生事害民者,本主及该管牛录果系知情,问连坐之罪。除本犯正法外,妻孥家产,尽行入官。若本主不知情,投充之人罪不至死者,本犯及妻孥不必断出。以前有司责治投充之人,曾有革职问罪者,以致投充之人益加横肆。今后各该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与属民一体从公究治。尔部刊刻告示,严行晓谕,务使天下咸知。[3]458
与顺治二年多尔衮所下谕旨相比,这里有4点值得关注:一是约束对象的细化。前者约束对象为“京城内外满洲人等”,所指显然含糊不清。后者则细化为上自皇帝之包衣、牛录,下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侯、伯、诸臣,指明了重点的约束对象。二是约束范围扩大。前者仅对“威逼投充”的现象予以约束,而后者在约束范围上更加广泛,凡“生事扰民者”均予处罚。三是惩罚措施更为严厉。前者的惩罚仅限于当事人——满洲庄头——他们在身份上也不过是“旗主”的奴仆。而后者则规定可连坐于旗主、佐领,已经触及了投充链条中的最后一环。四是明确了地方官吏可以直接处置违法投充者。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虽规定地方有司可“行拏”投充庄头,但尚需押解户部审理。而顺治帝则明确了投充人犯罪,令地方有司“与属民一例究治”,加大了地方有司的惩治权力。可见,这道谕旨对诸王大臣是颇具震慑的,尤其是对“妻孥家产,尽行入官”一条,表面上是将没收的财产归国家公有,但此时顺治帝已经亲政,且已掌控了大部分国家政权,真正成为了“一国之主”。那么,“归国所有”的实质,也就是在皇权的掌控之下。
顺治帝在投充问题上之所以会采取不同策略,是多尔衮逝世后的政治形势使然。顺治帝亲政后,一方面对诸王存有戒心,“以后一应奏章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3]489。但另一方面,年仅14岁的福临,在许多朝政问题上,又不得不依赖诸王大臣辅政,“国家政务,悉以奏朕,朕年尚幼,未能周知人之贤否……诸王议政大臣,遇紧要重大事情,可即奏朕。其诸细务,令理政三王理之”[3]405。对诸王既要约制,又需拉拢的政治现实,让顺治帝在治理清初泛滥投充乱象时,不可能也对其它诸王之违规投充地亩毫无顾忌地清查与收缴。
上述顺治帝对泛滥投充的约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成效。京师周围各县纷纷兴起对威逼投充的诉讼,以致“讼牒日盈于司徒之庭”[12]320。又如清初畿辅地区的带地投充现象,据赵令志先生统计如表1[13]136:

表1 清初畿辅地区投充地亩表(节取) 单位:亩
上表显示出,自顺治八年讫康熙初年间,带地投充地亩数量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可见,自顺治亲政以后至康熙初年间,“泛滥投充”现象相比于多尔衮专政时期,已有缓解。
概言之,多尔衮欲借清初“泛滥投充”之乱局,借以拉拢满洲诸王,实现削弱皇权的目的;又利用“泛滥投充”所引起的皇权与王权的利益冲突,借以形成对皇权的约制,从而稳固其专政统治,这成为清入关之初“威逼投充”与“带地投充”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顺治帝亲政后,在投充问题上,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对多尔衮及其势力的投充地以清查、收缴为主,对诸王的投充地则多从制度层面加以制约。而清初皇权与王权彼此间的互相倾轧,则根源于清初较为特殊的政治体制格局。清廷入关以前,努尔哈赤建立了满洲八旗制度,实行大汗与诸旗主“共议国政”的体制。从清太宗皇太极起,就以加强皇权为目的,逐渐开始了对这一体制的变革,建立了“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框架。自清廷入关以后,随着封建中央君主集权制度的不断加强,皇权与王权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清初皇室与诸王围绕投充问题所产生的权益冲突,本质上反映的正是满洲入关前八旗领主制与入关后封建专制主义君主制两种政体的矛盾与冲突[14]418。
尽管满洲贵族间的政治权力斗争纷繁复杂,但在涉及满洲贵族根本利益方面,他们却貌离神合。就在顺治帝亲政不久,刑部尚书刘余祐、云南道监察御史杨世学、户部左侍郎王永吉3人曾先后上疏,要求废除投充弊政。但随即便遭到满洲权臣阻挠,他们议曰:“若将投充人发出,满兵难照汉兵给养。若以留此投充为不便,则退出投充尤有不便之处。且系年来久定之事,难以复行退出。”[9]78顺治帝批红曰:“著按满官议。”可见,顺治帝所出台的制约泛滥投充的措施,也不过是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的一种权宜之计。故而,“泛滥投充”之风仅平息一时,康熙中期以后又逐渐地在社会上蔓延。直至清末投充政策被完全废除后,“泛滥投充”现象才最终得以消弭。
[1]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M].清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满文老档[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孙家淦.孙文定公奏疏[M].清敦和堂刻本.
[5] 康熙.怀柔县志[M].北京:北京市银祥福利印刷厂,2000年影印本.
[6] 李鸿章,黄彭年.光绪《畿辅通志》[M].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
[7] 昆冈,李鸿章.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
[8] 佚名.沈馆录[M].台北:台北广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9]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4辑)[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 秦廷秀.雄县新志[M].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11] 乌廷玉.清代满洲土地制度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12]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丙编第4本)[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13] 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14] 李洵.下学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Analysis of Unchecked Touchong Policy in the Shunzhi Reign of Qing Dynasty
LI Li-m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Dorgon arrogated all authority to himself.H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unchecked Touchongpolicy to weaken the imperial authority and stabilize his ruling,which became the reason why the phenomenon of Touchongturned even more violent.When he took over the reins of government,Emperor Shunzhi adopted some strategies which restrained initially this phenomenon.However,Emperor Shunzhi himself was also the beneficial owner of this policy.So his control measures were merely an expedience.The result was that this phenomenon spread again gradually during the mid-Kangxi-Reign.The clash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centering on Touchongpolicy between imperial authority and monarchical power reveals in nature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he feudal lord system of the Eight Banners and the monarchy within the feudal autocracy.
Touchongpolicy;imperial authority;monarchical power
K 249.2
A
2095-462X(2014)02-0052-04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40328.1739.027.html
(责任编辑 薛志清)
2013-11-07
李立民(1979-),男,黑龙江牡丹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和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