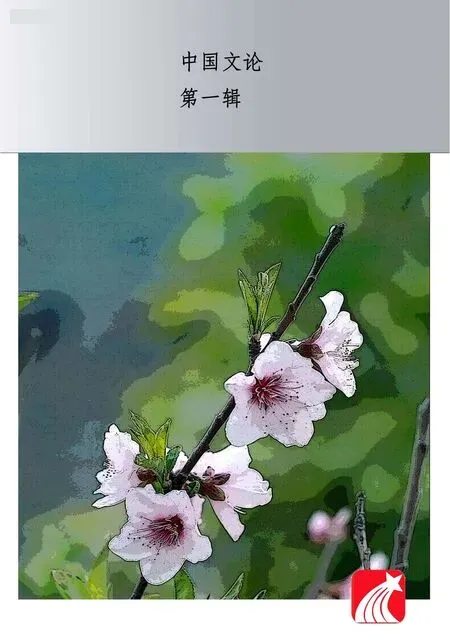《文心雕龙》与汉译《诗镜》之相通性初探
陈允锋
《文心雕龙》与汉译《诗镜》之相通性初探
陈允锋
刘勰《文心雕龙》与古印度檀丁《诗镜》在写作年代上虽前后相距约两个世纪,但就文坛背景及理论宗旨而论,两者之间颇有相通处:其一,《文心雕龙》出现于“文学自觉”观念愈益明确之时代,《诗镜》则产生于古印度文学与宗教相分离、古典梵语文学鼎盛发展阶段,两者都具有总结既往文学创作经验及当代文坛演变趋势之作用;其二,《文心》与《诗镜》皆推崇藻饰之美,但又充分注意过度修饰之弊端,追求有“情味”之“修饰”;其三,两者皆能正视百家飚骇、议论腾跃、“人相掎摭”之文坛现状,洞悉诸家观点利弊,明确提出了审美理想境界。此外,虽然目前尚无直接史料说明《诗镜》在中国古代的汉文翻译及其对汉文典籍之影响,但《诗镜》在中国藏族地区的流播情况则信实有征,影响至为深远。即此而论,《文心》与《诗镜》之比较,亦有助于探讨汉、藏民族文学思想之异同。
《文心雕龙》;《诗镜》;相通性;文坛背景;审美理想
引 言
鲁迅曾经指出:“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这一论断,一方面高度评价了东方古典名著《文心雕龙》在世界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另一方面则导夫先路,启发人们以比较的方法,探讨《文心雕龙》与西方文论之异同,并逐渐成为《文心雕龙》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心雕龙》“比较研究”中,多瞩目于两个层面:一是《文心雕龙》与域外文论,尤其是西方文论的“平行”研究;一是《文心雕龙》与中国古代文论之间的“影响研究”。而专力于《文心雕龙》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论之比较者,则寥若晨星。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汉民族文论之典范,虽然早在隋唐时期即已“远离中土,在西域敦煌落地生根,在东方日本大放异彩”,但是,到目前为止,《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之研究,尚属极为薄弱之环节。个中原因,显然是复杂的。比如相关史料匮乏问题、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少数民族文论资料的发掘与整理问题、不同民族之间文章体式及其审美观念差异问题,等等。当然,这也提醒我们,在《文心雕龙》与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关系研究方面,还需多加留意,投注心力。
除此以外,本文之写作,也有感于二十余年前季羡林先生说过的一段话:“中国地处东方,同印度作了几千年的邻居。文学方面,同其他方面一样,相互影响,至深且巨。按理说,印度文学应该受到中国各方面的重视。可是多少年来,有一股欧洲中心论的邪气洋溢在中国社会中,总认为印度文学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文学不行,月亮是欧美的圆。这是非常有害的。”同样,在《文心雕龙》研究中,虽然学界颇为关注刘勰文论与佛教思想、佛典汉译理论之关系,但《文心雕龙》与佛教发祥地古印度文艺理论之间的比较研究,则尚不多见,其主要原因之一,或即缘于“欧洲中心论”之观念。

与《诗镜》藏译本相比,《诗镜》之汉译,颇为晚出。金克木先生于1965年选译了若干种印度古代文艺理论著作,其中包括《诗镜》第一、三章,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0辑。这应该是最早的《诗镜》汉文节译本。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出版“外国文艺理论丛书”,有金克木译《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单行本,《诗镜》汉文节译亦收其中。时至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其中包括赵康先生译注之《诗镜》汉译全本。由于笔者既不懂藏语,更不识梵语,故本文所作尝试性之比较,《诗镜》文字主要以赵康汉译全本为依据,并酌情参照金克木之选译。
一、“文”之相对独立繁荣发展与文论著作之出现
刘勰《文心雕龙》之产生,乃得益于汉末魏晋以还日渐明晰的“文之自觉”这一历史文化土壤之滋养,约成书于南朝齐明帝建武三、四年(496—497)。从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刘宋文帝元嘉年间设“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列,以及明帝在藩国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再到范晔《后汉书》于《儒林传》外另辟《文苑传》,辞章之学日兴,文集创作日盛。章学诚谓:“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王瑶《文论的发展》一文以为,“南朝的文学和文论,虽都自有特点,但都可以认为是魏晋的发展……首先是文学的地位和独立性,是越增加了。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立总明观,以集学士,亦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使文学与儒史分离并立,成为学术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是以前所没有的事情。”
《诗镜》之撰著,有一点与《文心雕龙》颇为类似,皆基于对既往文学创作经验之总结及当代文坛繁盛风气之熏染。刘勰《文心雕龙》重要内容之一,在于“品列成文”,所谓“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者是也;而其时之文坛,据《时序》篇所言,亦属文事“鼎盛”之世:“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麒麟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檀丁《诗镜》撰成之时代,恰值印度古代史上最为繁盛时期,不仅在经济、贸易、商业、建筑、天文学和宗教等方面获得很大发展,其文学艺术创作也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尤其是在公元4—6世纪,号称“盛世”的笈多王朝,出现了古典梵语文学的“黄金时代”,最杰出的古典梵语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就生活于这一时期。文艺理论方面,则出现了婆摩诃《诗庄严论》、伐摩那《诗庄严经》、优婆咜《摄庄严论》等论著;《诗镜》也是这样一个梵语文学蓬勃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对梵语文学极盛时期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所以《诗镜》第一章就说:“综合了前人的论著,考察了实际的运用,我们尽自己的能力,撰述了[这部论]诗的特征[的书]。”
在印度文学史上,公元1—12世纪是梵语古典文学之时代,在文学表现内容、艺术方法和文学体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发展变化。同时,这又是一个文学获得独立发展的时代——文学逐渐脱离政治、道德的束缚,自觉寻求文艺自身的规律。金克木认为:印度“古典文学中有一种显然以前没有的情况。这就是文学有了独立性,由此又产生了形式主义。前一时代的作品都是公然宣传一定的内容的……文学只是一种宣传工具……可是到了古典文学发展起来以后,文学可以和其他分家了,诗歌、戏剧、小说独立出现了。这时有一批文人的作品并不公然宣传什么思想,或则只是以娱乐为主要目的,有的更只是在语言形式上讲求精雕细琢。”季羡林也指出:“从这一时期开始,印度文学步入了自觉的时代。梵语文学已不必依附宗教,梵语文学家开始以个人的名义独立创作……从总体上说,古典梵语文学已与宗教文献相分离,成为独立发展的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古典梵语文学才成为印度古代文学中最成熟、最富有艺术性的文学,它在戏剧、抒情诗、叙事诗、故事和小说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古代文明世界中大放异彩。”这一点,与中国古代魏晋以迄南朝“摈落六艺,吟咏情性”之文学环境何其相似——随着汉末“涤荡放情志,何为自结束”呼声的出现,建安以降,儒家伦理道德实在难以束缚活泼丰沛之性灵,文学开始摆脱儒学之樊笼,逐步转向抒写性灵、讲究藻饰,获得了相对独立之发展。王瑶在讨论魏晋文学和文论发展进程时,已注意到“儒学衰微”如何“影响文学发展”问题,认为早在汉代,扬雄、桓谭、王充等人因不满“传统经学”,“由此而逐渐引导至重视著作和重文的趋势”。又,日本汉学家冈村繁撰《〈文心雕龙〉中的五经和文章美》一文,从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发展角度入手,认为汉魏六朝时的诗文文体“大多是在与儒学的五经无缘的创作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而《典论·论文》、《文赋》、《文选序》中有关文体理论也是“把诗文与圣人、经典完全分离开来,纯粹从创作美学观点出发来进行的”。此一观点虽有绝对化倾向,但魏晋以来“文学之自觉”,也确实跟逐渐远离儒门规范有直接关系,萧纲所谓“文章且须放荡”之论调,颇足以说明这一点。
二、文坛藻饰之风日盛与文论家针砭时弊之用心
《文心雕龙》与《诗镜》产生之背景,还有一点亦相近似,即藻饰之风日炽而文坛百病丛生。刘勰虽然盛称他所生活的年代“文思光被”、“才英秀发”,同时又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魏晋以来文事之盛兴,固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章作手及杰出篇章,而弃本逐末、好奇矫情之恶习,亦与日俱增。《明诗》篇已经注意到这种倾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定势》篇则明确指出:“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刘勰以为,文坛“逐奇失正”之缘由,不外有二:一是因为“去圣久远,文体解散”,具体表现是“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序志》);二是由于“为文而造情”,其后果是:“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采》)刘勰生活于文采勃兴的齐梁时代,预其流而崇尚雕缛之美,故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序志》)之论,且从“自然之道”的高度,主张“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原道》)《情采》篇除标举“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外,更援引众说,以为“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然其难能可贵处,在于既顺应崇尚藻饰之文坛大势,复超越时流,深知随波逐流之大弊,力倡“衔华佩实”之文境。
如前所论,刘勰的时代既是文事日兴之时,也是华丽文风变本加厉之世。王瑶《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一文,即借用刘勰《明诗》篇“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二语,以为:“从西晋起,诗的作风便是向着这个方向的直线型的发展;除东晋经过了一阵玄言诗的淡乎寡味的诗体外,一般地说,诗是逐渐由稍入轻绮而深入轻绮了;‘采’是一天天地缛下去,‘力’是柔得几乎没有了。追求采缛的结果便发展凝聚到声律的协调,这就是永明体;力柔的结果便由慷慨苍凉的调子,逐渐软化到男女私情的宫体诗。”同样,《诗镜》作者檀丁所处的公元7世纪,也是印度“古典文学由盛极一时而开始衰退的转变时代”。
就其“开始衰退”一端而论,则檀丁《诗镜》写作之时代,文学创作同样存在着刘勰所批评的“饰羽尚画,文绣鞶帨”之风气。金克木指出:《诗镜》的出现,“证明当时文人重视形式的推敲已胜过内容的独创,而且已经有丰富的经验需要总结”。“古典文学发达起来,追求修辞技巧的形式主义倾向几乎就随着兴起。马鸣的诗中已经可以看到注重谐音(双声叠韵),词句往往粗糙而不自然;迦梨陀娑修辞美妙,还不显堆砌;后来的作家就越来越重辞藻以及诗和剧的格式规定,陈词滥调日多。这种倾向发展下去,终于形成一种风气和逆流,淹没了脱离现实生活的作家。”季羡林也认为:“606年,戒日王登位……他也是一位奖掖文学和学术活动的帝王,本人也创作梵语诗歌和戏剧。著名的古典梵语小说家波那曾经蒙受他的恩宠。但从戒日王时代开始,古典梵语文学主潮中出现雕琢浮华的形式主义倾向,将古典梵语文学引上日趋僵化和陈腐的狭路。”这种文坛思潮,与刘勰所讥评的“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之风,几乎别无二致。
檀丁与刘勰一样,身处修饰之风盛行的时代,在持论上既肯定语言藻绘之美,又明确指出应当避免的主要弊端。《诗镜》中说:
世上大贤们的学说,
以及其余人的著作,
正是由于它们的恩德,
人们才有处世的准则。
所谓“世上大贤们的学说”,指的是“按照文法家波尔尼等人所制定的文法规则而写的梵文著作”,而“其余人的著作”,则指“后来用俗语写成的各种著作”。在这些“学说”与“著作”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关于修辞诗学的。因此,檀丁接着说:
为此智者考虑到,
要使人们通诗学,
订出风格多样的
作品写作的规则。
他们明确指出了,
诗的形体和修饰。
形体即按写作愿望,
表意的词的连缀。
关于通晓“诗的形体”之重要性,檀丁以为“此学是意欲进入深邃诗海者的船只”;至于“修饰”在文学创作中的功用,则是《诗镜》论述的重点之一,以为在文学创作中,修饰不可或缺,要“为之装点,不简略”,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处处充满情和味”。檀丁《诗镜》又说:
典雅不仅在语言上,
内容方面也有味,
就象蜜蜂贪花蜜,
它使智者得陶醉。
听到任何一类音,
感到与某音同类。
它的字形等近似,

檀丁如此看待“修饰”与文学作品艺术效果“味”之关系,颇类似于刘勰《神思》篇论修饰润色之效用:“杼轴献功,焕然乃珍。”在《文心雕龙》中,论文章之“味”,一方面与“情”有关,如《体性》篇:“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另一方面,也与修辞艺术相关联,如《宗经》篇赞美儒家五经具有“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之特点,故“余味日新”;《丽辞》篇赞曰:“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隐秀》篇赞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物色》篇则情、味并举,以为在修辞上要遵循“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原则,处理好“物色”之“繁”与“析辞”之“简”的关系,以期达到“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的文章佳境。刘勰认为“英华弥缛,万代永耽”(《明诗》);“一朝综文,千年凝锦”(《才略》),优秀的诗歌作品,情采兼备,足可流芳千古。这种观念,在《诗镜》中亦有表述:“诗篇若具妙修饰,永远流传到劫尽。”在他们心目中,“英华”之美,“修饰”之义,与文学艺术魅力息息相关。
正如刘勰既推崇藻饰之美又充分注意过度修饰之弊端一样,檀丁《诗镜》在详尽论列各种修辞手法之后,也明确指出了文学创作中应当注意避免的十种“诗病”:
意义混乱、内容矛盾、词义重复、
含有歧义和语句次序颠倒、
用词不当和失去停顿、
韵律失调和缺少连声、
违反地、时、艺、世间、
以及违反正理、经典,
这十种诗的毛病,
诗人们应当避免。
由于《诗镜》所讨论的是梵语文学,而《文心雕龙》所面对的是汉语文坛,因此,此间所列十种诗病,在类型及其具体内涵上,与刘勰所论文章之“讹滥”,未必完全等同。但是,就一些基本规则而言,两者之间又未尝没有相通之处。比如关于“意义混乱”问题,刘勰《文心雕龙》亦曾论及。《神思》篇论文章写作之“二患”,其中之一就是“辞溺者伤乱”——词语芜杂、漫无依归,必然导致意义混乱。《熔裁》则意在解决“词义重复”问题:“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赘疣也。”《章句》篇又论及“语句次序颠倒”之病:“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而《指瑕》篇列举文人写作容易出现之瑕疵,有些问题也与《诗镜》所关注者相近,如批评曹植“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属于用词不当之例;又说“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蚩,反音取瑕”,则属语音犯忌之例。至于“违反正理、经典”一类的重要问题,《文心雕龙》亦屡屡论及,无须枚举。所可言者在于:《诗镜》与《文心雕龙》如此重视文学创作、文章写作中的种种弊端,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两者皆致意于文章完美之境。故《诗镜》有言:“为此诗有小毛病,决不可无动于衷,即使身躯甚美丽,斑疹一点毁容颜。”刘勰亦标举“篇体光华”之作,对于文章之小疵,以为亦应注意避免,如《文心雕龙·指瑕》篇谓:“凡巧言易标,拙辞难隐,斯言之玷,实深白圭。”由此可见两者对尽善尽美之境界的共同追求。
又,刘勰《总术》篇综论各种修辞术之总体原则,以为“才之能通,必资晓术”,只有这样,才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倘若“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傥来,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可见“文术”之重要。檀丁之《诗镜》第三章论“音庄严”与“诗病”,其基本立意,亦在帮助作者掌握修饰艺术,获取创作上的成功,故一则曰:“字音和意义的修饰很丰富,写作方法也各有难易之分,还有诗德和诗病,这些都作了概括地说明。”再则谓:“通过上述途径通晓了诗德和诗病,人们获得了顺心的语言伙伴和名声,就像醉眼女和小伙子结为情人,获得了幸福愉快和众人的称颂。”而在两者看来,修辞艺术运用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创造有“意味”的作品,故刘勰《总术》篇以为“执术”得当,“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檀丁说:“诚然一切修饰上,均已赋予了意味。”
三、论家飙起与折衷之思
《文心雕龙》与《诗镜》撰述背景之相近处,还在于文坛论家飙起,众说纷纭。文事的兴盛,自然带动了文论的发展,其间之关系,恰如王瑶所言:“中国先秦两汉,文学的作品虽然很多,但专门论文的篇章却是到魏晋才有的……但文论为甚么会特别在这个时期兴起和发展呢?这我们可以分‘文’和‘论’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是‘文’底发展影响了和引起了‘论’底发展;一方面是‘论’底发展之所以要以‘文’来为它底议论的题材和对象。”其时论文之卓著者,《文心雕龙·序志》篇多已提及:“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而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之《诗品》,则堪称公元5、6世纪南朝齐梁时期文论之双璧。王瑶以为“就文论本身说,南朝所作数量之多,已经够令人惊异了”,“实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灿烂时期”。
印度古代梵语文学“黄金时代”除了在创作实践上“盛极一时”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体现,就是公元5—7世纪印度古代文学理论的独立发展。“古典文学理论”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部门,称为“庄严论”,属于一种广义的修辞学,是一门关于文学技巧的专门学问。其起源可能很早,但像中国古代文论《文心雕龙》、《诗品》那样勒为专书者,则大致出现于公元5世纪以后,而印度现存的典籍中,则以檀丁《诗镜》和婆摩诃《诗庄严论》为最古老的两部论著,其写作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而随着“庄严论”成为一种专业性的学问,出现了一些观点不同的流派,“在形式的分析、推敲和解说上争论不已”。这种情况,《诗镜》第二章开头一节是明确提到了:“美化诗的各种手法,就被称之为修饰;分类至今犹纷纭,有谁能说清它们!”按,刘知几谓:“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两相比较,此与《诗镜》所处的“争论不已”之文论环境,其相似性固不待言。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檀丁面对当时文坛论家纷纭、“人相掎摭”之现状,一方面能够周照圆览,注意诸家观点之利弊,另一方面又能融会贯通、自铸伟辞,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审美境界。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评骘魏晋以来各论家之优劣:“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在论述具体问题时,刘勰既吸收了前辈时贤的合理主张,也对其中有悖文章写作内在规律之观点,给予必要的辨析与驳斥。这就是《序志》篇说的一条论文方法原则:“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这种“擘肌分理,唯务折衷”之思想方法,在檀丁《诗镜》中也有体现。按,“诗镜”亦译作《诗镜论》,藏语称“年阿买隆”,或译作“美文镜”或“文镜”;但此“镜”之具体内涵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学界意见并不一致。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镜”者,是指“因其在书中吸纳的前人关于诗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像明镜一般映现在书中,故取名《诗镜》”。从《诗镜》的实际情况看,如此理解有一定道理。因为在《诗镜》中,作者确实“吸纳”了不少他人的诗学观点。印度学者帕德玛·苏蒂指出:“就诗歌中的美而言,迦梨陀娑给了除婆罗多外的所有诗人们以灵感,他们在自己的诗歌中无处不引用他的文学作品。他似乎还用自己的权威性作品给了所有理论流派以灵感。”而在这些从迦梨陀娑诗美观获得灵感的理论家中,檀丁就是突出的一位:“檀丁非常熟悉作为‘拉撒’(味)的‘卡马特卡拉’(身心解放)一词。他接受了八种情趣及其永恒情趣的存在,以及融为一个叫做‘拉撒拉特·阿拉姆卡拉’(有味的诗歌修辞学或诗歌美)的种类之观点。”这种情况,在《诗镜》中颇为常见,如谓:“用于诗的诸语种,学者们说可分为:雅语、俗语和土语以及杂语等四类。”又如:“牧牛人等说的话,诗中称之为土语,学术论著中认为,雅语之外皆土语。”这里所提到的“学者们”,金克木以为就是指“圣贤”;而“学术论著”,据赵康译注,则指文法著作。当然,对于一些既有观点,檀丁也有自己的判断,比如《诗镜》中说:“诗人遂心做标记,别处也不算缺点,为达愿望创开篇,学者怎可受局限!”金克木指出:“据说这是反驳与檀丁同时或稍前的文艺理论家婆摩诃的主张。”又如《诗镜》:
不分诗句的长行,
便称做是散文体。
又分小说和故事,
其中小说据说是
只能领袖来叙述;
故事尚可他人叙。
由于赞颂甚贴切,
宣扬己德不为弊。
然而并不成定理,
小说亦有他人叙,
他人或则自己叙,
有何区分之根据!
此中所“据说”者,指的是婆摩诃《诗庄严论》关于散文体的小说与故事之划分,檀丁既转述其观点,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故曰:“然而并不成定理”、“有何区分之根据”。
刘勰《文心雕龙》、檀丁《诗镜》之所以能成为各自国度古代文论之名著,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在于两者之立论思维,皆善于协调各种不同创作和理论倾向。比如,在《诗镜》第一章中,檀丁将风格(mārga)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维达巴风格,另一种是高达风格。前者是南方派,后者属于东方派。从理论倾向上看,檀丁更偏重于南方派之维达巴风格,因此,他所详细列举的十种诗德,皆为南方派所特有者:“和谐、显豁和同一,典雅以及甚柔和,易于理解和高尚,壮丽、美好和比拟。”他认为“这十种诗的美德,是南方派的命脉”。对于东方派,则一语带过:“与此相反的,是东方派的文采。”对于这一问题,金克木先生指出:“作者偏向南方派而不喜东方派,解说诗‘德’时以南方派为主,而对东方派时有微词;因此在‘显豁’下面引了东方派的晦涩的诗句来对比。例句中的词和词义大都冷僻古怪,诗句读起来音调也很别扭。”
但是,就总体情况而论,檀丁还是充分认识到文学风格的多样性,并没有一味否定东方派。他说:“语言风格有多种,彼此稍微有差别。”因此,更多的时候,他一方面客观地比较南方派和东方派风格上的区别,另一方面,则撮举两派之共同审美追求。比如《诗镜》第一章论十种诗德之一“和谐”:
和谐多用软音字,
却不感到有松散,
例如“贪婪的蜂儿,
聚在豆蔻花丛间。”
由于用了同音引类,
得到了东方派的喜欢,
南方派则更喜爱:
“豆蔻丛中蜂盘旋。”
从其表述中,看不出有何轩轾抑扬之意。又如关于“引类”(谐声)问题,《诗镜》曰:“听到任何一类音,感到与某音同类。它的字形等近似,有此引类方有味。”这种类型的谐声,为南方派所推崇,而“东方派不欣赏它,而喜爱同音引类,南方派则欣赏它,甚过于常见引类”。按照金克木的解释,南方派所欣赏之谐声,指的是“同一部位的发音”及其所构成的呼应关系,而东方派所推崇的,则是“同音重复”之谐声。这里也不存在对不同观念的高下判断。
当然,在《诗镜》中,檀丁谈得最多的,还是两派之共性。赵康先生指出,《诗镜》“选择、比较、分析和研究了梵语文学作品的大量诗例,一共提出了三百零九种修饰。其中南方派与东方派不同风格的十种;两派相同风格中,意义修饰分为三十五类包括二百零三种,字音修饰分为三类包括八十种,隐语修饰十六种。”可见檀丁虽偏爱南方派,但论述南方派、东方派修饰共同者毕竟占绝对多数,而南方所独有之风格,仅占十种。这也足以说明在文学风格、修辞美学方面,檀丁并未局限于一己之见,而是善于会通。即使在他所论的两派十种“不同风格”中,也是如此。比如关于“易于理解”、“高尚”风格问题,檀丁《诗镜》即南方、东方两派并提:“两派对于此风格,都觉理解不容易,它违反了组词法,此法多不被采取。”“句中说了若干话,高尚品德得领悟,这种诗风叫高尚,两派以此为怙主。”“壮丽”风格也是南方派推崇的“诗德”之一,而《诗镜》论述该体时,亦连带而及东方派:“壮丽中多省略字,这是散文体的生命。东方派特别强调,它是韵文体的要领。”
这样,[依据诗德.]描述了它们[两派]的特性,[可见南方与东方]两派的不同。至于每一个诗人所有的相异之点就不能细说了。
甘蔗、牛奶、糖浆等等的甜味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即使是辩才天女也不能把它说出来。
这是《诗镜》第一章末尾具有一定总结性质的两小节,明确表达了作者的圆通观点,肯定了风格多样性与差异性。即此而论,以为“《诗镜》的发表统一了两派的观点”,确为有据之论。
由檀丁《诗镜》“甘蔗、牛奶、糖浆”之取譬,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类似的比拟思维:“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此以草木为喻,讲人类文章写作,有“同性”的一面——“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又有“异品”的一面——“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无论是“同性”还是“异品”,其实都与风格问题直接相关。而刘勰对待文章之风格,同檀丁一样,也是衡以圆通之思,并未偏执一隅。
在《文心雕龙》中,《定势》篇侧重从理论上阐明不同文体之内在规定性,讲了诸文体之“势”,也就是文体风格问题:“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刘勰首先讲到“情致”之“异”、“文术”之“殊”,以为这决定了作者选择不同的文体,而不同之文体,其“势”也自别。如此立论,既看到了文体之“势”与作者之“情”的关联性,也突出了文体之“势”存在的客观性及其多样性。因此,《定势》篇谓:“是以囊括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
在《文心雕龙》中,又有《体性》一篇,专论与作者主观因素相关的个性风格问题:“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正,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强调了人之才、气、学、习四大因素之异,及其由此而形成的文章体貌风格之别。《体性》篇“总其归涂”,列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种风格类型,以为“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且“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
《体性》、《定势》皆从文章写作角度,谈论风格之异品、多样,其理论宗旨,则与专论鉴赏批评之道的《知音》篇遥相呼应: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
这种反对以“一隅之解”而“拟万端之变”的明确态度,以及强调“圆照”与“博观”的方法,在立论思维上,皆与檀丁之论风格,差相仿佛。
不仅如此,檀丁《诗镜》兼论南方、东方二派之理论,其中南方派“较注重思想感情内容”,而东方派更“重语言排比堆砌”,檀丁则运以圆通之思,将两者统一起来,这在“注重辞藻已成风气之时”,其针砭文坛时弊、标举文学正道之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同理,在《文心雕龙》中,虽然并未明确标出“流派”之争,但据刘畅教授研究,可知刘勰所确立的理想文风,实际上暗含着“尚北宗南”、致力于“融合南北文学两长”的“折衷”之意,以为唐初魏徵《隋书·文学传序》所倡导的合南朝江左“清绮宫商”与北朝河朔“贞刚气质”之长的主张,在刘勰《文心雕龙》中已有所体现。比如《风骨》篇“虽未明言南朝尚‘清绮’、北方重‘气质’及其融合两者的必要,却形象地提出了风骨与文采、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问题,实际上已触及了魏征等人所言的问题”;又如,刘勰“文质兼顾,采取一种较为圆融周洽的态度:思想气质上尚北,而审美取向上宗南”。这一特点,与檀丁《诗镜》亦有相合之处。
结 语
以上结合相关既有成果,重点从刘勰《文心雕龙》、檀丁《诗镜》撰著背景的角度,阐述了两者之间的相通性问题。兹简要归纳总结如次。
其一,《文心雕龙》、《诗镜》在写作年代上虽前后相距约两个世纪,但都与各自民族历史文化之繁盛发展密切相关。具体而论,《文心雕龙》出现于“文学自觉”观念愈益明确之时代,文章之学摆脱了两汉经学之束缚,改变了隶属儒学之格局,获得了独立地位且蓬勃发展;《诗镜》则产生于印度古典梵语文学之黄金时代,文学与宗教相分离,成为一个独立部门。因此,两者都具有总结既往文学创作经验及当代文坛发展新趋势之功效与意义。
其二,中国古代南朝时期,文事日兴,藻饰愈盛,名篇佳作固自弗乏,而文坛浮诡爱奇之习尚,亦如影随形,将遂讹滥。故《文心雕龙》标举郁然有采,不待外饰“自然之道”,重文采而斥侈艳,尚清真而远朴陋。在崇尚“情采”之同时,又以儒家经典为轨范,以“衔华佩实”为美文极境,针砭文坛时弊,痛贬弃本逐末、为文造情之徒。《诗镜》之作,恰逢印度古代梵语文学盛极而衰之转关阶段,虽名家辈出,然雕琢浮华之风亦日益滋长,辞藻愈加精致,陈词滥调亦与日俱增。因此,檀丁之诗学,与刘勰之文论一样,既推崇藻饰之美,又充分注意过度修饰之弊端,其并重十种“诗德”与十种“诗病”,立意即在于此。即此而论,《文心雕龙》与《诗镜》无疑都具有拯治百病丛生之文坛的现实意义,追求有“情味”之“修饰”,自然也成了两者共同之目标。
其三,刘勰与檀丁所面对之文坛,另有一共同点,即文事兴盛所带来的文论之发展,百家飚骇,议论腾跃。《文心雕龙》出现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之灿烂时期,《诗镜》完成于印度古典文学理论独立发展阶段,绝非偶然之事。因此,两者之理论贡献在于:正视论家纷纭,“人相掎摭”之现状,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洞悉诸家观点之利弊,博观圆照,融会贯通,明确提出了理想的文学审美境界,促进了各自民族美学思想之发展。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厄尔·迈纳教授说:“在不同的文学和不同的社会里,彼此不同的某些成分,由于具有相同的功能,因而互相间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以上所作类比性初探,侧重于《文心雕龙》与《诗镜》之相通性,而且仅仅是两者相通性中的一个具体方面。至于两者在修辞理论方面的共同点以及两者之间的不同特征,则未遑涉及。不过,这一管中窥豹式的初步检视,对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些相关问题,或许不无裨益。比如,虽然檀丁《诗镜》较《文心雕龙》晚出,但其思想渊源有自,且在思想方法上与佛教典籍一样,长于分析,体现了“着重分析和计数以及类推比喻作说理的证明”这一古代印度的传统习惯,由此
返观《文心雕龙》,则有助于更深入探讨刘勰论文方法与佛教思维方式之关系。又如,魏晋南朝时期,虽然注重藻饰蔚然成风,但专力总结修辞方法与理论者,唯长期受佛门熏染之刘勰一人而已,因而,《文心雕龙》又被视为一部修辞学著作,这与《诗镜》中所反映出来的古印度以修辞学为专门学问之传统,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也未尝不可作为一个重要论题予以深入系统之考察,而不仅仅局限于备受关注的“声律”问题。再如,《诗镜》既已在中国藏族诗学史上发挥过重要奠基之作用,且转化为藏族古代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则以《诗镜》为参照,梳理其影响轨迹,并与汉族文论比照而论,求其同而存其异,对更全面地寻求中华民族共有之美学精神、各民族独特之审美旨趣,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允锋,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