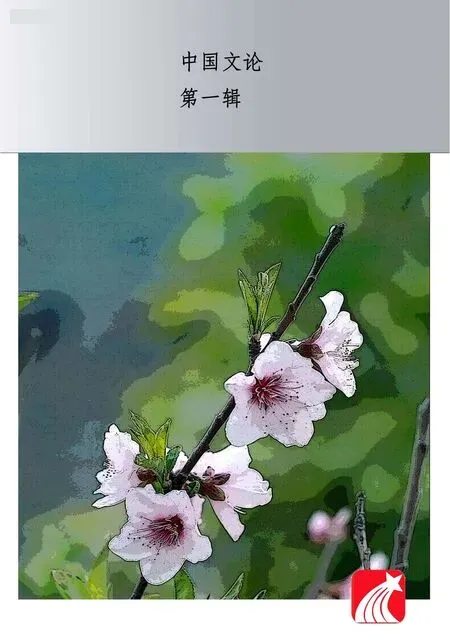中国古代多种小说概念辨析
吕玉华
中国古代多种小说概念辨析
吕玉华
中国古代对于小说有多种称呼,这些内涵相似的概念在具体来源和文论应用当中各有特点。稗官、稗史体现了小说作为史之苗裔的特征,相关论述集中在劝诫、补史的功用层面。说部相当于小说总汇,概念涵盖极为宽广,甚至包括戏曲在内。传奇概念几经变迁,不过最核心的内容一直是才子佳人世情故事。演义的方式来源于儒经、佛经等典籍的俗讲,是以大众喜爱的通俗方式解读历史经典。在文献记载当中,这几种小说概念一直并用。直到近代,“小说”一词方才彻底取代了前几项,实现了术语的统一和规范。
小说;稗官;稗史;说部;传奇;演义
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可分为两大序列、三条发展脉络。
一大序列是班固《汉书·艺文志》确立的小说概念,可命名为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该概念为小说正宗,从汉代一直沿用到清末。这一大序列就是一条独立的发展脉络,从始至终,其概念内涵保持稳定性,也为历代正统史家所固守。该序列小说的语言特征为文言。
另一大序列是文学意义的小说概念,包括两条发展脉络,均与正宗的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有关。下面就结合作品实际来看。
发展脉络之一是杂传记。杂传记是以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材料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并且接受了史传散文的写法,其典型代表就是唐传奇。该发展脉络可表述为:汉、魏晋志人、志怪、杂传记——唐传奇(杂传记)——宋传奇——明文言小说——清文言小说。此类小说体现了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和史传的结合。有许多小说集是一书二体,既有曼妙铺陈的杂传记部分,也遵循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传统,体现为大量的材料杂纂。清代著名小说集《聊斋志异》就是如此。该类小说的语言特征是文言形式。
发展脉络之二是白话通俗小说,是市井伎艺以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为表演材料,并进行了口语化通俗化的加工,逐渐形成的新型文本,其发展脉络可抽绎为:俳优小说——俗讲/说话——话本——白话通俗小说。因为题材来源以及服务对象、影响范围的相似,戏曲也经常被归入此类小说。该类小说的语言形式为通俗白话,体现了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和市井伎艺的结合,其创作取材范围包括了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以及文学意义的小说之杂传记。
文学意义的小说概念被广泛应用,是从明代中晚期开始的。这个理论现象,与相应的白话通俗小说创作蓬勃发展大有关系。
“小说”一词作为概念术语,经历了词语内涵的变迁和发展。在“小说”概念的演变过程中,也出现了其他称呼,如稗官、稗史、说部、传奇、演义等,皆属于对小说文体的命名。本文对其一一辨析,有助于理解小说概念的复杂内蕴。
一、稗官、稗史
稗史的概念来源于稗官,而且是先有稗官,再有稗史。两者亦常常通用。
《汉书·艺文志》明确说过:“小说家流,概出于稗官。”并引如淳注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先秦至汉的古籍文献当中并无名为“稗官”的职务。那么稗官究竟是什么?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或认为是天子左右之士,或认为就是小官,如汉代的待诏、郎官等。
稗官言论等同于小说(也就是文献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小说作者就有方士待诏等稗官。在汉代以后具体的理论应用中,人们时常用稗官来代指小说。对此余嘉锡先生批评曰:“自如淳误解稗官为细碎之言,而《汉志》著录之书又已尽亡,后人目不睹古小说之体例,于是凡一切细碎之书,虽杂史笔记,皆目之曰稗官野史,或曰稗官小说,曰稗官家。不知小说自成流别,不可与他家相杂厕。且稗官为小说家之所自出,而非小说之别名,小说之不得称为稗官家,犹之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不得名为司徒儒家,亦不得称儒书为司徒家也。治学之道,必先正名,名不正,言不顺,莫甚于所谓稗官家矣。”余先生此处所用“小说”概念,就是对文献目录学原初意义的坚持。
本文认为,既然目前“稗官”一职无文献支持,则可以看成一个有修饰意义的词。稗通粺,就是碎米,首先有细碎意;又碎米价值低于好米,稗也有低贱之意。后人曾质疑曰:“稗官非细米之义,野史小说异于正史,犹野生之稗,别于禾,故谓之稗官。”(清代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其实,无论稗是细米还是野草,以“稗”来修饰,都不脱琐碎、低贱两层意义。稗官,理所当然就是“小官也”。(《汉书》唐代颜师古注)
稗官职责,或为民间庶人传言,记录他们的言行,“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矣”。(鲁迅《古小说钩沉序》)所记录的内容既是一些琐碎的、不成系统的民间言论,则价值也较为有限。
小说概念在发展过程中衍变,稗官等于小说,所以其实际上的内涵也跟着小说变化了。稗官、稗史在文学理论当中被使用的频率从明代起增多,这与小说文体的发展是相关的。
刻于明代万历年间的王圻《稗史汇编》,其分类形式沿袭历代类书,列“天文门”、“时令门”、“地理门”、“人物门”、“伎术门”等,每一门下又分类,如“人物门”下列“帝王”、“德行”、“节义”等,内容全属小说类。从该书命名及收录内容来看,“稗史”都等同于从汉代一脉相承下来的杂著“小说”,内容琐碎杂多,编纂的目的乃是补正史之阙。“稗史”的命名内涵基本等同于文献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但其具体所指却包括了文献目录学意义、文学意义两方面的小说。如《文史门·尺牍类·院本》(卷一零三)中有言:“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今读罗《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这里明确以《水浒传》为稗史。
稗史从其名称来看,自然也是史之苗裔,但在具体使用中更多地凸显了与史乘的差异。这个概念的使用,充分说明了理论家们的命名尝试,更能突出小说依附史传的自觉主动性,故对于稗官、稗史总是从劝诫、补史角度进行论述,并经常和野史、野乘等并列使用。
是编虽稗官之流,而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明代凌云翰《剪灯新话序》)
后之君子能体予此意,以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盖予之至愿也夫。(明代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
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其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明代熊大木《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数百千种,而《三国志》、《西游记》、《水浒传》及《金瓶梅演义》,世称“四大奇书”,人人乐得而观之,余窃有疑焉。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清代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
稗官与稗史内涵完全一致,不过在具体使用中有微小差异,即稗官、稗史均可作为文类称呼,但是“稗史”及其相似词语可以用来命名,如《呼春稗史》、《绣榻野史》、《禅真逸史》、《女仙外史》、《儒林外史》等,而“稗官”鲜有此例。
二、说 部
“说”是先秦时代出现的一种文体。有学者主张“说体”以论说道理为主,如韩非有《储说》,《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记载了《伊尹说》、《黄帝说》、《封禅方说》等。“说炜晔而谲诳”(陆机《文赋》),则“说”这种文体夸张虚饰、重文采的特征很突出。亦有学者认为“说”指传闻故事,“始于讲述、后被记录”成文本,与“传”、“语”同类,“说体中的‘小说’与后来纯文学分类中的小说文体,在许多特征方面的确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宽泛地讲,它们本身即可被视为文学性的小说”。
先秦时代,与“说”相关的重要著作就是《韩非子》,该书有八篇纂集式作品以“说”命名,即《说林上》、《说林下》、《内储说上》、《内储说下》、《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这些篇章都体现出故事集成的性质。
先秦之后,从西汉刘向的《说苑》到南北朝时刘义庆《世说》、刘孝标《续世说》、沈约《俗说》、殷芸《小说》种种以“说”命名的著作,皆为丛残小语、故事材料的缀集。
但是,“说部”一词并非“说”类文体的集合,而是与小说概念紧密相关。可以说,“小说”之部就是“说部”,这个“小说”是偏于文献目录学意义的概念,如下文所述:
唐、宋以前,治学术者,大抵多专门之学,与涉猎之学不同,故丛残琐屑之书鲜。唐、宋以降,治学术者,大抵皆涉猎之学耳,故说部之书,盛于唐、宋,今之见于著录者,不下数千百种。详考之,约分三类:一曰考古之书,于经学则考其片言,于小学或详其一字,下至子史,皆有诠明,旁及诗文,咸有纪录:此一类也;一曰记事之书,或类辑一朝之政,或详述一方之闻,或杂记一人之事,然草野载笔,黑白杂淆,优者足补史册之遗,下者转昧是非之实:此又一类也;一曰稗官之书,巷议街谈,辗转相传,或陈福善祸淫之迹,或以敬天明鬼为宗,甚至记坛宇而陈仪迹,因祠庙而述鬼神,是谓齐东之谈,堪续《虞初》之著,此又一类也。(刘师培《论说部与文学之关系》)
可见,唐宋人编纂的笔记类杂著,是说部的正宗内容。
北宋官方编纂小说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影响深远。南宋曾慥则以私家之力修撰《类说》,亦广集小说,《四库全书》归入子部杂家类。其《类说序》曰:“小道可观,圣人之训也。……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如嗜常珍,不废异馔,下筯之处,水陆具陈矣。览者其详择焉。”
元末明初陶宗仪撰《说郛》,内容也包罗万象,“盖宗仪是书,实仿曾慥《类说》之例,每书略存大概,不必求全。亦有原本久亡,而从类书之中钞合其文,以备一种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子部杂家类七)
明代人对于小说格外重视。陆楫编《古今说海》一百四十二卷,辑录前代至明代小说。后顾起元编《说略》,“其书杂采说部,件系条列,颇与曾慥《类说》、陶宗仪《说郛》相近。故《明史》收入小说家类。然详考体例,其分门排比、编次之法实同类书。但类书隶事,此则纂言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六子部类书类二)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说部”一词正式出现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其四部分别为“赋部”、“诗部”、“文部”、“说部”,从形式上看,当是对经、史、子、集四分法的借用。既有说部,则其后各种“说”类书层出不穷,如《说荟》、《说铃》等。“近代说部之书最多,或又当作经、史、子、集、说五部也。”
清代宣统二年(1910),王文濡等编成《古今说部丛书》,共十集六十册,乃是“仿《说荟》、《说海》、《说郛》、《说铃》、《朝野汇编》之例,汇而集之,俾成巨帙”;“要皆文辞典雅,卓有可传,上而帝略、官制、朝政、宫闱以及天文、地舆、人物,一切可惊可愕之事,靡不具载,可以索幽隐、考正误,佐史乘所未备。或寥寥短章,微言隽永;或连篇成帙,骈偶兼长。就文体而论,亦觉无乎不备”。(《古今说部丛书序》)
说部类容纳的著作无所谓文体,完全属于内容分类,包罗万象,驳杂繁多,体现出文献目录学方面的杂纂、裨补史阙、增广见识的意义。
自稗官之职废,而说部始兴。唐、宋以来,美不胜收矣。而其别则有二:穿穴罅漏、爬梳纤悉,大足以抉经义传疏之奥,小亦以穷名物象数之源,是曰考证家,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之类是也;朝章国典,遗闻琐事,巨不遗而细不弃,上以资掌故而下以广见闻,是曰小说家,如《唐国史补》、《北梦琐言》之类是也。(清代李光廷《蕉轩随录序》)
说部之体,始于刘中垒之《说苑》、临川王之《世说》,至《说郛》所载,体不一家。而近代如《谈艺录》、《菽园杂记》、《水东日记》、《宛委余编》诸书,最著者不下数十家,然或摭据昔人著述,恣为褒刺,或指斥传闻见闻之事,意为毁誉,求之古人多识蓄德之指亦少盩矣。(清代计东《说铃序》)
说部一词被逐渐等同于小说,并且随着小说概念的扩容,说部所涵盖的内容也扩展开来,最终包括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和文学意义的小说。至民国时期,则“说部二字,即小说总汇之名称”几成为公理,杂纂笔记、白话故事甚至戏曲皆为说部。
三、传 奇
传奇与小说相关,已经是唐代的事情了,晚唐裴铏所撰小说集名曰《传奇》。“传奇”应该是由“搜神”、“志怪”所引生,三个词语同一结构,意义相近。就整个唐代而言,“传奇”并不是文体专名,唐代人自己所写的小说如《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也并无统一的文类专名,因为他们是在按照史传的方式进行创作,虽然着意好奇出新,并虚拟情节,文心巧构,但结撰形式完全是正统的纪传体。故北宋编撰《太平广记》,所收录的十几篇唐代传奇小说,统命名为“杂传记”。宋人也在写作类似的杂传记文章,如《绿珠传》、《赵飞燕别传》、《李师师外传》等,同样也不以“传奇”命名。
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中有一则记载:“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这大概是第一次以传奇来命名“体”。因为《岳阳楼记》无甚故事情节,能够和传奇联系上的无非是其骈散相间的华美语言。故这个“传奇体”仍然不能看作文体,而只是一种对语言形式特征的概括,就像明代胡应麟的疑问:
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仪谓唐为传奇,宋为戏诨,元为杂剧,非也。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铏所撰,中如《蓝桥》等记,诗词家至今用之,然什九妖妄寓言也。裴,晚唐人,高骈幕客,以骈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其书颇事藻绘而体气俳弱,盖晚唐文类尔,然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喜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或以中事迹相类,后人取为戏剧张本,因辗转为此称不可知。范文正记岳阳楼,宋人讥曰传奇体,则固以为文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庄岳委谈下》)
说话伎艺在宋代兴盛一时,因说话的素材来源十分广泛,不同的题材势必影响到表演方式;听众各有喜好,也会造成听众群有所区分。故说话伎艺发展盛时,依据所说内容不同,逐渐形成不同的家数。
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小说讲经史》)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南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术、神仙。……论《莺莺传》、《爱爱词》、《张康题壁》、《钱榆骂海》、《鸳鸯灯》、《夜游湖》、《紫香囊》、《徐都尉》、《惠娘魄偶》、《王魁负心》、《桃叶渡》、《牡丹记》、《花萼楼》、《章台柳》、《卓文君》、《李亚仙》、《崔护觅水》、《唐辅采莲》,此乃为之传奇。(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
说话伎艺影响一时,其文化信息与大众之间是良好的互动关系。民间爱好的题材以及审美的、道德的观念会被说话伎艺采纳,说话伎艺又推动了这些故事、观念的传播。就宋代来讲,“传奇”所指范围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话伎艺之小说当中的一个门类,以及相似题材的诸宫调(详下文)。从《醉翁谈录》列举的小说名称可知,传奇基本上都是男女爱情故事。
《莺莺传》被列在“传奇”第一位,可见它本身就是说话的热门题材而长演不衰。南宋赵令畤《侯鲭录》卷五“辨传奇莺莺事”引王性之所作《传奇辨正》云:“尝读苏翰林赠张子野有诗曰:‘诗人老去莺莺在。’注言:‘所谓张生,乃张籍也。’仆按元微之所作传奇,莺莺事在贞元十六年春。”同卷“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条载:“夫传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载于本集而出于小说,或疑其非是。今观其词,自非大手笔,孰能与于此?”《传奇辨正》、《侯鲭录》皆以“传奇”指元稹小说《莺莺传》,这应该是文人接受了说话伎艺影响而应用“传奇”概念的一个证明。
唐人作品被宋代民间伎艺采纳为题材,且归类为“传奇”,流播日久,形成大众文化观念,反过来又影响了文人看法:“盖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乐,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元代虞集《道园学古录·写韵轩记》)至此,唐代的杂传记才正式得名为“传奇”。
“唐传奇”成为专有名词,专指唐代那些才情绝艳的文言小说。但是“传奇”仍非专有名词,它还是偏重于人间悲欢离合之情事,至于表达载体用文章还是用戏曲,倒是次要的事情。故宋金元时代的诸宫调、杂剧等也时常被呼为传奇。《录鬼簿》中有“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其下录关汉卿、高文秀、郑廷玉、白仁甫、马致远、王实甫等五十六人的杂剧剧目。
明清时代,传奇指南戏,被归入乐府。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辨析戏曲中“传奇”一名的流变,可与以上所论相参照,对于传奇概念的演变会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传奇之名,实始于唐。唐裴铏所作《传奇》六卷,本小说家言,此传奇之第一义也。至宋,则以诸宫调为传奇,《武林旧事》所载“诸色伎艺人”,诸宫调传奇,有《高郎妇》、《黄淑卿》、《王双莲》、《袁太道》等。……则宋之传奇,即诸宫调,一谓之古传,与戏曲亦无涉也。元人则以元杂剧为传奇,《录鬼簿》所著录者,均为杂剧,而录中则谓之传奇。……至明人则以戏曲之长者为传奇(如沈璟《南九宫谱》等),以与北杂剧相别。乾隆间,黄文旸编《曲海目》,遂分戏曲为杂剧、传奇二种,余曩作《曲录》从之。盖传奇之名,至明凡四变矣。
四、演 义④参见谭帆:《演义考》,《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黄霖、杨绪容:《“演义”辨略》,《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李舜华:《小说与演义的分野》,《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
说到演义,今人的第一反应估计都会是《三国志演义》。
演义之萌芽,盖远起于战国。今观晚周诸子说上世故事,多根本经典,而以己意饰增,或言或事,率多数倍。若《六韬》之出于太公,则演其事者也;若《素问》之托于岐伯,则演其言者也。演言者,宋、明诸儒因之为《大学衍义》;演事者,则小说家之能事。根据旧史,观其会通,察其情伪,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谈巷议,亦使田家孺子知有秦汉至今帝王师相之业;不然,则中夏齐民之不知故国,将与印度同列。然则演事者虽多稗传,而存古之功亦大矣。
这段话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路,演义就是“多根本经典,而以己意饰增,或言或事,率多数倍”,演义等同衍义。其中的“演言”一系与小说关系不大,兹不赘述;而“演事”则演变为小说,故专门论述。
《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载有苏鹗《演义》十卷,是目前所见较早以“演义”为名的著作。《苏氏演义》的撰写体例与文献目录意义的小说相同,被《新唐书·艺文志》归入小说家类,更多是体例上的考虑。但是,该书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入杂家类(卷十):“唐光启进士武功苏鹗德祥撰。此数书者,皆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有益见闻。”可见该书重在考证,有相当的实用价值。《四库全书》也收入子部杂家类,其内文是从《永乐大典》当中辑录出来的。
《苏氏演义》二卷(永乐大典本)
唐苏鹗撰。鹗字德祥,武功人。宰相颋之族也。光启中登进士第,仕履无考。尝撰《杜阳杂编》,世有传本。此书久佚,今始据《永乐大典》所引裒辑成编。《杂编》特小说家言,此书则于典制名物具有考证。书中所言,与世传魏崔豹《古今注》、马缟《中华古今注》多相出入。已考证于《古今注》条下。然非《永乐大典》幸而仅存,则豹书之伪犹可考见,缟书之剿袭竟无由证明。此固宜亟为表章,以明真赝。况今所存诸条为二书所未刺取者,尚居强半。训诂典核,皆资博识。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伪谬,可与李涪《刊误》、李济翁《资暇集》、邱光庭《兼明书》并驱,良非溢美,尤不可不特录存之,以备参稽也。原书十卷。今掇拾放佚,所得仅此。古书亡失,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是固不以多寡论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八子部杂家类二)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苏氏演义》的考辨订正之用也是大加赞扬。若说演义就是以经典为根本而衍发,则《苏氏演义》或许就是考证经典文献当中的名物制度,但该书久佚,究竟演哪种经典文献不太清楚。由此个例可见,“演义”的言论是比较琐碎的,又有其独特的价值,属于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
唐代至明代,陆续出现了很多儒经、佛经以及子部、集部书的演义之作,如王炎《春秋衍义》、真德秀《大学衍义》、钱时《尚书演义》、梁寅《诗书演义》、徐师曾《周易演义》、杨慎《绝句衍义》等。“从南宋至明初,一种以广泛地引录圣哲议论和史事故实,适当参以作者个人意见,或用较为通俗的语言,明白、详细地阐发原书义理的一类作品被通称为‘演义’或‘衍义’。”
当士人们孜孜不倦地演义经典的时候,世俗说话伎艺当中的小说也出现了“演史”一门,以大众喜爱的通俗方式解读历史经典,其受众比儒经演义更广,受欢迎的程度更甚。与之相关的文本是元代刊印的《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其实,世俗和高雅之间并无壁垒分明的界限,作为文化传承者和解释者的士人,既是朝廷的要员,也是市井生活中的俗人;既正襟危坐讲经典,也前仰后合地听说话。很多概念内涵原本就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正统的经典可以演义其哲理,严肃的史传也可以演义其故事,就这样“演义”成为一个使用率较高、被普遍认可的文化普及概念,与之相关的意义首先就是“通俗易晓”。
小说者,正史之余也。《庄》、《列》所载化人、伛偻丈人,昔事不列于史。《穆天子》、《四公传》、《吴越春秋》,皆小说之类也,《开元遗事》、《红线》、《无双》、《香丸》、《隐娘》诸传,《睽车》、《夷坚》各志,名为小说,而其文雅驯,闾阎罕能道之。优人黄翻绰、敬新磨等,搬演杂剧,隐讽时事,事属乌有,虽通于俗,其本不传。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而通俗演义一种,乃始盛行。(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
今天所能见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刊本出现于明代嘉靖壬午年(1522),“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首弘治甲寅庸愚子序。章二,曰‘金华蒋氏’,曰‘大器’。又:嘉靖壬午关中修髯子引,有‘关西张尚德章’”。
庸愚子即金华蒋大器,其序作于弘治甲寅(1494),序中曰:“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
这段序文几乎为其后所有的历史演义作品定下了基调,“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借助演义的形式,中华民族重史的传统从上层走进民间。
此时,“小说”概念属于文献目录学意义与文学意义双轨制运行,“演义”也同样在走双轨路线,一是偏史的,就是史的通俗化,语言通俗,内容引人入胜,有虚构成分,形同今天的历史小说概念;一是偏文学的,凡是与历史有点儿关联的人物事件,都可成为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也都是演义。在发展过程中,随着文学意义的小说概念更加成熟和稳定,演义也确定了自己的位置,逐渐被“历史小说”一词代替。“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征之陈寿之《三国志》与坊间通行之《三国演义》,其比较厘然矣。”
稗官、稗史、说部、传奇、演义诸概念在明清两代直至近代皆并用,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同义词,如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标题明确“说部”,文中则论述曰:“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

故事主题、故事情节的沿袭,使得文言作品与白话作品、高雅作品与通俗作品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从理论上对不同作品进行归纳时,采用同一个概念也是比较自然的。
“小说”一词在近代取代了前几项,实现了术语的统一和规范,成为该类文体唯一的称呼,并沿用至今。其原因大概是小说一词产生时代最早,且在正史目录当中有位置,其内涵文学化也是最早的。再者,“小说”一词,与其他学科门类没有太多语词上的关联。稗史,总难免想到史;说部,似乎是个分类词;传奇、演义,总有些题材限制,这几项都不足以表达一个独立的文体。故“小说”被理论家重复使用,格外凸显,最终成为唯一的现代学科术语。
吕玉华,女,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