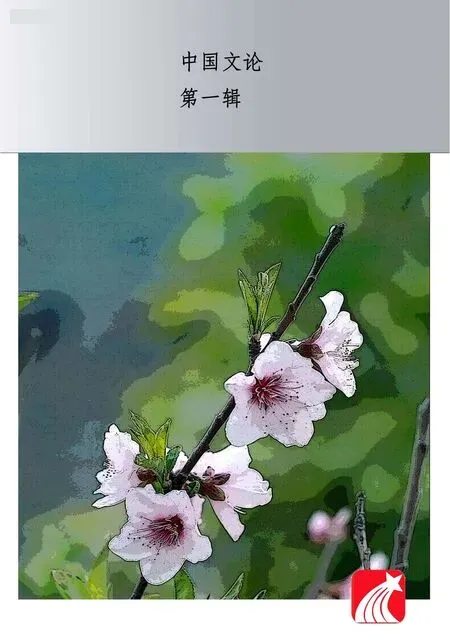六朝文体内涵重释与刘勰、钟嵘论“奇”关系再辨
——兼评中日学者关于《文心雕龙》与《诗品》文学观的论争
姚爱斌
六朝文体内涵重释与刘勰、钟嵘论“奇”关系再辨——兼评中日学者关于《文心雕龙》与《诗品》文学观的论争
姚爱斌
比较《文心雕龙》与《诗品》的文学观,不能根据一个抽离语境的概念“奇”的内涵和价值倾向推论出两书文学观的对立,也不宜从形上笼统的儒家文学观直接推导出具体观点的同异,单个概念和基本文学观的比较都应以对《文心》和《诗品》理论内涵和概念关系的整体把握为前提。从核心观念看,《文心》与《诗品》都是以六朝文体观为理论平台(六朝文体观是对文章自身整体存在及其内在结构和特征的自觉),属于六朝文体批评的不同维度:《文心》为解决“文体解散”之弊,借助五经文体典范重构一般文体规范,突出的是文体的历时性正变与共时性结构之维,故《文心》之“奇”与一般规范文体或典范文体之“正”相对,指的是异于规范文体并能够破坏文体内在完整统一的新奇、浮诡、险仄的因素和特征。《诗品》要解决的则是诗作太多而不辨文体优劣的问题,突出的是作者文体间的品第之维,故《诗品》之“奇”与常见作者文体的“平”“庸”相对,指的是在一般文体规范基础上能充分体现文体的“自然”品质与作者“才气”的独创性和生命力的优秀文体品质。两书之“奇”评价的是不同维度的文体关系,因此两者之间是差异互补,而非相互对立。
《文心雕龙》;《诗品》;奇;文体维度;差异互补
引 论
在《文心雕龙》和《诗品》的现代研究史上,中日学者间曾有过一场延续20多年、参与人数较多的学术论争。论争的对象是刘勰《文心》与钟嵘《诗品》文学观的异同,焦点则是《文心》与《诗品》中“奇”一词所表达的文学观是否对立。论争始于1982年第2期《文艺理论研究》发表的日本中国古典学者兴膳宏的论文《〈文心雕龙〉与〈诗品〉在文学观上的对立》(彭恩华译,以下称《对立》)。其后若干年有萧华荣、邬国平、谭帆、张明非、王运熙、吴林伯、蒋祖怡、贾树新、禹克坤、梁临川等中国学者,先后著文对兴膳氏的观点作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回应,同时对《文心》与《诗品》的文学观异同作了更广泛深入的比较。除谭文和梁文外,大部分文章都对兴膳氏的“对立”说持否定态度,而倾向于认为刘、钟文学观基本相同或大同小异。1993年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氏又撰《中国1980年以后钟嵘〈诗品〉研究概观——以〈诗品〉、〈文心雕龙〉文学观异同之争论为中心》(周文海译,日本《中国文学报》第45册)一文,对中日学者围绕刘、钟文学观是否对立的论争作了详细介绍和评点,其赞同兴膳氏“对立”说的立场非常明确,而评析中国学者观点和论述时则不乏直率和尖锐。清水氏自道其用心,是担心“日中之间好不容易引起的争论将要半途而废”,希望以这种“突出”的方式激发论争者对这一问题继续探讨交流的热情。但清水氏“激将法”的效果并不明显,中国学界并未对他这篇挑战意味甚浓的文章作直接回应。2000年此文的主要部分又以《与兴膳宏之钟嵘刘勰文学观对立说论争概观》(张继之译)为题再次发表在当年第1期的《许昌师专学报》。作者显然心有不甘,认为这一问题并未尘埃落定,还有继续论争的必要。2000年后至今,比较《文心》与《诗品》异同并涉及刘、钟论“奇”的文章仍时有发表,如石家宜、王承斌等人的相关论文,其中对兴膳氏“对立”说也有肯否之别,如石文将二人论“奇”的对立视为两者诗学观整体差异的重要体现,王文则从整体层面证明刘、钟包括“奇”论在内的诗学观的性质应该基本相同。
综观三十余年来直接或间接参与这场论争的双方的文章,笔者虽不赞同清水氏的基本论断和“裁决”,但和他一样认为这场论争确有接续的必要。尽管整体上看论争双方尤其是回应方的中国学者已经从宏观到微观对《文心》与《诗品》作了较兴膳氏所论更广泛、细致的比较,但与此相关的一些甚为关键的学理问题并未在论争中得到关注和探讨,以致论争双方虽然看起来都有各自的文本根据和论证逻辑,却又难以从学理上说服对方。
撇开具体观点的是是非非,单从论述逻辑层面来看,双方文章整体上都存在一些明显的粗疏之处。如兴膳氏文直接根据《文心》和《诗品》中“奇”这一具体概念所表达的评价态度的差异,推导出两书基本文学观念的“对立”,而对“奇”和其他具体概念与两书理论体系、基本观念、概念关系之间的密切联系却未详察细辨。这实质上是以部分作为整体的逻辑前提,以单个概念内涵的表面差异作为体系对立的主要根据。在持“相同”说或“大同小异”说的诸多中国学者的文章中,则有着与兴膳氏文相反的逻辑缺陷,即习惯于先确立两书形上层面文学观念(如认为两书同属于儒家文学观)的相同之处,或者将两书产生时代的共同的“文学风气”作为理论前提(即清水氏所批评的“简单套用公式性的观点”),再分析“相同之处”的具体表现,以此反证兴膳氏的“对立”说不能成立,同时又多在“相同处”后列举若干“不同之处”,以示全面而不绝对。但这种论述方式的问题是,儒家文学观是包括《文心》和《诗品》在内绝大多数传统文论著作的基本观念,如果在比较某些具体文论的文学观念和概念内涵时都直接以这一形上观念为大前提进行推论,就很容易将具体研究对象同质化、普泛化,不能准确把握这些文论著作的特殊内涵,也无法呈现其理论体系和概念关系的内在逻辑,结果往往只能停留于看似全面实则浮浅的平面式罗列以及看似辩证实则简单的“一分为二”式划分。另有一类中国学者的回应文章,直接就兴膳氏文的主要论据“奇”一词在两书中的意义关系作重新阐释,对“奇”的不同涵义作了更具体审慎的辨析,对两书“奇”义的异同关系及可比性也作了更具体的说明,但其论述思路仍然主要是就“奇”一词本身而论,而未能自觉将“奇”纳入两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关系中进行定位、定义和定性,因此也同样难以避免兴膳氏文的简单与片面。
只有从文论(含诗论)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概念关系出发,确立其理论基点和主线,将形上观念和具体概念等不同层次的思想内容融会贯通,才能准确理解不同文论的特殊内涵,并据此对不同文论进行比较,确认彼此是否存在相同、差异或对立。因此,欲知《文心》、《诗品》之“奇”有何涵义、能否比较及是否对立,则须知“奇”在两书理论体系和概念关系中的位置;欲知《文心》与《诗品》文学观的异同,则须知两著的基本理论内涵和主要概念关系。
一、《文心雕龙》与六朝“文体”概念的基本内涵
若问《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在当前“龙学”语境中人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是一部“文章学”著作,即是一部论述文章写作之道,指导文章写作的文论著作。但是“文章学”这一笼统的说法只是给《文心》的理论性质划定了一个范围,并未反映其特殊内涵。
一种理论的特殊内涵是由其欲解决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决定的。从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入手较从理论的逻辑前提开始,能够直接切入理论核心,揭示理论的本质。《文心》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序志》篇说得很明白:“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其核心是“文体解散”一语,这是刘勰对楚汉以降文章之弊的高度概括,是他“搦笔和翰”撰著《文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去圣久远”是“文体解散”的历史根源,“辞人爱奇”是“文体解散”的现实原因,“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是“文体解散”的具体表现。“文体解散”也因此成为理解《文心》理论内涵的关键。
进而言之,“文体解散”不惟指出了问题所在,还同时明确了问题所在的具体层面——“文体”。尽管《文心》整体上是一部“文章学”著作,讨论的是怎样写好文章及如何克服长期累积、近世弥盛的文弊,但在讨论文弊的产生、表现和解决等具体问题时,则会落实、集中到“文体”层面,在“文体”层面说明问题的种种表现,分析问题产生的各种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方法。从《文心》中的概念关系看,“文体”也是诸多概念的中心:或作为“文体”的上位概念,如“道”、“神理”、“文”、“文章”等,以说明“文体”产生的逻辑前提和存在的现实根据;或作为“文体”的下位概念,如“情—辞”、“情—采”、“雅—丽”、“文—质”、“实—华”、“正—奇”等,是对“文体”规范、构成和特征的描述与评价。至于“奇”与“文体”的概念关系,刘勰在这段话里实已作了一个很基本的提示,即“奇”是导致“文体解散”的主要因素,是“文体”之弊的主要表现,其内涵和性质都与“文体”密切相关。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为什么是“文体”?刘勰为什么把文章写作的问题集中到“文体”层面来谈?这可以从“文体”自身的内在规定(即“文体是什么”)及刘勰所处的文章观念和文论话语的历史语境两个方面来理解。
说到“文体是什么”,我们很容易想起学界对古代“文体”一词的种种解释。最常见的是“体裁”与“风格”二义说,其次是徐复观提出并被很多学者接受的“体制”(“体裁”)、“体要”与“体貌”三义说,余者还有“四义”说、“六义”说,甚至十多义说者。从“文体”释义的形式看,研究者似乎有一种以多为贵的心理,以为释义愈多就愈能表明研究的细致和全面,也愈能体现“文体”概念的多义性和复杂性——而且这也似乎符合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缺乏统一界定、涵义模糊多变的整体印象。但实际上这些“文体”释义及其思维方式中的误区和误解甚多,笔者对此有详细辨析和指正:其中既有近现代以来所受到的西方文类学与语体学(Stylistics)两论并列模式的长期曲折的隐性影响,也有释义者对古代文体论观念内涵和话语特征的隔膜。破除陈见的最好办法就是直接面对原始文献,根据文论自身的内外关系,运用理性常识和一般逻辑规则进行分析、归纳和推理。
文体究竟是什么?《文心》实已提供了足够的线索。上引“文体解散”一语甚为关键,不妨仍由此处入手。所谓“文体解散”,其直接的字面意思是说文体已遭分解、破碎,不再完整、统一;但这句话同时也提示了文体的另外一面,即正常的文体应该是完整的、统一的,完整与统一应该是文体最基本的内在规定。刘勰关于文体的这一基本观念在《文心》全书中有非常自觉和充分的体现:
首先,《文心》屡以人和动植的有机生命整体直接譬喻文体的完整与统一。其中尤以《附会》篇的表述最为集中鲜明,如谓“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其中“体制”为“文体构成”之义。这是从具体结构层面将文体与人的有机生命整体类比。又谓“首尾周密,表里一体”,这是从首尾和表里关系强调文体的完整和统一;“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这是强调文义的统一和贯通对保持文体有机完整的重要性。其他篇中也有类似表述,如《章句》篇谓“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这是以内外首尾的统一喻文体的有机统一。
其次,通过直接描述文体的具体构成呈现文体的完整与统一。如《宗经》篇云:“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体有六义”,意为以五经文章为典范的文体应符合六个普遍要求。其中“情”与“风”为一组,“风”为“情”之用,是发挥感染教化作用时的“情”(参《风骨》篇);“事”与“义”为一组,可合称“事义”,指为文章征信的事类及其所涵义理;“体”与“文”为一组,主要指文体的表现形式和语言修饰。(“体约而不芜”之“体”偏指文章的整体直观,相对于人之“形体”,而与“体有六义”之“体”有异,后者取“整体”之义。)如果再进一步概括,这“六义”三组又可分为两类,前四“义”为文意内容,后二“义”偏指语言形式。显而易见,这“六义”、“三组”、“两类”正是一篇完整文章的基本构成要素,统一起来即为完整之文章。
第三,从《宗经》篇“体有六义”一段还可看出,“文体”之完整统一实为“文章”之完整统一的体现,“文章”之完整统一乃是“文体”之完整统一的基础。前引《附会》篇一段即已显示,构成完整统一之“文体”的基本要素如“情志”、“事义”、“辞采”、“宫商”(即声律),也即一篇完整统一之“文章”的基本要素。由此关系可见,作为“文体”之基本内在规定的完整统一并非仅属“文体”的某种特殊之物,也不是某种特殊的概念内涵,其实质是“文章”内在基本要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刘勰反对“文体解散”,实因“文章”不能“解散”。作为人之心灵的创造物,“文章”不仅具有如一般人工制品那样的完整结构,更有如其创造者一样的生命有机性。因此,有机的完整统一本来即是一篇合格“文章”的基本要求,刘勰论文也自当以这一基本要求为基础。受传统及六朝流行的文章观念影响,刘勰在具体论文时习惯于将完整文章的基本构成要素二分为“意”与“言”、“情”与“辞”、“义”与“辞”、“情”与“采”等,以此为框架描述不同类型或不同作者文章的特征,总结一般文章写作的普遍规范或不同类型文章写作的特殊要求。比较而言,《文心》下篇综论文术主要在一般层面体现了刘勰对二分式文章整体结构的理解,如“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神思》),“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神思》),“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体性》),“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风骨》),“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风骨》),“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情采》),“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理资配主,辞忌失朋”(《章句》),“或义华而声悴,或理拙而文泽”(《总术》),“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子云)故能理赡而辞坚矣”(《才略》),“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知音》)等。上篇“论文叙笔”则主要体现了刘勰在分论各类文章时所贯穿的二分式构成意识。如《诠赋》篇论赋体:“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颂赞》篇论赞体:“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杂文》篇论连珠体:“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论说》篇谈论体:“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要言之,刘勰对“文体”的内在整体构成的认识与其对“文章”的内在整体构成的认识是相互统一的;从“文章”的内在整体构成层面来看,更有助于深化对“文体”之完整统一性的体会和理解。

如果说“卦体”、“国体”、“君体”、“臣体”、“政体”、“治体”、“兵体”等概念反映了人们对身外不同事物整体存在的直观认识和自觉,《人物志》之“九征”论和“体别”论总结了东汉后期以来对个人之独特存在的整体认识和自觉,那么,以“体”论文及“文体”概念和文体论的产生,则反映了人们对文章自身有别于其他事物的整体存在以及不同类型文章自身整体存在的自觉。纵观古代文论的发展历史,正是在东汉萌芽、魏晋成熟、南朝集大成的“文体论”出现之际,古代文论进入了彬彬大盛的时期。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文体论的视野中,论文者的关注中心在整体上从文章的教化功能和润色功能等外部关系转向了文章自身的内部关系,转向了对“文体”类型特征辨析、“文体”内在构成、“文体”写作规范和方法、“文体”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要之,“文体”已经成为六朝人认识文章和文章实践的观念平台。因为文体论的产生,人们对文章自身的整体构成的认识空前具体,在传统的言意、神形、文质、辞情、词义、事义、辞采等概念之外,气韵、神韵、风韵、情韵、风骨、风力、气力、骨力、骨鲠、气质、形似等取譬于人之生命整体的文论概念大为流行,而且以“文体”概念为核心直接衍生了一系列表示文体构成的概念,如体制、体裁、体式、体要、体义、体气、体韵、体势、体统等。因为文体论的出现,文章分类进入文体分类(“辨体”)阶段,人们对不同类型文章及其特征的辨析日益精细。由于“文体”(即文章自身的整体存在)成为关注的中心,人们认识“文体”的角度摆脱了传统的约定俗成的“文类”区分(诗、赋、奏、议等分类)的限制,获得了全方位的开放与自在,可以根据认识的需要从任何一个角度和层面区分“文体”:内部与外部、宏观与微观、文类(相对客观)与作者(相对主观)、个人与时代、文义与文辞、题材与结构、概括与具体……随着文体分类的多样化,文章自身的特征也得到多方面、多层次的呈现、概括和描述。如曹丕《典论·论文》将奏议、铭诔、书论、诗赋四类文体的特征分别概括为雅、实、理、丽;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一段辨析更为具体;而在《文心雕龙》的《明诗》至《书记》20篇中,每篇都有对一种至若干种文体特征的精当总结。这种在“文体”名义下对各类文章特征的规定与东汉刘熙《释名》之《释书契》和《释典艺》两卷(其时“文体论”尚未成熟)对近四十种文类的解释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关注的是各类文章自身的特征,而后者说明的则是各类文章的功用。此外,人们还开始区分不同作家、不同时代的文体,如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将当时作者文体分为三类,并分别描述其特征;《南齐书·武陵昭王晔传》有“谢灵运体”之说;《宋书·谢灵运传论》提出自汉至魏的四百余年间“文体三变”,并举有每种文体的代表作家;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所归纳的贾生之“文洁而体清”、长卿之“理侈而辞溢”、子云之“志隐而味深”、子政之“趣昭而事博”、孟坚之“裁密而思靡”、平子之“虑周而藻密”、仲宣“颖出而才果”、公干之“言壮而情骇”、嗣宗之“响逸而调远”、叔夜之“兴高而采烈”、安仁之“锋发而韵流”、士衡之“情繁而辞隐”等,更显示时人对作者文体的鉴识、区分之全面和精确。(这些关乎作者、时代等的“文体”概念,学界多释为“风格”,不确。应同样指文章之整体存在。下文论《诗品》之“文体”概念内涵时详解。)
通过“文体”观念与“文章”观念的这种比较,我们可以对“文体”概念形成这样一个认识:“文体”概念是“文章”概念的发展,是对“文章”之现实存在的进一步自觉,“文体”突出、彰显了“文章”自身的整体存在,由此将文章自身的各种内外关系、整体与构成、类型与特征等充分呈现出来。“文体”概念的基本内涵可理解为:呈现了丰富构成与特征的文章整体存在。其中“整体存在”是基础,“构成”和“特征”是对“整体存在”的内部关系的具体认识。
二、《文心》之“奇”与刘勰文体重构的规范之维
刘勰《文心雕龙》正是在“文章整体存在”这个基本层面确立其全部论述的。整体性是文章写作的基本要义,文体的完整统一自然也是刘勰确立文章写作规范、衡评文章写作利弊的基本标准。围绕这一基本标准,刘勰在《文心》中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说明内在完整统一的文体应该是什么样的,怎样才能写出完整统一的文体?二是说明“文体解散”是如何导致的,有什么具体表现?应该如何克服?“完整统一之文体”与“解散破碎之文体”是刘勰论文的两端,很多具体问题即在这两端之间展开。
文体的完整统一在《文心》中并非笼统的规定,而是有多层次内涵和丰富的具体形态。从文体的基本结构来看,“完整”最基本的要求是言与意、情与辞的统一,这也是刘勰论文一以贯之的思路和理念(见前)。但在具体文章中,言与意或情与辞的统一又有其具体的呈现方式。从文章类型看,可分为五经文体的内在统一与一般文体的内在统一两个层次。关于五经文体内在统一的表述集中在《征圣》、《宗经》两篇,如谓“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征圣》),“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征圣》),“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宗经》),“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宗经》),“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宗经》)等。至于对一般文章的完整统一的要求,在“论文叙笔”各篇的“敷理以举统”部分有集中总结和明确规定(见前引)。但在刘勰的观念中,与经典文体的完整统一相比,对一般文体的内在统一关系的总结带有明显的理想性质——与其说是对现实文章特征的总结,不如说是刘勰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理想标准和要求。因为至少在刘勰看来,现实情况是,自楚汉以后,各体文章(以辞赋最为典型)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文体解散”的弊病。这是刘勰论文的靶的,只要有机会就会对此痛砭一番。如《诠赋》篇:“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定势》篇:“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情采》篇:“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刘勰的这些论述,对文体的完整统一和“文体解散”的具体状况作了相当清楚的说明。刘勰以五经文体为完整统一之文体的极则,其特点可概括为:其一,完整统一文体的内在基本结构关系是“意”(或志、义、情、理、旨等)与“言”(或辞)的统一。其二,完整统一的文体对“意”与“言”有一定的要求,要求文义真实可信,真挚深刻,合乎道德,充实精要,要求文辞端直精约,表达准确,条理清晰,修饰恰当。简言之曰“正言体要”,即用端正规范、准确精炼且修饰恰当的言辞表达真挚的情志和精深的事义。“文体解散”的现象在楚汉以后的辞赋中最为常见,其表现可概括为:其一,“文体解散”同样与“言”和“意”两个文体基本要素有关,是两者统一关系的偏离和破坏。其二,“文体解散”的问题在“言”和“意”两个方面各有表现:一方面是“逐末”,一方面是“弃本”;一方面是“采滥”,一方面是“忽真”;一方面是“心非郁陶”,一方面是“苟驰夸饰”……简言之,即一方面缺乏真情实感,无深刻事义,不合乎道德教化;一方面过分追求辞采,滥施雕饰,夸大其词,炫耀技巧。
就这样,通过正反对比,刘勰将文章演变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集中到文体的内在关系中来讨论,将文章的纵向衍变转换成文体的横向结构,在意与言、情与辞的相互关系中展开具体论述,根据意与言、情与辞关系的不同状态评价其价值的正反,表达自己的臧否。
由此也可知,刘勰要解决的“文体解散”问题乃是文章写作中一个最基本、最普遍的问题,他要总结的是一篇“好文章”的基本规范,他所提出的是一篇“好文章”的基本要求。他根据文章(文体)的内在要求,为所有的“好文章”划出了一条底线,即文体不能“解散”,文体至少要完整统一。这条“底线”也为我们理解《文心》中的诸多评价性概念的关系、涵义和性质提供了明确的基准,也是我们理解“奇”一词性质与涵义的基准。
兴膳氏《对立》一文曾说“奇”一词在《文心》中的涵义“具有循环小数那样不可分割的特征”,以喻《文心》中“奇”义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大略看去,似乎的确如此。但倘若以刘勰论文的“底线”(即文体不可解散,文体内部应该完整统一)来衡量,会发现在“奇”的看似模糊难辨的用法中自有区分其涵义性质的内在根据。这就是:如果“奇”的因素和倾向被控制一定程度,并未破坏文体的完整统一而导致“文体解散”,那么这一类“奇”就至少不含有负面价值。如“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正,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等例中之“奇”。反之,如果“奇”的因素和倾向突破了文体完整统一的“底线”而致“文体解散”,那么这一类“奇”就具有明显的反面价值。如“新奇者,摈古竞今,危趣侧诡者也”(《体性》),“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风骨》),“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时序》),“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知音》),“辞人爱奇,言贵浮诡”(《序志》)等。
在刘勰的文章观念中,作为众体之源的五经文体是最初的“正体”,所谓“经正纬奇”、“四言正体”等,而后世那些以五经文体为楷式的一般文体也会被纳入“正体”之列,如谓“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论议》)。五经“正体”的特点是义与言、情与辞的高度统一。刘勰对此有两种描述方式:其一是结构性描述,如谓“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等;其二是评价性描述,如谓“商周丽而雅”,“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等。“正体”不唯有真实、端正、精深的文义,亦且有恰当精美的修饰,但这些修饰都是必要的,是“文章”自身规定性的正常体现,所谓“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与之相对,“奇”是被刘勰视为五经“正体”的异数而出现的。“奇”本义为“异”(《说文》),故在《文心》中,凡异于“正体”的因素和倾向,基本都可以归入“奇”之类。纬异于经,故曰“经正纬奇”;《楚辞》异于五经,故称《楚辞》的出现为“奇文郁起”。相对而言,《楚辞》对后世文章的影响较纬书大得多,为后世辞赋之祖,辞人之渊薮,故《楚辞》之“奇”也成为后世文体之“奇”的重要渊源。“奇”的出现,对以高度完整统一为要求的“正体”文章观形成了挑战甚至威胁,并造成了实际上的破坏。不过,刘勰论文一直采取“唯务折衷”的谨慎态度,使得他并未对“奇”这个“正体”的异数一概否定。刘勰倡导文章“宗经”,以经体为正,但其目的不在复古,而在纠偏;刘勰不满因“辞人爱奇”造成的浮诡、穿凿、怪诞文风,但他并不因此逢“奇”必反,而意在戒其淫滥,导之入正。
这样,根据“奇”与“正体”的不同关系,《文心》中的“奇”在意义和价值上被区分为两类:一类“奇”可为“正体”驾驭和控制,在不破坏文体完整统一的前提下,还可增加文体的内在张力,增强文体的表现力和生命力。另一类“奇”则已走得太远,违背了文体的基本规范和要求,破坏了文体的基本结构。因此,依据刘勰确立的文体底线,不仅可以恰当区分《文心》之“奇”的不同价值与涵义,且可以从文体的内在结构关系的变化揭示“奇”之不同价值和涵义的产生机制。以此再反观兴膳氏的“不可分解”说,就能够看出其含糊所在。另外,兴膳氏对《文心》中“奇”义两用的解释是:“立足于正统性的基础之上,‘奇’能转化为崭新与独创性;在偏离正统性时,就会沦于反常一途。”乍看似乎很明白,但何谓“立足于正统性基础”?又何谓“偏离正统性”?仍语焉不详,因未从“正体”的内在关系说明“正统性”及“偏离正统性”的具体机制。又,“偏离正统性”为“反常”,但“崭新与独创性”也同样是“反常”,为何两者价值又有正反之分?据前文所论,《文心》“奇”义两用的实质不是“立足于正统性”与“偏离正统性”的对立,而是“偏离正统性”的程度有别:能为“正体”(即正统性文体)吸纳、驾驭之“偏离”为利,而不能为“正体”所控制,反而破坏文体完整统一之“偏离”为弊。
分析“奇”作为一般用词的语义特点和规律,更有助于理解《文心》“奇”一词的用法和涵义。《说文》释“奇”有二义,一为“异”,一为“不耦”。两义之间有一定关联,但兴膳氏及后来论争者所讨论的“奇”主要与“异”这一意义相关。所谓“异”,即不同于一般事物、情况和特征。如《淮南子·主术》篇:“夫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公劳而用朋党,则奇材佻长而干次。”高琇注“奇材”之“奇”曰“非常为奇”。因此“奇”本身即包含了比较的性质,相对性、比较性是“奇”一词的基本规定。不过,“奇”之异于一般、正常或平常之事物、状态和特征,只是一种中性的规定,其本身无所谓褒贬。“异”这一中性涵义使得“奇”在具体使用中能借助语境或与其他概念的关系,生成很多有具体规定和确定价值倾向的涵义。如《老子》第57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汉书·王褒传》:“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此类例中奇兵、奇战、“奇士”、“奇文”以及前引《淮南子》“奇材”之“奇”,显然都表示不同一般、有异平常且值得肯定的事物品质。在此语境中,“奇”之“异”具体化为手法超常、不拘陈规、卓越杰出之“异”。又如《礼记·曲礼上》:“国君不乘奇车。”《管子·任法》:“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国语·晋语》:“奇生怪。”这几例中的“奇车”、“奇邪”、“奇怪”之“奇”,则具有明显的贬义,所指为有异正常的应予否定的性质。
“奇”一词表义的这种相对性与其词性直接相关。“奇”解作“异”时,其基本词性应为现代所说的形容词。从其所说明的事物来说,“奇”是对该事物性质的一种形容;从其使用者来说,“奇”反映使用者对该事物的评价和情感态度。因此,“奇”一词究竟是褒义还是贬义,取决于“奇”所评价的事物自身的内在关系和使用者对该事物内在关系的认识和评价(一体两面,实不可分)。这是确定“奇”一词在具体语境中所体现的价值倾向的关键。如前引《孙子·势篇》之“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若仅看到“奇”与“正”对,尚无法确定“奇”的性质是褒是贬,甚至可能认为“奇”有贬义。但如果注意到“奇”与“正”都是对战法性质的形容,而战法的内在要求是以“胜”为佳,那么能致胜的战法之“奇”自然是值得肯定的。其他如“奇士”、“奇材”、“奇文”等词中之“奇”,是对超出常人才能或超出一般文章品质的形容和评价,故亦为褒义。而《礼记·曲礼上》之“国君不乘奇车”,此“奇”所以为贬义,究其根本是因为不合乎国君之车的正常礼制。下面两例能让我们看得更显明。《周礼·天官·阍人》:“奇服怪人不入宫。”《九章·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同为“奇服”,但前贬而后褒,其根由在于前例“奇服”之“奇”为不合乎正常服饰规范和礼制之“异”,后例“奇服”之“奇”体现的是较一般服饰更显主人公情志美好高洁之“异”。
因此,欲区分和确定“奇”之褒贬,既要看使用者的态度和倾向,还要看“奇”与所形容、评价之事物的内在关系。从认识“奇”的角度来说,使用者的态度和倾向可作为确定“奇”义褒贬的直接依据,而“奇”所评价之事物的内在关系和要求则是决定“奇”义正反的根据。而且,理解了“奇”所评价之事物的内在关系,不仅有助于区分“奇”义褒贬,更重要是能够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此处之“奇”为正面评价,而彼处之“奇”为反面评价。
为了使本义为中性之“异”的“奇”在具体语境获得确定的具体内涵和价值倾向,使用者除了以其所评价的事物内在关系为根本依据外,还经常会通过中性之“奇”与其他情感和价值色彩明显的概念相结合来表现。如《礼记·祭义》:“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礼也,虽有奇邪而不治者,则微矣。”《史记·留侯世家》评张良:“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面,状貌如妇人好女。”王充《论衡·对作》篇两例:“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又云:“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奇”与“伟”合词,“伟”是褒义,故“奇”与“奇伟”也为褒义;“奇”与“邪”、“怪”相合成词,则明显为贬义。借助《文心》中的概念关系,也可以更直接判断“奇”的涵义和价值倾向。《文心》论文体之“奇”主要有如下数例: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辨骚》)
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辨骚》)
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按:同“正”),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
新奇者,摈古竞今,危趣侧诡者也。(《体性》)
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
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风骨》)
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定势》)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定势》)
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秉兹情术,可无思耶!(《定势》)
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时序》)
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知音》)
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通变》)
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追异,故喉唇纠纷。(《声律》)
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序志》)
前引兴膳氏、邬氏、贾氏、王氏等人文章都认为《文心》中“奇”一词有褒贬两义和正反两种价值,但细味上引数例,除第一例“奇文郁起”之“奇”为明显赞赏之义外(此例之“奇”与其他数例之“奇”属不同维度,后文析《诗品》之“奇”时详论),其他数例之“奇”与其说有正反性质的对立,不如说是中性与反面的程度之别。如:双方多认为“酌奇而不失其正”、“执正以驭奇”中的“奇”有肯定之正面价值,但既为正面价值,为什么还需“酌”之、“驭”之?至于“马扬沿波而得奇”,根据上下文意,此“奇”应该也属于“酌奇”之“奇”。倘若再比较双方多认可的《文心》反面之“奇”的使用特点,可以进一步证实这里的怀疑。在上引数例中,这些具有明显贬义色彩的“奇”在使用时有一个普遍特点,即多与其他贬义色彩更加明显的概念并举;或者不如说,这些“奇”的贬义色彩并非由其自身显示,而是来自其他贬义概念的限定。如“新奇”之“奇”定性于“危趣侧诡”,“奇字”之“奇”定性于“纰缪”,“效奇”之“奇”定性于“颠倒”,“奇意”之“奇”定性于“诡俗”,“爱奇”之“奇”定性于“浮诡”等。因此,的确很难直接说《文心》之“奇”有明显的正反之分和褒贬之别。
但如果回到前文总结的“奇”义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即“奇”本义为“异”,为价值中性概念,其具体涵义和价值倾向由语境决定,也许就能对《文心》之“奇”的表义特点有一个更切合《文心》语境的理解。在《文心》中,“奇”首先是作为有异于“正”的因素出现的,也就是说,《文心》之“奇”最基本的规定是“异于正”。刘勰将五经文体和能“宗经”的一般文体立为“正”体,即已经明确了关于文章正面价值的归属。刘勰既以“正”体为正面价值所在,则对于那些异于“正”体的文章因素和属性,自然需要用其他概念来概括。从这一内在逻辑来看,刘勰没有必要再使用与“正”相对的、有异的“奇”一词来表示文章的正面价值。理清了这一关系,便可以对“奇”在《文心》中表义特点作一个整体概括:
第一,“奇”以本义“异”为基础,在《文心》中表示有异于“正”体的文章因素、性质和倾向,因此“奇”在《文心》中不具有明确的正面价值。第二,“异”于“正”体的“奇”在《文心》中也并不内在地、自然地具有反面价值,因为差异不等于对立。第三,细味刘勰的表述与修辞,“奇”价值倾向的正反最终取决于作家对“奇”这一异于“正”体的文体因素和性质的态度:如果是“爱奇”、“苟异”或“逐新”,即将“奇”作为喜好和追求的对象,“奇”就会具体表现为“诡”、“怪”、“乱”、“黩”、“讹”、“诡巧”、“诡俗”、“浮诡”、“颠倒”、“纰缪”等,成为“正”的否定因素,体现为反面价值。此即“逐奇而失正”,“苟异者以失体成怪”。如果能“酌奇而不失其正”,“执正以驭奇”,坚守“正”体的规范和要求,对“奇”的因素和性质作审慎辨别和选择,在不破坏“正”体的内在结构的前提下,适当融入一些“奇”、“异”、“新”的因素,如《楚辞》的“伟辞”、“朗丽”、“耀艳”、“深华”等,实现古与今、旧与新、正与变之间的平衡,这样的“奇”就是被允许的,是可以接受的。但从价值倾向来看,这种“奇”与其说是正面的,不如说是中性的。第四,《文心》中“奇”一方面常常与负面价值内涵明显的概念相关联,并由这些概念规定其具体的语境内涵,一方面又需接受“正”的约束和驾驭,但却几乎不与那些具有明确的正面价值内涵的概念相结合,没有出现诸如“奇伟”、“魁奇”、“奇杰”等一类有正面价值倾向的双音节词。由此一端也可看出《文心》之“奇”概念整体上不表示正面文体价值。试将《文心》中“正”与“奇”的价值关系图示如下:

相较于多数将《文心》之“奇”的价值内涵分为正反两种的观点,石家宜先生对“奇”义性质的区分和整体把握似更有分寸。他认为,刘勰所谓“奇”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源于屈赋的不同于“经”的创作倾向和特色,对此他虽未否定但又处处防范;第二层意思指的是“等而下之的辞人之‘奇’,即形式主义淫靡文风的末流”,是刘勰全面否定的。但总的来看,“‘奇与正反’,正是一条与传统文学路线相悖的另类路线”,与六朝淫靡文风有密切联系,因此刘氏始终主张“以‘正’驭奇、以‘正’统奇、以‘正’制奇”。但石家宜先生紧接着又根据《诗品》对“奇”“赞不绝口”,得出刘、钟文学观有守成与创新之异的结论,则又显得有些仓促。
如石家宜先生所说:“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目的本为遏制每况愈下的形式主义新变文风……以‘经’为体,以‘变’为用,构成了他观察和规范文变的根本。”但还需指出的是,刘勰始终是从文体内部的结构关系这一层面来观察和规范文变的,因此他将文变带来的负面问题归结为“文体解散”,将文变的主观原因归结为“辞人爱奇”,将用以规范文变的经典文体的特征描述成“正言体要”,而将能够做到“昭体”与“晓变”统一的文体特征描述为“意新而不乱”与“辞奇而不黩”。历时的经典之“正”与文变之“奇”被内化为文体共时结构的不同状况,并根据文体结构关系的状况判断“奇”相对于“正”的性质和内涵。说得再形象一点,刘勰藉此所呈现的是一个由纵横二维组成的文体评价系统,这个文体评价系统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历时的正奇通变与共时的正奇合离,标示出一篇“堪称典范的文章”、一篇“符合规范的文章”以及一篇“失体失范的文章”分别对应的“函数变量”——“奇”——的“取值范围”及各自呈现的“函数图像”。
三、《诗品》之“奇”与钟嵘文体品第的高下之维
《诗品》中“奇”一词的内涵与性质也自当根据《诗品》的理论体系和概念关系来理解,而《诗品》中理论体系和概念关系的特殊性也同样是由《诗品》所解决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所决定的。观《诗品序》全文,钟嵘批评的问题很多,大小不一,但核心问题应该在《诗品序》第一部分即全书总序的这段话中:
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嵘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这段话出自《诗品》总序,于文于义应该是对作者所欲解决的主要问题的评述。钟嵘所批评的问题有:五言诗爱好者众多,但良莠不齐;五言诗创作数量极大,但文体平庸杂乱者为多;单独看不乏精彩,但整体看多数平平;学诗者喜新厌古,不辨高下,弃高明而择下乘;评诗者一任喜好,不辨优劣,随口臧否而不立标准。概言之,即当时五言诗的学习、创作和鉴赏中都存在着良莠不辨、优劣不分的问题,致使五言诗创作的整体水平低劣平庸。
序文接下来一段从评述前代文论得失角度进一步明确了《诗品》的论文(诗)宗旨: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
前段文字直接批评现实中的五言诗写作问题,不妨详述;这段文字则由点评前人论文得失间接提示,更为扼要。一方面是现实作者优劣不辨,朱紫莫分;而另一方面是前代论者“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并义在文,曾无品第”。作者“不辨优劣”,多不能也;论者“不显优劣”,多不为也。两相映照,《诗品》主旨甚明:品第五言诗优劣,确立五言诗优劣的标准,通过论者“显优劣”帮助作者“辨优劣”,以取法“高明”,预于“宗流”。
“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一句不仅指明现实问题所在及《诗品》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且间接表明《诗品》与前代论文著作之不同。虽然比较对象中没有提及《文心雕龙》——原因可能有多种:或尚未接触《文心》,或已知晓《文心》但对同时在世者有意回避,但根据《文心》的主要内容(《梁书·刘勰传》即言《文心》“论古今文体”),也当归入钟嵘所说的“就谈文体”著作一类,因此这句评语实际上也适用于《诗品》与《文心》的关系。据此,这句话不仅是理解《诗品》理论内涵的关键,亦且是理解《诗品》与《文心》异同的关键。循此入手,能够在比较中更鲜明地呈现《诗品》的理论体系和概念关系。
学界常引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诗话》中的一段说明《诗品》与《文心》之别:“《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体大而虑周”与“思深而意远”、“笼罩群言”与“深从六艺溯流别”云云,概括确有见地,但在概括时也不可避免地将两者的差异抽象化了,可能会因此掩盖掉一些更能体现两者关系本质特征的关键表述。另外,这种概括性评价也可能会偏离对象的理论中心,造成以次为主的误读。如章氏突出《诗品》的独特性在于“深从六艺溯流别”,此说虽不为无据,但从《诗品序》无一语道及来看,宜并非钟嵘著《诗品》的命意所在,而更适合理解为对传统论文惯例的沿用和对“品第优劣”的强化——既能明其优劣之所在,又能知其优劣所从来。且“从六艺溯流别”之例实际只见用于小部分诗人诗作,而非真正一以例之。因此,从钟嵘本意和《诗品》的内在体系来看,似不应特别突出“溯流别”在《诗品》中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无论是根据《诗品序》的自明宗旨,还是从《诗品》的实际内容看,“品第优劣”都是《诗品》论诗的主旨、主线和主体。
明确了理解《诗品》理论特质的关键在“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一句,下面的问题即是该如何理解其意。这句话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即前代文论主要是谈文体而不是显优劣,而《诗品》主要是辨五言诗优劣而不是谈文体。观钟嵘所提及的前代论文著作之见在者,如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残)、李充《翰林论》(残)、颜延之《庭诰》论文之篇(残)等,确实是以论诗、赋、铭、诔、章、表、奏、议等一般文体为主,而所论也主要关乎各类文体的一般特征和写作要求,未尝属意于各家文章优劣。但反观钟嵘《诗品》,虽以品第各家五言诗优劣为要,但实际上“文体”(或“体”)一词使用极为频繁,其品第优劣与“文体”概念关系颇为密切。如下例:
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诗品序》)
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诗品序》)
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诗品序》)
其体源出于《国风》。(上品“古诗”评)
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上品曹植诗评)
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上品王粲诗评)
才高辞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上品陆机诗评)
文体华净,少病累。(上品张协诗评)
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上品谢灵运诗评)
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中品曹丕诗评)
其体华艳,兴讬多(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中品张华诗评)
宪章潘岳,文体相晖,彪炳可玩。始变中原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中品郭璞诗评)
彦伯《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中品袁宏诗评)
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中品陶潜诗评)
故尚巧似,体裁绮密。然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中品颜延之诗评)
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中品江淹诗评)
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馀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中品沈约诗评)
元瑜、坚石七君诗,并平典不失古体,大检似。(下品阮瑀、欧阳建诗评)
张景云虽谢文体,颇有古意。(下品张永诗评)
思光缓诞放纵,有乖文体,然亦捷疾丰饶,差不局促。(下品张融诗品)
王屮、二卞诗,并爱奇崭绝。慕袁彦伯之风。虽不弘绰,而文体剿净,去平美远矣。(下品王屮、卞彬、卞录诗评)
也就是说,直接就内容和概念来看,钟嵘批评前人论文只谈“文体”而不显优劣,他本人则实际上既谈“文体”,也辨优劣。但这一说法可能会马上招致否定,否定者可能认为,《诗品》品第优劣时所用的“文体”一词与陆机《文赋》、李充《翰林论》、挚虞《文章流别论》等前人文论所用的“文体”一词并非一个概念,前者所说“文体”的意思是“风格”,而后者所说“文体”的意思是“体裁”;《诗品》整体上属于“诗歌风格论”,而前代文论多属于“文章体裁论”。
辨析至此,已触及理解《诗品》理论内涵和概念关系的一个更具体的关键问题,即如何理解《诗品》中“文体”概念与前代文论中“文体”概念间的关系。不过,本文并不赞同流行的“风格”与“体裁”之分,这里仍然坚持前文已经提出并作过多方论证的观点,即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体”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指具有内在完整构成与丰富特征的文章整体存在,而且这一基本内涵无关乎人们对“文体”的分类——诗赋之“体”的基本内涵如此,作家之“体”、时代之“体”的基本内涵也是如此。此处还想针对《诗品》的具体情况补充几点论证:
第一,直接从用词看,《诗品》中的“文体”与“诗体”乃是同一概念之别名。书中屡屡言及的某某“文体如何”,其中“文体”并非另有所指,仍然是指某诗人所作五言诗之体,如评“古诗”,前曰“诗体未全”,后曰“推其文体”,又如评江淹“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直接用“诗体”而不用“文体”,可见在《诗品》中二词基本内涵相通。
第二,从逻辑层面看,因为“文体”表示“文章自身的整体存在”,自然会与题材、意义、结构、语言等各种文章内部因素以及作者、时代、流派、读者等各种文章外部因素有关,批评者也就自然可以从内外各种角度对“文体”进行分类,因此也就有了从文类角度区分的诗体、赋体等,从作者角度区分的曹刘体、谢灵运体、鲍照体等,从时代角度区分的正始体、南朝体等,从流派角度区分的元白体、西昆体等。但在各种分类中,作为分类对象的“文体”(简称“体”)仍然是指“文章(诗歌)自身的整体存在”。《诗品》中对诸多诗人“文体”的品第,即是从作者角度对“文体”(专指五言诗之文体)的区分。
第三,《诗品》中“文体”概念的内涵与其他文论著作中“文体”概念的内涵,都带有古人用词“用中见义”的特点,即主要不是通过自觉的逻辑化、形式化的定义来说明,而是在具体使用、分析和描述中自然见出,因此需要今人进入语境,用心体会,再以现代逻辑话语加以表述。前述《文心》如此,此处《诗品》也是如此。如评曹植诗云“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之诗既“体被文质”,也“体”涵“辞”“情”。评陆机诗曰“才高辞赡,举体华美”,则直接以“举体”一词强调了“体”即诗之整体。另外,《南齐书·武陵昭王晔传》评“谢灵运体”一节也可列为旁证:“晔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上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论者认为“谢灵运体”的缺点是“作体不辨有首尾”,也自然是将“谢灵运体”(谢灵运所作五言诗之文体)当作整体来看的。
第四,学者多将《诗品》中“文体”概念理解为“风格”,还应该与一个逻辑误判有关,即误将钟嵘所描述的“文体”之特征(如“文体华净”之“华净”、“平淡之体”之“平淡”等),作为理解“文体”概念内涵的主要根据,混淆了“文体”与文体特征的区分。其“逻辑”为:因“华净”、“平淡”等表示诗歌“风格”,故“文体华净”、“平淡之体”即意为“风格华净”、“平淡之风格”,所以“文体”即是指“风格”。但正如不应将“文章华净”中的“文章”理解“风格”,也不可将“文体华净”中的“文体”理解为“风格”。类似这种对“文体”概念内涵的误解还出现在很多地方。
辨明了《诗品》中“文体”一词与钟嵘所批评的前代文论中的“文体”一词实为同一个概念,就可以对《诗品序》中的“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这一关键判断有一个更完整、辩证的理解。观六朝论文篇章著作可知,“文体”概念应该是六朝文论中除“文章”(或“文”)概念外的一个最基本、最关键的文论概念。如果说六朝文论的研究对象是“文章”,那么就可以说“文体”是六朝文论研究文章的“平台”,尤其是理解文章自身关系的平台。钟嵘评诗不可能离开、也没必要舍弃“文体”这个理论平台。因此分析“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一句的内涵,需要根据前代文论和钟嵘《诗品》的实际内容以及这句话的句意和语气综合理解。言前人“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并不意味着《诗品》“不谈文体,只显优劣”,更合理的理解是:《诗品》区分的是文体的优劣(而非“风格”的优劣)。
理清了这句话的表里两层内涵,《诗品》与《文心》的理论特征及其关系就大体呈现出来了:包括刘勰《文心》在内的前代文论主要研究的是文体的一般结构、特征、规范和写作要求,其主要内容是区分一般文体(即文类文体,如诗、赋等)类型,辨析不同类型文体的特征,总结不同类型文体的写作规范,与此同时也呈现文体的基本结构。钟嵘称其“皆就谈文体”,即言其主要就“文体自身”而论,只谈“一般之文体”与“文体之一般”。前代文论对文体也有评价,如挚虞《文章流别论》对赋体弊病的批评,《文心》对“文体解散”现象的针砭,但这种评价不是其论文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批评与肯定,彰显文体的内在完整统一,维护文体的基本写作规范。
比较而言,《诗品》论述“文体”的角度和方式有其明显的自身特征,其主旨不在于指导学诗者掌握诗体写作的基本规范,而在于品第不同作者五言诗体的高下,帮助学诗者识别诗体的优秀与平庸。不过,《诗品》的实际内容要比这种比较式概括所突出的特征要复杂一些:作者文体的优劣品第固然是其主要内容,而五言诗体的一般规范和特征也同样有详细论述(与前代“就谈文体”的文论著作大体相同)。这是因为,按正常道理,在品第作者诗体优劣之前,自应先掌握五言诗体的基本规范和要求,明白五言诗的典范文体有何特征,而平庸低劣之作又有何缺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如《文心》那样着重“谈文体”,还是如《诗品》这样侧重“显优劣”,都需要确立文体之底线(完整统一),树立文体之高标(文质兼美)及指出种种文体之下乘。实际上,《诗品》从序文到正文,都或显或隐地体现着关于五言诗体的规范、典范和失范的意识,而且《诗品》对五言诗体基本特征和典范品质的认识与《文心》并无明显不同。其一,《诗品序》云:“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将“风力”与“丹采”的统一目为五言诗体的理想,此与《文心·风骨》篇主张内在风骨与外在文采统一以使“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的文体理想近乎完全一致。区别只在于刘勰因泛论文笔,抒情、纪事、论理各体兼综,故“风”“骨”并提,将情感之真挚感人与语言之端直有力同视为文体之本;而钟嵘所论五言为典型的吟咏情性之体,故以“风力”(即以情动人之力)为文体之本。其二,钟嵘在具体品评中也自觉体现了这一文体理想。如评作为五言诗体典范的曹植诗体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再如评刘桢诗体云:“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以其有“风”有“骨”为高,而以其缺乏文采雕饰为憾,其意与《文心雕龙·风骨》篇“鹰隼乏采”、“骨劲而气猛”之论相类。其他如评班昭诗之“怨深文绮”,评王粲诗之“文秀而质羸”,评陆机诗之“才高辞赡,举体华美”,评郭璞诗之“文体相晖,彪炳可玩”,评袁宏诗之“鲜明紧健”等,都是这一理想文体标准的体现。其三,有违这一文体理想的诗病,也被钟嵘一再批评。如评谢灵运诗:“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评曹丕诗:“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评嵇康诗:“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评张华诗:“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评鲍照诗:“贵尚巧似,不避危仄。”评宋武帝诗:“雕文织彩,过为精密,为二藩希慕,见称轻巧矣。”评惠休诗曰“淫靡”,评张融诗曰“缓诞放纵,有乖文体”等。第四,对“雅”这一文体品质一贯肯定。如谓“情兼雅怨”(评曹植诗),“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评嵇康诗),“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评应璩诗),“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评颜延之诗),“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评任昉诗),“气候清雅”(评谢庄诗)等。同时将“雅”与“俗”对举,类同《文心》以宗经之“雅正”与趋俗之“新奇”对立。如评鲍照诗:“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评张欣泰、范缜诗:“欣泰、子真,并希古胜文,鄙薄俗制,赏心流亮,不失雅宗。”
综上可见,文体的规范和典范既是《文心》论一般文体规范与否、雅丽与否的标准,也是《诗品》品评作者文体优劣高下的标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品第标准,也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品第标准,其具体内涵是在漫长的文体实践中经无数创作反复探索、调整、积累、完善而成,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和稳定性。无论是要“拨乱反正”,重建文体规范,还是要辨彰清浊,品第文体优劣,这都是一个离不开的标准。这个标准也是品第者与世人对话、交流、论争的一个公共尺度。就此而言,《诗品》与《文心》的确在文体观念层面是相通的,两者共享着大体相同的文体批评标准,因此两者的相同之处绝不止于“儒家文学观”这个笼统形上的层面,而是有着丰富的具体内涵。
不过,当《诗品》以五言诗的文体规范和文体典范为标准品第作者文体优劣时,实际上又拓展、建立了一个不同于《文心》的文体批评维度。如果说《文心》建构的是一个以“逐奇而失正”所导致的文体解散的历时衰变之维与以“执正以驭奇”所致力恢复的文体完整统一的共时结构之维构成的二维批评体系,那么《诗品》是在其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个度量和标示作者文体优劣高下的第三维度。也就是说,《文心》与《诗品》文体批评维度呈现的是一种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综合反映了六朝文论家对文体认识的广度(各类型文体的历史)、深度(文体的内在规定)和精度(作者文体的品鉴)。在建立六朝文体批评的“第三维度”过程中,《诗品》也合乎情理地与《文心》一同使用了一个属于“六朝习径”的文体标准,即要求情采符胜,质文统一,雅丽兼备。
正因为不同批评维度采用的是基本相同的文体评价标准,所以在上文具体分析中可以看到《文心》和《诗品》之间存在的这一现象:刘勰所肯定的文体因素或特征,也基本上为钟嵘所褒扬;而刘勰所否定的文体因素或特征,也多为钟嵘所贬低。表现在概念层面,刘、钟用来表示肯定和否定的具体概念也基本一致。但是,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文心》中少数为中性而更多为贬义甚至作为不合文体规范的因素和特征之总名的“奇”一词,却在《诗品》中无一例外地被用作一个表示正面价值的概念?论争中有学者正是根据这一现象认为刘、钟文学观对立或部分对立。而在已经明确《文心》与《诗品》在六朝文体批评中的关系的基础上(即两者的理论体系属于六朝文体批评的不同维度),应该可以对“奇”这个一开始就成为论争焦点的问题有一个合乎逻辑的理解:
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诗品序》)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上品曹植诗评)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上品刘桢诗评)
才高辞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上品陆机诗评)
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讬多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中品张华诗评)
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中品谢朓诗评)
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中品任昉诗评)
才难,信矣!以康乐与羊、何若此,而二人之辞,殆不足奇。乃不称其才,亦为鲜举矣。(下品何长瑜、羊曜璠、范晔诗评)
王屮、二卞诗,并爱奇崭绝。慕袁彦伯之风。虽不弘绰,而文体剿净,去平美远矣。(下品王屮、卞彬、卞录诗评)
首先,正如多篇文章(如邬文、王文等)所指出,在《文心》中“奇”是与“正”相对的一个概念,而在《诗品》中“奇”是与“平”相对的一个概念。这是显示“奇”在两书中不同价值倾向的最直接的概念关系:“正”的正面性质从对立面规定了“奇”的非正面价值(中性或反面),而“平”的消极意义则从对立面规定了“奇”的正面价值。究其原因,这首先与“奇”本义“异”的相对性有关。作为“异”,“奇”本身并没有明确的价值倾向,而由其相对关系和具体语境规定。但无论实际价值倾向如何,“奇”作为“异”,总是属于非“常”事物、性质或状态,总是有别于一般常见的事物、性质或状态。简言之,“奇”之为“奇”,是因为它有异于“常”——可以是“正常”之“常”,也可以是“平常”之“常”。因此,“奇”的基本性质和价值倾向取决于以何者为“常”。
具体到《文心雕龙》,因为刘勰处理的是文体规范与文体解散(失范)之间的冲突,所以自然是将符合规范的文体(包括一般规范文体和典范文体)作为“常”,而将有异于破坏规范的因素和特征作为“奇”。而从价值层面来看,这样的“常”自然具有肯定性的正面价值,因为符合规范的文体不仅应该是文体的常态,且也应该是文体的“正常”状态;而这样的“奇”自然具有否定性的反面价值,因为导致“文体解散”的滥采、乱意、黩辞等不仅是一类非“常”因素,也是一类非“正常”因素。也就是说,《文心》中的“正—奇”相对关系和价值倾向是由刘勰所要分析和解决的规范文体与文体解散之间的矛盾决定的。而在《诗品》中,因为钟嵘的任务是要从大量的平庸之作中挑选出一些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品,所以相对来说那些大量存在、屡见不鲜甚至很多作者都“习以为常”的平庸之作构成了当时诗坛的“一般状况”,自然就成为“常”的一面,而作为有异于这种“平常”的“奇”自然就成了少数优秀之作的品质。换言之,《诗品》中的“平—奇”相对关系和价值倾向也是由钟嵘所要解决的问题(品第优劣)决定的。
因此,“奇”在《诗品》中被视为一种很突出的正面文体品质,是一个很高的文体评价标准。首先,从文体自身的内在关系看,是否符合五言诗体的规范也是区分“奇”与“平”的一个“底线”,虽然符合五言诗体规范的作品未必可以称“奇”,但是有悖五言诗体内在要求的作品就只能归入平庸。从《诗品》的具体批评看,那些不能称“奇”或品质庸劣的诗作都会在某些方面与五言诗体的规范有违,其中尤以喜用、多用甚至滥用“事义”(即事类、典故)最为普遍。而在钟嵘关于诗体的基本观念是:“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这应该是诗体区别于奏议书论等其他实用文体的基本特征,因此他对创作中以“用事”为能的现象一再批评。如《序》中批评任昉、王融等人“词不贵奇,竞须新事”,以至“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将诗体弄得支离破碎,生气全无,而这样做不过是以增加“事义”的方法掩盖其诗作水平的“失高”。在中品,钟嵘又再次批评任昉诗“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诗品》中还多次指出诗体的“平”与用典、谈理等“贵于用事”的做法之间的直接关系,如:“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品序》)“宪章潘岳,文体相晖,彪炳可玩。始变中原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中品郭璞诗评)“元瑜、坚石七君诗,并平典不失古体。”(中品阮瑀、欧阳建诗评)
一方面违反五言诗体基本要求的“动辄用事”之诗“不得奇”,而另一方面谨守一般诗体规范之作也于“奇”有碍。如上品批评陆机诗云:“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所谓“尚规矩”,即谨守五言诗体的一般规范,其立意遣词、结构条理、辞采声律等都中规中矩。这样写出来的诗固然挑不出明显的缺点,但也很难从大量诗作中脱颖而出,表现出一种超拔卓越的优秀品质。钟嵘认为,出“奇”之诗,“规矩”之外还须有“直致”。如果说符合一般诗体规范是“奇”之文体的“下线”,那么“奇”之文体还有更高的文体要求,这就是钟嵘在《诗品序》中强调的“自然英旨,罕值其人”的“自然”,表现在具体创作机制上,即是“即目”、“直寻”、“直致”等。
从创作主体层面来看,与“自然”相对应的素质是“天才”。所谓“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以“自然”与“事义”相对,这是从文体层面说明与诗体之“奇”正反相关的两种重要因素;所谓“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以“天才”与“学问”相对,这是从主体层面说明与诗体之“奇”正反相关的两种重要因素。“自然”和“天才”分别从文体和主体两个方面规定了《诗品》之“奇”的具体内涵。比较而言,主体的“天才”因素更具有决定意义,是《诗品》之“奇”的正面价值的根源。
《诗品》论及“才”处甚多,除上引评曹植、刘桢、陆机、何长瑜等例外,余者尚有:
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诗品序》)
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诗品序》)
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诗品序》)
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上品李陵诗评)
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上品潘岳诗评)
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嵘谓:若人学多才博,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曲新声,络绎奔发。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上品谢灵运诗评)
其体华艳,兴讬多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中品张华诗评)
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中品刘琨、卢谌诗评)
戴凯人实贫羸,而才章富健。观此五子,文虽不多,气调警拔。(中品郭泰机、顾恺之、谢世基、顾迈、戴凯诗评)
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固是经纶文雅;才减若人,则陷于困踬矣。(中品颜延之诗评)
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中品谢瞻等诗评)
小谢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中品谢惠连诗评)
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中品鲍照诗评)
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中品谢朓诗评)
希逸诗,气候清雅。(下品谢庄诗评)
惠休淫靡,情过其才。(下品惠休诗评)
元长、士章,并有盛才,词美英净。(下品王融、刘绘诗评)
综观上引及前引诸例,显然不能将“才”与“天才”等同,也不能将“才”与“自然”、“奇”完全直接对应。钟嵘所说的“才”,实有层次之分:论其高则有“天才”之“才”,论其强则为“才气”之“才”,论其用则为三品者皆有之“才”。“天才”上文已述,这里再就一般之“才”及“才气”与文体及文体之“奇”的关系作一些分析。
从整体上来看,《诗品》中的“才”是一个与“文体”内外相对的概念,“才”之高下直接关乎“文体”之成败优劣。《诗品》虽诗分三品,但根据《序》中所言“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说明三品之诗都是“才子”之作,而大量平庸之作都因未预宗流而被钟嵘筛除了。在钟嵘看来,“才”是写好诗的最基本的主体条件,有“才”者才能有好诗,有“才”方能克服平庸,超出流俗,避免“繁芜”、“困踬”、“清浅”、“淫靡”等诗体之弊。正如合乎一般规范是诗体之“奇”的文体基础,有“才”应该是“奇”诗得以产生的主体基础。如“下品”评何长瑜、羊曜璠二人诗“殆不足奇”,原因即在于二人“才难”。但有“才”又并不必然有“奇”诗,“奇”诗的创造还需要比一般诗才更高的主体条件,这就是以“才”为基础的“气”。如陆机诗虽因“才高”而“举体华美”,但又因“气少于公干”,而缺少“自然英旨”,“有伤直致之奇”。刘桢诗虽因“气过其文”,而有“雕润恨少”之憾,但又因能够“仗气爱奇”,故其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张华诗则表现出某种矛盾:一方面“兴讬多奇”,一方面又“务为妍冶”;“多奇”源于“风云之气”,“妍冶”则因其“儿女情多”。但对于以“奇”为贵的“疏亮之士”来说,则以其“风云气少,儿女情多”为憾。至于曹植,因才气兼胜,故其诗能获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之至誉。
由此可见,“奇”在钟嵘心目中之所以被视为文体的一种非常优秀罕见的品质,根本原因在于“奇”是作者旺盛杰出的才气在文体中的体现。“奇”不同于符合一般规范的文体品质,甚至也不同于堪称典范的文体的品质。“奇”是对文体的一般规范的超越,是诗人借助“才气”引领文体循作者的生命之维不断提升和创新,所臻达的“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的杰出境界。《诗品》中所说的“爱奇”,乃以“仗气”为主体根基,是一种植根于诗人整体生命的创造,因此这种“爱奇”能够赋予文体充沛的生命力,使文体不仅文质兼美,雅丽相胜,而且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让文体成为生命相互感动、慰藉的中介(即所谓“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这种“奇”以其丰富的生命内涵和真正的创造精神与《文心》中所批判的“爱奇”者对那些外在于生命、附会于流俗的新异之“奇”的追逐渔猎有着根本不同。
论述至此,便可以对前文曾提及的《文心雕龙·辨骚》篇赞《离骚》之“奇”的一段话有一个恰当的理解。其云: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此句中之“奇”虽与后文“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之“奇”同属一篇,相距甚近,但两“奇”所评价的文体关系并不相同。首先,“奇文郁起”一句为赞叹语气,“奇”也无疑是对《离骚》的正面评价。其次,“奇”修饰的对象是“文”,此为“文章”之“文”,而非文字之“文”,故“奇”所评价的是《离骚》全文,而非其文采;而《文心》他篇之“奇”所评价的多是新意、诡辞、异字等具体因素。第三,此处又将“奇文”与“多才”相联系,说明《离骚》之“奇文”是因楚人之“多才”而产生,也说明此处“奇文”之“奇”是相对于其他作者文体而言,体现的是楚诗人文体的独创性,而非指违背文体规范的新异因素和特征。因此,与《文心》中其他“奇”(如该篇后文的“酌奇而不失其正”之“奇”)相比,此处之“奇”属于作者文体维度的评价概念,是一种正面评价,与《诗品》之“奇”的用法和性质相同。不过,只此一例不足以影响对两书中“奇”一词内涵和性质的整体关系的判断。
结 语
尽管《文心》中“奇”概念所涵以否定价值为主,而《诗品》中“奇”概念表现为纯粹的肯定价值,但并不能因此得出两书中“奇”概念的内涵和价值倾向相互对立的结论。这是因为:《文心》之“奇”与一般规范文体或典范文体之“正”相对,指的是异于规范文体或典范文体并能够破坏文体内在完整统一的新奇、浮诡、险仄的因素和特征,而《诗品》之“奇”与常见作者文体之“平”或“庸”相对,主要指的是在一般文体规范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文体的“自然”品质与作者“天才”、“才气”的独创性和生命力的优秀文体品质,两书之“奇”评价的是不同维度的文体关系,所以无法构成对立。更恰当的说法也许是:两者差异互补。
因此,我们不能仅根据两书中“奇”概念所表现的价值倾向,判断两者的文学观是对立还是相同。合理的比较思路不应该是先抽出两个概念比较然后推及整体,而应该先把握比较双方的基本理论内涵和概念关系,再据此辨析某两个具体概念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涉及像“奇”这样一个主要由具体语境和概念关系规定其内涵和价值的概念,更需整体把握,耐心梳理,细心分辨。
姚爱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