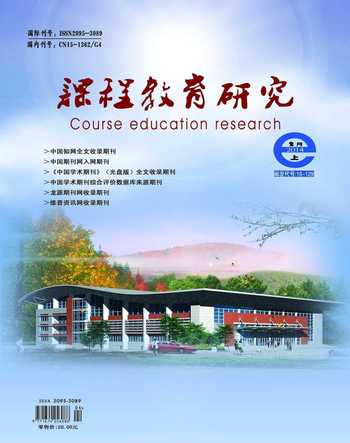《年轻的好小伙子布朗》中“粉红色丝带”的意向多义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G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2-0079-02
一、引言
纳撒尼尔·霍桑是19 世纪前半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都探索人性和道德。他还擅长在小说中运用各种各样的意向用来辅助表达主题。短篇小说《年轻的好小伙子布朗》发表于1835 年,许多文学评论家都认为这篇作品是“霍桑最复杂的小说,它揭示了一个令人懊恼的事实,就是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别人心中真正的想法。”还有许多人认为这篇作品是“霍桑对发生在1692 年萨勒姆女巫事件的最好诠释。”
《年轻的好小伙子布朗》讲述的是一位年轻的清教徒古德曼·布朗的一趟深夜旅途。布朗不顾新婚妻子费思的再三劝阻,在黄昏时分作别妻子,在一位身份不明的老人的引诱下,步入森林参加恶魔的聚会。并见到了平日里看起来德高望重的长者和自己心爱的妻子。在故事的结尾,霍桑并未给出读者明确答案:布朗所见所闻是梦还是事实,但布朗在参加完聚会后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心灰意冷且充满怀疑,直至死去。作为一名清教徒,布朗想不通为什么既然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还要将原罪带给每个人。布朗是一元论的信徒,他只能接受一个:上帝或者撒旦;善或者恶;信仰或者原罪。他的世界是个纯粹的世界,他接受不了任何不纯洁的事物,在文中唯一一位有意识地保持自身纯洁远离恶魔的“好小伙子”。
二、“粉红色丝带”的多义性
“粉红色丝带”是戴在布朗的妻子费思头上的饰品,在文中反复出现了五次。这五次的出现不是巧合,“粉红色丝带”的每一次出现都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它不只是布朗妻子一般的头饰,而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重要线索。小说中,前两次丝带都戴在费思的头上,粉红色的丝带将布朗那新婚的娇妻映衬的更加娇羞,惹人怜爱。粉红色丝带第三次出场发生在古德曼这一对新婚夫妇刚刚分别不久,“……尽管她的粉红色丝带在飘扬,但神色忧郁”我们不禁要对文中的“尽管”一词提出疑问,粉红色丝带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力量?难道因为粉红色丝带在飘扬,费思就不应该忧伤吗?在参加完恶魔的聚会后,布朗伤心欲绝,当他看到他心爱的妻子头上的粉红色丝带飘落的时候,他也随之失去了信仰。在小说的结尾,布朗又一次回到萨勒姆姆村庄,他的费思依旧戴着那条粉红色丝带迎接他,此时的费思还是那个纯洁无暇的费思吗?作者也没给出我们一个明确地答案,但是布朗的人生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他不再相信任何人,郁郁寡欢,孤独终老。
十九世纪,清教主义陷入了认识论的危机:不可知论和形而上学的矛盾。不可知论是指在上帝被清教徒严格地按照《圣经》无条件地接受,除《圣经》以外任何形式的解读都是对上帝的亵渎。当时教堂的许多神职人员利用清教徒对上帝的虔诚,制定清教徒的日常行为准则。在他们的眼中,不同既是一种罪。在霍桑的小说中,他大量的运用意象从而激发读者多元化的猜想和理解对抗清教主义中那所谓的“统一。”这就决定了我们对“粉红色丝带”的解读不可定义只可试着从不同角度分析。霍桑短篇小说中重要的意向“粉红色丝带”是用来敲醒清教主义古板腐败处世哲学的警钟。
三、“粉红色丝带”——原罪
年轻的好小伙子布朗身上带有霍桑的自传性质。布朗和霍桑的家乡都是同一座美国的历史名城萨勒姆。小说开篇,霍桑就交代说:“小伙子古德曼·布朗走出家门,来到萨勒姆村街道上,可跨出门槛又回头,与年轻的妻子吻别。”小说中其它的环境描写都是模糊的,作者所提及的唯一确切的地名就格外引人注意。这座小镇之所以有名是因为震惊全美的萨勒姆就发生在这里也是霍桑和他祖先生活过的地方。
霍桑的祖先都给他的成长刻下了深深的印记。Leland Person教授曾经表示:“在《年轻的好小伙子布朗》以及《红字》中,霍桑都在小说中渗透他个人对于家乡以及他曾经生活在萨勒姆小镇的祖先的看法。”霍桑自己也曾经这样回忆他的祖先:“他们有的是士兵,有的是法官,有的是教堂的管理者,他们身上都有清教徒的烙印,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由此可见,霍桑为和他的祖先们一样是清教徒而感到自豪。
历史所记载的霍桑的祖先都是清教徒,他们中的一些也同时因为参与多起迫害无辜清教徒案而名声狼藉。霍桑有两位非常有名的祖先。一位是萨勒姆女巫案的法官。萨勒姆女巫案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宗最惨烈的宗教灾难。1692 年夏天,萨勒姆审判法庭把十九名“巫师”送上了绞刑架。后经历史证明,这些人全部都是无辜的清教徒。负责审理萨勒姆女巫案五名法官的其中重要的一位就是霍桑的祖先——约翰·霍桑 。Margaret B. Moore 曾在《霍桑的撒莱姆世界》一书中这样形容约翰·霍桑:“霍桑与萨勒姆女巫案的纽带就是他的许多祖先都参与过对萨勒姆无辜女性的迫害。特别是梅尔·威廉 和安娜·霍桑的第三个儿子约翰·霍桑,曾经因为参与过1692 年的萨勒姆女巫案的审判,并在该审判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受人指责。他继承了迫害的基因以至于他在迫害女巫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的血液里就有着污点,这个污点已经深入骨髓,即使是被埋葬了也还是看得见。”霍桑的另一位有名的祖先也是一名法官,参与另一起迫害贵格教信徒的案件。作为这两位祖先的后代,纳桑尼尔·霍桑不可能不知道他祖先的罪行。霍桑祖先的罪行在《好小伙子布朗》有所体现。
布朗祖先的所作所为与霍桑本人的祖先极其相似。由此可见,霍桑对其祖先所犯下的错误并不是熟视无睹的,相反,他勇于承认并且还把这些故事经过加工以后写进了《年轻的好小伙子布朗》这本小说中。当粉红色色带从空中飘飘落下后,布朗对他祖先犯下的罪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粉红色丝带的飘落象征着布朗对其祖先犯下罪行态度的转变,从最初的不以为意到最后对原罪深深忏悔,布朗完成了他人生课堂中最重要的一课。
粉红色是白色与红色的结合。白色是纯洁的象征,就如同他原本心中的费思(信仰);而罪恶是鲜红的。“粉红色丝带”象征着他与费思纯洁的爱情是布朗心中快乐的源泉。也就难怪霍桑在文章开头写道:“尽管她的粉红丝丝带在飘扬,但神情忧郁。”(霍桑 250)有了“粉红色丝带,”费思就有了纯洁的爱情本是不该悲伤的,但布朗的远行却让费思失去安全感愁挂眉梢。小说开篇的“粉红色丝带”的明艳与其它阴森恐怖哥特式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它就像一道光指引着布朗在黑暗中前进。布朗的信仰随着“粉红色丝带”的飘落轰然崩塌,他认为原本纯洁无暇的人已经变了样,每个人都生来有罪。
四、“粉红色丝带”——粉碎清教教义中一元论的工具
19 世纪,一元论在清教教义中占主导位置。一元不仅论证了上帝的真实存在性还进一步加强了对清教徒的思想统治:“上帝是唯一的神,上帝的存在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好小伙子布朗深入森林参加聚会就是对绝对真理的一种探索。然而,探索的结果让他大为失望。尽管清教神职人员对清教徒的思想进行了规范和教育,但是大多数清教徒仍想布朗一样无法理解:既然上帝真实存在,为什么撒旦也存在?既然真善美存在,为什么罪与恶还要存在?这些疑问让许多清教徒像布朗一样信仰缺失,人格分裂。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粉红色丝带”纯白的特质已经被红所污染。再也没有纯粹的善,因为恶正参杂进来;上帝不是唯一的神,因为撒旦也在举行聚会;信仰不再纯粹,因为原罪正在作祟。
霍桑正是想通过 “粉红色丝带”想清教徒说明,对立体可以合理存在,这些对立体是对清教徒的考验,让他们有选择的权利。上帝赋予他的子民选择的权利,使他们成为有血有肉,有选择权利的人而不是一味地像机器人一样只懂得执行制造者所编辑的程序。清教徒选择了恶并不等于上帝放弃了拯救他。布朗的结局警示大家,怀疑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再相信善。“粉红色丝带”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管布朗怎么看它。文章的开篇,“粉红色丝带”是纯洁的象征,在文章结尾它又成了罪与恶的象征。尽管布朗经历了心灵上的巨大打击,它最后还是一动不动的戴在了费思的头发上,重要的不是它意义的改变而是布朗心态上的改变。如果在经历过恐怖森林聚会的人生探索之后,布朗仍然相信上帝是唯一的神,相信善的存在并且尽力帮助周围被原罪所困扰的人们脱离魔鬼的纠缠,他才真正是无忧无虑好小伙子布朗,他的费思仍然通过他的努力而再次纯洁无暇。遗憾的是,布朗在分不清聚会是现实还是梦境的情况下就决定放弃,不再相信任何人,这导致了他最后的信仰崩塌,孤独终老。霍桑正是想通过“粉红色丝带”和布朗的思想转变警告所有清教徒,多元论是合理存在的。善与恶,好与坏,上帝与撒旦都客观存在,但是最重要的是清教徒们自身的选择。选择正是他们宗教修行与人生道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粉红色丝带”像是一个望远镜让今天的读者看到:在面对发生在三百多年前清教主义发生的宗教危机时,霍桑尝试用小说意向的多义性来对抗一元论,霍桑认为,他小说中的意向只可从多角度揣摩不可被定义;“粉红色丝带”又像是一个显微镜放大了人性中的原罪与恶的成分。《年轻的好小伙子布朗》带有霍桑一定的自传体性质,随着“粉红色丝带”的缓缓飘落,布朗加深了对原罪的理解,即对祖辈和人类始祖所犯罪恶的无条件继承。霍桑还通过“粉红色”向读者说明:矛盾体可以共存,多元论也有其合理性。他鼓励清教徒接受矛盾体的存在,坚持自己的信仰,认真对待每一次选择,以得到道德品质的提高和精神生活的升华。
参考文献:
[1]Amy Lang, The Synax of Class: Writing Inequ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37-38.
[2]Arthur Coxe,“The Scarlet letter”and Other writings [A]. In Leland Person. The Church Review [C]. New York:W.W. Norton, 2005:258-259.
[3]Brenda Wineapple, Hawthorne: A Life [M]. New York:Knof, 2003:133.
[4]Crews,Frederick, The Sins of the Fathers: Hawthorne's Psychological Theme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88.
[5]Frederick Crews, The sins of the Fathers: Hawthorne's Psychological Theme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73-78.
[6]Hawthorne Nathaniel, The Contemporary Review[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27, 231.
[7]Hawthorne Nathaniel, The Scarlet Letter[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9.
[8]Person Leland S.,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Nathaniel Hawthorn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9]纳撒尼尔·霍桑. 霍桑名作精选[M]. 余士熊等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249-264.
[10]彭石玉. 霍桑小说与《圣经》原型[J]. 外国文学,2005 (4): 64-69.
[11]张晶. 从宗教哲学视角解析霍桑作品中的清教主义观[J].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5 (9): 82-86.
作者简介:
崔玮崧(1989~),女,辽宁省抚顺市人,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2011 级硕士研究生,曾赴美西佛罗里达大学交流一年,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