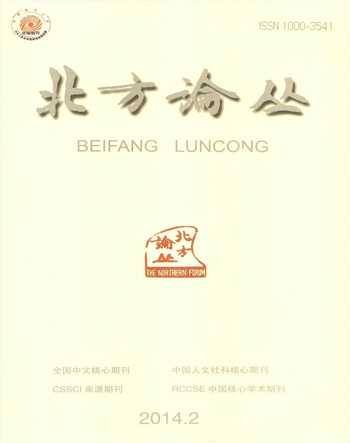论吴经熊自然法理论
杨明莉
[摘要]吴经熊的自然法理论是在对施塔姆勒及霍姆斯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又吸取了托马斯及中国儒家孟子的相关思想建立而来,具有浓厚的天主教色彩,尤其推重中国传统的直觉方式。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方式来重新解读自然法的尝试,是他的自然法思想与欧洲其他法理学家的最大不同之处,为融合并超越东西方文化做出了新的尝试。
[关键词]吴经熊;自然法;超越东西;直觉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2-0136-03
[收稿日期]2014-01-05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3年度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20世纪中国最具盛名的法学大家,吴经熊在中国近现代法律史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他的法律思想——尤其是自然法理论,对近代中国法制走向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国第一位世界级的法理学家。
一、 吴经熊自然法思想的形成脉络
吴经熊的自然法理论是东西方自然法观念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其思想的形成是建立在对当时自然法观念的批判以及对天主教和中国儒家相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之上。
20世纪20年代,吴经熊留学德国,师从当时最具盛名的法学家、新康德派领袖施塔姆勒,研究法律哲学。吴经熊对施塔姆勒敬佩之余,对其关于法律的一些观点却有着不同见解,这些分歧为吴经熊的自然法思想的建立提供了基础,主要有两点:其一,吴经熊并不认同施塔姆勒对于法律的定义。吴经熊认为,施塔姆勒“具有变化内容的自然法”(Natural Law with a variable content)与其本人的“在进化中的自然法”(a growing Natural Law)表面上看似相同,在含义上却有着根本的差别。作为新康德主义的领袖,一位批判理性主义者,施塔姆勒希望把所有形而上和本体上的假想和难题一概避而不谈。于是在施塔姆勒看来,自然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并不相信其真实存在,虽然其用过“具有变化内容的自然法”这样的字眼,但也只是一种“假借性的用法”而已,以致后来,施塔姆勒用“一个客观的公道法律之可能性”来替代。[2](p.46)这与吴经熊始终相信自然法存在的基本思想相去甚远。其二,吴经熊也不认同施塔姆勒关于公道的原则与定义。施塔姆勒认为,法律的理想在于公道,由此对公道的法律推演出四条普通原则,并将其分为两类:两条互敬的原则和两条分享的原则,其中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意味。吴经熊对施塔姆勒产生这种观点的逻辑以及这些原则的渊源产生质疑。在吴经熊看来,施塔姆勒的这四条普通原则以及其对“公道”的理解,是源于其自身的道德观念以及宗教的正义感而做出的判断,就其特性上来看,过于抽象而陷入一种个人化的境地,接近于个人理性主义。施塔姆勒混淆了自然法与法律整体之间的区别,与其说这些原则是法律之公道的原则,不如说是自然法的原则。
对与施塔姆勒思想迥异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的法律思想,吴经熊也持批判态度。霍姆斯认为,法律不过是一种测度法庭在事实上将其如何判决的预言,其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而关于思维的形式,不论形式观念有没有价值,形式的唯一用处就在于保存内容。[1](p.105)这与施塔姆勒的法律哲学思想几乎完全相反,施塔姆勒认为,法律不能任意改变,具有强制性,是关于社会生活意志。而在探讨法律的过程中,施塔姆勒始终强调“逻辑第一”,强调“形式”与“内容”相对立。从实质上来看,二人思想上的迥异正是一个德国理性主义者与英美经验论者在法律体现出的巨大差别。对此,吴经熊持调和主义,认为二人在各自的立场上都是正确的,却又都有失片面,吴经熊将二者的法律分别定义为法律的“概观”和“个观”,认为若要充分地理解法律的本质,不应只看部分,而应从整体上的直觉去认识和把握。
吴经熊的自然法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并发展了托马斯及孟子的相关思想。在吴经熊看来,自然法的观念是现代法律哲学上最具争论性的主题之一,他在选择颇具“内在的价值”的托马斯的哲学作为阐扬自然法的典型代表进行分析研究之后,认为一些怀疑论者以及独断论者之所以否定自然法,恰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懂得托马斯的自然法哲学。吴经熊认同托马斯的思想,进而认为自然法是属于“评价式的理性”,它不是依赖于逻辑和经验的推理得出来的,而是“不待证明而自明的不易原则”,是靠直觉来整体把握。吴经熊继承了托马斯对自然法所下的定义“人类理性对于永恒法的参与”,认同托马斯在回答自然法是否能变化的问题时所说的“自然法可以经由‘加增的一途而变化”,将其理解为自然法能够而且应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它的内容方面跟着演进,继而形成吴经熊后来所提出的自然法是“在进化中的自然法”这一核心观念。
在分析托马斯自然法哲学的同时,吴经熊又深受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的“良知”思想影响。在吴经熊看来,“儒家的道则是伦理的极则,相当西洋哲学的所谓自然法”[3](p.54),而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之所以“配享永恒盛名”,就是在于他对人性和自然法的透彻而精辟的见解。吴经熊评价孟子的人性论:“一方面,他把人性论奠基于存有论上;二方面,他崇尚实际,了解人性四端的发展与充实,逐渐培养之必要。”[2](p.235)孟子以人性本具有善端为出发点,强调后天人格的完全长成在于“仁义礼智”这四种主要美德的充分发展。吴经熊认为,自然法应依赖直觉、良知来把握,自然法第一原则就是“为善避恶”。从孟子的人性论中,吴经熊形成了他的自然法雏形,指出真正的自然法哲学的五项标准,且认为孟子的人性论与天主教的原罪说有着惊人的相似,孟子虽然只谈人性本具有善端,而不提人性本善良,这与天主教的原罪说近似,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人的限制性。
二、 对“在进化中的自然法”的学理分析
吴经熊曾将自己的法律哲学的核心要旨统为两点:第一,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基础;第二,自然法不是死僵僵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有机体。若用一个标题来概括,即“在进化中的自然法”。
自然法之所以称之为自然法,其关键在于“自然”二字。深受中国儒家孟子思想的影响,吴经熊认为良知是人的本性,而自然法是“不待证明”的,它内在于人性,是人的良知和良心的证明。“良知是我们认识自然的天赋官能,而良心则是把良知所体认的自然法,适用到个别情况上的作用。”[2](p.40)同时,自然法也具有拘束性。这种拘束性即是来自于忠于本性的道德律的命令,正是基于“为善避恶”这一自然法的第一原则,所以事实上,自然法的制裁力比人定法的更大。
自然法是沟通永恒法与实证法的桥梁。永恒法(eternal law)是“神的睿智”的另一名称,是绝对完全而不容有任何变更的,也没有什么成长的过程。自然法始终环绕着“为善避恶”这一核心及根本原则不断成长,其边缘则与人定法(human law)紧密连接。而人定法则纯粹是与时势相关联,时势会变化,人定法也无恒常。虽然自然法与永恒法、实证法不同,但三者之间却构成了“具有一贯性的连续体”。在没有任何变更的永恒法与无恒常性可言的人定法之间,就是起着沟通和中介作用的自然法。吴经熊以树作比三者之间的关系:埋在地下的树根相当于永恒法,枝叶则相当于实证法的不同制度,而连接树根与枝叶的树干则相当于自然法。
自然法是在进化中的自然法。正是自然法的这种沟通作用,使永恒法得以被人认识、发现,并实现“存在”的可能性,但自然法却存在缺陷,即它是经由直觉知觉来把握,虽是不证自明,却又是不可证真。由此,自然法需要人定法“加增的一途”来得到补充。吴经熊赞同托马斯所说“自然法是人类理性对于永恒法的参与” ,人的理性有进化完善的过程,则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人类理性参与永恒法的广度和深度也会随之演进,能力也会随之成长。由此,自然并非如永恒法般不可变更,而是始终处于动态的进化之中。
由此,吴经熊从不证自明的良心出发,将“为善避恶”作为自然法的第一原则,在此基础之上,以自然法与时俱进的特性沟通永恒法与人定法,使三者成为一以贯之的有机整体,建立起他的自然法理论。
吴经熊自然法理论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其中贯穿始终的浓重的天主教意味。吴经熊曾被公认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主要在俗诠释者之一,并曾作为“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驻梵蒂冈公使。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的自然法观念对其整个法律哲学产生着重大影响。他本人笃信上帝的存在,赞同杰姆士·甘德(James Kent)首席法官的观点,认为“信奉基督教的人,依赖上帝的启示,在发现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方面,曾经获得甚大的助益。”[2](p.41)这种天主教背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吴经熊对自然法的概念及其原则的理解上。在阐释过程中,他将托马斯的自然法观念与孟子的人性论相结合,把永恒法、自然法提升到新的高度。与托马斯护教意味深重的自然法观念相比,吴经熊更在意永恒法在人间的实施,更关心如何将上帝的意旨体现到人身上的过程,这也是吴经熊与其他天主教哲学家在自然法观念上的一大区别。
与很多欧美的自然法学家不同,吴经熊的自然法理论特重中国传统文化直觉方式的运用。在阐述应该如何认识“在进化中的自然法”这一问题上,吴经熊认为,只能依赖直觉。一方面,吴经熊将理性分为推断式的理性(Speculative Reason)和评价式的理性(Practical Reason)两种。认为自然科学属于推断式的理性,而自然法则属于评价式的理性,与“善”相同,均为“不待证明而自明的不易原则”。另一方面,吴经熊在批判施塔姆勒“法律的概观”与霍姆斯“法律的个观”基础之上,为了调和二人的对立立场,他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提出观点,主张法律的本质必须从整个知觉中探求。吴经熊将对孟子“良知”思想的理解运用到对自然法的认识方法上,认为都是要采用直觉的方式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直觉方式的运用,使吴经熊的自然法理论与欧洲的自然法学家形成了明显的不同。他的自然法理论没有将法律局限在理性的逻辑推理与经验的实际操作之中,而是用一种较高的角度实现对其的整体把握。但是这种直觉方式的运用,也多多少少带上了某种神秘主义意味,也将内在于自然法的人性由“不证自明”带上了“不可证真”的性质。
吴经熊的自然法理论之所以区别于欧美很多自然法学家,是他试图实现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尝试的结果。超越东西方是吴经熊毕生的理想,也是同时代人一直在做的努力。为此,吴经熊曾将自己的自传即命名为《超越东西方》。天主教徒的宗教背景使他多次试图通过宗教的力量来融合、贯通东西方文化上的冲突。吴经熊的自然法理论即是在对批判理性主义代表施塔姆勒以及经验主义者霍尔姆斯的思想进行批判基础之上,又融合了托马斯为代表的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儒家代表孟子的某些思想,建立起来的。一方面,他没有局限于逻辑推理和实用经验,将施塔姆勒的“概观”与霍尔姆斯的“个观”相结合,把自然法定位在“天命之谓性”的基础之上,“提升到另一较高的观点”去应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重的直觉来从本体和整体方面理解法律;另一方面,他打破“恒常”与“无常”的界限,主张在自然法的观念上应将二者进行融通,以此才能更好地理解永恒法、人定法与自然法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吴经熊曾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一文中表示,近代以来,西方过于注重现代的需要,而忽略了做人的道理。而西方近代思想家最大的毛病就是过分相信自然科学定律而认为伦理的原则没有客观标准。由此,他提倡一种“新自然法的哲学”,这种原则在道德与法律方面都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且正确性决不在自然科学之下。正是这种超越思想的始终存在,使吴经熊能持批判的态度理性客观地看待欧美的自然法观念,同时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体悟方式融入其中,为解决如何认识自然法这一问题提供了另一种选择途径。
三、“超越东西方”的自然法探索之路
某种程度上来看,吴经熊的进化中的自然法理论对之前的东西方的自然法观念实现了一些超越。一方面,他的自然法理论对当时的自然法观念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调和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并受西方基督宗教的“原罪”说启发,赋予自然法在概念以及原则上新的意义;另一方面,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将孟子的人性论以及以儒家、道家、佛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力图在理论及实践中形成超越东西方的产物。但不能不看到的是他在重视人的充量可完美性(maximum perfectibility)之余,未能用足够明显的文字强调人的最低限度的个体性(minimum individuality),从而对人性的个体性缺少充分重视。尽管如此,吴经熊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值得我们关注及思考。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方式来重新解读自然法的尝试,是他的自然法思想与欧洲其他法理学家的最大不同之处。吴经熊留学期间,以英文、德文、法文在国外权威杂志上发表诸多论文表述其对传统自然法观念的见解,引起当时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及新康德派领袖施塔姆勒等一些享有盛名的法学大家的关注,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法学界的地位及一定的话语权。回国之后,又担任法学教授、法学院院长、律师、推事、法官、法院院长、立法委员、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对中国古代及近代的法律及法制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出版有《中华民国六法理由判解汇编》、《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释义》、《中国制宪史》等论著,并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又称《吴氏宪草》),奠定了在中国法学界的权威地位。在此过程中,吴经熊始终将他的自然法理论贯穿其中,努力用行动实现着他超越东西方的愿景,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布道者,更是一个法律的实践家。随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思想在国际上的传播越来越广,将有更多学者从新的角度来关注、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的方法和途径,而吴经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与解读以及对超越东西方的探索与追寻也将为中国法律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与视角。
[参考文献]
[1]吴经熊.超越东西方[M].周伟弛译雷立柏,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吴经熊.内心悦乐之源泉[M].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1.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共黑龙江省直属机关党校讲师)[责任编辑张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