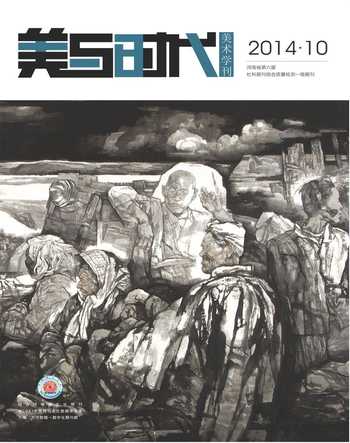从晋唐人物画来论“六法”


摘 要:“六法”是中国古代美术品评的标准和重要的美学原则,它的每一条法则都是直接地、本质地以人物画的要求和标准表现来衡量绘画作品。晋唐时期人物画的创作是对应“六法”。
关键词:六法 晋唐 人物画
“六法”是中国古代美术品评的标准和重要的美学原则,它最早出现在南齐谢赫的著作《古画品录》中。它在《古画品录》中总结和发展了前代绘画在法则上的理论认识,提出艺术创作之“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转移模写。“六法”中的每一条法则都是针对人物画提出的,以人物画的要求和标准表现来衡量绘画作品。“六法”确立的意义在于规定了范围,明确了方法,方便了学习。从“气韵”之第一法则顺推,是美术鉴赏的思路,而从“转移”这第六法则倒溯,则是绘画实践的过程。“六法”是一个互动的理论体系,谢赫的理论反映了古代绘画艺术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美学认识。这个认识既肯定了根据对象来造型的必要性,也提出了理解对象内在性质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笔墨是表现对象的手段。[1]
南齐谢赫“六法”的本质为儒家思想崇尚士大夫文化人的“阳春白雪”之标准。“气韵生动”为庄学的清淡、玄学之标准,“应物象形”为道家学说“象意之辨”,“形意之辨”的“写形写意”之升华。在晋唐,“气韵生动”的含义主要是指对于客观物象的描绘达到了“形神兼备”的标准,因此而要求画家具有扎实的造型基本功,不但能真实的刻画出对象的形,更能以形而传神,还要能将主观的情感迁想妙得于对象之中。[2]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到“彦远试论之曰。古之画,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与俗人道也。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上古之画,迹简意澹而雅正,顾陆之流是也。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展郑之流是也。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今人之画,错乱而无旨,众工之迹是也。” [3]张彦远的这段话表明晋唐的“气韵生动”重在客体,这时期的人物画家,如曹不兴、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昉等。他们开始注重刻画人物外貌的特征和个性的差异,更进一步注意形貌不同所表现出的神态差异,强调以形写神,注重人物神情的描绘。如《历代帝王图》、《唐太宗像》、《高逸图》、《步辇图》、《重屏会棋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等。晋唐时代的人物画除了政教方面的实用功能,还有描绘日常生活的作品,如《虢国夫人游春图》、《纨扇仕女图》等,以现实宫廷生活中的人物为对象,造型更加准确生动,更注重人物之间形态的刻画和细节的描绘。是即谢稚柳所谓的“从对象中来,到对象中去,而来摄取对象的形与神、态与势”。[4]
转移模写:这实则是人物画大画以及佛教、道教壁画题材与内容创作时由小稿子放大到壁画稿子的重要过程。佛教、道教内容都以寺廊壁画的形式展示和宣传,在晋唐几乎所有的人物画家都参与了佛教、道教题材壁画的绘画。“转移模写”是人物画写形法则的基础所在,是壁画人物画转写与创作运行的基本法则。“转移”即直以印度寺壁之模样,完全转写。“模写”实际是根据“画样”的原本进行壁画的创写。“写”与“画”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写”融进了书法的精神。实际将真实的人物形象或佛教“画样”“转移”到大尺寸画壁或壁画上的过程,不仅要求形似,而且要加强用笔的气度、风范,更重要的是形似之外的神韵。从晋唐的人物画中可以看出,晋唐人物画重转移模写,从前人经典之小样为粉本,传而移之,模而写之,所谓创作者,实为依样制作。[5]在《列女仁智》、《历代帝王》、《竹林七贤》、《西方净土》、《维摩经变图》上可以看出画面上的人物形象有相同之处。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的《五百强盗成佛图》的景物、动物和人物的布置,与我们在顾恺之《洛神赋图》上所见的画面相似,也是“人大于山”,其树木的勾画,也如张彦远所形容,是“刷脉镂叶,多栖梧菀柳”,显得比较幼稚。在人物造型上的风格如菩萨和供养人的清癯瘦削的面容,与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列女古贤图》等画面上的人物形象风格近似,属“秀骨清像”一类,人物体态夸张生动,特别善用流利飞舞的长线条。唐代大画家吴道子“吴带当风”的艺术手法,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经营位置:即整合各单体之形象。为总体形象,今称之为构图。根据小样,粉本来定下所画的人、景、物的位置,大小,疏密,主次规画远近。依据客观实际,从内容出发,合乎规律地进行构图,使物象之间互相联系成为一个主题突出的完整作品。在唐以前,南北朝的宗教绘画题材中,从西土传来的图式,基本上照搬既定的程式,完全是自己创作的很少,包括内容题材,造型规范及式样配置原则等均来自印度健陀罗和佛经中的具体记载。唐朝的吴道子在他的绘画技巧中对人体的结构比例,亭台楼阁的透视关系,包括构图上的微妙细节,参照现实生活中的各色人等创造了道教始祖老子及各类道教神仙的艺术形象,开拓了整个道教绘画题材,历代延用下去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从传世的《八十七神仙卷》及《朝之仙仗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这种完美的图式。吴道子以唐人为原型创造出符合中国审美习惯的佛教的一系列艺术形象,确立了中华名族自己的佛教艺术样式,并丰富了佛教绘画题材。吴道子的《地狱变相》被后世画家广为传摹,千百年来地狱成为最广泛的文艺创作母题,传为吴道子画的《送子天王图》的人物样式,在今天山西永乐宫三清殿的壁画中可以看到这一风格样式的传续,每个神袛的高度都在三米出头,人物的排列极其自然而富有变化,疏密虚实连贯而统一,运用“兰叶描”方法,满壁风动,飘带萦绕迂回,起到连接人物的巧妙作用。人物“朱粉厚薄,皆见骨高下而肉陷处”,“旁见周视,盖四面可以意会”,看去“如塑”。
随类赋彩:“随类,赋彩是也”,“赋”通“敷”。在画法中是“平涂”之意。赋彩即施色。“随类赋彩”是指绘画应根据不同的粉本,稿子分类而平涂,以色彩取其体面精神。在人物画中,作为轮廓的笔线勾勒是关键,体面的色彩涂染留给工人、弟子去完成,构成人物体面的衣袍是不同类的平面构成,红色为红色,绿色为绿色,在人物画的设色里多用平涂法。在中国晋唐时期的人物画受印度佛画传统的影响,在敦煌魏晋时期的壁画上仍然可以看到著名的“凹凸法”,当时的壁画人物在眼眶、髋骨、胸、肌、手肘、腹部等表现结构,并且在容易产生阴影的地方用非常厚实的肉色晕染。进入隋唐之后,人物画便全以线条为主,即使还有渲染,也是以线条为主,色彩渲染为铺,吴道子用色“浅深晕成”,“敷粉简淡”的“吴装”,便是很好的列证。进入盛唐时期的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可谓典型的“随类赋彩”的代表之作。作者对客观物象精心观察以后,对客观物象经过物化提炼后的重新阐释与诉说。画中人物的形象生动,气韵传神,面庞丰润,蚕眉凤眼,体态婀娜,气质温婉,设色也异常考究;明丽典雅,雍容华贵,凸显闲适,安逸的贵妇生活状态,清晰地表达了唐代浓丽的时代审美特征,色彩技巧的运用上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周昉对于所描绘的对象可谓观察入微,刻画细致。薄如蝉翼的丝质纱裙若隐若现,惟妙惟肖,衣服图案的平面化处理,人物形象的典型化风格。在强调对象的特征,尊重物的固有色上,强调的并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主义描绘,不是模拟自然色彩的的色彩关系,对丰富的客观色彩世界加以高度的概括处理。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更具有表现性。
应物象形:“应”是指人对事物的感应,“物”是指客观存在的事物。“应物象形”是指造型要以客观物象的依据,正确地、真实地、有感受地表现处其艺术形象,就是看它轮廓是否正确如实,神采是否一致,讲求形神兼备,物我交融。[6]就是依据真实的对象来塑造艺术形象。以在晋唐反复被画家画过的《竹林七贤图》为例:在南朝时期的砖印壁画上“竹林七贤”以平列构图的形式表现七贤饮酒抚琴等生活形象,每个人的个性鲜明突出,是南朝士大夫“秀骨清像”的特有风格。清瘦,修长的体形特点,用笔以短线描为主,真实传神。顾恺之,陆探微也画过,都已失传。唐代的孙位画的《竹林七贤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将人物形象不断提高,但画中人物造型的“抱膝”、“举杯”、“如意”等动作是保持一致的。用线细劲圆润,设色典雅古朴。人物形象头面手足的刻画有质的飞越,面部、头发、胡须、衣服的勾描是用不同轻重的用笔节奏而形成的质感,精细入微,栩栩如生。画面湖石及其他补景简括而有皴染,代表了晚唐人物画的风格,《益州名画录》说他的形象符合“拙规矩之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的最高标准,被称为“逸格”。这种风格是艺术家经过长期对所表现的客观物象研究,理解,反复描绘过程中提炼概括的结果。盛唐中后期的张萱的作品在当时的“绮罗人物”中是典型的代表。他根据那个时代贵族妇女的真实写照,人物造型特点是曲眉丰頬,体态肥胖,是富贵人家的慵倦神态。《虢国夫人游春图》以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为造型对象,描绘虢国夫人及家眷仆从们,在阳春三月骑马踏青的情景。全卷不设背景,人物艳丽明快的服饰与鞍鞘华丽的马匹,线条劲健圆润重彩设色,渲染得当,色彩对比明快活泼,艳而不俗,恰当地表现出女性的体态特征和丝织衣服的质感,人物仪态端庄,形体准确,生动自然。画中女性佩戴的饰物和所梳理的发型,如唐代流行的高发髻、百合髻、垂练髻,这些细节说明画中人物的年龄和身份。艺术家主观能动的描绘真实人物不断升华后的主观和客观巧妙结合的产物,这便是“应物象形”,也是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形象塑造,以神似置于形似的基础上,以主观置于客观的基础上,是晋唐人物画保持活力的源泉。[7]
骨法用笔:包含了关于对绘画对象形体结构的认识,是画面总体效果和用笔方法相结合的产物。人物画在晋唐时期的道释,帝王、将相、仕女、高士作为描绘的对象,人物画则重于线描的用笔。轮廓的勾勒是“骨”。所以,“骨法用笔”又称“骨线”,而体面的涂染则是“肉”。鲁迅曾评价唐代的佛画人物,认为“线描空实明快,色彩辉煌灿烂”,这便是骨肉兼济,有骨有肉,是人物画的最高境界。但二者相比,骨的重要性又在肉之上,所以,在谢赫的“六法”论中,“骨法用笔”被作为第一技法。而“随类赋彩”则仅作为第二技法。那么,怎样的笔线才是优秀的笔线呢?概而言之,它必须是生动的,迥劲的,有骨气的,但用时又必须是严格配合了客观对象真实的描绘而不断变的。我们从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中看到在东晋现实生活中的高士、仕女,他们所穿着的大多是轻软飘逸的丝质服装,因此运用了被后人称之为“高古游丝”的线描,紧劲连绵,自然舒缓而有具有节奏感。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有一种心平气和的静运神韵。在吴道子的道释人物,意气发扬,冠盖迎风,所运用的是被后人称之为“兰叶描”的线描形式,挥霍磊落如莼菜条的灵动笔势,富有粗细、轻重、顿挫、转折的多样变化。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成为艺术家所向往的精神生存空间,人物画家更多地专注于对客观对象内在精神的体现。在人物画的发展过程中,儒教与玄学的相互作用使得“形”与“神”的关系逐渐向着“形神兼备”发展。唐朝人物画继承和发扬了魏晋以来“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特点:初唐人物绘画的人物造型,形体各种动态和神态及表情,较之以前在技术上有了推进。以阎立本、尉迟乙僧等人物画家为代表,画家对人本身更加关注,对人物造形和神情刻画更加深入和成熟,用笔洗练坚劲;到了中唐时期的人物画,画家在造型上注重外貌描写与实体接近,并发展出特有的造型风格样式和审美图式,线条工细劲挺而流畅,设色鲜艳而明快,以张萱、周昉的体态饱满、丰腴健壮、艳丽多姿的“绮罗人物”最为典型。相对于魏晋南北朝人物画以“以形写神”,唐代人物画从整体上是“形神兼备”、“六法俱全”,唐代人物画“形神兼备”是对“以形写神”的继承与发展,是在人物整体的“形”的追求与自律上的进一步加强。[8]综上所诉,在晋唐人物画的时代“六法”中的“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转移模写”是技术标准,而评判标准则是“气韵生动”。“气韵生动”则“形神兼备”是也。
参考文献:
[1] 孙乃树.美术鉴赏[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2]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 俞建华.中国古代画论概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1
[4] 谢稚柳.水墨画[M].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2
[5] 徐建融.长风画尘[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6] 王朝闻.中国美术史[M].济南:齐鲁书局,2000
[7] 徐建融.晋唐美术史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
[8] 惠剑.传统人物画“形”的意义演化[J].文艺研究,2006(11)
作者简介:
黄曦,2011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艺术硕士。四川美术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