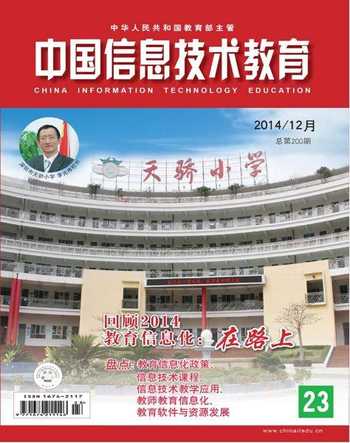让我们聊聊历史吧
魏宁
据说一百多年前,数学、物理、化学课给人的感觉有点冷冰冰,甚至让人昏昏欲睡。原因是教师只知道从头到尾向学生灌输干巴巴的定义、定理,课堂上全无生气。于是,西方一些高校的理科教授开始尝试在课堂上聊一聊这门学科的历史。没想到,竟一下子激起了学生的兴趣,课堂开始变得津津有味起来,这就是科学史教育的发端。慢慢的,在课堂上聊历史已经不再是为了取悦学生,而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但直到今天,在信息技术课上似乎还不太容易听到这门学科的历史。是因为信息技术学科太年轻,历史匮乏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下面咱们就看看在课堂上聊历史的好处。
最早在课堂上聊学科的历史当然是想让课堂变得有趣起来,在那些教授的嘴里,大科学家们的发明变得颇具喜剧色彩——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了浮力原理,牛顿被树上掉下的苹果砸中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同样,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们的人生故事也让科学巨匠变得更有人情味、更真实。
在信息技术领域同样不乏这样的人物,如因对博弈论做出开创性贡献从而影响到人工智能发展的怪才约翰·纳什,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甚至还被拍成了电影《美丽心灵》,在2002年一举获得了4项奥斯卡奖。从21岁时提出奠定其博弈论大师地位的“纳什均衡”理论,到30岁时突然精神失常,再到66岁时奇迹般的从疯癫中清醒过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约翰·纳什如过山车般的人生就如同剧本一般,并有着颇为喜剧的结局。
在课堂上聊历史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吸引学生,因为,历史、人物还具有励志作用。爱迪生历经6000多次实验后,终于点亮了第一盏电灯;富兰克林冒着生命危险坚持进行雷电实验,最终发明了避雷针……这些“励志故事”无不激励着孩子们对科学的向往。
在计算机发展史上,也有这么一位“励志大师”——1978年图灵奖得主罗伯特·弗洛伊德。提到计算机科学家这个群体,绝大多数人都是受过长时间专门教育的科学精英,弗洛伊德的成长故事绝对另类,是一位完全自学成才的计算机科学家。本是学文科出身的他误打误撞当上了一名计算机操作员,给IBM的计算机房值夜班却勾起了对计算机的兴趣,于是,凭借刻苦自学,弗洛伊德终于成为计算机的大高手:26岁开发出世界上最早的ALGOL 60编译器;31岁发明了验证程序正确性的“归纳断言法”,34岁被聘为斯坦福大学教授……
除了趣味性和激励性,学科历史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学生理解学科的本质。因为,让学生知晓整个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比让他们记住某些固定的结论更能接近学科的本质,就像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一系列尖锐论战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量子力学的本质一样。
在现代计算机诞生的过程中就曾有过一场“工程师派”和“逻辑学家派”的激烈争论。那是在ENIAC接近完成时,大家开始讨论它的后续机器EDVAC的设计方案。由谁来主导EDVAC的设计就成了一次“论功行赏”的大好时机,“工程师派”的领导者——在ENIAC开发中立下大功的埃克特认为新机器应该由他来主持设计,因为让15000根热真空管共同完成一项工作,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实现的;但EDVAC的领导者们却并不这样看,在他们看来,不管ENIAC有多少工程技术上的突破,它仍然得服从计算机器的逻辑思想,那才是一台机器运行的幕后法则。因此,他们坚定地在EDVAC设计报告上写下了逻辑学家派的领导者——冯·诺依曼的名字,这才有我们今天学习到的“冯·诺依曼结构”。事实证明,半个多世纪以来,计算机的基本结构依然是当年冯·诺依曼奠定的。这段历史无疑能让学生理解计算机背后的科学原理才是计算机的基础。
学科历史是学科教育的一笔财富,它能让课堂更有趣味、更能激励人心、更能碰触到学科的本质,在信息技术课堂上聊聊历史,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