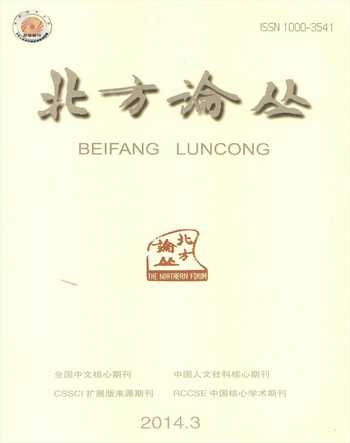战后联邦德国阶级(阶层)构成演变
王涌



[摘要]战后联邦德国由于经济和经济结构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即社会中层人数急剧上升为社会主导性力量,而上层和下层人数则明显萎缩成社会少数,就使得社会性质由原来战前的阶级社会转变成战后的阶层社会,其标志是社会人员不再由彼此对立的两个阶层组成,而是由彼此基本相安无事的多阶层组成。战后联邦德国主要由精英,业主,职员,工人,穷人和外来移民这六大阶层组成。就社会地位而言,其中绝大部分属社会中层,上层和下层均属少数。
[关键词]战后西德;社会结构;阶级
[中图分类号]K5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3-0001-06
1949年,德国学者盖格(Theodor Geiger)在其名著《抚平的阶级社会》(Die Klassengesellschaft im Schmelztiegel)中,分析了此前几十年中,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差别在德国已开始消亡,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对立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差别,如城乡差别、不同阶层的差别等。50年代时,立场保守的社会学家塞尔斯基(Helmut Schelsky)开始尝试去描述由此产生的社会新结构,并称之为“没有差别的中产阶层社会”(die nivellierte Mittelstandsgesellschaft)。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兴起,曾有人提出,西德依然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社会。今天,这种声音虽然已经没有了,但这种观点启发人们,阶层的区别与收入、市场机遇等经济因素相关,而且事实上并没有出现像塞尔斯基所说的“一致化或无差别化”(Nivellierung)。此后,德国研究界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阶层分析,主要专注于分析导致阶层差别的一些本质性因素,如职业,收入等。到了80—90年代,哈贝马斯又用“新的不清晰性”(neue Unuebersichtlichkeit)概念描述当时德国社会的现状[1],意指社会阶层区别,不平等等现象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无法轻易看清。这其实指出的是社会阶层分析面临的困境,并非否定该分析本身。就联邦德国战后的社会发展来看,阶级或阶层结构方面的变化还是展现出了一些可以捕捉到的量性因素,借此又可对德国社会做出一些质性方面的分析。
一、社会阶层的构成
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相同,战后联邦德国的社会阶层大体上由精英,业主,职员,工人,穷人和外来移民六大部分组成,德国在这方面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这些阶层的具体构成和各自社会份额方面。总体而言,战后联邦德国是一个较之其他发达工业国显得更平民化、更均等的社会,不仅各社会阶层的构成呈现出较大的开放度,而且个人发展也呈现出较大的伸展空间。
首先,就精英阶层而言,战后联邦德国呈现出了较明显的平民化趋势,也就是说,更彻底地抛开了世袭因素,更明显地呈现出开放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还是一个西方社会中相对落后的贵族世袭制国家,社会精英主要由那些世袭的贵族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德意志帝国的瓦解,贵族体系开始消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消亡的速度尤甚。就使得战后德国的社会精英主要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等组成,即由这些领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人,而不再由贵族组成。这些领导人中社会各阶层人都有,但都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可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工人家庭相对来说还是较少。对出身这些家庭的人来说,往上层爬的途径主要是加入工会,先在里面进入领导岗位。从前还有加入社民党,在党派里担任领导,现在已不多见,因为社民党的领导现在越来越少由来自底层的工人家庭人员担任,现在加入绿党或民社党还有这样的可能。与法国,英国和美国不同,德国没有专门培养精英的学校或专门由未来精英上的学校。要成为精英,主要靠文凭和能力。当然,文凭只是条件,还不是一切。同样具有文凭,来自社会上层家庭的人就容易进入领导岗位,尤其在经济界,这主要并不是因为关系,而是因为一些由家庭带来的个人气质,素质,精神状态等。总体而言,战后联邦德国的社会精英与政治关系最密切。其次,与经济,传媒界,再次与学术界。最后,与法律,教会,文化界也存在着特定关系。这些精英的组成虽然理论上有很大程度的开放度,而且不再世袭,但实际上还是相当程度地依赖于教育和个人能力的培养,而这些又不是彻底均等的。所以,战后德国社会精英阶层还是呈现出了一定的稳定性,一种不是系于个人,而是系于类型的稳定,比如,战后德国政治精英所学专业大多是法学和经济学。
业主(Selbstaendige)在德国被称为“中产阶层”(Mittelstand),大企业家例外。德国政府长期以来奉行“扶持中产阶层政策”(Mittelstandspolitik)。因此,这一阶层在战后联邦德国一直保持着较大的比重,两德统一后甚至出现了增长。就其构成来看,除了主要指中小企业主之外,还包括自由职业者(Freiberufler),如艺术家等。此外,独立经营的农民也属于此列。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这些小型业主(kleine Mittelstaende)将被大企业吞并。战后50—60年代的德国,这批人减少,无法与大企业竞争,该时间段开始创办企业的人明显减少,因为随着经济腾飞,大企业的发展,在大企业中谋取一个好的职位越来越成了一个更明智的选择。到了80年代情况开始有所变化,新兴产业的出现给创业提供了新机遇,90年代这一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增长。1989年,德国就业人口中88%是这样的业主,2000年则上升到103%,一方面与新加入的原东德公民的创业热情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政府支持分不开。政府的“扶持中产阶层政策”有着坚实的经济和社会考虑,即为了发展经济,提升总体经济实力必须让企业做大,而这必然伴随着机械化和高失业;也为了消减由此而来的高失业,开始支持由于占据某方面领先技术而同样具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因为这些企业由于机械化程度没有大企业高而消化了大量失业人口,如90年代初,全德国250万家这样的小型(员工50人以下)企业,消化了全社会整个劳动大军的2/3。这些中小企业往往占领了一些大型企业不想占领的特殊市场,创新能力强,工作效率高。欧共体层面,1999年,这些中小企业主占整个劳动大军的平均值是144%,虽然高于德国,但那是由一些经济结构不甚合理的南欧国家所致,如1999年,中小企业主占社会整个就业人口比,希腊是32%,葡萄牙25%,意大利24%,西班牙19%。显然,从社会发展角度看,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应处于合适比例中,德国的情况应较好地调动起了两者的长处。此外,属于这一阶层中的农民(拥有土地)在战后德国处于快速萎缩中,20世纪初,这样的农民仍占全德国就业人口的1/3,1950年时降为1/4,70年代开始萎缩成社会的极少数人。原来东德农民虽然比西德的比重高,但统一后,也快速消失。
职员(Angestellte)是战后联邦德国快速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社会阶层,既包括企业非体力从业人员,也包括公务员。在德国社会发展中,职员是作为工业化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登上“社会舞台”[2](p13),1925年时上升到总就业人口的12%。50—6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1950年时占总就业人口16%,到了1974年上升到了33%,在80年代后期超过工人,成为最大就业人群,到了2000年达到50%以上,而工人此时只占32%。总体而言,德国的职员有三类:商业、技术和管理。后者人数众多,而且非常多样化,他们大多属于职员中的中上层,大约2/3的职员和所有公务员属于该阶层。职员群体在战后德国的快速增长主要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关,第三产业的兴起使得这一群体快速形成,尤其是德国大型工业企业内部也在战后出现了一股第三产业化潮流,即企业内部越来越多的人不是工人,而是职员,从事着第三产业的工作。此外,国家公务员(Beamte)人数在战后德国不断增长,1950年,西德公务员人数为80万,1993年为200万,尤其在70年代初,增长最快,这样的增长也使为国家工作的职员人数在不断上升。这个快速增长的就业群体给战后德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带来了深刻影响,因为这些人不仅在收入方面,也在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方面,明显不同于原来作为就业大军的工人。这一阶层的快速成长使得战后德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工人这一群体在战后联邦德国出现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他们虽然还是社会的重要阶层,但无论从量,还是质上看,都出现了巨大变化。正如所述,早在50年就有人认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已经消亡,这不仅指作为劳动大军的生产主体,也指对既存社会具有不满的颠覆性力量。这个变化从量角度看,从40年代末占整个劳动大军一大半的份额降到了2000年的约36%。这些人的行业分布也发生了变化。2000年时只有1/3的工人在工业,而一半的工人分布在第三产业,只有24%的工人分布在农业[3](p116)。战后联邦德国的工人经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去无产化”(Entproletarisierung)过程,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幅改善,生活和职业有了保障,反抗和颠覆现实的动力降到几乎零点。与此对应,工人群体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化,出现了工人精英,专业工人和一般工人的差别。但是,就收入,教育,职业前景,社会地位等而言,工人在战后联邦德国总体上还是处于社会底层。
穷人也是战后德国社会的一道移除不去的景观,他们位于社会的最底层。如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由于战后德国奉行的主要是自由经济政策,竞争使得一些社会弱者被淘汰,而社会保障又使得这些人往往失却了努力奋斗的动力。于是,渐渐滑向社会边缘,成为穷人。在德国,穷人通常指收入只有社会人均收入的60%,而欧盟的界定是50%。主要指的是那些无家可归者(Obdachlose)和长期失业者,他们靠领社会救济金(Sozialhilfe)生活。这样的人口在战后德国一直存在,数量在欧盟内部居于平均水平。据欧盟统计署公布的数据,1996年,以60%国民人均收入为标准的穷人在欧盟平均占人口总数的17%,德国16%,法国16%,芬兰9%(1994年),丹麦11%,卢森堡12%,荷兰12%,奥地利13%,比利时17%,西班牙18%,爱尔兰18%,英国19%,意大利19%,希腊21%,波兰22%[4](p74)。值得关注的是,战后德国的穷人在经济高速增长后也明显增多,即60年代起,德国的穷人数量一直处于增长中(见表1),该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越来越完善的保障体系相关。此外,战后德国,传统意义上的穷人团体:老人和妇女也越来越被改善了的社会保障排除,穷人主要有4类:单亲家庭、多子女家庭、失业者和外来移民。其中最糟糕的是无家可归者。据估计,在德国2 000年这样的人口在13—15万之间,其中包括没住房,但住在亲戚、社会救济机构住房里的人,还有一些人直接在露天过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在2000年的德国估计有24万,其中大部分是20—50岁之间的单身男性。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采取与他人同居的方式避免露宿街头。根据Caritas的一项调研,1991年无家可归者中约一半是一般工人,1/5多是专业工人,其中一半人小时候家庭环境不好,但有1/3来自很好的家庭。其中9%是外来移民,7%来自原东德;1/5是刑满释放人员,找不到工作。虽然原东德由于宪法保护,每个人都有工作,但两德统一后,没有了这种保障,原东德地区出现的穷人则明显多于西部,与西部情况不同的是,这些穷人中大部分是老人,这些老人中尤其以妇女为多。统一后,失业率,无家可归者在东部地区都出现,而且明显高于西部。这些穷人成了战后德国位于社会最底层的人。
外来移民也是战后联邦德国越来越坚实的一个社会阶层。就整个西欧国家而言,德国的外来人口数不算多。西欧国家中外来人口比重高的是:卢森堡(35%)和瑞士(19%)。尽管如此,由于战后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有越来越多的移民进入德国。这样的移民总体而言在德国经历四阶段:11955—1973年,主动争取阶段(Anwerbephase)。21973—1980年的正常化阶段(Konsolidierungsphase)。1973年开始停止主动争取,此后进入的外国人开始减少。1972年开始有可能入籍,但人数很少,仅入籍费用就需要5 000马克。31981—1998年抵制阶段(Abwehrphase)。80年代后,外来人口又开始上升,其中许多的少来自欧洲战争地区的难民。于是,制定法律限制难民和外国劳工进入。1993年入籍放宽,费用降至100—200马克,入籍人数增加。41998年开始的正常接收阶段(Akzeptanzphase)。2000年出台了新国籍法, 为IT人士发放绿卡,于是德国成为移民国。外来人口中最多的是土耳其人;其次,原南斯拉夫人;再者依次是意大利、希腊、波兰、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荷兰、法国等。就数量而言,60年代开始,外来移民渐渐成为德国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1960年,生活在西德的外国人在70万,1970年上升到300万,由占总人口的12%上升到49%。2002年,初外国人在德国为730万,占总人口89%,其中不包括约100万加入德国籍的外国人[5](p226)。两德统一后,德国的外来移民中又有一部分来自原东德地区。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德开始引进劳工。1989年,6万越南人、52万波兰人、25万古巴人和莫桑比克、安哥拉的非洲人来到东德,年龄均在20—40岁,70%为男性,占当时东德总人口的12%。两德统一后,这些人按协定进入的人必须回国,1993年,只有约19万留下,其中17万为越南人。被允许在德国工作的外来移民从事的工作主要在下层,他们虽较长时间生活在德国,但生活方式,价值观等都与德国人有一定差异。
二、历史变迁
当然,这六大阶层是在战后联邦德国社会发展中渐渐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的,此前的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拥有的是明显不同的阶级(阶层)结构。但是,即便在战后五六十年间,这样的阶层结构也有一个成型、演化的发展过程,一个从战前劳资两元分化到战后多元并存的发展过程。具体来看,与战后德国经济发展几乎对应,这个社会阶层的多元新结构成型于60年代,即德国经济经历了十几年重建后,又开始成型的时代。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同,新成型的阶级或阶层结构也呈现出明显不同于此前第三帝国或再前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情形,即阶级差别开始缩小,社会开始向多阶层转化。到了80—90年代随着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阶级间的差别进一步缩小,阶层结构内部进一步出现庞大的中间阶层,导致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
随着战后德国社会新结构在60年代的初步成型,相关研究也开始在60年代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当时德国社会学家玻尔特(Karl Martin Bolte)在其“联邦德国社会不平等的历史比较”一文中,根据职业,收入,影响力等因素,提出的“洋葱结构”(Zwiebel-Modell),即将社会阶层分成上中下三等,中等阶层人数最多,其中又分成上中下,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居于中等偏下和下等偏上部位,即洋葱—社会的主体部分[6](pp27-50)。 具体见表2。
由上表可以看出,60年代的西德,约有2%的人属于社会上层,19%属于中上层,58%属于社会中层,其余21%属于社会下层,其中约有4%属于被人蔑视的底层。有必要说明的是,属于社会上层的2%是承袭而来,没有什么变化。在19%的中上层中,绝大部分是新贵,少部分是原有阶层的沿袭;在58%的社会中层里,新诞生与沿袭者约各占一半,其中约有一半是工人;在21%的社会下层中,几乎全是原有地位的留存,而且都属于工人阶级。值得关注的是,居于社会底层的4%被固定下来,没有什么变化。
玻尔特的研究一方面表明,60年代的联邦德国已经清楚地出现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新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表明德国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有接近半数的人口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原来较低的社会阶层上升到了较高阶层,唯有社会顶层和底层人数没有多大变化。具体而言,60年代的德国,绝大部分人已经属于社会中层,成了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其余两端——上层和底层都是少数。这些位于两端的少数人群,数量上在60年代几乎没发生过变化。与之相反,挤入中上层的人大部分是新贵,而社会下层几乎都是保留了原有的地位。可见,60年代的德国,有接近一半的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由社会下层进入中上层,这与50—60年代德国经济腾飞形成呼应。可以说,这一时段的经济发展使社会近一半人受益,社会地位上升。但在50—6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约超过一半的大部分人则在社会地位方面没有什么改变。尽管如此,那些近一半的改变还是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原来下层人数大幅减少,中上层人数大幅增加。当然,这里的改变仅是相对于原有地位而言,并不是指绝对增长,50—60年代的经济发展实际使得全社会人员收入都有增长。
同样是60年代,对于当时西德社会阶层的分析还出现了达仁多夫(Ralf Dahrendorf)的“房屋结构”图表,达仁多夫的研究虽然没有指出社会阶层所属出现的变化,但更具体标出了当时阶层所属的职业背景。
在达仁多夫的“房屋结构”图表里,居于社会顶层的只有1%,宛如屋宇的顶端部分;接下来的中上层人员迅速上升至34%,宛如屋顶坡面部分,其中中产阶级是主干,占了20%,所谓服务产业人员,即第三产业人员,绝大多数位于此列,占了10%,他们不是属于职员就是公务员,还有极少工人精英,以及“误认的中产阶级”挤入该阶层,所谓“误认”是因为他们表面上属于社会中上层,但实际应归为中下层;其余的65%则属于屋宇的主体部分,其中60%属于社会中下层,真正属于社会底层的只有5%。中下层主要由工人阶级组成,占了45%,此外还包括那些误认的中产阶级(11%),极少数服务产业人员(2%)和部分工人精英(2%)。
达仁多夫的“房屋结构”表明,60年代西德社会中有约超过一半的人属于社会下层,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至于上层,只有全社会约1%的人才作为社会精英位于顶层,其余大部分其实属于中层,也就是说,当时西德社会中约99%的人不是属于社会中层就是属于下层。如果说,玻尔特的“洋葱”图展现了60年代德国社会阶层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达仁多夫的“房屋结构”图则展现了当时社会极小部分人位于顶层的上小下大结构。两种结构分析一个突出社会中层作为社会的主体,一个则突出极少部分人高高在上的地位。无论如何,两种分析都清楚地表明,60年代的西德社会是一个极少数人统领的社会,社会资源,影响力等都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这是60年代时西德社会定下的格局,以后的变化主要并不是在这个上小下大层面,而是在作为社会主体的中下层内部出现了结构性变化。
2002年,盖斯热(Rainer Geissler)在达仁多夫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房屋结构”在2000年发生的新变化,这个新变化便主要发生在社会中下层内部结构层面。
盖斯热的图表表明,到2000年,德国社会阶层依然是上小下大的结构,而且位于社会顶层的依然是1%的社会极少数,这些人被称为是“权力精英”(Machteliten);接下来的中上层主要由高级领导组成,外加人数不多的中小业主,包括极少数自主经营农民,共有275%;至于占281%的中层则主要由中级领导组成,同样外加人数不多的中小业主和极少数自主经营农民;工人,除了极少数工人精英外,则全部处于社会中下层和下层,其中14%的人作为专业工人位于社会中下层的顶端,12%则作为普通工人位于下层;社会下层中还有约9%的人作为第三产业领域中的体力劳动者居于其中。盖斯热的“房屋结构”图表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外国人成为德国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2000年时有9%的人是作为外国人加入到德国社会中去的,其中,1%的人是作为中小业主分布于社会中上层和中层,2%是作为专业工人居于社会下层中的顶端,即中下层,其余6%则位于社会下层的末端,即下层。
从盖斯热的研究来看,到了2000年,德国社会阶层结构又发生一系列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社会中层人员的数量由60年代的30%多(据达仁多夫的研究)上升到了50%多,由60年代不到一半变成了明显超过一半。与此对应,社会下层人士也由原来的60%多下降到40%多。这充分反映了社会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并由此体现了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有知识和技术含量的劳动明显增多;此外,外国人群体以9%的比重在德国社会结构中的出现表明了德国社会已开始渐渐步入文化多元,但是,这些外国人大多位于社会下层,只有少部分进入社会中层。
如上三个图表呈现了战后德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鲜明趋势:阶级(阶层)差别开始一步一步减少。其鲜明的体现是,位于社会最顶层和最底层的人居社会极少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成为社会中层,进而使得该阶层人士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且这些人大多是新起之辈,即从原来较低层经过奋斗转变而来,包括外国人。
三、变化背后潜伏的事实
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清晰地映现了战后联邦德国社会开始转型。所谓转当然是相对于此前社会而言。单纯从时间角度看,此前是第三帝国和魏玛共和国,但从社会形态角度看,此前德国社会可能要从更早的19世纪下半叶说起,那是一个德国社会快速工业化,迅速转向现代社会的时期。如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19世纪启动的工业化在德国同样是在私有制框架下展开的,技术和机器的投入使得劳动力有了高产出和高效益,而高份额的产出却绝大部分被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即资本家,而不是劳动者拥有。于是,伴随着工业化转向,19世纪的德国社会也开始由等级社会转向阶级社会,等级主要由出生决定,而阶级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不仅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斯泰因(Lorenz von Stein,1815—1890)和韦伯(Max Weber)等学者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个转向阶级社会的过程就像工业化本身一样,在德国是一个虽快速但依然渐进的过程。1849年时,普鲁士只有54%的人在工厂就业,到1861年普鲁士工业还主要由小企业(员工17—20名)组成,1 000名员工以上的大企业极少。到了帝国时期,工业化速度明显加快,动力主要来自资本投入增大,社会保障建立,由工业化而来的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适,该时期,社会就业总人数中工人已经达到了一半,其余大部分是农民,其次是业主,还有一些是职员或公务员。1850—1913年间,社会资本翻了5倍;1870—1913年间,工业生产总值翻了5倍,而且原先占主导地位的纺织、制衣、皮革行业的增长很快被冶金、化工和电子行业的增长所超越,尤其是铁路建设成了当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1882—1907年,德国1 000人以上企业的增长翻了4倍。可见,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经济快速发展也带来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快速转化,社会也完成了从原来等级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始终是这样一个阶级社会:社会劳动大军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是工人,其余则是业主和职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50—60年代,阶级社会开始向阶层社会转化,标志是工人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职员的数量直线上升,以至工人只占整个社会就业人员不到一半的份额。所以,早在50年代,德国学界就曾出现阶级差别开始缩小,阶级开始消亡的观点。其实,就大量中间阶层取代原来的工人和农民而言,所谓阶级消亡指向的是,原来的阶级差别向阶层差别的转化。所谓阶层虽然很大程度上依然与经济因素相关,但主要的已不是由经济因素决定,而是由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支撑,当然,这往往离不开经济基础。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别明显大于阶层社会,而且由于阶级之间没有起码的认可,有的往往只是冲突。工人数量的减少和职员这些中间阶层的增多,表明原来阶级社会的劳资冲突不再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因为那些占劳动大军多数的中间阶层的工作条件和收入水平,已经不像原来工人那样低于认可,即便50—60年代的工人也与以往差异巨大,工作条件和收入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当然,阶层社会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社会冲突开始消失,而是呈现出了多元、复杂的局面。原来工业化早期的德国(19世纪始),社会冲突主要来自劳资之间,而且大多呈现为利益冲突。战后德国,由于新社会结构的出现和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冲突已不再单一地出现在劳资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甚至同一阶层中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都会出现冲突,而且越来越少地呈现为利益冲突,利益之间的问题已经由越来越清晰和细致的规则规范了,冲突开始越来越明显地由文化因素引起,如不同世界观、价值观、乃至生活方式等,这些已经与阶层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此外,冲突开始淡出阶层之间也与日常生活的日益非阶层化有关。战后德国,由于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管理日趋一体化,原来的阶级特殊性从日常生活中几乎消失,这就使得阶层之间的差别在日常生活中不再有明显体现。虽然冲突不再带有阶层之间色彩,但阶层之间的差别还是存在,这个差别主要已不再因经济因素产生,而是由不同生活方式和追求等文化因素所致。
随着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冲突的趋缓乃至消失,以及庞大中间阶层的出现,就整个社会而言,形成了一个近乎自发的稳定机制。此前阶级社会中,德国社会的大部分人生活在下层,而且整个下层对上层,乃至整个社会存在着明显的不认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当社会上大部分人满足于现状,不愿有所改变的时候,社会的稳定性因素开始出现。当然,战后德国社会新结构的出现并不是社会维稳的产物,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正是战后德国经济腾飞中,第一产业萎缩,第二产业减速,第三产业从业人员飞速增长,使得社会人员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再作为社会的大部分出现,其中很大一批上升为社会中层,即便作为社会少部分的那些原有的无产阶级也发生了变化,不仅劳动条件和收入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而且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产者,他们中许多人程度不等地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由此,进行革命、改变现状的动力大幅下降。这些都从不同角度促成了社会的新稳定机制。
进一步看,新社会结构的出现又会在整个生活方式,生活追求方面引发一系列变化。尤其当整个社会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坚实的社会保障建起之后,人的职业态度,日常生活方式都会相应地出现变化,这些变化往往是由进取,奋斗转向智取,效率。战后德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就引发出了一系列其他领域的相应变化。
[参考文献]
[1]Juergen Habermas: die neue Unuebersichtlichkeit, FrankfurtaM1985
[2] HPBahrdt: Gibt es noch ein Proletariat?, FrankfurtaM1973
[3] Statistisches Jahrbuch 2001
[4] EC/Eurostat:Beschreibung der sozialen Lage in Europa, Luxemburg 2001,S74
[5] 参见HWLederer:Migration und Intergration Ein Handbuch Bonn 1997,S18; RGeissler: Die Sozialstruktur Deutschlands Zu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mit einer Zwischenbilanz zur Vereinigung, Opladen 1996
[6]Karl Martin Bolte: Sozialungleichheit in der Bundesrepublick Deutschland im historischen Vergleich,in:PABerger und SHradil(hrsg), Lebenslagen-Lebenslaeufe- Lebensstile, Goettingen 1990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