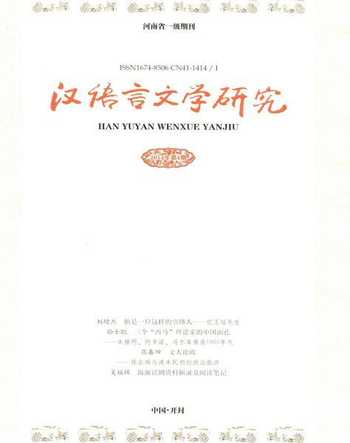张际亮与道光年间的唐宋诗之争
代亮
摘 要:张际亮的诗学宗趣与姚鼐渊源甚深。他指斥以翁方纲等人为代表的“肌理”诗风,不遗余力地标举盛唐,称颂李白和杜甫等诗人。他还以唐诗的承传为基准来构建诗学谱系,以与宋诗相抗。在道光年间宗宋诗风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张际亮与一时名流如徐宝善、黄爵滋、潘德舆、姚莹等人标举唐诗。他们敏锐地觉察到宗宋诗风的弊端,如生涩、险僻、千篇一律等,并力图以唐诗为对症良方予以纠正,自有其价值所在,在诗学史中应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张际亮;诗学渊源;诗学宗趣;宗唐诗风
对于清代道光以降的诗学风气,从晚清民国的陈衍、汪辟疆等人开始,论者多关注宗宋诗人的创作及主张。实则在道光前中期,宗宋诗风固然是方兴未艾,但宗唐诗风的力量也不可小觑,而张际亮则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张际亮(1799-1843),字亨甫,福建建宁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张氏其人其诗,在嘉道年间享名甚高,“年未满五十,声名遍九州……海内作者十数,皆吐弃一切,而言及亨甫,莫不敛衽”{1}。在致力于创作之外,他对诗坛现状也有深入思考,论诗文字甚夥,且颇具深度和现实针对性。张际亮指斥以翁方纲等人为代表的“肌理”诗风,与之针锋相对,他不遗余力地标举盛唐,称颂李白和杜甫等人,又以唐诗的承传为基准来构建谱系,矫正当下流行的宋诗风。他与一时名流如徐宝善、黄爵滋、潘德舆、姚莹等人志同道合,标举唐诗,指斥宗宋诗风之弊,在宗宋诗风外自树一帜。
一
张际亮的诗学观与桐城派的“开山祖师”姚鼐渊源甚深。其在《马小眉诗序》文中有以下自述:“余年十三,得桐城方望溪先生文,读而好之。其后读刘海峰、姚惜抱二先生所为文诗,则益好之。”{2}桐城三祖中,方苞短于诗才,很早就弃诗不作,而刘、姚则在古文创作外,也重视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尤其是姚鼐,虽主要以古文闻名于世,但其诗作亦不为少,诗名亦迥出时流之上。张际亮在十三岁时就阅读二人的诗文,且又“好之”。应当说,刘、姚的诗学观点在少年张际亮那里已有了先入为主的存在。其中,姚鼐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和持久,这从其后来的夫子自道中可以寻得若干例证。其作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送许乡韭秀才归桐城》曰:“我生亦已晚,不及游门墙。尝读翁遗书,亦访翁梓桑。”③作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为朱濂甫琦太史阅诗题其后》云:“当代谁高咏?桐城(自注:惜抱先生)继阮亭……众流趋末派,后起失前型。”{4}前诗嗟叹自己因生年太晚而难得进入姚氏弟子行列,言下不无遗憾,对姚鼐的景仰之意即此可见;后诗则将姚氏与清初诗坛巨擘王士禛相提并论,并引以为诗坛典范,高山仰止之情一览无余。张际亮其人恃才自傲,对前贤罕有许可,他曾评价乾嘉诗坛诸名家曰:“袁(枚)佻赵(翼)犷,蒋(士铨)薄黄(景仁)轻,张(问陶)介于黄、蒋之间,惟沈(德潜)之持论颇正,惜才力不厚,故其所自著,无足感人。”{1}一时名家,为其批评殆尽。与此相映成趣,他唯独对姚鼐再三致意,既以其私淑弟子自居,又明确宣称要“庶几嗣惜翁,肯逐颓波狂”{2}。姚氏诗学思想的沁入其心脾自在情理之中。若仔细比较二人诗论可以发现,他的若干观点与姚鼐的轨辙相继之迹亦宛然可寻。
首先,二者在主体修养论上一脉相承。姚鼐皈依宋学,强调诗人应有“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荷塘诗集序》)③,并奉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苏轼和黄庭坚等人为典范。受其影响,张际亮论学也以宋学为宗,在对诗人道德修养的要求上,他在祖述姚鼐观点之余,又略有改造和发挥。《赠姚伯山柬之大令即送之粤东》诗开篇即谓:“君家惜抱翁,好学老益纯。”已然点明了其与姚氏的渊源。继之曰:“词章盖末艺,根本义与仁。处为贞介士,出为经济臣。”{4}以“贞介”和“经济”作为诗人人格修炼的理想境界,与姚鼐所论大体一致。同时,他又奉曹植、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等人为诗家楷模。与姚鼐所列人物相比较,他增添了阮籍,舍弃了黄庭坚,其余则完全相同。其次,在对前代诗歌的评价尤其是尊崇明代前后七子这一点上,二者也若合符契。众所周知,姚鼐论诗以熔铸唐宋为归,学界多关注他推崇宋诗的一面,但实则他对乾嘉时期宗尚宋诗的名家不无微词,曾指责厉鹗为“诗家之恶派”(《与鲍双五》){5}。同时,他推举宗尚盛唐的明七子,并且特别强调:“学诗不经明李、何、王、李路入,终不深入。而近人为红豆老人所误,随声诋诃明贤,乃是愚妄耳。覃溪先生正有此病,不可信之也。”(《与陈硕士》)⑥反对钱谦益以及翁方纲等人的“随声诋诃明贤”,以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等人为师法榜样。这一倾向在张际亮那里得到了继承。张氏《润臣以近诗见示,率题三绝》之二云:“李何骖驾见高徐,风骨孤骞世未知。不信后人轻七子,翻成老马戒前车。”{7}为李、何等人的不为世知深表痛惜,为其遭受菲薄而鸣冤叫屈,表明了以七子为典范的坚定立场,与姚鼐遥相呼应。我们知道,明七子倡导诗歌尤其是近体必须以盛唐为法。由七子向上一关,自然会追溯至唐诗。上引中,张际亮将姚鼐与王士禛等量齐观,已将二者一并当作宗唐的典型来看待。由此可见,张际亮得闻姚鼐遗文之謦欬,对其推崇唐诗实有直接影响。
张际亮私淑姚鼐,但他对后者推举宋诗的一面兴趣不高,而着力发挥其褒扬唐诗的一面,此与其性情气质也有直接关系。“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8}。张际亮生当嘉道衰世,少时就喜欢谈论兵事,他仰慕贾谊、诸葛亮、周瑜和郭子仪等人,向往在马背上建功立业,有着强烈的政治热情,“不欲经生、辞客自为,而深慕古之奇伟之士,其功业足以震惊夫一世,其声名足以垂誉而无穷也”{9}。对未来不乏光明的想象和乐观的展望,洋溢着人生在青年时期所特有的奋发和自信。其平生更是“慕古所谓豪杰磊落者之所为,于谨严之意,蔑焉无有也”{10}。这与盛唐诗人的慷慨不羁较为接近,而与宋人的内敛深沉相去较远,自然更易向往盛唐诗风。
二
张际亮对乾嘉以迄当下的诗坛现状有深入思考,自称“至于诗道利病,十颇得其七八”{1}。而他力图纠正的弊病,就是“性灵”和“肌理”诗风,主要对象则是后者。他又积极地为诗歌发展寻找正道坦途,在“破”的同时又能“立”,即以唐诗为宗,奉李、杜等人为典范,以唐诗的承传来构建谱系,借径前贤,上攀唐风。
乾嘉年间,袁枚提倡的性灵诗风和翁方纲标举的肌理诗风各树一帜,从者甚众。张际亮对袁、翁二人好感无多,屡有批评和讥讽之词。《岭南后三家诗序》说:“当乾隆、嘉庆间,诗道稍榛芜。或以议论考订为诗,或则轻佻浅鄙,无与于风雅之旨。”{2}其中,“以议论考订为诗”直指翁方纲等学者诗人,“轻佻浅鄙”一语则将矛头对准袁枚等性灵诗人。张际亮的诗学活动集中在道光前中期,其时性灵诗风受到士人的口诛笔伐,已无复昔日之盛,甚至有渐趋消歇的迹象;但肌理诗风所标榜的宋诗则日渐风行,身处其中的包世臣就观察到:“宋氏以来,言诗必曰唐,近人乃盛言宋。”③在此背景下,张际亮的批评主要指向宗宋诗人。在与友人徐宝善的书信中,其言:
竹君学士欲自溯源于昌黎,然徒以奇字险韵为工,则所谓工者,亦何与于温柔敦厚之教邪!况昌黎之诗,其佳在气奇而骨重,学邃而理粹,不于此求之,而欲横空盘硬语,何可得邪?翁则直以诗为考订,而盛传海外,实怪事也。近日颇有知袁、赵之非者,然复扬竹君、心余、覃溪之余波,则亦为狂澜而已。{4}
认为朱筠效法韩诗的“奇字险韵”和“横空盘硬语”,未得韩诗根本,而这两方面正是宋诗的典型特征。他又对翁方纲的“以诗为考订”能流传海外感到迷惑,目为“怪事”,可见对翁诗鄙夷不屑;而近日诗人虽“颇有知袁、赵之非者”,却又滑向朱筠、蒋士铨和翁方纲等人的宗宋一路。显然,如何扭转诗坛日益偏向宋诗的局面,已成为他思考的主要问题。
张际亮所以对宗宋风气尤其是翁方纲倡导的肌理说深致不满,深层原因在于二者在诗学观念和审美情趣上的全方位差异。比如,在对创作主体和创作方式的认识上,二人一重学力,一尚天赋。在乾嘉年间汉学兴盛的背景下,翁方纲重视诗人学养,尤其是经史实学,强调“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5}。在诗歌创作上,他虽然不废天赋,但更推崇理性化的创作,注重法度与规则对天才的引领和限制,“其必至于专骋才力,而不衷诸节制之方,虽杜公之精诣,亦不敢也”⑥。张际亮虽也要求诗人须“读书”、“积理”,但更偏重天赋才能,《仙屏书屋诗序》曰:“夫备极文章之能事,为一代之上焉者,盖有天焉。”{7}在诗歌创作上,他力主摆脱各类法则的束缚,甚至主张诗作以少改为佳,《答朱秦洲书》云:“日日作诗,日日改诗,必不工……终日作之改之,徒挠乱其真气,蹶僵其美才。”{8}这与反对“专骋才力”的翁方纲形成了鲜明对立。在诗歌的题材选取和审美趣味上,二者的看法亦相去甚远,翁氏重理,张际亮则重情。翁方纲崇尚学问,倡导作诗当从读书学古中来,其论宋人诗曰:“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9}而“观书”和“研理”正是他诗作的主要题材。他的诗集中充满了题图、题画、题拓本之作,以考据入诗,缺乏灵气和情感。洪亮吉就批评说:“最喜客谈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诗。”{1}与之相对,张际亮则提倡诗歌从自然界和社会人生中取材,在此基础上抒发主体情感。《南来录自序》云:“古人之心,有以周夫山川风土、人情事物之原;其阅历有足以穷其变。其幽忧愤快,劳思慷慨,虽时有不同,而言之皆出于其中之不容己,其言之长短、高下、疾徐,亦有不同,而读之皆足以使人掩卷而叹,沉吟而思,高歌往复而起舞,或且泣下不能止。此则诗之至也。”{2}表现出对诗歌抒情传统的回归。
在张际亮看来,唐诗是古代诗歌的巅峰,此后则步入衰落期,如《诗话楼》所说:“诗坠三唐后。”③体现出对唐以后诗歌的不屑态度。这一立场在《答姚石甫明府书》中有更加明晰的表现,信中有论曰:“故三百篇之作,首夫《风》,以‘风者动于天人之交,其声之自然而发者也。《雅》、《颂》则近于侈人事矣,然其志正而义高,故次焉。风人之作,大抵比兴为多,《雅》、《颂》则赋也。自唐诗之既衰,宋作者起而变之,风人比兴之义几息矣。故至今之为诗者,可悦人者多,可感人者恒少也。”{4}认为宋诗一变唐诗旧格,使“比兴之义几息”,而后人效法宋诗,结果不免“可感人者恒少”,暗示宗宋诗风已步入歧途,非诗家正道。同文中,他又以“神骨”、“才情”和“气韵”为标准,论唐宋诗曰:“诗之至者,曰入神,其骨重则神愈永也;曰雄才,其情深则才始完也;曰真气,其韵高则气乃固也。六者具备,此盛唐大家之诗也,骨、才、气有余而神、情、韵不足,此宋大家之诗也。”{5}宗唐绌宋的诗学宗趣于此表露无遗。
在灿若繁星的唐代诗人中,张际亮对李白和杜甫最为心仪。在评论他人诗作时,他经常以李白或杜甫作比,表达推许之意。有时他则径直以李杜并举,流露出俯首和赏叹之情。其《武平钟秀才来予邸索诗,不值屡矣,而来益勤,于其归以诗送之》云:“维唐首李杜,力与风人争。立言盖深厚,一字非遽成。垂辉映千载,后来莫与京。我思浣花翁,稷契许平生。谪仙少豪侠,天子呼不醒。二公有大略,乃破蟋蟀鸣。”⑥认为他们在唐诗人中出类拔萃,能“力与风人争”,难为后人企及,并对李白的豪情壮采及杜甫的忧国忧民情结深表仰慕。
张际亮壮游天下的经历,狂放不羁的个性,才高而不遇的遭际,以及不畏权贵的处世方式等,都与李白类似,这无形当中拉近了二者的时空距离。他时常赞赏李白的人生风采,《太白书堂》云:“此实千秋一豪士,谈笑不知天子贵。前有庄马后大苏,睥睨乾坤得此气。”{7}《壬辰九月出都,留别都下交朋》曰:“谪仙自合老蓬蒿,醉后空吟旧锦袍。”{8}在到李白去过的地方游玩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遥距千载之上的诗人:“翘首香庐高,太息李白狂。”{9}“豪”和“狂”是李白气质的核心,又何尝不是张际亮本人的写照呢。与对李白的推举相映成趣,张际亮诗集中的诸多七古、五律以及绝句,均能得李白诗豪放壮朗、清新飘逸的神采。对于杜甫,张际亮也不吝赞美之词:“尝谓杜诗如汉高祖……自是三代后第一雄杰。”{10}生当如日之夕的嘉道衰世,张际亮有着强烈的忧患情结,时刻关注国计民生,并力图有为,挽救江河日下的政局,这与杜甫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再光中兴业”的人生追求比较接近。他对杜甫的“诗史”品格和“沉郁顿挫”的诗风尤表倾慕,这既见之于批评,又落实在创作实践中。关于前者,其《十八夜宿练潭雨骤作次日竟日不止二十日午微霁始行是夜宿新安渡口号十首》之十云:“诗从征信史,世亦练吾才。”{1}力图以诗歌写时世,并注重现实生活对诗作的陶冶作用。关于后者,其《石甫明府出示方植之东树先生诗因题》谓:“要从沉郁得飞动,岂贵蹶张与剽诡。”{2}奉杜诗的“沉郁”为创作金针。张际亮足迹踏遍南北各地,视野开阔,目睹了嘉道时期的民生凋敝和外敌入侵等种种情状,这些在诗作中都有全面的描写和展现。其《江车谣》、《哀流民》、《福州观灯》、《临清》、《湖上渔家》诸诗,描绘民生疾苦,指陈时弊,力透纸背,发人深省;而《诸将》、《须怀》、《定海哀》、《镇海哀》、《宁波哀》、《后宁波哀》等诗作,或谴责作战不力的兵将,或痛诉外敌的侵凌,饱含悲怆之情,低回起伏,能得杜诗沉郁顿挫之风神。
在推举李、杜等人的基础上,张际亮还以唐诗为基准来建构诗学谱系,以与宗宋诸人相抗。他强调学诗当以古人为法,而不能一味步趋时人:“新诗要与追前辈,肯向时贤逐后尘。”③“来者未知何日再,古人可作不吾欺。”他所要继踵的“前辈”和“古人”,就是那些拥护或承接唐诗审美传统的作家。张际亮以唐诗为核心,上溯其源,推本风雅,下探其流,追寻其在宋明清时代的承传和流变,构建“诗统”。“诗统”一说,虽未见他有明确的理论表述,但将其在不同场合的言论合观,则这一统系的存在则甚为明晰。今引其论如下:
风雅微茫有正声,渔洋惜抱两分明。为君更话沧浪旨,千载骚人过眼轻。
大雅虽微有正声,尚书(沈文慤)余论半新城(王文简)。新诗意到青邱后,无限苏台晓月情。
旷代王(弇州)吴(梅村)溯太仓,云间(陈忠裕)健笔亦飞扬。期君大手追骚雅,莫问高名拂水庄(钱虞山)。
江河之源,当求之于宿海岷山之上,如吴梅村、王渔洋、宋荔裳、施愚山诸先生,固犹利济之舟楫也。{4}
他所心仪的人物,从南宋批评宋诗、倡扬唐诗的严羽开始,向下延伸到明清两代,包括了明代学唐的诗人王世贞、陈子龙,以及清初继踵唐诗的吴伟业、王士禛、宋琬、施闰章和清中期的沈德潜、姚鼐等人。张际亮认为他们是“利济之舟楫”,引以为典范。相反,对于执清初诗坛牛耳的钱谦益,他则引以为学诗者戒,盖因钱氏“力诋弘、正诸公,始缵宋人余绪”{5}。至于宗宋的著名诗人如査慎行、厉鹗、蒋士铨、翁方纲、朱筠等,在这一谱系中则难觅踪影。他所建构的诗学谱系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意义,强有力地传达出建构者对唐诗的热慕,而更深层的含义则在为学诗者指明方向与路标。言下之意,盖认为诗歌当沿着严羽、王士禛等人的轨辙前进,这与宗宋诗者大异其趣。
三
论清道光以来诗学思想者,自陈衍、汪辟疆以降,多关注宗宋诗风的代表人物和主张,似乎其时诗坛就是宋诗风的一统天下。他们的若干经典性论述,也为今人所著若干批评史和清诗专题著作继承和发挥。不过,若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则事实殊未必然。在道光年间,宗宋诗风固是蔚然成盛,但宗唐诗者的力量亦不容小觑。张际亮与诸多志同道合的友人如徐宝善、黄爵滋、潘德舆、姚莹等,为唐诗而鼓与呼,大力指摘方兴未艾的宗宋风气,拔戟自成一队。张际亮则以突出的创作成就和理论建树,成为群体中最积极和最重要的鼓手。潘德舆《赠张亨甫》诗曰:“万物务纤密,百家谁典型?凭君压群响,骚雅奉遗经。”{1}颇能说明他在群体中的地位和影响。
张际亮一生数入京师,结识了诸多友朋。他在道光六年(1826)初次赴京,以诗才而得盛名。在道光七年(1827)离京前,他与黄爵滋、徐宝善、姚莹等已经成为至交。他说:“姚侯意气自雄豪,燕市徐(廉峰)黄(树斋)亦我曹。”{2}虽主要是就慷慨报国的志向而言,但也包括了诗学观点的相通。此后他又数度入京,并在道光九年(1829)结识潘德舆,私交亦自深厚,关于二者的交谊,张氏有言云:“余再至京师,倦于游,不复见客。二三交故外,惟与君往还不厌。”③二人时常谈论诗坛弊病,立场较为接近。早在道光六年(1826),张际亮就约徐宝善等人同结诗社。虽然后来因行踪不定和其他因素,诗社之约并未落实,但他们或以书信方式商榷诗坛利病,或在唱酬赠答中沟通声气,切磋琢磨,彼此的诗学见解得以沟通,促进了诗学群体的形成。张际亮在与徐宝善的书信中曾大声疾呼:“窃念诗道榛芜,欲相与大声疾呼,振起聋聩。”“阁下与树斋诸君子皆心知其弊者,固宜力挽颓波,勉成砥柱。幸毋怖于前辈之名大,众人之势盛。”{4}期望对方能挺身而出,扭转诗坛偏向宋诗的局面。张际亮宗唐的诗学主张,也得到了诸多友人的有力支持。他们桴鼓相应,在推崇唐诗,批评宗宋之失的同时,又通过编刻自家诗选或刊刻前贤诗选,彰显宗唐的诗学宗趣。
宗唐群体诸人大力揄扬唐诗,对宋诗则不乏微词。他们虽有宗唐绌宋或宗唐容宋的区别,但在以唐诗成就高于宋诗,唐诗理应成为最高典范这一点上则基本相近。此处不妨以潘德舆为例说明之。潘氏虽能兼容宋诗的异质之美,但其以唐诗优于宋诗的立场则坚如磐石。他说:“唐诗大概主情,故多宽裕和动之音;宋诗大概主气,故多猛起奋末之音……宋不逮唐,大彰明较著矣。”{5}同时,他又指摘宋诗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之失,认为“宋诗似策论,南宋人诗似语录”⑥,“以粗俗直率为盘硬排戛”是“宋人习气”{7}。在此基础上,他提倡“学者大纲,自宜于宗唐”{8}。
与此同时,他们对于宗宋诗风的弊端亦有深刻反思与中肯的批评。黄爵滋视宗宋诸人的效法韩、黄为优孟衣冠。《艾至堂诗序》曰:“若夫效韩而肆……师黄益艰。非孙叔之遇优孟,即黄老之遇申韩焉。”{9}姚莹《薦青诗集序》分析宗宋诗风的不足说:“国朝诸公病明代复古之弊,乾隆、嘉庆以来,多避熟就生,以变其体。大约不出苏、黄二公境中,究未能自辟生面也……若必以常见为非,力求新异……岂复言志之旨?虽复自矜沈奥,及乎群辈为之,久更生厌。”{10}认为自清初以迄当今的宗宋诗人未能摆脱苏、黄牢笼,他们的“力求新异”违背了诗歌的“言志之旨”。为了纠正这些流弊,他也旗帜鲜明地提倡“盛唐兴趣是吾师”{11}。另外,他们还着意表彰本朝前贤特别是那些宗唐的诗人如王士禛等,一方面以为己论张本,自重渊源由来;另一方面也有引以为今人镜鉴和指南的用心。姚莹就说王氏“鉴诣之精,持论之允,固古今诗人一大总汇也”{12}。黄爵滋则沿用王氏的神韵说,认为神韵是诗歌的本质特征,他说:“文未尝无神韵也,而制胜者必以理;诗未尝无理也,而制胜者必以神韵。”{1}区分诗文各自的特质,显示出不满宋诗的立场。
另外,他们通过编选诗歌选本或刊刻前代诗选,与诗学批评相配合,彰显自家诗学趣味。作为诗学主张的载体,选本更易普及,影响力也更广泛。在前一方面,潘德舆的成就不可忽视。他编选盛唐李杜诗歌一千余篇,名曰《诗本经》,拟之为儒家经典,强调李杜诗歌为学诗者之本。其《作诗本经序》曰:“三代而下,诗足绍《三百篇》者,莫李、杜若也……窃怪近代作诗之人于李杜也,貌崇而心违之……盖心专乎唐者,十无一;心专乎盛唐者,百无一;心专乎李杜者,千无一也。其去《三百篇》安得不远哉?”{2}他编选此书的目的,实在于号召学习李杜,最终复归《诗三百》。在后一方面,徐宝善的作为尤其突出。徐宝善曾出资重刻姚鼐的《今体诗钞》,他特意“以唐人万首绝句中佳构,湘帆马君所授自姚氏者,附而行之”③。徐氏《冯吾园前辈以诗枉题拙集奉酬》诗曾批评宗宋诗者的“腹瓠夸祭獭”,认为如此一来,只能是“迁流变加厉,风雅日雍于”{4}。两相联系,则此举实有推举唐诗的动机在内。
应当承认,宗唐诗学群体的辐射力虽不为小,但并不能与宗宋诗学群体平分秋色,在当时处于弱势。道光前中期,以汉学家程恩泽、祁寯藻、何绍基等人为核心的诗人群体,以及以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为核心的诗人群体,均为宋诗鼓噪呐喊。对于盛唐诗的不受重视,张际亮屡有慨叹:“谁寻李杜意,汶济日流东。”“世任萧曹法,天穷李杜诗。”{5}在他生前和身后,宗宋潮流也一浪高过一浪。宗唐诗风在晚清的渐趋消退,主要原因盖有以下几点。首先,这一群体的主要成员在道光中后期相继去世,客观上加速了宗唐诗风的落潮。徐宝善和潘德舆分别在道光十八年(1838)和道光十九年(1839)去世,张际亮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离世,姚莹和黄爵滋均在咸丰三年(1853)去世。一时精英至此凋零殆尽,而其余诸人或限于创作成就,或限于自身政治地位,并不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其次,宗唐诸人的诗学取向与时代心理难以相合。学唐还是学宋,看似是一个诗学路径问题,而根源则在于士人的心态和精神风貌。盛唐气象以时代政治的相对清明安定为背景,与士人慷慨激昂的人生精神相表里。而嘉道年间政治日益凋敝,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到咸、同时代后则变本加厉。生当衰世末造的诗人,很难再有乐观的人生态度,他们力图改造的雄心壮志,在江河日下的政治形势中亦难得施展,心态日趋黯淡。在这样的背景下,盛唐气象自然可望而不可求,这或许也是宗唐的诗学主张难得普遍响应的根本原因。在同光时期宋诗日益占据强势地位的背景下,同光体诗论家着力表彰道咸时期的宗宋诗人,而很少关注宗唐诸人,使后者作为一个群体的呼声逐渐湮灭无闻。但无论如何,作为道光年间诗坛的重要力量,宗唐诸人自觉地与宋诗风保持距离,敏锐地觉察到其弊端,如生涩、险僻、千篇一律等,并力图以唐诗为对症的良方予以纠正,自有其价值,在晚清诗学史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责任编辑 王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