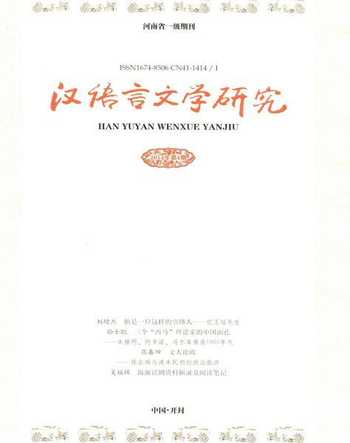是“译官”还是“翻译”?
陶磊
摘 要:本文认为,一贯被用来证明“译”的本义为“译官”的《礼记·王制》和《周礼·秋官》两篇文献,由于创作时代存疑,实则不足以成为支持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据;而相关出土文献的缺失,使得从文字学角度切入的分析亦无法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根据词义引申的一般逻辑推断,“译”的本义更有可能是指“翻译”这一行为,而非“译官”。
关键词:译;本义;译官;翻译
一
翻译史研究者在讨论中国早期的翻译活动时,往往会专门谈到“译”这个词,而其含义和现在并不相同。比如《礼记·王制》中有这样的记载:
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1}
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要“达其志,通其欲”自然得仰赖翻译。但也有人指出:仅仅依据这段文字,很难判断“寄”、“象”、“狄鞮”和“译”究竟是对翻译工作者的称呼,还是对他们所从事的翻译工作的称呼。{2}为了佐证前一种情况,《周礼·秋官》对“象胥”的描述常常被拿来同时引用:
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③
《周礼》明确将“象胥”列为一个官职,{4}主要负责与外国使臣的沟通工作,即充当译者。所以郑玄在注文中借用西汉经学家郑众的话说:“象胥,译官也。”{5}这里的“象胥”被认为就是《礼记·王制》所说的“象”,所以“寄”、“狄鞮”和“译”应该也都是译官的称谓⑥。汉代,“译”取代“象”成为译官的统称。武帝先后设立“译官令”、“译官丞”和“九译令”{1},“象胥”等词不再使用,但其职司一脉相承。许慎的《说文解字》也把“译”解释成“传译四夷之言者”{2},不再按照四个方位“依其事类”③进行细分,后人认为这可能和汉以来与北方民族交往频繁有关(“北方曰译”){4}。
《周礼》和《礼记》的这两段文字在翻译学界一般被视为关于“周王朝”(甚至“远古”时期)翻译官职的记载,{5}于是研究者长期以来“对先秦‘译概念的认识往往限于‘北方语译官层面(而行为‘译的出现又往往被推迟至汉代以后甚或更晚)”⑥。但是,我们似乎很少注意到《礼记》和《周礼》这两部书本身存在的巨大争议,{7}尤其是其中的断代问题可谓聚讼纷纭,迄无定论。
一般认为,《礼记》是记载和阐述先秦礼仪的资料汇编,系西汉今文经学家戴圣辑录而成。其内容广博,门类杂多,作者并非一人,各篇的写作时代也不尽相同——其中尤以记录了所谓“周王朝翻译官职”的《王制》篇的情况最为复杂。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关于该篇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封禅书》,其云:“(前元十六年)夏四月,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8}按照司马迁的说法,《王制》篇是汉初博士根据儒家“六经”写成的,并非先秦“实录”。东汉末年的经学家卢植同意《史记》的记载,但郑玄认为该篇的创作紧挨在东周灭亡之后,孔颖达则推定“《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9}。近代以来,廖平、康有为等人认为《王制》是“孔子改制之作”,即战国末期的作品;任铭善、钱玄、沈文倬也各有不同看法。{10}据洪诚分析,《王制》篇的内容甚至可能是由不同时期的材料“层累”而成的。{1}那么,篇中的“北方曰译”等记载到底为真还是后人杜撰?如果属实,又始于何时?这些问题目前很难有明确答案。
同样,《周礼》的成书情况也不明朗。《周礼》原名《周官》,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和百官职守的典籍,始出于西汉景帝、武帝之际。虽然被刘歆颂为“周公致太平之迹”,但关于该书真伪及创作年代的争论至今莫衷一是。各方的说法归纳起来,至少有五种:西周成书说(或称周公手作,或以为非);春秋成书说;战国成书说;周秦之际成书说;汉初成书说(或称刘歆伪作,或称王莽伪作)。{2}与《礼记》类似,也有论者认为《周礼》不成于一人一时。③
概而言之,《礼记》(特别是《王制》篇)和《周礼》都未必成书于西周(遑论“远古”),甚至可能是后世经学家附会而成的作品,其中涉及“译”和“象胥”的记录是不是“关于周王朝的翻译官职”{4}的真实记载,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
除了传世文献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之外,目前见到的先秦出土文献中也都没有可资验证的材料。{5}据笔者所知,目前仅有一位学者从战国楚简中辨识出可以作“象胥”解释的“象”字,⑥但这也只能说明“象”这个词可能被用来指称译官;关于“译”字的先秦出土材料仍付阙如。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学者毕鹗(Wolfgang Behr)把《礼记·王制》的相关记载称为“难以核实的假设”(such an assumption is rather hard to verify){7}也是合乎情理的判断。在我们把“寄”、“象”、“狄鞮”和“译”视为“曾经的官方头衔”(at once official titles)乃至“用隐喻和象征性语言对现在被称为‘翻译的那种行为进行描述、命名和包装的一种重要的理论尝试”(theoretically significant attempts made in the past to describe,to name,and to wrap around with metaphors and figurative language the activity now called “fanyi”){8}之前,似乎应该先对其历史真实性进行审慎的论证。
虽然周王朝是否把译官称为“译”值得商榷,但“译”在古汉语曾被当作“译官”来使用则是毫无疑问的。《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载:“丘力居等闻虞至,喜,各遣译自归。”{1}《汉书·佞幸传》曰:“单于怪(董)贤年少,以问译。”{2}这两处“译”都作“译官”解释。成书更早的《吕氏春秋》亦然:
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③
这里把“象”、“译”、“狄鞮”并列起来,倒是与《礼记》和《周礼》的记载吻合,但孰先孰后仍无法确定。一般认为《吕氏春秋》作于战国末期{4},也就是说:用“译”来指称“译官”的做法大抵在秦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尽管未必早到西周)。然而,“译官”究竟是不是“译”这个词的本义呢?
二
有人借助文字学的方法,从词(字)形的角度分析“译”的本义。牛云平、杨秀敏根据《说文解字》对“译”(譯)的字形分析试图“还原”该字的本义,他们认为:“其形部‘言表示‘譯是口头语言行为;其声部‘睪在表声之外,从其篆体形象来看,也含有会意‘观察的意味。因此,‘译字的本义就是指把自己观察到的内容用口讲出来,使人明白。”{5}这种说法看似有一定道理,其实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要考察汉字的本义,必须先找到这个字的原始形体,而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里没有见到“译”字,最早的只有汉简中出现的隶书⑥。《说文解字》分析的虽然是早于隶书的小篆字形,但仍不足以作为“造字本义”的判断依据。而且,某个汉字的义符在单独使用时可能有多种含义,甚至可以表示不同的词,这势必导致孤立的字形分析得出不统一的结论。比如“译”(譯)这个字,我们也可以给出另一种分析:把“睪”视为“驿”(驛)的省略,表示传递。译(譯)=言(说)+睪(同“驿”,传递),“译”的造字本义就变成了“用一种语言传达另一种语言”{7}。以上两种字形分析的结论都可以从后人的训释中得到“呼应”,比如朱骏声就指出“译”可以假借为“睪”{8};陆德明解释《孝经·圣治章》旧注中的“重译”时也说:“译,本亦作‘驿。”{9}然而,用这些后世语料来解释原初字形实则近乎“循环论证”,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以上的字形分析其实都带有相当程度的主观性,在没有比较过重复字形之前,仅凭孤立个案揣测“造字本义”很容易出现差错。王宁曾指出,追究汉字的本义(“以形索义”)必须经过“溯本”(如为借字,则求本字)、“复形”(寻找字的原始形体)、“归纳异字同词”和“分析字形”四个阶段。{1}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译”这个字恐怕还无法从文字学的角度勘明其本义。
即使我们能够还原“译”的造字本义,问题也并非迎刃而解。按照陆宗达和王宁的说法,“字”的本义是“体现在文字字形上的字义”{2},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词”的本义,因为“象形、会意以及形声字中的义符都是比较具体的,但它所代表的词,却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意义,而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抽象的意义。只是既然用意音文字来表示,那么抽象意义也就不得不以一个具体的字形或义符为依托了”③。这种“抽象意义”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能表现出来。{4}所以,考察词的本义不能光看字形,还要结合实例综合分析。但正如上文提到的,早期文献的稀缺使得我们很难通过这样的方式分析“译”这个词的本义。
三
高守纲曾指出,探求词的本义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综合考察:义位之间的联系层次;词的书写形式;用例始见文献。{5}上文讨论的分析方法实际上是从后两个方面着手,但都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那么,分析“译”各义位之间的联系能为我们提供怎样的线索呢?
现代汉语中的“译”一般作及物动词使用(如“译书”“译经”等),指“翻译”这一行为,⑥和古汉语中表示“译官”的动词“译”分属不同词类。根据蒋绍愚的观点,同一个汉字表示的几种意义之间只要有一定关系,即使其语法功能发生了变化,一般仍看作同一个词的不同义位。{7}也就是说,“译官”和“翻译”行为可以视为“译”这个词的不同义位,而其间的变化过程即“词义引申”的过程。正如陆宗达和王宁所指出的:“引申是一种有规律的词义运动。”{8}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词义引申的一般规律来推测“译”的本义呢?
高守纲在归纳古汉语词义引申的方式时,曾把“借动作行为指代动作行为的实施者(多指以实施该动作行为为职业的人)”专门归为一类,比如“倡(唱)”由“领唱”引申为“以演唱为职业的人”;“贼”由“杀害”引申为“刺客”;“将”由“领兵”引申为“领兵的人”。{9}罗正坚列举的“乞”(乞讨→乞讨的人)、“候”(侦查→侦查敌情的人)和“侦”(同上)也属此类。{10}但反过来的情况,即由动作行为的实施者引申出动作行为的例子则未见到。这种现象符合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方式。试想:若要描述某个具体行为的实施者,势必先对这一行为做出界定,因为该行为本身是其实施者区别于其它行为实施者的唯一特征——亦即我们不可能避开行为过程而直接表达行为实施者的概念;反过来,当我们要描述某个行为时,则不一定会涉及该行为的实施者。具体到“译”这个词,曾有论者指出过:“理论上应该是先有表行为活动的‘译概念的出现,然后才是其它(译者、译文等)。”{11}从逻辑上看确实如此:当我们要表达“译官”的概念时,必须先界定“翻译”这个行为,因为从事“翻译”行为是“译官”区别于其他职官的唯一特征。简言之,“译”的“译官”这层意思无法离开“翻译”行为而单独存在。因此,把“译官”视为“译”的本义,认为由表示“翻译行为实施者”的义位引申出表示“翻译行为”的义位不符合词义引申的一般逻辑。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后世经学家解释《礼记·王制》中的“译”字时暴露出的“词性冲突”:孔颖达承认这里的“译”是“通传北方语官”(即承认其为名词),同时又认为“译”和“陈”同义,指“陈说外内之言”(即动词);{1}贾公彦同意郑玄“通夷狄之言曰象”的判断(可以据此推测他也认可“译”是译官),但又用“易”来训“译”,指出其含义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2};张自烈也指出“译”和“寄”、“象”、“狄鞮”都是“通远人言语之官”,同时又说:“译,释也,犹言誊也。谓以彼此言语相誊释也。”③以上这些学者虽然都把“译”看作官名,却又不得不用动词来加以解释。这种矛盾在许慎以“译”释“译”的做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说文》称“译”为“传译四夷之言者”{4}——释文中的“译”当动词用,而作为被释字的“译”则显然是个名词。可见,我们确实无法绕开翻译行为来指称翻译行为的实施者,“翻译”(行为)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包含在“译官”这个义位里了,因此,前者的出现应当先于后者。如果用语义成分分析的方法来描写“译”从“翻译”引申出“译官”的过程,可以粗略地表示成:
翻译=[转换]+[语言]→译官=[转换语言]+[官员]
这一引申过程在修辞学中被称为“转喻”(metonym),其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一种“相关联想”(关系联想),即由对象之间的某种联系所唤起的联想。{5}实际上,本义始见文献晚于引申义的情况确有发生,比如“理”(治玉→整治)和“習”(鸟反复飞→学习)这两个词根据字形分析和义位关系整理得出的本义在文献中的用例都比引申义的用例要晚。这种现象可能是由“文献语言在反映口语方面的局限性和不平衡性”⑥造成的,即本义在口语中的早期用例没有被记录下来或记录了但没有保留下来;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字本身就是为引申义造的,比如“侯”(诸侯→箭靶)、“啟”(开启→启发)、“陽”(日光→山南水北)等。{7}
本文从用例、字形和义位三个角度,尝试对“译”这个词的本义作了探讨。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译”这个词并非是“由最初的指代职称和官衔发展到了指代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8};实则恰好相反,“译”本来的意思就是指翻译行为,“译官”才是后来衍生的含义。
【责任编辑 孙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