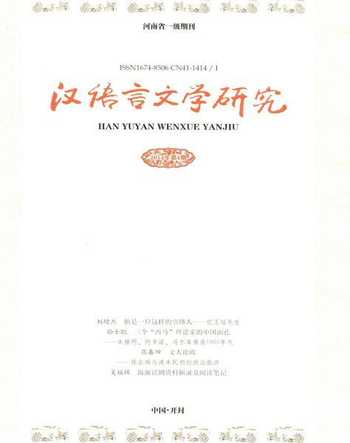他是一位这样的引路人
一
比起1958年许多高校掀起的批判教师的“拔白旗运动”,1959年高等学校里紧张的政治气氛开始有所缓和。此时,拥有雄厚师资实力的北京大学,向国内高校伸出了援手,同意一些学校选派青年教师来北大进修,期限一年。我是北京大学这一开放政策幸运的受惠者。暑假后,我和来自北京、天津、辽宁、福建、贵州、河南等地的现代文学青年教师,获准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王瑶先生指导下进修学习。
王瑶先生的名字当时我并不陌生。早在1954年开始学习中国新文学史的时候,我们学校教这门课的老师,在课堂上就拿着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向大家作过郑重的推荐:“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新文学史著作,内容丰富,史料也相当完备。”这位老师看着《中国新文学史稿》版权页又说,你们听一听这部著作印刷的数字:1951年9月开明书店出版后,曾接连印刷了五次。1954年3月,新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就又重印了15000册,现在已经累计印了35000册。同学们发出了一阵赞许声。在老师的介绍下,我们每人都买了一部《中国新文学史稿》。当时,教材的有些内容读起来还似懂非懂,但我们学习的热情却很高。五年后,当获知有机会到北京大学直接来听王先生讲课,我顿时产生了一种喜从天降的感受。
在北京大学学习生活开始的时候,也有过一点不知所措的精神紧张。到中文系办公室报到的时候,工作人员一声不响地递给了我一张油印小报。小报的名字叫《大跃进》(第29号),出版的时间是1958年4月18日。这一期《大跃进》是批判王瑶先生专号,通栏标题是:《这决不是客观主义!》副标题是《致王瑶先生》。小报共两版,发表了八篇批判文章。1958年全国高校开展的“拔白旗运动”,是对在学术上有成就的教师进行批评、批判的政治运动。学校发动学生和青年教师,开大会、小会,写大字报,对这些教师“上纲上线”,进行揭发、批判,要求被批判者在会上作“深刻”检讨,改造思想。所不同的是,我所在的学校对老师的批判,只采用了开会、写大字报的形式,没有像北大这样印刷小报,竟然还记录在案。作为去年曾经同样卷入了“拔白旗运动”,也批判过老师的青年教师,我后来认识到:这是利用年轻人的幼稚,把矛头直接指向学术上有成就的老教师,实际上对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造成了难以补救的精神内伤。读了《大跃进》上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批判王瑶先生的文字,我的心情异常沉重,想到了先生当时所承受到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因为正是在“拔白旗运动”之后,王瑶先生担任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文艺报》编委职务都被撤销了。我担心,王先生在指导我们学习的时侯,也许会变得小心谨慎,不敢畅所欲言。
但是,我的顾虑很快被现实打消了。开学不久,我们接到了王先生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说,我邀请大家来家里坐坐,见见面,谈谈对你们学习的安排。带着几分兴奋和一丝不安,我们很快地来到了王先生的中关村寓所。先生家的客厅不大。沙发前面的桌子上,摆放着糖果、茶水。我们围着先生坐下后,他一面端起糖盘请大家吃糖,一面拿起一张进修教师名单,一一核对名字,询问来自哪个学校,问长问短。先生和我们每个人握手的时侯,总是微笑着说:“欢迎,欢迎!”气氛和谐轻松。先生还说,系里告诉我,进修教师和研究生的政治学习呀,两周一次的劳动呀,你们都要参加,活动由中文系统一安排。进研班教学以外的具体事情,由青年教师严家炎、孙庆升两位负责。然后,王先生又望了望我说,系里要你协助一下他们两位的工作,有事的时候跑跑腿。琐事安排后,王先生接着说,时间宝贵,现在上课。上课采取两种形式。一是我定期在家里上课、辅导;二是你们可以按照课程表,随着学生一起在教室听课。他又说,中文系对你们很重视,同时还安排了章川岛先生给你们上课,随后你们可以和川岛先生直接联系(川岛是鲁迅的学生,著名的鲁迅研究家)。王先生强调:“新文学史是基础课,很重要。重要就在于它距离我们很近,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你们除听课外,主要靠自己阅读,课堂上只是提供一些线索。阅读除了看我开的书目外,还要多看一些相关的书。课堂上要记笔记。记记要点,记记课堂上触动过自己思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需要通过进一步的阅读来解决。手不要懒。记笔记有助于培养自己勤于思考的习惯,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思绪。”
长达一年听先生讲课,以及每个月到先生寓所讨论问题,不时地听听先生三言两语的点拨,收获良多。在课堂上,先生从绪论讲起,一直讲到了建国十年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原原本本,实实在在。在思想受压抑的年代,先生对某些文学现象的阐释,虽然难免从俗,沿用了某些流行的说法,但从总体上看,王瑶先生仍然保持着内心的强大,精神上的坚韧,有着学术开路人的胸怀与魂魄。教学上,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鲁迅研究。在讲授鲁迅生平和文学活动时,先生反复申明,学习五四文学传统,主要是学习鲁迅。鲁迅的作品可以看作当时文化斗争发展的史料。《人民日报》曾说,鲁迅的文化遗产超越了许多前代人留下的的遗产。鲁迅写农民,是很了不起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像鲁迅小说这样写农民的作品(《水浒传》写的农民已经脱离了生产)。鲁迅第一次从农民的角度看问题。过去的小说都是从上层去暴露封建制度的罪恶,鲁迅则从统治者和农民的对立关系上来写。鲁迅小说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对辛亥革命的失败批判彻底、深刻。
1960年3月17日,王瑶先生还做了《鲁迅作品的民族风格》专题学术报告。报告详细分析了《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现实依据。王先生说:“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章太炎都曾经被称为疯子。章太炎1906年到东京发表演说时就说,当时别人都叫他疯子。鲁迅受章太炎的影响极大。他在杂文中称章太炎有先哲精神,是后人的楷模。”王先生把作品人物分析和现实巧妙地紧密结合,能够开拓思路,给听众带来强烈的震撼。王先生有着岁月沉淀下来之后的那一份淡定。他对作品艺术个性的把握,常有诱人的艺术灵气的闪现。王先生的教学,时常真见迭出,妙语连珠,机智幽默,左右逢源。听他讲课,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在课堂上,先生用炽热的爱温暖着学生,同时也消融了“拔白旗运动”带给自己的冰冷。
二是教育学生要掌握丰富的史料。王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抗日战争以前的报纸、期刊比较齐全。你们来这里进修,不看看这里的图书、期刊,一年以后两手空空回校,太可惜了,等于白来了一趟北大。可是,由于当时我们都还没有进入研究状态,对先生的指引重视不够。我在北大图书馆虽然坐了几天,但缺乏全局眼光,只是在那里着重看了看河南作家如冯友兰、曹靖华当年在北京创办的一些影响不大的小刊,辜负了先生的良苦用心。多年以后,才醒悟到了掌握基础性史料对于研究的决定性意义。
三是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在进修期间,我们多数人还缺少从事研究的能力。到王先生家里听课,往往提不出真正的学术问题。有一次,我突然冒出了一句傻话:“王先生,现代文学现在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呢?”话一出口,我就发觉自己说了无知的话。但王先生并没有直接批评我,反而笑着说:“这也算一个问题吧,不过,你提的问题太大了。”略微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学术研究就是研究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当前研究涉及较少,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说一个具体问题吧,比方说,戏剧研究中的喜剧问题,或者叫轻喜剧问题,用喜剧形式写出来的剧本,或演出,或供阅读,使观众或读者看过后得到消遣,安慰,会心一笑,调节一下生活。这个问题就值得研究。现代文学史上,从胡适开始,到欧阳予倩、陈大悲、丁西林、李健吾、陈白尘、熊佛西、袁俊、沈浮等人,他们都写出过带有趣味性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进行系统梳理,结合国情进行独立研究,一定会很有意义。在座的哪一位如果感兴趣,不妨找来剧本,以及演出时候的相关材料,认真研究,开辟出一片研究的新天地。不过,你们现在的阅读量可能不够。目前试着搞研究,还是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展开,比较适宜。”王先生这时突然放慢了谈话的语速:“研究就是发现,发现来自实践,来自阅读与思考。实践多了,总会有所提高。你们不用太急,但也要开始起步。”先生的话语重心长。大家当时虽然没有直接来回应先生,听得却非常认真,手在笔记本上写个不停。回想起来,自己走过的路虽然至今还歪歪斜斜,但总的来说,还是沿着王先生当时指引的路走过来的。
五十五年后,望着当年记录的这一册纸已发黄的课堂笔记,心中荡起的是对先生久远的思念。
二
钱理群先生曾说:“我隐隐觉得,自己好像和河南近现代学术界之间,有一种‘缘分。……这样的亲和关系,更存在于我所在的北大和河大之间,我的老师严家炎、樊骏,我的同学吴福辉,还有本身就是河南人的赵园,都与河南大学文学院有着不解之缘。这背后,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也说不清楚,或许是学术路向、追求与学风的某些相通吧。”{1}
钱先生所说的“缘分”,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始于前述的1959年。即我有缘来北大进修,师从王瑶先生那段日子。此后,经历了1960年代前期持续的文学批判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自己的专业学习虽然时断时续,但和王先生的联系却未完全中断。高校恢复招生后,我到北京看望了王先生。久经折磨,先生依然目光深邃,内蕴锋芒。他热情地介绍了北大研究生的培养经验,还把钱理群、吴福辉两位高足撰写的论文打印稿拿出来让我带回学校参考。王先生带着欣赏的口吻说,年轻人思维敏捷,他们的文章有新意,势头很好。你们招研究生,要格外重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当时,我还受学校委托,邀请王瑶先生来河南讲学。先生也爽快地应允了。通过书信往来,讲学活动很快成行。当时王先生的心情很好。讲学期间,对我们专业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都主动提出了一些切实的建议。他和任访秋先生有过深入的交谈。王先生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少林寺、开封相国寺等景点,和师生一起照相留念,留下了特定瞬间的面影。
此后,王瑶先生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走向,更有过切实的指导。比如,我后来从事解放区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就源自王瑶先生的直接推动。我在一篇接受郝魁锋访谈的文章里,对此有过介绍。郝魁锋问:你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听说得到过王瑶先生的指导,具体情况怎样?
我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作过这样比较详尽的陈述:“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征集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80年9月初,主持单位邀请相关出版社编辑、高校、研究机构的代表,在安徽黄山召开了现代文学资料会议,具体讨论了编辑三种丛书的原则与任务。三种丛书即:甲种:“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乙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丙种:“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落实编选任务的时候,讨论到“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中的《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一书时,会议冷场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他,却没有人站出来认领任务。会场里不时还能够听到有人低声地议论:战争环境下,资料丢失太严重,搞起来困难……。片刻沉寂后,会议主持人之一的王瑶先生,突然抬起头来,微笑着望了望我说:‘刘增杰,你们单位人多,承担起来怎么样?我那时已经答应了编《师陀研究资料》等作家研究资料的任务,却对从事解放区文学资料编选没有思想准备。听到了王先生的问话,我支支吾吾,讲了一些对研究对象不熟悉等理由进行婉拒。没想到,针对我列举的理由,王先生竟逐条作了‘反驳。他说,对研究对象不熟悉,不是理由。你下点功夫不就熟悉了么?还说,编选史料的学术价值,主要是看编选者的认真程度,学术见识的高低。王先生雄辩滔滔。他一边陈述自己的理由,一边诙谐地哈哈笑着,好像等待着我应答时出现新的漏洞,再来和我较量。会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显然,大家都被王先生机智的论辩方式征服了。我自知不是与先生论辩的对手,又已经被聘为乙种丛书编委,应该支持编委会工作,就忙笑着接受任务了。王先生和我论辩时直言快语,随意而亲切,显然是源于二十多年前,我们之间的师生之谊。解放区文学史料的征集、编选任务,就这样落实到了我和教研室几位老师肩上。三卷本《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编好后,经过责编王瑶先生、徐迺翔先生审定,1983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王瑶先生对这部资料的学术质量是肯定的。徐迺翔1981年10月11日给我来信说,‘王瑶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说,从他经手审稿的几部稿子来看,你们这一部是内容比较扎实丰富的。这是我们共同的印象,我想也是符合实际的!应该说,我在史料研究实践中所逐渐获得的一些感悟、收获,受惠于王瑶先生等学术前辈的关爱。他们强大的人格力量,献身学术的精神,对我们的指点、呵护,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前进的脚步。”{1}
事实上,此后我在解放区文学的研究中,继续得到过王先生的鼓励与支持。王先生很重视解放区当年研究鲁迅的经验;他还建议我写一写编选资料过程中访问作家的具体情况,认为,这些鲜活的史料很容易被时间淹没;他和徐迺翔先生共同催促我具体谈谈解放区文学资料编选过程中的曲曲折折。这几项要求,我都按时完成了任务。{2}1987年10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将在四川成都举行。年会讨论的学术内容之一,是关于解放区文学研究进展的回顾。5月,我收到了樊骏先生恳切的来信。他说,他和王瑶先生商量,关于解放区文学的发言,由我准备,并且要我定下题目后给他回信。由于多种因素,我对承担这项任务一直犹豫不决。心想,不承担任务,怕王瑶先生有意见;承担了任务,又担心有些问题比较敏感,一时说不准确,影响不好,所以一直拖着没有给樊骏复信。谁知他等急了。1987年6月11日,他来信说:
……
记得上次给你的信提到请你准备一个有关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文学的发言,作为今年十月召开的学会年会上的一个重点发言。来信只字未提此事,深感焦虑。此事系王瑶先生一再叮嘱的,说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发言,责成我组织。我提议你承担,他也同意了。
我想你可以讲整个概况,也可以抽几个问题说说,或者综述以往对于这段文学研究的成就和不足。
我等着你的回音,并且希望你能利用暑假作些准备。在当前形势下,讲的内容自然得以成绩为主。
祝
好
樊骏
6.11
为了免除王瑶先生和樊骏先生的牵挂,我当即给樊骏先生写了回信,并着手做发言的准备工作。这篇题为《期待着深化的研究领域——解放区文学研究断想》的发言,由于准备比较充分,发言后还有一定的反响。到会的两家刊物,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擅自同时将它发表了。③有的朋友还以为我是一稿两投,我当时曾写信作了澄清。1989年,中国现代文学理事会苏州会议召开前夕,会议的召集人同样要我就解放区文学研究准备发言。开会期间,王瑶先生还询问过我准备的情况。我告诉先生,我想谈一点对解放区几部较有思想深度作品的看法。这些作品对现实的警示意义常常被人为地遮蔽了。王先生表示同意,并说,你做得对。质疑孕育着突破,解放区文学研究要有点新意,不能年年千篇一律。没有想到,这次理事会期间和先生的交谈,竟是和他的诀别。我在会议上的发言,会后整理成文,成了对先生默默的纪念。{1}王瑶先生逝世后,1994年在西安召开的学术会议和王瑶先生纪念会,我本来决定参加,并着手撰写纪念短文,但因为临时遇到的突然情况不能脱身,未能成行。此后,钱理群先生筹备出版王瑶先生纪念集一书,但出版遇到了困难。我获知消息后,立即和有关方面进行多次沟通,河南大学出版社爽快地答应了出版这部纪念集。纪念集得以出版的消息,使朋友们感到了由衷的欣慰。钱理群在1995年3月17日来信说,“接志熙来信,得知你一直为出版《王瑶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费心,我十分感激,也觉得很不安。我深知在目前形势下,出版这类论文集的难处,给你添了不少麻烦。”5月15日,钱理群又来信说,“王师母得知《王瑶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能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感到十分高兴。让我代她向你及出版社同志表示感谢。”樊骏先生同时也给我来信说:“听钱理群说,这次关于王瑶学术思想的论文集的出版事宜,又落到老兄头上,为又一次麻烦你而既感激又抱歉!”我给樊骏先生回信说,作为王瑶先生的学生,能够为这本纪念集的出版尽一点微薄之力,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表彰先生一个人,更是为了延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使文学记忆成为久远的历史启示。对于王瑶先生,我只是做了一个学生应该做、能够做的事。这些,也许就是钱理群先生所说的“学术路向、追求与学风”有“某些相通”的内在因素吧。记忆充满着阳光。正是王瑶先生的学术精神,把国内几代研究者连结到了一起。
王瑶先生是一位这样的引路人:当他发现你性格里有几分怯懦,就会善意地刺激你一下,将你一军,用诙谐的方式逼你上路。上路以后,见面的时候话虽然不会很多,但双方却有着心灵的默契,沟通。他以纯真的性情,在暗中会继续注视着你,鼓励着你,让你自身生长出前进的力量。王先生的引路是切实的,严格的,纯洁的。所有的大师都润物无声。王瑶先生赐予我们这几代人的东西很多。人要学会感恩。感恩不只是对先生单纯的颂扬、纪念,感恩的要义是经营好自己的人生,像前辈那样正直地做事、做人;在学术上,要设身处地体察初创者的艰辛,不随时潮俯仰,要像先生那样拥有自我独立的学术人格。只有这样,在研究中才有可能坦然面对未知的挑战。
2014年8月25日草于河南大学
【责任编辑 穆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