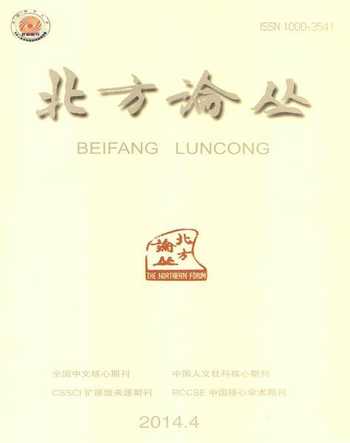1949—1979年汉语新诗文本生成要论
陈爱中
[摘 要]1949-1979年是汉语新诗发展史上相对独特的时间域段。意识形态所营造的社会文化语境、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诗歌理念、汉语诗歌主体等各种语词互相冲突、纠结,经过从诗人到诗歌的痛苦转变,并最后融汇到诗歌的公共话语的整体语境中,汉语诗歌从个人写作到集体写作的变身,使得汉语新诗从本质上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并因之影响到新时期以来的汉语新诗认同。
[关键词]穆旦;个体话语;公共话语;30年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5-0040-05
[收稿日期]2014-07-05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术团组项目(SYG2011-01)。
① 著名诗评家谢冕说:“三十年诗歌的症结不是在形式。根本弱点是诗歌没有思想。标语口号化的结果,诗人失去了他的独立见解,以及表达这一独立见解的自由”(谢冕:《和新中国一起歌唱——建国三十年诗歌创作的简单回顾》,《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从20世纪40年代就参与并目睹随后汉语新诗发展历程的诗人郑敏,在新世纪初总结汉语新诗近百年的历史脉络时,只用下面的寥寥数语来评价:“这是一个政治术语成为权威的阶段。通过会议发言和政治学习,革命大批判和报章评论等各种途径,政治意识形态语汇已经深深渗入日常生活用语和文学语言。文学作品自我否定了其过去的文学语言。这时期的诗歌写作除了用学院派的政治语言,就是民间的政治化口语。大跃进迎来歌颂人民公社的全民诗歌运动,农民作家们发展出一种文白相间的革命诗体,颇有特色。60年代的大字报运动则发展一种辩论文体,它的痕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影响着我们的议论文和议论者的写作心态”(见郑敏:《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的汉语新诗,已经在否定的记忆里被遗忘了三十多年①。汉语新诗从郭沫若的《新华颂》和何其芳的《时间开始了》开始,以乐观者的姿态从本质上开始重塑生命。无论是被动地参与社会文化的建构,还是积极地在社会文化的引领下丰富和创造着新的诗歌文体,影响并改变着社会文化对汉语新诗合法性的认识,这种与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文化的互文,从实践上影响到汉语新诗的自我认同。作为一段可以忽视但无法抹杀的历史,否定性的思维可以从文学价值论的角度无视它,但从整个汉语新诗发展历程上说,它“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也许才是真正的历史主义的态度,也才能为真正具有价值论意义的诗歌作品的涌现寻找因果逻辑。
一、荒芜的个体话语:另一种诗歌生命
20世纪40年代之后,时代有了对新文学进行改造的欲望。相比于小说、散文在阅读接受上的间接性,因为形式上的可操作性和观点传达上的便捷,汉语新诗在实现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意图时,尤为得心应手。墙头诗、街头诗、民歌体等短小精悍、鲜活明快的诗歌体裁被创造出来并发扬光大。从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田间的《给战斗者》等代表性诗篇的纷至沓来,以“民歌”和乡土的身份涌现的这一个层面的汉语新诗很早就融入意识形态所指定的轨道,并随后成为一统诗歌江湖的代表。
意识形态与汉语新诗之间的互文关系是有历史的,并深深影响着汉语新诗的生命样态。意识形态通过成立作协、文联等半官方的组织来统一管理诗人,将诗人的生存理念、生活方式和创作方式纳入集体管理的模式,通过作家研讨会、专题学术会议的形式来展开关涉诗歌写作的主题、形式、语言等问题的讨论,将其置于先验的理论框架和题材域限内,采取相似或相近的主题或题材进行集团性创作,从而改变了诗歌素来的个性化写作模式。这样,诗人和诗歌成为一种统一化的集体行为,在处理汉语新诗问题时,往往也采用集体攻关、“攻占堡垒”等颇富军事化色彩的行事策略。比如,1950年3月10日,《文艺报》第1卷第12期就刊出诗歌笔谈——《新诗歌的一些问题》,刊有萧三的《谈谈新诗》、冯至的《自由体与歌谣体》和王亚平的《诗人的立场问题》等论文,从语言特点、新诗与旧诗、格律等问题出发开始有意识地探讨和规范汉语新诗的创作方向。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的召集和传播下,将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王力、冯至等众多行家里手都囊括进来,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讨论会的形式,报刊集中做更为系统的学术论文的媒体轰炸,等等。这些集团式的做法试图依靠理性的推理和观点逻辑的推演,来为汉语新诗发展的形式问题提供灵丹妙药。应该说,这种理论指导创作而非单纯的总结创作的情形,在汉语新诗发展史上并不鲜见,或者说这是现代认识论上理性觉识的必然产物。如闻一多的格律理论对新月诗歌的引领,象征派诗歌对李金发、穆木天等人的诗歌的影响,以及新时期以来,诗歌界不停探讨的新诗写作和判断的标准问题,等等。但一般来说,这种诗歌活动大多是沙龙化的同人行为,局限在有着同一志趣的小圈子里,在组织上并不那么严谨,也并不遵循多么严格的写作纲领,诗人和诗歌的个性还是分外鲜明,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汉语诗歌的写作路向。如20世纪50年代新诗格律这样的参与人数之多、并带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大规模的探讨,则超越了单纯的沙龙而溢出到诗歌之外的意图。并以此为先例,在30年的时间内,还有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小靳庄诗歌,等等,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逐渐成为汉语新诗的集体无意识,在外部环境上相对限制了诗人的创造性。对于现代新诗来说,一旦诗人和诗歌失去个性的审美肌理,诗歌也就被躯壳化了,内容的大致恒定,诗歌也就剩下分行的外形,人人皆可成为诗人,失去相应的规范和审美准则,汉语新诗开始毫无节制地狂欢:“狂欢节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1](p.11)。于是,我们看到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中的诡异景象:“在那些最激动人心的大跃进高潮的日子里,一个工厂、一个农业社,在一夜之间,人们创作的诗歌,往往要用千首万首来计算,真个是‘百花怒放,万紫千红。在大跃进高潮中,往往出现这样的事情,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就使一座城市变成了诗城。街头巷尾,机关商店的里里外外,到处都贴满了诗,挂满了歌,人们称这为‘一夜东风吹,跃进诗满城。”“群众诗歌创作的规模,在出版物上,也得到了应有的反映。在民歌运动的初期,报纸和刊物就大量刊出了民歌,许多报纸,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用大量篇幅,经常刊出以‘最好的诗、‘跃进战歌、‘口号和战歌等为名的民歌专栏或专页。全国报纸毫无例外地经常刊载了民歌和论述民歌的文章。许多文艺期刊,如《边疆文艺》《文艺月报》《处女地》《前哨》等等,都在这一年出了诗歌专号,大量地选登了民歌。书籍出版上更是一种无比宏伟的景象,据极不完全的统计,全国省以上出版社出版的民歌集子总数达七百多种,至于专区、县、区、乡,乃至社出版的民歌集子,那更是无法计算”。而且这种现象的出现被归结为和诗歌不那么有联系的因素上,“大跃进诗歌创作的雄猛来势,是与生产大跃进的情势和规模相适应的”[2](pp.9-11)。无论是参与人群,还是“成果”的数量,都堪称“硕果累累”。30年的汉语诗歌以“运动”的机制重塑着汉语新诗的发展轨迹。于是,诗歌越来越成为一个公共事件,无论是题材、主题,还是形式都行走在公共的轨道上;无论是大跃进诗歌运动,还是小靳庄诗歌运动,都是一次诗歌的全民“狂欢节”。这种狂欢对新诗的另一个巨大影响是,它营造出足以裹挟个人情性、让人迷失的激情氛围,进而诱惑每个诗人积极而主动地参与到这种氛围中,唯恐被抛弃,主动消解掉个人的痕迹:“‘狂欢节效应指的是当一群志趣相投的寻欢作乐者决定纵情享乐,不顾后果与责任时,他们会暂时放弃传统对个人行为的认知和道德约束。这就是群体行动的去个人化过程”[3](p.353)。而且这个“去个人化过程会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此一心理状态下的行为受到当下情境的指挥,以及生物性的、荷尔蒙的分泌驱使。于是,行动取代了思想,立即享乐凌驾了延迟的满足,而小心谨慎的自我克制也让路给愚蠢的情绪化反应……内在的约束被搁置时,行为完全受到外在的情境操控——外在控制了内在。做一件事时考虑的不是正确与适当与否,而只看可不可能、做不做得到。个人和群体的道德罗盘已不再能够指挥方向”[3](p.352)。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就可以理解曾写出《大堰河——我的保姆》《在北方》《黎明的通知》的大诗人艾青,在20世纪50年代写出的如“杨家有个杨大妈/她的年纪五十八/身材长得高又大/浓眉大眼阔嘴巴”的荒诞诗句了,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艾青写作此诗时的真情与投入。
剑桥大学教授刘易斯(C.S.Lewis)在其著作《核心集团》(The Inner Ring)中说:“我相信,想打入某个核心的渴望及被排除在圈外的恐惧,会占据所有人一生中的某些时期,甚至许多人从婴儿时期到垂垂老矣,终其一生都被这些念头盘踞……在所有热情之中,成为圈内人的热情最善于让本质还不坏的人做出罪大恶极的事。”[3](p.304)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政治运动,进一步压缩了持不同文学主张人的生存空间,让曾经远离主流审美的人群颇有不安感,并渴望着能被新的语境接纳。坎坷生涯的积淀和丰富学识滋养下的诗人穆旦,在20世纪40年代汉语诗歌领域做出了卓异的成就,其诗歌中创立的分裂的“我”的形象,非常深刻地透视出现代人的酸涩和灵魂纠结,面对生与死,爱恋与离别折磨的痛苦思考,一个诗人兼哲学家的穆旦影响着许多人。到20世纪50年代,穆旦开始彻底放弃早已蜚声的“我”,而阐发出颇富原罪感的忏悔。他发表在1957年《诗刊》5月号上的《葬歌》表现得比较充分:“历史打开了巨大的一页,/多少人在天安门写下誓语,/我在那儿也举起手来;/洪水淹没了孤寂的岛屿”,被冷落的孤独感应然而生,于是诗人说“我看过先进生产者会议,/红灯,绿彩,真辉煌无比,/他们都凯歌地走进前厅,/后门冻僵了小资产阶级”。经历过20世纪40年代初丛林逃生的生死体验的诗人越发感觉到内心的不安:“这时代不知写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诗,/而我呢,这贫穷的心!只有自己的葬歌。/没有太多值得歌唱的:这总归不过是/一个旧的知识分子,他所经历的曲折;/他的包袱很重,你们都已看到;他决心/和你们并肩前进,这儿表出他的欢乐。/就诗论诗,恐怕有人会嫌它不够热情:/对新事物向往不深,对旧的憎恶不多。/也就因此……我的葬歌只算唱了一半,/那后一半,同志们,请帮助我变为生活。”这是一个以否定过去,并对未来表示惶恐的一代“旧知识分子”的象征,出身的原罪感让他们不敢有“信心”和“希望”,在为过去的诗歌生命唱“葬歌”的同时,在灵魂深处依然留恋着“回忆”,在“你可是永别了,我的朋友?”的疑问中,诗人也在痛苦地思索如此丢弃诗性心灵中最瑰丽的东西是否值得,尽管以眼泪洗身,但也不得不为自己开始的忏悔感到“欢喜”。但无论如何,诗歌结尾的谦逊还是真实地表露心迹的,“就诗论诗,恐怕有人会嫌它不够热情”,从此,表征汉语诗歌的高贵头颅的影像断然沉寂。然而,现实比诗人想象得更为残酷,也因为这种纠结,很快被人认为,这首诗“好像是旧我的葬歌,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颂歌”[4](pp.96-98)。认为穆旦并没有响应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号召。这使得诗人随后不得不以更为卑微的心态,面对诗歌和现实的人生世界。
这里,应该论论以写政治抒情诗著称的郭小川。他的真诚在这一时期诗人心灵转变过程中,颇具代表性。1969年1月8日,政治抒情诗人郭小川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我必须抓紧一切时间交代检查自己的问题,革面洗心,重新做人……往日的罪过,将成为我永生永世的教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将是我的强大武器。伟大领袖毛主席啊,下半生我将永远忠于您!”[5](p.246)1970年12月10日,在给儿子郭小林的信中,郭小川这样写道:“我过去写的东西,有些实在是不行的。那时候,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加以检验。今后,决不能这样瞎干了。处处要突出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准确,文学这东西是生活的能动的反映……不要以为诗可以由自己随意去写。”[5](p.263)因之,郭小川在谈及叙事诗的写作时说:“叙事诗要有适合它的题材,并不是什么题材都可以写成叙事诗。这种艺术问题,也实际上是政治思想问题,我大概也说不清楚。”[6](p.47)被称为“政治抒情诗人”的郭小川显然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情怀。
穆旦、郭小川代表一类知识分子的心态,郭沫若、何其芳和胡风等另一批诗人则因为根正苗红,呈现出另一种豪情。1954年,曾经在《预言》《画梦录》里“如烟似梦”地描画“扇上的烟云”的何其芳写了《回答》,表达出在新的局势面前的诚惶诚恐:“从什么地方吹来奇异的风,/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颤动:/我的心就是这样被鼓动着,/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轻一点吹啊,/让我在我的河流里勇敢的航行,/借着你的帮助,/不要猛烈得把我的桅杆吹断,/吹得我在波涛中迷失了道路”。一样地对前途不知所踪,一样地自我忏悔,但和穆旦、郭小川的痛苦纠结不同,何其芳迅速背叛过去,走向了新生,写出《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到街上来,/到广场上来,/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庆祝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节日”。新中国刚刚建立,郭沫若就写作了《新华颂》:“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道,辐射寰空”。胡风则有长诗《欢乐颂》问世:“时间!时间!/你一跃地站了起来!/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在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独立的激情里,胜利者的心态笼罩一切,代言人的欢乐和发自肺腑的赞扬是自然的,也是真诚的。正如张志民所说:“为新中国而歌,几乎成为诗人们一个共有的题目。”[7](p.2 )
无论如何,伴随着30年社会文化历史中的“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数次文化改造运动,汉语新诗得以重塑,个体话语被潜隐在心灵的底层,逐渐形成潜在写作和主流写作对立的诗歌形态。诗人在运用主流话语创作的同时,所涌现的如食指的《相信未来》,黄翔的《野兽》《独唱》等,但在当时的诗坛上,相对来说,这部分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只是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其价值才逐渐被发现。从接受的角度说,这些诗歌当属“新时期”,并不能改变30年汉语新诗的认同趋向。
二、诗的泛化:公共话语的载体
诗歌作为内心生活与灵魂的表达,通过语言,揭示出平常人所难以感受到的东西,“引人惊赞的新鲜事物”,以“一种人们所不经见的神奇的本领和能力,能使隐藏在深心中的东西破天荒地第一次展现出来”[8](p.65),从这样一种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上来说,30年的汉语新诗是背离这个宗旨的,诗歌被庸俗化为宣传的工具,甚至可以承担改造世界观的认识功能,“通过诗歌作品,帮助我们提高分辨是非、分辨善恶、分辨进步和落后的能力,从而能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9](p.63)。诗歌的描述内容也有着特定的指向性:“诗必须抒发无产阶级或英雄人民的革命豪情规定性与,而不是‘中间人物或‘反面人物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其它剥削阶级的感情”[6](p.20)。即便是抒情诗,也是如此,“抒情诗的思想内容还需要两个条件:新和奇(也可以说是一个:新奇)。既是马列、毛主席的思想,又跟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新奇了”[6](p.84)。按照这种模式生产出来的诗歌,也就只能是泛化的、毫无文体特征的所谓诗篇了,“我们这个时代,真是一个出诗的时代,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真是一个盛产诗人的国家。无论你走到哪里,在城市的街头,在乡村的墙壁上,在矿山的井架上,在车间的机器旁,在部队的枪杆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诗;我们许多同志在会议上是用诗发言;许多地方的斗争口号,实际就是诗;我们有好多大字报也写的是诗。我们常常用诗歌颂我们的生活,用诗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也用诗批评生活中的某些缺点,指责某些不得人心的人和事……我们的外国朋友,有时候也问我们:你们有多少诗人?每年可以出多少诗集?我们现在可以答复他们:我们国家的诗人大概不会比桂树少。(诗人不是要戴桂冠吗?)至于我们的诗,它的储藏大概不会比石油少,而开采量可要比石油多得多”[6](p.105)。当我们看到郭小川以神气扬扬的自豪口气来写出这段文字的时候,诗歌无处不在、无所不为,这恰恰说明一个问题,新诗失去了贵族气息,失去了相应的规定性,那也就无所谓诗歌了。
外在社会文化界定的汉语新诗,也就决定了汉语新诗的呈现状态远非“黑格尔”的神秘,而是广场化的公共意识载体。第一,意象的“日常化”,所指意义的单一性和明了性。譬如,“井冈山”不再是拥有美丽自然风光的山峰,而成了承载革命理想和追忆伟人革命足迹的固定意象:“井冈山啊是摇篮,/催着幼芽快发展;/井冈山啊是全书,/刻下史诗千万卷;/井冈山啊是丰碑,/高瞻远瞩向明天”(徐刚《我爱井冈山》)。“啊,井冈山:红色的山!光荣的山!啊,井冈山:革命的山!英雄的山!”(杨德祥《井冈礼赞——喜读毛主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甚至是和井冈山相关联的八角楼、茨坪等,也都基本是指向此意。比如,太阳:“彩云缭绕的韶山上屋场,/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群星簇拥的北京纪念堂,/是红太阳安息的地方”(苏方学《太阳的殿堂》)。其他如春风、春雨、东风、雷电,几乎都有相对应的固定内涵,在不同诗人的不同诗篇中,意义并没有质的差别。第二,“从小见大”的升华式叙述结构,集体化的谋篇布局。虽然“古典+民歌”的“公式”没有将汉语新诗引领到光明的前途,但在内在结构上,却是影响甚大。比如,30年的汉语新诗运用最多的叙述结构则是传统汉语诗歌的“比兴”手法,从太阳、春雨、夜色等自然现象出发,进行比附,从而最终表达出崇高的革命理想或者伟人崇拜,或者政治豪情。比如,木棉树在西彤的笔下成了固守边疆的哨兵:“我心爱的木棉树,/和我一起守卫着海防”,“木棉树呀像我的战友,/斗争中肩并肩锻炼成长。/威武而坚定的英雄树呀,/高高地挺立在国境线上。/哎,我心爱的木棉树,/和我一起守卫着边疆”。乌篷船不再是周作人笔下娓娓道来的“有趣的东西”,它在诗人朱丹的笔下成为:“乌篷船/载着青春的欢乐航行”的青春叙事。再如,柯仲平的《革命长征征不断》:“踏过万水千山,/革命落脚延安;/革命长征征不断,/脚底板下出春天”。“敢叫日月换新天”,在这种进化论的未来叙述模式下,在五四诗歌中,总是凄凄私语、月落长恨天的“夜”开始焕发出光明的色彩,在革命者叙事的情境中,“夜”的意象走向了内涵的反面。唐祈在《水库夜景》中如此描写夜色:“夜半的水库工地,/恍如一片神奇的梦境。/宝石般璀璨的灯光,/像一阵黎明的雨/洒落在墨绿的河面上”。野曼的《夜猎》写晚上打猎归来:“归来一路吹叶笛,/绿色山村已入眠。/树梢挂一弯峨眉月,/公社啊/闪动着一双大眼睛!”章长石的《夜航机》写“夜空的流萤”,“夜空的流萤,/你提的灯笼,/怎的那么亮,那么红?/不,你瞧哪家窗口的灯光,/不比我的更亮更红。/燃烧的不是油,不是电,/而是守卫祖国的忠诚”。秋天也不再是“秋风秋雨愁煞人”,而是 “秋天来了,大雁叫了;/晴空里的太阳更红、更娇了!”(郭小川《秋歌之一》)“一江秋水一江绿,/两岸翡翠两岸霞,/碧天连麻麻连水,/百里麻乡一幅画”(孙伦《麻乡秋色》)。
诗歌能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公共事件,也要源于出版机制。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发表新诗的杂志和出版社,成为意识形态管控的官方机构,是“事业”单位。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践行者,每一个出版机构都有相应的刊载诗歌的要求,如1957年,《星星》创刊号上登载的稿约中对诗歌稿件:“我们只有一个原则的要求:诗歌,为了人民!”汉语新诗只有符合这个要求才能得以发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有诗歌编辑在执行相关方针政策的时候,所把握的尺度和个人喜好,这些都可以成为主宰诗歌命运的重要因素。比如,郭小川在写作《毛泽东颂》的时候,在初稿中,“郭小川下笔称毛是‘世界的太阳,主持《东方红》创作的周巍峙不同意,郭又改为‘人间的太阳。周巍峙仍觉不妥,再三争论之后,最后定稿为‘光辉的太阳”[5](p.231)。
现代传媒机制的诞生营构出独特的诗歌生产和阅读模式,给诗歌评论和文学史的编撰带来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这就是所要研究的对象一般是公开发表的为主。这就为期待进入批评家视野乃至“文学史”青睐的诗人陡增了另一层源自非诗歌的压力,再加上现代稿费制度的运作机制,又关涉诗人的生活和生存。这样,各种因素融合在一起,能否发表和出版就成为诗人创作的必然关卡,诗人就得想方设法按照这些期刊的要求来进行写作。相对于注重说明和理性的小说和戏剧,以感性和原初体验为肌质的诗歌在非诗歌的建议下不停地“修改”,就很难说是幸事了,发表后的诗篇显然就不只是诗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发自性情的文字了。出版文化对30年汉语新诗的介入和影响,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不能忽视的还有专业阅读的话语霸权的确立。诗歌历史上曾有很多相得益彰的诗人和评论家和谐共生的例子,但更多的则是诗人瞧不起评论家的例子。文体本身的特征决定了诗歌是职业评论类的专业阅读和文本原初体验存在分野的可能性最大的文学形式。作为互文和平等的互相成就的两个链条,和谐共存、互相阐释是诗人和评论家应有的生存理念。但在此30年中,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失衡,诗人在评论家面前表现 “噤若寒蝉”,姑且不说被强力推行的“三突出”和“三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是诗人写作必须遵循的宏观原则,在诗歌的形式和意象选用上,也处处体现出评论家的指导性阅读。30年的汉语新诗却通过诸如诗人的创作谈、访谈等夫子自道式的文本揭示方式,以及“权威评论家”的确定性解读,等等,来实现普通读者接受的被动性,读者参与诗歌创造的话语权基本是贫乏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等社会学的文本创作和接受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厘定了汉语新诗的内容指向。如果按照接受美学的“文本”生成模式来说的话,这显然是一个缺失读者的“决定性”参与的诗歌,或者说30年的汉语新诗还没有创作就已经完成了。
正是从出版到评论的文本生产和阐释机制的形成,使得这两者之外的最大多数的受众成为旁观者,阅读的诗篇限于正式出版物,对文本的理解倾向于评论家的解读和作者以评论家身份所谈的创作经验谈。
三、结语
30年的汉语新诗的演进痕迹,有很多现象还是值得反思的。在诗歌观念上,数量的繁华取代了质量的困窘,成为影响汉语新诗历史的重要观念。经过几十年的大浪淘沙,30年的汉语新诗文本能被后人记忆的屈指可数。但谁也不能否认,30年的汉语新诗在这30年的文学中的主流地位。新时期以来,人们总是埋怨汉语新诗的被边缘化,感叹诗人的生不逢时,繁华落于沉寂。之所以有这个落魄的感受,相对应的显然是30年的汉语新诗所拥有的“喧嚣”传统。大跃进民歌、小靳庄诗歌运动、红卫兵战歌、四五诗歌运动,贺敬之、郭小川、郭沫若、王老九等等,都是响彻一时的诗歌元素,这些喧噪一时的“诗歌现象”眩晕了汉语新诗的眼睛。在诗歌功能上,过分强化诗歌的宣传作用,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成为30年新诗存在的合法性。放弃了写作诸如死亡、爱情等人性永恒主题,而注目于暂时的政治书写,足以彪炳千古的诗篇也就难以诞生。当运用各种各样的会议讨论、政治指示等外部的理念,来试图解决属于汉语新诗的某些问题时,不但不会取得预想的效果,往往会走向反面。徒增诸多应景之作,局促于社会事件的反映,是30年来汉语新诗的一个标志。即便是后来被誉为来自民间的自发诗歌行为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20世纪80年代的诗学狂欢,其内在的精神根源,恐怕都和这个有关系。欧阳江河曾在20世纪80年代做出以下论述:“有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人人写诗和没有一个诗人是同样可悲的。在文学领域内,权威的丧失可能并非一件幸事,因为这样一来就难以形成必要的支援意识,使文学本身缺少内聚的、可以保持住的、强硬的核心部分,而只拥有散布的、花样翻新的、把黑暗或光芒平均分配的外在部分。想象一下这样的局面:无论是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珍贵的感情,人人都在写它、复制它,使之成为流行的大众文化,成为它自己的赝品。”[10](pp.63-64)实际上,朦胧诗的很快被跨越和被抛弃,与它在内在精神上承续1949—1979年的诗歌运作机制和价值理念有内在的关系。由于过于强调外部的非诗歌话语和诗学内部的先验性理论的指导和引领地位,因此,扭曲了汉语新诗应有的前进方向,这也是30年汉语新诗所结下的苦果。
[参 考 文 献]
[1][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天鹰.一九五八年中国民歌运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3][美]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M].孙佩妏,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
[4]李树尔.穆旦的“葬歌”埋葬了什么?[J].诗刊,1958,(8).
[5]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6]郭小川.诗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
[7]张志民.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66)·诗集·导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8][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李岳南.与初学者谈民歌和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10]欧阳江河.从三个视点看今日中国诗坛[J].诗刊,1988,(6).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