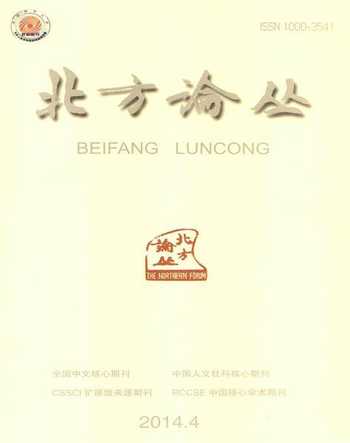明代情性思潮与两性文学演变
刘士义
[摘 要]明代文人对女性及两性关系的人文关注比以往朝代更加强烈。这萌芽于明初知识分子对情与理之探讨,并发展为明代中期的人性启蒙运动,由此延及明人对夫妇及两性关系的重新审视,从而生发出明代中后期的名妓崇拜与狭邪风尚。明代情性思潮直接促发了两性、女性及青楼文学的繁兴,反映了明人对传统伦理秩序的变革与妥协,亦折射出启蒙者对情与理的人文思索。
[关键词]明代;情性思潮;两性;女性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5-0029-06
[收稿日期]2014-07-04
由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伦理关系与人文思潮诸方面的原因,明代文人对女性与两性文化的关注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要强烈,从历代女性诗文的编纂,到繁夥的女性传记整理,再至发达的艳情小说与民歌散曲中的情欲描写,都反映了明代文人对女性及两性关系的深刻思考。人文启蒙者企图利用情教思想来改造传统的两性关系,却遭到社会保守势力的强力阻扼。然而,新兴商贾势力的奢靡纵欲与恣情狭邪之生活方式逐渐浸渗到明代文人群体,从而为人文启蒙者解决情与理之矛盾提供了新的解决方式,并由此引发了明代中后期的名妓崇拜与狭邪狂热之现象,反映了启蒙者对情与理的人文思索,亦折射出明人对传统伦理秩序的变革与妥协。
一、明代两性关系的情性哲学演变
笼统而论,中国传统社会之思想、文化呈现出两元对立与统一的状态。作为社会精英的文人哲学,往往偏向于形而上的哲学寻绎,而忽略哲学的现实实践意义。与之相对,世俗社会及其生活方式则表现出一种更加务实与通融的实践价值。然而,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形而上的文人哲学与世俗社会的生存经验保持着一种静与动、流与源、精与广等复杂关系,并且这种关系随着世俗社会和城市文化的发展而表现得愈为强烈。
明代中后期,由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城市生活的繁盛,在城市市民与富商巨贾中,逐渐形成一种开放、自由、纵情、适性的社会风气,并且逐渐浸袭至文人群体与精英士族集团。文人阶层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生活途径来践行人性启蒙运动的哲学实绩,而社会新兴集团亦需要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维系来做现实生活的文化支持。于是,在对抗对人性严重压抑的宋明理学问题上,明代士族文人与领风气之先的市民阶层形成了统一识见。在此基础上,明人开始了人文觉醒的“情”“性”复兴运动。文人士夫有意打破传统的理学束缚,进行思想、文化、伦理诸领域的人文解放运动。在继承以往儒学先哲对“情”“性”等哲学命题探讨的基础上,明代启蒙者的关注视野逐渐从对自我人格的修持敬养,转向了对世俗伦理、男女情爱的文化鼓吹,并由此导致明代启蒙运动由形而上之“情”“性”哲学转向形而下之人伦事理与世俗情爱,从而弱化了明人变革两性关系的阻力,亦促进了情性思潮的蔓延与普及。
明代情性启蒙运动的实质是将形而上之“情”、“性”与“理”及“欲”之概念从哲学层面走向世俗社会,并与明代中后期所兴起的市民思想相融合,进而形诸人性解放思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场启蒙运动亦是明代启蒙知识分子从世俗社会寻找情性变革依据的有效实践。因此,当明代启蒙者的情性哲学走向僵化状态时,那么必然会向世俗社会寻求通融与变通的革新手段。明初文人的情性之论多沿袭宋元理学论调,专注于形而上的哲学探究,强调自我品格的修持与格物致知的理论实践。明初大儒,如宋濂、方孝孺、吴与弼、胡居仁辈,皆从形而上之层面来观照“情”、“性”与“理”之关系,总言之不外乎“性善情恶”、“灭情复性”、“心统性情,性体情用”诸论调,并未与世俗生活相结合而形诸风行的情性启蒙运动。
明人情性启蒙运动发轫于明代中期兴起的文坛革新运动与哲学领域的阳明心学启蒙思潮。明初,理学家陈献章曾高举异帜,鼓吹心性与情性,并由此开启了明代理学由“理”向心学转变的滥觞。以此为端,陈氏亦将心学引入诗文评注之中,“诗之发,率情为之,是亦不可苟也,不可伪也。”[1](p.10)“故七情之发,发而为诗,虽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1](p.11)此后,李梦阳承续发力,将哲学之“情性”思想正式引入诗文领域,“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真诗乃在民间。”[2](p.102)李梦阳的“真诗乃在民间”反映了明代情性启蒙者向世俗生活汲取诗文革新依据的有益尝试,亦初步表现了明人情性哲学世俗化的渐变过程。
与此同时,启蒙者在哲学领域亦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理学革命。王守仁承继白沙心学,以心为体,奠定了“情性合理”的哲学基础,从而为阳明后学进行情性世俗化实践扫平了障碍。阳明心学从启始即保持了鲜明的革新性,从王守仁的“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到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再至泰州后学杨复的“要晓得情也是性”,乃至明后期阳明心学讲学思潮之繁盛,都反映了明代情性哲学向世俗生活浸渗的趋势。
文学与哲学领域的情性世俗化过程,在明中叶以后逐渐有交合的趋势。明代后期,启蒙知识分子多兼摄理学与文学笼统论之。李贽是明代中后期启蒙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一生与王畿、王艮、耿氏兄弟(耿定向、耿定理)、焦竑诸理学家有着密切的交往。这些交往对李贽后期“离经叛道”思想之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仕宦二十余载后,李贽辞去官职,寄居麻城,聚徒讲学,听任男女妇孺求学问道。此时,李贽思想已趋于成熟,著《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诸书以宣扬其说。在与程朱理学家的论辩中,李贽提出了“童心”说, 强调知识分子在创作中要“绝假还真”,独抒己见;在生活中,肯定自我欲望的合理性,“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3](p.361)在政治中,提倡人人平等,“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主。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3](pp.16-17)童心说的实质,在于打破程朱理学关于人之“情”“性”的神圣性,促进哲学与文学之“性”“情”向世俗生活的转变。
李贽是明中叶情性启蒙运动的中军人物:上承阳明心学之革新传统,下启明后期重情文学之盛行,集理学、文学、史学之大成,推动了明代情性启蒙运动的实绩。重情尚性,崇实致用,融事理于世俗人欲之中,可谓李贽对情性思潮一大功绩。于此以后,明代文人多继承李贽的方式,继续把形而上之情性哲学推向世俗领域。明后期情性启蒙运动蔚然成风,中间所出现之人物,如公安三袁(宗道、宏道、中道)辈高举性灵说,均深受其影响。即如王之祚在《花镜隽声跋》中所论:
《花镜》行世必有呼之为情句者,噫!实性书。臣忠、子孝、夫义、妇节,生于性,实天下大有情人。臣不情不忠,子不情不孝,夫不情不义,妇不情不节,人情合天性,人情即天性。情于君臣者,载情于夫妇,情于父子者兼载之,正言反言规言寓言总括于无邪……故与天下谈性,莫先与天下谭情。[4]
王之祚所论之“性”多有形而上之哲学意味,而所论之“情”则更倾向于世俗社会的人伦事理。王氏这段论述在于打通形而上的哲学之“性”与形而下之世俗之“情”的逻辑关系。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各尽其职,与世俗之情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有世俗之情,所以,才会有社会的整体和谐。如此一来,王氏便把形而上之哲学性理转化为形而下之人情世故,即“人情合天性,人情即天性”。王之祚所言之“人情即天性”,实际上反映了人文启蒙者将哲学之天理(天性)物化为世俗社会之情爱的哲学尝试。王之祚之情性哲学的世俗化倾向,可以充分地代表明代中后期明代文人的情性世俗化路程。
然而,即使如此,王之祚所论之情性仍然未能完全褪尽理学气息,而真正的情性复兴大旗的则有待于冯梦龙等辈的高举。冯梦龙出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此时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辈,皆以重情尚性之学说声名于世,且冯氏成长之苏州,亦是经济繁荣、人杰地灵、情性思潮至为发达地区。这些条件都为冯氏提出情教思想并践以实行奠定了基础。冯梦龙继承了前代启蒙者的情性世俗化理论,提出了情教思想并将其理论化、形诸系统,并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实践。在冯梦龙的情教体系中,情是万物之本原,几乎褪尽了理学对“性”、“心”及“理”的抽象概念,这一点较之阳明后学更加具有世俗性的实践意义,即如其在《情史》中所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相环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5](p.3)
如果说,阳明后学是通过立教、授业、讲学等方式、自上而下地进行心学之传播的话,那么冯梦龙则是以世俗社会的生存经验为基础,进行情教理论的完善与总结。由此而论,冯梦龙实质充当了世俗社会之生存方式的代言人。世俗社会的生存经验,往往比文人的哲学命题更加直接与实际,正因如此,冯氏才绕过了文人式的辩难、授业、讲学等方式,而利用了更加直接、有力的世俗文学来进行情性启蒙运动。
二、情性思潮下的两性实践
明代情教思潮的发生、发展与变革,是明代诸多社会因素合力的结果。其中交织着商业势力的推波助澜、奢靡享乐社会风气的浸淫,与理学士夫的哲学变革及文人骚客的文学革新诸多因素。对人性与物欲的肯定,是明代人性启蒙运动的主要目的,但是,如何将这种理论加以实践执行,则是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如果说阳明后学所进行的讲学活动,是自上而下的哲学启蒙的话,那么文人书商所开展的通俗文学之整理与出版等活动,则是自下而上的宣扬与鼓吹。满足城市生活的需求、反映市民的理想与价值,则成了启蒙者的实践基础。与空论性理的哲学讲学风潮不同,启蒙实践的知识分子必须与世俗生活相结合,才能最大程度地获得市民阶层的认可。空谈心性命理必然陷入形而上的哲学说教,往往不如对切近本性的两性关系更为真实与贴近现实生活。
先哲圣贤对人性的研究,总不外乎心、性、命、理诸学说,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阳明心学,都特别关注人与社会的外在关系,强调个体人的社会实践意义,必然导致对个体人之情感的忽略。那么,当个体人满足于自我价值的社会肯定时,必然会转向自我适娱方向的解脱。这就表现为对物欲、享乐及自我情感的释放。那么,明代情性思潮所宣扬的人性启蒙之理想,就很容易地蜕变为对男女情爱关系的鼓吹。因为在所有的世俗情爱关系中,男女情爱关系最为基础,亦最为引人瞩目,正如方鼻甫在《青楼韵语》中所言:“人情莫甚于男女。”[6]冯梦龙编纂《情史》而“事专男女”,独以男女情事为长,都充分反映了这种情教蜕变之事实。
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有《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求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俾勿作于凉,于是疏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
冯梦龙把情教渊源追溯至儒家的六经,从而把情教的地位提高至与宋明理学并肩的文化高度,进而在法理上树立了“情教”的法统地位。不仅如此,冯梦龙亦打破了前哲的“泛情”思维——把现实的男女爱欲之情笼统地目为世俗伦理之“情”,而建立起以男女之情为世间情爱基础的情教体系。在冯氏看来,情之最根本者在于男女之情,因此,圣人作六经,以阐发两性关系之微妙。由万物之“泛情”而类化为人类之“性情”,再由人之“性情”进而论证“两性相悦”的合理建构,冯梦龙建立了一种切而可行的论证方法,同时亦确立了明代情教普世思潮的基本理论。从阳明心学的讲学启蒙到情教体系之建立,明代情性启蒙运动表现出一条明确的发展路线:心性(哲学途径)——泛情(理论构建)——两性(具体方式)。
然而,中国古代社会的两性关系表现出了极大的复杂性,它包括家庭体系中与家庭体系之外的两性关系。家庭体系中的两性关系包括丈夫与妻子、妾室、侍婢、家妓等关系,而家庭之外的关系则包括通过狭邪、偷情、通奸等方式而保持的两性维系。事实上,在古代社会中,男权文化作为社会文化而存在,女性文化依附于男权文化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两性关系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对女性文化的塑造上。程朱理学鼓吹的女性文化主要体现为官方意识形态下的女学宣教体系,它包括传统的女学宣教书籍与史著、方志、族谱等文献中的列女传记等。总体上讲,明代女学体系在继承前代女学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了女性对男权社会的依附性。
夫妻关系是维系家庭伦理关系的基础,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然而,对于如何建构夫妻双方之地位,传统女教文化与启蒙知识分子则有着较大的区别。传统女教文化对于夫妻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基于阴阳体系之上的“两极阐释”,男女角色被定义为:夫性秉阳刚之气,主积极进取、自强制外的强势文化;女性持阴柔之性,承恭顺卑弱、主静内守淑的内敛之德。班昭在《女诫》七篇中,以“卑弱第一”为首篇。在《女诫·敬顺第三》则明确地表述到:“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7]基于这种理念,传统社会似乎形成了家庭关系中的女性分工:嫡妻的作用在于持家与传衍子嗣;妾室则是家庭夫妻关系的补充;侍婢与家妓的职责则在于对男性物质与精神方面的服侍。对于这种女性角色的界定与演变,我们可以从文人笔下的历代女性形象塑造中来寻绎。高方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女性形象审美嬗变》(《北方论丛》2013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道:“叙事文学中的女性审美主潮从偏重日常实用和道德教化的‘德言容功逐渐过渡到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对生活品味和艺术气质的追求”。然而情性启蒙者于此则有不同的论断。启蒙者试图以情教为基础建立起两情相悦、自由平等的夫妻情爱标准。明代中后期思想启蒙者,如李贽、汤显祖、冯梦龙等人对此均有相当多的阐述。
尽管明代情教启蒙者采取了谨慎而渐缓的态度,夫妻及两性关系的重塑运动仍然遭到社会顽固保守势力的强力阻扼。在启蒙思想传播方面,李贽最终因异端思想而死于囹圄,何心隐因妖言倡道而被诛杀,冯梦龙亦因传播世俗情爱思想被官员训诫。而在婚姻自主、情爱自由等实践方面,情性启蒙者更是遭受保守势力的强力排抵。钱谦益娶名妓柳如是被世人报以砖块瓦砾,龚鼎孳与顾媚结合亦被杭人目为妖人,吴三桂与陈圆圆的情爱纠葛更成为世人唾骂的口舌。这种强大而顽固的社会阻力之形成,与古代等级制度、伦理体系及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在儒学精英所制定的伦理体系中,传统社会形成了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两性关系维系与君臣民庶、尊贵低贱的等级制度。因为历代政府对这种伦理制度的强力执施,传统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群体文化的价值分野与等级壁垒。男权文化与女性文化、士族文化与民庶文化,它们分别代表了儒家所构建的男、女、良、贱之方面。那么,当明代情性启蒙者宣扬女性之才学、艺术等人性质素,以及平等、情爱、独立之两性关系时,就必然与明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冲突。因此,某种程度上讲,人性启蒙者所引领的女性文化重塑运动是在与整个传统伦理体系进行持久的对抗。这也注定了情性启蒙者在改革传统两性关系时遭受社会与制度强力扼杀的历史必然。
因此,在启蒙运动遭受强烈的社会阻扼时,启蒙者不得不选择一种灵活的变通方式——狭邪——来解决两性关系变革所带来的社会排抵。在启蒙者看来,狭邪文化与乐户制度是儒家伦理体系与政权执行的一个体制性的伦理漏洞。在儒学精英所设定的两性伦理秩序中,并没有对家庭之外的两性关系进行制度上的规划,而此亦为启蒙者对狭邪与乐户文化进行两性文化实践提供了理论上的契机。不仅如此,以富商巨贾为代表的社会新兴势力之出现与其纵情狭邪之生活方式的推波助澜,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的伦理体系,亦助长了启蒙者的两性变革信心。以新安商人为代表的富商巨贾,他们奢靡纵欲、恣情享乐、冶游青楼的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江南与京师一带的社会风气。明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商贾的地位远低于官宦士子,他们受传统伦理制度的制约远较文人士夫松弛。在生活上,他们纵情狭邪,与青楼女子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关系;在价值与文化上,他们更崇尚近实尚利的享乐主义;在婚姻与两性关系上,他们更倾向于一种自由而较少伦理约束的两性关系。至明代中后期,因户籍界限而造成的文化壁垒逐渐趋于消融,士民商贾等户属的交往更趋于一种自然状态。商贾势力与文人集团的密切交往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群体的生活方式,从而将新兴的享乐、情爱、恣情等生活方式浸渍到文人群体。
对苦于探索新型两性关系却找不到合理伦理阐释的知识分子来讲,青楼无疑是一个最佳的爱情实践场所。对于明代文人的理想伴侣,明人徐石麒在《凤凰台上忆吹箫·意中美人》一词中,有着明确地展现:
一点常凝,频年不遇,依稀有个卿卿。要兼花比色,选玉评声。那更温柔心性,挑剔尽、词赋丹青。堪怜是,高怀独绝,于我多情。
盈盈。时来醉眼,自不屑凡媛,舞榭歌亭。有风流万种,拟向他倾。待阙鸳鸯社里,消受我、雾帐云屏。何时幸,销魂真个,笑眼双青。[8](p.1804)
在明代文人的美人角色设定中,这位美人要色艺兼绝、温柔款洽,更要文采风流,当然用情忠贞亦是必备条件。然而,这种女性形象在传统的闺帏世界里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那种温柔多情、才艺兼绝的美人与自由浪漫、款款通情的男女情爱关系,仍然是传统家庭关系的禁区。但是,这种文人式的理想美人与明代青楼名妓的形象颇为契合。不仅如此,狭邪女子亦投其所好,刻意将自我与生存环境文人化、脱俗化。明人卫咏在《悦容篇》中,通篇讨论了闺阁女子的生活营造,通过对美人的情性、居室环境、室内陈设、才艺诗画,以及美人的仪态姿容、修饰装扮,阐述了明人对女性美的理解和认识。书中所论之设计恰恰可以印证明代青楼文化之营建。另一方面,青楼女妓与士人亦保持了一种相对平等而自由的关系,从而为士妓交往营造了一种浪漫情愫。对文人士子来说,青楼世界是一块脱离传统伦理制约的自由之地。被传统女学所禁止的歌舞声乐、妩媚多情等女性因质,在青楼世界中得到了尽情的展现。
明代情性思潮是启蒙知识分子尝试改变两性文化的一种实践与努力。然而,由于传统保守势力的强力阻扼,启蒙知识分子不得不把改革的视角从两性关系转移到对女性文化的塑造上。即使如此,启蒙者仍然无法突破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伦理制约,而再一次把改革的锋芒从夫妻关系转移到对狭邪文化的营建中来。与之相随,在情性思潮的不断发展与突破中,启蒙者利用文学所进行的种种尝试与实践,亦促进了明代两性及女性文学的发生与发展。
三、明代两性及女性文学之演变
明代情兴思潮直接促发了明代启蒙文学的发展,而启蒙文学的实绩则在于对人性及情感的重新审视。在对抗“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束缚中,对人性及情感的再审视很容易褪变为对两性及女性文化的重新诠释。这种文化再诠释反映在文学作品中集中地表现为以两性关系与女性文化为主题的文学革新思潮。由此而来,随着明代情兴启蒙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富有人文启蒙性质的文学革新思潮,便呈现出其独特的发展脉络。
明代中期,当启蒙知识分子将启蒙文化的旗帜转向世俗生活时,那么由此亦开启了明代情性文学风潮的滥觞。明代启蒙文学最早发源于诗歌领域,李梦阳的“真诗乃在民间”理论,实质是知识分子向民间寻找文学变革依据的有效尝试,表明了精英士人对世俗情爱关系的认同与接受。李梦阳将真诗与明代民歌相联系,正是发现了民歌所禀赋的真情精神与包含的世俗情欲内容。在李梦阳看来,这些恰恰是根治浮泛文学的一剂良药。民歌是底层社会的心声,多以赤裸裸的男女情爱为主题,反映了世俗社会的情爱状态与心理诉求。李开先在《市井艳词序》中所论:
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锁南枝》……二词哗于市井,虽儿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艳亵狎,不堪入耳,其声则然矣。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虽君臣友朋,亦多有托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风出谣口,真诗直在民间。[9](p.142)
尽管民歌“俱以男女相与之情”为主题,且语言“淫艳亵狎”,但因其“直出肺肝”、“情尤足感人”的特质,所以,仍然得到众多诗文变革者的认同与支持。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两点:其一,民歌的直率纯真、真情流露,为其诗文变革运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源泉;其二,民歌中所阐发的底层社会之男女情爱关系,为情性启蒙者提供了最直接而有力的实践依据。从李梦阳、李开先诸辈的文学启蒙,到沈德符、袁宏道、王骥德等人的文学鼓吹,再至冯梦龙诸辈的编辑与创作,基本上体现了明代士人借民歌而改革两性关系的有力实践。这一点,冯梦龙在其民歌集《山歌》中有着明确的认识:“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10](p.317),因为山歌之绝假纯真,才会有“淫艳亵狎”之“私情谱”,正是这种歌颂男女情爱之“私情谱”,才会有“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情性启蒙实践。
明代中后期,情性思潮在戏曲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徐渭较早地将哲学情爱思想拓展到戏曲领域,“人生堕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战,拈叶止啼,情眆此也”[11](p.1269)。在徐渭看来,人生为情爱所驱使,而戏曲之本质则在于“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弥远”[11](p.1269)。因此,戏曲应该摹写人类的真情实感,这也恰恰论证了情性存在的合理性。徐渭对戏曲之情爱思想的推崇,在汤显祖的戏剧理论与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完善。在《牡丹亭》的故事架构中,汤显祖的主情理论正是以两性情爱为基础,而生发出“世总是情”的泛情论与“一往而深”的至情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9](p.142)。很明显,汤显祖将泛情论作为至情论的存在基础,然而,至情论却明显地表现出其历史局限性。以《牡丹亭》为例,至情论的实践主体有意地忽略两性关系中的男性质素,而过多地焦聚于以杜丽娘为代表的女性群体上。这种“阴盛阳衰”的故事构建,恰恰折射出启蒙知识分子改造两性关系的历史局限。在明人所编纂的以两性关系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成为情爱故事的主体,决定两性关系的发展。以冯梦龙《情史》为例,此书虽冠以《情史》之名,以宣扬两性情教为宗旨,但实际上其内容仍不脱女性色彩,且在全书诸多类目之中,以女性冠名的篇目达2/3以上。
作为早期的戏曲启蒙者,汤显祖的两性情爱思想深刻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的戏曲创作与理论批评。明代后期活跃于剧坛的作家与理论家,多受其情性思想的影响。戏曲批评者如何良俊、王骥德、袁宏道、潘之恒辈,均有对两性情爱关系的集中论述。情性理论在戏曲领域的流播与发展,亦促生了大量的以男女情爱为题材的剧作,以孟称舜、吴炳和阮大铖为代表的风情剧作家,均有大量的以男女情爱为主题的戏曲实践。与《牡丹亭》等剧作中女方积极主动相比,此时故事已逐渐转变为男女双方共同争取爱情的情节。这些都反映了情性启蒙者从单纯的女性关注转为两性关系之思考的变革过程。
事实上,当明代启蒙者大张旗鼓地在民歌、戏曲领域发起情性启蒙思潮时,保守势力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情性思潮进行苛责与抵制。在儒家精英分子看来,男性是维系社会与政权稳定的主导力量。他们认为,过分地强调男女情爱关系必然导致男性主体地位的丧失,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失衡。明代政府多次颁发戏曲与小说禁令,就足以证明保守势力的强大。正是在这种文化高压下,另一些启蒙分子避开了情性变革中的男性阻力,集中于女性文化的重塑运动,而女性文化重塑运动的实绩则集中体现在女性文学领域。因此,可以说,在女性文学领域所兴起的文学整理运动,是明人改革两性关系的另一种突破与实践,其实质在于维系两性关系中不可动摇的男性地位。
明代启蒙者对女性文学的整理风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对女性诗歌、词作、文赋等文学作品的整理与编纂;其二,对女性传记类作品的搜辑与汇编。与大规模女性诗文整理运动同时,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大量的女性传记类作品总集。较著名者如《绿窗女史》《艳异编》《广艳异编》《青泥莲花记》《情史》,均收录大量的女性事迹。实际上,两者都可视为明代文人“女史”思维的一种文化展现这种“女史”思维在明人所编纂的书籍中,每每见诸卷端,诸如田艺蘅以《诗女史》命名其编纂的女性诗集,而《亘史钞》《绿窗女史》《情史》诸女性史料汇编直以“史”概括全书主旨。不仅如此,女性文学编纂者亦以“女史”自居,如梅鼎祚在《青泥莲花记》各卷之末均有“女史氏”之评语;冯梦龙在《情史》中自署“詹詹外史”,并且在所叙故事之后多附有“女史”之按语。。史学思维的建构在于通过对某一特定文化的记忆与传承,还原历史风貌,以古证今,从而建立起一套现时可执行的理论范式。因此而论,明代启蒙文人因整理女性文化而表现出的女性史观,正体现了明人重建女性文化的实践与努力。而明人对女性文学的大规模整理活动,实质上反映了启蒙者对女性之“才艺与妇德”、“身份与才华”、“情感与婚姻”等问题的深刻思索。
明人对女性之才艺、妇德与身份等因素的思索,可以从女性诗文集的编纂过程中窥略一斑。嘉靖年间,张之象编纂《彤管新编》,其书在广泛搜辑女性诗作的基础上,明确表示以妇德为范式,“庶垂百代之规式,附风劝之本”[12]。这些都表现出明代文人对女性才艺观的重新审视。然而,编辑者仍然保留了强烈的道德说教意味,郦琥在其所编《姑苏新刻彤管遗篇》中曾论道:
余博阅群书,得女之工于文翰者,几四百人,编次成帙,名曰《彤管遗编》,盖取诗人“彤管有炜,悦怿女美”意也……学行并茂,置诸首选;文优于行,取次列后;学富行秽,续为一集;别以孽妾文妓终焉,先德行而后文艺也。[13](p.879)
郦琥以“学行并茂”、“文优于行”、“学富行秽”为编排顺序,其目的在于强调女性才艺的同时,亦明显地流露出强烈的说教意味。不仅如此,作者有意将“孽妾文妓”别为一篇,更表现出强烈的等级身份意识。在以郦琥为代表的文人看来,对女性才艺的赞诵应当建立在身份与德行之上,才艺不能成为超越等级与德行的女性标准。然而,随着女性文化的持续推进,这种思想很快被先锋知识分子所打破。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田艺蘅编选《诗女史》,以时间为序,选辑上古至明代女性诗人三百余位,打破了以往以宫阁闺淑、命妇贞女、婢女娼妇为分类的编次体例,表现出作者强烈的妇女平等意识,如其在《诗女史叙》中所言“乾坤异成,男女适敌。虽内外各正,职有攸司,而言德交修,才无偏废”。[14]万历四十六年(1567年),赵时用刊刻《夜珠轩刻历代女骚》,更是有意忽略妇德在编纂体例中的主导地位,以才艺为衡,分次编排女性诗人,体现出强烈的革新思想,“稽其贞淫互记,仙俗杂陈,夷夏兼录,良贱并存,品格行谊,不尽足挂齿牙。”[13](p.885)
嘉靖年间出现的文学启蒙思想,经过数十年的酝酿,在万历中后期已发展为两性文学启蒙的自觉。在此背景下,明代文人的女性诗文整理运动逐渐形诸高潮。然而,由于传统保守势力对启蒙思想的抵制与扼杀,亦使女性文学的发展面临着强大的社会阻力。尽管如此,新兴商人阶层的奢靡、纵欲、适性之生活方式,深刻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俗。一方面是传统势力对女性文化的强力阻扼;另一方面是奢靡纵欲之社会风俗的推波助澜,因而造成启蒙文学主体由传统女性群体逐渐局限于狭邪女性,并由此而滋生了大量以狭邪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在狭邪诗歌整理方面,明代社会出现了繁多的名妓诗歌选本。万历年间,杨慎整理《丽情集》,多有狭邪女子诗篇辑录在内。稍后,冒愈昌编选《秦淮四姬诗》,辑选秦淮名妓马守贞《马姬诗》、赵燕如《青楼集》、朱泰玉《绣佛斋集》、郑妥《寒玉斋集》各一卷。与之前后,相继有梅鼎祚《青泥莲花记》、朱元亮、张梦徵合编之《青楼韵语》,均以青楼诗词编选为目的,专门辑录历代名妓小传及诗词。此外,还包括诸多女性诗集选本中的女妓作品,如《众香词·数集》中的大量女妓词人;《历朝诗集·香奁集下》中的诸多女妓诗人等。与狭邪诗词之整理活动相对,明人对青楼女子的关注亦体现在对青楼女子传记的整理上。从署名王世贞的《艳异编》《续艳异编》、吴大震《广艳异编》,到潘之恒《亘史钞》、秦淮寓客《绿窗女史》,再至冯梦龙的《情史》,都以汇编的方式记录了大量的女妓传记。不仅如此,晚明社会还出现了大量的狭邪指南类书籍,诸如日用类书中所载之《风月门》与青楼品评类书籍《吴姬百媚》、《金陵百媚》等,亦折射出部分士人在改革两性关系遇挫后的颓废与放浪。然而无论是女妓诗歌整理,还是女妓传记辑录,都体现了明代启蒙知识分子面对强大社会阻力时所表现出来的革新勇气。
小结
明代是一个人性觉醒的时代。明代中后期所兴起的阳明心学与文学启蒙思潮,实质上反映了世俗生活向哲学与文学领域的强势渗透,并导致人文启蒙运动逐渐发展为情性复兴运动。明代情性复兴运动交织着启蒙者对两性关系、女性文化与狭邪文化的多重审视。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与纲领,这场运动自始至终表现出一种非系统、百花齐放的状态。正因如此,才会生发出明代“两性—女性—狭邪”文学创作的自由、自觉之人文启蒙精神。
[参 考 文 献]
[1]陈献章.陈献章集[M].孙通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2]李梦阳.诗集自序[A].蔡景康.明代文论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3]张建业.李贽文集:第七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王之祚.花镜隽声[M].明天启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5]冯梦龙.情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6]方悟.青楼韵语广集[M].张几绘图,明崇祯四年刊本,台北图书馆藏.
[7]王相.闺阁女四书集注[M].光绪庚子年刊.江荟宝文堂藏本.
[8]徐石麟.美人词[M].全明词[Z].北京:中华书局,2004.
[9]蔡景康.明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0]刘瑞明.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1]徐渭.徐渭集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张之象.彤管新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十三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13]胡文楷编著.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4]田艺蘅.诗女史[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2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作者系山西师范大学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