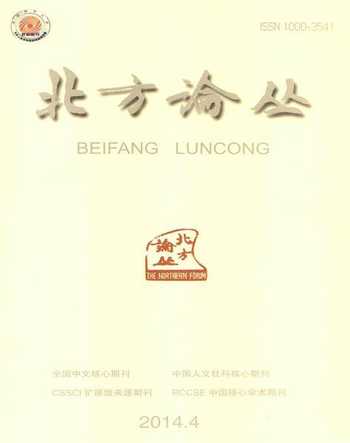两宋之际诗、道冲突与平衡
王建生
[摘 要]两宋之际的一些诗人,既潜心于诗艺,又精研理学或禅学的心性之“道”。而要专意学“道”,则需摒除世虑及文字牵绊;对于诗人来讲,这意味着要放弃对诗艺的求索。他们陷入了诗、道冲突的困惑中。吕本中的实例,生动地呈现了诗、道冲突与平衡的全过程。吕本中最初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而后兼修禅学之“道”,并精研理学。梳理这一生动的历史细节,可以深化我们对宋代诗歌史的认识。
[关键词]吕本中;禅学;理学;诗学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4-0024-05
Conflict and Balance Between Poem and Dao During Song Dynasties
——Focus on Lv Benzhong
WANG Jian-sh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ng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Some poets during Song Dynasties studied poetry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Meanwhile,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Dao. They must give up common customs and temperament of the characters, once they intended to study Dao. Therefore they fell into confusion. How to balance poem and Dao was an important project. The example of Lv Benzhong displayed process the whole vividly. The analysis of this lively details can deepen our comprehension of the history of poetry.
Key words:Lv Benzhong; Zen; New Confucianism; Poetics
[收稿日期]2014-06-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南宋前期中原文献南传研究”(11YJCZH166);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南宋文人的中原记忆与文学写作”(2012CWX028);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2012T50634)。
两宋之际的一些诗人,既潜心于诗艺,又精研禅学或理学的心性之“道”。而对心性之“道”的体悟,需摈除世虑,直指本心,尤其要疏脱文字牵绊;对于诗人来讲,放弃对诗艺的探索,几乎不大可能。因此,他们陷入了诗、道冲突的困惑中,如何平衡诗、道关系,成为他们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吕本中最初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而后兼修禅学之“道”,并精研理学。他的实例,生动地呈现了诗、道冲突与平衡的全过程,为后世留下了动态的诗歌史与思想史的互动印迹。
一
政和三年(1113年)前后,30岁左右的吕本中的诗歌才华,已博得时人的赞誉。黄庭坚的外甥徐俯以为他“尽出江西诸人之右”;谢逸也极相推重,“以为当今之世,主海内文盟者,惟吾弟一人而已”[1]。徐俯、谢逸的称誉,虽属于江西诗派文人圈内的品评,却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吕本中作为出色的诗人,得到同时文人的认可。那么,在北宋后期,吕本中有哪些突出的文学实绩?
吕本中在政和三年(1113年)就对宋代文学成绩作了总结,并提出今后学习的范式,在写给外弟赵承国的书信中,对“为文”、“为诗”都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学诗须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越过人。”[2](p.12)仅就以诗歌而言,吕本中较早地树立了苏、黄互补的诗学范式。事实上,早在大观三年(1109年),吕本中对于诗学理论尤其是活法论,已经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在《外弟赵才仲数以书来论诗,因作此答之》说:“胸中尘埃去,渐喜诗语活。孰知一杯水,已见千里豁。初如弹丸转,忽若秋兔脱。旁观不知妙,可爱不可夺。” [3](卷三)本年,吕本中26岁,还作有《喜章仲孚朝奉见过十韵》[4]( p.338),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语道我恨晚,说诗我不迂。丁宁入汉魏,委曲上唐虞。历历有全体,匆匆或半途。”[3](卷三)从上引诗歌可以看出,吕本中在大观三年(1109年),即26岁时,已经形成了“活法”与宗黄(庭坚)的基本观念。同时还可以看出,到大观三年(1109年)时,吕本中对自己在“诗”和“道”能力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基本判断:对诗歌创作与诗法都很在行,但对“道”则不那么自信,所以说“恨晚”。吕本中诗歌中所传达的“语道恨晚”的讯息,说明“道”对其精神世界的刺激之强烈,也可以理解为他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需要加强“道”的修养。
据《紫微诗话》记载:“江西诸人诗如谢无逸富赡,饶徳操萧散,皆不减潘邠老大临精苦也。然徳操为僧后诗更高妙,殆不可及,尝作诗劝予专意学道。”[5]饶节字德操,崇宁二年(1103年)出家,从饶节写给吕本中的诗来看,“专意学道”的内容必定是禅学。吕本中诗歌中的另一记述,可以与《紫微诗话》的这段记载相互印证,《又寄无逸信民》有“虽非问道赌狂曲,犹胜遗书访子公”之句,诗下自注:“璧公数讥二子学道不进。”[3](卷一)饶节出家后法号如璧,此处故名“璧公”;二子,指谢逸、汪革。由此可见,在吕本中的交游圈内,饶节是督促众人“学道”的重要力量。另外一位朋友关沼也曾劝勉他“学道”,吕本中后作诗追述,诗题曰“往年与关止叔相别甬上,止叔见勉学道甚勤,且曰无为专事文字间也。及今五年矣。尚未有所就,因作诗见志且以自警也”[3](卷五)。关沼字止叔,元祐三年( 年)进士;从吕本中《师友杂志》及相关诗歌的记述,可以看出关沼乃有气节、重学行之人,与吕本中的交谊当在师友之列。在饶节、关沼等人的督促下,吕本中的学“道”效果如何呢?
政和五年(1115年)至七年(1117年),吕本中任济阴主簿期间,专门作了《学道》诗[4]( p.356),来述说自己的学道体悟,全诗如下:
学道如养气,气实病自除。验之寒暑中,可见实与虚。颓然觉志满,乃是气有余。岂惟暖脐腹,便足荣肌肤。但能严关键,百岁终不枯。道苟明于心,如马得坚车。养以岁月久,自然登坦途。江河失风浪,草莽成膏腴。熟视八荒中,何物能胜予。时来与消息,吾自有卷舒。死生亦大矣,汝急吾自徐。捷行不为速,曲行不为迂。一沤寓大海,此物定有无。谁能具此眼,况望捋其须。学有不精尽,遂至玉碔砆。昔人中道立,为汝指一隅。千言不知要,徒自费吹嘘。所以季路勇,不如颜氏愚。请子罢百虑,一念回须臾。忽然遇事入,此语当不诬。[3](卷七)
全诗着力阐述“道明于心”的意义:心安而理得。首句“学道如养气”,是拿道家气功之术,与禅学修习作对比,认为二者具有共通性,这是吕本中思想的特色,往往用已有的知识储备来消化新思想。“玉碔砆”比喻以假乱真、似是而非。禅学修养工夫达到一定程度时(即“养以岁月久”),遇事优游不迫,利害、得失、死生、贵贱等,皆等闲视之。禅学对吕本中的意义,在于本心修养方面,即通过禅学的修习,保持心性的平和。
不过,即便在政和年间,吕本中也不曾忘怀其诗人本色,也可以视为吕本中以诗人名世的本证。他曾《寄外弟赵楠才仲》自述道:“古县疏还往,微官绝簸扬。事业烦诗卷,生涯在药囊。颇闻能吏事,仍不废文章。”[3](卷四)《汴上作》云:“平生事业新诗在,送与江南旧钓矶。”[3](卷七)将诗歌作为平生之事业,可见他对诗歌倾入了大量的精力与情感。“学道”就要摈除世虑,直指本心,对吕本中来说,别的可以舍弃,却不能丢弃诗歌。
既想学“道”养心,又不愿放弃诗歌写作,吕本中陷入了难以适从的境地。政和年间的诗歌记录了他这种心境,《试院中作二首》其一:“客梦断复续,角声寒更长。疏篱拥残月,老木犯新霜。斗絷身何恨,驰驱汝自忙。稍知诗有味,复恐道相妨。”[3](卷七)对自己境况做了实录,诗歌的末尾表明,诗歌的钻研与道学的体悟,造成了吕本中精神世界的冲突。说到底,专意“学道”就要放弃诗艺的探索,这对吕本中来说,几乎是难以做到的。
诗与道的冲突,不仅仅发生在吕本中身上,汪革的例子也表明“诗”、“道”之间是相斥关系,《紫微诗话》有如下记载:
汪信民革,尝作诗寄谢无逸,云“问讯江南谢康乐,溪堂春木想扶疏。高谈何日看挥麈,安步从来可当车。但得丹霞访庞老,何须狗监荐相如。新年更砺于陵节,妻子同锄五亩蔬。”饶德操节见此诗,谓信民曰:“公诗日进,而道日远矣。”盖用功在彼而不在此也。[5]
汪革卒于大观四年(1110年),谢逸卒于政和二年(1112年),饶节卒于建炎三年(1129年),《紫微诗话》该条所记必在大观四年之前,“公诗日进,而道日远”仍为饶节语,与上引劝勉吕本中“专意学道”之语,实有相同之意:指出吕本中、汪革用功在诗而不在“道”。上引吕本中“稍知诗有味,复恐道相妨”的心理纠结,亦源于此。不过,这仅是问题的一面而已。该材料进一步印证了吕本中的交友圈内,存在习禅学、重“道”本的倾向。
吕本中的诗歌记录了他与禅学的动态关系,已如上文所论。政和以后,“道”与“诗”成为吕本中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不仅吕氏本人这样说,其友人也这么认为。谢薖在《读吕居仁诗》这样评价道:“居仁相家子,敛退若寒士。学道期日损,哦诗亦能事。自言得活法,尚恐宣城未。”[6](卷一)谢薖卒于政和六年(1116年),故他对吕本中的评价必在此之前。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在北宋大观、政和时期,吕本中开始“学道”,步入禅学领地。吕本中始终保持着诗人本色,在参禅悟道中,为诗学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二
吕本中在大观、政和年间“学道”并不专意,除了难以割舍诗歌外,他对于儒学的新形态——“理学”也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他曾有这样的自白:“儒生活计亦不恶,蒲团坚坐到日落。”(《久雨路绝,宾客稀少,闻后土祠琼花盛开,亦未果一往也》,《东莱先生诗集》卷六)“蒲团坚坐”乃禅学静修工夫,而“儒生活计”中显然指儒学工夫。从吕本中的自述来看,他参禅而不忘儒。
在引入儒学之后,有必要对吕本中诗歌中的“道”加以分辨。本文前一部分所论的“学道”之“道”,大体上是在禅学范围之内。而在吕本中的诗歌中,“道”还有另外一层涵义,那就是儒家圣学,在吕本中的时代,宋代理学已经具有了“传圣人之道的学问”的意义[7](p.7)。《京师赠大有叔》:“闭门不识故人面,豪气直欲轻元龙。平生为道不为食,少小所期皆目击。”[3](卷四)根据全诗之意,当作于政和元年(1111年)客居京师时,“道”与“食”对举,为考查“道”之本义提供了线索。《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子思问耻,孔子曰:‘国有道,谷。国无道,谷,耻也。”由此可知,“道”指实现政治主张从而达到治世局面。在《寄晁以道》中,他也说:“吾祖早闻道,晚与夫子熟。相期千载外,未得一世伏。”[3](卷九)“吾祖”指吕希哲,曾从程颐问学;晁说之字以道,司马光弟子。大观年间,吕希哲、晁说之二人交往密切,据《师友杂记》记载,晁说之赴明州船场任,路经真州,与吕希哲晤谈数日。根据吕希哲之行实及全诗之立意,可知其祖所闻之“道”,乃指孔门千载所传之圣学。由以上二例,可初步断定吕本中诗歌中另一涵义的“道”,乃孔、孟以来政治主张、义理等儒家学说的高度凝结,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具有本体意义的儒学范畴。除了诗歌这些本证外,吕本中在政和年间向理学家杨时问学,更进一步证实吕本中确实在向理学靠拢。他的这一行为将诗学引向新的天地。
理学本是吕氏家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本中之祖吕希哲曾从程颐学,而程门弟子如谢良佐、杨时“亦皆以师礼事荥阳公(指吕希哲)”[1]。在随侍吕希哲期间,吕本中有机会接触一时贤达之士,程门弟子亦在其中。吕氏家族的开放性及社会地位,为吕本中的师友渊源提供了广泛的人脉资源和高起点的交流平台,如吕本中生平交谊中颇为重要的三个人:谢逸(无逸)、汪革(信民)、饶节(德操),就是因吕希哲的感召力而与吕本中成为忘年交的;这种开放性还促成他“不主一门,不私一人,善则从之”[1]的求学态度,因此,他遍游名儒之门,如陈瓘、杨时、游酢、尹焞等,黄宗羲总结说“其不名一师,亦家风也”[8](卷三十六)。
政和年间,吕本中加大了向外求学问道的力度,如向晁说之、杨时问学,希望自己能在理学修养方面更为精深。吕本中向杨时问学的书信,早已佚失,所幸杨时的回信还在。《龟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一存有三封《答吕居仁书》。书信围绕“问学”展开,但篇幅较长,仅根据论述需要予以节录。
《答吕居仁书》(一):“《大学》曰:‘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盖致知乃能明善,不致其知而能明善,未之有也。此不须分为二说……世儒之病,正在以言语文字为学,不可不知也。浅陋妄意如此,高明试一思之如何?”
《答吕居仁书》(三):“承问格物,向答李君书尝道其略矣。六经之微言,天下之至赜存焉。古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岂徒识其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夫学者必以孔孟为师,学而不求诸孔孟之言,则末矣。《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徳。《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世之学者欲以雕绘组织为工,夸多斗靡,以资见闻而已。故摭其华不茹其实,未尝畜徳而反约也,彼亦焉用学为哉!某老矣,虽有志焉,而力不逮,区区有望于左右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9](卷二十一)
问学类书信,一般来讲,有问必有答,所以,从杨时的回信中约略可以推知吕本中的疑问。吕本中于政和年间向杨时问学,此事实与吕本中的诗歌写作有密切关系。从第一、三封信的内容来看,主题当是探讨格物致知的圣学工夫,可以看出吕本中对理学已有初步之了解,杨时又有针对性地加以点拨。由此也可以响应本节开始时的疑问,吕本中所说的儒生工夫,当是格物、明善的道学内修工夫。上引《答吕居仁书》一、三中,杨时反复提到“世儒”、“世之学者”的弊病,要矫其弊,须以孔孟为师,深赜先儒之言,“志于道,依于仁”。杨时书信中,“以言语文字为学”、“以雕绘组织为工”当为提耳棒喝之语,说这些话时,杨时必有深意。吕本中作为诗坛新秀的声望,杨时必有耳闻,故第一封书信的结尾,既可以看做劝勉,也可以看做是委婉的批评。
来自杨时书信的劝诫,无疑为上节所论诗、道冲突(即“稍知诗有味,复恐道相妨”,见《试院中作二首》之一)查找到另一原因。与上节所论饶节、关沼等人劝勉“学道”不同,杨时的劝诫,则属于道学家对于文学态度的顺延。早在程颐那里已有“作文害道”之论[10](p.239),程颐另一位高弟尹焞在南宋绍兴年间经筵讲读时,还坚持类似的见解:“黄鲁直如此做诗,不知要何用”[1]。来自禅学、道学两个方面的意见,竟如此一致:都希望他不要专事文字、要务本。对吕本中而言,两方面的劝诫,对其精神世界构成巨大的冲击。
当精神世界的冲突无法解决时,吕本中于政和六年(1116年)向杨时写了第二封信,所以,杨时《答吕居仁书》(二)中,开头就说:“辱问所疑,皆非浅陋所知也。”书信的结尾仍落在“诗”上,“夫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特发于言者,故于动天地、感鬼神,言近而已”;中间部分,杨时花了很大笔墨谈如何悟道,“夫守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敬足以直内而已,发之于外,则未能时措之宜也,故必有义以方外。毋我者,不任我也,若舜舍己从人之类是也。四者各有所施,故兼言之也。道固与我为一也,非至于从心所欲不踰矩者,不足以与此。言志于道,依于仁,固无害”[9](卷二十一)。
在杨时的回信中,“道固与我为一”,乃全篇之要旨。吕本中“诗”、“道”相妨的困惑,归根结底就是“我”与“道”的冲突,即诗歌要表达个体之情志,同时还有诗法技艺等要求,势必妨碍格物悟道的工夫。最值得玩味者,杨时在这封回信中,一改《答吕居仁书》一、三中对“以言语文字为学”、“以雕绘组织为工”进行批驳之态度,而从儒家言志的立场对“诗”进行了阐释,极大地肯定了“诗”之价值。杨时说得很明白,只要在“敬”、“义”内外两个方面加强修养,“志于道,依于仁”,作诗亦无害。相比程颐“作文害道”之论,实在是惊人的进步。杨时所说的“道固与我为一”之论,不仅有效地消除吕本中的内心困惑,还为他平衡“诗”、“道”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心理安慰。
作诗不妨道,悟道不废诗,保持诗、道之平衡,吕本中真的做到了。例如,他在《试院中呈工曹惠子泽教授张彦实》中说道:“忍穷有味知诗进,处事无心觉累轻。”[3](卷七) 固穷守道,保持平和之心,也能真切地感受到诗歌的生命力。
三
经历了诗、道冲突后,吕本中有选择地向理学靠拢,影响了他对文学价值的判断,最为突出者乃“余事及文章”。与“余事”相对应的圣学工夫,则处于“本”的位置。从研习道学、习文的时间分配上,要以前者为主;从道、文的价值来讲,仍然以前者为重。
在《叔度、季明学问甚勤,而求于余甚重,其将必有所成也,因作两诗寄之》其二,吕本中作诗曰:“念我少年日,结交皆老苍。曹南见颜石,甬上拜饶汪(原注:颜平仲、石子植、汪信民、饶徳操)。敢幸江海浸,得沾藜藿肠。诸郎但勉力,余事及文章。”[3](卷九)该诗当作于宣和元年(1119年)至宣和六年(1124年)间[4]( p.370)。吕本中这首诗是要度金针于后学的,通过亲身经验勉励他们转益多师、以修身砺学为本。在政和三年(1113年)帖中,他还专门讲学者的文字特点:“学者须做有用文字,不可尽力虚言。有用文字,议论文字也。”[2]( p.12)又,《徐师川挽诗三首》其二:“异日逢明主,端居不复藏。一心扶正道,极力拯颓纲。已病犹轩豁,临衰更激昻。始知操韫处,余事及文章。”[3](卷九)吕本中对于徐俯生平功业的评论,着力彰显的是“扶正道”、“拯颓纲”,而文章乃其余业而已。绍兴十一年(1141年),吕本中已经58岁,本年七月徐俯卒于饶州,在间隔二十余年之后,吕本中再度援引“余事及文章”,可见它已成为吕本中重要的文学观念。
“余事及文章”,不仅仅是吕本中的夫子自道,早在徽宗宣和年间王及之评价吕本中时就用了类似的语言,引次如下:“闻居仁名,十五年矣。比者获见,乃大过所闻。文章议论,超绝一时,在公为余事耳。”[1]吕本中积极投入昌明道学的工作中,并勉励同侪尤其是年轻一代为之奋斗。这种例子很多,绍兴五年(1135年),吕本中弟子林之奇赴行在,吕本中作诗送行,云:“子之于为学,其志盖未已。上欲穷经书,下考百代史。发而为文词,一一当俊伟……穷通决有命,所愿求诸己。圣贤有明训,不在于青紫。丈夫出事君,邪正从此始。”[3](卷九)激励林之奇不以穷困通达为念,而要在穷通经史、求诸己方面下工夫。吕本中不仅自己勉励年轻一代以圣学为职任,还把一些人推荐给当时理学核心人物,如将王时敏推荐给尹焞[11](p.18),将周宪介绍给王蘋[8](卷二十九)。从上面的诗文本证及其他例证可以看出,吕本中对理学寄予了足够的热望,投入了极大的精力。
吕本中研习道学,无疑为诗学创作提供更为坚固的根基。两宋之际诗坛的主体人物,直接或间接经历过党争之害,精神气度因外在压力变得局促,作品题材过于狭窄,蹈袭黄庭坚的字法、句法等形式,无论是创作主体的气象,还是学养,都呈现出一种颓势。为了力挽这种颓势,必须提高诗学创作主体的心性修养,加固诗学根基。理学在心性修养和格物致知两方面都有可资借鉴之处,吕本中取理学之所长,为诗学所用。吕本中向理学靠拢,而不废弃诗文,形成以理学为本位的文章观念,在两宋之际至南宋诗学史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它要求诗人注重学问的积淀与心性的涵养,无疑为诗学培植了深厚的根基。
“余事及文章”既是吕本中政和之后奉行的原则,也是他劝勉后学的主题精神。汪应辰是吕本中晚年弟子,在《挽吕舍人二首》中追忆中本中平昔教诲时说道:“相期深造道,不为细论文。”[12](卷二十四)虽说是以道学为本位,但吕本中从没有放弃过“文”,他的道学修养为“文”带来新鲜血液。与吕本中同时代的张九成,识破了吕本中的诗法三昧:“词源断是诗书力,句法端从践履来”[13](卷四),指出吕本中吸取理学践履工夫,恰恰是为诗歌寻找源动力的。
在禅学、理学两种思想体系的刺激之下,吕本中的诗学观念呈现出即此即彼、相互融通的特征。他为了达到胸次圆成、波澜自阔的目的,不仅转借理学涵养、格物论,还借助了禅学静修工夫,他的诗学实际上是融通两家之后的理论形态。所以,在看待其诗学与理学(或禅学)的关系时尤须谨慎。北宋大观、政和年间,是吕本中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无论是文学、禅学,还是理学,都有很深的体悟。在经历诗、道的冲突后,吕本中形成以理学为本、兼顾诗学、不废禅学的思想,这在他的诗歌中可以得到印证。
政和四年(1114年)吕本中作《别后寄舍弟三十韵》,诗歌绝大篇幅探讨诗歌写作问题,不妨视作吕本中诗学心得的一次集中总结:“笔头传活法,胸次即圆成。孔剑犹霄炼,隋珠有夜明。英华仰前辈,廊庙到诸卿。敢计千金重,尝叨一字荣。因观剑器舞,复悟担夫争。物固藏妙理,世谁能独亨。乾坤在苍莽,日月付峥嵘。凛凛曹刘上,容容沈谢并。直须用款款,未可笑平平。有弟能知我,他年肯过兄。初非强点灼,略不费讥评。短句《箜篌引》,长歌《偪侧行》。力探加润泽,汲取更经营。径就波澜阔,勿求盆盎清。吾衰足欿坎,汝大不欹倾。莫以东南路,而无伊洛声。”[3](卷六)诗歌大体上涉及了胸次圆成、参悟前辈、观物得理等具体环节。“因观剑器舞,复悟担夫争”,以张旭悟草书之笔法、神意,承前句“炼字”而启下四句之“悟理”,宇宙万物、日月星辰皆有妙理。“凛凛曹刘上”至“长歌《偪侧行》”十句,指应当遍参汉、魏至唐各体文学,虚心地琢磨。“力探加润泽,极取更经营”转入新的议题,即追求“波澜自阔”的境界,须加强心性涵养。“盆盎”句意谓自己要做好内修工夫,高蹈俗世之外。结语“莫以东南路,而无伊洛声”,乃吕本中援引伊洛之学入诗的明确宣示。
经过十余年的理学积淀,吕本中成为文学、理学兼擅的元祐子弟,出入于文学、理学之间,在两宋之际的学术、文学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不独吕本中如此,两宋之际的另一位重要诗人曾几,也自觉地加强理学的研习,并向理学家请教,胡安国《答赣川曾几书》保存了原始的信息。在信中,胡安国对曾几以圣门事业相劝勉,说道:“穷理尽性,乃圣门事业。”紧接着,胡安国度以金针,讲述如何格物循理,“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贯之,知之至也。无所不在者,理也;无所不有者,心也。物物致察,宛转归己,则心与理不昧。故知循理者,士也。物物皆备,反身而诚,则心与理不违。故乐循理者,君子也。天理合德,四时合序,则心与理一,无事乎循矣。故一以贯之,圣人也。”[14](p.556)曾几研习理学的事例,说明诗人向理学靠拢,绝不是一个单独的个案。本文意在呈现一个生动的历史细节;通过这一细节,来透析宋代诗歌史与思想史的互动关系。此外,诗坛深受理学的浸润,实为宋代诗学史之大事,揭示其意义亦为本文命意之所在。
[参 考 文 献]
[1]吕本中.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2]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M].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5.
[4]王兆鹏.吕本中年谱[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5]吕本中.紫微诗话[M].何文焕.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
[6]谢薖.谢幼槃文集[M] .宋集珍本丛刊,第3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7]陈来.宋明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黄宗羲,等.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杨时.龟山先生全集[M] .宋集珍本丛刊.第29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10]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韩淲.涧泉日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2]汪应辰.文定集[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张九成.横浦先生文集[M] .中华再造善本,第195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14]胡寅.斐然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作者系郑州大学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