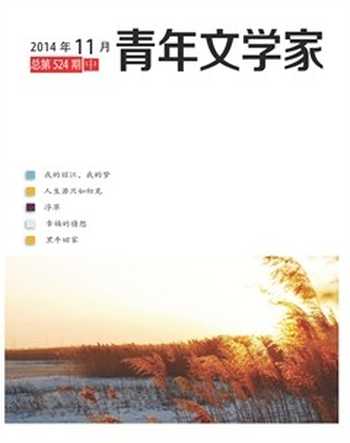福斯特小说中女性知识分子在文化联结中的努力与困境
摘 要: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1970)是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之一,其小说的特点之一就是将旅行中的英国知识分子置身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不同文化间的联结是他作品的主题之一,其中女性知识分子在文化联结中的作用和处境又是他关注的重心。小说《霍华德庄园》和《印度之行》中女性知识分子在文化联结陷入两难处境:努力探索却面临困境。
关键词:福斯特;女性知识分子;文化联结;困境
作者简介:何双(1979-),女,江西分宜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工作单位: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2-0-03
福斯特是爱德华时代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主要发表于爱德华时代,并对这个时代进行了观察与思考。工业文明的冲击使得“爱德华时代”处于动荡之中,知识分子精英对象牙塔外的种种变化不可能无动于衷,诚如福斯特所言:“我不能把自己关在艺术之宫或哲学之塔里,而无视人世间的疯狂与悲惨。”[1]
福斯特以跨文化视角在多部作品中探讨了文化联结主题。这种联结愿望的达成常常又是以“婚姻”为载体的,正如文学评论家安妮·赖特明确指出,福斯特小说中的婚姻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一种尺度。在这“联结”愿望的实现过程中女性知识分子有着非凡的地位和作用。他在作品中主要描述了女性在婚姻中的选择与取舍,呈现了她们在文化联结中努力探索和困难处境。
一
在《霍华兹别墅》中福斯特呈现了现代文明的尴尬处境:物质创造与精神生产的矛盾,工商业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冲突。
姐姐玛格丽特是达成文化联结愿望的使者。小说通过玛格丽特和威尔科克斯的结合来体现这种联结的实现,他们一个代表文化人,一个代表实业人。玛格丽特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人的优越生活条件来自实业人的艰辛劳作,是实业人的物质创造奠定了文化人精神享受的基础,文化人对此应该予以正视,而非对实业人嗤之以鼻。
在与亨利的交往中,玛格丽特认识到物质与精神、金钱与文化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决心把二者结合起来,试图借助婚姻来企图来弥补亨利身上的弱点:虽有“健全的头脑”但道德上并非如此,而是肤浅、狭隘、缺乏想象力和同情心。他需要同情心和理解力,需要拥有精神层面来实现心灵的完整和人格的完善;同时玛格丽特认为这也能给自己的生活输入一些新鲜的空气,那就是实业人士的能干精明!
显然差别存在于玛格丽特和亨利之间,鸿沟也存在于文化世界与失业世界间,而且妹妹海伦极力反对反对姐姐和亨利的结合,可是玛格丽特终于跨出了“沟通”或“联结”至关重要的、直面现实的第一步。
联结的道路是艰难的。不仅玛格丽特与亨利的婚姻遭到极大的反对,而且婚后两人之间也并非没有抵牾,亨利与玛格丽特分属不同的世界:生意人与文化人。自信又充满活力的亨利虽然有着很多文化人所没有的优点,但始终不能够进入到玛格丽特的精神世界中。玛格丽特非常积极地投入到双方的沟通中,为了能够更接近亨利,精神世界远远丰富于亨利的玛格丽特为了和丈夫取得一致的观点,她常常隐藏真正的看法和压抑自己的本性。即便如此,玛格丽特努力追求的和谐并没有收到相对的回应,亨利对他人的冷漠和自私自利也没有因为玛格丽特对他的宽恕和温良而有所改善,连怀有身孕的海伦在庄园过夜他都不允许,玛格丽特的努力最终也只是徒劳,彼此的分歧既来自不同理想和价值观的矛盾,也来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传统与现实。
《圣经》种下了西方社会男权中心的种子,认为女人是隶属男人的,不仅体力不如男人,智力也要低于男人,她们的角色只是妻子和母亲。男尊女卑是颠簸不破的“真理”,而且这种看法渗透了人们认识的意识深处。阿尔弗雷德·特尼森(Alfred Lord Tennyson)在其诗作《公主》中说:“男人耕作,女人炊煮;男人持剑,女人拿针;男人有脑,女人有心;男人发令,女人服从。”[2]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治生活中虽然女王高居王位,但她作为女性发出的声音却十分微弱,因为活跃在政治舞台的都是男性。在家庭生活中,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从属于丈夫,妻子唯丈夫之命是从。即便是经历了从19实际下半叶开始的争取女性地位和权力的妇女运动,女性的地位和命运很大程度上有了改变,但是传统的男權家长制社会却动用一切手段来强化男性的地位,处处压制女性,为此男子尽力剥夺女子的思维,要她们以为妇女应该是没有个性、没有自我的,更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而要达到和男性思想的交流沟通则是奢谈。
玛格丽特作为一位知识女性,她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信念,甚至精神境界要高于亨利,然而作为妻子的她按男权社会的要求是要绝对的从意识和灵魂层面完全服从丈夫,而不只是在形式上取得一致。试问作为妻子的玛格丽特怎么能希冀通过“婚姻”来联结自己和丈夫之间的世界?即便不存在文化与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她也会遭到来自亨利所代表的男权文化的抵制。
玛格丽特和海伦最终冰释前嫌和好如初,她们重新审视了所发生的一切,最后善良的玛格丽特决定继续维持她和亨利的婚姻。有人认为福斯特所希望的“联结”只是一种形式的慰藉却没有实质意义,也缺乏说服力。
在形式上终于保住了但在实质上显然不能让人信服。然而笔者认为玛格丽特的妥协并不意味着是对文化艺术传统的背叛,也非女性对男性的屈从,而是作为女性知识分子以其责任意识架起实业文化与人文文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联结中付出的艰辛努力和面临的艰难。
二
《印度之行》将人物置于更广泛的国际政治背景,展示的是英国宗主国文化与印度殖民地文化间的冲突,作品以印度为背景,在这个宗教、种族、语言、文化复杂多元的国家展现了两位英国女性为东西方文化的“联结”、人与人真诚的“沟通”所做的努力与遭遇的困难。
殖民文化和印度文化间的冲突,作品以印度这个地域广阔,宗教、种族、语言、文化多元化的国家为背景,表现了两位英国女性试图跨越东西方之间文化的鸿沟,为实现人与人之间真诚的“联结”和文化的“联结”而做的努力。
出身英国中产阶级的阿黛受过正统的英国教育,具有人文主义意识,长得不漂亮,不够有魅力,而且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思考精神,严肃对待人生,并不把婚姻当成一种生活的手段,为此,从男权社会的标准来看,她并不符合英国淑女的标准,甚至可以说是男权社会的异类。
阿黛拉来印度是为了和未婚夫朗尼结婚,她和朗尼在英国已经订了婚,彼此相处也很不错。小说中作家将他们的关系放在印度,一个更为多元化、更为复杂的跨文化背景中,他们的关系会如何?阿黛拉将会如何面对异质的印度呢?
从小说的叙述中我们发现,福斯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社会中女性低下的地位的社会现实。在英属印度,英国殖民者尤其是男性他们根本无视印度女性的存在,她们只是作为母亲和妻子存在于家庭中,在社会政治场合中,她们的存在毫无意义。虽然从种族角度而言,英国女性享有印度女性不可能拥有的特权,英国女性所面临的处境比印度女性也好不了多少。
在马拉巴洞穴事件中,阿黛拉是受害者,但大家却把同情的目光投给朗尼,当他走进俱乐部时,所有俱乐部成员除菲尔丁之外居然都起立表示对他的理解和遗憾之情。作品这样写道:
Miss Quested was only a victim, but young Heaslop was a martyr, he was the recipient of all the evil intended against them by the country they had tried to serve. [3] (P192)
细心的读者显然清楚作者运用一种反讽语气对俱乐部成员的心理进行描述。这句话中运用非常关键的两个词“only”和“martyr”准确地指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only”一词绝妙地淡化了阿黛拉作为事件受害者应得的理解和支持,并将其痛苦也忽视了。而“martyr”(受难者)一词将最大受害者给了阿黛拉的未婚夫朗尼。可见,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私有财产而存在,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当女性受到伤害,人们只是觉得男性的财产受到了侵犯,而并不关注女性作为人被伤害,无视她们的感情、权力、身心被侵犯的感觉。
在英属殖民地印度,女性也常常被认为是只需服从命令为英国殖民者统治服务的工具。当阿黛拉在法庭上于众目睽睽之下撤回了对阿齐兹的起诉后,作者这样写道:
The Superintendent gazes at his witness as if she was a broken machine. [3] (P232)
我们看到在英国殖民者起诉阿齐兹的案件中,案件的重要“证人”阿黛拉被看做是“a broken machine”只是一台“机器”,毫无自己意志和思想,只要按照英国殖民者既定计划,听从他们的意志和命令运行,就能达到他们以控告和惩罚印度人来加强他们的统治地位和优越感的目的。
当马拉巴事件之后,作为殖民地的最高官员,特顿先生宣称他要保护他们的女性,他这么做也只是为了显示其所谓的男子气概,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却是:……“After all, its our women who make everything more difficult out here” was his inmost thought. [3] (P217)
特顿作为英国男性,他的绅士教养让他去保护女性,但在这个保护女性的绅士风度之下却是他内心里对她们的怨恨。他恨女性的原因是因为她们并不情愿成为男性保护的对象,在他看来,阿黛拉就是这样一个不愿生活在男性设定的圈子里而按自己意愿说话做事的女性。他甚至认为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糟糕的关系以及印度混乱的状况阿黛拉是始作俑者,必须负责。
可见,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异质文化中,阿黛拉要去熟悉并了解印度这片陌生的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东方文化,并试图打通相异文化的融通,她所面临的困难远远比玛格丽特要大得多。面对英国夫人们对本地人的冷漠和歧视,善良的阿黛拉感到焦虑:“我听说,一年之后我们都会变得粗暴起来。”她拒绝其同胞对她进行殖民意识同化:“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绝不应该变成这样一种人。”“我要与我的环境对抗,去避免成为她们一类的人。”[4] (P165)当然,阿黛拉毕竟生活在英国殖民者之中,多少受本国人对印度人偏见和不信任思想的影响,因此她并没有完全做好接收异质文化的心理准备,这也就成了她产生错觉的心理因素。因此在游览马拉巴山洞时,她对阿齐兹产生了误解,并状告阿齐兹侵犯了她,导致了后果严重的“马拉巴山洞事件”。但阿黛拉凭着自己的良知和勇敢在真相正义和谎言欺诈之间做了选择,撤销了对阿齐兹的起诉,哪怕是担着被当作叛国者的危险。最终也取消了与朗尼的婚约。朗尼以印度执政官的身份来到印度之后,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自以为是和专横无理,嫣然以大英帝国的忠诚卫士身份带着种族偏见对待印度人。阿黛拉则愿意和印度人友好相处,真诚相待。文化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是两人通向婚姻之路失败的重要原因。
马拉巴山洞事件是阿黛拉小姐的一次自我探索和自我成长,事件发生后她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她不再对婚姻抱有幻想,更不想因为婚姻使自己的自我附属于男性的自我。徘徊在民主自由思想和殖民主义思想之間的她,最后撤销了对阿齐兹的指控,避免了成为英印殖民者的帮凶,没有成为英印文化交流的障碍。
阿黛拉解除了与罗尼的婚姻,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既没有沦为男性的附属,也没有成为英印殖民者的帮凶。尽管在之后的日子里,她不是足够坚强,但她敢于坦诚女性的不足和脆弱,直面压力和误解,按自己的思想奔向与过去不同的生活,她再也不是作为男性的附属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她自己而存在。作为一个男性作家,福斯特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男性拯救女性的模式,女性自己能够拯救自己。
至此我们发现一个问题:阿黛拉借助婚姻力量联结不同文化的努力最终放弃的行为似乎与采取“联姻之路”为求文化联结这一目的相背离,其实不然,“联姻之路”的取而又弃一方面反映了作家在不放弃联结努力的同时对采取何种方式所产生的困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阿黛拉较之露茜和玛格丽特的成熟和进步,反映了作家更深沉的思考。福斯特并不因为自己是男性作家就避讳呈现女性的自我斗争,他并不害怕这样会改变自己的自我意识。
福斯特常常将其作品中女性置于不同文化语境之中,描写她们在为不同文化架起联结桥梁途中的积极探索和努力追求,并试图以“婚姻”为载体达成联结愿望。评论界对福斯特以“婚姻”为媒介的文化联结观看法不一,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肯定,或否定,或支持,或反对,我们对其联结观并没有定论。难能可贵的是福斯特面对争议,面对困惑,他没有知难而退。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福斯特努力的探寻着不同文化的“联结之路”,并对女性知识分子在这联结之路中的努力给予充分肯定,对其在联结之途中的困境倾注莫大关注,给我们以无限的思考和警醒。
参考文献:
[1]英国文学指南[M].鹈鹕书社.1978.
[2]陆伟芳.对19世纪英国妇女运动的理论考察妇女[J].研究论丛.2003(2).
[3] Forster,E·M.A passage to India[M].London:Penguin.1984.
[4](英)E·M·福斯特.杨自俭 译.印度之行[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