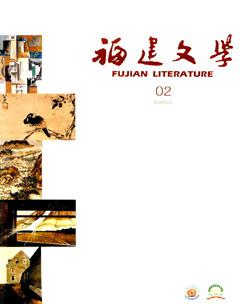西夏,青花已瘦(外二篇)
刘梅花
西夏的颜色,总是素淡,瘦峭,从不鲜艳。
最多的是青灰。青色,是醇浓的那种,一点也不黯淡。灰呢,灰得干净,不拖沓,不迷茫。还有土黄,也是清冽的。褐色呢,简练,素雅。奇怪啊,这些颜色掺在一起,弥漫起淡淡的风雅来,像是诗经里的意境,跟胡风的党项人没有关系一样。
可是,这样朴素的色泽,就是西夏的颜色,仔细嗅,好像有淡淡的清香,从西夏的时空里袅绕而来,盘桓在壁画、塑像,残破的瓷器里。这些古董,一定储存着西夏的气息、党项人的味道,挥之不去。
党项人,好像不喜欢艳丽的颜色。无论塑像还是壁画,都是清瘦的颜色,青,灰,褐,白,土黄,墨色,暗绿。蔓延着清婉的气息,却暗含着华丽,也不沧凉。明亮光鲜的色系,大红大绿绚黄,都没有。偶尔,一绺儿青紫,也是素淡的,不酽。
青砖,白墙,一点点灰瓦的屋脊,屋檐上枯黄的草。菩萨手携莲花,目光安详。衣裳也是青灰的,莲花是青灰的,莲叶是暗绿的。真是清雅得好看啊。
西夏,在凉州的光阴里,素素地优雅。用浓的淡的青,点染出世俗光阴里橘黄的温暖。
你看,西夏酿酒图。
画面是大片墨色的底子,却不压抑,反而有一种沧桑质朴的厚实。一张青色的低案,青得有些铺张。这青色,也青得透彻凛冽,让人看一眼心里微微一颤。案角,一卷木简,未打开,卷得好好的,斜斜丢在那里。低案地下,肯定有一只慵懒的猫儿,咕噜咕噜一边念经一边做梦。
酿酒的大火炉却是土黄的。清冽酣畅的土黄,火焰一样在一片墨色的底子里张扬地跳跃。酿酒的,是两个女子,都半跪着。添柴的女子,纯白的衣裙,清绿的裙角儿散落在地上。云鬓高耸,眼神是柔软的。她脚边是一只剔刻釉扁壶,想必是盛满了美酒吧。
日常穿着打扮,胡人最喜欢白色。
火炉另一侧,是黑衣衫的女子,也是半跪着,面色白皙,侧目看着地上的酒碗。黑色的深衣镶了纯白的边,露出一抹淡黄的胸衣。她的神情,真是让我惊讶,多么的柔暖啊。女人的味道,就在那侧目的一瞥里花儿一样芬芳。
她看着的那只酒碗,是青花瓷上雕了折枝牡丹的吧?
两个酿酒的西夏女子,她们在火炉前说了什么呀?是拿胡话在低低地说着吧?那胡话,想必也是掺杂了汉话的吧?凉州的胡人汉人,总是操着一种含混的语言。
明眸,红唇,微醺,裙裾飘逸。女人轻柔的韵味,扑面而来。有点丰腴,却还是柔弱,真是美啊,美得令人绝望。隔着千年的时光,仍然忍不住嫉妒。
西夏的女子,你美就美吧,美得这样柔软干嘛呢。软软的神态,微微撒娇地嗲。不要说那黄沙茫茫里一路风尘赶来的男人们看了心疼,连我,千年后的一个小女子,看了都心里轻轻颤动。
火炉上空,是袅袅的水气,凝成一团,悬浮在屋子里。大约,这是个冬天的夜里吧。院子里下着雪,而屋子里,却火炉红红的,酒味儿一定在屋子里弥漫了又弥漫。
再粗犷彪悍的西夏男人,再铁石心肠的男人,看到这样的女子,心里怕是都要温软得化成一汪清水吧?家的念想,就是这样枝枝蔓蔓疯长起来的吧?
谁人夜色踏雪来
那张低案,还空着。白釉剔花的酒壶,却温好了酒。水波纹的酒碗,也等着一枚红唇的亲临。
西夏的瓷器,总是有一种疏朗之美。一点点瘦峭,不肥硕,不俏丽。但暗暗的,却又一种张扬的气场。运头纹、九点纹,缠枝莲,折枝牡丹,精心剔出来。瓮也好,罐也好,钵也罢,都那样朴实可爱。
胡人好酒。一日三餐之外,酒是必不可少的。甩着腮帮子啃完了羊腿,呼噜呼噜喝了葱花羊肉汤,然后,温一壶凉州美酒来消食。这是西夏贵族的日子吧?穷人,喝一盏稀粥果腹,哪里能奢望美酒呢。褐釉的粗瓷大碗,粥里摇晃着光阴的影子,那么苍凉,薄寒。
门外的雪,下得真是大啊。边塞凉州,雪花大如席子,漫天翻卷,飘落。大雪下得铺天盖地的时候,酒的味道就弥漫起来了。
万籁俱静。没有一声犬吠,也没有一声马嘶。夜,真是干净啊。只有十万大雪乘风而来。
少顷,脚步声簌簌的,走夜路的人回来了。马蹄声也是簌簌的,不响亮。大雪稀释了声音。风雪夜归人,是怎样的诗意呢?
隔了千年的时空,我只能想到诗意,不能体味到他的寒冷。
一盏昏黄的灯光,投过雪地上,夜色里多了一抹轻柔。拴马,抖去衣袍上眉毛上的大雪,跺跺脚。推开木头的门,吱呀,声音也是暗哑的,不脆。
扑面的温暖呀!屋子里,酿酒的火炉正红艳艳的,火苗莲花一样盛开。青铜的灯盏,灯花些微瘦,但仍然是明亮的。木简尚未打开,猫儿尚未醒来,酒碗尚未填满。
温热的酒,清洌洌的,冒着一丝儿若有若无的白气,注满了酒碗。碗沿的青花,也透亮起来。女子慵懒娇媚的目光,落在酒碗里,落在低案上。喝呀!话还未说,心里先醉了。
他盘腿坐下来,拾起一根柴,添进火炉里。火光落在面庞上,有点浮,像佛像上的镀金,不甚真切。看一眼身边的女子,那目光里,必定是满满的眷恋与爱怜吧?
门外的大雪,覆盖了凉州的大野。边塞之地,白雪皑皑。他是从野外归来的吗?一路跋涉,战马嘶鸣在冻僵的土地上。凉州有好马啊!心里暗自感叹一声。
大野空旷,牛皮帐篷里升腾起千盏灯火,像一朵一朵暖和的橘红的灯盏花儿,开在皑皑大雪里。西夏的兵士,都被大雪压弯了腰,伏地叩拜菩萨。他们掖紧身上的皮袍子,青铜灯盏里添一点清油,哀伤地说,让我们温一壶酒,来抵御这彻骨的寒凉吧!
酒味一飘,这个想家的人就再也无法抗拒回家的念头了。就如同号角一起,必须要冲向战场一样。
烈马啊,天亮之前,我们一定要返回到帐篷里来。他心里默默祈祷了一下。思念一个人,真是无法抑制的事情,想得心里疼呢。想得让人任性妄为,不顾一切。酒,不过是想念的药引子而已。
戎装策马的人,裹紧皮袍,像一枚落叶,卷进一场大雪里。不用扬鞭,烈马亦是想家的。凉州的宝马啊,马鬃在风雪夜里猎猎飞扬。他在心里默默唱:紫花马儿出营来,四蹄生风……
风雪夜归人。他是驮着一身眷恋回来的,你想想看,何等的柔情温婉呢!
酿酒图上还没有他,因为正在归来的途中呀!
等等吧。思念着的心,距离不会很远,一想,就到了。
塞外有美人,亦有大雪
塞外有美人,美得天姿国色。不是我,是昭君呢!我只能想象一下昭君的裘衣,狐狸毛皮做的,多么隆重而摇曳地好看。
古凉州,北凉王沮渠蒙逊的女儿,西域的美人,更有风情,楼兰美人的那种,真是美啊!可惜,胡人懒散,没有文字流传下来,是我自个儿想的。
还有呢,河西鲜卑人南凉王秃发乌孤的妃子,叫乌啼禅,也是美得睡莲一样,不忍多看。多看一眼,心里一惊,就会涌起怜惜万分来。这个美人嘛,你自然是不知道的,只有我清楚,是我的小说里编出来的。
大雪下呀下呀,我在塞外之地的一个小山村里,坐在茫茫大雪里编故事。编得都是美人,穿了裘衣,对镜贴了黄花,点了朱唇。写累了,听雪。
可是,听不到雪落下来的簌簌声。掀开门帘,满眼都是洁白。
院子里,路上,房顶上,都是雪。
一点一点偷偷地落下来,一朵一朵踩着大地的气息落下来。
突然就想起来,儿时念书,有孩子看着窗外感叹:啊,鸡毛大雪漫天飘。那哄堂大笑,好像还是昨天,人却一下子老了,沧桑了。
喜欢两个节气:小雪,大雪。读来,也是美得心颤。好像很多很多的雪,就藏在这两个节气里。时令一到,苍天一声令下,走你!十万浩浩大雪就熙熙嚷嚷赶往人间。
大雪就这么没心没肺下啊,下啊,落在屋顶上,树梢上,越下,越静。天地之间,就剩下雪,剩下纯洁的白。小小的山村,顶着一头雪打盹。
一条黄狗驮着一身雪,从柴扉的缝隙里挤进来。柴扉暗哑地响了一声,接着沉默了。门楣上,还贴着去年的春联横批:紫气东来。
木头栅栏的院墙,歪歪扭扭在雪地里搂紧几间土屋。土屋顶上,早已经被大雪攻占。万物静谧,都戴了白雪的棉帽子。幸好,雪不是绿色的。
可是又想,下一场绿色的雪怎么样呢?不要老苍的绿,不要傲孤的绿,只要浅浅的,淡淡的绿,有些亲和的意蕴。我要披一身菲绿,一走,搅起暗暗的草木清香气儿,多么好……
窗户里透出来一晕昏黄的光,睡眼朦胧的样子。美人的醉眼,大约也是这样的吧?让人看一眼就心神迷离,美得措手不及。
雪,好像下在梦里一样迷幻。繁华,惊艳。暗暗地隆重,暗暗地惊天动地。
屋后的大树,也许是柳,也许是槐,也许是白杨。也许都不是,是另外的一种树。总之,这树枝桠干枯,在夜色里伸展开了,和我的心一样,有些苍凉的姿势。
雪就一点一点小心地垒满枝头。一簇一簇的雪朵儿,装作梨花的样子盛开,怯怯的,不胜风寒。那枝桠,轻微地颤动一下,两下,一粒雪也没有掉下来。也没有风。
一只麻雀泊在屋檐下,饥肠辘辘看着大雪发呆。饿啊。一场大雪藏起了它的食物。
雪尽管下着,心无挂碍。
院子里黄狗走过的爪印儿都被大雪覆盖了。它蜷缩在墙角的窝里,爪子抱紧嘴头。它是怕冷的。
门前也没有人走过的踪迹,只有干净柔美的雪,一层层加厚。
偌大的静谧,被大雪倾情覆盖。山村里,是空灵轻软的水墨意境,是硕硕天地之间清美的大写意。
偶尔有走夜路的一个人踏在乡村的路上,咯吱咯吱的声音也全是柔和的,细弱的。有点醉酒的醇,不冽。
一头闲逛的牦牛磨叽着走几步,又去一棵树上蹭,枝头的雪就簌簌抖落下来。哞——它叫了一声,声音朴素,温和,擦着大雪落在空空山野里。
这雪,下得像一阙宋词,阿娜,柔和,瘦而妖娆。却分明有些慵懒的意思。
乌鞘岭的雪,下得越大,越暖和,并不冷。深山在夜色里孤寂,河水在雪地里枯萎。乌鸦的一声叹息,也凋零了。
一只猫从墙头上跳下来,脑门上顶着一撮雪,蹑手蹑脚进了柴房。它的爪印,是一朵一朵柔软的花瓣,一路开进柴房里去了。它一定是想捡起这串脚印儿,不被老鼠发现。
乌鞘岭,万物静籁,寒梅瘦水。就算晚饭喝着一碗粗粮粥,依然静心挑灯夜读。煮字疗饥,是半辈子修炼来的,就是这样的意境。
没有风的雪,真是好,好得贴心贴意。雪夜闲坐,可以拿这种温软的意境,来针灸内伤。内伤也不是很伤,一点点禅意的雪落就痊愈了。
屋子里,红泥小火炉,一盏老酒,一卷古书,一缕佛音。还有一枚不染尘的女子,素淡,简约,青灯独坐,像老僧。轻轻捻动指尖,书页翻过去一页,“嗤啦”响了一声,声音轻微。
酒盏里冒着一丝热气,弥漫起酒香。少少地抿一口,好了,不要醉了。醉了,就无端伤感起来,就把心里的美人也编得一地落红。最好,不要让她们去飘零。最好,让儒雅的男人一辈子好好呵护着她们。最好,不要让她们为了果腹的粮食而天天惆怅难过,不去为一碗米费心。
心界空旷,大音声稀。只有扑簌簌的雪,蓬松松地饱满。心空了,容得下一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大意境。容得下十万雪花繁华降落。容得下西域美人惊鸿一瞥。
院子里,人间烟尘气息,都藏在一场大雪里,不动声色。心不动,红尘自然不动。如果有一点小小的忧伤困惑,就粘贴一枚雪花,让风邮走。今夜,如果大雪想快递给我什么,就赐给我一份灵感,让我写出最最空灵妙曼的女子,在火炉前轻轻描眉。
塞外有大雪,也有美人呢。
责任编辑 林芝